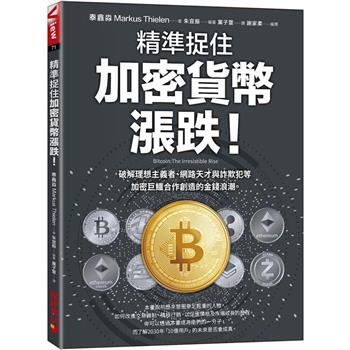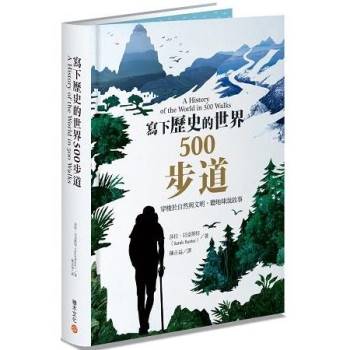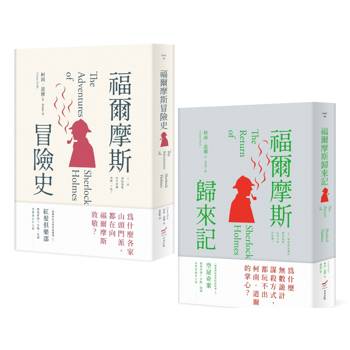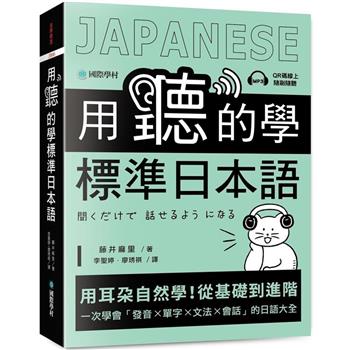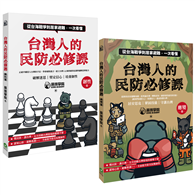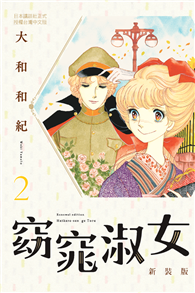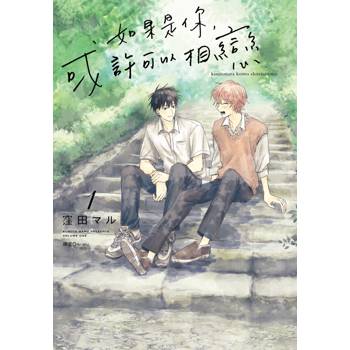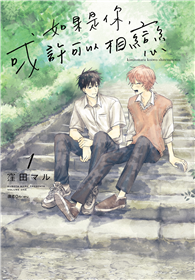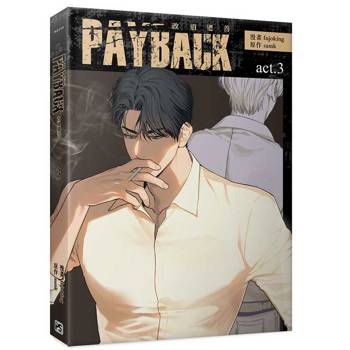中華書局成立八十周年的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該書局編輯部從庫存舊檔案中選編精印了一部大十六開硬精裝的《中華書局收藏現代名人書信手跡》,於一九九二年一月公開發行。書中有梁實秋的五封書信手跡,都是談書稿的、都是寫給時任中華書局負責人舒新城的,我們來讀這五封書信中的第一封。
新城先生執事:前承約編《文藝批評綱要》及《現代英美文學》二書,盛意至感。弟自離滬後南北奔波,數月間迄未安頓,至今方稍得暇晷,惟兩書均未動手。若不寬假期限,誠恐有誤出版,盼即另覓高明,以免延誤。專此道歉。即頌
著安 弟梁實秋頓首 四日
欣賞梁實秋這封書信手跡,很顯眼地可以發現他是在「國立青島大學用箋」的公用箋紙上給舒新城寫信的,這就得略敘一下梁實秋當時和稍前的行蹤了。
在這封書信中,梁實秋說的他「自離滬後南北奔波,數月間迄未安頓,至今方稍得暇晷」,是指他一九三○年夏應楊振聲邀請,與聞一多一道先去青島大學參觀,在接受聘請後又返回上海舉家遷往青島而正式「離滬」這一持續「數月」的青滬兩城之間的「奔波」。梁實秋應聘的是青島大學外文系主任兼圖書館館長,聞一多應聘的是青島大學中文系主任。這一年梁實秋雖然只有二十八歲,結婚也才三四年,但已是一雙兒女的父親了。兩個孩子,女兒梁文茜兩歲多、兒子梁文騏剛出生三四個月,一家四口的長途遷移,還得在短時期內再在青島重建一個家,自然不是易事。
關於這次應聘青島大學,梁實秋的〈憶楊今甫〉中有一段精彩的回憶,此文最早收在臺北志文出版社一九七四年四月初版《看雲集》一書中,寫及應聘青島大學的一段為:「民國十九年夏,今甫奉命籌備國立青島大學,到上海物色教師,我在此時才認識他。有一天他從容不迫的對聞一多和我說:『上海不是居住的地方,講風景環境,青島是全國第一,二位不妨前去遊覽一次,如果中意,就留在那裏執教,如不滿意,決不勉強。』這『先嘗後買』的辦法實在太誘人了,於是我和一多就去了青島,半日遊覽一席飲宴之後我們接受了青島大學的聘書。今甫待人接物的風度有令人無可抵拒的力量。」
經過「數月」的「奔波」,終於在「風景環境」方面屬「全國第一」的青島安居下來,「方稍得暇晷」之際,「文債」的償還已成了梁實秋此時的要務。他首先記起來的,是前年春中華書局負責人舒新城的約稿。舒新城為了他的中華書局向梁實秋約稿,也是值得一說的,因為這與魯迅有很大關聯。一九二九年前後,魯迅多次撰文攻擊比他年幼二十二歲的梁實秋,使得梁實秋的聲名陡漲。同時在與魯迅的論戰中,梁實秋確實也充分展示了他的文化思想水準和理性論辯能力。正因為這一點,剛剛出版了梁實秋翻譯的短篇小說集《結婚集》的中華書局當家人親自又約梁實秋趕寫兩部書稿,都屬於文藝理論方面的,是當年已為世人熟知的梁實秋的文化強項。
從書信後半部分的內容可以看出,梁實秋已是一派大家名家的謙讓風度,他兩次強調怕影響中華書局業務,建議舒新城「另覓高明」。然而,舒新城卻是認準了這顆文壇新星,一心要鎖定梁實秋,要他供稿,而且一約就是兩部書稿。仔細辨認書信左上方舒新城以「城」的狂草署名的批示,為「請指定交稿期」。也就是說,中華書局當家人體諒梁實秋的現實情況,鬆口說可稍緩「交稿」,但最終還是得提供書稿。或許是真忙,一直到一年之後的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六日梁實秋才將其中一部名為《文藝批評論》書稿最後該補充完善的「應備之序文、編輯凡例、各章問題及參考書目等項擬就」,並從青島郵寄發出。這部專著《文藝批評論》,一九三四年三月由中華書局在上海出版。
梁實秋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日在青島為《文藝批評論》所作〈自序〉開首的「一九三○年春余應中華書局之約,開始編一本短簡的《文藝批評》」,就恰好印證了這封書信一開始所講「前承約編《文藝批評綱要》」的敘述。「一九三○年春」被中華書局約稿,將近一年後才正式函復,而且還是不太積極的回復,表明當年梁實秋的名聲、地位和底氣支撐着他可以如此作派。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民國文人私函真跡解密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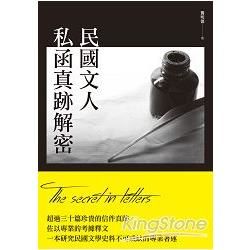 |
民國文人私函真跡解密 作者:龔明德 出版社:獨立作家 出版日期:2015-03-16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88頁 / 25k正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部份全彩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89 |
小說/文學 |
$ 299 |
華文文學研究 |
$ 299 |
華文文學研究 |
$ 306 |
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民國文人私函真跡解密
超過三十篇珍貴的信件真跡
佐以專業的考據釋文
一本研究民國文學史料不可或缺的專業著述
★ 重現真跡:
收錄超過三十篇信函真跡,包括徐志摩、梁實秋、林語堂、巴金、郭沫若、巴金等五四文學名人!
★ 史家本色:
詳細考證每封信札手跡,豐富對歷史人物的多面認識!
本書精選超過三十篇珍貴的民國文人真跡,抽絲剝繭,細探每一封書簡所涉之人、事、物,透過專業的考據和辨證,探前人所未竟,充分發揮了「文學偵探」的精神。
書中對徐志摩、梁實秋、林語堂、巴金、茅盾、沈從文、葉聖陶、張元濟等文化名人信札的解讀,糾正了某些事件的慣常說法,或豐富對歷史人物的多面認識。據實寫史,而不作過多闡釋,一二點睛之句,卻令慧心人明瞭其中所藏的判斷與傾向,展示了作者深厚的史家本色。
作者簡介:
龔明德,中國湖北人。自十六歲起先後在小學、中學與大學任職,其間有二十五年投身於四川出版事業。回歸教職後,服務於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為本科生講授中國現代文學專業課、為碩士研究生講授中國現當代文學考據和版本研究的必修課。專注於探究五四後三十多年內的文壇人事之真相。被謂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中的福爾摩斯」。
章節試閱
中華書局成立八十周年的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該書局編輯部從庫存舊檔案中選編精印了一部大十六開硬精裝的《中華書局收藏現代名人書信手跡》,於一九九二年一月公開發行。書中有梁實秋的五封書信手跡,都是談書稿的、都是寫給時任中華書局負責人舒新城的,我們來讀這五封書信中的第一封。
新城先生執事:前承約編《文藝批評綱要》及《現代英美文學》二書,盛意至感。弟自離滬後南北奔波,數月間迄未安頓,至今方稍得暇晷,惟兩書均未動手。若不寬假期限,誠恐有誤出版,盼即另覓高明,以免延誤。專此道歉。即頌
著安 弟梁實秋頓首 四日 ...
新城先生執事:前承約編《文藝批評綱要》及《現代英美文學》二書,盛意至感。弟自離滬後南北奔波,數月間迄未安頓,至今方稍得暇晷,惟兩書均未動手。若不寬假期限,誠恐有誤出版,盼即另覓高明,以免延誤。專此道歉。即頌
著安 弟梁實秋頓首 四日 ...
»看全部
目錄
賀宏亮序
列寧去世時徐志摩致胡適的信
張元濟欲配齊第二卷《生活》
葉聖陶函謝施蟄存「餉魚」
梁實秋回復中華書局約稿
僅存的茅盾一九三一年間一信
徐志摩「喪中」致梁實秋的信
丁玲函覆黃萍蓀約稿
梁實秋懇薦部下書稿
梁實秋自薦譯稿未果
彭家煌「十二日」留交陳伯昂的便條
冰心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日致林語堂
葉聖陶一九三六年間倖存短簡
沈從文函托陳夢家為戴望舒拉稿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旬郭沫若在滬三天記事
林語堂「捐交」蔡元培子女教育基金的信
梁實秋致劉英士談《雅舍小品》
梁實秋再致劉英士談《雅舍小品》...
列寧去世時徐志摩致胡適的信
張元濟欲配齊第二卷《生活》
葉聖陶函謝施蟄存「餉魚」
梁實秋回復中華書局約稿
僅存的茅盾一九三一年間一信
徐志摩「喪中」致梁實秋的信
丁玲函覆黃萍蓀約稿
梁實秋懇薦部下書稿
梁實秋自薦譯稿未果
彭家煌「十二日」留交陳伯昂的便條
冰心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日致林語堂
葉聖陶一九三六年間倖存短簡
沈從文函托陳夢家為戴望舒拉稿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旬郭沫若在滬三天記事
林語堂「捐交」蔡元培子女教育基金的信
梁實秋致劉英士談《雅舍小品》
梁實秋再致劉英士談《雅舍小品》...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龔明德
- 出版社: 獨立作家 出版日期:2015-03-18 ISBN/ISSN:9789865729196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88頁 開數:14.8*21 cm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華文文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