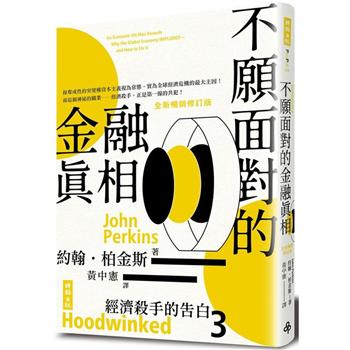第一部 唉,都是公家的事兒,犯不著
一、好人學不壞,壞人學不好
尿床是一種病,但是六十年代初期的那幾年,中國尿床的小孩都沒有病,因為晚飯他們喝下的不是水煮的糧食,而是糧食煮的水。水在尿泡裡,非排掉不可。
晚間,我跟著兩個姐姐從村裡食堂打上全家的飯,端了回家,路上擱在地上喘氣,天上的星星掉進了鍋裡一般清晰可見,隨著稀湯湯水在鍋裡浮動。一九五八年把各家各戶的飯鍋砸爛了煉鋼鐵,村裡人背地裡罵那些個造孽的人不得好死,隨後的幾年村裡人餓得連罵聲都沒有了。等到上面一聲令下,各家各戶可以置辦一兩個大鍋,到食堂打上全家的飯端回家裡喝,大傢伙兒聽了歡天喜地,趕快把鍋買回來,爭先恐後地去食堂往家打飯,誰都沒有想起來當初砸鍋煉鐵的慘狀,如今又讓老百姓買鍋,是玩弄老百姓,愚弄老百姓,應該罵他娘個八輩祖宗才解恨!沒有人罵,大家只想把稀飯打到家裡喝,怎麼都比端了一碗稀湯湯水圍在食堂周圍「吸溜吸溜」地喝,要像過日子。
如同中國千千萬萬的小孩子,我晚上喝了稀湯湯,夜裡被尿憋醒了就起夜,沒有憋醒就尿床。一天夜裡,我被尿憋醒了,從炕上跳下地迷迷糊糊地找尿鍋撒尿。憋足的尿泡一點點鬆動起來,睡意隨著尿撒掉了一半。我睡眼朦朧的眼睛的餘光,發現暗淡的煤油燈下父親和母親一動不動地守著一籮頭玉茭穗,雕像一般。我揉了揉眼睛,赤裸裸地站著,打量著那一籮頭玉茭穗,籮頭的旁邊分明是父親和母親,但是他們誰都沒有說話。山村深秋的夜裡,涼嗖嗖的夜氣襲來,我不由得渾身哆嗦一下,父親和母親還是沒有吭聲。我以為是做夢,回到了炕上,躺下。然而,過了一會兒,傳來了母親的聲音:
「他看清楚了嗎?」
「不知道。」
「他看出來我們在幹什麼嗎?」
「不知道。」
「他要是問起來怎麼對答他呢?」
「不知道。」
父親和母親沙拉沙拉地把玉米穗收拾妥當,母親又問:
「這些玉米殼兒怎麼辦?」
父親作答:
「我擓到牛屋去餵牲口。」
牛屋就是村裡的飼養院。自打土地歸公,父親就一直給隊裡餵牲口。我原本跟父親一起去牛屋睡覺,只因在鬧肚子,留在家裡喝和肚水。
過了一會兒,傳來了父親開街門的動靜。然後,一切安靜下來,我聽見母親窸窸窣窣地上了炕,睡下了。等到母親發出輕微的鼾聲,我卻一點睡意也沒有了。屋子裡黑洞洞的,伸手不見五指,我把所見所聞想了又想,得出了一個可怕的結論:偷來的玉米穗,滿滿一籮頭!可是,可是,真是父親從公家的地裡偷來的?我視若天大地大的父親會偷東西嗎?那麼……我不敢再往下想,卻又忍不住往下想,很多假設一個接一個閃現,又一個接一個熄滅。我翻了一個身又翻一個身,身上這裡癢一下那裡癢一下,好像滿炕的跳蚤、臭蟲和蝨子都在咬我,一直折騰得外面滴答滴答地響起下雨的聲音,我才迷迷糊糊地又睡過去了。
村裡有兩個飯場,東頭一個,西頭一個。自打成立了人民公社,村裡辦起食堂,村裡的飯場圍在食堂周圍,便只有一個了。兩個月前食堂不再對個人而對家戶開放,東西兩個飯場才又興起來了。飯場上的飯開始是一摸一樣的,都是從食堂的大鍋邊打進各家的鍋裡,各家端回家中,每個人再從家中的鍋裡舀上,端到飯場來喝,吸溜吸溜,此起彼伏。不過沒過多久,變魔術似的,飯場上的飯食發生了一些變化,有的人碗裡多了野菜,有的人碗裡多了豆葉,還有人索性不怎麼上飯場了。辦食堂前,父親會端上飯碗到西頭飯場去;食堂散掉,他碗裡的稀飯不經喝,走不到西頭就喝完了,所以多在東頭的飯場上。西頭的飯場大,人們坐在老槐樹下的石頭上,黑壓壓一片,上面有什麼精神、鄰村有什麼動靜、食堂什麼時候散夥,都是話題。如同東頭的大槐樹比較小,東頭的飯場也比較小,只有五六家人在場。話題的範圍也小一些:這樣清湯寡水肚饑腹餓的日子什麼時候是個頭;誰家的老人餓倒在床多少日子了,誰家大人的腿也腫起來了;誰家的小孩餓得在地上抓土吃……
父親是個喜歡蹲飯場的人,喝完第一碗總是懶得去盛第二碗,只要我在飯場,他就會衝我伸伸碗,叫我去給他盛。這點事兒由兒子來做,是顯耀自己的孩子長大了,能給大人盛碗飯了。有人要是趁機奉承幾句,父親聽了心下喜歡,會說:
「多會兒能給我掙碗飯吃,那才叫本事!」
我把飯碗端回來遞給父親時,卻別有用心,大聲問道:
「東傘村那個賊漢還活著嗎?」
父親接過碗,吸溜了一口,愣愣地看了我一眼,說:
「早死了!」
我回到我坐的地方,端起我的飯碗,又問:
「他真的是讓他哥哥把眼弄瞎的嗎?」
「那還有錯?我都給你講了八遍了,你還問!」母親插進話來,像是要阻止我再問這個問題。
「方圓幾十里裡都知道這事兒,」當中院大爺接話說。「那是個慣偷,一天不偷東西都睡不著。他家人把他捆起來打了他多少次都不改,後來商議好,把他的眼用石灰煞瞎了。他出村偷東西不行了,就夜裡摸進村子裡不論誰家的院子,偷一樣不論什麼東西,第二天再送回去。我見過他,生得跟白面書生一般,有模有樣,老遠聽見你走過來,嘿嘿衝你笑,兩隻眼睛一翻一翻的,眼珠上的灰皮一骨碌一骨碌的。」
我更小的時候一直以為當中院大爺和父親是兄弟倆,因為每年大年初一父親都要催促我去給當中院大爺大奶拜年,跪下磕頭後他們會給我壓歲錢。當中院大奶幾乎每天晚上都要來串門,家長里短的,好像在商量第二天兩家都吃什麼,能不能互補點什麼。第二天,大奶往往會端來些好吃的。他們家就一個兒子,我叫哥,對我極好;我家姊妹六七個,卻只有我一個男孩,因此大奶端來的好吃的,多少我都能吃上點兒。村裡成立了食堂,這樣的串門少了;即便來了,也只是唉長氣短的,抱怨日子沒法過,窮日子久了,什麼壞事都可能發生。兩家人都擔心兩個男孩會餓出什麼毛病,尤其當中院大爺家,因為我的哥哥比我大八九歲,快成小夥子了,餓得天天喊著要回河南去,因為那裡有吃有喝。漸漸地,我才聽明白,我的這位哥哥是要來的,背景還頗複雜;由此我也明白了,我們不是一家人,只是有些特殊的原因,兩家走得很近,非同一般。當中院大爺對我這樣一個小孩子的話當真,不厭其煩地回答了一大通話,是關心我的成長,教育我學好。
「他偷東西是天生的毛病,不是學壞的!好人學不壞,壞人學不好。」父親說話的口氣不容置疑,隨後狠狠地吸溜了一口稀飯,眉頭皺得緊緊的,找補說:「多會兒能不再喝這鳥稀溜溜,稠稠的吃上一碗飯呢?」
「聽說秋後就散夥了。」有人搭話說。
「什麼散夥?」有人問。
「食堂。」
「誰說?」
「上面傳達下精神了。」哥哥說。
「左一個精神又一個精神,沒有一個精神是為老百姓的!」又有人說。
「食堂散夥,各家各戶過日子,也得有糧食吃啊!一個人一天四兩糧食,一隻老鼠也吃不飽!」父親說。
「集體食堂不逞這個能了,就把苦日子推給老百姓了!以後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了。」哥哥說。
「老百姓可不是八仙,等著受苦吧!」父親說。
飯場上你一句我一句,越扯越遠,甚至當初成立食堂時人們跟著上面的精神瞎嚷嚷,說什麼以後電燈電話,樓上樓下,大家都是一家,到頭來卻是睡醒了被窩裡撿了一條被子,自己蒙自己。人們什麼都說,可就是沒有我想聽的話。我只是想發現蛛絲馬跡,說明父親夜裡是去集體地裡偷東西了;不知道是我那時還不善於觀察,還是父親母親臉色就沒有變化,我竟然什麼也沒有看出來。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文革的起源:公有制啟示錄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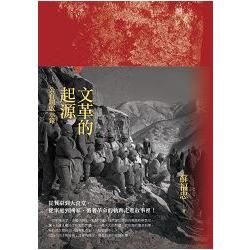 |
文革的起源:公有制啟示錄 出版社:獨立作家 出版日期:2015-09-0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40頁 / 25k正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57 |
社會人文 |
$ 369 |
中文書 |
$ 370 |
社會 |
$ 378 |
中國歷史 |
$ 378 |
社會人文 |
$ 378 |
歷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文革的起源:公有制啟示錄
一百年過去了,古國只開了一點點門縫,他們便以百倍的熱情和幹勁兒,讓十五億人解決了吃飯的問題――一個天大的問題,而依靠的還是科學。至於民主和自由,沒有私有制,一切都談不上,因為「民主和自由」這樣的概念,是私有制的意識形態。從餐桌到大食堂,從家庭到國家,循著革命的軌跡走進故事裡!
●第一手文革回憶錄,完整重現當代歷史面貌。
●旁徵博引古今中外事典,正反論述文革之影響。
●雖為回憶錄著作,卻以具故事性的筆調敘事,引人入勝。
在堆滿黃土層的山腳,有個古老的小山村,家家戶戶隨著時代的腳步走進了文化大革命,那是一個混亂失序的年代,整個社會的浪潮拍打著村子裡的人們,在食堂裡、在集會場裡、在耕作的田裡,辛勤的、困苦的、瘋狂的,每一家有每一家的故事;爸爸與兒子、媳婦與婆家、兄弟與整個家族,在這個古老的大國裡,作者以「微觀」的角度帶出了幼年時的整個世界,也讓人得以一窺文化大革命下的社會面貌,家家戶戶裡真實的生活場景。
作者簡介:
蘇福忠,天津南開大學英語系畢業,原人民文學出版社外文編輯,從事外國文學編務三十五年,編輯多種翻譯作品,現為退休人士,專職寫作。作品《母親周年祭》和《我的同窗學友》曾獲北京市廣播電臺優秀散文展播獎;《誠實工作》獲《中國青年報》雜文一等獎;《兒子》(約翰•厄普代克)獲《譯林》雜誌翻譯二等獎。
TOP
章節試閱
第一部 唉,都是公家的事兒,犯不著
一、好人學不壞,壞人學不好
尿床是一種病,但是六十年代初期的那幾年,中國尿床的小孩都沒有病,因為晚飯他們喝下的不是水煮的糧食,而是糧食煮的水。水在尿泡裡,非排掉不可。
晚間,我跟著兩個姐姐從村裡食堂打上全家的飯,端了回家,路上擱在地上喘氣,天上的星星掉進了鍋裡一般清晰可見,隨著稀湯湯水在鍋裡浮動。一九五八年把各家各戶的飯鍋砸爛了煉鋼鐵,村裡人背地裡罵那些個造孽的人不得好死,隨後的幾年村裡人餓得連罵聲都沒有了。等到上面一聲令下,各家各戶可以置辦一兩個大鍋,到食堂...
一、好人學不壞,壞人學不好
尿床是一種病,但是六十年代初期的那幾年,中國尿床的小孩都沒有病,因為晚飯他們喝下的不是水煮的糧食,而是糧食煮的水。水在尿泡裡,非排掉不可。
晚間,我跟著兩個姐姐從村裡食堂打上全家的飯,端了回家,路上擱在地上喘氣,天上的星星掉進了鍋裡一般清晰可見,隨著稀湯湯水在鍋裡浮動。一九五八年把各家各戶的飯鍋砸爛了煉鋼鐵,村裡人背地裡罵那些個造孽的人不得好死,隨後的幾年村裡人餓得連罵聲都沒有了。等到上面一聲令下,各家各戶可以置辦一兩個大鍋,到食堂...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村祭
寫作這些人,不是因為我年屆花甲,人老了喜歡回憶往事,而是這些人始終活躍在我的腦海裡,陪伴我,激勵我,撫慰我。從一個小小山村走出來,與文字結緣,與英語結緣,這種概率大大小於過去的中舉人、中狀元;抑或在百萬分之一也未可知。正因如此,如果我不能寫一寫他們的艱辛和悲苦而無所作為,我會成為罪人。
大約過了五十歲,我總喜歡對我以為有頭腦、會寫作的朋友以及有些名氣的熟人反覆說:「這個體制下,我們的經歷是罕見的,獨特的,不要拿外國人的說法當法寶,更不要拿主流宣傳當準則,認真地把我們所見所聞所經歷...
寫作這些人,不是因為我年屆花甲,人老了喜歡回憶往事,而是這些人始終活躍在我的腦海裡,陪伴我,激勵我,撫慰我。從一個小小山村走出來,與文字結緣,與英語結緣,這種概率大大小於過去的中舉人、中狀元;抑或在百萬分之一也未可知。正因如此,如果我不能寫一寫他們的艱辛和悲苦而無所作為,我會成為罪人。
大約過了五十歲,我總喜歡對我以為有頭腦、會寫作的朋友以及有些名氣的熟人反覆說:「這個體制下,我們的經歷是罕見的,獨特的,不要拿外國人的說法當法寶,更不要拿主流宣傳當準則,認真地把我們所見所聞所經歷...
»看全部
TOP
目錄
村祭
寫作這些人,不是因為我年屆花甲,人老了喜歡回憶往事,而是這些人始終活躍在我的腦海裡,陪伴我,激勵我,撫慰我。從一個小小山村走出來,與文字結緣,與英語結緣,這種概率大大小於過去的中舉人、中狀元;抑或在百萬分之一也未可知。正因如此,如果我不能寫一寫他們的艱辛和悲苦而無所作為,我會成為罪人。
大約過了五十歲,我總喜歡對我以為有頭腦、會寫作的朋友以及有些名氣的熟人反覆說:「這個體制下,我們的經歷是罕見的,獨特的,不要拿外國人的說法當法寶,更不要拿主流宣傳當準則,認真地把我們所見所聞所...
寫作這些人,不是因為我年屆花甲,人老了喜歡回憶往事,而是這些人始終活躍在我的腦海裡,陪伴我,激勵我,撫慰我。從一個小小山村走出來,與文字結緣,與英語結緣,這種概率大大小於過去的中舉人、中狀元;抑或在百萬分之一也未可知。正因如此,如果我不能寫一寫他們的艱辛和悲苦而無所作為,我會成為罪人。
大約過了五十歲,我總喜歡對我以為有頭腦、會寫作的朋友以及有些名氣的熟人反覆說:「這個體制下,我們的經歷是罕見的,獨特的,不要拿外國人的說法當法寶,更不要拿主流宣傳當準則,認真地把我們所見所聞所...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蘇福忠
- 出版社: 獨立作家 出版日期:2015-09-02 ISBN/ISSN:978986572981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40頁 開數:14.8*21 cm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