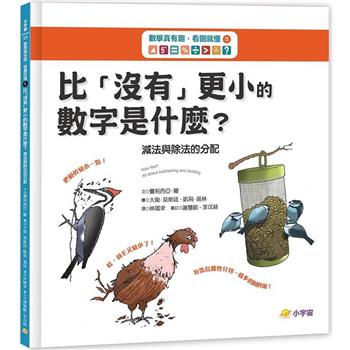★本書以豐富的史料、生動的文筆、全景式的視角描寫了他們在民國時期多難歲月中的生活、愛情、事業與創造。不僅具有自由詩意的敘述魅力,更具有真實人性的訴說光輝。精裝本更具收藏價值。
冰心(1900-1999),中國現代著名作家、詩人、兒童文學奠基人、社會活動家,五四運動中文壇,成為新文化運動中最具影響的女作家,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其小說、散文、詩歌、兒童文學、翻譯等不同類型的作品,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讀者。
吳文藻(1901-1985),中國社會學、民族學的奠基人,「燕京學派」的開創者,同時也是民國時期的外交家,他的「社會學中國化」的理論,在學界有著深遠的影響。1929年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十年內最優秀的外國留學生、文博士之後,回到北平燕京大學任教,與冰心結為連理,成為一對在文壇與學界璀璨的雙子星。
本書以豐富的史料、生動的文筆、全景式的視角描寫了他們在民國時期多難歲月中的生活、愛情、事業與創造。不僅具有自由詩意的敘述魅力,更具有真實人性的訴說光輝。
作者簡介:
王炳根
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系。1992年發起成立冰心研究會,任秘書長,巴金出任會長,開始籌備建立冰心文學館。1997年8月,冰心文學館開館,任常務副館長、館長。在冰心研究會成立之後,由當代文學研究,進入對冰心和現代文學研究,開始了二十年的學術生涯,接觸、閱讀、研究了冰心、吳文藻所有的著作以及尚未公開出版的日記、筆記與書信,尋訪過冰心吳文藻在全世界生活過的地方等。
主編自五四運動以來冰心研究的系列叢書《冰心論集》(十冊),著有評論集《特性與魅力》、《逃離慣性》;專著《冰心:非文本解讀》、《冰心:冰心非文本解讀(續)》、《郭風評傳》、《少女萬歲―詩人蔡其矯》;傳記《永遠的愛心―冰心》、《世紀情緣―冰心吳文藻》、《鄭振鐸―狂臚文獻鑄書魂》、《林語堂:生活要快樂》;散文隨筆集《慰冰湖情思》、《雪裡蕭紅》及演講集《王炳根說冰心》等二十餘種。
章節試閱
第三章 一個女大學生的「五四」
1,煩悶的少女
辛亥革命結束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並且頒佈了具有資產階級民主精神的法令,這在中國的歷史上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但辛亥革命與後來的共產黨鬧革命不一樣,它不是徹底地告別一切,許多東西保持一定的延續性,僅從軍隊而言,基本是晚清的軍隊起義與改編,海軍尤甚。1912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任命的第一位海軍部總長便是長江艦隊臨時艦隊司令黃鍾瑛,晚清海軍部及各艦隊的許多官員,大都在原崗位任職。謝葆璋曾經任職的「海圻號」巡洋艦當時在英國訪問,中華民國成立後,「海圻號」只是在英格蘭北岸的巴羅因弗內斯港舉行了一個易幟儀式,在艦長程璧光「換旗」令下,降下了黃色青龍旗,升起了紅黃藍白黑五色旗。
南京臨時政府的存在,實際上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所以,臨時政府海軍部的人員基本未到位,當袁世凱贊成共和、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後,南京海軍部就宣佈裁撤了,北京的袁世凱接收了清政府的海軍部,建立了北京政府的海軍部,首領則是譚學衡。待海軍部正式移交之時,黃鍾瑛因病辭職,劉冠雄為海軍部總長。隨後,黃鍾瑛被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袁世凱任命為海軍部下設的海軍總司令處的總司令,黃因健康原因,仍駐上海未至北京。1912年12月4日病逝。
我之所以要使用這些游離於冰心、甚至也游離於謝葆璋的文字,目的在於要糾正一個在所有的傳記中沿用的史料,即認為謝葆璋從福州到北京海軍部任職,是得到了海軍總司令黃鍾瑛的電召,有的還將其北上的時間定在1912年。其實,謝葆璋到北京任職,是延續了他在煙臺海軍學校離職後的職位,是為袁世凱接收清政府海軍部之後使用舊部人員所致。謝葆璋到北京政府海軍部的時間為1913年的春末夏初,正式任命是4月7日,「海軍總司令處二等參謀」,7月授銜為「海軍上校」,一個月之後晉升為「海軍少將」,10月提升為「海軍部軍學司司長」。所有的任命都為「北京政府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令」。
謝婉瑩便是這個時候從福州進京的,從此成了北京人。當年這位海軍少將的公主走進北京,留下了是並不美好的印象。如果用色彩來描述,煙臺是藍色的,福州是碧綠的,而北京是灰黃的。黃土鋪就的塵土飛揚的馬路,秋日夕照下的蒼黃的城廓,灰頭土臉的四合院,謝婉瑩和三個弟弟坐在馬車裡,探出頭來望著布幔下灰黃的街道、匆忙而又迂緩的行人和流汗奔走的人力車夫……
在茫然漠然的心情之中,馬車把他們送到了東城鐵獅子胡同中剪子巷十四號,父親為家眷的到來租住的房子。大門左邊的門框上,掛著黑底金字的「齊宅」牌子。進門右邊的兩扇門內,是房東齊家的住處。往左走過一個小小的長方形外院,從朝南的四扇門進去,是個不大的三合院,便由謝葆璋一家居住。
這個三合院,北房三間,外面有廊子,裡面有帶磚炕的東西兩個套間。東西廂房各三間,都是兩明一暗,東廂房作了客廳和父親的書房,西廂房成了舅舅的居室和弟弟們讀書的地方。從北房廊前的東邊過去,還有個很小的院子,這裡有廚房和廚師父的屋子,後面有一個蹲坑的廁所。北屋後面西邊靠牆有一座極小的兩層「樓」,上面供的是財神,下面供的是仙!
海軍少將將寶貝女兒安排在北屋的正房。兩明一暗的正房,有玻璃後窗,有雕花的「隔扇」,隔扇上的小木框裡,都嵌著一幅畫或一首詩。框裡的畫,是水墨或彩色的花卉山水,詩多半是《唐詩三百首》中的句子,冰心很喜歡這種裝飾,詩句大多是在煙臺與福州讀過的,但有一首七律是從來見過的:「飄然高唱入層雲/風急天高(?)忽斷聞/難解亂絲唯勿理/善存餘焰不教焚/事當路口三叉誤/人便江頭九派分/今日始知吾左計/枉親書劍負耕耘」。冰心覺得很有哲理意味,便將它記下來了。
也就是冰心在文章中記下這首詩後的不久,我曾來尋訪過這座房子,門牌不是14號而是33號,簡陋地釘在土牆上,完全沒有了「齊宅」的氣派,裡面全然不是冰心所描寫的那般規整有序,正房、廂房、庭院,而是雜亂無章,門窗油漆斑駁,院落中的空間全被加建的刀把子房佔據,只有一條總有好幾個90度夾角的甬道,可以走到正房的門前,空間小到拍一張照片都無立足之處,只有房頂那棵大槐樹依存,墨綠的槐葉下掩著屋脊,才算殘存了一點當年的風貌。
住進三合院的謝婉瑩感覺到的是狹仄冷清,既不能與福州前後幾進的大院相比,更無煙台的海闊天空。父親任職的海軍部,就在鐵獅子胡同,離中剪子巷僅一箭之地,但海軍部的父親不能像煙臺那樣「跟班」,不能帶她去「衙門」,弟弟們又小,周圍沒有哄著她玩的水兵,屋裡也沒有一大堆的堂哥堂姐之類的夥伴。她自將煙臺與福州的生活喻為「山中歲月」「海上心情」,將北京視為「輦下風光」。那多彩的山中歲月與海上心情都已遠去,眼前的輦下風光卻未看到,那時故宮、景山與北海都不開放,別的景區父親也不曾帶她去過。婉瑩只能整天在家跟著母親,為母親做一些家務,學些針黹,幫母親梳頭,晚間則在堂屋的方桌邊,和三個弟弟各據一方,幫他們溫習功課,儼然成了一位小先生。
北京做官的父親,比煙臺卻消沉多了。新的政府沒有令他興奮反而使他消沉,婉瑩完全不明白。父親既沒有興致帶孩子們外出遊玩,自己也不出去打牌、聽戲、喝酒、應酬,只是對舊日的同學、好友還有一些交往。冰心記得父親曾去瀛台與「囚禁」的副總統、昔日天津紫竹林海軍學校的同窗黎元洪下棋。在家的父親也是個不甘寂寞的人,從海軍部下班回家,便在院子忙乎開來,砌花台,捲起袖子種花、澆水,還搭起一個葡萄架子,把從煙臺寄來的葡萄秧子栽上。後來還把花園漸漸擴大到門外,種了野茉莉、月季、蜀葵之類的花朵,又為孩子們立了一個秋千架,周圍的孩子就常來看花,打秋千,把這大院稱作「謝家大院」。
就在這時,京味文化開始進入謝婉瑩的生活:
「謝家大院」是周圍的孩子們集會的地方,放風箏的、抖空竹的、跳繩踢毽子的、練自行車的……熱鬧得很。因此也常有「打糖鑼的」的擔子歇在那裡,鑼聲一響,弟弟們就都往外跑,我便也跟了出去。這擔子裡包羅萬象,有糖球、面具、風箏、刀槍等等,價錢也很便宜。這糖鑼擔子給我的印象很深!
舅舅帶著逛了隆福寺市場,這對我也是一件新鮮事物!市場裡熙來攘往,萬頭攢動。櫛比鱗次的攤子上,賣什麼的都有,古董、衣服、吃的、用的五光十色;除了做買賣的,還有練武的、變戲法的、說書的……我們的注意力卻集中在玩具攤上!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棕人銅盤戲出。這是一種紙糊的戲裝小人,最精彩的是武將,頭上插著翎毛,背後紮著四面小旗,全副盔甲,衣袍底下卻是一圈棕子。這些戲裝小人都放在一個大銅盤上。耍的人一敲那銅盤子,個個棕人都旋轉起來,刀來槍往,煞是好看。
北京東安市場內的吉祥戲院。我站在樓上堂客座的欄旁,戲院裡人聲嘈雜,打手巾把的,熟練地從觀眾頭上高高地扔著手巾……戲臺上立著很大的紅紙海報,大軸子戲是梅蘭芳先生和王鳳卿先生的《汾河灣》……忽然間後面有人推我一把,「快看」,梅先生出臺了,流水般的踱步,送出一個光彩奪目的人兒,端嚴的妙目,左右一掃,霎時間四座無聲!
從糖鑼擔子到民俗表演,從放風箏至梅蘭芳,這些最能代表京韻文化的符號,都是煙臺、福州所不曾有過的,文化的反差才令謝婉瑩有一種興奮與新鮮感,但也有種陌生與惶惑,有時還會產生心理的隔膜與失落,冰心是這樣描述自己當時的心境的:「弟弟們睡覺以後,我自己孤單地坐著,聽到的不是高亢的軍號,而是牆外的悠長而淒清的叫賣『羊頭肉』或是『賽梨的蘿蔔』的聲音,再不就是一聲聲算命瞎子敲的小鑼,敲得人心頭打顫,使我彷徨而煩悶!」
冰心晚年憶及這段生活時,認為她在北京的頭一年,在她少女生活的開步之時,如同列車進入了黑暗的隧道,「窗外黑糊糊的,車窗關上了,車廂裡電燈亮了,我的眼光收了回來,在一圈黃黃的燈影下,我仔細端詳了車廂裡的人和物,也端詳了自己……」
婉瑩在她不開心的時候,也曾嘗試過寫作,想以自己的想像與描寫,填補生活中的不足,沖淡煩悶的心情。與她的鄉賢林琴南以文言文翻譯小說一樣,她也用文言體寫作小說,她自己後來記得的是曾寫過一部偵探小說,書名叫《女偵探》,還用文言體寫過一部女革命家的小說,叫《自由花》,但她與在煙臺寫過的章回小說一樣不成功,只留下一個記憶中的存目。但另一項文學活動卻是成功,就是給弟弟們講故事,婉瑩講的故事不是書中現成的,但也不完全是杜撰。她將自己看過的新舊譯著幾百種的小說,人物佈局,差來錯去的胡湊,自成片段,講起來繪聲繪色,讓弟弟聚精凝神,笑啼間作,且對姐姐充滿了敬意。冰心後來說她在一年多的時間內,講過「三百多段信口開河的故事」,給弟弟們也給她的煩悶的生活平添了幾分亮色。
平淡的生活也有多彩的時候,母親到北京後,訂閱了《小說月報》、《東方雜誌》等報刊,每當郵差送來雜誌,如同送來了歡樂,不等母親看過,便一頭栽進了多彩的世界裡。
2,教會女中的「同性愛」
冰心從福州來到北京,應為輟學,放棄了福州師範預科的學業,到了北京自然應該繼續上學,卻因易地休學了一年,生出了許多煩悶的心情。終於在一個黃昏後,謝婉瑩悄悄地向舅舅楊子敬提出繼續上學的要求。舅舅一打聽,離中剪子巷不遠處的燈市口,有一所女子中學,名為貝滿女子中齋,是一所美國基督教公理會辦的學校。
貝滿女子中齋建於1864年,沿用了中國傳統對學校劃分的名稱:小學叫蒙學,中學稱中齋,大學則為書院。謝婉瑩入校時,中齋已改稱中學了,但在校園的牆壁上四個金字依然為「貝滿中齋」。貝滿是英文的音譯,BRIDGEMAN,捐款興建這個學校美國人的姓氏,學校以捐建人的名字命名。中國自1840年被西方列強以槍炮打開大門後,在中華大地上橫行無忌,簽訂不平等條約、設租界、掠文物,但傳教士辦學校、興教育卻不是什麼壞事,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教會學校,中國現代文明與科技的進程可能會受到不小的影響。與冰心同時代的美國傳教士、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這樣說:「19世紀80年代和19世紀90年代中國建立的教會學校是基於經驗和知識的教育方法,和舊的封建體制基於詩歌和書法的教育方法完全不同。傳教士們教授學生數學、科學,介紹現代醫學,實行諸如飢餓救濟等干涉主義政策,積極推動女性解放運動。」
入教會學校,對謝婉瑩而言,不能像林語堂那般順理成章,他們家沒有基督徒。好在福州也有教會學校,倉前山的英華書院便是,婉瑩的二伯父謝葆珪在此教中文,堂兄謝為樞也在那兒讀書。教會學校的外籍教師均為傳教士,到過他們福州的家,留下的印象並不壞,尤其婉瑩出生,接生婆便是傳教士。自然母親不會反對上教會學校,父親對教會學校瞭解,認為他們教學認真,英語口語純正,便對女兒說,去貝滿上學也好!
海軍少將這個決定對女兒的成長十分重要,但海軍公主與她在福州上師範預科一樣,開始卻很不習慣,甚至覺得「很苦」,第一天上學便將要交的學費弄丟了,不知道到那兒去就餐,一天沒有吃飯等等。冰心後來列舉了「很苦」三個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我初小是在山東鄉下上的,程度遂不及貝滿,剛一來便感到應付的為難,尤其是算學一科,分數很低的。第二年才補上,以後才有很好的成績。第二個原因是我口音的關係,才從山東來,國語一點也不會說,開口感到困難,一切練習口才的集會便不敢參加。第三是聖經不熟,我是生活在非基督教家庭的,對於聖經沒有絲毫根底。」數學跟不上,作業與考試都不及格,說話山東口音很重,老師與同學聽不太懂,回答問題只能到講臺上將答案寫在黑板上,同學們賜她一個外號「侉子」。
顯然,冰心被「現代教育」的課程卡住了。福州女子學校的預科,僅學過算學中的加減乘除,而中學的數學從代數起步,一到上課,便覺得「腳跟站不牢,昏頭弦腦,踏著雲霧似的」。如此情景,十道題能做對五道就不錯了,考試不及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但這一切並沒有難倒從水兵堆中走出來的聰慧而又倔強的謝婉瑩。因為代數的缺課,母親請了培元蒙學的一位數學老師來給女兒補課,冰心也極是用功,「我每天回家以後,用功直到半夜,因著習題的煩難,我曾流過許多焦急的眼淚。」眼淚可以開花、也可以結果,代數補習完畢,數學便追上去了,而其他的如幾何等一切難題迎刃而解,甚至成了同學們崇拜的偶像,遇有難題便來向她請教。此時的冰心對數學甚至有些出神入化了,「竟有幾個困難的習題,是在夜中苦想,夢裡做出來的。」
口音問題也很快得到糾正,並且練成了一口標準、地道的京腔,以至沒有人能聽出她曾有過的山東或福建的口音。
在貝滿還有一個集體活動,是每星期三下午的「文學會」,是同學們練習演講辯論的集會。這會是在大課堂裡開的。講臺上有主席,主持並宣告節目;還有書記,記錄開會過程;台下有記時員,她的桌上放一隻記時鐘,講話的人過了時間,她就叩鐘催她下臺。節目有讀報、演說、辯論等。辯論是四個人來辯論一個題目,正反面各有兩人,交替著上臺辯論。大會結束後,主席就請坐在台傍旁聽的教師講幾句評論的話。我開始非常害怕這個集會。第一次是讓我讀報,我走上台去,看見台下有上百對的眼睛盯著我看,我窘得急急忙忙地把那一段報讀完,就跑回位上去,用雙手把通紅的臉捂了起來,同學們都看著我笑。一年下來,我逐漸磨練出來了,而且還喜歡有這個發表意見的機會。我覺得這訓練很好,使我以後在群眾的場合,敢於從容地作即席發言。
我沒有聽過冰心的演講,但據與她一道出國訪問的夏衍與巴金說,冰心大姐的即席演說生動、風趣、幽默,無論是中文還是英文。冰心認為這個本領是在中學練成的。
那麼《聖經》呢?由於沒有基督教的家庭背景,沒有接觸過《聖經》,並且一開始便是難讀《列王記》,講述猶太國古王朝的歷史,小小年紀謝婉瑩對本國的歷史都不甚了了,猶太古國的歷史還不「枯燥無味」?這個時候協和女子書院的校長麥美德教士以講聖經故事的形式講述《聖經》,卻是引起了冰心的興趣。「聖經故事」雖然也來自《聖經》,但以故事的形式進行講述,這對初步者來說形象而生動,冰心便是通過這種形式,走進《聖經》,接近上帝。當《聖經》課從《舊約》讀到《新約》時,謝婉瑩便已沉入其中了,她從《福音》書裡瞭解了耶穌基督這個「人」,看到了一個窮苦木匠家庭的私生子,竟然能有那麼多信從他的人,因為宣傳「愛人如己」,而被殘酷地釘在十字架上,這個形象是可敬的,也是可親的。此時冰心尚無信仰,在她心目中,耶穌尚是人子,而非神子,但《聖經》對她日後形成的愛的哲學,卻是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當入校時困擾謝婉瑩的三個問題都一一解決之後,另外一個潛藏的情感問題便浮上來了。冰心入貝滿女中,正值豆蔻年華,青春的騷動、情竇的初開,都令海軍公主萌生了交友的情懷;同時,社會上也是西風漸進,知識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會漸成時尚。冰心平日閱讀的《婦女》雜誌,有專門欄目介紹女性社會交往。但在教會所辦的女校,校規甚嚴,青春期的慾望與嚮往,不僅受到校規的嚴格限制,同時受到性別的限制,如何衝破種種限制,成了教會學會女生的情感苦惱。女校的交友無法在異性之間,在青春期缺乏自我控制能力的情況下,捨遠求近,面對了身邊同性,開始了交友,並且由交友到產生感情,最後成為了一種教會女校特有的風景―同性愛。
彼時風氣初開,各同學競以交友為時髦課程之一。乃又格於校章,管理嚴密,平時不能輕越雷池一步,不得已,在可能範圍中,捨遠求近,棄異性而專攻同性戀愛之路途。初則姐姐妹妹,親熱有逾同胞,繼則情焰高燒,陷入特殊無聊恨海,終則竟超越情理之常,來一下卿卿我我,雙宿雙飛,若婦若夫,如膠如漆。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此中醜象百呈,怪事不能勝數。常見有第三者參與其中,居然吃醋拈酸,打雞罵狗,或則嬌啼宛轉,搶地呼天,如喪考妣,如失靈魂。
冰心說她「我非超人,不能免俗,亦曾一度為同性戀愛之蠶絲沾惹」,那麼,誰是沾惹謝婉瑩的「同性愛的蠶絲」呢?
根據冰心在慕真女中的演講與後來的回憶文章,大致可以推斷為:
首先愛上的是一位年輕的女老師,她教過冰心的「歷史、地理、地質等課」,名字叫丁淑靜。後來在描寫丁淑靜《我的教師》時,改變了一下課業,成為了代數教師,但「其他的描寫,還都是事實。」
冰心說丁淑靜老師是在她入校時還未站穩,「便在這雲霧之中,飄進了我的生命中來。」對丁淑靜的描寫是這樣的:
「螓首蛾眉,齒如編貝」這八個字,就恰恰的可以形容她。她是北方人,皮膚很白嫩,身材很窈窕,又很容易紅臉,難為情或是生氣,就立刻連耳帶頸都紅了起來,我最怕的是她紅臉的時候。
在描寫與丁淑靜單獨相處時的情態,非初戀人的心境可比:
在我抬頭凝思的時候,往往注意到她的如雲的頭髮,雪白的脖子,很長的低垂的睫毛,和穿在她身上穩稱大方的灰布衫,青裙子,心裡漸漸生了說不出的敬慕和愛戀。在我偷看她的時候,有時她的眼光正和我的相值,出神的露著潤白的牙齒向我一笑,我就要紅起臉,低下頭,心裡亂半天,又喜歡,又難過,自己莫名其妙。
惡補代數的時候,冰心說她用功到半夜,遇到難題時,也曾流過焦急的眼淚,而在淚眼模糊之中,燈影之下,往往湧現出丁淑靜美麗慈和的臉,一想到她,彷彿就得了靈感,「擦去眼淚,又趕緊往下做。」
教師在學校自然屬公眾人物,同學中敬愛她的,當然不止一人,但大概都有一種「私意,」以為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一個男子,配作丁老師的丈夫,然而向丁老師求婚的男子,那時總在十個以上,有的是學校的男教師,有的是校外人士。學生們對於丁老師追求者,「一律的取一種譏笑鄙夷的態度。對於男教師們,我們不敢怎麼樣,只在背地裡替他們起上種種的綽號,如『癩蛤蟆』、『雙料癩蛤蟆』之類。對於校外的人士,我們的膽子就大一些,看見他們坐在會議室裡或是在校門口徘徊,我們總是大聲咳嗽,或是從他們背後投些很小的石子,他們回頭看時,我們就三五成群的哄哄笑著,昂然走過。」謝婉瑩暗戀著丁淑靜的時候,聖經課正讀著《所羅門雅歌》,她便模仿雅歌的格調,寫了許多讚美心目中丁淑靜的句子,「在英文練習簿的後面,一頁一頁的寫下疊起。積了有十幾篇,既不敢給人看,又不忍毀去。那時我們都用很厚的牛皮紙包書面,我便把這十幾篇尊貴的作品,折存在兩層書皮之間。」
就在冰心沉浸在對教師的愛戀之中時,她自己卻也被高年級的同學所愛戀。在當時的教會女校,學生愛上同性的老師與高年級同學愛上低年級同性的同學,都是常事。
貝滿女中的學生人數並不多,卻有相當部分住校者,她們來自河北保定、通縣或外省,家庭不一定富庶,基本都是基督教徒。這些同學的衣著單調,不是藍便是青,梳髻穿裙,冬天裡是黑色臃腫的棉衣,平時說話行事都很拘謹、嚴肅,幾乎聽不到她們的笑聲。城裡的學生就不一樣,比外鄉學生活潑多了,淘氣多了,也會開玩笑。城裡的學生不住校,謝婉瑩每天由一位高高大大、名叫王祥的車夫,拉著洋車送她到校門口,放學時則又來接她回家。在學校遇到生活上的問題,也是城裡的同學來幫助,最首幫助她的是一位二年級的女生,名叫陶玲,「一個能說會道、大大咧咧的滿族女孩子」,帶她走進自修的大教室,進入大餐廳的內間,享用四菜一湯的「小灶」等等。按說冰心很容易被陶玲所「獵獲」,但同性的戀情也是有緣分的。婉瑩是典型南方人的身材與體型,個兒小、瓜子臉蛋、苗條、秀氣,在她的成績好上之後,在她被「小碗兒」「小謝」愛稱般的被叫著的時候,同學們也就悄悄地喜歡上她了。「在中學最壞的現象就是交朋友,因為那時社交嚴緊,發現感情的對象只有同性,在那時很容易與高班的同學因同學的起哄而成朋友。我那時彼也和一個四年級的同學好起來」。這個同學根據後來冰心的回憶與描寫,可知她名字叫陳克俊。與丁淑靜一樣,「男士」在《我的同學》中稱她為C女士。「C女士是廣東人,卻在北方生長,一口清脆的北平官話。」只不過,冰心對她的描寫,沒有放在貝滿女中而是放在升入大學之後的時間段裡,但那初次的印象與交往,應該是發生在貝滿女中裡。
第一次見面便是那麼的與眾不同,「那時的女同學,都還穿著制服,一色的月白布衫,黑綢裙兒,長蛇般的隊伍,總有一二百個。在人群中,那竹布衫子,黑綢裙子,似乎特別的襯托出C女士那妖嬌的游龍般的身段。她並沒有大聲說話,也不曾笑,偶然看見她和近旁的女伴耳語,一低頭,一側面,只覺得她眼睛很大,極黑,橫波入鬢,轉盼流光。」這是一個遠的鏡頭,隨之拉近,「及至進入禮堂坐下―我們是按著班次坐的,每人有一定的座位―她正坐在我右方前三排的位子上,從從容容略向右倚。我正看一個極其美麗瀟灑的側影:濃黑的鬢髮,一個潤厚的耳廓,潔白的頸子,美麗的眼角和眉梢。臺上講話的人,偶然有引人發笑之處,總看見她微微的低下頭,輕輕的舉起左手,那潤白的手指,托在腮邊,似乎在微笑,又似乎在忍著笑。這印象我極其清楚,也很深。以後的兩年中,直到她畢業時為止,在集會的時候,我總在同一座位上,看到這美麗的側影。」遠景與特定、正面與側景,從穿著到說話的聲音,從眼睛到鬢髮,從「潤厚的耳廓,潔白的頸子」,低眉、托腮,一舉手一投足,無不呈現了「情人眼裡出西施」的風姿。每當集會,便是她們相會之時,「在末座靜靜的領略她穩靜的風度,聽取她簡潔的談話。……她的溫和的美,解除了我們莫名其妙的局促和羞澀,我覺得我並不是常常紅臉的人,對別的女同學,我從不覺得踧踖。」因為不在同一班級與年段,相處只能在集會中或查經班裡,謝婉瑩本來覺得查經班與做大禮拜都是負擔,希望星期天多與母親在一起,但因為陳克俊的原因,竟然對各種集會、對查經班與做禮拜,有了某種的期盼。「夢境中還常常有著C女士,她或在打球,或在講演,一朵火花似的,在我迷離的夢霧中燃燒跳躍。」在一次教會學校組織的西山郊遊中,謝婉瑩與陳克俊還穿了從天津中西女校借來的白綢子衣裙,表演「天使」的形象,引起同學的讚美與羡慕。
於是,可以看到,在貝滿女中冰心既在暗戀著年輕老師丁淑靜,同時在與高出兩屆的陳克俊產生了夢中情人般的戀情,由於社交的阻隔,豆蔻年華的謝婉瑩,將交友與愛戀的對象,投入到了同性的身上。從人性的經驗而論,這也是一種自然現象,當她(他)的性欲初開而受到環境的限制時,發洩的對象往往便是選擇了同性。但無論是異性愛還是同性愛,都具有佔有性與自私性,用冰心自己的話說「無論同性或異性的戀愛都是有佔有性的,兩人便或彼此監視,禁止交朋友,」處於同性三角戀情中的謝婉瑩,自然也脫不了這種規則的制約,所以,當她寫給丁淑靜的「雅歌」與信件,被陳克俊發現之後,感情的決裂就成了必然了。「感到朋友之無趣,便將以前和那朋友的信一同燒掉,從此對於朋友感情皆盡」。從冰心後來的講述中,這種情感的切斷很是決然,認識到這種同性之間的愛是一種「不健全的、自私的有害的」情感行為,並且對這種交友的方式有了「反感」。後來,低年級的學生有追求者,冰心也都一概拒絕,不再陷入同性愛的情感漩渦。但是,冰心與陳克俊的感情,決裂之後並非成為了「敵人」,依然還是朋友,在進入大學之後依然還有交往,在一起照相、參加歌詠隊,甚至還參加過一次共同演出:
在C女士將要畢業的一年,我同她演過一次戲,在某一幕中,我們兩人是主角,這一幕劇我永遠忘不了!那是梅德林克的《青鳥》中之一幕。那年是華北旱災,學校裡籌款賑濟,其中有一項是演劇募捐,我被選為戲劇股主任。劇本是我選的,我譯的,演員也是我請的。我自己擔任了小主角,請了C女士擔任「光明之神」。上演之夕,到了進入「光明殿」之一幕,我從黑暗裡走到她的腳前,抬頭一望,在強烈的燈光照射之下,C女士散披著灑滿銀花的輕紗之衣,扶著銀杖。經過一番化裝,她那對秀眼,更顯得光耀深大,雙頰緋紅,櫻唇欲滴。及至我們開始對話,她那銀鈴似的聲音,雖然起始有點顫動,以後卻愈來愈清爽,愈嘹亮,我也如同得了靈感似的,精神煥發,直到終劇。我想,那夜如果我是個音樂家,一定會寫出一部交響曲,我如果是一個詩人,一定會作出一首長詩。可憐我什麼都不是,我只作了半夜光明的亂夢!
在揮別了同性愛的情感之後,冰心把心思都放到了學習上了,「對於功課更加用功,課外服務也特別努力,到一九一八年更加用功,更能欣賞友誼之重要,對於全校同學都熱誠,交接,與幫助,這時是最快樂的一年。」一個在入校時代數成績不合格的學生,經過四年的努力,現代科學中的基礎課,數學、物理、化學、英語等等各門課程都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包括體育,她還記得當時的體育老師是美國人,下肢運動這樣下口令:「左腳往左撇,回來!右腳往右撇,回來!」國文就更不用說,曾經得到過100+20的高分。在畢業考試中,謝婉瑩的成績名列前茅,按照校規,應屆畢業生中的最高分者,要在畢業會上致「辭師別友」的演講,要編寫歌詞,在畢業會上演唱。這些,謝婉瑩都做得很到位,但她並無得意反倒有了傷感,中學時代的生活與友誼這麼快就結束了。「而今回憶起來,中學時代的生活,是較大學時代甜蜜得多,所得的朋友也親密得多,而現在最好朋友,仍是中學時代所認識的。」
中學時代的同性愛,如果不是冰心自己說了出來,大概是不會有人知道的。1936年5月,冰心與吳文藻即將赴歐美遊學,由天主教會辦的慕真女子中學,邀請冰心演講。面對與自己二十年前一樣處於豆蔻年華的女生,冰心講起了她在貝滿女中的學生生活。演講並非追懷遠逝的同性愛的戀情,而是意在說明這種情感的不健全性與有害性,顯然是希望對慕真的女生有種勸導與警告的作用。也許邀請者希望已成為著名作家的冰心講講中學生交友的話題,冰心便帶出了同性交友的經驗與認知。當時有人做了記錄,主要的觀點刊在了慕真女校的校刊上,同時配發了馬玉波《謝冰心印象記》,記載了演講的情形。內容「與《我自己的中學生活》是基本一致的。在馬玉波筆下,《我自己的中學生活》中所說的『交朋友』,被稱作『專一的友誼』,並且也談到冰心從『專一的友誼』上『覺悟過來,改到普遍的友愛』,稱讚冰心『富於理智和自斷』。馬玉波的文章可以看做是聽眾的反饋;應該說,冰心的演講是溫和的、親切的、實在的,也是成功的。」
刊登冰心演講《我自己的中學生活》的《慕真半月刊》,是為校刊,發行範圍不大,影響也有限,但由於冰心的知名度、尤其是演講的話題,立即被上海的一些報刊所注意,也就在同年的6月,30年代在「女學生們人手一冊」的暢銷雜誌《玲瓏》,刊登了據說是從上海日報上轉載來的署名「玉壺」的文章,題目叫《冰心演講同性愛記》,將《我自己的中學生活》中關於「同性愛」放大為標題。
文章的前言云:
擅寫母愛著名於中國文壇之謝冰心女士,執教於燕大,聞近將赴美考察。日前為燕大女同學所包圍,要求赴慕貞女校演講。冰心不獲辭。因講《我的中學時代生活》。內說及同性愛及女士對於戀愛之見解,甚為珍貴。原文見於上海日報,特轉錄之。
冰心的演講本為口語,倩茵記錄的《我自己的中學生活》也為保持了口氣的方式,到了《冰心演講同性愛記》變成了文白參半,內容基本相同,只是有詳略之別,因而可推斷為《玲瓏》雜誌上的文章,並非從《慕真半月刊》來,而是別有稿源渠道。比如入校時的成績就更詳細:
考入中學,國文一科,尚能勉強應付。可是算學一竅不通,「如之何其可」。雖能拼命加工陶煉,究非種田插秧,一學便會者可比。每見同學精通此道者,輒自慚自怨,然第一月考,即獲六十三分,評訂雖短少七分,方能及格,但退一步想,亦足以自慰矣。經過努力不斷之猛烈練習,三閱月後,即增至八十三分,與其他同學可云並峙。至於國語一層,使余窘絕,無論如何留心注意拗腔,終不免「茄兒」意味。由此即為許多捉狹姐妹作為調笑原料,余只能含笑受之。
與《我自己的中學生活》一樣,冰心談自己的並不多,但在該文則出現了較多的對同性愛現象的描述與勸誡的文字,以及同性感情自生自滅的觀念:
現在余將一談女學生進一步向女校長或女教員作不健全不合理之單面的或雙面的表示親熱戀愛。其事較學生與學生之間發生「那個」,尤臭尤醜。平時格於種種環境,不敢或不便與教員談話,或作其他進一步之熱烈舉動。唯一至西曆新年耶誕節時,籍此機會,恭而敬之,正楷端書,送一份藏頭露尾之匿名賀年信片,與其平日所愛慕之教員。因為教員多數在改卷時,已認清各生之筆跡,雖不具名,亦可知悉為誰氏手筆。教員自愛者,當然付諸紙麓,佯作不知。設有不能自檢者,必將就此上了圈套,而陷入痛苦無謂之地獄。雖如此說,然竟有若干女子,認為與教員戀愛為特殊光榮者,可謂悖謬人道,乖舛倫常之可憐蟲耳。該問同性戀愛,意義何在?根據何在?生活趣味又何在?滿盤盡錯,尤欲認為光榮,罪過罪過。今之辦女子中學者,對於此點之絕大污點,絕大錯誤,應如何注意,在校女生之言行品德,應如何設法作深切之明朗教導,務使其勿入迷津孽海,然後始無虧於職責。
在學生個人方面,並不需要教師來糾正,也該從道德人格方面大處著眼。須明瞭不健全之戀愛,最是引起感情衝動。而求饑不擇食之非法發洩,實足以戕害身心,等於磨刀使快,而後慢慢自削其骨肌,結果入於死亡悲苦之絕路。為何大學校中即罕有此種現象發現,此理簡單特甚,蓋年齡漸長,智理力健全,猛省過去了可羞無聊之錯誤,不待他人指正,即能幡然改革。因此中學時代之甜朋蜜友,一升大學之後,百分之八九十,都一變而成淡泊疏遠矣。至婚姻問題,簡略撮要而言之,婚姻必需經戀愛之過程中,譬如二人共建一屋,必須一德一心,始終負責,則此屋必堅固永久。否則一人負責,一人偷安,則難免強築成,亦必不能持久而中途崩潰也。
冰心有關同性愛的話題,直到四十年代仍然被媒體炒作,但是奇怪的是,1949年之後,甚至是在所有的冰心研究文章中,均未出現過這方面的內容。直到2012年冰心文學第四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後,青年女學者趙慧芳「在一個偶然的機緣中,筆者看到1936年第6卷第28期《玲瓏》雜誌上刊有一篇《冰心演講同性愛記》。」繼爾追溯到《慕真半月刊》上的《我自己的中學生活》,還查到了四十年代的那兩篇炒作的文章。趙慧芳女士對此發現,即驚喜又十分慎重,先後求證過多人,最後才成文發表,成為冰心研究的另一個「突破口」。之所以說是「突破口」,是因為冰心曾描寫過諸多女性,與許多女性成為一生知己,尤其有《關於女人》中,對十餘位女性的精彩描寫,在《我的教師》與《我的同學》中就涉及到「同性愛」的內容,但是沒有一個研究者從這個視角進行研究,包括在重慶國際學術研討會,創作於此的《關於女人》成為研討會的重要話題,但無一人言及「同性愛」三字。所以,當趙慧芳發現有關「同性愛」這一組文獻之後,她對冰心與女性的交往、冰心的《關於女人》等作品,便有了初步的新理解:
當我們由冰心演講而得知其同性愛經歷時,對《關於女人》中一些篇章的判斷就會複雜一些。實際上,這應該是一種意味深長的「易性寫作」:冰心是在以男士的身分重寫當年經歷過的同性愛情,試圖把當年的同性愛在易性表達中寫出,以達到既不逾規越矩、亦可告慰師友的效果。
冰心四年貝滿中學生活,尚可記載的還有:
一次是郊遊。先是坐了王祥的洋車到西直門,之後改騎小毛驢前往西山。婉瑩在煙臺騎過大馬,騎毛驢自不在話下,加上第一次出城郊遊,情緒亢奮,在上山的石板路上一路揚鞭馳騁,第一個到達目的地臥佛寺,很有一些她在習作小說中描寫過的女偵探與女英雄的氣概。這次郊遊並不是一個學校,由教會中的女青年會組織,有從包括從天津來的教會女校,冰心記得她們的衣著比貝滿同學講究、鮮亮。
二是課外綜合的訓練。琴、棋、書、畫,是舊時培養才女的四項標準,而一些大家閨秀常常具備這些涵養。翻開一部《紅樓夢》,金陵十二釵哪一位不是才藝雙全,琴、棋、書、畫樣樣精通?所以,富家女子,不一定接受仕途教育,但培養她們的才藝卻是普遍的。謝婉瑩在她的童年時代,對此便有了耳聞目濡,在她進入少女時代,家庭更是有意識培養。這個任務不是由她的父母親、也不是請了琴師、畫家面授,而是由革命黨人、小舅舅楊子玉來完成。楊子玉此前已從唐山路礦學校畢業,並且回到家鄉參加過福建的光復之役,辛亥革命之後,也到了北京,一方面從事有關的革命活動,一方面參加鐵路的測量工作。楊子玉在北京,謝家便是他的基本落腳點,而要將婉瑩培養成才女的任務便由他承擔。他鼓勵婉瑩學寫字,給她買了許多字帖,還說要先學顏真卿,以後轉學柳宗元、再學趙孟頫;給婉瑩買了顏料和畫譜,勸她學畫;買了很講究的棋盤和黑白棋子,教她下圍棋,通俗易懂地啟發她「圍棋不難下,只要能留得一個不死的口子,就輸不了」;還送給婉瑩一架風琴,在婉瑩初入貝滿中學時,交了學琴的費用。冰心雖然說她自己與琴、棋、書、畫結不上緣,但實際上這些教育影響了她的一生,給她優雅的人生之途平添了色彩。比如她的字清秀雋逸,晚年向她求字者眾,留下的書法作品,給她的喜愛者、研究者不盡的喜悅。
三是參加過反對「二十一條」的示威遊行。1914年到1918年,社會動盪,政壇像走馬燈似的變化無常,翻翻這幾年的大事紀便可知曉。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軍侵佔山東濟南、青島,袁世凱稱帝,袁死後黎元洪任總統、張勳復辟、段祺瑞執政等等,這些都不可能不影響到那怕是美國人辦的學校,影響到一個女學生平靜的校園生活。就在婉瑩入校的第二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提出了吞滅中國「二十一條」,袁世凱為了換取日本對他的支持,竟然接受了日本的要求。顯然,這種出賣國家與民族的行為,遭到了全國人民強烈反對,各地掀起了大規模的討袁抗日愛國運動。貝滿女校的同學也是群情激憤,沖出校門,與全北京的學生一起,彙入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謝婉瑩走在貝滿遊行的隊伍中,帶隊是齋四同學、學生會的主席李德全。
在萬人如海的講臺上,李德全慷慨陳詞,說:「別輕看我們中國人!我們四萬萬人一人一口唾沫,還會把日本兵淹死呢!」集會後,婉瑩交上了愛國捐,並與同學一道宣誓不買日貨。謝婉瑩滿懷悲憤回到家裡,見到父親沈默地在書房牆上貼上一張白紙,上用岳飛筆跡橫寫著「五月七日之事」六個大字。婉瑩與父親默默地站在橫披的下面,發誓永遠不忘這個國恥日!另一次是張勳的辮子軍進京。辮子軍紀律極壞,為了防止家人被騷擾,海軍少將不得不將家眷送到外地避難。謝葆璋選擇了煙臺,那裡還有他的部下與朋友,於是婉瑩在母親的庇護下,從塘沽乘船,到了煙臺,躲過了十二天的復辟鬧劇。如此的經歷,在中國的知識分子身上早早地烙下了時代與社會動盪的印記,從而引發出莊重的使命感與責任感。
第三章 一個女大學生的「五四」
1,煩悶的少女
辛亥革命結束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並且頒佈了具有資產階級民主精神的法令,這在中國的歷史上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但辛亥革命與後來的共產黨鬧革命不一樣,它不是徹底地告別一切,許多東西保持一定的延續性,僅從軍隊而言,基本是晚清的軍隊起義與改編,海軍尤甚。1912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任命的第一位海軍部總長便是長江艦隊臨時艦隊司令黃鍾瑛,晚清海軍部及各艦隊的許多官員,大都在原崗位任職。謝葆璋曾經任職的「海圻號」巡洋艦當時在英國...
作者序
引子
我在初夏一個陽光燦爛的晌午,漫不經心地翻看莫里循收藏的照片圖集,義和團、八國聯軍、毀於大火的正陽門箭樓、推著小車挑著擔子拉著黃包車的雜亂的人群,滿目瘡痍、斷垣殘壁中卻還依然有猛獅威蹲的漢白玉短牆。
這是一位叫凱利的牧師1900年拍攝的發生在北京的義和團事件的照片。莫里循先生在大使館被義和團圍困時,積極參與防守與戰鬥,曾救出與安置了被追殺的華人教民,本人也險些丟命,以至外界誤傳他已被殺。但他活著,並且收藏保存了記錄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許多照片。
開始確實有些漫不經心,因為那畢竟是一個世紀前的故事了。正陽門,現在稱之為前門的箭樓不是在天安門廣場的北邊巍然屹立麼?(記得有一年也是夏日的傍晚,我一個人站在箭樓下,看暮色中飛進又飛出的一群群蝙蝠與烏鴉,並沒有意識它曾經被毀。)但是,當「1900」這4個熟悉的阿拉伯數字不斷地跳顯在眼前時,我開始意識到了這一歷史事件、這些圖片中保留的歷史畫面,與我有了密切的聯繫。
我已經寫過好幾本冰心的傳記,但我認為那都不過是一些片斷與表象的描述,我也讀過好幾本冰心的傳記與評傳,有的雖還全面,但我認為那大多數是冰心人生與作品的演繹與解讀,甚至是某種的記錄。我認為,一本好的傳記,應該既入其中,又在其外,既是真實的也是藝術的,既是場景畫也是心靈史,既是史料的揭示也是自我的敘述。僅從真實、史料與製造場景原料的佔有而言,可以說,我獨一無二。但是我卻不敢動筆寫一本像樣一些的冰心傳或冰心吳文藻傳。
奇怪的是,我是在看了這些圖片之後,忽然有了想法,似乎明白該怎麼寫了。這不僅是因為這個事件中的教會、傳教士、庚子賠款等幾個關鍵字,將會不斷跳躍在他們的生命長旅中;更是因為這個事件代表著其後惡劣的生存環境,動盪、戰爭、苦難、鬥爭,再也沒有停止過,整整一個世紀多災多難,但是,一個柔弱女子,一介書生,竟然可以在漫漫長夜裡,盛開出燦爛而優雅的花朵?
引子
我在初夏一個陽光燦爛的晌午,漫不經心地翻看莫里循收藏的照片圖集,義和團、八國聯軍、毀於大火的正陽門箭樓、推著小車挑著擔子拉著黃包車的雜亂的人群,滿目瘡痍、斷垣殘壁中卻還依然有猛獅威蹲的漢白玉短牆。
這是一位叫凱利的牧師1900年拍攝的發生在北京的義和團事件的照片。莫里循先生在大使館被義和團圍困時,積極參與防守與戰鬥,曾救出與安置了被追殺的華人教民,本人也險些丟命,以至外界誤傳他已被殺。但他活著,並且收藏保存了記錄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許多照片。
開始確實有些漫不經心,因為那畢竟是一個世紀前的故事了...
目錄
序/李玲
引子
第一章 三坊七巷至大海
1,大家族中的女嬰
2,父親的巡洋艦
3,海邊的「野」孩子
4,十一歲之前讀過的書
5,詩人與燈檯守 >>> 038
6,大家庭中的女紅
第二章 揚子江至京城
1,揚子江岸的少年
2,清華園裡的莘莘學子
3,五四運動來了
第三章 一個女大學生的「五四」
1,煩悶的少女
2,教會女中的「同性愛」
3,五四驚雷,震上文壇
4,女性解放與《婦女雜誌》
5,燕大精神與《燕大季刊》
6,青春與《生命》
7,文學研究會與《小說月報》
8,泰戈爾與《繁星》、《春水》
9,靜美中的《惆悵》
10,反響
11,貢獻
第四章 留學美國
1,離愁別緒與《寄小讀者》初刊
2,上海的餞行與話別
3,橫渡太平洋
4,登上新大陸 >>> 203
5,初入校門
6,慰冰湖與閉璧樓
7,一病足惜―聖卜生醫院
8,一病足惜―青山沙穰
9,遨遊於新英格蘭大地的山水之間
10,「大江會」與《琵琶記》
11,綺色佳之戀
12,《漱玉詞》與《求婚書》
13,《寄小讀者》、《民族與國家》的出版與意義
第五章 燕園風采
1,Faculty Baby(教授會的娃娃)
2,曼哈頓的回應
3,臨湖軒的婚禮
4,初登講壇與燕園落成
5,死的哀傷與生的歡樂
6,雙峰:冰心作品的出版與研究
7,雙峰:吳文藻創建「燕京學派」
8,60號小樓的客人們
9,一樁公案的「東西南北中」
10,平綏沿線的旅行
11,燕園時期的小說
12,為「燕大之父」祝壽
13,環繞地球、遊學歐美
14,最後的燕園
第六章 抗戰歲月
1,艱難跋涉向雲南
2,雲南教育與民族建言
3,呈貢「默廬」
4,戰時對民主與制度的思考
5,因「民族問題」而中暗箭
6,重慶的「忙」與「擠」
7,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
8,《關於女人》及其它
9,心繫燕大、心繫社會學
10,山上山下
11,出訪印度與美國
12,戰後去向
第七章 旅居日本
1,戰後駐日外交官
2,日本的謝冰心旋風
3,日本房屋與美國精神
4,東京大審判、《菊與刀》、李香蘭
5,回國的謝冰心旋風
6,心情起了變化
7,繼續日本的文學活動
8,1948年的心境
9,未遂的起義
10,東京隱居
序/李玲
引子
第一章 三坊七巷至大海
1,大家族中的女嬰
2,父親的巡洋艦
3,海邊的「野」孩子
4,十一歲之前讀過的書
5,詩人與燈檯守 >>> 038
6,大家庭中的女紅
第二章 揚子江至京城
1,揚子江岸的少年
2,清華園裡的莘莘學子
3,五四運動來了
第三章 一個女大學生的「五四」
1,煩悶的少女
2,教會女中的「同性愛」
3,五四驚雷,震上文壇
4,女性解放與《婦女雜誌》
5,燕大精神與《燕大季刊》
6,青春與《生命》
7,文學研究會與《小說月報》
8,泰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