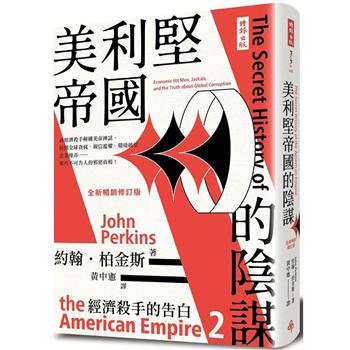第一章 《三國志演義》的史傳淵源
第一節 史傳‧小說‧歷史小說
史傳與小說乃至歷史小說三者的關係頗為複雜,也是學界頗有爭議的大問題。本文限於課題範圍,只能作概略闡釋,在逐層深入的論述中,焦點還是在《三國演義》與史傳的關係上,目的是要從史傳的角度切入,以透視《三國演義》的史傳淵源。
一、中國小說與史傳
信史或曰正史,是指所記史事總體上真實可信的史傳。中國的史傳典籍汗牛充棟,蘊藏著極為豐富的文化內容與無比巨大的精神能量,具有廣遠的涵蓋面。它以神話歷史化的思維方式,吞噬了上古神話,使其成為史傳中的組成部分;它孕育了中國小說,成為小說的源頭之一。甚至連「六經」也幾乎脫不開它的籠罩,歷史上就不斷有「以經為史」的呼聲,作還經書為史籍的努力。「六經」是凝聚和沉積著中華民族觀念、意識、思想精神的文化元典,屬經典文化的範疇。史傳連「六經」都能涵容,足見其文化蘊涵之豐厚深邃。因此,從總體上說,中國的史傳也應屬於經典文化的範疇。
從文化傳統與敘事傳統的發展嬗變角度說,史傳上承神話,下開小說,開闢了中國小說的獨特發展道路,影響著中國小說的文化內涵。
從文化傳統的層面上看,受著經典文化濡染的史傳作者,將其文化觀念與審美理想傾注進史傳之中,潛移默化地引發同受經典文化影響的小說作者的心理共鳴,影響其所撰小說的文化內涵與審美趣味。同時,史傳作為文化元典的組成部分,作為經典文化的形象化、具體化,作為經典文化的載體之一,其對小說作者乃至小說讀者的文化觀念具有著延展性的代代承傳的巨大而深遠的影響,而廣大讀者的文化觀念反過來又影響著小說作者的文化心理,這種交叉影響便使史傳的文化內涵輻射加倍增值,同時也藉助讀者這個媒介,使經典文化與大眾文化達成某種對流與交融。
中國小說始終把道德評價置於首位,注重忠義觀念的弘揚,注重是非善惡的甄別,注重興亡治亂意識的寄寓,注重功名利祿追求的實現……,皆有著史傳的直接影響。而此前小說研究界卻往往只注重「六經」等儒家經典及莊老佛禪對小說文化內涵的影響,忽略了同為經典文化、同應屬文化元典的史傳在文化傳統上對小說內涵的影響,而後者恰恰是經過史家對文化元典的消化、理解、吸收、認同,又寄寓在歷史人物事件之中的心理再創造過程,因而其影響更為直接、更為形象、更為具體,更加心悅誠服而不可抗拒。
在敘事傳統的層面上看,史傳之影響小說,主要表現在敘事、結構、表達方式與語言風格諸方面。劉知幾曾將史傳的敘事方式概括為「直紀其才行」、「唯書其事蹟」、「因言語而可知」、「假贊論而自見」(《史通》卷六《敘事》)四種方式,這恰是小說描寫、敘述、對話、議論四者之所自。另外,史傳在採用第三人稱全知視角的敘事模式與運用順敘、倒敘、插敘、平敘等敘述方式上,也為小說提供了可供模仿的敘事經驗。
史傳諸多結構方式中以編年與紀傳二體為主,這也為後世中國長篇小說情節結構的類型模式提供了可資借鑑的經驗。後世長篇小說的結構方式,或採編年體,或用紀傳體,或二者兼而有之,溯其源,皆是在史傳基礎上的再創造。
史傳的表達方式既包括史家主觀傾向的表達方式,也包括修辭技巧與語言風格。主觀傾向的表達主要有司馬遷開創的「寓論斷於序事」的方法與劉知幾概括的「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的原則。這影響著小說作家將主觀評價寓含在敘事中傳達給讀者,而不是直接說出來,也影響著小說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時注重其多面性與複雜性。修辭技巧在比喻、對比、排比、對偶等語言表達技巧上,也給後代小說提供了豐富的範例。
史家語言風格或言簡意賅,文約意豐;或文采斐然,形象生動。前者以陳壽的《三國志》為代表,後者以司馬遷的《史記》為典型。二者皆對中國小說語言風格的形成有著不可低估的示範作用。相比之下,後者的影響顯然要更大一些。這方面的研究,此前關注的還不夠,值得進一步作細密化研究。
二、歷史小說與史傳
從概念、範疇的界定上說,史傳與歷史小說屬於不同範疇的概念,前者是史學概念,屬歷史學範疇,後者是文學概念,屬文學範疇。這是二者的根本差異。但史傳也有一定的文學性,如《史記》等史傳的文學價值還相當高,給歷史小說以諸多方面的影響,而歷史小說也要接受史實的規範與制約,這又使二者有了相通性與聯繫性。
從寫作者的主觀評價說,史家與小說家皆要運用歷史評價與道德評價這兩把尺,這是二者之同。若細加比較,史家是歷史評價第一,道德評價第二,即求真兼善,在言直事核的前提下寓褒貶、別善惡,司馬遷、班固、陳壽、司馬光莫不如此。而歷史小說家則是道德評價為主,歷史評價為輔,是求善兼真,羅貫中及步其後塵的歷史小說家基本上皆遵循此原則。這又是二者的同中之異。
從所寫內容與史實的關係說,史傳是實事求是,只有選擇史料的餘地而無虛構的權利;歷史小說是實事求似,允許想像和虛構。這正如萊辛在《漢堡劇評》中所指出的:「劇作家並不是歷史家;他的任務不是敘述人們從前相信曾經發生的事情,而是要使這些事情在我們眼前再現;讓它再現,並不是為了純粹歷史的真實,而是出於一種完全不同的、更高的意圖;歷史真實不是他的目的,只是他達到目的的手段;他要迷惑我們,從而感動我們。」這可以借用來評價中國史家與歷史小說家的區別,也是二者的顯著差異之一。
從相通與聯繫的角度說,史傳與歷史小說的關係,除具有上面所論史傳與一般小說關係的共性之外,還有其個性化的特殊關係。約而言之,似可歸結為以下幾點:第一,史傳為歷史小說的情節建構提供了歷史事實的整體框架。第二,史傳為歷史小說的人物形象塑造提供了群體形象系統,描繪了主要人物的整體面貌及主要思想性格特徵,敘述了一系列人物的人生歷程,提供了評價人物的標準、依據及基本傾向。第三,史傳為歷史小說的材料取捨提供了史料剪裁的方法與處理虛實的原則……比較而言,歷史小說與史傳的關係,顯然比一般小說還要密切。如曰史傳為一般小說之淵源,那麼史傳則為歷史小說的母胎。因此,我們既要看到歷史小說與一般小說的共性,也要把握其獨特的個性。關於這一點,劉敬圻教授在《困惑的明清小說》中有一段精闢的論述:「歷史小說自然是『小說』而不是歷史,它鼓勵藝術想像和虛構,這是歷史小說與一般小說所共有的屬性。但歷史小說又畢竟與歷史有不解之緣,它有必要接受最基本的事實規範與制約,這一點,則是歷史小說不同於一般小說的獨特個性了。」這無疑是具有理論指導意義的。
三、《三國志演義》與史傳
遍觀中國小說史,《三國志演義》具有獨特的歷史地位,它與史傳的關係最具典型性。作為中國第一部長篇小說,它充分體現出一般小說與史傳的關係,而作為第一部長篇歷史小說,它又典型地代表著歷史小說與史傳乃至與文化的關係,因此,本文即以它為個案來透視,期以個別而見一般。而探索其源流演變之關係,又必須從史傳入手。
中國歷史上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是有史載以來的春秋列國、楚漢之爭後的又一個分裂時期。「亂世出英雄」,群雄蜂起、逐鹿中原的亂世,尤為世人矚目,亦是小說家最喜演義講說的時代。相比之下,「當時多英雄,武勇智術,瑰偉動人,而事狀無楚漢之簡,又無春秋列國之繁,故尤宜於講說」(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三國志演義》的作者羅貫中乃是「據正史,采小說,證文辭,通好尚」(高儒《百川書志》),創作出了中國第一部長篇小說。因此,要追溯《三國志演義》之源,還須從正史入手,這個正史即是陳壽的《三國志》、裴松之的注釋與《資治通鑑》中的三國歷史部分。
亂世雖為小說家提供了好素材,但對史家來說,修亂世之史要比治世難度大得多。陳壽面對史料匱乏的困難,發揚了中國史官的優良傳統,既追求秉筆實錄,又「寓褒貶,別善惡」,並以「文質辨洽」的表達書寫出來,從而將求真、兼善、言文三者辯證地統一了起來。後繼者裴松之的注釋與司馬光《資治通鑑》的「三國」部分,在保持其求真兼善的同時,又進一步豐富了其文學色彩。總而言之,《三國志》、裴注與《資治通鑑》這三者對羅貫中創作《三國志演義》影響甚鉅。有鑑於此,本章所要論析的重點亦集中於此三者。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三國演義源流研究 上編:成書研究的圖書 |
 |
三國演義源流研究上編:成書研究 作者:關四平 出版社:龍視界 出版日期:2015-01-10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62頁 / 25k正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79 |
文學 |
$ 294 |
中文書 |
$ 295 |
中國古典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三國演義源流研究 上編:成書研究
本書立意新穎,構架恢弘,視野開闊,資料豐贍,論證嚴謹精當,時有精闢之論,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多有創新,是《三國演義》與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新收穫。
本書是一部具有開拓性意義的學術力作,首次將《三國演義》的成書、文本與傳播作為一個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整體,進行全方位的系統的考察與研究,力圖在中國文化流變的大背景上,探求這一文學和社會精神現象的形成機制,及其所包含的文化意蘊與美學特質,揭示其文化史意義,進而從特定角度與側面觀照中華民族追求真善美的心路歷程,總結中國長篇小說演進的某些規律性內容。上編四章為成書研究,著重探討三國題材演化史中史傳、傳說、講史、詩歌、戲劇等各個環節所蘊含的文化意蘊與美學特徵及對《三國演義》成書的影響。
作者簡介:
關四平,祖籍山東省平度市,1953年生於黑龍江省綏化市。1987年畢業於哈爾濱師範大學中文系,獲文學碩士學位;1999年畢業於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獲文學博士學位。現任哈爾濱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文學院院長。
關四平主要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在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上用力尤勤。著作主要有:《后妃的命運》(1991年)、《中國古代文學叢論》(1999年)、《三國演義源流研究》(初版於2001年)、《中國古代禁毀小說漫話》(合著,1999年)。校點有:周曰校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合作,1994年)、《中國才子佳人小說精選》(合作,1994年)、《太平廣記》(合作,1995年)。此外,在《文學遺產》、《文藝研究》、《紅樓夢學刊》、《明清小說研究》、《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文摘》等報刊發表學術論文多篇。社會兼職主要有:中國三國演義學會副會長、中國紅樓夢學會理事、中國西遊記文化研究會理事、黑龍江省紅樓夢學會秘書長。
章節試閱
第一章 《三國志演義》的史傳淵源
第一節 史傳‧小說‧歷史小說
史傳與小說乃至歷史小說三者的關係頗為複雜,也是學界頗有爭議的大問題。本文限於課題範圍,只能作概略闡釋,在逐層深入的論述中,焦點還是在《三國演義》與史傳的關係上,目的是要從史傳的角度切入,以透視《三國演義》的史傳淵源。
一、中國小說與史傳
信史或曰正史,是指所記史事總體上真實可信的史傳。中國的史傳典籍汗牛充棟,蘊藏著極為豐富的文化內容與無比巨大的精神能量,具有廣遠的涵蓋面。它以神話歷史化的思維方式,吞噬了上古神話,使其成為史傳中的組成部...
第一節 史傳‧小說‧歷史小說
史傳與小說乃至歷史小說三者的關係頗為複雜,也是學界頗有爭議的大問題。本文限於課題範圍,只能作概略闡釋,在逐層深入的論述中,焦點還是在《三國演義》與史傳的關係上,目的是要從史傳的角度切入,以透視《三國演義》的史傳淵源。
一、中國小說與史傳
信史或曰正史,是指所記史事總體上真實可信的史傳。中國的史傳典籍汗牛充棟,蘊藏著極為豐富的文化內容與無比巨大的精神能量,具有廣遠的涵蓋面。它以神話歷史化的思維方式,吞噬了上古神話,使其成為史傳中的組成部...
»看全部
目錄
序言 李時人
前言
第一章 《三國志演義》的史傳淵源
第一節 史傳‧小說‧歷史小說
一、中國小說與史傳
二、歷史小說與史傳
三、《三國志演義》與史傳
第二節 肇始奠基的三國史元典
一、以實錄精神寫史
二、寓褒貶論斷於事
三、豐厚的文化意蘊
四、運奇筆再現奇人
第三節 添枝加葉的注釋與增補
一、史實綱目的情節化
二、人物形象的立體化
三、褒貶方式的多樣化
第四節 兼收集成的三國史編年
一、串珠成鏈的系統化
二、敘事藝術的典範性
三、錦上添花的形象化
四、結論和餘論
第二章 野史傳說中的小說因素
...
前言
第一章 《三國志演義》的史傳淵源
第一節 史傳‧小說‧歷史小說
一、中國小說與史傳
二、歷史小說與史傳
三、《三國志演義》與史傳
第二節 肇始奠基的三國史元典
一、以實錄精神寫史
二、寓褒貶論斷於事
三、豐厚的文化意蘊
四、運奇筆再現奇人
第三節 添枝加葉的注釋與增補
一、史實綱目的情節化
二、人物形象的立體化
三、褒貶方式的多樣化
第四節 兼收集成的三國史編年
一、串珠成鏈的系統化
二、敘事藝術的典範性
三、錦上添花的形象化
四、結論和餘論
第二章 野史傳說中的小說因素
...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關四平
- 出版社: 龍視界 出版日期:2015-01-10 ISBN/ISSN:978986573283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62頁 開數:14.8*21 cm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中國古典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