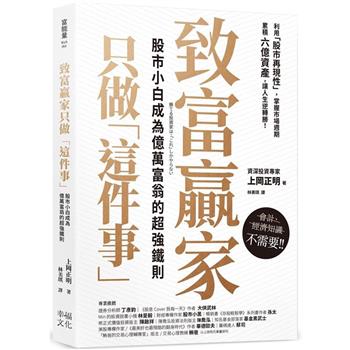一 多少素箋寄深情——沈從文與張兆和
捲簾又見春風,春風已忘了舊顏。人世間,還是山長水遠,迢遞高城。你看,天空依舊明藍,大地依然廣博,那個曾懷揣愛情和夢想,仰望北平的天空只想下跪的人,卻已如煙霓消逝無蹤。
——「我一個人在船上,看什麼總想到你!」
——「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雲,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
——「望著北平高空明藍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給我的影響恰如這天空,距離得那麼遠,我日裡望著,晚上做夢,總夢到生著翅膀,向上飛舉。向上飛去,便看到許多星子,都成為你的眼睛了。」
彼時,他那麼年輕英俊,他噴薄的才華如朝陽初升,在思潮紛湧的民國年代,點燃了無數仰慕的心;那個被他愛著的女子,也正明媚青蔥,她像一隻黑鳳掠過他的眼簾時,便落在他的心底,成為一生永不褪色的美麗虹影。
他是從邊城鳳凰走出的才子沈從文,而她,是他的月亮,張兆和。
不知為什麼忽然愛上了你
被冷落的情書
是誰說過,當愛情來臨,往往我們不懂愛情。
一朵花悄然開了,美得心驚。她自己尚不知覺,卻灼痛了愛她的那顆心。刻骨銘心地愛一個人,心是會痛的,儘管,他願意這樣不計後果地為她燃燒,願作那劫後灰燼。
我無數次想,被他這樣用心愛著的那個女子,是何其幸福。
一九三○年二月的某一天,對名門閨秀張兆和來說,是她一生情緣美麗的起點。這天以後,她成了愛情傳奇中風華絕代的女子。
在這個尋常冬日,一封信,輾轉抵達她的手中。她展信來讀,開頭第一句便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忽然愛上了你。」信的落款人是沈從文。
我無法揣度半個多世紀以前那個妙齡女子的心思。以我現在的感覺去想,若換了別一個姑娘,那一刻,一定會有一個盛大的春天,鋪滿了她整個身心,在她心底捂不住地要發芽。
但這個姑娘偏偏是張兆和。這個臉龐微黑、清麗俊秀的女子,彼時是上海吳淞中國公學的學生,一個習慣了在無數追慕者的熱烈眼神中淡然自處的美麗姑娘——世家門第合肥張家的三小姐。
她讀著那封浸滿愛意輕愁的信,沒有懷春女子的驚喜,眉端輕鎖的,是不知所措的苦惱。這個追求者不同以往那些青澀的學子,他是中國公學主講現代文學選修課的年輕講師,張兆和不只一次去聽過他的課。
而在此之前,沈從文三個字,已在中國文壇聲名鵲起。
彼時,正逢沈從文最好的年華,他在最好的年華中飽經歷練。人世的張皇局促、生命的無常悲喜,他在生養他的湘西,在童年少年的成長歲月中,已盡數品嘗。這些浸滿生命血淚的體驗,像一塊黑色土壤中的養分,滲進他的血脈,滋養著他敏銳的心靈,使他的創作豐富靈動,也使他整個人,有了深度和內容。
這樣的年輕男人無疑是有魅力的。青布長衫,英俊儒雅,鼻梁上架一副眼鏡,鏡片後的目光深邃朦朧,有滄桑的閱歷,也有正正好的風華年歲,當他在校園裡穿行,就像他筆下的作品曾打動了無數讀者那樣,也不難打動女孩的心。
在當時,沈從文的外形算得上儒雅出眾,因為早在幾年前,丁玲就曾聽胡也頻說沈從文「長得好看」,一起專程去北京沈從文的「窄而霉小齋」看望過他。
然而這一切對兆和小姐來說,都不足以令她怦然心動。她並非不懂這個男子的好,只是她情感的成長稍許有些遲慢。
她是那枝伸出籬外的帶露花蕾,春風愛了她,忍不住來輕吻,蝴蝶也戀了她,止不住為她蹁躚,她卻只顧酣甜地,沉沉睡在夢裡。關於愛情的萌動風情,她的情竇尚未開啟。
因而,像對待此前任何一封求愛信一樣,對年輕老師的示愛,張兆和選擇了沉默不應。
沈從文的第一次愛情告白,雖如初陽,如暖風,卻無法照徹他愛著的這個女子,無法拂開她的心扉。
這個冬天,依然蕭寂寒冷。窗外的老牆下,衰草枯黃,藤蘿懸壁,沈從文耐著性子和它們一起,等待春的訊息。
佳人的回音遲遲不來。萬般痛苦的沈從文又接二連三給張兆和寫了多封情書,均石沉大海杳無音訊。
他離她這樣近,在中國公學,他幾乎每天都能見到這個面龐黑黑、俏麗沉靜的女學生。在他眼底,她純淨如一枝水蓮,千種芳菲在她面前,都作了背景和陪襯。見了她,他似乎看見故鄉的沱江和清澈的沅水,以及他動盪不寧卻無比親切的青春少年。
他為她著了魔般,一想到她,他的心便又溫柔又疼痛,彷彿整顆心都被她生生地掠奪捲走。這個喝湘西水長大、經歷過漂泊磨難、又奇蹟般崛起於中國文壇的年輕人,為一個女學生,陷入了煉獄般的單相思。
多年後,回首這段不盡如人意的初逢,會有微笑在心底綻開:原來,這一切,皆是一種成全。
命中註定,他們的情緣,要以這樣的方式開始。
佛說,前生五百次的凝眸,方換得今生一次擦肩。那麼佛有沒有說過,要多少次的人海擦肩,才能換得今生的相遇結緣?他和她相遇,必是那前世註定,無論曲曲彎彎錯過多少風景,最終都會相逢在同一座橋上,默默對視。
所謂緣,是千絲萬縷織就的那張網上,必然要連綴的結;是繁複迷宮中,必定會相逢的曲徑。這樣那樣的安排,坦途也好,迷障也罷,都是通往終點的必經之路。
沈從文日思夜想的,是能夠被張兆和接納;但同時這個女子對他的緘默疏遠,和骨子裡的淡定孤傲,對他又是致命的吸引。他痛苦著她的冷漠,卻又為這冷漠而著迷。
能被他看上的女子,必然是生在崖壁上的仙草,脫俗孤清難以企及,他才會愈發珍惜。
這或是他愛上她的理由。也或者是上蒼的刻意安排。
這個沅水邊曾經的少年,他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完成了成長歷程,然後翻越千山萬水,歷盡世事浮雲,最終來到上海教書……似乎所有的前事鋪墊,都只為了這一刻的來臨——像一株臨風碧樹,出現在她的面前。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他們曾這樣相愛:在最好的年華遇見你(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168 |
文學小說 |
$ 252 |
傳記 |
$ 266 |
中文書 |
$ 266 |
現代散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他們曾這樣相愛:在最好的年華遇見你(上)
我不必問什麼地方是天堂,我業已坐在天堂門邊。 ──沈從文
……我無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淚流到你的墳頭,直到我不能來看你的時候。 ──石評梅
……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
……何日飛故里,不作寄籬人。 ──潘玉良
……我將於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徐志摩
此刻若問我什麼最可怕,我說:氾濫了的情感最可怕。
──蕭紅
不知所由的一往情深
觸動你我靈魂的最深處
本書分為上下冊,選取了五對風華絕代的名人,有沈從文與張兆和、徐志摩與陸小曼/林徽因、石評梅與高君宇、蕭紅與蕭軍、潘贊化與潘玉良等五對才子佳人。
通過他們的文字,讓我們重回當下去感受他們最真、最深的情感,讓這些最真的愛,觸動你我心靈的深處。
作者簡介:
張詩群,安徽繁昌人。安徽省作家協會會員,蕪湖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已出版文集《陌上清歌》、《相思樹上合歡枝——李商隱的詩歌人生》、《張詩群散文集:初夏》、《浮生六記——浮生與溫暖》等多種。現供職於某文化單位。
章節試閱
一 多少素箋寄深情——沈從文與張兆和
捲簾又見春風,春風已忘了舊顏。人世間,還是山長水遠,迢遞高城。你看,天空依舊明藍,大地依然廣博,那個曾懷揣愛情和夢想,仰望北平的天空只想下跪的人,卻已如煙霓消逝無蹤。
——「我一個人在船上,看什麼總想到你!」
——「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雲,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
——「望著北平高空明藍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給我的影響恰如這天空,距離得那麼遠,我日裡望著,晚上做夢,總夢到生著翅膀,向上飛舉。向上飛去,便看到許多星子,都...
捲簾又見春風,春風已忘了舊顏。人世間,還是山長水遠,迢遞高城。你看,天空依舊明藍,大地依然廣博,那個曾懷揣愛情和夢想,仰望北平的天空只想下跪的人,卻已如煙霓消逝無蹤。
——「我一個人在船上,看什麼總想到你!」
——「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雲,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
——「望著北平高空明藍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給我的影響恰如這天空,距離得那麼遠,我日裡望著,晚上做夢,總夢到生著翅膀,向上飛舉。向上飛去,便看到許多星子,都...
»看全部
作者序
自序
江南的柳絮已開始四處飄飛了。
這是一年中最馨柔和暖的季節。每日我走在小城的豔陽下,像一尾魚游在春光裡。天空淺藍,仰臉去看,直教人心若潮起,胸間彷彿生出了一雙翅,撲喇喇地要帶人飛去。
春日遲遲,莫負煙景。城中的峨溪河,荒天寒地沉睡了一冬,楊柳風一吹,便醒了,似一匹新緞,軟柔柔鋪展開,在兩岸初綠新紅簇擁下,浮淺淺一層細紋,一路凌波微步的,直向那春水盡頭掠去。那份明澈動人的嬌羞,像二八佳人,很有些思緒撩人。
街角,一株泡桐,高與樓齊。四望裡的街市,只獨獨那麼一棵樹,一整個冬天就那...
江南的柳絮已開始四處飄飛了。
這是一年中最馨柔和暖的季節。每日我走在小城的豔陽下,像一尾魚游在春光裡。天空淺藍,仰臉去看,直教人心若潮起,胸間彷彿生出了一雙翅,撲喇喇地要帶人飛去。
春日遲遲,莫負煙景。城中的峨溪河,荒天寒地沉睡了一冬,楊柳風一吹,便醒了,似一匹新緞,軟柔柔鋪展開,在兩岸初綠新紅簇擁下,浮淺淺一層細紋,一路凌波微步的,直向那春水盡頭掠去。那份明澈動人的嬌羞,像二八佳人,很有些思緒撩人。
街角,一株泡桐,高與樓齊。四望裡的街市,只獨獨那麼一棵樹,一整個冬天就那...
»看全部
目錄
一 多少素箋寄深情——沈從文與張兆和
不知為什麼忽然愛上了你
美麗總是愁人的
愛君筆底有煙霞
二 無窮紅豔煙塵裡——石評梅與高君宇
在錯的時間,遇見對的人
她只要冰雪有情
情歸陶然亭
三 知君用心如明月——潘玉良與潘贊化
風塵劫,風塵緣
君心相待似月明
為了愛,成全愛
不知為什麼忽然愛上了你
美麗總是愁人的
愛君筆底有煙霞
二 無窮紅豔煙塵裡——石評梅與高君宇
在錯的時間,遇見對的人
她只要冰雪有情
情歸陶然亭
三 知君用心如明月——潘玉良與潘贊化
風塵劫,風塵緣
君心相待似月明
為了愛,成全愛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張詩群
- 出版社: 龍視界 出版日期:2014-12-24 ISBN/ISSN:978986573285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38頁 開數:14.8*21 cm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