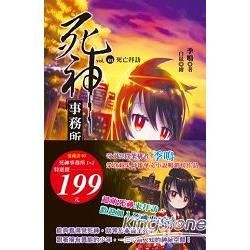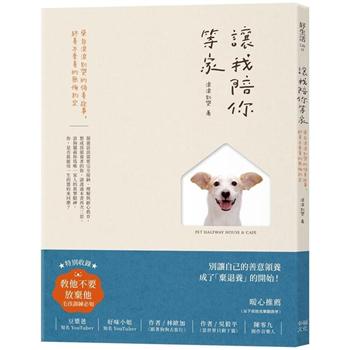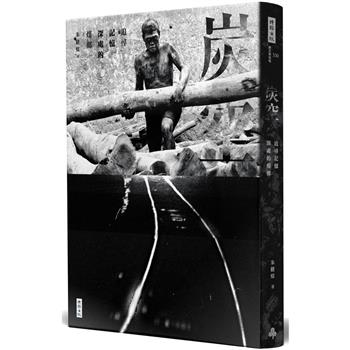序章
故事該從哪裡開始講起呢?
雖然有點倉促,但我的生命現在正受到威脅。
一把黑色短刀指著我的脖子,隨時都有朝喉嚨劃下去的可能。
是碰上搶劫嗎?還是遇到殺人犯?
並不是。
拿刀對準我的人,從他身上散發出一種非人氣息,不管是髮色還是是瞳孔,怎麼看都不像是生活在現實世界裡的人。
不只是人,就連身處的環境也很莫名其妙,放眼望去是一片死灰,空間裡不管是頭上頂著或是腳下站著的,都是呈現出混濁的灰色。
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得不作出選擇,要不就是生,要不就是死,非常兩極化的抉擇。
「如果不願意,那麼我手上這把刀可就不留情了。」
那個人是這麼說的,拿刀挾持我的他,臉上露出理所當然的笑容,彷彿這麼作對他來說一點都不需要猶豫。
「我也很無奈,上頭的命令是將見死者抹殺掉,但因為你對我們來說還有點用處,所以我們要求將你留著,但條件就是你得加入我們。」
然而這個空間裡存在著另外一個人,那人在我的印象中只是一個再平凡不過的普通人,但是現在,他已不再是我所孰悉的那個人了。
他們的穿著清一色都是黑色西裝,嚴肅與慎重簡直成了他的座右銘。
這是你們的工作嗎?因為是工作,所以導致你們非得這麼作不可?
完全想不出個所以然,直到現在我還是處在狀況外,一大堆從來沒遇過的鳥事卡在腦袋裡無法消化。
然而現在似乎已經沒有時間讓我去慢慢了解。
因為我必須給他們答案,要與不要兩者之間選其一。
為什麼我得這麼作?為什麼我得接受這樣的事實?
這使我困惑不已。
此時此刻只知道一件事。
——我似乎擁有什麼特殊的能力。
一種就連創造生物的神也為之忌諱的能力。
第一章 貓
1
在一間人潮逐漸疏散的教室裡,黃昏的光芒透過四角窗戶滲進教室裡,斜角的光線映照著桌椅。
天氣逐漸由秋轉冬,一到傍晚便會帶有絲絲涼意。
「嚴翔!今天要不要去書店逛一下,聽說今天有出很多新的漫畫哦!」
一位少年對著正在收拾書包的我說道。
嚴翔,是的,那是我的名字。
服裝儀容完全不符合校規,白色襯衫沒有繫在褲子裡,反倒是整個拉出。領帶在一下課的同時便馬上卸下,像是非常厭惡繫領帶一樣。西裝外套的鈕扣沒扣,下擺就這樣讓尾端隨著自己的動作擺動。
如果從老師的那傳統觀念角度來看當然是百分之百的不良學生,不過實質上只是我得穿著比較邋遢罷了。
而在我旁邊跟我一樣有著不良少年封號的人名叫做司馬隆俊,是我幾個月前交到的朋友。
為何要說幾個月前呢?
因為幾個月前,原本因為父親工作緣故而跟著他似乎奔波轉學的我,突然被扔回台南市老家,才剛念完高一的我,就這樣進入了這間私立基督教學校就讀。
隨之而來的課業壓力幾乎讓我放棄了英文數學。
然而跟我一起參加英數擺爛小隊的,就是司馬隆俊。
他是住在我家隔壁一家茶房老闆的兒子,那老闆跟老爸事舊識,既是鄰居又是同班同學,交到這朋友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總之,那是一段故事。
在聽到隆俊的邀請,我的表情開始有些不自然,應該說僵硬比較貼切。
老實說我有輕微的公共場所恐懼症,這似乎也是拜常常跟著老爸四處奔波所導致。
當然這件事司馬隆俊並不知道。
「嗯……今天有點不舒服,你就自己去吧!」
隆俊聽了露出一副不可思議的表情。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有沒有聽錯,咱們一向健壯如牛的空手道大師兄竟然也會生病?」
「我也是人好唄!就這樣!今天就不坐你的摩托車了。」我白了隆俊一眼。
我對大師兄這名詞感到排斥,不過腦袋隱隱作痛是事實。
「好好好,那我先走了,明天開始就放寒假了,到時候再看要去哪裡玩,順便帶你那女朋友一起吧!」說著,隆俊比出了小拇指。
「就說了我們不是!」
這傢伙擺明在消遣我,他拉起書包便向門口快步跑去。
「你才是哩!可別在書店看A書看到誤了補習的時間。」
總覺得作這種反擊讓我更感無力。
現在的時間是學生們的放學時段,廣闊無盡的天空,因夕陽的光芒而染成一片橘紅,被宣染成淡淡紅色的雲朵在天空緩緩飄浮著。
明天起,將會有整整兩個禮拜的假期。
腦袋又開始隱隱作痛,看來真的是感冒了。
教室裡的人走得快差不多了。
將書包往腋下一夾,又檢查了一下抽屜裡有無殘留尚未收拾的物品,在確定東西收拾好之後,我便離開了教室。
這陣頭疼非比尋常,跟以往有點不一樣,甚至一度懷疑,自己是否生了什麼大病。
邁出大門,看著車水馬龍的街頭,我不免有些後悔,要從學校走到家裡,大約得花三十分鐘的路程。剛才真不該拒絕隆俊的好意。
平時上下學不是被他載,就是騎自己的自行車。
很少會有徒步的情況發生,今天就是特例之一。
三十分鐘對現代居住在都市裡的人們而言是很累的。
更別說是在身體不適的時候了。
不過天下間沒有後悔藥可以吃,抱怨的同時,也得踏上回家的路。
來到離自己家附近的公園。
因為打算抄近路回家,於是想拐個彎走進公園。
但現在,公園門口擺了塊施工中的牌子。由此可見裡頭人行道正在進行施工。不得已只好繞道而行,我改走公園外圍的人行道。
只不過人若走霉運,那麼倒楣事一天下來絕對不可能只碰到一次。
一輛救護車剛剛好停在公園外的人行道旁,公園四周圍幾乎都是住宅,湊熱鬧的住戶都在那圍觀,因此阻擋到了去路。
「搞什麼啊……真是……」
自然沒有興趣去那人擠人,我一心只想快點回家休息。
「不管了,抄捷徑。」
要從入口進入公園還得繞更遠的路,這等於是在考驗本大爺我的耐性。
也不管維修中的路道是否有危險,用手撐住高度差不多只到自己腰部的公園圍欄,二話不說直接翻了進去。
「嘿嘿!入侵成功。」
邁開步伐,快步地走在公園的步道上。
朝著外面剛剛救護車所停放的方向看去,圍觀的人似乎又增加了許多。除了人們互相討論,嘰嘰喳喳的聲音以外,比起那些,音量更大的應該就是那有如失去親人一般的痛哭聲。
「哭成這樣,那邊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不想聽卻還是聽見的哭聲,我不予理會,繼續朝著自己家的方向走。
就在經過涼亭的榕樹旁時,意外發現榕樹下,趴著一隻從來沒見過的黑貓。
黑貓注意到那外來的視線之後,與我兩眼視線相交。
「奇怪了,這附近什麼時候有隻黑貓?我怎麼都沒看過。」
不是我自誇,我自認對這附近一向很熟悉,就連平常生活在這裡的小動物有哪些,一貓一狗都一清二楚。
大概是路過的吧。我下了一個定論。
就像是被黑貓眼神所誘惑般,我慢慢地朝著那方向走去。
黑貓也知道有人正逐漸向牠靠近,不但沒有畏懼或是逃開的舉動,反而隨著我的移動,碧綠色的瞳孔也隨之慢慢上仰,看著距離與自己越來越接近的我。
「這小傢伙真特別,牠竟然不怕生。」再走進一點看看,這種毫無惡意的動機,我甚至在短短幾秒內忘了頭疼以及任何不舒服。
就連眼睛都不眨一下,貓兒彷彿雕像般動也不動,縱使我與牠已經只剩下一大步的距離了。
漆黑的身體依舊無動於衷,在與黑貓四目相交時,只感覺這隻黑貓帶給人有種不可思議的神秘感。
對了,記得中午的午餐好像還有喝剩下的牛奶。
也不知道今天哪根筋不對,中午時我去福利社買了瓶裝牛奶,但因為不合我胃口,所以便收起來了。
二話不說掀開書包,從裡頭拿出瓶裝牛奶。
因為頭疼的緣故,冷不防一陣痛楚在腦袋裡翻攪。
「該死,頭又開始在痛了……」
手貼著臉,一邊身子壓低,連看都沒看就將牛奶瓶放置在小黑貓的面前。
「請你喝吧!」
說完便轉過身子想離去。
不過此時我才驚覺……
「我是腦袋燒壞了還是頭殼壞去啦!貓怎麼可能喝的了瓶裝牛奶,更何況我連蓋子也沒打開…」
方才根本沒有想到這一點,應該說,是完全沒有考慮到這種邏輯問題。
正在為這種舉止感到可笑時,猛然將頭一轉。
「……咦?」
「奇怪?貓勒?」
原本還在樹下的小黑貓,才短短幾秒的時間,宛如空氣般消失了。
更令人為之驚奇的是,原本瓶子裡應該還殘存一半以上的牛奶存量,現在卻倒在旁邊,裡頭連一滴液體都沒有。
我對眼前所發生的怪異現象感到困惑。
或許是小黑貓自己想辦法喝掉了吧。
貓是很聰明的動物,這點我可是再清楚不過。
並沒有多想,只是自嘲的以為「小黑貓大概是被自己的舉動嚇跑了吧?」
又走了幾步路,這時才發現,事件發生的地方竟然就在面對自家門口的左邊隔壁。
這下原本想安安靜靜的睡上一覺,被這群人以及救護車的吵雜聲一弄,看來是沒辦法獲得寧靜了。
來到家門口,發現一位年約四十、下巴留著一撮鬍子的中年大叔站在自家鐵捲門前面。
我走到他旁邊。
「司馬叔叔,那邊發生什麼事了,怎麼左右鄰居通通都跑出來看熱鬧?」
「哦!阿翔你回來啦。」先是打了聲招呼,鬍子大叔以重低中帶有點沙啞的嗓音接著說:「其實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只是有路人被樓上的盆栽砸到,似乎是一命嗚呼了。」
鬍子大叔全名叫做司馬杜,此人的最大特點就是留有一撮大鬍子,個性開朗且直接,這就是老爸的朋友,也是我所認識的司馬叔叔,同時也是隆俊的父親。
「就因為這樣也可以把整條馬路堵的水洩不通?這群人也未免太無聊了吧!好個白爛鄰居。」我不禁想抱怨起這群人的吃飽沒事幹,譴責跑去湊熱鬧的這份好奇心。
「真是的,吵都吵死了!」
為鄰居的陣陣八卦以及喧嘩聲感到不耐煩,現在巴不得衝回房間,關上房門然後把頭整個埋進枕頭裡好隔離這些對自己而言毫無意義的喧雜聲。
「唉呀!你也別這麼說,畢竟住在這住宅區的就只剩下我們這些老芋頭,會住在這裡年輕人少上加少,你也知道嘛!老人們平常就閒閒沒事做喜歡看熱鬧,反正等一等屍體…不對……等等人運走之後就安靜了,你就暫時忍耐一下吧!」
司馬叔叔對自己一時用錯名詞而感到困擾。
死者是名男性,在一旁的女性年齡似乎和死者差不多。男子一動也不動的躺平在大馬路上,醫師正在幫他做最快速的確認。
除了救護人員以外,現場還有了兩位員警。
看的出這兩名男女是對夫妻,小倆口似乎是出來散散步,誰曉得一個盆花的不慎掉落下,莫名奇妙地奪走了男子的性命,搞不好就當事人而言,連自己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破得粉碎的盆栽碎片為了提供警方採證,所有散落的位置以及方向幾乎可說是動都沒動過。
盆栽的主人因為當時不在場,所以稍後必須到警局去做偵訊。
這種既定程序我還是懂得。
「花只要再種就有了,但人可就……」司馬叔叔嘆了口氣。
在醫師判斷這名男子已經沒有生命跡象時,妻子就像現在這樣趴在丈夫的身上痛哭,聲音十分淒慘。
這哭聲勾起了我一些不愉快的回憶。
「哼!無聊透頂!」我哼了一聲,轉身從口袋裡拿出一串鑰匙,打開那鐵製的大門。
「話又說回來,今天隆俊有乖乖去上補習班嗎?」像是要打探什麼一樣,司馬叔叔突然問道。
「嗯…今天是我自己走回來的,所以隆俊有沒有去上課,這我也無從得知,只能說不去上課的機率應該不大吧!」
也沒有再跟鬍子大叔多說什麼,丟下這番話之後,碰的一聲就把門關上並且上了鎖。
進到屋裡,我按照習慣進屋就喊著「我回來了!」這麼一句話,同時也打開了設置玄關旁的電燈開關。
一進門便是客廳,我面對放置在玄關的鞋櫃,將皮鞋脫下。
皮鞋是學校服裝儀容的基本規定之一,然而這皮鞋一穿就是兩年,雖然有些破舊,但從外觀看起來還算可以穿出去見人的程度。
屋裡空無一人,在日光燈的照射下,整個空間也開始明亮了起來。這個家,裡頭的物品都很俱全,客廳裡有沙發、一張方形桌以及桌子前面所擺至的液晶電視,看起來似乎就是個相當小康的家庭。
這棟房子一共有四樓,從二樓開始每一樓都有陽台,三樓主要有三間房間,一間是書房而另外一間連結陽台的是我的房間,最後一間則是父親的房間。四樓的透天頂樓,以前似乎是放置東西以及曬衣服的樓層,不過也有廁所之類的設置,從新整理過後,現在的四樓已經是間可跑可跳的玩耍空間。
整棟房子給我一個人住實在太大了,但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父母在我小時候就離婚,離婚的原因是因為母親另結新歡,在外有了另外一個男人。
房子是過入父親嚴道名下。
自己的父親是名考古學者,常常因為工作天南地北的奔波,不過講老實話,他實際的工作情況我一點都不瞭解。
可能是因為母親受不了父親這樣奔波吧,因而耐不住寂寞做出這樣的事情,至少我是這麼想的。
然而父親也沒有多說什麼,沒有任何想留住枕邊人的意思,反倒是順著母親的意思簽下了離婚協議書。
簽下協議書的當天,老爸照舊沒有改變行程,下午搭飛機前往阿拉斯加,而我則被丟在親戚家暫居,這讓我印象深刻。
雙方沒有爭奪小孩的扶養權,母親狠心的丟下自己的小孩和別的男人走掉了,扶養權自然落到了父親手上。
總之這幾個月下來,老爸都有按時給予生活費,生活費裡當然也包括了學費以及零用錢,說多也不多但也沒有少給,在生活上可以不必擔心那麼多。
突然間,家中就只剩下我孤零零地待在家裡,忍受著寂寞與孤獨。
這種生活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如今我已經是個比同年齡都要來的早熟以及穩重的高二生,應該說是環境迫使自己成熟呢?還是說早就有這方面的自覺與覺悟?恐怕這連自己本身也無法解釋清楚。
從父母離婚那天開始,我和母親就沒有任何聯絡,彷彿母親就此從人間蒸發了一樣。
我的這一句「我回來了」,並不期望有任何人回應。起先這種日子很難熬,但久而久之這種日子也習慣了。現在想想,這只不過是家常便飯,根本就沒有什麼好在意的,也不希望得到別人的憐憫,堅強的活下去才是最根本就解決之道。
就在此時,唯一有回應的是…
一隻小白貓的叫聲。
慢慢地從樓梯上走下來。優雅的背部輪廓,尾巴隨著下樓梯的動作而晃動。純白的軀體,看起來就像毫無汙染、純淨並且聖潔,同時也象徵虛無。
小白貓是我在國二那年的冬天在路邊撿到的。
當時的天空正下著濛濛細雨,我撐著雨傘走在回公寓的路上。
一陣喵喵叫的聲音引起了注意,在一個小紙箱裡,全身上下已經髒到無法辨認出毛的顏色,一隻小貓孤苦伶仃的被丟棄在路邊的電線桿下,不時的用著無力的前肢抓著紙箱表面。
唯一能取暖的報紙已經發揮不了作用,小貓全身都在發抖,讓人看了鼻子一酸。
姑且不論是哪個沒良心的人把牠丟在這裡,瘦弱的身軀是絕對經不起這雨天和冷到刺骨的寒風。
也不顧衣服,我二話不說的就將小貓從紙箱中抱起並將牠塞到自己的外套裡以避免再淋到雨水。
不管小貓會不會弄髒衣服,被憐憫之心驅使著,就這樣將小貓帶了回家。
如今這隻純白的貓,與以前在路邊發抖的那隻小貓簡直天壤之別。
為了這隻貓,我甚至翻遍了所有跟貓有關的書籍。
當初還為了養貓跟老爸吵了一架。
弦,這是貓的名字。
不知道為什麼,當我第一眼看到牠時,這名詞就在腦中浮現,沒有任何理由,沒有任何能夠解釋的邏輯。
弦是隻不折不扣的母貓,這名字跟牠也挺相襯的。
弦聽見自己的主人回來了,立刻從樓梯上跳了下來。
一見到主人的反應就是在他的腳邊,用自己身上的毛磨蹭著我的腳,像是在撒嬌一樣。
將書包丟在沙發上,蹲下身子將小白貓抱在懷裡,撫摸著毛茸茸的背部。
抱著牠又走了幾步路,這時我像是想到了什麼一樣,將弦舉了起來,將牠的臉面向自己。
與弦四目相交,彷彿可以讀出牠的心思似的,自言自語的說:「是嗎,妳也覺得外面很吵對吧。」
說完,又將牠抱回懷裡,緩緩地走上樓。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死神事務所(1、2合售)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死神事務所(1、2合售)
超萌死神來拜訪,歡迎加入死神事務所!
能夠看得見死神,就等於掌握生死?!
跟著擁有異能的少年,一探不為人知的神祕空間!
光鮮亮麗的現代城市裡,存在一個神祕的空間──「靈域」。
這裡是天堂與人間的交會處,更是某一群特定異能者處理死神大小事務的地方,因此,這裡又被稱為──「死神事務所」!
在昨天之前,嚴翔還只是個平凡的高中生,直到他與一隻落單的黑貓相遇,他的世界從此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憨厚的鄰居大叔褪下偽裝的外衣,化身為負責帶領靈魂到天界的引路人;自己所豢養的白色貓咪,沒想到竟也大有問題。嚴翔一步步踏入這奇詭的世界,還被「懲戒人」冥烏以一把大刀架在脖子上威脅,最後只能乖乖同意成為死神事務所中的一員,擔任「死神管理人」。
只是,死神究竟是誰?祂又在哪裡出沒?這些困擾嚴翔許久的問題,終於在那隻偶遇的黑貓身上,很快地找到了答案!
本書特色
★奇幻空間架構者 季鳴 榮登蘋果日報華文小說暢銷榜作品
★1+2特價套書版,讓你一次看個過癮!
作者簡介:
季鳴
1987年出生於台南市,目前為崑山科技大學某系所之菸酒生,退伍後展開不一樣的作家生涯,最近以都市奇幻做為題材撰寫故事,更貼近於生活周遭的內容總讓人特別興奮,自己的生活為故事的一部分,相對的故事也反應出生活常態,想把這份美好分享給每個讀者。
退伍後由原本的半瘋癲進化成了完全體,或許是對事物的看法改變,但對於創作的熱誠依舊沒有絲毫動搖。
最近喜歡上騎單車,新的夢想是騎單車環島的熱血青年,運動方面對於空手道是情有獨鍾。
正文開始,請正襟危坐!
.
章節試閱
序章
故事該從哪裡開始講起呢?
雖然有點倉促,但我的生命現在正受到威脅。
一把黑色短刀指著我的脖子,隨時都有朝喉嚨劃下去的可能。
是碰上搶劫嗎?還是遇到殺人犯?
並不是。
拿刀對準我的人,從他身上散發出一種非人氣息,不管是髮色還是是瞳孔,怎麼看都不像是生活在現實世界裡的人。
不只是人,就連身處的環境也很莫名其妙,放眼望去是一片死灰,空間裡不管是頭上頂著或是腳下站著的,都是呈現出混濁的灰色。
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得不作出選擇,要不就是生,要不就是死,非常兩極化...
故事該從哪裡開始講起呢?
雖然有點倉促,但我的生命現在正受到威脅。
一把黑色短刀指著我的脖子,隨時都有朝喉嚨劃下去的可能。
是碰上搶劫嗎?還是遇到殺人犯?
並不是。
拿刀對準我的人,從他身上散發出一種非人氣息,不管是髮色還是是瞳孔,怎麼看都不像是生活在現實世界裡的人。
不只是人,就連身處的環境也很莫名其妙,放眼望去是一片死灰,空間裡不管是頭上頂著或是腳下站著的,都是呈現出混濁的灰色。
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得不作出選擇,要不就是生,要不就是死,非常兩極化...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季鳴
- 出版社: 大翼 出版日期:2014-11-11 ISBN/ISSN:978986574320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576頁 開數:25開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輕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