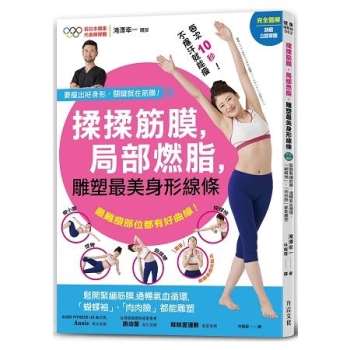殺手記事一‧需有接受駭人真相的心理準備
『雷馮斯,剛才接到消息,有兩名疑似是二和三的人已經出境,經過監視器畫面比對及出境記錄來看,應該沒錯……』
駛至人煙稀罕的郊外,我將車子停在路旁,後背倚著坐椅輕嘆:「唉,看來這根本就是預謀好的,怪我居然沒料到他們會直接逃到國外……」
我懊惱地蹙緊眉頭,伸手敲了敲這顆魯鈍的腦袋,為什麼我沒想到要先到機場去呢?如果我一開始就將目標鎖定機場,也許能追得上的……
『你別太自責了,事有一弊總有一利,雖然不知道他們兩人飛去的國家是否正是札飛索所在的總據點,就算不是,至少還能藉著這個機會殲滅他們的支部也說不定,既然確定了他們前去的國家了,那我也能立刻調派人馬進行後續追蹤調查。』
「是嗎……既然資料追不回了,你趕緊聯絡梟收手吧,讓他接受黃泉保護。」
資料追不回不僅是反戮芒計劃會悉數遭對方破解,另外就是身為第一手情報獲取者的梟最為危險,身為駭客界第一能手的他,照理而言是沒有人能夠順利攻破他的防火牆的,就算他以遭人入侵的說詞作為辯解,也絲毫沒有說服力可言。
『我剛才撥了幾通電話他都沒接,兄長他只要一忙碌起來就不會接電話,也許我直接入侵他的電腦給他留言會快一些。』
我吊起眼珠思忖半晌後說:「不用了,我現在過去找他一趟好了,你也很清楚這傢伙有多固執,正好我去當面跟他談談,軟的不行、我就來硬的,打暈他也要將他帶回去。」
『呵呵,麻煩你了,那我去向老闆報告二和三的事了。』
「你去忙吧,我也要出發了。」
丟下這句話後,我們結束了通話,我隨著托蒙的指示踩緊油門,開往許久未曾踏足的那個地方──梟的地下王國。
※※※※※※※※※※※※
「來晚了……」
鈴聲響了許久仍未接起,讓我心中焦急更添幾分,就在即將進入語音信箱留言之前,阿爾多終於接起了電話,他先是帶著歉意道:『抱歉,剛才與老闆才說到一個段落,所以……』
「那不重要!我、我來晚了,我找不到梟的人影,現場似乎留有掙扎的痕跡,現在我正翻查現場,看看能不能找到一點蛛絲馬跡。」
『哥……!』
我懊悔地走回吧台,準備針對此處進行搜索,但壓在心底的那股憤懣總是難平,我握緊了右拳,憤怒地朝身側的牆面猛力一撞。
原來以為會撞上厚實的牆面,但是撞上的卻是一片薄木板,在我使盡力的下場,便是貼上壁紙的木板碎裂,一處凹槽立現,我狐疑地輕鎖眉宇,將殘留在牆面上的木片扳折拔除,再將掉入凹槽中的木板取出丟棄在一旁。
凹槽裡頭置放的是一只隨身碟及一張以平實的木製相框框起的相片,由相片略顯泛黃的程度看來,應是經歷了一段不算短的時日。
「是阿爾多吧……這麼說,這個男人就是梟沒錯吧,沒想到光是笑容就讓一個人有這麼大的差異。」
由三人的笑容之中,可以讓人感受到一股打從心底的溫暖,在笑顏之中毫無虛偽做作,其中的羈絆與情感更是不言而喻,一張看似平凡無奇的相片,竟能帶給人如此奇妙的感受……
『雷馮斯。』
托蒙的嗓音在我耳畔輕喚一聲,我這才將視線由相片上抽離,我略吃驚地抬起首後,托蒙又道:『發什麼呆?』
「哪有……啊,這裡有只隨身碟。」
像是要掩飾自己的心虛似的,我連忙伸手將凹槽中的隨身碟取出,在搜遍了酒吧仍然未果的情況下,這只隨身碟可謂是最後一線希望了。
我收妥隨身碟,思忖半晌,仍決定將相片帶回給阿爾多,我隨即動身離開酒吧,手中緊握著這枚相框,我快步朝原路走回,空曠的下水道中迴響的是我急促的腳步聲。
『你帶走人家的相片幹嘛?』
聞言,我挑著眉答覆:「一張相片都能被梟那傢伙當成寶貝似地藏在那種地方,現在那裡少了可以保護它的主人,由我轉交至相關人士手中保管也不為過吧?」
『呵,你這多管閒事的傢伙……嘛,不過我並不討厭你這多管閒事的個性就是了。』
托蒙笑道,我也因此笑著說:「嘿嘿,半斤八兩!你如果不是和我一樣愛多管閒事,也許我們就不會認識了。」
我與托蒙你一言、我一語,一路拌嘴至帝維瑟的宅邸才宣告結束,推開門扉進入走至大廳時,便見略顯劍拔弩張的氣氛。
「妳到底想去什麼地方?」
十哥的神情銳利而認真,由他緊鎖的雙眉來看,似是十分焦躁而苦惱,能讓他擺出與平時那副天真高中生模樣迥異的,無非是他緊抓著手腕的──八姊。
雖然八姊的身形與十哥相仿,但是兩人的氣力卻完全不成正比,只見八姊緊抿下唇使勁地欲擺脫十哥強而有力的手掌,她一對冷然的灰色眼眸直視著十哥,輕鎖起的柳眉亦是對此狀況感到棘手的表現。
八姊……將頭髮給剪了。
原來八姊留有一頭栗色的蓬鬆長髮,擁有自然捲的八姊極少整理自己的頭髮,但是蓬鬆而及腰的長髮卻十分自然美麗,毫無凌亂之感……現在的八姊卻將一頭長髮剪至約莫僅能觸及領口的長度,仍舊蓬鬆的髮絲雖然同樣不覺凌亂或不適,但是總會讓人不禁歎惋,可惜了那頭美麗的長髮。
「我去什麼地方還得向你報告嗎?快放手!」
「妳不向我報告,也得向雇主報告,別忘了妳現在受僱於黃泉之下!」
聞言,八姊不再作任何抵抗,她淒然地嗤哼一笑道:「是,我是要向雇主報告……但是我的雇主並非黃泉老闆,而是飛先生,這樣的答案你滿意了嗎?」
果然……
不只是二姊和三哥,連八姊也是潛伏在保鑣群中的內奸,但是事已至此,八姊又為何要將身為內奸之事托出?現在她可是身處敵陣。
「我早就知道了……」
十哥輕輕道出這麼一席話,八姊僅是沉默著蹙緊了眉,十哥又說:「妳見到我時表現出異樣,那時我就知道了……所以我更加無法理解,為什麼妳仍執意要回去?」
「因為除了那裡,我沒有地方可回!」
八姊衝著十哥吼道,她的胸口不停起伏著,可見情緒之激動。
片刻,十哥略顯疲憊地半覆眼眸道:「這裡可以成為妳值得效力的歸宿,但是因為我在這裡,所以妳將這唯一的選擇也否決了。」
八姊的眼神瞬間動搖了,她愕愣了須臾後,又是那副張牙舞爪的模樣反駁著十哥的論調:「你以為你是誰?我有什麼理由非得因為你而放棄在這裡生存的選擇?」
十哥的雙眸堅毅不已,瞬也不瞬地凝視著八姊的雙眼,字句分明地回答八姊的問題:「……沒有理由,就像我想將妳留在我身邊一樣,沒有任何理由!」
像是無法承受十哥眼眸中承載的堅毅與情感一般,八姊別過了視線,垂下了眼簾低語:「不是那樣的……我只是認為為飛先生效力才能讓我這輩子的生活衣食無虞,其他的地方……我無法信任。」
「不對,妳只是認為自己無法再承擔我看著妳的眼神。」
我伸出右掌輕掩著因為過分驚訝而無法閉合的嘴,瞠圓的雙瞳直視著這幕在我眼前上演的戲劇化景象,專注的程度比過去看過的每一部連續劇都來得認真,但是理解的難度卻也比過去看過的每一部戲都要高出許多。
剛剛由十哥嘴裡吐出的台詞,通常不是用在……身陷情網的男女身上嗎?
眼前上演的戲碼明明既肥皂又狗血,正因為如此,這樣的戲碼真實地反映在自己周遭的人身上時,才讓人感到虛幻得不可思議──現在是在上演哪一齣?
我緊鎖眉宇,不由得將拇指觸著唇瓣,時而以上下唇瓣含著指腹,看著我這副異常的模樣,阿爾多狐疑地看著我,以肘部輕輕撞了我後低聲問道:「你怎麼了?」
「我只是納悶,這些台詞在我以前看過的連續劇中應該出現過不少次,但是為什麼唯獨這次我無法理解……」
聞言,阿爾多無奈地瞥了我一眼後說:「你只要想像站在你眼前的男女主角是兩個正在演對手戲的影劇明星就明白了。」
啊,這麼說……
「十哥喜……」
當我止不住內心的驚愕,險些失控地放聲喊出之際,我連忙伸手摀住自己這張就要管不住的嘴,緊急踩了剎車。
阿爾多略顯欣慰地輕輕頷首:「嗯,看來是明白了。」
我的雙瞳瞪得猶如兩枚硬幣一般,我也不敢將摀著嘴的手掌放下,因為搞不清楚自己對於眼前令人難以置信的景象究竟是驚喜、驚惶還是驚嚇了,深怕自己一旦鬆了手就會像小女生看著令人揪心不已情節的連續劇而忍不住驚叫出聲。
八姊柳眉輕蹙,現場呈現一片沉寂,在這片刻的寧靜,我這才想起手中的相片及被我收妥的隨身碟,伸手摸入配件包中取出隨身碟,將這兩樣東西一併交給阿爾多。
阿爾多先是狐疑地看了我一眼,由他眼瞳中那絲抹不去的陰鬱來看,他肯定努力壓抑著自己擔心梟的心情,將目前該做的事好好完成、堅守崗位吧。
他接過東西後,疑惑地半瞇起眼眸看著那只隨身碟,之後將相框翻過正面,瞬也不瞬地凝視著相片低喃:「這是……那一天拍的照片……」
「這兩樣東西被梟藏在一個相當隱密的地方,現在他已不知所蹤,我認為應該將這些東西轉交給你保管,至於這只隨身碟就得麻煩你調查看看裡頭是否有任何線索了。」
阿爾多緊握著隨身碟,向我頷首後斂起眼眸道:「我知道了,我馬上調查。」
語畢,他隨即走向帝維瑟,屈身附耳說了幾句話以後便由一旁的沙發椅上提起筆記型電腦朝階梯快步走去。
我瞥了帝維瑟一眼,他竟下顎一抬,要我上前居中調解,我表示拒絕地搖搖首,帝維瑟掄起右拳、瞪大雙眼作勢要揍我的模樣,我也以同樣的動作回敬他後,還是硬著頭皮走向前。
我站至距離兩人約莫一公尺外的地方低聲說道:「那個,我說……」
「閉嘴!這與你無關!」
我才一說出發語詞,立即就遭到八姊毫不容情地回吼,睜著一對帶有敵意的銳利眼神看著我,我輕嘆一口氣後,側過身白了帝維瑟一眼,只見他似乎也感到相當尷尬地別過視線,佯裝咳嗽的模樣。
這是意料之中的反應,從我有意識以來,八姊就十分討厭我,而且那股厭惡之情是毫無掩飾,一看見我總是緊鎖眉頭、掉頭離開,雖然八姊赤裸裸的排斥讓我介懷,但是我卻無法討厭八姊,至少八姊能做到公私分明,出勤任務時還是能夠好好地看著我的臉龐。
十哥稍顯動怒,他再使更多力勁地拉過八姊的手腕,迫使八姊與他面對面,十哥微鎖眉宇向八姊說:「這是我跟妳之間的問題,別把脾氣出在小三身上!他是我們的弟弟,妳別處處針對他!」
「他這麼一個思想與我們相左的小鬼也想插手我的事?憑什麼!」
「妳……!」
只見十哥怒意橫生,我只得連忙安撫道:「八姊說的也不無道理,我是影侍之中年紀最小的,本來就沒有資格過問兄姊們的事,所以你別生氣了,十哥。」
「年紀再小,你今年也二十四歲了,怎麼可以……」
正當我努力思考著該如何表達才能讓八姊按捺下性子聽我說話時,階梯方向傳來了腳步聲,我隨著聲源轉過視線,看著四哥眼神既無奈又嚴肅地雙手交抱胸步下階梯、朝此走來。
四哥走定至八姊面前,他先以眼神示意十哥鬆開八姊的手腕後,斂著一對眸子凝視著八姊的雙瞳道:「既然小弟的話妳聽不進去,那我這個比妳年長的哥哥不知道說話夠不夠份量?」
「四哥……」
八姊不由得半覆眼簾、低垂臉龐,四哥雖然平時給人一副散漫又隨和的印象,但是一旦認真或發怒卻也不容小覷,此時的他眼中夾帶著幾分怒氣,讓她身周的戾氣頓時退卻。
「妳堅持要回去是嗎?四哥不會留妳,希望這是妳審慎思考後所作的明智抉擇,不過我想妳應該很清楚吧,被蒙在鼓裡、獨自一人被留在國內代表的是什麼意思。」
四哥不疾不徐地作出了分析,其實在場的人皆心知肚明,一個大方向敵人表明自己是奸細身分的內奸,肯定早就心裡有數──自己只是一枚棄子。
迫於現實考量,八姊不由得連雙肩也頹然垂下,她的眼裡盡是絕望與茫然,讓四哥一針見血地說出了殘酷的事實,她也因此如同腳上生了根,即便想提步卻不知應該前行的方向。
十哥走至八姊眼前,搭上她的雙肩說:「留在這裡,和我們一起留在這裡。」
「我……」
八姊的態度顯然軟化了許多,她悄悄抬眼看了帝維瑟一眼,已表明其意,於是我微笑著喚道:「老闆。」
帝維瑟瞥了我一眼,小指硬是往耳裡掏,一面低聲說道:「你們剛才在說些什麼我可沒聽清楚,嘖,看來堆積了不少耳屎啊……」
耳裡到底要堆積多少耳屎才能聽不見聲音?帝維瑟這理由也找得太牽強了吧。
帝維瑟打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舉動,讓十哥笑顏逐開,情緒激昂地抱起八姊轉了兩圈,笑容之中是毫無虛偽的幸福:「太好了、太好了!」
「咳,十弟。」
在四哥的提醒之下,十哥這才發現自己的行為有些失態,連忙將八姊的身子放下,她也因此泛起一片緋紅而別過視線。
就算已經弄清楚十哥的情感,但是再一次看到這過於駭人的景象,我的一張嘴仍忍不住越張越開,就在即將叫出聲時趕忙伸出手掌覆上。
四哥突如其來地朝我的額際一拍,勾起一抹曖昧的弧度道:「嘿嘿,你這傢伙,表現得這麼誇張是想讓誰害羞得無地自容啊?」
我撫著額際、挑了挑眉,回以同樣不懷好意的笑容說:「我只是默默地表示訝異,某人挑明了說出來是何居心?」
「你們……事情才不是你們想像的那樣,人類在情緒亢奮時很容易做出不理智的舉動,所以、所以別再笑啦!」
八姊羞窘得慌了手腳,雙掌分別拉上我與四哥的衣袖使勁一扯,好讓我們停止這兩張帶著曖昧笑顏的欠揍嘴臉。
此時,帝維瑟站起身子,蠻不在乎地朝著小指吹了口氣後走了過來,我們也因此收起笑顏、停下了玩鬧的舉動,帝維瑟僅是勾著淺笑凝視著八姊不發一語。
八姊先是輕輕覆上眼皮,深吸了一口氣後,睜開了一對彷若毫無情感波動的灰瞳,將右臂橫於胸前、微躬著身子:「老闆。」
聞言,帝維瑟勾在唇邊的弧度也拉了開來,他伸出手拍了拍八姊的腦袋說:「別這麼拘謹,妳看看在場的幾個傢伙有哪一個對我如此畢恭畢敬的?」
八姊愕然地抬起頭,環視了我們過後,我便說道:「老闆,我可是很尊敬您老人家的,相處這麼長的時間還感受不到我的敬意嗎?」
帝維瑟立馬瞪大雙眼指著我的鼻頭,咬牙切齒地說:「我跟你說過了,你老闆我是永遠的三十歲!」
「是、是。」
我不以為意地聳了聳肩,這樣的景象看在八姊眼中猶如世界奇觀,驚愕了好半晌而吐不出任何隻字片語。
收起玩笑的姿態,帝維瑟再將視線投以八姊道:「那麼,身為老闆,我下達的第一個命令是──將妳所知全盤托出,不得有半點欺瞞。」
八姊斂起眼眸後,中氣十足地應答:「是,我在……」
此時,阿爾多前臂靠著二樓圍欄,朝我們揮手喊道:「雷馮斯,你上來一下!」
「知道了!」
被阿爾多點了名,我向眾人頷首示意離開原地走向階梯處,待我上樓以後,阿爾多領在前頭走向他方才所待的房間。
入了房,他坐回電腦前,指著螢幕說:「你看,這只隨身碟設有密碼,我已經嘗試所有可能的密碼和其他破解途徑,但是都無法成功,果然是哥哥留下的東西。」
「嗯……我在現場也沒能找到可能成為密碼的線索,還是你找個時間回老家一趟,搞不好能找到什麼資料?」
阿爾多聞言,僅能對著螢幕輕嘆:「唉,看來也只能這麼做了,但是哥哥他……」
我拍了拍他的肩頭道:「你放心吧,我想梟暫時不會有生命危險才是,如果飛先生的目的是要除掉他,大可當場動手,沒必要特地將他帶回去再處理掉。」
「但願如此……」
我拉了一旁的木椅後坐下,無奈地說:「不過,還真是出師不利,居然反戮芒的第一場就被逮個正著,搞不好這根本是飛先生特意留下的陷阱,否則戮芒對象何其多,怎麼可能剛好第一次就踩到地雷、掉進陷阱?」
阿爾多也低垂臉蛋沉吟:「也許……札飛索底下其實有著許多像哥哥這種專門獲取情報的人員,每個人所負責的名單底下都佈有陷阱,只要誰所負責的名單出了問題,也能夠就此揪出內奸。」
「這的確像是那個疑心病超重的飛先生會做的事。」
我認同地點頭如搗蒜,此刻,房間門板傳來『叩叩』的敲門聲,阿爾多請對方自行入內後,房門緩緩被推了開來,一抹嬌小的身影映入眼簾。
「阿爾多哥哥、雷馮斯哥哥。」
眼前正是帶點羞澀微笑的男孩米歇爾,他禮貌地向我們問候,阿爾多便向他揚起溫雅的笑容問:「怎麼了?米歇爾有什麼事嗎?」
「爸爸和蕾麗雅姊姊醒來了,爸爸要我請你們過去。」
「是嗎?那我們一起過去吧。」
「嗯。」
我們兩人站起身,與米歇爾一同下樓走向莫與蒂莉亞休養的客房,我們並未敲門就旋開門把入內,莫雖然仍躺在床上,卻立即轉向我們說:「麻煩你們,在孩子面前作個好榜樣,進來之前請先敲個門。」
「是,對不起……」
我與阿爾多歉然地對著眼前這位滿口爸爸經的父親致歉,蒂莉亞與帝維瑟這對父女掩嘴竊笑,我分別送了兩人一記白眼後隨著阿爾多的腳步走至床前。
「你們兩個都還好嗎?」
阿爾多朝兩人投以關切的眼神詢問著,蒂莉亞隨即揚起最燦爛的笑容說:「當然沒問題,這種傷勢睡個一晚就能痊癒了。」
我不以為意地道:「少來了,妳那傷勢好歹也要兩週的時間才能痊癒啦。」
「閉嘴啦!」
被戳破謊言的蒂莉亞惱羞成怒地朝我吼了一聲,阿爾多則朝她投以責備的眼神,讓她不得不低下頭反省。
「我沒有大礙,不過母親留給我的墜鍊……」
帝維瑟微笑著安慰莫說:「看來,你的母親至今還守護著你,果然為人父母的,就算離開了還是牽掛著自己的孩子。」
米歇爾坐在莫的床沿把玩著那條墜飾破損的墜鍊,倏地發出疑惑的聲音,他瞇起雙眼凝視著墜飾,莫也轉向寶貝兒子問:「怎麼了?」
「唔……這裡面好像有什麼東西。」
莫不解地偏了腦袋後伸手:「我看看。」
米歇爾將墜鍊遞至莫的掌中,他在接過後亦是瞇起眼眸端視了半晌,爾後他微啟唇瓣,將墜鍊遞向阿爾多的方向說:「阿爾多你看看,好像是一塊晶片。」
阿爾多伸手接過後摘下眼鏡,端看片刻道:「沒錯,是晶片。」
「難道我還有一些事沒想起來嗎?我不記得母親對我說過裡頭有東西……」
莫沉思般地將視線朝旁輕移,阿爾多便說:「我幫你看吧,晶片的內容。」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異能殺手Mission(5):自由的真諦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09 |
二手中文書 |
$ 162 |
小說/文學 |
$ 175 |
中文書 |
$ 179 |
幻奇冒險 |
$ 179 |
奇幻/科幻 |
$ 179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異能殺手Mission(5):自由的真諦
劇情高潮迭起!
十三影侍一一現身,
一段被刻意隱藏的記憶即將甦醒!
是搭檔,也是家人,
托蒙為了點醒雷馮斯,
竟然決定關閉系統!
縱使具備神效,Fantasy細胞還是有副作用的!
為了避免雷馮斯的壽命縮短,
托蒙極力希望他能接受手術。
但若是失去這份力量,
雷馮斯恐怕再也難以保護托蒙……
在「六」的挑釁與暗示之下,
雷馮斯開始懷疑記憶是否被人動過手腳,
多年來午夜夢徊,總是出現在夢中的女人究竟是誰?
不斷反覆播映的記憶裡,即將浮出水面的,
究竟是多麼令人難以置信的真相?
本書特色
★新生代輕小說作家‧玦晴,首部搞笑冒險長篇力作!
★本作推出首周就登上蘋果日報華文輕小說週排行第一名!
★路癡殺手從組織裡偷出來的最高機密,竟是一個成天愛吐槽的GPS?
作者簡介:
玦晴
玦乃半面美玉,晴乃煦日之陽;玦指不完美的自身,晴是完美玦玉的存在,有你們的支持,才能完美不完美的我,玦晴是我,卻也有你。
但是玦晴其實不絕情,所以請別看到上述道貌岸然版的自介就退避三舍,欲見無障眼法版自介請到噗浪報數。
【玦晴的噗浪】www.plurk.com/growlanser1
想看《異能殺手》相關番外篇、節日賀文、賀圖,或其他小說作品,歡迎到個人小屋玩耍喲!
【玦晴的Blog】http://home.gamer.com.tw/a54313
關於封面繪者
絮丹
台灣人,喜歡紅茶和兔子,
愛好畫美少年和幼女,請大家多多指教。
歡迎來我的blog坐坐:
http://watani0522.bolgspot.tw/
章節試閱
殺手記事一‧需有接受駭人真相的心理準備
『雷馮斯,剛才接到消息,有兩名疑似是二和三的人已經出境,經過監視器畫面比對及出境記錄來看,應該沒錯……』
駛至人煙稀罕的郊外,我將車子停在路旁,後背倚著坐椅輕嘆:「唉,看來這根本就是預謀好的,怪我居然沒料到他們會直接逃到國外……」
我懊惱地蹙緊眉頭,伸手敲了敲這顆魯鈍的腦袋,為什麼我沒想到要先到機場去呢?如果我一開始就將目標鎖定機場,也許能追得上的……
『你別太自責了,事有一弊總有一利,雖然不知道他們兩人飛去的國家是否正是札飛索所在的總據點,就算不是,至少還...
『雷馮斯,剛才接到消息,有兩名疑似是二和三的人已經出境,經過監視器畫面比對及出境記錄來看,應該沒錯……』
駛至人煙稀罕的郊外,我將車子停在路旁,後背倚著坐椅輕嘆:「唉,看來這根本就是預謀好的,怪我居然沒料到他們會直接逃到國外……」
我懊惱地蹙緊眉頭,伸手敲了敲這顆魯鈍的腦袋,為什麼我沒想到要先到機場去呢?如果我一開始就將目標鎖定機場,也許能追得上的……
『你別太自責了,事有一弊總有一利,雖然不知道他們兩人飛去的國家是否正是札飛索所在的總據點,就算不是,至少還...
»看全部
目錄
殺手記事一‧需有接受駭人真相的心理準備
殺手記事二‧了解追尋自我的重要性
殺手記事三‧慎防酒後胡言
殺手記事四‧擺脫原地踏步的窘境
殺手記事五‧戴上虛偽的假面
殺手記事六‧不同視角能眺望不同風景
殺手記事七‧與人溝通要拿出誠意
殺手記事八‧將資源作最有效的利用
殺手記事九‧防不勝防
殺手記事十‧聆聽弦外之音
殺手記事十一‧雨過天青
殺手記事十二‧凡事總難兩全其美
殺手記事十三‧注意周遭人的心理狀態
殺手記事十四‧見證絕對強悍的實力
殺手記事十五‧與他人一同背負肩上重擔
殺手記事二‧了解追尋自我的重要性
殺手記事三‧慎防酒後胡言
殺手記事四‧擺脫原地踏步的窘境
殺手記事五‧戴上虛偽的假面
殺手記事六‧不同視角能眺望不同風景
殺手記事七‧與人溝通要拿出誠意
殺手記事八‧將資源作最有效的利用
殺手記事九‧防不勝防
殺手記事十‧聆聽弦外之音
殺手記事十一‧雨過天青
殺手記事十二‧凡事總難兩全其美
殺手記事十三‧注意周遭人的心理狀態
殺手記事十四‧見證絕對強悍的實力
殺手記事十五‧與他人一同背負肩上重擔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玦晴
- 出版社: 大翼 出版日期:2014-09-16 ISBN/ISSN:978986574359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88頁 開數:25K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輕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