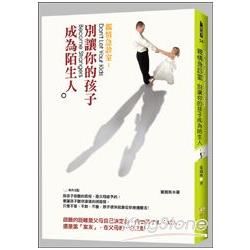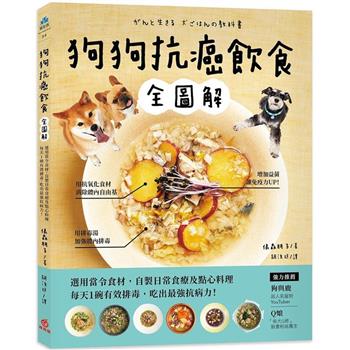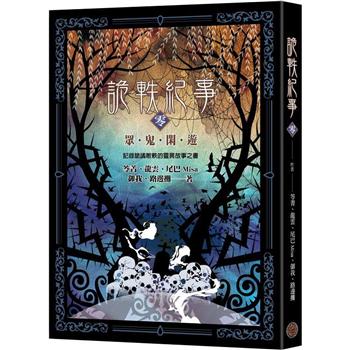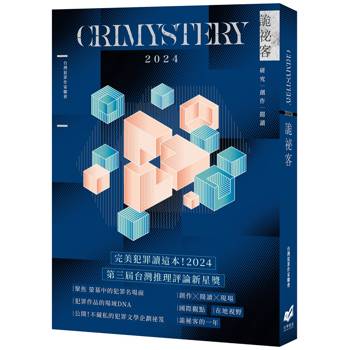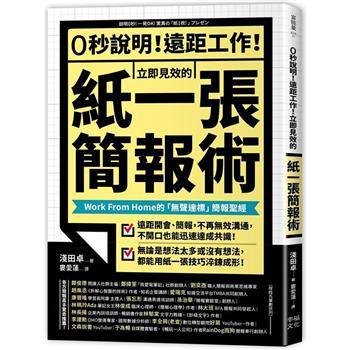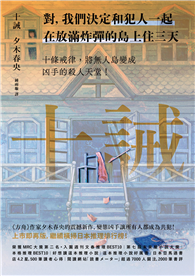與孩子距離的長短,是父母給予的,要讓孩子離你遠遠的很容易,只要不管、不教、不養,孩子很快就會從你身邊離去!
疏離的距離是父母自己決定的,要讓孩子當「家人」,還是當「室友」,在父母的一念之間。
高爾基說:「誰最愛孩子,孩子就愛他,只有愛孩子的人,他才可以教育孩子。」
孩子在出生後,便背負父母的期待和理想而活,我們很少會去關心他們的背包重不重,而是在意背包內的東西有沒有準備夠。
但是當孩子背不動時就只好選擇逃避,而心也離父母越來越遠。
要如何把心抓回,是父母與孩子維持近距離的關鍵。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親情急診室:別讓你的孩子成為陌生人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76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154 |
親子教養 |
$ 194 |
中文書 |
$ 194 |
親子關係 |
$ 198 |
生活教養 |
$ 198 |
父母隨筆 |
$ 198 |
社會人文 |
$ 198 |
親子教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親情急診室:別讓你的孩子成為陌生人
內容簡介
目錄
01 你是吃人頭路的上班族嗎? 009
02 你是忙碌的生意人? 019
03 你是麻將桌上的座上賓? 028
04 你是嚴肅型的父母? 037
05 你是溺愛家族的成員? 046
06 你是媽寶的會員? 055
07 你是老子「無為而治」的信徒? 064
08 你是體罰型的父母? 074
09 你是不好玩型的父母? 082
10 你是隔代教養的父母? 091
11 你是權威型的父母? 100
12 你是斤斤計較型的父母? 108
13 你是電視機前的父母? 116
14 你是火爆型的父母? 125
15 你是潔癖完美型的父母? 133
16 你是責罵型的父母? 142
17 你是孤僻完美型的父母? 151
18 你是朋友至上型的父母? 160
19 你是比較型的父母? 169
20 你是忽視型的父母? 177
21 你是謙虛型的父母? 185
22 你是嘮叨型的父母? 193
23 你了解孩子嗎? 201
24 你跟孩子相處時間有多長? 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