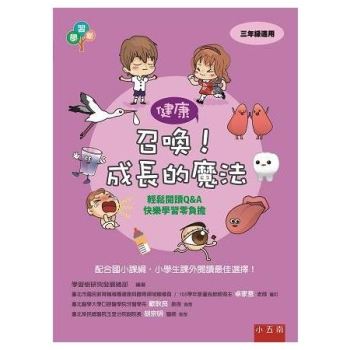塵世裡的初相見
紫藤花開了
輕輕的放著香,
沒有人知道……
紫藤花開了
輕輕的放著香,
沒有人知道。
樓不管,曲廊不作聲,
藍天裡白雲行去,
池子一脈靜;
水面散著浮萍,
水底下掛著倒影。
紫藤花開了
沒有人知道!
藍天裡白雲行去,
小院,
無意中我走到花前。
輕香,風吹過
花心,
風吹過我,——
望著無語,紫色點。
紫藤花開了
輕輕的放著香,
沒有人知道……
塵世裡的初相見
提起江南,總使人想起那首耳熟能詳的漢樂府來: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江南最好的季節不是春。哪裡的春天,都是群花爛漫,都是一樣的花團錦簇。等各地的花潮都退去,滿世界只剩下葉的綠,江南的好便突現出來,滿湖的蓮與荷,清純活潑,千嬌百媚。——遊人只合江南老了。
我曾跟人開過玩笑,我說我下輩子一定要生在江南。在六月天微雨的黃昏,穿碎花的旗袍,撐一頂碎花的小傘,走在江南的雨巷裡。想想那等搖曳生姿,兀自醉了。如若再逢上一段豔遇,那整個人生就再完美不過了。
這是江南骨子裡的媚。
相遇江南,是每個女人的夢。不消說它的粉牆黛瓦。不消說它的小橋雨巷。不消說睡意淺淺的早晨,被賣玉蘭花的婦人濕濕的叫賣聲喚醒。就說它滿湖的蓮與荷吧,六月湖上的風,吹著也還清涼,採蓮的女子,頭紮藍印花布的頭巾,身穿藍印花布的斜襟衫,蓮藕般的胳膊,在蓮葉間,魚樣的靈活。她左採右採,整個畫面看上去,恰如仙子落凡塵。
這麼一說,林徽因委實幸運,她生在江南,生在江南最好的六月裡。
那是清光緒三十年的六月。陽光拍打著青碧的西湖水。湖上的蓮已長成,有的正含苞,有的已然盛開。面容嬌嫩,清澈純淨,猶如小生命。岸邊楊柳依依,綠意森森,一派江南的初夏風光。
這是亂世。腐敗的清政府統治已日趨式微,行將就木。有識之士開始了救國活動,四處奔走呼號。山雨欲來風滿樓。
但這關陽光什麼事呢?陽光照舊潑潑洒洒,如銀似金,照亮了一個世界。這關花朵什麼事呢?荷開了。蓮開了。梔子花更是開得不管不顧,整個杭州城密布著它的香,濃烈纏綿,如炒熟的糖栗子。
自然界的法則就是順其自然,該出太陽時出太陽,該開花時開花。這就如同一個人的出生,是無可逆轉的事。
六月十日,陸官巷深處的林家老宅裡,人影幢幢,笑語喧喧。一個女嬰,在眾人的期待中,呱呱墜地。
多年後,這個長大後的女嬰,驗證了這樣一條真理:亂世出佳人。
每個嬰兒的出生,都是塵世裡的初相見。
只是,相見的是溫雅純良,還是愚昧無知;是錦衣玉食,還是苦貧饑寒;是陽光琳瑯,還是風雨如晦。這真是沒得選擇的事。
所以,常有人哀嘆生錯了人家,哀嘆生不逢時逢地。
林徽因哀嘆過嗎?
六月天的暖陽下,她是一朵清香,是柔嫩的喜悅。塵世迢遙,江湖浪高,暫都與她無關。
這個時候的林家,在杭州城赫赫有名。
林氏一族,本是福建一帶的名門望族。到祖父林孝恂時,家道中落,很是清苦了一段時期。後來,林孝恂考中進士,身列翰林之選,與康有為同科,先後在浙江海寧、石門、仁和各州縣任地方官,後代理了杭州知府。林氏一族迅速崛起。
林孝恂雖身為晚清官吏,境界卻早已超越了同僚們,他飽讀詩書,知識淵博,接受西方政法思想,眼界頗為開闊。在對子女的培養上,他大刀闊斧,捨得投資。他在杭州首創開設家塾之風,晚輩中不分男女,一律進家塾接受教育。他既請了國學大師林琴南這樣的人到私塾來,給孩子們講授四書五經,又聘請了新派名流林白水,給孩子們介紹天文地理、境外概況,還招聘了加拿大人華惠德、日本人嵯峨峙到私塾,教習孩子們英文、日文。這使得林家子侄,個個都思想激進,詩書滿腹,文采不凡。寫下《與妻書》而慷慨赴義的林覺民,就是其中之一。
祖母游氏,也不是個只識針線活和鍋臺的小腳婦人,她容顏端莊,氣質高雅,喜典籍,會書法。長子林長民的書法,頗得她真傳。而長大後的林徽因,頗得她的遺韻。
這一對睿智的夫婦,開明開化,在長子婚後久久不育,他們竟很能沉得住氣,耐心地等。這一等,就是八年。八年後,葉茂花開,終於等來了林徽因。雖是個女孩,他們一樣歡天喜地,心肝寶貝地對待著。
飽讀詩書的祖父左掂量,右斟酌,給這個孫女取名徽音。《詩經‧大雅‧思齊》裡有: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短短幾句裡,分別誇讚了三位不平凡的女性。第一位是文王的母親大任,她是多麼的雍容端莊。第二位是文王的祖母周姜,她是多麼的賢淑美好。最了不得的是第三位,她是文王的妻子大姒,享譽於世,為文王生下許多兒子。
老爺子的心思不言自明,他希望他這個寶貝孫女,將來能夠像大姒一樣,美名遠揚。也寄希望於自她之後,他們林家能夠子嗣興旺,門庭發達。
若干年後,這個孫女果然不負他所望,如一顆耀眼的星星升起,光華熠熠,風華絕代。只是那個時候,老爺子早已離世多年。這個孫女也不叫徽音了,而改名為徽因,原因是一個男作者林微音,與她的名字相撞,常被人混淆。這大概是老爺子磕破腦袋也沒想到的事。
林徽因現存最早的一張照片,攝於三歲那年。
西窗下,枇杷樹前,草地上,祖母的雕花籐椅作了擺設。陽光透過樹隙,灑下一圈的光,箔片似的。小徽因被這圈光裹著,白衫,白褲,加紅色小筒靴。額上的髮被抿上去了,露出她光潔的柔軟的額。小小的身子,倚著籐椅,一隻手搭在身後的椅座上,一隻手擱在前面,露出手腕上的玉鐲來。前面眾人在逗她笑,徽兒,笑一個!笑一個!她望著黑乎乎的機器,不知怎麼辦才好了,神情有點拘謹,小臉蛋圓鼓鼓的,微皺著小眉頭,想笑,卻憋著。看上去,像朵含苞欲放的花骨朵兒,讓人想一抱在懷,好好地親。
這是她最好的童年吧,金枝玉葉,備受恩寵,日子是清清亮亮的一串水晶,剔透晶瑩。她展顏一笑,世上所有的花兒便都開了。多年後,林徽因寫過一首題為《笑》的詩:
笑的是她的眼睛,口唇,
和唇邊渾圓的漩渦。
豔麗如同露珠,
朵朵的笑向
貝齒的閃光裡躲。
那是笑——神的笑,美的笑;
水的映影,風的輕歌。
笑的是她惺忪的鬈髮,
散亂的挨著她的耳朵。
輕歌如同花影,
癢癢的甜蜜
湧進了你的心靈
那是笑——詩的笑,畫的笑
雲的留痕,浪的柔波。
誰能展露出這樣清純的如同露珠般的笑?只有孩子。寫這首詩的時候,林徽因已為人母,女兒梁再冰剛好是她現在的年紀,小小的天真,盛滿唇邊的酒窩,如柔波似的光陰。
(待續……)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築夢林徽因:塵緣相誤,無計花間住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0 |
二手中文書 |
$ 257 |
文史哲 |
$ 261 |
文學人物傳紀 |
$ 290 |
現代散文 |
$ 290 |
現代散文 |
$ 297 |
傳記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築夢林徽因:塵緣相誤,無計花間住
透過林徽因的詩句,娓娓敘述她的生命與心路歷程,同時以典雅又浪漫的文字,生動地勾勒出她與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沈從文等當代才子們的邂逅與交往,牽引讀者細細品味這位絕代佳人的文字纏綿,一起經歷繁華瑰麗的人生傳奇。
作者簡介:
筆名梅子,紫色梅子。喜歡用音樂煮文字。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讀者》、《青年文摘》等雜誌簽約作家。在《哲思》等多家報刊闢有專欄。
章節試閱
塵世裡的初相見
紫藤花開了
輕輕的放著香,
沒有人知道……
紫藤花開了
輕輕的放著香,
沒有人知道。
樓不管,曲廊不作聲,
藍天裡白雲行去,
池子一脈靜;
水面散著浮萍,
水底下掛著倒影。
紫藤花開了
沒有人知道!
藍天裡白雲行去,
小院,
無意中我走到花前。
輕香,風吹過
花心,
風吹過我,——
望著無語,紫色點。
紫藤花開了
輕輕的放著香,
沒有人知道……
塵世裡的初相見
提起江南,總使人想起那首耳熟能詳的漢樂府來: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紫藤花開了
輕輕的放著香,
沒有人知道……
紫藤花開了
輕輕的放著香,
沒有人知道。
樓不管,曲廊不作聲,
藍天裡白雲行去,
池子一脈靜;
水面散著浮萍,
水底下掛著倒影。
紫藤花開了
沒有人知道!
藍天裡白雲行去,
小院,
無意中我走到花前。
輕香,風吹過
花心,
風吹過我,——
望著無語,紫色點。
紫藤花開了
輕輕的放著香,
沒有人知道……
塵世裡的初相見
提起江南,總使人想起那首耳熟能詳的漢樂府來: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看全部
目錄
塵世裡的初相見
◎ 塵世裡的初相見
◎ 童年是一尾活潑的魚
◎ 紫藤花開,輕輕地放著香
三生三世
◎ 三生三世
◎ 一路與你同行
◎ 風吹過花的心
◎ 半生緣
誰把流年暗換
◎ 如煙花,芳華剎那
◎ 上好的白瓷上,有了裂痕
◎ 誰把流年暗換
在最美的時光,與你相遇
◎ 在最美的時光,與你相遇
◎ 七分鵝黃,三分橘綠
◎ 塵緣相誤,無計花間住
◎ 愛像水墨青花
◎ 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
◎ 愛是唯一的榮光
在一穹勻淨的澄藍裡
◎ 君生我亦生
◎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 智慧的葉子掉在人間
◎ 在一穹勻淨的澄藍裡
◎ 風不定,人初靜
◎ 逝去與...
◎ 塵世裡的初相見
◎ 童年是一尾活潑的魚
◎ 紫藤花開,輕輕地放著香
三生三世
◎ 三生三世
◎ 一路與你同行
◎ 風吹過花的心
◎ 半生緣
誰把流年暗換
◎ 如煙花,芳華剎那
◎ 上好的白瓷上,有了裂痕
◎ 誰把流年暗換
在最美的時光,與你相遇
◎ 在最美的時光,與你相遇
◎ 七分鵝黃,三分橘綠
◎ 塵緣相誤,無計花間住
◎ 愛像水墨青花
◎ 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
◎ 愛是唯一的榮光
在一穹勻淨的澄藍裡
◎ 君生我亦生
◎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 智慧的葉子掉在人間
◎ 在一穹勻淨的澄藍裡
◎ 風不定,人初靜
◎ 逝去與...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丁立梅
- 出版社: 龍時代 出版日期:2014-09-03 ISBN/ISSN:978986575515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92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