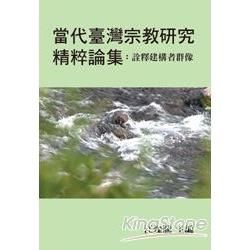方廣錩
2013年12月中旬,因參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遺書》首發、參加有關的學術演講會、尋訪台灣公私收藏的敦煌遺書,再次來到台北。在此期間,特意抽出時間,到北投江燦騰先生寓所拜訪他。
與江先生相識有年。還記得90年代他初次訪問北京,在北長街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作講演時的揮斥方遒的神態;也記得後來我到台灣參加某學術研討會,在我發表論文後,江先生“發難”的場景——不過他“發難”的對象不是我,而是評點我論文的另一位先生。在一般的學術研討會中很難出現這種情景,所以記憶更加深刻。其後我們多次見面,也時有電郵往還,就某些問題進行討論乃至相互質疑、爭辯。每次到台北,衹要時間許可,我總會去拜訪他。與他交談是一種快樂,交流的內容都是學術,是佛教研究,交流的內容非常廣泛,信息非常密集。與他交流時經常會有不吐不快之感,於是兩人經常會搶著說話,但往往話一出嘴,便相互會心,後半句話也就不用再講。對一些學人、著作與學術問題,我們的觀點往往相近。有時從表面看來似乎差異較大,但一經深入質辯,結果發現實際上大家的觀點本質一致。記得有一次他寄來一份學術爭議材料,我回信談了不同看法,並說如能就此“借火燒荒”,推動這一領域的深入研究,很有意義。或許這就是他的真實用意。他回信說:“你完全知道我的用心。”又有一次談到一位我們兩人都熟悉的學者的論著,他用“寫作技巧”四字加以評述,而這正是我的看法。衹是我曾在某次給學生上課,用了大約5分鐘來評論這位學者的論著,而他衹用四個字便輕鬆地概括了這位學者的優點與不足。他的這種能力,使我佩服不已。所以我經常會說他“眼光狠辣”、“眼毒”。雖然我經常承他青睞有加,用他的話說:是看你一個人在默默地工作,所以鼓鼓掌。但有時也會受到他不客氣的批評。如一次我把由我主持的讀書班所完成的敦煌本《壇經》校讀疏釋寄給他,他回信說:“覺得校對工作相當細膩,可是在對禪思想的解說上,執筆者並不嚴謹,並且佛教哲學的訓練有待加強,行文中的過於自信並不可取。”坦率說,學術界有時猶如一片荒漠,不管如何大聲呼喚,都很難聽到回聲,更不要說認真而善意的批評。因此,雖然我並不完全認同江先生的批評,但依然空谷足音,感懷不已。自然,他的批評也使我警惕,所以我把他視為學術的“諍友”。
今年這次拜訪,就我而言,不像以前那樣僅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地神聊,而有著明確的目的。在我看來,從上世紀初以來,大陸的佛教研究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三個階段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大家都承認,三十多年來,大陸佛教研究取得很大的成績,也有不少不足之處。但我更加關注的是,三十多年來,一些重大問題,蛹伏在大陸佛教研究的深處逐漸孵化,很可能在不遠的將來,這些問題將破蛹而出,使大陸佛教研究出現突破,出現轉型,甚至面貌大為改觀。那麼,台灣的情況如何?六十多年來,台灣與大陸走過不同的道路,兩岸的佛教研究,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台灣佛教研究未來的走勢如何?將會與大陸佛教研究有怎樣的互動?所以我對江先生說:我要對你做一次專訪,請你談談對台灣佛教研究今後發展趨勢的評估。
江先生向我介紹了他已經編就,即將出版的《當代台灣宗教研究精華論集》。當夜將全部稿件用電郵發給我,命令我寫一篇序言,並說稿件已經發排,序言必須幾天內交稿。雖說《當代台灣宗教研究精華論集》中的文章,大多數曾經在《世界宗教文化》上發表,故我曾經瀏覽,對其中幾篇關於佛教研究的文章,則讀得仔細一點。但幾天內完成序言,實在不敢承當。因為我在台北時間很短,日程排的很滿,且屁股下面已經積累了一批火燒火燎的文債。但江先生說:寫這篇序言,不僅是請你發表意見,也是我們這麼多年學術友誼的見證。他好比一個武林高手,一下子點中對方的要穴,使我無言以答,衹好硬著頭皮答應。話說回來,江先生實際是用這本書來回答我的專訪,我自然要重視這本書,於是衹好勉為其難。
當初閱讀《世界宗教文化》上發表的這些文章時,我並不知道這些文章實際由江先生在策劃、組織,但深感每篇文章能夠在不長的篇幅中完整描述台灣宗教研究的某一領域,的確很不容易。如今有機會把這些文章貫穿為一個整體重新閱讀,則二十篇文章與兩個附錄從各個不同角度展示了台灣當代宗教研究的全貌以及在其中活動著的人物,特別是《編者序》從宏觀上對本書及台灣當代宗教研究作了高度概括,實屬非大手筆不能為也。
現代社會,隨著知識爆炸,學科越分越細,在知識的海洋中,每個研究者祗能取一瓢水飲。這是事物的一個方面。然而另一方面,我們所生活的社會卻因為信息的順暢流通而越來越小,於是各學科之間的相互關係變得越來越密切。無論研究者本身是否意識到這一點,各學科間的交互影響正在日益深入,這已經是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記得魯迅曾經說過這樣的話:評價一個人的作品,要了解他的一生,要了解他的全部作品,要了解他生活的社會(大意)。《當代台灣宗教研究精華論集》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當代台灣宗教研究的具像全貌,使我們得以把握台灣當代宗教研究的總體情況;又給我們提供了在具像大環境中活動著的研究者個體的精細描述,使我們得以深入解明這些研究者的研究活動及其業績產生之所以然。我想,這或許是《當代台灣宗教研究精華論集》獨特價值之所在,這是任何一個單獨的問題研究史或某一領域的斷代研究史所無法企及的。從這一點講,本書對學術研究提供了一個方法論的範例,並將成為後人了解、學習台灣當代宗教研究的基本參考書。
本書按照“當代性、現代性、臺灣本土性特色”等三個要求為基準,“針對每位作者,按其曾在各類宗教研究上的近十五年成果、或其最新的發展趨勢、乃至其和國際學界的互動狀況,再來確定其論述的個別主題的。”所以正好回應了我此次拜訪想談的題目——台灣佛教研究今後的發展趨勢。俗話說,看一個人的過去,可以知道他的現在;看一個人的過去與現在,可以知道他的將來。所以,要感謝江先生組織一批優秀學者編纂這樣一本著作,使像我這樣的人可以直接利用他們的成果,把握台灣宗教研究的過去、現在與將來。當然,為了達成上述目標,我還要繼續認真研讀《當代台灣宗教研究精華論集》中的每一篇文章。
大陸過去流傳一句話:“不能光低頭拉車,還要抬頭看路。”其實,學術研究乃至任何工作都一樣,必要的時候,都應該停頓一下,回顧來路,瞻望前程,總結經驗與教訓,以利更好地前進。這個道理,大家都懂;這件事情,做起來很難。特別是學術研究的回顧總結,往往是“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何況還有學派差異、人事糾葛。因此,做這種事,不但要有高屋建瓴的學力,統攬全局的能力,還要有勢如破竹的魄力。江燦騰先生做成了這件事,本身說明了一切。
拉拉雜雜,說不上是序。就是也算與江先生多年學術交往的一份記錄吧。
2013年12月22日夜,從台北返回上海的第二天。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當代臺灣宗教研究精粹論集:詮釋建構者群像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當代臺灣宗教研究精粹論集:詮釋建構者群像
本書是匯集當代研究臺灣各類宗教學術精英群,空前未有的首次非正規集體合作的代表性展現,也是本書的每位詮釋建構者,都各以兼具當代性、現代性、臺灣本土性這三大特色,並在已凝聚高度共識下,所撰出──各具新穎視野,及體系性明確、嚴謹──的高素質出色論文薈萃集。其中,佛教學、道教學、新儒教學、宗教人類學、宗教社會學、基督教學、天主教學、大眾信仰及教派學(媽祖、王爺、一貫道、乩童)、武士道精神文化,都是最豐富、最簡潔、最流暢、卻又各具獨特性詮釋建構體系的新探索論述。因此若你想了解當代臺灣宗教研究的全體詮釋建構者群像,非讀本書不可!
作者簡介:
江燦騰
1946 年生,桃園大溪人,漢族。臺灣大學歷
史研究所文學博士;現職: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兼任中心教授。學術專長:臺灣佛教
文化史、中國近代佛教思想史、東亞近代佛教
史等。相關著作:已有十多本,其中《臺灣佛
教史》(臺北:五南出版社,2009)、《二十
世紀臺灣佛教文化史研究》(北京:宗教文化
出版社,2010)、《戰後臺灣漢傳佛教史》(臺
北:五南出版社,2011)、《認識臺灣本土佛
教》(臺北:2012)等,是最新結集專書。學
術榮譽:(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
斯年紀念獎學金的八次得主。(2)第一屆宗
教學術金典獎得主。(3)第二屆臺灣文獻傑
出工作獎的得主。(4)教育部補助建國百年
讓學術詮釋歷史的戰後臺灣漢傳佛教史撰述計
畫主持人。
作者序
方廣錩
2013年12月中旬,因參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遺書》首發、參加有關的學術演講會、尋訪台灣公私收藏的敦煌遺書,再次來到台北。在此期間,特意抽出時間,到北投江燦騰先生寓所拜訪他。
與江先生相識有年。還記得90年代他初次訪問北京,在北長街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作講演時的揮斥方遒的神態;也記得後來我到台灣參加某學術研討會,在我發表論文後,江先生“發難”的場景——不過他“發難”的對象不是我,而是評點我論文的另一位先生。在一般的學術研討會中很難出現這種情景,所以記憶更加深刻。其...
2013年12月中旬,因參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遺書》首發、參加有關的學術演講會、尋訪台灣公私收藏的敦煌遺書,再次來到台北。在此期間,特意抽出時間,到北投江燦騰先生寓所拜訪他。
與江先生相識有年。還記得90年代他初次訪問北京,在北長街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作講演時的揮斥方遒的神態;也記得後來我到台灣參加某學術研討會,在我發表論文後,江先生“發難”的場景——不過他“發難”的對象不是我,而是評點我論文的另一位先生。在一般的學術研討會中很難出現這種情景,所以記憶更加深刻。其...
»看全部
目錄
編者與作者簡介
序………………………………………………………………方廣錩
編者序…………………………………………………………江燦騰
謝詞
第一輯
1. 當代臺灣佛教史學論述及其思想詮釋衝突… ……………江燦騰
2. 人類學視野下的台灣宗教與性別研究… ……………………張珣
3. 宗教社會學視野中的台灣新興宗教︰
歷史概述與理論反省…………………………………………丁仁傑
4. 台灣媽祖研究新論︰清代媽祖封“天后”的由來… ……王見川
第二輯
1. 當代台灣“佛教文學研究”
的詮釋建構者群像及其相關論述……………...
序………………………………………………………………方廣錩
編者序…………………………………………………………江燦騰
謝詞
第一輯
1. 當代臺灣佛教史學論述及其思想詮釋衝突… ……………江燦騰
2. 人類學視野下的台灣宗教與性別研究… ……………………張珣
3. 宗教社會學視野中的台灣新興宗教︰
歷史概述與理論反省…………………………………………丁仁傑
4. 台灣媽祖研究新論︰清代媽祖封“天后”的由來… ……王見川
第二輯
1. 當代台灣“佛教文學研究”
的詮釋建構者群像及其相關論述……………...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江燦騰(主編)
- 出版社: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1-21 ISBN/ISSN:978986575705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20頁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