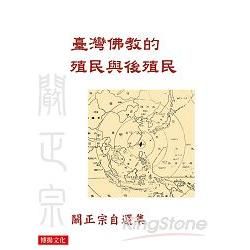青鞋印我痕
――學也無涯思
壹、古人智慧
南宋一代文人楊萬里(1127-1206)〈庚子正月五日曉過大皋渡〉一詩云
:「霧外江山看不真,只憑雞犬認前村;渡船滿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
。」楊萬里是紹興24(1154)年的進士,曾任太常丞兼吏部右侍郎、吏部員
外郎,因反對鐵錢行於江南諸郡而辭官歸里。淳熙7(1180)年庚子新年間
,楊萬里在一個大霧茫茫的清晨時刻過大皋渡,心有所感地寫下這首傳唱數
百載的詩文。大皋渡位於江西省中部偏南,為吉安市所轄的泰和縣境內,因
縣北八十里有大皋渡城,蓋以大皋渡名。其實,楊萬里還另一首膾炙人口的
詩〈桂源鋪〉:「萬山不許一溪行,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
堂溪水出前村。」這兩首都有他極高的人生智慧。
在前路難辨的水路中,只憑雞犬相聞,一路逶迤前進,在已經積滿厚雪
的船板上無意中印踏出青鞋痕。想必當時渡船定如過江之鯽,船上多賢之士
不免踏雪尋蹤,然當楊萬里從自己的渡船上印出第一痕之後,步步似乎都有
了方向。「青鞋印痕」看清自己的腳步,與船家同在霧中摸索,寒晨雞犬相
聞中知道又經一村了。
貳、三位老師
從無常的定律言,命運不該是天注定。齠齔之年,親族命算謂我將當「
和尚」。年幼時對什麼是「和尚」我一無所知,也不放心上。對宗教也沒什
麼特別偏好,高中輟學後,開始感受人生的「苦」。及從嘉義北上重考,進
入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今世新大學前身),一本〈心經〉開啟入佛因緣。
世新是一個學風極度自由的學府,因「臺大哲學系事件」而被臺大解聘
的王曉波老師,當時就在世新任教,開設哲學概論課程。王老師第一堂課的
第一句話「教授就是會叫的野獸」,至今音猶在耳。世新自由的學風,深深
影響了我的學與思。
畢業服役後,1985 年末至1986 年間即服務於佛教雜誌、出版業,之間
雖仍摸索佛法,然始終未有確定目標與方向。1989 年9 月,原佛教雜誌社負
責人赴美進修,於是將雜誌交予我,繼而專心於佛教文化的經營。在編採的
過程中,與佛教文化交涉日深,結識的佛門善知識倍增。
1990 年在為日後重拾課業的準備中,先於文化大學夜間部選修黃慶明
老師的理則學(邏輯學),他也是涉及「臺大哲學系事件」的相關老師之一
。而透過邏輯學的學分,雖然對於佛教哲學研究有所助益,但始終無緣進入
哲學學門。由於投身臺灣佛寺與人物的採訪工作,深覺無論從義理或歷史研
究,近代日本佛學研究皆是世界重鎮,何況日本曾殖民臺灣半世紀,意識到
日文可能會是將來研究的工具。1992 年以一整年的時間在永漢日語學習,從
五十音一直上到高級班結業。1993 年夏,在楊白衣夫人楊林寶璧的引薦下,
插班進入京都佛教大學(通信教育),校方准從大三讀起,但考量自己的日
文尚不足應付,於是選擇從東洋史專攻二年級開始。
佛教大學的通信教育,有些類似臺灣的空中大學,每年必須於暑假至少
一個月在校上課、考試,稱之為schooling,其餘時間在家研修學校規定的課
程及撰寫報告。原本需讀三年,但由於家庭與工作忙得分身乏術,於第三年
開學後即辦退學。但在京都兩年的兩個夏天,因接觸日本近代佛教的海外布
教過程資料,進一步引發後來研究臺灣殖民時期佛教的因緣。其中在日文的
教授、解說,楊師母是我的恩師。楊師母畢業殖民時期的北二女,日文造詣
深厚,1957 年曾在新竹一同寺女眾佛學院旁聽一年,法名「如實」,後下嫁
楊白衣老師,為楊老師從事中日文佛學著作翻譯工作。這三位老師對我日後
在佛教的研究工作上啟蒙不少。
參、初履學涯
從1986 年至1995 年的十年新聞編採過程中,累積了許多資料,田野調
查的體驗,進一步引發臺灣佛教史研究興趣。佛教相關學術研究會亦如雨後
春筍,常在採訪過程中聆聽了學人的研究發表,然部分對於臺灣佛教的歷史
討論,與我在田野的見聞,乃至所蒐集的史料並不完全吻合,於是便思考撰
文回應一些問題。於茲走進了學術研究的領域渾然不知。
1996 年夏,現代佛教學會舉辦首屆「臺灣佛教研討會」,會長為楊惠南
老師,承其錯愛,於會中發表個人學涯第一篇調查研究論文:〈戰後臺灣佛
寺的轉型與發展──以南投地區佛寺齋堂為例〉,論文背景正是配合當時調
查南投地區佛寺與人物的歷史研究。此後與現代佛教學會關係日深,諸多啟
蒙者如藍吉富、楊惠南、蔣義斌、林光明、蕭麗華、恆清法師等老師,更因
為這樣的因緣還忝任兩屆現代佛教學會蕭麗華、賴賢宗會長的秘書。從而每
年幾乎都發表一至兩篇取材於田調的臺灣佛教史相關研究。
2000 年元月,為印順法師的祝壽學術研究會上,在陳一標老師的鼓勵下
,於翌年報考玄奘大學宗教研究所第一屆在職碩士專班。諸多宗教領域的視
野開拓,如開設《大唐西域記》的黃運喜老師、《宗教社會學》的鄭弘岳老
師等等,豐富了宗教學的素養。2004 年1 月口試通過,決心朝歷史學研究邁
進。2005 年報考廈門大學與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僥倖同獲錄取,因
地緣關係遂捨廈大而就成大。
成大一向以臺灣史與明史享譽學界,五年的成大研究生生涯,明代佛教
史陳玉女、明代海洋史鄭永常、臺灣宗教文化與日文陳梅卿、日本文化史顧
盼等諸位老師給予醍醐灌頂般的指導,是學術生涯的重要轉折。
肆、做好一件事
投身佛教學術研究是人生意外之旅,雖最終與「和尚」無緣,亦不信宿
命,但冥冥之中似與佛教深緣難解。已故的世新學長李國修(1955~2013)因
為父親的一句「人,一輩子能做好一件事,就功德圓滿了」,深重地影響他
的一生。資質駑鈍如我,相信勤能補拙,每當吟味前人充滿大智慧之語,時
心有所感。惕勵自己這一輩子也能做好一件事。
臺灣佛教的研究,因歷史很短,看似容易,其實不然。明鄭清代以降,
方志對佛教的記載十分有限,出現的僧侶雖多,但乏生平背景,更遑論宗派
思想,這樣的佛教面貌很難清晰。研究者所能做的亦十分有限。在此不利的
條件之下,結合田野調查乃必要之舉。
僧侶的活動場域,除一般所熟知的佛寺外,民間宮廟絕不能忽略。無論
是媽祖廟或是關帝廟,甚至城隍廟,清代以來都不乏僧侶住持。這從近年來
越來越多被發現的祖堂牌位得到佳證。祖堂牌位往往有歷代住持名號,或所
屬宗派別,單獨的牌位背後,常常有該僧人的生卒年,甚至牌位下會鑽洞紙
藏僧侶生平資料,這大都是方志不曾記載的,皆是拼湊臺灣佛教的第一手資
料,如果不作田野,將一無所獲。
祖堂牌位固不可小覷,而跑田野時又往往可以獲得第一手資料,如手抄
本、善本經書等等,到日本殖民時代,甚至有許多珍貴照片,這些都是研究
佛教、齋教流傳、演變的文獻。
清代臺灣佛教研究一般以為難脫閩粵佛教影響,但其他鄰近地區僧侶來
臺的作用當不可忽視。如臺南開元寺首任住持志中和尚乃是來自江西,屬曹
洞宗湛然圓澄(1561~1626)一系,又如大甲鎮瀾宮僧侶歷代祖師演字與普陀
後寺一致,極可能是來自浙江普陀山法雨寺。凡此種種,絕不能理所當然地
認為,臺灣移民主要來自閩粵,佛教必全然受閩粵影響,就像戰後大批大陸
僧侶來臺,以江浙省籍為多,其影響較之閩粵更為深重一樣。
清代來臺僧侶系譜集中在贛、浙、閩、粵四省,如能釐清來臺僧人的身
份背景,將可推進臺灣佛教的研究,除文獻的研究外,對該僧人的原鄉祖庭
的田調將是必須的。最新例證,雲林北港朝天宮2012 年在福建仙遊找到當
年帶著媽祖來臺的開山住持樹璧和尚(1664-1723)的墳位,俗名嚴瑞義的樹
璧,出家仙遊龍紀寺,30 歲(1694)抵笨港創建北港朝天宮,46 歲回到故里
。1 如果沒有朝天宮相關人士到仙遊從事調查,當不會發現樹璧和尚的相關史
蹟。渡海來臺僧臺南開元寺首任住持志中行和的生平資料,透過田野調查或
許有一天也將出土,屆時研究臺灣佛教又將向前一步。
個人學涯從新聞相關科系,轉入宗教學門,最後歸於歷史。始終未從一
而終,時節變化與個人興趣的投射,是因緣相續的結果。雖然各學門的訓練
都觸及,但畢竟難比一以貫之的學習。故在長期的佛教文化鑽研上幾乎是傾
向於佛教史的研究,而方法學即集中於文獻與田調的比對應用,其中田調工
作某個程度上又相似於新聞學的採訪報導,至少個人對這兩方的結合是極為
自然。
臺灣佛教的研究,一方面是漢人移民歷史不過四百年,二方面自明鄭清
代以降,佛教與其他宗教都不是方志所重視的,往往只有寺廟歷史背景,而
1 蔡維斌,〈北港朝天宮傳說迎媽媽來台的和尚找到了〉,《聯合報》(2013年11月22日)
,A26。
僧侶住持僅聞其名,難得其生平資料,這在在都使臺灣佛教史,甚或宗教史
難以入手,這也就是為什麼清代臺灣佛教始終沒有一部完整專書出版。
臺灣佛教的研究難以「宏觀」,歷史短、文獻乏是主因,故大部分都屬
「微觀」研究。但宏觀有宏觀的好處,微觀亦有微觀之長,並無優劣軒輊可
言。明鄭至日本殖民時期的臺灣是政治「邊陲」,亦是宗教「邊地」,加上
佛教自晚明以來即呈衰微狀態,其不受重視,甚至受人鄙視。日本殖民之後
,臺灣佛教被導入日本殖民佛教新觀念與新研究,初步提升了臺灣佛教研究
品質。
歷史學式的佛教研究在臺灣恐怕非主流,投身其中者也不多,鑑往知來
確是歷史研究的迷人之處,自己從最初的個別寺院、齋堂研究,過度至區域
史、交涉史的研究,似乎是漸漸地點、線、面連成一氣。從清代經懺、香花
僧受眾人鄙視的佛教,過度至殖民時期,及至戰後佛教漸成主流,這種極大
變化的歷史,於未滿四百年漢人移民史上繽紛呈現,不可不謂「驚天動地」
、「可歌可泣」。
投身於臺灣佛教的研究,沒有預設,談不上目的,卻成為生活的大部分
,自己的工作是佛教文化出版,在大學、研究所開的課是佛教史學或佛教典
籍專題,鎮日所思、所言、所行,無不與佛教有關,工作即生活,生活即工
作。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誠哉是言。放心於生活
,放心於學問。《莊子‧ 養生主》說:「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
無涯,殆已。」知識無邊無涯,故說學海無涯,生命有限,做好一件事,做
到哪裡就哪裡,那裡就是圓滿。
闞正宗
2013 年12 月17 日於淡水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臺灣佛教的殖民與後殖民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95 |
佛教總論 |
$ 440 |
中文書 |
$ 440 |
台灣研究 |
$ 450 |
台灣歷史 |
$ 450 |
宗教命理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臺灣佛教的殖民與後殖民
本自選集為作者近十餘年來,關心日本殖民時期以降的臺灣佛教歷史、文化及其人物,共收錄論文十七篇、附錄一篇。從殖民佛教到後殖民佛教,臺灣佛教的面貌多變,而曾經因政治因素而「扭曲」的樣貌,因臺灣解嚴後的「民主化」而有所回復。
作者簡介:
闞正宗
生於臺灣嘉義市,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教於佛光大學、玄奘大學宗教研究所、法鼓佛教學院。著有《臺灣佛教一百年》、《重讀臺灣佛教─戰後臺灣佛教(正、續編)》、《臺灣佛寺的信仰與文化》、《臺灣佛教史論》、《中國佛教會在臺灣─漢傳佛教的延續與開展》、《臺灣日治時期佛教發展與皇民化運動──「皇國佛教」的歷史進程(1895-1945)》等專書,以及相關佛教論文集數十篇。
作者序
青鞋印我痕
――學也無涯思
壹、古人智慧
南宋一代文人楊萬里(1127-1206)〈庚子正月五日曉過大皋渡〉一詩云
:「霧外江山看不真,只憑雞犬認前村;渡船滿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
。」楊萬里是紹興24(1154)年的進士,曾任太常丞兼吏部右侍郎、吏部員
外郎,因反對鐵錢行於江南諸郡而辭官歸里。淳熙7(1180)年庚子新年間
,楊萬里在一個大霧茫茫的清晨時刻過大皋渡,心有所感地寫下這首傳唱數
百載的詩文。大皋渡位於江西省中部偏南,為吉安市所轄的泰和縣境內,因
縣北八十里有大皋渡城,蓋以大皋渡名。其實,楊萬里還另一首...
――學也無涯思
壹、古人智慧
南宋一代文人楊萬里(1127-1206)〈庚子正月五日曉過大皋渡〉一詩云
:「霧外江山看不真,只憑雞犬認前村;渡船滿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
。」楊萬里是紹興24(1154)年的進士,曾任太常丞兼吏部右侍郎、吏部員
外郎,因反對鐵錢行於江南諸郡而辭官歸里。淳熙7(1180)年庚子新年間
,楊萬里在一個大霧茫茫的清晨時刻過大皋渡,心有所感地寫下這首傳唱數
百載的詩文。大皋渡位於江西省中部偏南,為吉安市所轄的泰和縣境內,因
縣北八十里有大皋渡城,蓋以大皋渡名。其實,楊萬里還另一首...
»看全部
目錄
自序 1
著作年表 6
圖集 13
前篇:殖民時期 21
第一章 日本殖民時期臺灣佛教的特點與研究 23
第二章 日僧佐佐木珍龍的臺灣開教
――佛教曹洞宗在殖民初期(1895-1901)的活動 51
第三章 殖民初期(1895-1906)日本東本願寺派在福建的活動
――以「廈門事件」為例 75
第四章 殖民...
著作年表 6
圖集 13
前篇:殖民時期 21
第一章 日本殖民時期臺灣佛教的特點與研究 23
第二章 日僧佐佐木珍龍的臺灣開教
――佛教曹洞宗在殖民初期(1895-1901)的活動 51
第三章 殖民初期(1895-1906)日本東本願寺派在福建的活動
――以「廈門事件」為例 75
第四章 殖民...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闞正宗
- 出版社: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5-26 ISBN/ISSN:978986575715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22頁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台灣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