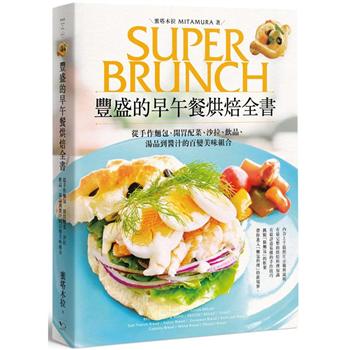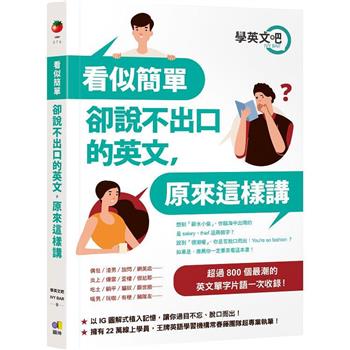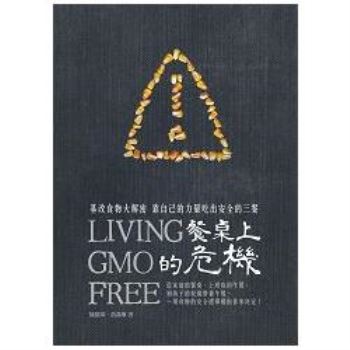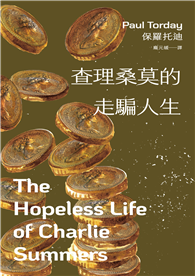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情繭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134 |
文學小說 |
電子書 |
$ 190 |
文學小說 |
$ 238 |
小說/文學 |
$ 246 |
大眾文學 |
$ 252 |
小說 |
$ 252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情繭
八年的記憶在一場車禍後被遺忘,
她想找回失去的人生,
但真相卻似被層層包裹在蠶繭中,無法觸及……
在倫敦街頭目睹好友車禍昏厥的艾蘿,醒來後躺在醫院病床上,遍體鱗傷的她被告知出了車禍。
她強忍身體不適尋找好友斐恩,但護士不但告訴她沒有斐恩這個人,醫院中所有人像是熟識她一般稱她為「尹芳」,而且還多了一位醫師未婚夫?!
她走進洗手間,注視著鏡中的影像,這再熟悉不過的面容卻隱約透露出一股莫生感,彷彿將一張張透明投影片疊起,明明同款同樣,上面的字跡圖形就是無法準確拓合。
猶如鬼魅的護士、與現實交錯的夢魘,讓她懷疑是否有人要害她,而她也快要分不清自己究竟是「艾蘿」還是「尹芳」……
作者簡介
韓商羚
臺大中文系、英國約克大學藝術史碩士畢。高中時開始寫作,於當時課本中讀到曹丕《典論‧論文》,以及劉勰《文心雕龍‧情采》,遂以此二文為創作圭臬,至今不改。曾擔任澳洲《東方郵報》「光陰博物館」專欄作者、發表各類作品於報章及文藝月刊。曾獲金筆文學新詩獎、紫絲帶小說獎、中華電信大賞文學組小說獎。現居住於美國西雅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