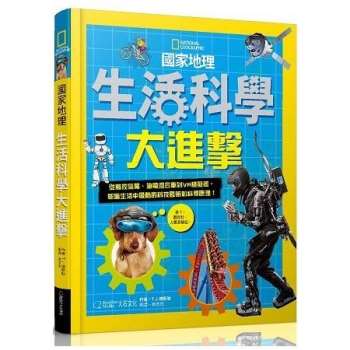★本書榮獲第35屆金鼎獎圖書類非文學獎藝術生活類入圍
這本書將「古典音樂」放在文化、權力、政治、國家等多重場域的分析語境裡,政治化(politicise)了西方古典音樂在台灣與全球的意義生產,和行動的可能與限制等問題,這是方向基進、具有開創企圖和視野的學術計畫。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暨系主任 郭力昕
本書作者受到兩種迥然不同的學術訓練養成,先音樂藝術,後社會科學,皆游刃有餘,這樣的跨領域人才,並不多見,但我始終相信這背後仍源自於他對於藝術感受的敏銳。
音樂家、雲門舞集基金會董事長暨總統府國策顧問 申學庸
本書視交響樂團為社會行動者,將Bourdieu的場域(field)理論,重新設計為:「交響樂團行動者-古典音樂場域-文化場域-權力場域-國家政權/社會空間」,以線上交響樂團(on-line orchestra)、離線交響樂團(off-line orchestra)縱走當代生活場景。
作為一種社會性譬喻(metaphor),它藉國家交響樂團深描台灣社會、文化場域轉型;藉YouTube線上交響樂團,刻畫全球性的文化、藝術典範轉移。
它關於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身分認同(identities),也本於國族(the national)、在地(the local)與全球(the global)
我必須說,作為廣義上古典音樂社群的成員,以社會學的方法與理論來解釋古典音樂在變動社會裡的運作,並非源自於優雅的「跨領域」研究風潮,我實質想要回到一項基進的社會學議程,即視古典音樂的現狀,為一項有問題的問題(problematic problem),我想要以出身音樂學院實作者的反身性經驗,在歷經社會學場域方法及理論訓練,並途徑音樂、文化及社會現場的田野觀察,來反思古典音樂。
作者簡介:
作者:黃俊銘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學士、碩士,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社會學系文化與社會研究所碩士。
曾任《聯合報》文化組記者,同時任《西日本新聞》(Nishinippon Shinbun)亞洲專欄主筆,曾連續獲第十八、十九屆吳舜文新聞獎。
目前專任於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音像藝術學院應用音樂學系,並兼任於國立中山大學音樂學系,曾擔任古典樂刊《MUZIK》客座總編輯。
2010年以「文化實作及其公共性的浮現」獲國科會年輕學者學術輔導獎勵,並擔任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國家交響樂團調查研究」計畫主持人。
近期入選學術會議發表:台灣社會學年會、CSA文化研究學會年會、政大傳播學院「數位創世紀」國際研討會。
視覺設計者:李根在
旅美台灣設計師。
1991年實踐專校應用美術科畢業,2001年台灣師範大學設計研究所畢業,紐約Pratt學院。
歷任國華廣告創意部設計,太一廣告助理藝術指導,於1996年創辦李根在平面設計工作室。2001年任教於明志技術學院。
現任台灣藝術大學客座副教授。
2002年赴美,在美期間,嘗試多種不同媒體,並與不同專業人士合作,如攝影師、動畫師,並從事藝術創作。
從1996年自行創立工作室以來,獲得台灣及海外專業設計獎項及參展超過兩百餘次,包含 D&AD獎、圖形設計、海報、型錄年鑑白金、金獎、傳遞藝術年獎、紐約字體指導俱樂部年獎,One show設計獎,Red-dot 傳遞設計獎,How 雜誌國際設計競賽,自我宣傳設計競賽、東京字體指導俱樂部年獎、香港設計師協會金獎、IDN亞太平面設計大賽全場最佳平面設計大獎、時報廣告獎等。
2002年受邀與其他三位台灣設計師共同出版設計作品集《放4》(台灣長松文化出版)。
2003年獲推薦選入紐約費頓出版社出版Area一書,為100位國際注目的平面設計師之一。
2005年柏林 Hesign出版社出版國際平面設計一百單八將,選為108位國際平面設計師之一。
2005年出版【Fame】專輯。
2006年受邀評審紐約廣告節設計部門。
2006年個展於紐約蘇活區456畫廊。
2007年個展於中國南京藝術學院。
2010年受邀評審台灣國際學生設計大賽。
2010年受邀評審澳門視覺藝術節。
章節試閱
第一部
Part One
文化實作及其公共性的浮現
Cultural Practice and the Emergence of Its Publicness
第二章 國家交響樂團的研究定位:文化與社會學的觀點
Chapter Two: The 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e and Sociology
本章透過Giddens對結構(structure)與能動性(agency)的討論,來說明國家交響樂團如何進行音樂實作,包括它如何協商它自身的古典音樂身分;如何協商社會意義;如何穿梭於不同場域,而形成「公共」;如何身處結構,而能維繫能動,並藉 Bourdieu 的「場域」(field)理埨,探討交響樂團行動者與不同層次權力場域之互動。
本章先從英國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學者 Williams(1981)對於文化(culture)如何成為社會學(sociology)主題而形成之「文化社會學」(sociology of culture)出發,來對於上述研究主題做理論、方法及文獻上的定位;本節透過文化的界定及用途(in use),來定位國家交響樂團作為研究主體,可行性的聚焦面向。
第二節回顧社會結構與行動者之間互動的爭辯,包括 Giddens 聚焦於人經由行動而再生產社會結構的「能動性」討論;以及 Bourdieu 強調資本(capital )、慣習(habitus)以及場域爭鬥(field)的實作邏輯,試圖定位國家交響樂團作為行動者,在不同場域的重疊與交互作用經驗,如何成為具能動性的主體,不斷滲入被結構的結構(structured structures),亦同時成為結構中的結構(structuring structures)。
第三節,本節以國家交響樂團作為公共文化機構,如何與「公共性」對話,為後面章節研討「行政法人化交響樂團」預做研究定位。本節藉 Habermas 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結構轉型做相關考源及評估主張,包括它如何浮現、衰退以及再封建化,用以接合行政法人論述。另外,本節朝向 Bennett「將政策放入文化研究中」(putting policy into cultural studies)的主張,認為 Bennett 以 Foucault 的 governmentality(治理性),可作為修正並重建Habermas的公共領域的參考,因而批判理性及公共性仍具潛力存在於現代的文化機構;而這項意見,將作為本研究考察國家交響樂團之能動表現的研究意喻(implication)。
第一節 交響樂團作為「文化」
2.1 Symphony Orchestra as “Culture”
如同 Williams(1983)所言,「文化」(culture)是英語裡最複雜的二、三個字詞之一,它在早期的用法裡,意指一種「過程」(process),比方對農作物及動物的照料,與栽種、培植(cultivation)有關;後來,它的延伸意涵逐漸從自然界擴充至社會教育場域,演變成為文明(civilization)的同義詞,並以形容詞「文化的」(cultural)暗示與禮節及品味相關,而在現代用語裡,唯有在它指涉藝術、知性及人類學意涵時,才會被作為獨立名詞使用(Williams, 1983: 87-93)。
一種文化會有兩面性,其一為已知的意義與意向,此為該文化的成員經習訓可知,另一則是新的發現及意義,供人檢視。這些是人類社會及心靈的平常過程,透過它們,我們得以看穿文化的本質:文化總是關乎傳統及開創性的,它具有最平常的共同意義及最精細的個別意義。因此,我們使用「文化」表達兩種意涵:一、意指「全部生活的方式」(a whole way of life),這是通用的意義。二、意指藝術與學習,這是發現與創造力的特殊過程。部分學者擇其一意涵,我則堅持兩意涵皆取,堅持兩者相連的特殊性,我對我們的文化所提問一般及相通的目的,還包括深層個體意義的問題。文化是平常的(ordinary),存在於每一個社會及每一個心靈。(Williams: 1989: 4)
首先,Williams 放棄了部分學者先驗式地將「藝術文化」與「大眾文化」對立起來的意理,而堅持將「最平常的共同意義」與「最精細的個別意義」連結起來;意即,他同時承認人類學式的「平常性」,並點出文化的雙重性:即認為文化乃「全部生活的方式」,但不忘它永遠具有新的發現及意義(例如許多藝術作品所宣稱擁有的「奧秘」)。McGuigan 認為(1992: 27),Williams 刻意與不加批判的民粹主義及大眾消費加以區別,意在兼取文化的雙重性,因而建立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意涵的共同文化(common culture)。
William 從字源的考察,提醒了我們一件事:即文化被暗示與品味、藝術場域有關,同它的早期意涵,是一種演變而來的「過程」。但是,身為研究者,我們必須接著追問,是什麼樣的歷史發展與社會變遷,選擇(select)了當今的「文化」。Williams 提出了文化的三個層次,也認為唯有如此深究,才能分析「文化」(1961:49):一、「活生生的文化」(lived culture),只有生活在相同時空的人,才可以體現。二、「記錄的文化」(recorded culture),可稱為時期的文化(culture of a period),從藝術到日常生活事實無所不包。三、連結「活生生的文化」與「記錄文化」之間,一種經過「選擇性傳統」之文化。
首先,Williams 說明了文化的特定時空性質,他的重點在於:文化必須透過在歷史現場的「親身經驗」才可以顯現。他用「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Williams, 1961: 48)來指出這種特定社會情境、社群及經驗所共享;而第二個層次「紀錄的文化」,就是當「活生生的目擊者保持沉默時,用最直接的方式來表達文化」(Williams, 1961: 49)。不過,Williams 強調的是,被紀錄的文化是「經選擇」來的作品,或許可以透過它來接近(approach)這種「感覺結構」,卻必須意識到作品的紀錄涉及第三層次「選擇性傳統」的支配,總無法完全恢復生活的感覺(that sense of the life)(Williams, 1961: 50)。
文化無法透過載體,而真正紀錄所有生活感覺,如同樂譜,固然可以紀錄作曲家的樂思、靈感的形式,卻無法紀錄靈感的細節,又如影音科技固然可以補捉「真實一瞬間」,卻無法紀錄「一瞬間」的情感細節、時空氛圍以及身心體驗。
透過「紀錄文化」,Williams 顯然很早就察覺文化的「可中介性」及「不可中介性」之雙元的媒介特質,中介的經驗帶我們去碰觸文化傳統選擇下的「感覺結構」,但是,即使紀錄的工具從圖形、文字、樂譜進展至影音雙效,卻無法完全捉摸;我們因此可以說,通過媒體中介,它同時擁有「可紀錄性」、以及由於生活感覺細節流失之「不可紀錄性」。
Williams 倡議的文化分析主要聚焦於第三種層次。他認為一個社會的傳統文化總是傾向於呼應當代的利益及價值體系,而我們總是低估了文化傳統作為一種持續的「選擇」(selection),實則也是一種對文化的「詮釋」(interpretation)(Williams, 1961: 52);如同Storey(2001: 47)所指,我們唯有透過考察「歷史裡的文化表現」,以及「在當代文化如何被使用」,「真正的文化過程才會浮現」。
因此,這項選擇的過程仍在持續進行,因為它遵循社會的進程,作品被翻案重新成為「經典」仍有可能,作品是社會性的選擇,Williams 藉此提醒我們,作品的未來重要性,是無法預則的(Williams, 1961: 52)。
Williams 小心翼翼地的暗示了文化乃是一系列利益、價值及社會性的選擇與詮釋,而非毋須驗證-如同多數「偉大作品」所宣稱,可見他對於隱藏在文化背後的選擇機制、社會意義協商以及無法完全中介「感覺結構」,相當敏感。
不過,Hall(1980a: 57-72)對於 Williams 的文化觀,則有一些批評。他以兩種典範(two paradigms)稱1950年末新左派、代表英國傳統的 Hoggart、Williams 及 E. P. Thompson 為「文化主義」(culturalism),強調人作為主體及表達的經驗拉力(experiential pull);而 1960、1968 年後代表法國傳統輸入英國的 Lévi-Strauss、Barthes 及 Althusser 等為「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聚焦於結構情境(包括語言、意識形態及階級)的作用(Ibid, McGuigan, 1992)。Hall 主要的用意是,文化主義關注的是「文化」,而結構主義則關注「意識形態」(McGuigan, 1992: 30),而這兩種分析文化的典範都有不足之處;他認為應該有一種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互不排斥的實作,卻又能同時將兩者接合起來(articulated)的不同形式(Hall, 1980a: 72)。
Hall 的重點,就在於強調「接合」(articulation)的作用。他解釋「接合」在英語字義上同時具有「清楚地表述」以及「連結」(connected)的雙重意涵(Grossberg and Hall 1986: 53):「接合」如同一種暫時性、卻不必然從屬(belongingness)的連接方式(用Hall的話來說);文化主義強調之人的作用,與結構主義關注的意識形態,可以透過「接合」(articulation),因而在表意實踐上將諸「清楚地表述」(articulation)。
Hall很可能簡化了 Williams 在文化上的洞察,Williams 不僅關注經驗及意義的生產,連同他談論的「選擇性傳統」,都已相當聚焦於文化生產的機制(institutions)、工具(means)及社會形構(social formation)等文化的社會過程。而 Storey(2010)亦認為,Williams 提出文化是一組「被實現的表意系統」(a realized signifying system, 1981: 209)顯示:文化是由被分享、被爭奪的意義活動所組成,已與Gramsci之社會權威為鞏固霸權(hegemony)所從事的意識形態抗爭相呼應。若我們考察 Culture(《文化》, 1981)一書裡,Williams 倡儀並具體地命名的「文化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culture),應該聚焦於以下幾個面向,亦突顯了類似的關懷(ibid.: 9-32):
一、 文化生產的制度(institutions)與形構(formations)
二、 文化的特定生產工具(specific means of production)及其與社會的關係
三、 文化產品的身分化社會過程(identifications)
四、 文化產品的藝術形式(artistic forms)
五、 社會及文化的再生產過程(processe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六、 透過表意系統(signifying systems)及社會形構(social formation)之文化組織(cultural organization)
Williams 透過上述六個面向的研究關注,打破了文化僅聚焦於文本意義、或意識形態、或霸權、或生產邏輯的限制,而將生產(production)的文化、社會及意識形態過程-借用 Hall 從 Gramsci 脈絡而得來的靈感,做一項突出的接合(articulation),它的用意在於,透過意義接合,更「清楚地表述」(articulate)文化產製的所有細節。
基於以上,本研究主張一種結合感覺結構及以人作為主體的社會性、歷史性、「選擇性傳統」的文化主義式的研究取徑;以及以語言、意識形態及霸權為聚焦之強調結構情境宰制的取徑。如同 Hall 與 Du Gay 提出的文化迴路概念:將再現(representation)、身分(identity)、規約(regulation)、消費(consumption)、生產(production)等五個層面「接合」(articulation),作為重新組織個別主體在文化過程裡的所有意義。再來,本研究藉此進一步勾勒出一套本文稱之為「文化機構(機制)研究」的研究方案,用以對「國家交響樂團」個案做所有文化過程、音樂實作、社會過程及意識形態過程的「接合」,以確保能「清楚地表述」(articulate)所有文化細節。
第二節 場域、結構與能動性
2.2 Field, Structure and Agency
國家交響樂團作為一種文化生產,首先應該被聚焦在,它是在什麼樣的社會情境下形成它的生產。Giddens 與 Bourdieu 分別以社會學裡「結構」(structure)與「行動」(action)以及「反思性」(reflexivity),表達了他們的現代性方案。
Giddens 在發展「結構化理論」的初期,曾經特別指出對於文化生產的省察。他認為文化生產的理論,必須包含能充分代表「人類能動者本性」(the nature of human agents)的理論,而結構主義者卻經常低估了闡述人類能動性的「實作意識」(practical consciousness)與「行動的情境性」(contextuality of action)等兩項要點(Giddens, 1987: 214)。
「實作意識」指的是人類具有一種反思性地監控其作為的本質,「行動的情境性」則因為反思性作用,而視情境為行動者不斷組織資源與規則介入結構的過程(ibid.: 215)。Giddesn 指出了,當我們聚焦於社會(the social)時,無可迴避卻又經常忽略的主題,即人在社會結構裡的能動作用。傳統社會學存在著「結構」與「行動」的兩元對立,但 Giddesn 認為這無助於解釋現代社會的矛盾運作,他以「結構的二元性」(duality of structure)同時勾勒了「結構」與「能動性」的交互作用,意即結構不再作為限制行動者權力的結構,因為行動者的能動作用不斷介入結構,也改變了結構。
Giddens「結構化」(structuration)理論,背後的核心概念即是「反思性」(reflexivity)的導入,反思性使得 Giddens 樂觀地相信,現代社會逐漸建立在一以反省、自我監控為生活形式的方案中。如同 Dodd(1999)指出,對於 Giddens 及 Beck 來說,現代性的方案沒有結束,而是透過反思性的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使得現代化亦更新了(renewal of modernity),它不但改變了社會結構及個人認同,更重要的意涵是,它意味著反思性已在當代社會中實質上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
Giddens(1984: 3)將反思性定義為:「持續流動的社會生活所具有受到監控的特徵,而不僅是自我意識」;它包含了「日常社會實踐中的使用與再生產知識(?),因此知識既是社會行動的資源,也改變了行動的特徵」(?)(Dodd, 1999: 189-190)。Giddens 的立論,帶有很強烈的實作意涵,意即組成人類行動的過程,並不單純是由人的意圖發動(或 Giddens 所稱「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ness),而是行動者對於「持續流動的社會生活」受到監控所進行反思的結果,因此,他建議將反思性理解成一種理性化的動態過程,意即:「根基在人類展示持續性的行動監控,也期待其它人如此展現的過程」(ibid.),而非僅是受到個別意圖、理由及動機所進行的反思行為。
Giddens 將反思性套用在他的結構化理論裡,於是乎社會關係隨著時間形成一種具結構、模式化的特徵,而此模式化的關係是一種再生產的過程,因而它組織了一種動態的行動與結構的相互介入(Dodd, 1999: 187),而此介質在 Giddens 看來,即是反思性的結果。
「反思性」很大程度提供了社會學定位現代社會之各種轉變與現象,一項解釋的資源。照Giddens的見解,反思是持續進行社會監控的再生產,它形塑了結構,也再結構化了結構,那麼,透過反思性,我們要怎麼來看待「結構」與日常生活的關係,它如何組成抑或重建我們的慣例?
Giddens(1984: 35-36)借 Lévi-Strauss 的「可逆的時間」(reversible time)來論證反思性對於日常經驗的作用,他認為個體的生命雖為「不可逆的時間」(irreversible time),但他再引「社會再生產」、「反覆性」(recursiveness)等概念提醒了日常生活在時間流動裡,仍是具重複性的。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他主張日常生活的「慣例」(routines),可被誤讀為結構的「基礎」(foundation),而認定社會制度以此為基礎;Giddens 真正的意思是,人與社會組織了日常生活的慣例,但這慣例透過反思的作用,形成「可逆的時間」,因為人會透過監控而具體實作可逆的慣例,而慣例總中介著人類的身體與感覺的資源,因此,這些慣例得以再度影響社會系統。
反思性(reflexivity)恐怕是伴隨現代性(modernity)最重要的課題,Giddens與 Bourdieu 都強調反思性在「結構」與「行動」之間的中介的性質。若比較之,從文化生產的角度來看,倘若 Giddens 的反思性方案是指人類能動性具有全面性社會監控與自我監探的「結構」能力,那麼 Bourdieu 則更強調的是,將經驗視為一項置於社會空間的主體(Bourdieu, 2009: 319,因此視能動性的主體,如何極細 緻地透過社會結構裡不同權力層次的場域,以慣習操作,進行複雜的資本轉換與協作。
◎文學及藝術場域的經濟邏輯
若論 Bourdieu 對於藝術社會學的貢獻,是他破除了藝術作品那「不可言喻」(ineffable)的部分。在 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藝術的規則》,1996)裡,Bourdieu 借福樓拜的小說《情感教育》,發展出一套直視諱莫如深的文學及藝術場域的運作法則:他用場域(field)來勾勒藝術家與權力場及社會空間中的文化生場的爭鬥範圍;他以不同「資本」(capital)間的複雜移轉來描繪藝術家在場域裡的動態;他以「慣習」(habitus)來說明累積資本的實作(practice)。
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係之一個網絡(network),或一個構型(configuration)。正是在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們強加於占據特定位置的行動者或機構上的決定性因素中,這些位置得到了客觀的界定,其根據是這些位置在不同類型的權力(或資本)-佔有這些權力就意味著把持這一場域中利害攸關的專門利潤(specific profit)的得益權-之分配結構中實際的和潛在的位置(situs),以及它們與其它位置之間的客觀關係(支配關係、屈從關係、結構上的對應關係等等)(Bourdieu, 2009: 158)。
不過,為何 Bourdieu 特別以文學與藝術場域作為場域理論介入的重點?若對Bourdieu的文獻做全面性的回顧將發現:與其說他對文學與藝術場域情有獨鐘,倒不如說他對於各種宣稱以自律、精神文明作為運作邏輯的場域,包括新聞場域、知識分子場域都抱持著極大的熱情(Bourdieu, 2005)。曾親炙 Bourdieu 本人的高宣揚(2002:139-140)就認為,文學與藝術場域在社會生活中扮演特殊的意義,藝術家往往不願直接參與社會、政治與經濟場域的爭奪;他們雖遠離政治、經濟,卻是以「巧妙的方式,迂迴地參與了社會的權力正當化和再分配的鬥爭」。
Bourdieu 以文學及藝術場域為例,繪製了一幅複雜資本交換的象徵場域配置圖(Bourdieu, 1996: 124)。首先,他將場域從內到外分為文化生產場域(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權力場域(field of power)、以及國家社會空間(social space(national);以文化生產場為例,它再細分為「小眾生產的次場域」(為藝術而藝術)及「大眾生產的次場域」,Bourdieu 認為兩個次場域基本上服膺生產和流通的兩套相反的經濟邏輯,可以說,它是促使「藝術的規則」得以運作的「潛規則」:一方面,有一套純藝術的反經濟(anti-economic)邏輯,建立在無私的價值、以及對於商業利益的否定上,它背後的意理來自於「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自律性原則。但 Bourdieu 提醒,這樣自律性的建構對於長期來講,反而使之累積成為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的發展,因此,這樣的象徵資本表面上「無私」,卻是非常「經濟資本」的。
另一方面,Bourdieu 仍在文學及藝術場域看到一套服膺於經濟的邏輯,它們將文化財視做與其它交易一樣,著重它的即時或暫時性的成功,即依賴客戶的需求來調整自己的內容,但即使如此,仍需要兼顧經濟利益及象徵利益,以確保其作為知識機構的場域特徵。Bourdieu 強調,文化及藝術場域同時存在「短期生產循環」及「長期生產循環」的機構,前者盼立即獲利、回收,後者則著重在於「文化投資」,目前毫無市場、完全將希望寄放在未來。
可以發現:「小眾生產的次場域」與「大眾生產的次場域」遵循層級化的相反方向流動,導至自主程度愈高,則兩個次場域的落差就愈深,例如,前者自主性愈強,它的特定象徵資本則愈豐,但暫時性的經濟資本卻趨緩;反之,後者自主性低,特定象徵資本偏弱,但暫時性的經濟資本反趨強。Bourdieu(ibid.: 148)藉此說明了文學及藝術場域一項矛盾的運作邏輯,意即,即時性的成功總帶有一些令人懷疑的成分,彷彿它削弱了無價的作品(priceless work)的真誠性,而單純進入一個商業交易的買賣關係。因此他也認為,經濟資本從來無法確保場域裡的特殊利益,除非它再次的轉換為象徵資本;無論對於藝評家、經紀人、出版商或劇院經理,唯一合法累積利益的途徑,就是製造出一種被熟知而且肯認的聲名(a name that is known and recognized)。
不過,Bourdieu(1996: 343)特別提醒,文化生產場域存在的自主性意理,各種權力及社會實作場域變化多端,必須考慮到不斷翻新的阻礙及權力,換句話說,它是資本不斷本競爭、重建及轉換的場域,比方教會、國家或大型經濟機構,或者掌握特定產品及流通的報紙、出版社及廣播電視等,這些勢力都透過統治階級舖排的議程,在權力場域裡進行資本交易。
Bourdieu 透過「藝術的規則」,打破了「結構」與「行動」的對立,而將人類的能動表現整合到透過經濟資本與象徵資本轉換的場域之中,如同 Wacquant (2009: 49)所說,場域是衝突與競爭的空間,藝術家的諸多行為實踐,要透過考察自律場域之外圍的權力場域(field of power)(Bourdieu, 1996: 215),才得可窺得真貌。
照 Bourdieu(ibid.: 216-216)的解釋,文學及藝術場域被權力場域包圍,用以暗示於它居於被統治的地位,而權力場域則是一座行動者們與各種機制(構)之間展示力量(force)關係的空間,因為權力者深知,挪用文化場域或經濟等其它場域的資本,是持續佔據權力場域、維持優勢地位之必要確保。同時,對於文學與藝術行動者而言,權力場域也是各種資本持有人彼此競爭之地,因為藝術家苦心「為藝術而藝術」,經過象徵資本累積,需透過權力機構獲得認可,轉換成為經濟資本,至於再度轉換為可操作的象徵資本,用以確保其長期合法化地位,亦需靠權力場域與制度擁有者的統治階級,進行協商與互動。至於資本轉換的幅度與侷限,牽涉到複雜的權力場域互動及資本邏輯,如 Bourdieu 所指,資本無時無刻都在決定這些爭奪的力量,因此是多元決定的(overdetermined)(Bourdieu, 1996: 215;2009: 169)。
基於以上,我們得到一項暫時性的結論:文學及藝術都在特定的場域裡運作,而這些特定的場域又同時受到外圍權力場域及社會空間的共構,兩者相互進入對方的結構,形成動態的爭奪。在場域內部,照 Bourdieu(1996 :215-216)的話語,一律同時以兩種層級化的原理(principles of hierarchization)作為爭鬥:分別是他律的原理(heteronomous principle)及自律的原理(autonomous principle)。但真正「決勝負」的場域.則必須同時連結至文藝場域外部的權力運作場域,如此一來,文藝場域行動者才得以從被統治的地位,由於統治階級對於象徵資本(文學、藝術性資本)之政治需要的深刻體驗,而透過不同資本之間的轉換,發揮能動作用。
◎資本作為社會區分
Bourdieu(高宣揚,2002:248-257)將佔據社會空間不同場域的資本分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及象徵性資本等四種。首先,經濟資本由生產因素(土地、工廠、勞動、貨幣等)、經濟財產、各種收入及各種經濟利益而組成。而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則是進行社會區分的兩大基礎,它用來暗示 Bourdieu 立論裡現代社會地位的確定,不能僅靠經濟資本,而要同時結合文化資本(高宣揚,2002:248-257)。Bourdieu 將文化資本分成以下三種形式:一、「被歸併化的形式」,指的是人類長期內在化形成的稟性系統,Bourdieud 常提及的「慣習」(habitus)即是重要的組件。二、「客觀化的形式」,即是客觀擁有的文化財產。三、「制度化的形式」,則是指合法正當化制度所確認的各種學位及名校榮譽等(高宣揚,2002:250)。
社會資本是指行動者能動員社會網路的幅度以及他所連結到的社會網路每個成員所持有的資本總額。至於象徵資本,則是累積威望的資本,不過 Bourdieu 提醒,象徵資本具有「同時被否認與承認的雙重性質」,它透過「不被承認」而「被承認」,因為各種資本都是以曲折且細緻的方式透過象徵結構的過程,被正當化及進行權力分配而轉換為象徵資本,而統治階級與菁英的工作,就是將這些權力場域角逐而來的資本,透過社會各場域的周轉換算之後,再進行象徵資本分配(高宣揚,2002:252)。
Bourdieu 認為文學及藝術場域爭鬥的正當化議程,特徵就是它經常採用反面或否定的形式,如以「不承認」代替「確認」;以「否定」取代「肯定」;以「迴避」代替「參與」,顯示該場域的掩飾性。(高宣揚,2002:140;Bourdieu, 1996)。然而,我們仍然要追問,是什麼樣的實作「默許」了這種「不承認」,卻能穿梭文藝場域及權力場域,合法進行社會實作。
至於,我們應該怎麼理解行動者在不同層次場域運作的關係,以及識別這些關係如何藉由資本的中介。Bourdieu 提出了三個層次必要的分析步驟,將整合納入本文的研究策略。
一、分析文學場域在整體權力場域裡所佔據的位置(position)以及它的時間演變。
二、分析文學場域的內部結構,文學場域有一套遵守自身運作與轉變的律法,因而佔據該場域的的行動者或機構為了獲得合法權威,因而相互競爭,形成不同的舖排,因此要看這些行動者或機構彼此之間如何呈現客觀的關係結構,才能夠得知他們在場域所佔據的空間。
三、分析這些佔據著的慣習,是源自於什麼樣的稟性系統,因為這系統是社會軌跡及行動者在文學場域裡的位置的產出品,因此透過分析促使這些慣習運作的稟性系統,如何有利於社會實作。
(Bourdieu, 1992: 214;2009: 168)
◎交響樂團式的慣習
「慣習」(habitus)是指「約制性的臨場發揮經長久建置而形成的孕生型原則,其所產生的實作,會將產生此類孕生型原則的客觀條件內含的規律,予以再製出來,同時又能依情勢裡的客觀潛有何需求,而作調整」(Bourdieu, 2009: 162???)。它是一系列「稟性」(dispositions)的結構組,它促使行動者展開行為與回應行動,它透過稟性形成實踐(practices)、感知(perceptions)及態度(attitudes),以利社會實作;但同時,它又是常態的,並非意識性地受規則管束(Thompson, 1991: 12)。
Bourdieu 曾有一比喻,將「慣習」形容成一種「交響樂團式」(orchestration)的象徵模式。首先,個人在社會中,如同交響樂團的不同器樂分部,乃被區分為不同群體;而作為交響樂團的全體演奏,個人分屬於不同器樂組,如同社會的階級排序,同時藉由個人的共通性與差異性實作、但不影響整體「默許/不承認」的和諧樂音表演,卻又同時實作了個人被區分為不同社會配置(階級)的事實。(高宣揚,2002:216-219)
Bourdieu 用意在於形容不同於「習慣」(habits)的慣習,它兼具建構性、創造性,以及再生性和被建構性、穩定性、被動性兩方面的雙重稟性結構(高宣揚,2002:195),它不斷成為「結構中的結構」(structuring structures)」,同時也是「被結構的結構」(structured structures)(1984: 170);而構成「慣習」的「稟性系統」則是可調教的(inculcated)、結構的(structured)、持久的(durable)、生成的(generative)及可轉換的(transposable)(Thompson, 1991: 12),它讓慣習既統合卻又帶著抗爭意涵穿梭在社會結構裡的不同權力層次,它在結構與行動之間,以「不可言喻」(ineffable)的含蓄,組織了社會「默契」,卻透過社會再生產,進行再結構的結構。
第一部
Part One
文化實作及其公共性的浮現
Cultural Practice and the Emergence of Its Publicness
第二章 國家交響樂團的研究定位:文化與社會學的觀點
Chapter Two: The 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e and Sociology
本章透過Giddens對結構(structure)與能動性(agency)的討論,來說明國家交響樂團如何進行音樂實作,包括它如何協商它自身的古典音樂身分;如何協商社會意義;如何穿梭於不同場域,而形成「公共」;如何身處結構,而能維繫能動,並藉 Bourdieu 的「場域」(field)理埨,探...
目錄
申學庸推薦序
郭力昕推薦序
致謝
前言
第一部 文化實作及其公共性的浮現
第一章 導論
研究方法
研究架構:理論與策略
第二章 國家交響樂團的研究定位:文化與社會學的觀點
第一節 交響樂團作為「文化」
第二節 場域、結構與能動性
第三章 歷史、行動與轉型
第一節 台灣政治與社會轉型
第二節 國家交響樂團的誕生與場域對話
第三節 「行政法人化」交響樂團
第四節 國家交響樂團的「場域」體驗
第五節 國家交響樂團作為政治宣傳(propaganda)
第四章 國家交響樂團如何想像「國家」
第一節 文化製作
第二節 文宣作為論述(discourse)
第三節 國家交響樂團在「國際」舞台
第五章 結論
第二部 「民主化」古典音樂?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網路與民主參與
第一節 民主參與理論
第二節 媒體作為公共領域
第三節 網路作為社群
第三章 古典音樂的社會過程
第一節 藝術資質與資本
第二節 常規、門檻與過程
第三節 重探實作
第四章 閱讀與批評:線上交響樂團YouTube Symphony Orchestra
第一節 評估:媒體格式
第二節 評估:近用性
第三節 三評估:參與性
第四節 評估:互動性
第五章 結論
參考書目
申學庸推薦序
郭力昕推薦序
致謝
前言
第一部 文化實作及其公共性的浮現
第一章 導論
研究方法
研究架構:理論與策略
第二章 國家交響樂團的研究定位:文化與社會學的觀點
第一節 交響樂團作為「文化」
第二節 場域、結構與能動性
第三章 歷史、行動與轉型
第一節 台灣政治與社會轉型
第二節 國家交響樂團的誕生與場域對話
第三節 「行政法人化」交響樂團
第四節 國家交響樂團的「場域」體驗
第五節 國家交響樂團作為政治宣傳(propaganda)
第四章 國家交響樂團如何想像「國家」
第一節 文化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