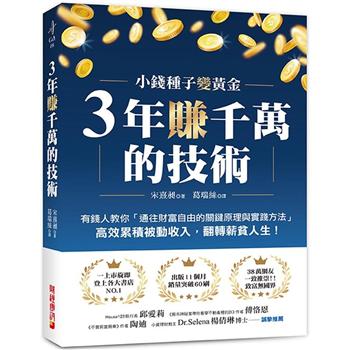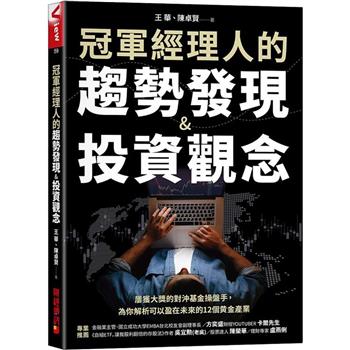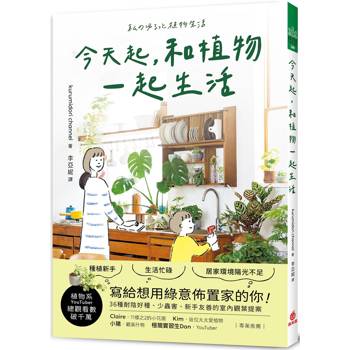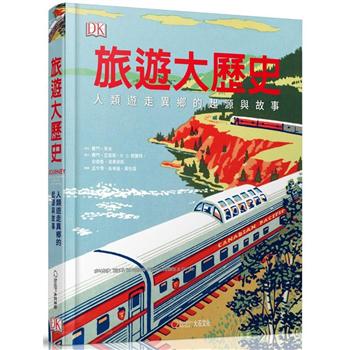竊盜事件
我認為在安置機構內的竊盜事件要嚴肅且認真地看待,它牽涉到的是心理層面的安全感問題。記得我到安置機構擔任社工的第一年,就有許多觸法少年向我反應物品遺失了,幾個月之後,那些物品才又神奇地出現,甚至有些因為上課或打工比較晚歸的孩子向我抱怨,因為晚歸,所以安置機構幫忙留的晚餐,較好吃的菜餚,例如:雞腿、雞排,總會不翼而飛。雖然這都不是什麼大事,不過對於那群孩子來說,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安置機構的生活真是草木皆兵,凡事都得防東防西,找不到絲毫的安全感。
詢問他們是否向生活輔導員或其他工作人員反應此事,多數的孩子無奈地表示:反應無效。沒有人會認真處理或正視這樣的事情,因為這種事情稀鬆平常。
我和幾位不同屬性安置機構的社工閒聊過,發現如果是育幼院屬性的機構,或是沒有透過法院安置觸法少年的機構,發生竊盜事件的機率微乎其微,不過如果是以司法處遇安置觸法少年為主的安置機構,這樣的狀況屢見不鮮,究竟是出了什麼問題?當我提出這個問題和安置機構內一名資深社工討論,他卻很不以為意地回應:「林老師,你才剛剛從事社工工作,所以,你還不懂,等你再做個兩、三年,你就知道了,這種事很平常,況且我們的少年竊盜案那麼多,抓不勝抓啦!」他一副「我太稚嫩、連一點社會經驗都沒有」的輕蔑口氣,至今仍叫我印象深刻。
我真的很難過,這種與觸法少年的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如果連安置機構的工作人員也覺得稀鬆平常且理所當然,怎麼不叫人為這群孩子感到心酸呢?之後,我和幾位不同屬性安置機構的社工更進一步地討論各安置機構是如何處理這樣的狀況時,某位社工提到,在他任職的安置機構中,觸法少年的物品都是統一化的,例如:沐浴乳都是一模一樣的牌子,不會給觸法少年零用錢或硬性規定每天將錢繳回安置機構,避免金錢來源不明的問題,更嚴禁抽菸,一聞到菸味就向法院聲請開立勸導書,而發生竊案就報警處理。另一名生活輔導員則表示在他們的安置機構,除了上述方法之外,零用錢的部分只能使用安置機構的代幣,只能在安置機構內補充生活用品,所有學校要用的東西或要吃的零食、飲料,只能從安置機構帶去,一旦發生竊盜,整個安置機構就要地毯式搜索一遍,猶如大地震的團體壓力,必能減少問題發生。
我很震撼也很掙扎,卻沒有理由去反駁這些給我意見的先進,相較於冷眼旁觀的處理方法,這些方法確實很有建設性,況且使用這種方法處理事情的安置機構,他們的評鑑年年優等,自然有專家學者背書。我思考很久,卻怎麼都不想改變目前安置機構內的原有體制。
面對這群孩子,我一直在想,現在這些孩子擁有什麼?未來他們還能擁有什麼?不該去剝奪他們什麼?想以制度去制約他們什麼?我不願過於理想化,只是不想抹煞我和孩子之間那種自然流露的信任關係。竊盜的問題,在行為改變技術理論上,我深信「正增強」的使用應該多於「負增強」。竊盜行為的部分,我寧願多花點時間,增加讓孩子面對問題的機會,我相信正向行為更能內化,而不只是以制約的行為,達到一時的警惕效果。
「為什麼要偷竊呢?」
「每天都上演的問題,該怎麼處理?」
深究其背景,安置機構內的觸法少年,其原生家庭功能大都不完善,在原生家庭中,多數的孩子甚至有一餐沒一餐的,所謂的「家」徒具形式,連基本的生理需求都無法得到滿足。比較不聰明的孩子,他們可能以竊盜的方式去滿足自我的需求;比較聰明的孩子,他們知道如何用非法的手段來快速賺錢,因此,從事圍事、暴力討債、販毒、酒店公關少爺……等等工作。無論方法為何,其核心價值,都只不過是要滿足他們的生理需求以及建立安全感而已。
「如果沒有這些物質,還能擁有什麼?」
「在安置機構中能擁有什麼?如果已經擁有了,還想再擁有什麼?」
讀大學時,一位和我一同念假日進修學士班的同學,因為家裡是寄養家庭,他就和我分享他帶過的寄養孩子。至今回想起他說過的片段,仍讓我難過心酸。他說那位寄養孩子剛到他家時,吃飯完全不知節制,就是一直拚命地吃,好幾次都吃到嘔吐,原本他的家人以為這孩子只是食量大或自制能力較差,後來,才知道因為那孩子覺得如果這一餐沒有吃飽,下一餐可能不知道在哪裡?當時,我難過得簡直難以用紙筆形容,無法想像在已開發的台灣社會,居然有如此不堪的景況,也無法想像社會底層的悲哀究竟有多深。究竟是怎樣的生命故事,會讓孩子如此不安?
我不斷思考著安置機構內的竊盜事件,也問過青霖覺得應該怎麼處理比較好?只見他義憤填膺地回答:「我早就知道是誰了!如果可以自己處理,我肯定會處理得比工作人員還好!」那種以暴制暴的說法,真叫我不寒而慄。
「青霖,你夠聰明,一定知道怎樣處理才會最有效。我想你的辦法一定也會比工作人員管用許多,不過我們可不可以試試比較不一樣的方法呢?」我禮貌性地邀請青霖一起來腦力激盪。
「既然你可以嘗試過著與以前截然不同的安置生活,那麼,碰到問題時,要不要也試試和以往經驗不同的處理方法呢?說不定,那個過程會很有趣喲!」我持續且小心地鼓勵著青霖,深怕一不小心,他會將我歸類為「反正,你是社工,就只會使用社工的方法來處理而已」。
討論中,我們帶有許多主觀性的想法,這牽涉到我們的成長背景、處理事情的經驗、社會的歷練。好幾次,我和青霖的生命交會了,然後再次分開……。
「如果可以,想像不會偷竊的你和那些慣於偷竊的孩子的差別。」
青霖是幸運的,有俊帥的外表、天資聰穎、有著理性的邏輯分析能力,更重要的是有許多倚重他能力的黑幫兄弟,以及他的野心,他仍然希冀著安置生涯結束之後可以東山再起。不過,那些慣於竊盜的孩子什麼都沒有。最後,我們的結論是,寫字條向偷兒溫情喊話,儘管最後效果不大,不過,我一直深信青霖和那些慣於偷竊的孩子的心,一定都曾經被稍稍撼動過。
我一直試著讓孩子們知道安置機構就是他們的家,家裡面當然都可以自由進出。
「家裡面會有小偷嗎?是不是哥哥或弟弟先借去用了?」在孩子們看來,我可能很幼稚。關於安置機構內的竊盜案件,其實我找不到更有效的解決辦法。數年過去了,孩子們仍然陸陸續續向我抱怨什麼東西不見了,幾個月之後,那些東西才又神奇地出現。晚餐預留的菜餚依然總是消失不見,而鬧鬼的傳聞也從不間斷。即便如此,我仍然沒有提議改變安置機構的制度,仍然沒有採用「不給零用錢、報警、統一物品」的方式來消極防堵,不過安置機構將會更謹慎地去了解發現孩子的需求,並盡可能地滿足他們。
曾經在某任職安置機構的會議中,當工作人員強烈提議裝設錄影機來預防打架和竊盜問題時,我堅決反對這項提案。很不幸地,沒多久,就發生安置機構觸法少年破壞辦公室門窗,撬開保險櫃竊取金錢的案件。那一年,辦公室和觸法少年的活動空間都被裝設了攝影機。
只是,竊盜問題真能因此解決嗎?許許多多安全感沒有被滿足的孩子,仍在暗處蠢蠢欲動……。
竊盜行為的背後
馬斯洛說過需求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最基本的溫飽階段,是對於生理以及安全感的渴望。安置機構內的觸法少年,無論是因為任何觸法案件或理由而被裁定安置輔導,我想這都是他們該享有的權利。我嘗試放下社會文化體制中批判觸法行為的負面價值,試著去理解竊盜成因的背後問題,協助引導青霖看到竊盜行為背後的意義,雖然當下他未必能認同,卻也願意一起嘗試對偷竊的孩子溫情喊話,努力捨棄有別於以往的既有經驗,並發展出新的思維來面對竊盜事件。
我也發現竊盜行為的發生,有時未必是自我需求沒有辦法被滿足或缺乏安全感而產生的行為,竊盜成因應該更深層地被看見、被理解。每個竊盜成癖的孩子,往往讓我更加不捨和難過。
竊盜行為淺層的意義,除了顯示當下孩子的需求沒有辦法被滿足,或是慾望無法克制之外,也可能是想透過竊盜行為去引起他人的關注,希望從被處罰或責罵的過程中,得到被關愛的眼神和被在乎的感受。我也曾發現,有些孩子的特質並不符合社會期待,在群體中總是被邊緣化,久而久之,便在心理層面上醞釀出反社會人格的特質,透過竊盜或其它觸法行為,去發洩情緒。在傷害別人的過程中找到報復的快感,進而得到自我滿足,而不再覺得自己很委屈。
值得一提的是,少年觸法行為的問題背後,也有可能是先天帶來的限制,例如:有先天性注意力不足或伴隨過動症的少年,因衝動行為以及自我控制能力不足而連續觸法,這在我工作的歷程中屢見不鮮。這樣的孩子大都是在成長歷程中,曾被不斷包容卻毫無改善,當社會對他們逐漸失去耐心之後,只能被指責、被放棄,而在安置機構的處遇過程中依舊忽視了他們先天上的限制。但在實務經驗中,往往有許多困境,必須有效統合多方資源,才能確實給予觸法少年協助。
我也遇過亞斯伯格症的少年,因為亞斯伯格症在人際互動過程會不斷遭受挫折、一直被排擠於外,導致憤世嫉俗,對社會充滿負面情緒。可以想見的是,每個孩子都有一段難以被理解的生命故事,就如同我們每個人都有一段自我成長的生命歷程那樣獨一無二,造就每個獨特的生命。生命成長的成因太多,該如何透過社工的專業才能,更細膩的被發現,進而透過這樣的發現更細緻地去處理,則是我在工作中的瓶頸。
我的工作不單是接觸孩子而已,如何與社會系統中可能與孩子發生關係的每個人一起努力,並讓社會理解並看見孩子的存在,的確不是容易的事。如果社會上的每個人都不吝於伸出手,借力使力地拉孩子一把,我想,有這般困境的孩子,必將不再孤單。
權力與位階
「呂瑋隆逃離安置機構了,或許是因為沒有錢買香菸,才偷了孫永新的錢,其他觸法少年告訴生活輔導員了,聽說可能會報警處理,呂瑋隆可能是怕有新的案件移進法院,會被送感化教育才逃跑的吧!」青霖對著剛進辦公室的我這麼說道。
青霖說安置機構中的觸法少年,目前分為兩派勢力,一派以呂瑋隆為首,另一派以徐國華為首。在少年觀護所時,就有認識的朋友透過關係,要徐國華幫忙照顧才剛剛被裁定安置輔導的青霖,所以,青霖和徐國華自然走得比較近。言談之間,聽得出來青霖對呂瑋隆頗有微辭。現在,呂瑋隆逃離安置機構了,派系之間的紛爭彷彿不復存在,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呂瑋隆和徐國華兩派壁壘分明,不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總之,一山難容二虎吧!兩個年紀相仿且同樣想主導安置機構同儕運作的他們,很容易為了一點點小紛爭就鬧成團體之間的衝突事件。舉例來說,新進到安置機構的人,雙方就會先以走私到安置機構的香菸各自角力拉攏,之後,就開始分屬於不同團體,在安置機構內相互制衡,井水不犯河水。只是,呂瑋隆會常常為了想出風頭,證明自己在團體中較『大尾』,便無故製造事端,造成雙方人馬的衝突。」青霖一氣呵成地說著。
青霖曾問我:「為什麼不乾脆將相同勢力或生活圈的人盡量分在同一組,像同一個房間、同一個打掃區域、相近的座位……等等,彼此不就井水不犯河水、相安無事了嗎?」
可想而知,這些社會化下的產物,形成團體生活中各自有小團體。無論從哪個觀點看,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特質,自然也會被相似特質的人所吸引,進而成為朋友,甚至於是知心朋友。然而安置機構中,不少孩子的社會經驗豐富且世故,即使在相同勢力的團體中,也各自有其階級。位階高的觸法少年往往會要求位階低的觸法少年處理其生活內務以及雜事(例如:幫忙洗衣、洗碗、整理內務……等等),位階低的觸法少年也擔心在團體生活中找不到依附感,多半逆來順受,忍氣吞聲地等待在團體中的位階能逐步提高,等媳婦熬成婆之後才能壯大自己。因此,若是將同屬勢力的觸法少年畫分在同一個生活圈,階級霸凌變得理所當然且合理化。
資源背後的小團體
我曾好奇地問青霖:「這樣的生活不是很辛苦嗎?況且,安置機構中,不過就幾十個人,大家還會選邊站嗎?」
「資源多的一方,自然會有比較多的人來靠攏。」青霖笑笑地回答。他說的資源是指香菸以及朋友來訪時偷塞的現金。
青霖告訴過我,有一次,在少年觀護所認識的乾哥哥來安置機構探視他,避過安置機構工作人員的耳目以及簡易檢查,走到安置機構遠處的牧場放置東西,之後,青霖找尋著一包零食,裡面放著那位乾哥哥偷塞給他的五千元現金。後來,雖然被工作人員發現,禁止那位乾哥哥再來探視,不過,那位乾哥哥每個月仍會直接跑去他的學校和打工的地方跟他見面。
看著青霖洋洋得意的笑容,我想,他的資源應該是蠻多的吧!足以讓他在安置機構中吃香喝辣、呼風喚雨。到安置機構之前,觸法少年大都有菸癮,安置機構考量這些少年被安置輔導的主要原因並非是為了戒菸,因此,對於抽菸這件事,大都是循循善誘,卻也間接合理化在安置機構中以香菸當做資源並建立團體勢力的正當性。
安置機構內,每天幾乎都有不同勢力衝突事件上演,例如:他們上課、上班搭交通車時遲到,引起其他也要上課、上班的人不滿,不同的團體就會開始相互嗆聲;又例如:某人的生活習慣較差、較髒亂,影響到其他人,不同的團體也會捍衛彼此各自的人馬,衝突往往一發不可收拾,必須由工作人員出面協調處理,才能回復平靜。說實話,衝突事件一直是暗潮洶湧,等待爆發罷了。
團體勢力中,與青霖處於敵對關係的呂瑋隆,因在安置機構內已經多次違規,與生活輔導員也發生過多次衝突,在安置機構外的工作狀況不佳,也與老闆多次發生口角,被安置機構暫時留園觀察。也因為被留園觀察,所以,沒有外出的零用金,也沒有親人或朋友能來探視,無法給予物質或資源支持。不久之後,呂瑋隆所屬勢力的觸法少年,在沒有資源的誘惑下,紛紛轉而投奔徐國華、溫青霖的陣營,新仇加上舊恨,儘管徐國華、溫青霖並不咄咄逼人,但向來放肆不羈的呂瑋隆已喪失表現的舞台,在安置機構內顯得孤立無援,最後,只得選擇逃離。
忽然之間,我能理解青霖口中喜歡無故製造事端的呂瑋隆了,在資源有限的狀況下,又要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確實非常辛苦。
鐵定被裁定感化教育的呂瑋隆
一進辦公室,我就聽到工作人員說道:「半夜孫永新突然跑下來說自己每天存下來的五百元不見了,『有人』看到被留園觀察的呂瑋隆,白天利用孫永新上課不在房間時,偷偷地溜進孫永新的房間內翻找,後來,在生活輔導員的確認下,果然在呂瑋隆的內務櫃找到五百元。生活輔導員因為考量他被留園觀察一陣子,並沒有外出零用金,所以質疑他的五百元從何而來。這時只見他忿忿地拋下一句:『你們都說是我偷的,那就是我偷的啊!』免不了他又因態度不佳而與工作人員起了口角衝突。」凌晨時分,呂瑋隆從安置機構逃跑。然而,此時的安置機構卻充滿著歡愉的氣氛。
從安置機構的觀點來看,呂瑋隆確實是個頭痛人物。根據工作人員的觀察,他像是個地痞流氓,往往藉由無故製造事端來證明自己的價值,所以,在安置機構的規範遵守以及外出工作時與老闆的配合度,都很讓人失望,加上呂瑋隆已經有多次逃跑和違規記錄,因此,這次除了在安置機構竊取其他觸法少年的金錢之外,加上再次逃跑,一定是會被法院裁定感化教育。所以,無論是安置機構的工作人員或是其他觸法少年,都鬆了一口氣。
即便呂瑋隆逃離安置機構已經一個多月,我仍忘不了初見他時那種桀驁不馴的神情,其實他根本沒有意願被安置,只是因為已經犯下多起竊盜案件和傷害案件,法官告訴他如果不接受安置輔導就會裁定感化教育。
呂瑋隆的成長背景,也讓我很心疼。他是非婚生子女,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親生媽媽是誰,小時候的記憶就是爸爸會一直打他,國中時開始蹺家,三天兩頭就寄居於朋友家裡,有一次,帶女朋友回家,卻遇到爸爸在家,這次,爸爸卻反常地對他關懷備至,並且,拿出珍藏的酒吆喝著一起分享,在不勝酒力的狀況下,他醉暈了過去,女朋友則被爸爸性侵了,後來因為覺得愧對女朋友,沒有顏面在原本的生活圈生活,便獨自一人到另一個城市生活,最後,因竊盜案件以及傷害案件而被裁定安置。
安置不久之後,法院以祕密證人身分傳喚呂瑋隆到法院協助指認他爸爸性侵女朋友的案件,他向法官表明拒絕作證,全身顫抖著說:「那個人再壞,畢竟仍是我的爸爸……。」
我忘不了呂瑋隆那防衛性的眼神,我想,自幼被爸爸家暴,最後,連女朋友都無法保護,這一切,教他如何能再信任別人?他的心早已碎裂,該如何修補?他與世界的信任橋樑早已斷了,又該如何銜接?他和安置機構工作人員的相處總是劍拔弩張,我也總是小心翼翼地和他相處。對於安置機構中擁有權力的觸法少年,呂瑋隆總會無端製造事端,且不願屈服,導致安置機構內一提到呂瑋隆,第一線的生活輔導員都束手無策,難有交集。
三個月之後,法院傳來消息,觀護人說呂瑋隆在南部被警察抓到,卻因再次犯下竊案被當做現行犯逮捕,召開臨時庭時建議該地院法官當庭收容在少年觀護所,正式開庭之後,由少年法庭裁定感化教育,移監到少年輔育院執行。
青霖要離開安置機構的前幾天,無意間我們再次聊到呂瑋隆,他徐徐地說著:「那五百元,其實是徐國華交給孫永新的,趁著沒有人注意時,藏在呂瑋隆的櫃子內,栽贓陷害呂瑋隆。」他又接著說:「那陣子,我們知道工作人員和大家都對呂瑋隆的脫序行為感到很頭疼,單純地站在『維護』安置機構和諧的立場才幫忙『處理』呂瑋隆的。」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我在少年中途之家的日子:一位少年保護社工與觸法少年的生命故事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09 |
二手中文書 |
$ 272 |
社會人文 |
$ 281 |
中文書 |
$ 282 |
社會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我在少年中途之家的日子:一位少年保護社工與觸法少年的生命故事
我想,我可能再也沒有勇氣做社工了……
家庭破碎、無法溫飽,生存與道德的界線該如何掌握?
當家人不再關心自己,我們是否正在失去對人的信任與美好?
一個來自少年保護社工的實務工作經驗,用時間和信任碰撞出的思考生命議題。
作者本身是一名輔導處法少年的社工,
多年的輔導工作,
曾讓他為了少年們的遭遇感到難過與落淚,
也曾經為了自己的無能為力而內心焦灼。
法律面前,是非對錯僅存二分法:無罪、有罪。
然而,我們深知人的內心和生活處境,遠比二分法更為複雜。
這個世界很小,如同這群少年曾感受到的愛,很小、很少……
作者一直認為,人的互動是十分微妙的,
永遠不會存在一種最佳模式可以被無限複製;
而是隨著時間的流動,在互動中不斷地調整、學習。
透過這本書,希望能讓讀者們看見不一樣的孩子,
放下標準答案、用更細膩的心去看待觸法少年的議題與內心世界。
作者簡介:
林劭宇
現為社團法人臺灣自立少年關懷協會理事長。對於弱勢少年有一顆柔軟的心,除了能敏銳地觀察生命的角落,又有著細膩的社會關懷。具有正向人格特質的他,高中畢業後,毅然選擇社會福利學系就讀,並在求學階段擔任課輔教師累積助人經驗;畢業後,為了成為弱勢少年更有力的支柱,同時在少年安置機構擔任少年保護社工,一邊進修研究所,以取得教育碩士學位。目前正積極於法律研究所進修,努力邁向實務和理論兼併的社會工作者。曾發行《你不會是一個人》音樂專輯。
TOP
章節試閱
竊盜事件
我認為在安置機構內的竊盜事件要嚴肅且認真地看待,它牽涉到的是心理層面的安全感問題。記得我到安置機構擔任社工的第一年,就有許多觸法少年向我反應物品遺失了,幾個月之後,那些物品才又神奇地出現,甚至有些因為上課或打工比較晚歸的孩子向我抱怨,因為晚歸,所以安置機構幫忙留的晚餐,較好吃的菜餚,例如:雞腿、雞排,總會不翼而飛。雖然這都不是什麼大事,不過對於那群孩子來說,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安置機構的生活真是草木皆兵,凡事都得防東防西,找不到絲毫的安全感。
詢問他們是否向生活輔導員或其他工作人員...
我認為在安置機構內的竊盜事件要嚴肅且認真地看待,它牽涉到的是心理層面的安全感問題。記得我到安置機構擔任社工的第一年,就有許多觸法少年向我反應物品遺失了,幾個月之後,那些物品才又神奇地出現,甚至有些因為上課或打工比較晚歸的孩子向我抱怨,因為晚歸,所以安置機構幫忙留的晚餐,較好吃的菜餚,例如:雞腿、雞排,總會不翼而飛。雖然這都不是什麼大事,不過對於那群孩子來說,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安置機構的生活真是草木皆兵,凡事都得防東防西,找不到絲毫的安全感。
詢問他們是否向生活輔導員或其他工作人員...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我想,我可能沒有勇氣再做社工了……
我的工作是少年保護社工,是在少年中途之家從事觸法少年的安置輔導工作。這麼多年來,對於少年輔導工作,我一直保有熱忱,工作的熱情從未消褪,不過,不可否認地,多年輔導工作,讓我曾經為了觸法少年的遭遇感到難過,也曾經為了自己的處遇不當而感到自責,更曾經為了觸法少年的麻木不仁而感到憤怒,甚而曾經為了自己的無能為力而感到內心焦灼。
這麼多年來,與觸法少年的生命碰撞過程,我曾經對觸法少年嘆氣,對這份工作感到沮喪,質疑自己工作的目的,其間經歷不少衝突與矛盾。體系規範與自我價值...
我的工作是少年保護社工,是在少年中途之家從事觸法少年的安置輔導工作。這麼多年來,對於少年輔導工作,我一直保有熱忱,工作的熱情從未消褪,不過,不可否認地,多年輔導工作,讓我曾經為了觸法少年的遭遇感到難過,也曾經為了自己的處遇不當而感到自責,更曾經為了觸法少年的麻木不仁而感到憤怒,甚而曾經為了自己的無能為力而感到內心焦灼。
這麼多年來,與觸法少年的生命碰撞過程,我曾經對觸法少年嘆氣,對這份工作感到沮喪,質疑自己工作的目的,其間經歷不少衝突與矛盾。體系規範與自我價值...
»看全部
TOP
目錄
作者序──我想,我可能再也沒有勇氣做社工了……
楔子 從一位觸法少年談起
第一章 被迫安置──不一樣的生命相遇:少年保護社工與觸法少年的初識
初見觸法少年溫青霖
我是漂撇的少年郎
溫青霖的童年回憶
我看風光江湖路
江湖路上多險惡
是一個怎樣變動的生命?
不一樣的少年中途之家
在少年觀護所初相遇
聽聽溫青霖怎麼說
安置機構是觸法少年的避風港?
第二章 接受安置──少年保護社工和觸法少年的生命交會與碰撞
請聽我說
在不斷的省思...
楔子 從一位觸法少年談起
第一章 被迫安置──不一樣的生命相遇:少年保護社工與觸法少年的初識
初見觸法少年溫青霖
我是漂撇的少年郎
溫青霖的童年回憶
我看風光江湖路
江湖路上多險惡
是一個怎樣變動的生命?
不一樣的少年中途之家
在少年觀護所初相遇
聽聽溫青霖怎麼說
安置機構是觸法少年的避風港?
第二章 接受安置──少年保護社工和觸法少年的生命交會與碰撞
請聽我說
在不斷的省思...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林劭宇
- 出版社: 九韵文化 出版日期:2015-09-28 ISBN/ISSN:9789865767716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社會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