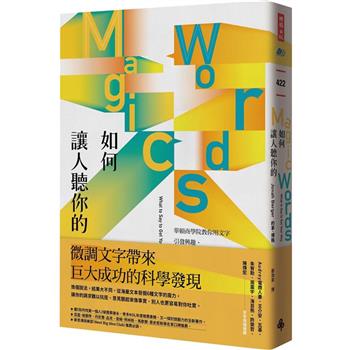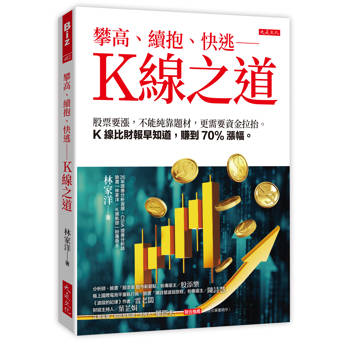第三十一章
林若拙吃驚的抬眼,說這種話,袁清波瘋了嗎?
又見早點攤的人都興致勃勃的圍觀,只得又垂了眼,輕聲道:「怕給你惹麻煩。」
中年女人第一個忍不住,快嘴快舌道:「袁大家,你認識秦姑娘?可是與她定親的未婚夫?」
未婚夫?袁清波一怔,隨即模稜兩可的接上:「妳怎麼就這樣出來了?」
林若拙暗讚一聲,不愧是演戲的老手,這話接得忒有水準,遂答道:「繼母欲將我嫁給她遠房的侄兒,我不肯依。想著上京來碰碰運氣,看能不能找到楊大哥。正巧兩個妹妹也要進京尋親,我們便搭夥一起離開了江寧。」
袁清波點點頭,道:「女孩子進戲班名聲不大好聽,妳有顧慮也是對的。只是我雖不才,替妳們張羅個落腳的地方還是行的,楊大哥的下落也可幫著打聽。」
兩人話一銜接,眾人立時明白了大概,也解釋出了為什麼三個年輕姑娘沒去戲班找人的原因。中年女人很有些遺憾:「袁大家,你不是她的未婚夫啊。」
袁清波笑笑:「秦姑娘自有婚約,我是早幾年去江南與她結識的。」與眾人打了幾聲招呼,領著三人離去。
走至無人處,林若拙開口問:「清波,你帶我們去哪兒?」
袁清波道:「戲班子不能去,妳的樣子幾個名角都能認出。我在外城有座私宅,地方不大勝在清靜,可安心住下。」又瞥了一眼畫船的腳,「還要請個大夫。」
林若拙這才無話。隨他走出幾個街道,來至一處僻靜小巷,綠竹森森探出牆頭,打開小小的清漆木門,是所一進小院。青石板鋪就的院中放著一張石桌,外有四個石凳。牆邊種了一叢竹子。木樁子間拉了繩子做晾曬用。正南三間屋子,內有簡單傢俱。東邊處是雪洞一樣的空屋。西邊則是廚房、水房、淨房。正房後有一片小小空地,稀稀落落爬了幾根扁豆藤。
袁清波道:「我平素少來這裡,故東西置辦得不大齊全,約莫要收拾一下,缺什麼我去買。這裡取水不大方便,井臺在巷子外頭。有專門送水的,只需與他們幾個錢。洗衣什麼的也可請人幫忙。」
錢她是不缺。林若拙苦笑,單挑水也罷了,請人洗衣便要上門,少不得應付打探閒扯,罷了,還是自己洗吧。左右現在穿的都是棉布,禁揉搓。
袁清波又道:「妳們先收拾著,我去請大夫。」
見他出了門,銀鉤猶豫道:「袁大家他會不會……」
畫船坐在石凳上休息,聞言也擔憂:「娘娘,您與他何時有往來?」
「叫姐姐!」林若拙正色糾正,道:「若事事都懷疑,做人未免太累。我自詡還有幾分眼光,清波目色清明,不是那等奸佞小人。再說,他連問都沒問咱們出了什麼事,要麼是早已知曉,要麼就是全然不在意。」末了又歎:「便是他真有二心,我們幾個傷的傷,殘的殘,能再去哪裡?別的不說,只要洗乾淨了臉,銀鉤妳出去走一圈試試,保管人人都盯著瞧。更何況還有那沿街巡查的,咱們在外城是生面孔,可禁得住詢問麼?」
大戶人家選丫鬟本就有平頭正臉的標準,林若拙又挑剔,非要素顏看著清爽才行。這一來,四個丫頭底子就都不錯,好吃好喝養成幾年,在靖王府那美人雲集的地方都能算中等姿容,更何況是這裡。
畫船歎了口氣:「小福姐姐說外頭營生艱難,果然如此。」
林若拙沒她們那麼多感慨,拎了包袱進屋,逕自安排:「三間正屋咱們盡夠住了,東廂就別管它。堂屋收拾出來吃飯起居,側間妳們兩個住一間,我住一間。這樣只需添一張床就夠,怎麼樣?」
畫船腳不便,銀鉤聽了她的話音進屋,道:「還得添張榻,奴婢晚間好給您值夜。」
「啊呸!」林若拙噴她,「奴婢?值夜?妳乾脆用大嗓門喊咱們這兒有問題算了!妳當挑水的是傻子?送米送家什的是呆子?假作真時真亦假!從現在開始,咱們三個就是同鄉!沒什麼主子奴婢的!那什麼口音給我帶上,尊卑放一放,把命保住是正經!」
袁清波帶著跌打損傷大夫進門時,銀鉤正在灶房燒水,裊裊白煙給小院添了幾分人氣。
畫船的腳沒傷著骨頭,但因為奔走整晚,傷勢加重,需休養三個月左右。老大夫言道這種傷敷幾次藥就行,主要在靜養,多吃點補身子的飯食。
大夫走後,送傢俱的上了門。架子床、梳妝檯、箱籠,衣架、水盆,一群人扛著東西,跟搬家的差不多。袁清波按照大戶人家規矩算,東廂布置成兩個丫鬟的住所,正屋一間做起居,一間做臥室,一間做繡房兼書房。
林若拙慶幸自己還沒洗臉,趕忙出來攔住,說她們姐妹三個住正房三間就行了,東廂沒必要收拾出來。
袁清波便道三人住一塊有個照應也好。退傢俱倒不必,那就索性將東廂收拾成一間書房、一間繡房。總而言之,東西買了不能退貨。
林若拙知道作為頂級旦角,袁清波不缺錢,他缺的是別的。笑笑,也就應下了。
送傢俱的一撥人剛走,送米麵糧油柴火菜蔬的又上門,將廚房堆得滿滿。接著,送衣料布料的又來,一撥接一撥。
等人都走完了,林若拙沒好氣:「這麼大張旗鼓,你就不怕?」
袁清波笑:「虛虛實實,妳住進來定有街坊好奇,待他們胡亂打探倒不好。索性一次性見一下,比遮遮掩掩的強,日後就無需如此了,守緊門戶,誰也說不了什麼。」
林若拙輕笑了笑,靜默片刻:「你不問我出了什麼事?」
袁清波不置可否:「妳願意跟我來,我便替妳安置打點。至於出什麼事,我也能猜到幾分。以妳的身分,能讓妳落魄至此的,定是天塌下來的大事。?親王已經好幾日不曾召我去了。」
聽到這裡,林若拙窘了一下。
?親王同學一如既往的將男男事業發揚光大。身為上流社會的已婚婦人,她的消息範圍比少女時代擴大得多。比如段如錦脫籍回鄉,袁清波成為?王新寵就是其中一項。說實話,她有些不能理解:「你師父……怎麼就回鄉了……」他和?親王之間不是真愛麼?
男男相戀都沒有真愛了,莫非唯一的希望只寄在人獸?
袁清波詫異於她的想法:「師父歸鄉是好事,他雖年歲大了些,手中積蓄卻不少。置房買田,足可做個富家翁。娶個好生養的女子延續香火,若是有幸,還能見著孫子出生。多虧王爺恩典呢。」
林若拙直接「囧」住,尼瑪,這到底是直男還是彎男:「段師父他,他不是……那個不喜女子?」她吭哧了好半天才想出適當的形容詞。
袁清波更莫名:「誰說師父不喜女子?只是跟了王爺,王爺不鬆口,總不好私下娶妻。」
「……」林若拙沉默,良久後道:「你呢,你喜歡的是女子還是男子?日後,也是如段師父這樣熬到年歲大?」
袁清波不禁笑:「真是說笑,我們唱戲的,哪個能唱到年歲大。尤其我這樣的旦角,本就是十來年工夫的事。」停頓了一會兒,又淡淡笑:「說起來還得謝謝王爺,若不是他擋著,不知有多少狂風驟雨侵襲。王爺是個長情念舊的人,師父當日就和我說過,伺候好了他,至少能得十年安穩。」
林若拙久久沉默,不知道該說什麼好,心中酸澀鬱鬱堆積。
袁清波卻是振作得快,轉瞬若晴,換了話題:「剛在街上,恍惚聽見有人說內城出了事,如今戒嚴得十分厲害,平素往各府送菜蔬的車都進不去了。」
林若拙歎一口氣:「說真的,我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就知道有士兵衝了進來,胡亂砍殺。虧我住得偏,才早早逃了出來。內城到處是黑甲士兵,也不知哪個大營的?」
袁清波便問:「要打聽一下嗎?」
林若拙想了想:「內城這麼多人,菜蔬肉魚不可能一直禁運,若能與送貨人攀談,可打聽一二,其他的不宜多做。」
袁清波點頭,又囑咐了幾句居家常識,去了。
至晚間又來,面色比早先壞了許多:「應是出了大事,城門守備多了一半多的人。幾處客棧都有人搜查。」略停頓了頓,他道:「?親王派了人給我送信,讓戲班子停演,說無事不要外出。我和來人打聽,來人什麼都不說。」
林若拙靈光一閃,忽的想到什麼,問:「?王的人是從哪兒來的?內城,還是外城??王現在在哪裡?」
袁清波搖頭:「來人沒說。不過我見他衣著整齊,不似妳早晨那般狼狽。」
林若拙理了理思緒:「也就是說,?王府沒事。」
那麼?親王,又是屬於哪個陣營呢?
想了半天也沒個頭緒。
袁清波已然告辭:「我先走了。妳且住著,有什麼消息我就來通知妳。若是我趕不及,就讓身邊的小路兒來。」
林若拙趕緊道:「等等,得防著有人冒了你的名號騙我們,定個暗號吧。」
袁清波:「……什麼暗號。」
林若拙:「我是一條小青蟲,你看怎麼樣?」
◎
清晨,內廷寢宮彌漫著一股濃濃的藥味,胡春來將空了的藥碗放至桌上,接過小內監手中巾帕,擦去楚帝唇角的一滴藥汁。
楚帝還不能說話,只半邊身體能動,喉嚨裡呵呵兩聲,指了指遠處的書案。
「陛下,您是想看……」胡春來話還沒說完,就聽外間傳來一陣嘈雜,面色一凜,起身走至外間:「怎麼回事?」
「總管大人!出出大事了……」小內監結結巴巴的衝過來,「不好了!四皇子帶著禁衛軍進了宮門!」
「什麼!」胡春來只來得及驚喝一聲,外面就呼呼啦啦闖進來一大群人,為首的正是四皇子赫連輝。
「胡總管。」赫連輝好整以暇的登上臺階,意氣風發的看著他:「父皇身體可好?」
胡春來八歲進宮,十三歲在楚帝身邊伺候,什麼風雨大浪沒經歷過,見他這樣子立刻就明白了七分,冷笑:「四殿下,陛下未曾召見,您何故闖入?」
自從封了王,外人對這幾個皇子就以封號相稱,寧王殿下可比四殿下氣派多了,赫連輝對於這番故意的提醒只是笑了笑:「城裡進了盜匪,本王怕驚了父皇,特來進宮瞧瞧。」
胡春來冷笑:「四殿下,且不說直隸一帶向來政清人安,無有匪亂。單是你不詔而入,領兵甲刀刃,可是要造反麼!」
赫連輝嗤笑一聲:「造反?我姓赫連,天下是赫連家的。我能造什麼反?胡總管老糊塗了吧。」
胡春來盯著禁衛軍領頭的人死看片刻,冷笑一聲:「王副統領,周統領何在?」
那位王副統領板著臉道:「昨晚城內進了匪徒,老周一家遭了匪盜,闔家正亂。無有空暇。」
「廢話什麼!」赫連輝不耐煩的打斷:「別和他囉嗦,咱們進去!」
胡春來大喝一聲:「誰敢亂闖!」
「對!誰敢擅闖宮禁!先過我這關!」一個氣勢洶洶的聲音接著他的話,高聲大喝。
眾人一看,卻是二皇子赫連勇帶著御林軍從另一條路而來,甲胄全身,怒氣沖沖的指著赫連輝鼻子罵:「老四,你喪心病狂!竟然指使禁衛軍冒充匪盜,夜闖內城,殺害兄弟,你這樣的禽獸,簡直天理難容!」
「你說什麼?」老四赫連輝先是一怔,不敢置信:「哪有的事?」他明明只是命人軟禁幾個兄弟全家,護衛隨從下人或許殺幾個,怎麼也輪不到趕盡殺絕。不然,豈不成了殺人魔王,誰還敢追隨他?
老二赫連勇皮笑肉不笑:「四弟,憑你說得天花亂墜也抵不過事實,不信你上朱雀街去看看,老三、老七、老八、老九府裡還有幾個活著的。」
赫連輝驚怒,恍然醒悟,大罵:「是你!是你幹的!」
「哼!」赫連勇輕蔑的瞥他一眼,對著胡春來拱了拱手:「胡總管,還煩奏明父皇,以正清明。」
赫連輝也不是傻子,立時反駁:「胡總管,分明是老二的人冒充匪盜,殺害幾位兄弟。」
胡春來冷冷的視他們狗咬狗,一言不發。手一拍,一隊黑衣繡暗金色花紋的帶刀侍衛從大殿兩側簌簌而來,圍住殿門。三方人馬互相對峙。
赫連勇冷喝:「胡春來,你要以下犯上?」
胡春來道:「兩位殿下,金衣衛乃帝王貼身護軍,保的是陛下,何來以下犯上一說。」
赫連輝冷笑:「父皇可下令攔住我們了?分明是你個老匹夫假傳聖諭。」又大聲對那些金衣衛挑撥,「如今父皇病重,全憑這閹人指手畫腳。你們大好兒郎,就這樣聽命一個內侍嗎?」
一個蒼肅莊嚴的女聲傳來:「那也輪不到聽你的!」
話音處,司徒皇后穿著一身玄色衣衫,金絲繡鳳,冷冷的走來:「我聽說宮裡熱鬧得緊,過來看看。呵呵,果然一場好戲。怎麼,你父皇還沒死呢,就等不及了!」
司徒皇后可比胡春來名正言順得多,她一出現,赫連輝再無挑撥可能。赫連勇一見,忙道:「母后,四弟他喪心病狂,將幾個兄弟全家都殺害了!」
「胡說!,明明是你幹的!」赫連輝哪肯被潑這盆髒水,怒斥:「你才是凶手!」
司徒皇后輕輕一笑:「爭執不下麼,沒關係,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我帶來幾個人,大夥兒慢慢聽,慢慢評斷。」
隨著她的話音,貼身女官瑤光領著一隊人走來,灰衣短打,押送著幾個衣著光鮮的女子,包含了所有生育子嗣的妃嬪,赫連輝的生母王貴妃、赫連勇的生母魏嬪、老五的生母穆嬪、老七的生母段淑妃、老八的養母張德妃,老九的生母李賢妃。
赫連輝和赫連勇眼珠子瞪得血紅:「竟敢領司徒氏私兵進宮,皇后,妳好大的膽子!」
司徒皇后輕笑:「不及你們膽大,親兄弟都敢殺。這幾個女人,說白了,和我非親非故,有什麼關係了,比你們罔顧血脈親緣要強。」轉頭笑看胡春來,「胡總管,你怎麼看?」
胡春來思索一番,決定和皇后結盟,畢竟皇后無子,要保住地位就得保住楚帝的性命。若是讓赫連輝或者赫連勇得逞,逼宮弒弟都做了,還有什麼是他們不敢的。
於是,有王貴妃、魏嬪在手,局面很快形成三足鼎立。司徒皇后帶著人退進了大殿。赫連輝瞪了赫連勇一眼,命禁衛軍占據一片地段,守住西邊宮門。赫連勇依樣畫葫蘆,尋了東邊地段駐紮,守住東段出入。
沒過多久,兩邊皆有人來報:「不好了,殿下,不好了!」
「出了什麼事?」赫連輝脾氣正暴著,喝問那傳訊兵,傳訊兵兢兢戰戰:「殿下,宋將軍叛變,傳下的命令是格殺勿論。康王府、靖王府、禧王府、順王府全被血洗。安王府早有準備,殺了我們不少人,突圍出去了。」
「蠢貨!」赫連輝一腳將他踢至老遠,「這會子才來報訊,頂個屁用!赫連勇這個王八蛋,老子就不該信他!什麼結盟,背後插刀子!格殺勿論,畜生心夠狠!」
「殿下……」傳訊兵跌跌爬爬滾過來,「有活口,有活口的……」
赫連輝眼睛一亮:「哦?是誰?」
傳訊兵道:「是康王。康王妃一人一騎,縛著康王跑了出來,她跑進了平王府,身邊有幾個懂武的侍女,挾持了平王的幾個兒子……」
赫連輝大驚:「什麼!」連叫不好,老五守的可是京城九門,專門防的老七。這回他的兒子都被抓了,後果不堪設想!
「康王夫婦呢?現在何處?」他緊急追問。
「不見了。」傳訊兵嚥了一大口口水,「宋將軍也知曉平王家眷動不得,帶了人去營救,結果內室空無一人。不知康王妃怎麼辦到的,兩人帶著孩子都不見了,只在牆上留下一句話:吾兒安,汝兒安。」
赫連輝頭皮立刻發麻,期盼的問:「康王的孩子,可有存活?」
傳訊兵頭也不敢抬,趴在地上哭喪著道:「殿下,禁衛軍先去的康王府,得的令是格殺勿論啊!」
赫連輝眼前一黑,差點暈厥過去。
另一邊,赫連勇也接到了同樣消息,一樣的發暈:「不好!立刻去攔住,嚴禁消息傳到城樓!」
傳訊兵又抖抖索索的彙報:「殿下,還有逃脫的。靖王妃、靖王次子失蹤。禧王失蹤、順王夫婦也失蹤不見。」
赫連勇一口氣差點哽住:「混蛋!」失蹤失蹤,合著忙活一通,老三、老八、老九一個沒死!加上離京在外的老七全活著。他媽的白忙一通!
幕僚上前勸道:「殿下,現下應全城搜捕才是。」
那邊,赫連輝的心腹也出了同樣的主意:「殿下,只要找到人,救了他們。就可將所有事推到二皇子那裡。」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書香貴女(四完)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90 |
中文書 |
$ 190 |
古代小說 |
$ 190 |
言情小說 |
$ 204 |
小說/文學 |
$ 216 |
古代小說 |
$ 216 |
華文羅曼史 |
$ 216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書香貴女(四完)
本書特色:
起點女生網粉紅榜常勝作品
《女帝》、《國色無雙》作者最新作品
內容簡介:
驚天宮變之後,做足準備的七皇子妃林若拙順利逃出,
前先得幼時故人袁清波的收留,
後又被初戀情人司徒九軟禁。
她知這是廟堂之爭造成的結果,
但她豈會被如此輕易拿捏,
就算身在古代,她也不會放棄掌握自己的命運!
而另一方面,對皇位勢在必得的赫連熙,
卻在娶了前世不曾存在過的林若拙後,
記憶中的軌跡似乎都變了調。
印象中大度溫柔的正妃,
於宮變之後,在他面前逐漸露出叛逆的真面目來了……
本書另附未公開番外。
作者簡介:
生肖屬蛇,星座天蠍,性別為女。勉強可算蛇蠍美人一名。由於孩童時代曾受蛀牙困擾,故而,「沒有蛀牙」是我的終身奮鬥目標。
性格特點為「慢」。動作慢、反應慢、寫文慢、說話慢。好友評價:這叫遲鈍。本人反駁:我也有快的時候呀,比如花錢很快。
最最討厭的事:現在的社會節奏太快!當然,網速什麼的還是快一點好,越快越好。
學過很多東西,學完之後也忘掉了很多。喜歡憑空幻想,幾乎每日不斷,雖然有些不實用,但我依然堅信,這是上天賜予我最好的禮物。
網路小說作品:《女帝生涯》、《國色無雙》、《星雲海》等。
章節試閱
第三十一章
林若拙吃驚的抬眼,說這種話,袁清波瘋了嗎?
又見早點攤的人都興致勃勃的圍觀,只得又垂了眼,輕聲道:「怕給你惹麻煩。」
中年女人第一個忍不住,快嘴快舌道:「袁大家,你認識秦姑娘?可是與她定親的未婚夫?」
未婚夫?袁清波一怔,隨即模稜兩可的接上:「妳怎麼就這樣出來了?」
林若拙暗讚一聲,不愧是演戲的老手,這話接得忒有水準,遂答道:「繼母欲將我嫁給她遠房的侄兒,我不肯依。想著上京來碰碰運氣,看能不能找到楊大哥。正巧兩個妹妹也要進京尋親,我們便搭夥一起離開了江寧。」
袁清波點點頭,道:「女孩...
林若拙吃驚的抬眼,說這種話,袁清波瘋了嗎?
又見早點攤的人都興致勃勃的圍觀,只得又垂了眼,輕聲道:「怕給你惹麻煩。」
中年女人第一個忍不住,快嘴快舌道:「袁大家,你認識秦姑娘?可是與她定親的未婚夫?」
未婚夫?袁清波一怔,隨即模稜兩可的接上:「妳怎麼就這樣出來了?」
林若拙暗讚一聲,不愧是演戲的老手,這話接得忒有水準,遂答道:「繼母欲將我嫁給她遠房的侄兒,我不肯依。想著上京來碰碰運氣,看能不能找到楊大哥。正巧兩個妹妹也要進京尋親,我們便搭夥一起離開了江寧。」
袁清波點點頭,道:「女孩...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流晶瞳
- 出版社: 知翎文化 出版日期:2014-09-03 ISBN/ISSN:978986578276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72頁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