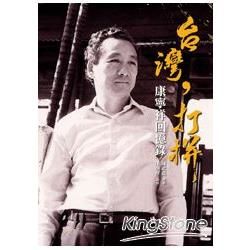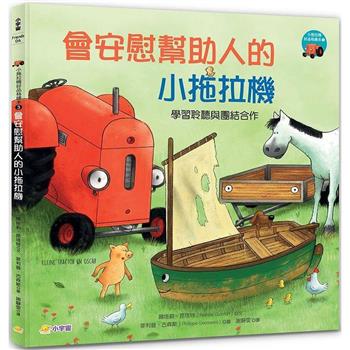從艋舺堀江町到國會殿堂
從加油站工人到入選《時代週刊》全球150位的未來領袖
康寧祥,《朝日新聞》推崇為台灣民主的見證者
《台灣,打拼》總結戰後台灣民主運動的劃時代鉅作
名人推薦
鄭欽仁‧鄒景雯‧陳傳岳‧陳永興‧齊邦媛‧管碧玲‧游錫堃‧楊祖珺‧黃爾璇‧彭百顯‧邱垂亮‧許雪姬‧南方朔‧呂亞力‧李筱峰隆重推薦
康寧祥從「黨外」運動到民主進步黨的成立,到台灣的民主化,幾經曲折坎坷之路,他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當時許多國內外政治觀察家認為,有朝一日康寧祥可以成為台灣的政治領導人。但是風雲際會的結果,後來居上的陳水扁成為總統,而康寧祥反而屈居其下。然而從歷史的觀點看,康寧祥對台灣民主化的影響,絕對不在陳水扁之下。很高興看到康寧祥先生出版了他的回憶錄,這位昔日台灣民主運動的重要推手,將為台灣的民主運動史、台灣的民主化過程留下珍貴的見證。要瞭解台灣民主化的過程,要瞭解台灣的政治變遷,就不能不看康寧祥這部回憶錄。
——李筱峰
在台灣真正稱得上「始終如一」的不多人裡,康寧祥可以說是一個質真價實的經典人物。他對台灣有著一種素直的情感關懷,他對自由民主更是執著不變。他對台灣人的主體認知,很有雖千萬人而吾獨往的壯志,雖然從一九六九年擔任台北市議員起,他已在台灣政壇四十餘年,但他的本色可謂毫無改變。在他一個人的身上,就縮影了上一個年代台灣民主運動波瀾壯濶大半的過程。
──康寧祥從政以來始終一貫的著重新知識分子的培養,過去在台灣發揮過知識分子領航作用的《台灣政論》、《八十年代》、《亞洲人》、《暖流》、《首都早報》都是他所創辦的。他培養出了一、兩個世代的新知識分子,一種新的文化認知因而在台灣形成。
《康寧祥回憶錄》的出版,乃是戰後台灣民主運動的一段總結,康寧祥無役不與,他是最有資格寫這段回憶的人,到了今天,深化民主的新的運動又到了再出發的時候,撫今追昔,康寧祥所做的貢獻更加歷歷在目,可供後人效法。老康,我們謝謝你!
——南方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