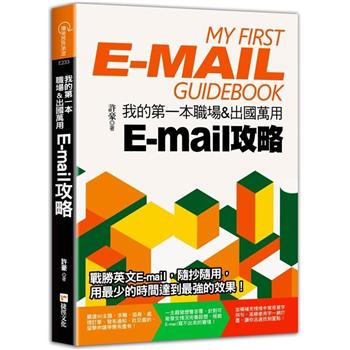曾以《土地與靈魂》一書獲得中山文藝獎,也曾獲得吳濁流文學獎的作家王幼華,創作不輟,極具個人色彩。 已出版的短篇小說有《惡徒》、《狂者的自白》及長篇小說《兩鎮演談》、《騷動的島》等。《東魚國夢華錄‧王幼華作品集》為其自選集,選錄代表性之創作,除了可綜覽創作軌跡外,更可看見作家長期以來對生命與存在感的一貫探索。
我的小說創作由一九七八年發表的〈雨季過後〉開始,直到今年已有三十五年了,此次輯錄的主要是短篇小說。收錄在這個集子中的,呈現了多年來創作的主要特色,也是個人認為最重要的作品。歷年來閱讀我小說的讀者,常常談到知解與詮釋的困惑,事實上作品完成後我也面臨同樣的迷障,並不能完整說清楚創作時的動機和情境,顯然它已成為獨立存在的個體。——王幼華
沒有蓓蕾時期,王幼華甫登文壇就是一朵盛開的惡之華。七、八十年代,時年二十餘歲的王幼華以充滿蠻力的快筆與企圖心,開始了他的憤怒書寫。學界曾根據王幼華不同階段、不同題材,給予了不同的流派名號。他兼寫三教九流呆兒癡漢各色小人物,被視為人道取向的現實主義作家、社會病理學家;台灣文壇風靡現代主義之際,他小說中頻頻出現狂徒、瘋子、超人、附魔者,被視為具有寓言特質的現代派作家;他以述代論的長篇力作《廣澤地》、《土地與靈魂》等探討原住民認同與尋根的文學,則被視為具有人類學視野的鄉土文學作家。然而,王幼華小說中有太多精神現象,彷彿是位腦波過於活躍的失眠者,暗夜未盡之際,以恣臆狂躁的話語,摹寫離奇的心理潛流與人格異變,其中告白、囈語與詛咒的敘事特質,造就了他獨樹一幟的「臆想體」風格。——陳器文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東魚國夢華錄:王幼華作品集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276 |
中文書 |
$ 277 |
中文現代文學 |
$ 308 |
小說 |
$ 315 |
小說 |
$ 315 |
現代小說 |
$ 315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東魚國夢華錄:王幼華作品集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王幼華
國立中興大學中文博士,曾任國立聯合大學華語文學系系主任,現任國立聯合大學台灣語文傳播與華語文學系合聘教授。出版作品有《土地與靈魂》、《騷動的島》、《洪福齊天》等小說集。學術論著有《清代臺灣漢語文獻原住民記述研究》、《考辨與詮說——清代台灣論述》、《蚌病成珠——古今作家論》等。曾獲吳濁流文學獎、中國文藝協會獎章、中山文藝獎等。作品意念繁富,深刻廣袤,在台灣文學作品裡獨樹一格。有關王幼華文學作品的評論,海內外(中國、日本、臺灣、香港等)共六十餘篇,部分作品亦翻譯為英文、日文。除文學創作、學術研究外王幼華亦展現「文學運動家」特質,以作家身分參與文化及社會運動,將理念付諸實踐。
王幼華
國立中興大學中文博士,曾任國立聯合大學華語文學系系主任,現任國立聯合大學台灣語文傳播與華語文學系合聘教授。出版作品有《土地與靈魂》、《騷動的島》、《洪福齊天》等小說集。學術論著有《清代臺灣漢語文獻原住民記述研究》、《考辨與詮說——清代台灣論述》、《蚌病成珠——古今作家論》等。曾獲吳濁流文學獎、中國文藝協會獎章、中山文藝獎等。作品意念繁富,深刻廣袤,在台灣文學作品裡獨樹一格。有關王幼華文學作品的評論,海內外(中國、日本、臺灣、香港等)共六十餘篇,部分作品亦翻譯為英文、日文。除文學創作、學術研究外王幼華亦展現「文學運動家」特質,以作家身分參與文化及社會運動,將理念付諸實踐。
目錄
自序─秋日夜宴荊棘園
評介—王幼華的本色原型與他的精神史 陳器文
狂徒 《聯合報》副刊,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六、十七日
歡樂人生路 《臺灣文藝》,一九八二年二月號
惡徒 《中國時報》副刊,一九八二年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二十日
健康公寓 《中外文學》,一九八三年四月號
救贖島 《台灣時報》副刊,一九八三年九月九日
洞悉者 《自立晚報》副刊,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超人阿A 《自立晚報》副刊,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八、十九日
花之亂流 《自立晚報》副刊,一九八七年三月六、七日
熱愛 《臺北評論》第五期,一九八八年五月一日
慈母灘碑記 《自立晚報》副刊,一九九四年三月三十日
癲狂與曖昧系列
1獅子 《臺灣日報》副刊,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2鐵絲網媽媽 《臺灣日報》副刊,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八日
3我有一種高貴的精神病 《臺灣日報》副刊,一九九八年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
啤酒徒旅行雜記系列
1航向美麗島 《臺灣日報》副刊,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2白皮膚天神 《臺灣日報》副刊,二○○○年四月二十日
3一起旅行吧!愛人 《臺灣日報》副刊,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4聖像島 《聯合報》副刊,二○○一年三月六日至八日
東魚國夢華錄 中國,《上海文學》,二○○六年七月號
剛果、剛果 中國,《上海文學》,二○○六年七月號
評介—王幼華的本色原型與他的精神史 陳器文
狂徒 《聯合報》副刊,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六、十七日
歡樂人生路 《臺灣文藝》,一九八二年二月號
惡徒 《中國時報》副刊,一九八二年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二十日
健康公寓 《中外文學》,一九八三年四月號
救贖島 《台灣時報》副刊,一九八三年九月九日
洞悉者 《自立晚報》副刊,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超人阿A 《自立晚報》副刊,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八、十九日
花之亂流 《自立晚報》副刊,一九八七年三月六、七日
熱愛 《臺北評論》第五期,一九八八年五月一日
慈母灘碑記 《自立晚報》副刊,一九九四年三月三十日
癲狂與曖昧系列
1獅子 《臺灣日報》副刊,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2鐵絲網媽媽 《臺灣日報》副刊,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八日
3我有一種高貴的精神病 《臺灣日報》副刊,一九九八年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
啤酒徒旅行雜記系列
1航向美麗島 《臺灣日報》副刊,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2白皮膚天神 《臺灣日報》副刊,二○○○年四月二十日
3一起旅行吧!愛人 《臺灣日報》副刊,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4聖像島 《聯合報》副刊,二○○一年三月六日至八日
東魚國夢華錄 中國,《上海文學》,二○○六年七月號
剛果、剛果 中國,《上海文學》,二○○六年七月號
序
評介
王幼華的本色原型與他的精神史
沒有蓓蕾時期,王幼華甫登文壇就是一朵盛開的惡之華。
七、八十年代,時年二十餘歲的王幼華以充滿蠻力的快筆與企圖心,開始了他的憤怒書寫。學界曾根據王幼華不同階段、不同題材,給予了不同的流派名號。他兼寫三教九流呆兒癡漢各色小人物,被視為人道取向的現實主義作家、社會病理學家;台灣文壇風靡現代主義之際,他小說中頻頻出現狂徒、瘋子、超人、附魔者,被視為具有寓言特質的現代派作家;他以述代論的長篇力作《廣澤地》、《土地與靈魂》等探討原住民認同與尋根的文學,則被視為具有人類學視野的鄉土文學作家。然而,王幼華小說中有太多精神現象,彷彿是位腦波過於活躍的失眠者,暗夜未盡之際,以恣臆狂躁的話語,摹寫離奇的心理潛流與人格異變,其中告白、囈語與詛咒的敘事特質,造就了他獨樹一幟的「臆想體」風格。又他在《野靈魂.惡筆記》、《蚌病成珠》等劄記論述中,興味盎然的探討有關創傷、躁狂、自毀、逐惡等精神症狀對作家的影響,發現非常的生理與心智狀態,每每成為作家獨特風格的催媒,因而不無得意地自稱:「我有一種高貴的精神病」、「我有一個非理性的瘋狂基地」……。無論文壇風向如何,無論小說上層文本呈現的意識形態與流派歸屬如何,閱讀王幼華筆下情節詭異、處處潛伏著人性騷亂的「臆想體」小說,不妨拋開流派定位,以最有趣最貼近的方式,來玩味他二、三十年來自覺或不自覺流露的本色原型與他的精神史。
從精神分析學派的論點來看,小說起源於「家庭傳奇」。作者說來說去其實都是編造身世故事,都是藉著寫作來舒解成長過程中的困窘與創傷。推而論之,小說基型只有兩種:一種是棄兒情結的浪漫文學,棄兒懷疑自己是撿來的孩子,一心希望更換好家庭,回到富貴風光的親生父母身邊。棄兒對社會認識不夠且拙於應對,只好創造一個與現實無關的夢幻世界,成為具有浪漫風格的作家。另一種是私生子情結的寫實文學,私生子想消滅父親(權威)取而代之,他一面投入人群,一面對主流社會痛加抨擊,成為富有寫實精神的作家。以「家庭傳奇」的角度來檢視《東魚國夢華錄》,選輯中林林總總的人物,最出挑的顯然是那位一如《倩女幽魂》聲勢奪人的姥姥型「媽媽」,媽媽舉動誇張、姿態高傲,脹痛的乳房可以擠出好幾碗乳汁分給鄰居小孩和小狗吃,讓「我」成為同儕間的傳奇與笑柄,而「我」卻成癮般又恨又歡地含著那顆暗青色的乳頭直到十歲。此外,小說中諸如母親將「命格奇特不可褻瀆的白癡兒」鎖入大鐵籠、又如母子搶喝死人傷口汩汩流出的血水、又如「我」以血手為母屍穿上不鏽鋼罩衫等等怪異已極的發想與意象,很難說不是母子癥結的異化。相形之下,臉色蒼白身子細長腳步虛浮的老爸,常常只是影子性的存在,濃妝大彩的母親與淡若幻影的父親,以強/弱、濃/淡的對比,表現出「我」與父、母的心理距離及情感關係,也揭露了王幼華在精神分析上所呈現的本色原型。接近原始大母神的惡靈媽媽,點燃了作者王幼華生理心理所有的激情,他以葷素不忌的題材、霸氣外露的筆調,輝煌野性的張揚,摹繪出惡之華的逼人火舌,火種顯然來自於母子間深刻的依賴與尖銳的厭斥。
有「東方的文化惡魔」之稱的魯迅,曾發表〈摩羅詩力說〉一文推崇惡魔派文學,以「吃人禮教」、「人血饅頭」、「黑暗閘門」等血腥的文學圖像,開啟了中國小說黑色現實主義路線。王幼華步武魯迅的文風,將血腥與醜陋納入書寫美學,追求一種惡魔的美。這種寫醜的美學,其一表現在對美醜的感應上:美是虛幻的,是偶然光影產生的幻像,是荷爾蒙作用的幻覺;醜陋則是具體實存的,像是泌出黑黃色奶水的腫脹乳房、流膿的生殖器、人吃的乾腦子、黑紫腫脹的吊陰功等異形化的身體。其二表現在男歡女愛的取材上:二、三十年來王幼華的小說,竟無一篇敘說愛情,只有赤裸裸的性:拉下褲子張開腿,躺在教室桌子上的女工、被鎖鍊綁成大字形展示的光裸女人、比腰下東西大小的性狂歡等等,作者還不忘譏誚說:「每個旅行的男人,胯下總是飽脹一袋精液」、「女人的陰道,讓和尚廟更輝煌」。其三表現在墮落史觀上:每個人都是時、空壓迫下的受創體,每個人的個性、人格乃至身體都會發生異變,越變越疑懼、怔忡、陰暗乃至瘋狂,光怪陸離的異變,看來荒誕,卻透露著生命內裏的黑暗與複雜,異變既是王幼華的敘述主題也是結構母題,故事中的主人翁:一非禮讚人性的利他者、二非卑微的被害者、三非合群的善良人,像尼采一樣,王幼華的小說是寫給強者看的,一切柔弱、自苦和忍耐者都應該被消滅和淘汰。不敢正視慘酷現實的人,就只有在生命大缺陷與人生大黑暗前,落荒而逃。
《蚌病成珠》序文中,王幼華夫子自道:「作家在自覺或不自覺裏向世人揭露創傷,發抒感性,書寫的是自己其實也是眾生」,小說中的情境雖然揭露的是傳統文化與現實社會的病態與邪惡,卻也暴露了作者本人內心的憤懣和陰暗。揮舞著文字魔杖的王幼華,精神上是個「個人主義之至雄傑者」,卻以馬戲團獅子和馴獸師雙面應世;他向傳統挑戰,與社會對立,與人群衝突,又很世故,為人圓滑,不以他的世故和圓滑混世;他慣用誇張的反語,又不是完全沒有真實性;在這個英雄與野性已經消失的時代,他對任何神聖的事物,都表現出一種顛覆的慾望,卻又沒有忘情於舊學,是一個「為往聖繼絕學」的文人,正襟危坐讀劉勰、讀杜甫、讀陳肇興的長篇歌行;他是一個自我拔高的狂人、瘋子、一個受迫害狂,又是一個好學生,好老師,一個大孝子。他坦率的自剖,讀者反而視為小說的虛構特性,沒有把小說人物和他的自剖聯繫起來,他在解剖自我的時候,故意籠罩上一層霧似的藝術之紗。正言若反,反話正說,迂迴的態度真誠的話語,是「破譯」王幼華下層文本的通幽曲徑。
唯心主義集大成者黑格爾說:「有人以為,當他說人性本善這句話時,是說出了一種偉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記了,當人們說人性本惡這句話時,是說出了一種更偉大的思想。」歷史上往往高估善良和仁慈的文化表相,善的文化一向是以合群性與整體性為標榜,反而導致頹廢化的後果,善良成為柔弱的代稱。中國文化以人性本善為基調,對惡的否定,使中國文化成為一種鄉愿與假面的文化、一種停滯的文化,強調文化的否定性與批判性,視惡為歷史發展的動力與能量,正是推崇魯迅為文化惡魔的著眼所在。「逢佛殺佛,逢祖殺祖」惡文化的思維模式,是一種自我覺醒之後的個人主義文化,是一種否定性與褻瀆性的文化,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對某一神聖事物的褻瀆,表現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習慣性的迎合的叛逆。褻瀆意識,剝開了僵硬虛偽的現實外殼,這使王幼華較一般社會寫實作家,更坦率地反映寫醜的意義:是對痛苦、罪惡以及一切可疑之物的面對面,是一種新生文化對舊文化的顛覆。
陳器文/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教授
自序
秋日夜宴荊棘園
我的小說創作由一九七八年發表的︿雨季過後﹀開始,直到今年已有三十五年了,此次輯錄的主要是短篇小說。收錄在這個集子中的,呈現了多年來創作的主要特色,也是個人認為重要的作品。歷年來閱讀我小說的讀者,常常談到知解與詮釋的困惑,事實上作品完成後我也面臨同樣的迷障,並不能完整說清楚創作時的動機和情境,顯然它已成為獨立存在的個體。這其間的歧義與縫隙,偶爾在評論者的論述中被解說、被發現出來,但大部分還是在誤讀與作者自我訴說的狀態裡。至於那些沒有發言的「隱藏讀者」,因為不可查知,就僅能期望「暫時相賞莫相違」了。
一般來說,人們在新書發表會、就職典禮、歡送會、喪禮、紀念會等,都會邀請重要貴賓參加,用意上既是宣告也是慎重。典禮中邀請適當的人上臺,說一說與主人的關係,推崇當事者的可敬表現,凸顯其人優點,減去枝節,使場面合宜而恰當。當然除非蓄意鬧場,不以為然者,通常不會出席。歷史上有兩場知名的聚會,這兩場都是在春光明媚時舉辦的,地點也選在花木繁茂,景色宜人之處。其一是王羲之的「蘭亭宴集」,另一是李白在「桃李園」的歡宴,聚會的參與者是親人和文友。這兩會之所以會流傳後世,是主人書法和文章的雋雅精妙,他們呈現了某些永恆的、難以超越的印記,令人低迴詠讚。我非名門貴冑,體無仙氣,這本作品集的出版,大約無法舉辦類似的宴會,也不請貴賓說些體面的話。不過,為了讓可敬的閱讀者,能較順利的進入我所構築的文學世界,在秋風冷肅、夕陽若血的某一夜晚,決定在荊棘滿地、枯樹蕭疏、烏鴉聒噪的「荊棘園」,宴請影響我創作的重要人物。經過一番斟酌,開列名單如下:釋迦牟尼、耶穌、孔子、杜甫、杜斯妥也夫斯基、梵谷、佛洛伊德、魯迅、黑澤明、卡繆、卓別林等(可能漏掉尼采)。
眾賢們接到我的邀請後,欣然的由四面八方陸續來到。他們不煩事主,各自帶來喜好的食物、菸和酒,自在入席。當晚賓客與主人,賓客與賓客之間,做了無窮盡的、不可思議的對話,激起了無數的機鋒,晃動了巨大的思辨波濤,成就了不欲人知的勝場。畢竟是個難得的聚會,眾賓客淋漓盡興之後,便各自怡然的離去。
荊棘園之會的殊勝,是難以記述、言詮的。畢竟再美好的盛宴, 總有人疲慮乏、燈熄酒盡的時候。看著空去的桌椅,不免感到激情之後的惆悵。幸好,他們的身影可以在我的作品中,若明若暗、糾纏不已的「 看見」,並不會就此寂然的消散。
王幼華的本色原型與他的精神史
沒有蓓蕾時期,王幼華甫登文壇就是一朵盛開的惡之華。
七、八十年代,時年二十餘歲的王幼華以充滿蠻力的快筆與企圖心,開始了他的憤怒書寫。學界曾根據王幼華不同階段、不同題材,給予了不同的流派名號。他兼寫三教九流呆兒癡漢各色小人物,被視為人道取向的現實主義作家、社會病理學家;台灣文壇風靡現代主義之際,他小說中頻頻出現狂徒、瘋子、超人、附魔者,被視為具有寓言特質的現代派作家;他以述代論的長篇力作《廣澤地》、《土地與靈魂》等探討原住民認同與尋根的文學,則被視為具有人類學視野的鄉土文學作家。然而,王幼華小說中有太多精神現象,彷彿是位腦波過於活躍的失眠者,暗夜未盡之際,以恣臆狂躁的話語,摹寫離奇的心理潛流與人格異變,其中告白、囈語與詛咒的敘事特質,造就了他獨樹一幟的「臆想體」風格。又他在《野靈魂.惡筆記》、《蚌病成珠》等劄記論述中,興味盎然的探討有關創傷、躁狂、自毀、逐惡等精神症狀對作家的影響,發現非常的生理與心智狀態,每每成為作家獨特風格的催媒,因而不無得意地自稱:「我有一種高貴的精神病」、「我有一個非理性的瘋狂基地」……。無論文壇風向如何,無論小說上層文本呈現的意識形態與流派歸屬如何,閱讀王幼華筆下情節詭異、處處潛伏著人性騷亂的「臆想體」小說,不妨拋開流派定位,以最有趣最貼近的方式,來玩味他二、三十年來自覺或不自覺流露的本色原型與他的精神史。
從精神分析學派的論點來看,小說起源於「家庭傳奇」。作者說來說去其實都是編造身世故事,都是藉著寫作來舒解成長過程中的困窘與創傷。推而論之,小說基型只有兩種:一種是棄兒情結的浪漫文學,棄兒懷疑自己是撿來的孩子,一心希望更換好家庭,回到富貴風光的親生父母身邊。棄兒對社會認識不夠且拙於應對,只好創造一個與現實無關的夢幻世界,成為具有浪漫風格的作家。另一種是私生子情結的寫實文學,私生子想消滅父親(權威)取而代之,他一面投入人群,一面對主流社會痛加抨擊,成為富有寫實精神的作家。以「家庭傳奇」的角度來檢視《東魚國夢華錄》,選輯中林林總總的人物,最出挑的顯然是那位一如《倩女幽魂》聲勢奪人的姥姥型「媽媽」,媽媽舉動誇張、姿態高傲,脹痛的乳房可以擠出好幾碗乳汁分給鄰居小孩和小狗吃,讓「我」成為同儕間的傳奇與笑柄,而「我」卻成癮般又恨又歡地含著那顆暗青色的乳頭直到十歲。此外,小說中諸如母親將「命格奇特不可褻瀆的白癡兒」鎖入大鐵籠、又如母子搶喝死人傷口汩汩流出的血水、又如「我」以血手為母屍穿上不鏽鋼罩衫等等怪異已極的發想與意象,很難說不是母子癥結的異化。相形之下,臉色蒼白身子細長腳步虛浮的老爸,常常只是影子性的存在,濃妝大彩的母親與淡若幻影的父親,以強/弱、濃/淡的對比,表現出「我」與父、母的心理距離及情感關係,也揭露了王幼華在精神分析上所呈現的本色原型。接近原始大母神的惡靈媽媽,點燃了作者王幼華生理心理所有的激情,他以葷素不忌的題材、霸氣外露的筆調,輝煌野性的張揚,摹繪出惡之華的逼人火舌,火種顯然來自於母子間深刻的依賴與尖銳的厭斥。
有「東方的文化惡魔」之稱的魯迅,曾發表〈摩羅詩力說〉一文推崇惡魔派文學,以「吃人禮教」、「人血饅頭」、「黑暗閘門」等血腥的文學圖像,開啟了中國小說黑色現實主義路線。王幼華步武魯迅的文風,將血腥與醜陋納入書寫美學,追求一種惡魔的美。這種寫醜的美學,其一表現在對美醜的感應上:美是虛幻的,是偶然光影產生的幻像,是荷爾蒙作用的幻覺;醜陋則是具體實存的,像是泌出黑黃色奶水的腫脹乳房、流膿的生殖器、人吃的乾腦子、黑紫腫脹的吊陰功等異形化的身體。其二表現在男歡女愛的取材上:二、三十年來王幼華的小說,竟無一篇敘說愛情,只有赤裸裸的性:拉下褲子張開腿,躺在教室桌子上的女工、被鎖鍊綁成大字形展示的光裸女人、比腰下東西大小的性狂歡等等,作者還不忘譏誚說:「每個旅行的男人,胯下總是飽脹一袋精液」、「女人的陰道,讓和尚廟更輝煌」。其三表現在墮落史觀上:每個人都是時、空壓迫下的受創體,每個人的個性、人格乃至身體都會發生異變,越變越疑懼、怔忡、陰暗乃至瘋狂,光怪陸離的異變,看來荒誕,卻透露著生命內裏的黑暗與複雜,異變既是王幼華的敘述主題也是結構母題,故事中的主人翁:一非禮讚人性的利他者、二非卑微的被害者、三非合群的善良人,像尼采一樣,王幼華的小說是寫給強者看的,一切柔弱、自苦和忍耐者都應該被消滅和淘汰。不敢正視慘酷現實的人,就只有在生命大缺陷與人生大黑暗前,落荒而逃。
《蚌病成珠》序文中,王幼華夫子自道:「作家在自覺或不自覺裏向世人揭露創傷,發抒感性,書寫的是自己其實也是眾生」,小說中的情境雖然揭露的是傳統文化與現實社會的病態與邪惡,卻也暴露了作者本人內心的憤懣和陰暗。揮舞著文字魔杖的王幼華,精神上是個「個人主義之至雄傑者」,卻以馬戲團獅子和馴獸師雙面應世;他向傳統挑戰,與社會對立,與人群衝突,又很世故,為人圓滑,不以他的世故和圓滑混世;他慣用誇張的反語,又不是完全沒有真實性;在這個英雄與野性已經消失的時代,他對任何神聖的事物,都表現出一種顛覆的慾望,卻又沒有忘情於舊學,是一個「為往聖繼絕學」的文人,正襟危坐讀劉勰、讀杜甫、讀陳肇興的長篇歌行;他是一個自我拔高的狂人、瘋子、一個受迫害狂,又是一個好學生,好老師,一個大孝子。他坦率的自剖,讀者反而視為小說的虛構特性,沒有把小說人物和他的自剖聯繫起來,他在解剖自我的時候,故意籠罩上一層霧似的藝術之紗。正言若反,反話正說,迂迴的態度真誠的話語,是「破譯」王幼華下層文本的通幽曲徑。
唯心主義集大成者黑格爾說:「有人以為,當他說人性本善這句話時,是說出了一種偉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記了,當人們說人性本惡這句話時,是說出了一種更偉大的思想。」歷史上往往高估善良和仁慈的文化表相,善的文化一向是以合群性與整體性為標榜,反而導致頹廢化的後果,善良成為柔弱的代稱。中國文化以人性本善為基調,對惡的否定,使中國文化成為一種鄉愿與假面的文化、一種停滯的文化,強調文化的否定性與批判性,視惡為歷史發展的動力與能量,正是推崇魯迅為文化惡魔的著眼所在。「逢佛殺佛,逢祖殺祖」惡文化的思維模式,是一種自我覺醒之後的個人主義文化,是一種否定性與褻瀆性的文化,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對某一神聖事物的褻瀆,表現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習慣性的迎合的叛逆。褻瀆意識,剝開了僵硬虛偽的現實外殼,這使王幼華較一般社會寫實作家,更坦率地反映寫醜的意義:是對痛苦、罪惡以及一切可疑之物的面對面,是一種新生文化對舊文化的顛覆。
陳器文/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教授
自序
秋日夜宴荊棘園
我的小說創作由一九七八年發表的︿雨季過後﹀開始,直到今年已有三十五年了,此次輯錄的主要是短篇小說。收錄在這個集子中的,呈現了多年來創作的主要特色,也是個人認為重要的作品。歷年來閱讀我小說的讀者,常常談到知解與詮釋的困惑,事實上作品完成後我也面臨同樣的迷障,並不能完整說清楚創作時的動機和情境,顯然它已成為獨立存在的個體。這其間的歧義與縫隙,偶爾在評論者的論述中被解說、被發現出來,但大部分還是在誤讀與作者自我訴說的狀態裡。至於那些沒有發言的「隱藏讀者」,因為不可查知,就僅能期望「暫時相賞莫相違」了。
一般來說,人們在新書發表會、就職典禮、歡送會、喪禮、紀念會等,都會邀請重要貴賓參加,用意上既是宣告也是慎重。典禮中邀請適當的人上臺,說一說與主人的關係,推崇當事者的可敬表現,凸顯其人優點,減去枝節,使場面合宜而恰當。當然除非蓄意鬧場,不以為然者,通常不會出席。歷史上有兩場知名的聚會,這兩場都是在春光明媚時舉辦的,地點也選在花木繁茂,景色宜人之處。其一是王羲之的「蘭亭宴集」,另一是李白在「桃李園」的歡宴,聚會的參與者是親人和文友。這兩會之所以會流傳後世,是主人書法和文章的雋雅精妙,他們呈現了某些永恆的、難以超越的印記,令人低迴詠讚。我非名門貴冑,體無仙氣,這本作品集的出版,大約無法舉辦類似的宴會,也不請貴賓說些體面的話。不過,為了讓可敬的閱讀者,能較順利的進入我所構築的文學世界,在秋風冷肅、夕陽若血的某一夜晚,決定在荊棘滿地、枯樹蕭疏、烏鴉聒噪的「荊棘園」,宴請影響我創作的重要人物。經過一番斟酌,開列名單如下:釋迦牟尼、耶穌、孔子、杜甫、杜斯妥也夫斯基、梵谷、佛洛伊德、魯迅、黑澤明、卡繆、卓別林等(可能漏掉尼采)。
眾賢們接到我的邀請後,欣然的由四面八方陸續來到。他們不煩事主,各自帶來喜好的食物、菸和酒,自在入席。當晚賓客與主人,賓客與賓客之間,做了無窮盡的、不可思議的對話,激起了無數的機鋒,晃動了巨大的思辨波濤,成就了不欲人知的勝場。畢竟是個難得的聚會,眾賓客淋漓盡興之後,便各自怡然的離去。
荊棘園之會的殊勝,是難以記述、言詮的。畢竟再美好的盛宴, 總有人疲慮乏、燈熄酒盡的時候。看著空去的桌椅,不免感到激情之後的惆悵。幸好,他們的身影可以在我的作品中,若明若暗、糾纏不已的「 看見」,並不會就此寂然的消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