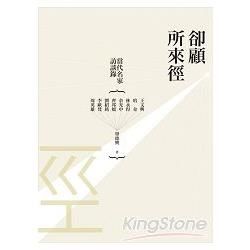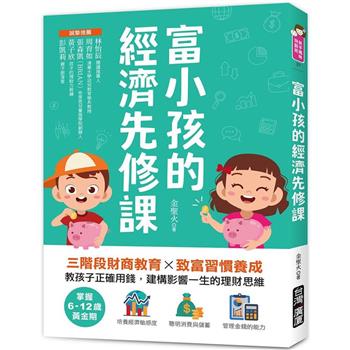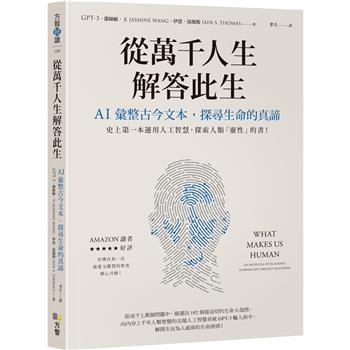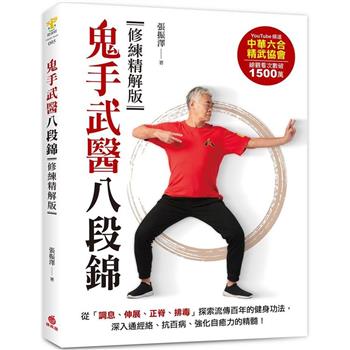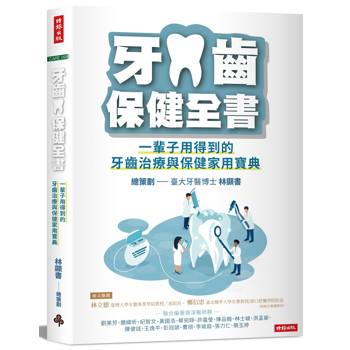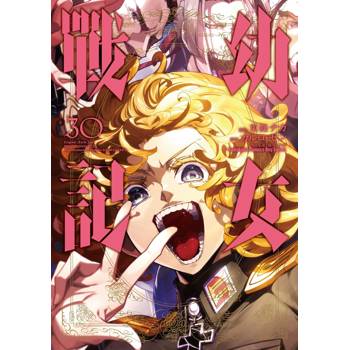本書是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單德興教授繼《對話與交流:當代中外作家、批評家訪談錄》(麥田,二○○一)和《與智者為伍:亞美文學與文化名家訪談錄》(允晨,二○○九)之後的另一本訪談力作。
以深度人文訪談知名於華文世界的主訪人,從台灣學者暨雙語知識分子的發言位置與人文關懷出發,針對具有帶表性的我國、香港與亞美詩人、小說家、學者、翻譯家進行深入訪談,對象包括王文興、余光中、李歐梵、周英雄、林永得、哈金、齊邦媛、劉紹銘等重量級人物。訪談雙方認識經年,在堅穩的互信基礎上,主訪人事先詳閱資料,準備問題,現場臨機應變,殷殷扣問;受訪人開誠佈公,侃侃而談,熱心無私地分享個人經驗、學思歷程、專業洞見。全書內容豐富多元,涵蓋了文學理念、創作歷程、翻譯經驗、學術心得、批評見解,並涉及文學與宗教、戰爭與文學、創傷與創作、歷史與正義等重要議題,以及對於台灣的人文生態與外文學門建制的體驗與觀察。透過這些深入淺出的對話與交流,不僅為受訪人留下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也提供華文世界讀者一窺受訪人的內心世界、分享其寶貴的人生經驗與專業見解的難得機會。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卻顧所來徑:當代名家訪談錄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69 |
二手中文書 |
$ 315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351 |
中文書 |
$ 351 |
華文文學研究 |
$ 359 |
其他文學總論 |
$ 359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卻顧所來徑:當代名家訪談錄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單德興
國立台灣大學博士(比較文學),現任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嶺南大學翻譯系兼任人文學特聘教授,曾任歐美研究所所長,《歐美研究》季刊主編,行政院國科會外文學門召集人,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理事長,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美國加州大學、哈佛大學、紐約大學、英國伯明罕大學訪問學人及傅爾布萊特資深訪問學人,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國立交通大學外文系兼任教授,靜宜大學英文系兼任講座教授,並三度獲得行政院國科會外文學門傑出研究獎,第五十四屆教育部學術獎,第六屆梁實秋文學獎譯文組首獎,第三十屆金鼎獎最佳翻譯人獎。
著有《銘刻與再現: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論集》、《反動與重演:美國文學史與文化批評》、《越界與創新:亞美文學與文化研究》、《翻譯與脈絡》、《薩依德在台灣》等,出版訪談集《對話與交流:當代中外作家、批評家訪談錄》、《與智者為伍:亞美文學與文化名家訪談錄》,譯有《近代美國理論:建制‧壓抑‧抗拒》、《美國夢的挑戰:在美國的華人》、《文學心路:英美名家訪談錄》、《知識分子論》、《格理弗遊記》、《權力、政治與文化:薩依德訪談集》等近二十本專書,主編或合編多種專書及期刊,並與李有成先生、張力先生擔任《朱立民先生訪問紀錄》主訪。研究領域包括美國文學史、亞美文學、比較文學、文化研究、翻譯研究等。
單德興
國立台灣大學博士(比較文學),現任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嶺南大學翻譯系兼任人文學特聘教授,曾任歐美研究所所長,《歐美研究》季刊主編,行政院國科會外文學門召集人,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理事長,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美國加州大學、哈佛大學、紐約大學、英國伯明罕大學訪問學人及傅爾布萊特資深訪問學人,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國立交通大學外文系兼任教授,靜宜大學英文系兼任講座教授,並三度獲得行政院國科會外文學門傑出研究獎,第五十四屆教育部學術獎,第六屆梁實秋文學獎譯文組首獎,第三十屆金鼎獎最佳翻譯人獎。
著有《銘刻與再現: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論集》、《反動與重演:美國文學史與文化批評》、《越界與創新:亞美文學與文化研究》、《翻譯與脈絡》、《薩依德在台灣》等,出版訪談集《對話與交流:當代中外作家、批評家訪談錄》、《與智者為伍:亞美文學與文化名家訪談錄》,譯有《近代美國理論:建制‧壓抑‧抗拒》、《美國夢的挑戰:在美國的華人》、《文學心路:英美名家訪談錄》、《知識分子論》、《格理弗遊記》、《權力、政治與文化:薩依德訪談集》等近二十本專書,主編或合編多種專書及期刊,並與李有成先生、張力先生擔任《朱立民先生訪問紀錄》主訪。研究領域包括美國文學史、亞美文學、比較文學、文化研究、翻譯研究等。
目錄
自序:扣問與迴響
創作篇
文學與宗教:王文興訪談錄
宗教與文學:王文興訪談錄
小說背後的作者世界:王文興鼎談錄
美國‧自由‧生活:哈金訪談錄
詩歌‧歷史‧正義:林永得訪談錄
翻譯篇
第十位繆斯:余光中訪談錄
翻譯面面觀:齊邦媛訪談錄
寂寞翻譯事:劉紹銘訪談錄
學術篇
曲終人不散,江上數峰青:齊邦媛訪談錄
狐狸型學者的自我文本解讀:李歐梵訪談錄
卻顧所來徑:周英雄訪談錄
出處
創作篇
文學與宗教:王文興訪談錄
宗教與文學:王文興訪談錄
小說背後的作者世界:王文興鼎談錄
美國‧自由‧生活:哈金訪談錄
詩歌‧歷史‧正義:林永得訪談錄
翻譯篇
第十位繆斯:余光中訪談錄
翻譯面面觀:齊邦媛訪談錄
寂寞翻譯事:劉紹銘訪談錄
學術篇
曲終人不散,江上數峰青:齊邦媛訪談錄
狐狸型學者的自我文本解讀:李歐梵訪談錄
卻顧所來徑:周英雄訪談錄
出處
序
序
沉甸甸的書稿交出時,我笑說:「明天要睡到自然醒。」
這本書集結了我近年來有緣訪談的華人世界代表性作者、譯者與學者的文字紀錄與圖片,文稿一改再改,圖片一增再增,終能在出國研究前六天,溽暑的七月下旬車水馬龍的南京東路一棟辦公大廈的六樓,交出這份逾二十二萬字、百張圖片的訪談稿,放下心中一塊巨石。
果然一夜好眠。
第二天早上醒來,內室還是一片黑暗,就著手錶的微光端詳,竟然不到五點,比平常還要提早不少。既然已經醒來,便趁著涼爽的清晨出外。記不得有多久沒這麼早出門散步了。沿著四分溪走在中央研究院裡,清晨的頭腦特別靈活,不禁想到任職中研院已超過三十一個年頭,在這一萬一千多個日子裡,除非出門在外,否則幾乎天天走路上班,這種生活已超過了半輩子,成為我全部的學術生涯,不禁感到「此身雖在,堪驚」。
不知不覺路過任職的歐美研究所(我初到時是「美國文化研究所」,一九九一年易名),來到民族學研究所旁的側門,穿過研究院路,就是胡適公園。我大約每週路過此地一次訪人。原先的小徑這幾星期在整修,平時不見有人工作,卻依然拉上黃布條。繞道的小徑經過胡適墓園和銅像,即使未曾駐足,每次依然對這位五四健將、中研院前院長油然生出緬懷之心。今晨無事,就在此流連片刻,遙想昔日風光,反思自己的研究生活:從不知中研院為何物,至今已成為資深研究人員,過著外人眼中逍遙、光鮮的自由生活,卻不知何為「朝九晚五」、「週休二日」,總是一篇論文接著另一篇論文,一個研究計畫接著另一個研究計畫,過著「債台高築」的日子,似乎永遠沒有償清的一天。年年月月就在學術之路尋尋覓覓中度過──難道研究(“research”)就是永無止境的尋覓再尋覓(“re-search”)?
於是一篇篇的論文和一本本的專書、譯作就成了尋覓過程中的雪泥鴻爪,記錄了自己思索與努力的階段性成果,集中於對人性的探索、對文學的喜好以及對人文的尊崇,而這些俱是人之所以為人,人類之所以有今日的文明與文化的核心因素。年屆耳順的我,益發感到時不我予,如何利用日漸短少消逝的時光與體力,將所見所聞所思所學記錄下來,與有緣者對話交流、切磋砥礪,成了當務之急。
《卻顧所來徑──當代名家訪談錄》是我繼《對話與交流:當代中外作家、批評家訪談錄》(台北:麥田,2001)與《與智者為伍:亞美文學與文化名家訪談錄》(台北:允晨文化,2009)之後出版的第三本訪談集。尤記得就讀台大外文研究所碩士班時,初次讀到《巴黎評論》(Paris Review)的訪談,甚受感動與啟發,不忍獨享,於是從數冊《作家訪談集》(Writers at Work)中精選、翻譯了十幾位英美名作家,包括數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翻譯時的細讀深思、字斟句酌使得《巴黎評論》的訪談標準深入我心,成為後來自己從事訪談時根深柢固的習性,算來也已超過三十年。
在《對話與交流》的〈緒論〉中,我根據中外資料與親身經驗,闡明了訪談這個文類(genre)或次文類(sub-genre)的特色與錯綜複雜,並強調其中涉及的美學、政治、倫理:亦即,訪談的文字、修辭與結構的整理、講究與安排,主訪者與受訪者之間微妙的互動與權力關係,以及主訪者對受訪者與讀者所獨具的再現的權力/權利與義務。在《與智者為伍》的序言中,我也指出與學有專精、充滿智慧與行動力的作家與知識分子交流、問學的樂趣與收穫。文中並以土耳其作家帕慕克(Orhan Pamuk)為例,指出《巴黎評論》一篇與美國作家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的訪談,在當時年方二十五、懷抱作家夢的異地青年心目中有如「一個神聖的文本」,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堅定了他寫作的信心,竟於三十年後同樣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並為《巴黎評論訪談錄,第二輯》(The Paris Review Interviews, II)撰寫序言,顯示了文字因緣的不可思議。
這些訪談與我個人的專業領域息息相關,很大程度反映了我個人的學術興趣與生命關懷。而在人生路程能與這些傑出的中外作家、學者、批評家相逢,建立文字因緣,留下白紙黑字的紀錄,對於個性內斂的我來說,也是難能可貴的事。因此,我在《與智者為伍》的序言結尾期許:「身為代言人、再現者的訪談者,在為自己求知、解惑的同時,也可藉由訪談錄將個人的關懷與受訪者的回答公諸於世,分享他人,縱使未必知道這些訪談的效應如何,但或許某時某地某個有緣人能像帕慕克一樣,在其中得到安慰、鼓勵與指引。」
相較於前兩本訪談集,本書的十一篇訪談集中於我國與華裔人士,都是我佩服的前輩師長與作家──余光中教授與王文興教授更分別是我在政大西語系與台大外文所的老師,以及文學、翻譯、訪談方面的啟蒙師。全書依主題分為創作篇、翻譯篇與學術篇。創作篇的篇數最多(五篇),幾佔一半,是在不同的時空因緣下訪談的三位作家──王文興(三篇)、哈金(Ha Jin)與林永得(Wing Tek Lum)各一篇──針對彼此關切的議題進行訪問。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八三年我為了第一篇國際會議論文,首次進行訪談,對象就是王老師,當時兩人都稱許《巴黎評論》的高規格訪談,而那篇仔細修訂的訪談逾三萬字,後來成為王文興研究的代表性文獻之一。將近三十年後再度因為不同的機緣向王老師請益,尤其是討論一般文學研究中較少觸及的宗教、靈修與終極關懷,再度令我大開眼界,也是師生之間難得的跨宗教對話(王老師是天主教徒,我是佛教徒)。至於第三代華裔夏威夷詩人林永得與第一代華美作家哈金都是我多年研究的對象,佩服他們透過寫作所表達的人道關懷。一九九七年與林永得的當面訪談收錄於《對話與交流》,二○○八年與哈金的書面訪談收錄於《與智者為伍》,之後一路追蹤他們的文學創作:林永得自一九九七年閱讀了華美作家張純如的《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之後,多年以詩作表達對於南京大屠殺的關切以及對戰爭的反思;哈金於《自由生活》(A Free Life)中展現了流亡美國、過自由生活的同時,在異域他鄉以非母語寫作的艱辛與挑戰、堅持與成果,於《南京安魂曲》(Nanjing Requiem)中頌讚美國傳教士、教育家魏特琳(Minnie Vautrin)在南京淪陷後保護南京婦孺的崇高義舉,譴責日本侵華戰爭的罪行。
翻譯篇為本書的特色,因為前兩本訪談集雖然偶爾觸及文學與文化翻譯,卻未專門針對翻譯這個重要議題進行訪談,而本書所訪談的三位華文世界的前輩學者──余光中老師、齊邦媛教授和劉紹銘教授──數十年推動翻譯不遺餘力,受到國內外學界、翻譯界、文化界普遍肯定,但在他們的多重角色與貢獻中,攸關文學與文化交流的翻譯卻不見深入的訪談。余老師自中學起便翻譯不輟,自稱詩歌、散文、評論、翻譯是他「寫作生命的四度空間」,與詩作相互影響,也曾將詩作自譯成英文,但翻譯卻成為他的文學世界中最被忽略的領域。齊老師自抗戰時代起便閱讀翻譯作品,任職國立編譯館時大力推動台灣文學外譯與外國經典中譯,多年擔任《中華民國筆會》總編輯,後來又與王德威教授為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合編「台灣現代華語文學」(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系列,是台灣文學向國際進軍的重要推手,數十年如一日。劉教授多年來以英文編譯中國古典文學、現代文學與台灣文學,成為美國大學的教科書,一九七○、八○年代分別以中文譯介猶太裔與華裔美國文學,開華文世界風氣之先。他們的翻譯成果都為文學界提供了重要的養分,促進文化交流,卻未得到應有的評價與重視。為了彌補這個缺憾,矯正華文世界與學界對翻譯的忽視與偏見,我特地針對這個議題向三位翻譯界與文學界的前輩進行訪談,請他們分享多年從事翻譯、推動翻譯以及評論翻譯的經驗與心得,為華文翻譯界留下難得的史料。
學術篇則與我關切的學術建制史(institutional history)有關,訪談的三位都是華文世界的知名學者──齊老師、李歐梵教授與周英雄教授。三人背景的異同正可發揮相輔相成之效。齊老師出生於中國東北遼寧省,於抗戰時期接受文學教育,受朱光潛先生啟發尤深,此訪談是繼先前為其回憶錄《巨流河》(台北:天下文化,2009)的口述底稿而做。她是光復後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第一位助教,創立國立中興大學外文系,為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的十二位發起人之一,參與並見證了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在台灣的推動與發展。李教授出生於中國河南省,於台灣長大,在訪談中他別出心裁地將自己視為文本加以解讀,有關新竹中學的敘述讓人緬懷辛志平校長的教育理念與深遠影響,保送進入台大外文系之後與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歐陽子等人同班,共同打造了《現代文學》的傳奇,赴美留學時所遭逢的名家與際遇,出入於文學、歷史與理論之間,對於美國與兩岸三地學界的觀察……在在令人回味。周教授則出生於台灣雲林虎尾,在訪談中敘述了就讀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與研究所時的情形,先後負笈夏威夷與加州,學成後赴香港任教多年,又返回台灣在不同的學術行政職位與民間學會推動台灣外文學門的研究與發展。由這三位的出身背景、求學過程、學術發展、經歷與貢獻,多少可以勾勒出台灣的外文學門,尤其是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的軌跡與特色,為台灣的學術建制史留下珍貴的經驗與紀錄。
由上述可知,本書涉及創作、翻譯、學術建制等不同面向,有其多元性,基本上是一位台灣學者在不同的機緣下,從其知識立場與發言位置,針對若干具有代表性的作者、譯者、學者所進行的訪談。另一種多樣性則在發生的場景。先前兩本訪談集幾乎全為一對一的訪談,本書的訪談雖然大多如此,但也有幾篇的情形比較特殊,比如與王文興老師有關文學與宗教的一篇訪談涉及當時拍攝中的《尋找背海的人》(「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大師系列電影之一),因此有林靖傑導演參與;王老師與我在紀州庵的對談,由於主持人柯慶明教授的參與,形成三人鼎談,加上與現場觀眾問答,更成為多方對話;哈金的訪談是為了美國在台協會當時籌畫中的「華裔移民對美國貢獻特展」(“Immigrants Building America”),於台北美國文化中心進行,現場並有錄影,錄影的片段後來於特展中播放;齊老師有關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的訪談,則是對台灣的外文學門建制史有興趣的我和王智明博士合訪。訪談的地點以台北居多(五次),其他包括了桃園(兩次)、新竹、高雄、香港與夏威夷。凡此種種都增加了訪談的複雜性,也呈現了更豐富多元的面貌。
十一次訪談中,以紀州庵那次最為複雜,對談之前半小時現場便已坐滿觀眾,由柯慶明教授主持,王老師事前表示希望我的發言能跟他一樣長,而我深知他是主角,絕不能喧賓奪主,但又不便違背師命。再加上三人發言長短不一,時間上也有限制(兩小時),又要現場問答……因為變數甚多,只能自己先充分準備,再隨機應變,以達到實問實答的效果,甚至引出一些獨特的回答(如多倍速網路時代的閱讀與書寫,《巴黎茶花女遺事》的譯者)。幸好不負眾望,現場氣氛熱烈,訪談稿並受到《慢讀王文興》叢書編者之一、加拿大卡加利大學(University of Calgary)黃恕寧教授高度肯定。
若干受訪者,如王文興、林永得、哈金,已出現於前兩本訪談集中,有些則在本書中出現兩次(齊老師)、甚至三次(王老師)。然而這些再訪非但不令人覺得重複,反而更凸顯了受訪者多元的面貌與豐饒的內心世界,見證了他們的發展以及在時光中留下的軌跡,也反映了我個人身為學者、訪談者及芸芸眾生之一的關切、發展以及變與不變之處。
此書另一個特色就是圖片很多,其中有些是訪談現場拍攝的照片,有些是訪談前後蒐集的資料以及網路上的資料,標明資料來源、攝影者與提供者,旨在為訪談提供佐證,讓文字文本與圖像文本彼此參照、相得益彰。在此感謝出版社不惜成本主動將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圖片特別處理,以提昇視覺效果。
此書雖不是學術論文集,但絕非研究「之餘」的副產品,而是與之同步進行的成果,具有其獨立的價值,若干資料且引用於筆者的論文中。準備這些訪談所花費的時間、精神、編輯作業不見得較論文少,反而因為涉及受訪者,在連絡與後續作業上花了更多的工夫,在此感謝受訪者的合作與用心,如余老師連一個英文字母都不錯過,王老師、齊老師、劉教授、周教授等人仔細校訂,哈金先生在百忙中迅速回傳校稿,林永得先生修訂英文錄音謄稿並兩度親赴華人墓園拍照,這些由所附的圖片可見一斑。
本書雖未編製索引,但彼此之間時有關聯:如從周教授的訪談中得知余老師在台師大英語研究所教過他翻譯,當時用的方法包括口譯王爾德(Oscar Wilde)的喜劇,由此可知余老師對王爾德垂青已久,經多年準備,終於將他的喜劇全部譯成中文;從劉教授的訪談中得知朱立民老師教他翻譯時是口譯米勒(Arthur Miller)的劇本;又如王老師、劉教授和李教授當初都是《現代文學》的創刊成員,劉教授撰寫發刊詞,選擇介紹的作家多出自王老師的主意,李教授至今依然非常推崇《現代文學》第一期的封面作家卡夫卡(Frantz Kafka)。因此,本書以腳註提示彼此之間的關聯,並提供相關資料,供讀者參考。
交出書稿後,我前往美國加州,在舊金山和洛杉磯進行短期研究與訪談。時差尚未調整過來的我在成立於柏克萊近半世紀的天馬書店(Pegasus)看到夏季號的《巴黎評論》,赫然發現悼念創刊者之一麥西森(Peter Matthiessen, 1927-2014)的短文。今年四月甫去世的他是小說家,也是禪修者,一九五三年在巴黎籌畫此刊物時,另一位創刊者普林頓(George Plimpton)為了省錢並打響招牌,想出作家訪談的點子,訪問了於英國劍橋大學認識的小說家佛斯特(E. M. Forster),果然一鳴驚人。主訪者事先的審慎準備以及事後受訪者的仔細修訂,使得《巴黎評論》的訪談長久以來成為全世界文藝訪談的標竿。最近一期距離這份季刊創刊已有六十一年,名為「小說之藝術」(The Art of Fiction)的訪談已是第兩百二十三篇,名為「詩歌之藝術」(The Art of Poetry)的訪談則是第九十八篇。一九六七年,文學批評家卡靜(Alfred Kazin)在為自己編輯的第三冊《作家訪談集》(New York: Viking, 1967〕)的緒論中,稱讚其為「晚近有關傳記藝術的最佳例證」、「當代作家的最佳側影」(vii, ix)。一九九五年,名編輯貝拉彌(Joe David Bellamy)於《文學奢華:千禧年末的美國寫作》(Literary Luxuries: American Writing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一書中稱許其為「世界史上單一最持久的文化對話行為」(213)。二○一○年,加納(Dwight Garner)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上也有如下的讚許:「在我們的文學宇宙中,《巴黎評論》的訪談是談話的經典,長久以來樹立了紙上精釀的對話的標準」(十月二十二日)。由這些橫跨數十年的讚美之詞,可知《巴黎評論》及其訪談在世界文壇的重要性,稱其為一「建制」當不為過。
我個人以其為標竿,三十年樂此不疲從事訪談,前後三本訪談集總計收錄三十八篇中文訪談,若干也曾發表於英文期刊,採用一問一答的形式,並經受訪者修訂,旨在兼顧現場感與正確性,減少主訪者的主觀介入。這些訪談固然有其客觀與學術的面向,但絕不只是「為研究而研究」或象牙塔內的產物,而是來自特定的時空、脈絡與關懷,借用曾三度訪談的薩依德(Edward W. Said)的用語,具有一定的「現世性」(worldliness),希望華文世界的讀者能找到相應或啟發之處。
本書出版首先要感謝多位受訪者的熱心與耐心,接受邀請,坦誠回應,悉心修訂。其次要感謝刊登與轉載這些訪談的期刊與專書的相關人士,尤其是《印刻文學生活誌》的初安民先生和周昭翡女士,《思想》的錢永祥先生,《文訊》的封德屏女士,《編譯論叢》的李奭學先生、張淑英女士和張嘉倩女士,《英美文學評論》的黃心雅女士,《人生雜誌》的邱惠敏女士,馬來西亞《蕉風》的許通元先生,香港《現代中文文學學報》的黃淑嫻女士和宋子江先生,汕頭《華文文學》的莊園女士,以及主編《管見之外:影像文化與文學研究——周英雄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的李有成先生和馮品佳女士,主編《偶開天眼覷紅塵:王文興傳記訪談集》的黃恕寧女士。也要感謝熱心提供照片的《文訊》、九歌文化與台大出版中心等。感謝楊啟巽先生繼《越界與創新:亞美文學與文化研究》與《與智者為伍》之後,再度為我的書設計封面,增色許多。
這些訪談錄音大都由黃碧儀小姐謄打,除了李歐梵教授的訪談未曾刊登之外,其他在刊登前都經受訪者修訂,由我和黃碧儀小姐、陳雪美小姐校對,補充資料。書稿交出前由我和黃小姐數度修訂,補充照片與圖片,撰寫圖說,有些原本沒有小標題的訪談也增加了小標,以利讀者閱讀,部分圖片承蒙楊厚嘉小姐協助處理,在此一併致謝。全書經多次校對,務期以最佳面貌呈現給華文世界的讀者。若有不盡理想之處,純為我個人之失。
最後要感謝允晨文化廖志峰發行人繼《與智者為伍》之後,再度出版《卻顧所來徑》,並列入「當代名家系列」,讓這些名家分享他們的多年經驗與寶貴心得,藉以接通學院與社會。雖然文學式微之說傳聞已久,但我深信「有人即有文」、「有文學即有人文」,而身為「學者」的我就是「終身學習者」,藉由訪談自我精進,並成為連結受訪者與讀者的重要橋樑,希望彼此各獲其益。
再次感謝受訪者與編輯,讓我能以中間人/中介者的角色出現,以訪談結緣。其實,訪談就是扣問與迴響,大扣則大鳴,小扣則小鳴,進而引發讀者的不同迴響,期盼能聲聲相連,緣緣相續,引發更多的扣問與迴響。至於因篇幅之限未能收入的訪談,以及這次赴美進行的訪談,希望未來能有適當機緣繼續與讀者分享。
沉甸甸的書稿交出時,我笑說:「明天要睡到自然醒。」
這本書集結了我近年來有緣訪談的華人世界代表性作者、譯者與學者的文字紀錄與圖片,文稿一改再改,圖片一增再增,終能在出國研究前六天,溽暑的七月下旬車水馬龍的南京東路一棟辦公大廈的六樓,交出這份逾二十二萬字、百張圖片的訪談稿,放下心中一塊巨石。
果然一夜好眠。
第二天早上醒來,內室還是一片黑暗,就著手錶的微光端詳,竟然不到五點,比平常還要提早不少。既然已經醒來,便趁著涼爽的清晨出外。記不得有多久沒這麼早出門散步了。沿著四分溪走在中央研究院裡,清晨的頭腦特別靈活,不禁想到任職中研院已超過三十一個年頭,在這一萬一千多個日子裡,除非出門在外,否則幾乎天天走路上班,這種生活已超過了半輩子,成為我全部的學術生涯,不禁感到「此身雖在,堪驚」。
不知不覺路過任職的歐美研究所(我初到時是「美國文化研究所」,一九九一年易名),來到民族學研究所旁的側門,穿過研究院路,就是胡適公園。我大約每週路過此地一次訪人。原先的小徑這幾星期在整修,平時不見有人工作,卻依然拉上黃布條。繞道的小徑經過胡適墓園和銅像,即使未曾駐足,每次依然對這位五四健將、中研院前院長油然生出緬懷之心。今晨無事,就在此流連片刻,遙想昔日風光,反思自己的研究生活:從不知中研院為何物,至今已成為資深研究人員,過著外人眼中逍遙、光鮮的自由生活,卻不知何為「朝九晚五」、「週休二日」,總是一篇論文接著另一篇論文,一個研究計畫接著另一個研究計畫,過著「債台高築」的日子,似乎永遠沒有償清的一天。年年月月就在學術之路尋尋覓覓中度過──難道研究(“research”)就是永無止境的尋覓再尋覓(“re-search”)?
於是一篇篇的論文和一本本的專書、譯作就成了尋覓過程中的雪泥鴻爪,記錄了自己思索與努力的階段性成果,集中於對人性的探索、對文學的喜好以及對人文的尊崇,而這些俱是人之所以為人,人類之所以有今日的文明與文化的核心因素。年屆耳順的我,益發感到時不我予,如何利用日漸短少消逝的時光與體力,將所見所聞所思所學記錄下來,與有緣者對話交流、切磋砥礪,成了當務之急。
《卻顧所來徑──當代名家訪談錄》是我繼《對話與交流:當代中外作家、批評家訪談錄》(台北:麥田,2001)與《與智者為伍:亞美文學與文化名家訪談錄》(台北:允晨文化,2009)之後出版的第三本訪談集。尤記得就讀台大外文研究所碩士班時,初次讀到《巴黎評論》(Paris Review)的訪談,甚受感動與啟發,不忍獨享,於是從數冊《作家訪談集》(Writers at Work)中精選、翻譯了十幾位英美名作家,包括數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翻譯時的細讀深思、字斟句酌使得《巴黎評論》的訪談標準深入我心,成為後來自己從事訪談時根深柢固的習性,算來也已超過三十年。
在《對話與交流》的〈緒論〉中,我根據中外資料與親身經驗,闡明了訪談這個文類(genre)或次文類(sub-genre)的特色與錯綜複雜,並強調其中涉及的美學、政治、倫理:亦即,訪談的文字、修辭與結構的整理、講究與安排,主訪者與受訪者之間微妙的互動與權力關係,以及主訪者對受訪者與讀者所獨具的再現的權力/權利與義務。在《與智者為伍》的序言中,我也指出與學有專精、充滿智慧與行動力的作家與知識分子交流、問學的樂趣與收穫。文中並以土耳其作家帕慕克(Orhan Pamuk)為例,指出《巴黎評論》一篇與美國作家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的訪談,在當時年方二十五、懷抱作家夢的異地青年心目中有如「一個神聖的文本」,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堅定了他寫作的信心,竟於三十年後同樣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並為《巴黎評論訪談錄,第二輯》(The Paris Review Interviews, II)撰寫序言,顯示了文字因緣的不可思議。
這些訪談與我個人的專業領域息息相關,很大程度反映了我個人的學術興趣與生命關懷。而在人生路程能與這些傑出的中外作家、學者、批評家相逢,建立文字因緣,留下白紙黑字的紀錄,對於個性內斂的我來說,也是難能可貴的事。因此,我在《與智者為伍》的序言結尾期許:「身為代言人、再現者的訪談者,在為自己求知、解惑的同時,也可藉由訪談錄將個人的關懷與受訪者的回答公諸於世,分享他人,縱使未必知道這些訪談的效應如何,但或許某時某地某個有緣人能像帕慕克一樣,在其中得到安慰、鼓勵與指引。」
相較於前兩本訪談集,本書的十一篇訪談集中於我國與華裔人士,都是我佩服的前輩師長與作家──余光中教授與王文興教授更分別是我在政大西語系與台大外文所的老師,以及文學、翻譯、訪談方面的啟蒙師。全書依主題分為創作篇、翻譯篇與學術篇。創作篇的篇數最多(五篇),幾佔一半,是在不同的時空因緣下訪談的三位作家──王文興(三篇)、哈金(Ha Jin)與林永得(Wing Tek Lum)各一篇──針對彼此關切的議題進行訪問。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八三年我為了第一篇國際會議論文,首次進行訪談,對象就是王老師,當時兩人都稱許《巴黎評論》的高規格訪談,而那篇仔細修訂的訪談逾三萬字,後來成為王文興研究的代表性文獻之一。將近三十年後再度因為不同的機緣向王老師請益,尤其是討論一般文學研究中較少觸及的宗教、靈修與終極關懷,再度令我大開眼界,也是師生之間難得的跨宗教對話(王老師是天主教徒,我是佛教徒)。至於第三代華裔夏威夷詩人林永得與第一代華美作家哈金都是我多年研究的對象,佩服他們透過寫作所表達的人道關懷。一九九七年與林永得的當面訪談收錄於《對話與交流》,二○○八年與哈金的書面訪談收錄於《與智者為伍》,之後一路追蹤他們的文學創作:林永得自一九九七年閱讀了華美作家張純如的《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之後,多年以詩作表達對於南京大屠殺的關切以及對戰爭的反思;哈金於《自由生活》(A Free Life)中展現了流亡美國、過自由生活的同時,在異域他鄉以非母語寫作的艱辛與挑戰、堅持與成果,於《南京安魂曲》(Nanjing Requiem)中頌讚美國傳教士、教育家魏特琳(Minnie Vautrin)在南京淪陷後保護南京婦孺的崇高義舉,譴責日本侵華戰爭的罪行。
翻譯篇為本書的特色,因為前兩本訪談集雖然偶爾觸及文學與文化翻譯,卻未專門針對翻譯這個重要議題進行訪談,而本書所訪談的三位華文世界的前輩學者──余光中老師、齊邦媛教授和劉紹銘教授──數十年推動翻譯不遺餘力,受到國內外學界、翻譯界、文化界普遍肯定,但在他們的多重角色與貢獻中,攸關文學與文化交流的翻譯卻不見深入的訪談。余老師自中學起便翻譯不輟,自稱詩歌、散文、評論、翻譯是他「寫作生命的四度空間」,與詩作相互影響,也曾將詩作自譯成英文,但翻譯卻成為他的文學世界中最被忽略的領域。齊老師自抗戰時代起便閱讀翻譯作品,任職國立編譯館時大力推動台灣文學外譯與外國經典中譯,多年擔任《中華民國筆會》總編輯,後來又與王德威教授為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合編「台灣現代華語文學」(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系列,是台灣文學向國際進軍的重要推手,數十年如一日。劉教授多年來以英文編譯中國古典文學、現代文學與台灣文學,成為美國大學的教科書,一九七○、八○年代分別以中文譯介猶太裔與華裔美國文學,開華文世界風氣之先。他們的翻譯成果都為文學界提供了重要的養分,促進文化交流,卻未得到應有的評價與重視。為了彌補這個缺憾,矯正華文世界與學界對翻譯的忽視與偏見,我特地針對這個議題向三位翻譯界與文學界的前輩進行訪談,請他們分享多年從事翻譯、推動翻譯以及評論翻譯的經驗與心得,為華文翻譯界留下難得的史料。
學術篇則與我關切的學術建制史(institutional history)有關,訪談的三位都是華文世界的知名學者──齊老師、李歐梵教授與周英雄教授。三人背景的異同正可發揮相輔相成之效。齊老師出生於中國東北遼寧省,於抗戰時期接受文學教育,受朱光潛先生啟發尤深,此訪談是繼先前為其回憶錄《巨流河》(台北:天下文化,2009)的口述底稿而做。她是光復後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第一位助教,創立國立中興大學外文系,為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的十二位發起人之一,參與並見證了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在台灣的推動與發展。李教授出生於中國河南省,於台灣長大,在訪談中他別出心裁地將自己視為文本加以解讀,有關新竹中學的敘述讓人緬懷辛志平校長的教育理念與深遠影響,保送進入台大外文系之後與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歐陽子等人同班,共同打造了《現代文學》的傳奇,赴美留學時所遭逢的名家與際遇,出入於文學、歷史與理論之間,對於美國與兩岸三地學界的觀察……在在令人回味。周教授則出生於台灣雲林虎尾,在訪談中敘述了就讀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與研究所時的情形,先後負笈夏威夷與加州,學成後赴香港任教多年,又返回台灣在不同的學術行政職位與民間學會推動台灣外文學門的研究與發展。由這三位的出身背景、求學過程、學術發展、經歷與貢獻,多少可以勾勒出台灣的外文學門,尤其是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的軌跡與特色,為台灣的學術建制史留下珍貴的經驗與紀錄。
由上述可知,本書涉及創作、翻譯、學術建制等不同面向,有其多元性,基本上是一位台灣學者在不同的機緣下,從其知識立場與發言位置,針對若干具有代表性的作者、譯者、學者所進行的訪談。另一種多樣性則在發生的場景。先前兩本訪談集幾乎全為一對一的訪談,本書的訪談雖然大多如此,但也有幾篇的情形比較特殊,比如與王文興老師有關文學與宗教的一篇訪談涉及當時拍攝中的《尋找背海的人》(「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大師系列電影之一),因此有林靖傑導演參與;王老師與我在紀州庵的對談,由於主持人柯慶明教授的參與,形成三人鼎談,加上與現場觀眾問答,更成為多方對話;哈金的訪談是為了美國在台協會當時籌畫中的「華裔移民對美國貢獻特展」(“Immigrants Building America”),於台北美國文化中心進行,現場並有錄影,錄影的片段後來於特展中播放;齊老師有關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的訪談,則是對台灣的外文學門建制史有興趣的我和王智明博士合訪。訪談的地點以台北居多(五次),其他包括了桃園(兩次)、新竹、高雄、香港與夏威夷。凡此種種都增加了訪談的複雜性,也呈現了更豐富多元的面貌。
十一次訪談中,以紀州庵那次最為複雜,對談之前半小時現場便已坐滿觀眾,由柯慶明教授主持,王老師事前表示希望我的發言能跟他一樣長,而我深知他是主角,絕不能喧賓奪主,但又不便違背師命。再加上三人發言長短不一,時間上也有限制(兩小時),又要現場問答……因為變數甚多,只能自己先充分準備,再隨機應變,以達到實問實答的效果,甚至引出一些獨特的回答(如多倍速網路時代的閱讀與書寫,《巴黎茶花女遺事》的譯者)。幸好不負眾望,現場氣氛熱烈,訪談稿並受到《慢讀王文興》叢書編者之一、加拿大卡加利大學(University of Calgary)黃恕寧教授高度肯定。
若干受訪者,如王文興、林永得、哈金,已出現於前兩本訪談集中,有些則在本書中出現兩次(齊老師)、甚至三次(王老師)。然而這些再訪非但不令人覺得重複,反而更凸顯了受訪者多元的面貌與豐饒的內心世界,見證了他們的發展以及在時光中留下的軌跡,也反映了我個人身為學者、訪談者及芸芸眾生之一的關切、發展以及變與不變之處。
此書另一個特色就是圖片很多,其中有些是訪談現場拍攝的照片,有些是訪談前後蒐集的資料以及網路上的資料,標明資料來源、攝影者與提供者,旨在為訪談提供佐證,讓文字文本與圖像文本彼此參照、相得益彰。在此感謝出版社不惜成本主動將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圖片特別處理,以提昇視覺效果。
此書雖不是學術論文集,但絕非研究「之餘」的副產品,而是與之同步進行的成果,具有其獨立的價值,若干資料且引用於筆者的論文中。準備這些訪談所花費的時間、精神、編輯作業不見得較論文少,反而因為涉及受訪者,在連絡與後續作業上花了更多的工夫,在此感謝受訪者的合作與用心,如余老師連一個英文字母都不錯過,王老師、齊老師、劉教授、周教授等人仔細校訂,哈金先生在百忙中迅速回傳校稿,林永得先生修訂英文錄音謄稿並兩度親赴華人墓園拍照,這些由所附的圖片可見一斑。
本書雖未編製索引,但彼此之間時有關聯:如從周教授的訪談中得知余老師在台師大英語研究所教過他翻譯,當時用的方法包括口譯王爾德(Oscar Wilde)的喜劇,由此可知余老師對王爾德垂青已久,經多年準備,終於將他的喜劇全部譯成中文;從劉教授的訪談中得知朱立民老師教他翻譯時是口譯米勒(Arthur Miller)的劇本;又如王老師、劉教授和李教授當初都是《現代文學》的創刊成員,劉教授撰寫發刊詞,選擇介紹的作家多出自王老師的主意,李教授至今依然非常推崇《現代文學》第一期的封面作家卡夫卡(Frantz Kafka)。因此,本書以腳註提示彼此之間的關聯,並提供相關資料,供讀者參考。
交出書稿後,我前往美國加州,在舊金山和洛杉磯進行短期研究與訪談。時差尚未調整過來的我在成立於柏克萊近半世紀的天馬書店(Pegasus)看到夏季號的《巴黎評論》,赫然發現悼念創刊者之一麥西森(Peter Matthiessen, 1927-2014)的短文。今年四月甫去世的他是小說家,也是禪修者,一九五三年在巴黎籌畫此刊物時,另一位創刊者普林頓(George Plimpton)為了省錢並打響招牌,想出作家訪談的點子,訪問了於英國劍橋大學認識的小說家佛斯特(E. M. Forster),果然一鳴驚人。主訪者事先的審慎準備以及事後受訪者的仔細修訂,使得《巴黎評論》的訪談長久以來成為全世界文藝訪談的標竿。最近一期距離這份季刊創刊已有六十一年,名為「小說之藝術」(The Art of Fiction)的訪談已是第兩百二十三篇,名為「詩歌之藝術」(The Art of Poetry)的訪談則是第九十八篇。一九六七年,文學批評家卡靜(Alfred Kazin)在為自己編輯的第三冊《作家訪談集》(New York: Viking, 1967〕)的緒論中,稱讚其為「晚近有關傳記藝術的最佳例證」、「當代作家的最佳側影」(vii, ix)。一九九五年,名編輯貝拉彌(Joe David Bellamy)於《文學奢華:千禧年末的美國寫作》(Literary Luxuries: American Writing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一書中稱許其為「世界史上單一最持久的文化對話行為」(213)。二○一○年,加納(Dwight Garner)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上也有如下的讚許:「在我們的文學宇宙中,《巴黎評論》的訪談是談話的經典,長久以來樹立了紙上精釀的對話的標準」(十月二十二日)。由這些橫跨數十年的讚美之詞,可知《巴黎評論》及其訪談在世界文壇的重要性,稱其為一「建制」當不為過。
我個人以其為標竿,三十年樂此不疲從事訪談,前後三本訪談集總計收錄三十八篇中文訪談,若干也曾發表於英文期刊,採用一問一答的形式,並經受訪者修訂,旨在兼顧現場感與正確性,減少主訪者的主觀介入。這些訪談固然有其客觀與學術的面向,但絕不只是「為研究而研究」或象牙塔內的產物,而是來自特定的時空、脈絡與關懷,借用曾三度訪談的薩依德(Edward W. Said)的用語,具有一定的「現世性」(worldliness),希望華文世界的讀者能找到相應或啟發之處。
本書出版首先要感謝多位受訪者的熱心與耐心,接受邀請,坦誠回應,悉心修訂。其次要感謝刊登與轉載這些訪談的期刊與專書的相關人士,尤其是《印刻文學生活誌》的初安民先生和周昭翡女士,《思想》的錢永祥先生,《文訊》的封德屏女士,《編譯論叢》的李奭學先生、張淑英女士和張嘉倩女士,《英美文學評論》的黃心雅女士,《人生雜誌》的邱惠敏女士,馬來西亞《蕉風》的許通元先生,香港《現代中文文學學報》的黃淑嫻女士和宋子江先生,汕頭《華文文學》的莊園女士,以及主編《管見之外:影像文化與文學研究——周英雄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的李有成先生和馮品佳女士,主編《偶開天眼覷紅塵:王文興傳記訪談集》的黃恕寧女士。也要感謝熱心提供照片的《文訊》、九歌文化與台大出版中心等。感謝楊啟巽先生繼《越界與創新:亞美文學與文化研究》與《與智者為伍》之後,再度為我的書設計封面,增色許多。
這些訪談錄音大都由黃碧儀小姐謄打,除了李歐梵教授的訪談未曾刊登之外,其他在刊登前都經受訪者修訂,由我和黃碧儀小姐、陳雪美小姐校對,補充資料。書稿交出前由我和黃小姐數度修訂,補充照片與圖片,撰寫圖說,有些原本沒有小標題的訪談也增加了小標,以利讀者閱讀,部分圖片承蒙楊厚嘉小姐協助處理,在此一併致謝。全書經多次校對,務期以最佳面貌呈現給華文世界的讀者。若有不盡理想之處,純為我個人之失。
最後要感謝允晨文化廖志峰發行人繼《與智者為伍》之後,再度出版《卻顧所來徑》,並列入「當代名家系列」,讓這些名家分享他們的多年經驗與寶貴心得,藉以接通學院與社會。雖然文學式微之說傳聞已久,但我深信「有人即有文」、「有文學即有人文」,而身為「學者」的我就是「終身學習者」,藉由訪談自我精進,並成為連結受訪者與讀者的重要橋樑,希望彼此各獲其益。
再次感謝受訪者與編輯,讓我能以中間人/中介者的角色出現,以訪談結緣。其實,訪談就是扣問與迴響,大扣則大鳴,小扣則小鳴,進而引發讀者的不同迴響,期盼能聲聲相連,緣緣相續,引發更多的扣問與迴響。至於因篇幅之限未能收入的訪談,以及這次赴美進行的訪談,希望未來能有適當機緣繼續與讀者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