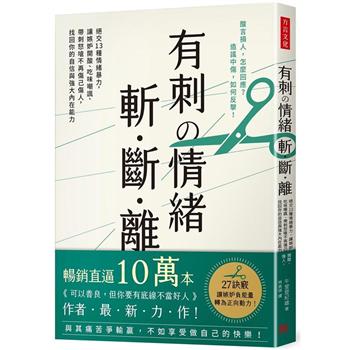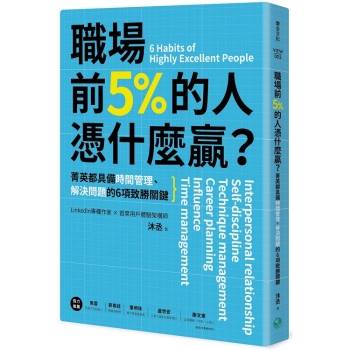2012年德國書業和平獎得主廖亦武,驚動世界文壇的代表鉅著
令人驚艷……在娓娓道來的細節中……作者以迷人的洞察力,引領我們進入形形色色販夫走卒的生活中……一本令人著迷的著作。——《圖書論壇》
閱讀《吆屍人》有如與作者結伴同行:雖然我們的雙腳並未起水泡,身體也未挨餓,最後我們還是感到震撼與激動不已。——《舊金山記事報》
我們對現代中國有了一個全面而嶄新的理解……一本徹底顛覆的書……廖亦武敘述的故事,都具有某些怪誕、奇幻及夢魘般的共同特質……以精煉的語句與對話,盡一個作家之所能,去填補構成中國現代藝術與社會記錄的大片空缺……強而有力。——《國家》
欲罷不能且深具啟發的閱讀……廖亦武是一位天生的訪談者;他感同身受的傾聽與極富技巧的提問,使得這本書的訪談,成為對不可預知之人生的重要啟示。——《芝加哥論壇報》
迷人的……欲罷不能的……勇敢的作品……這是為了確保近代中國史可怕的陰暗面,不致在經歷過後卻未曾留下紀錄,所做的崇高努力。——《紐約太陽報》
這二十七位受訪者,每一個……都有其自身的吸引力。——《芝加哥太陽時報》
一部中國百姓口述歷史的耀眼合輯……對毛澤東時代以及今日中國由高壓的共產黨員與資本家混和統治下的五十年,所做的殘酷觀照……廖亦武創造了一個令人難忘、毛骨悚然,卻又時而帶著詼諧的現代中國圖像。——《丹佛郵報》
令人看得入迷……恐怖、有趣並讓人不忍釋卷,一部橫跨這個國家最底層的各行各業的訪談合輯。——《新政治家》
廖亦武的風格是不假修飾,而黃文的編輯、翻譯與導讀,則令其資料為之增色。結果成就了這一套真人實事而且引人入勝的故事。——《標準周刊》
非常特別的口述歷史,為我們開啟了一扇窗,不像其他訪談錄,而是將重點擺在平常人的生活,通常是中國的社會邊緣人,男人與女人……作者藉由懷著敬意與同情提出一些挑戰性的問題,順利讓其訪談對象敞開心房談論他們的生活。——《亞洲期刊》
有一天晌午,剛下過雨,天氣陰沉,我才從家門出來,忽然有體積很龐大的東西從眼皮下一晃就過去了。我不禁打個冷顫,就好奇地跟上。我終於看清楚濺滿泥漿的黑袍子蕩起,有一雙落地很重的皮幫鞋,咚咚咚,沉得像夯土的木樁。
作者簡介:
廖亦武,1958年8月4日(農曆6月19日)生於四川省北部縣城鹽亭,1980年代,經常在中國官方文學雜誌上發表現代詩歌。但多數具有西方創作風格的反叛性前衛作品,曾多次在「反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等政治運動中,受到嚴厲批判。1986年至1989年,他相繼發表了《死城》、《黃城》、《幻城》、《偶像》等長詩。
1989年3月開始,中國幾十個城市爆發街頭抗議,隨後的6月3日下午,在天安門廣場集體悲劇徵兆頻頻顯示之際,他寫下《大屠殺》這首詩。6月4日凌晨,在天安門大屠殺進行之際,同步朗讀了這首詩,並與加拿大公民戴邁河一起,製作並複製成錄音帶,傳遍了全國許多城市。這是當時的血腥鎮壓和瘋狂搜捕中,唯一來自於文學的公開反抗。
1990年3月初,廖亦武組織劇組,籌備並拍攝了《大屠殺》的姐妹篇,詩歌電影《安魂》。3月16日清晨,《安魂》劇組,大約10人左右,在重慶被國家安全局抓捕。隨後,在全國,警察抓捕了幾十個詩人和作家,都是《大屠殺》詩歌的傳播者。其中包括他已懷有身孕的妻子。後來他被判定為「政治犯」,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的罪名,坐牢4年,輾轉了四個監獄,自殺兩次。由於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於1994年1月31日,提前43天出獄。為了謀生,他成為各地酒吧及茶館的賣藝人,他在監獄學會的洞簫演奏派上了用場。1999年初夏,出版《沉淪的聖殿——中國1970年代的地下詩歌故事》和《中國邊緣人採訪錄》,立即成為暢銷書,隨即,新聞出版局宣布是「反動書籍」。警察甚至查抄了印刷廠。2001年初春,他化名「老威」,出版了 《中國底層訪談錄》的60人刪節本,讓「不見天日的下水道裡的中國」浮出地面,激起軒然大波。出版社遭到整肅,高調讚揚過他的週刊《南方周末》遭到更嚴厲的打壓,主編和許多編輯被撤職。廖亦武從此被嚴禁在自己的祖國發表任何作品。《中國底層訪談錄》後來2003年在臺灣出版了繁體字的三卷全本。
廖亦武曾16次被阻止出境,終於在2010年9月,首度被允許出境,到柏林參加柏林國際文學節。而在2011年2月至5月,在多次要求出境不被允許的狀況下,終於在7月2日走過中越邊境,5日自越南河內登機,6日清晨飛抵德國,就此留在德國。
2008年,在美國出版《吆屍人》,讓他在西方一夜成名,此書的波蘭文版也於2012年獲得卡普欽斯基國際報導文學獎。其它獲獎紀錄有:1995年和2003年度,由美國世界人權觀察頒發的「赫爾曼-哈米特人權寫作獎」;2002年,由美國《傾向》雜誌頒發的「傾向文學獎」;2007年,由獨立中文筆會頒發的「自由寫作奬」;2009年,由澳洲齊氏基金會頒發的「推動中國進步獎」;2011年,由美國《當代基督教》雜誌頒發的「最佳圖書奬」;2011年,由德國圖書行業協會頒發的「紹爾兄妹獎」;2011年,由德國廣播協會頒發的「最佳廣播劇奬」;2012年獲德國書業和平獎;2013年,由德國阿沙芬堡頒發的「公民勇氣奬」;2013年,由法國政府頒發的「法蘭西文學藝術軍官獎章」。
2013年1月和6月,他的監獄自傳《六四‧我的證詞》法文版和英文版相繼問世。10月,在臺灣和德國同步出版《洞洞舞女和川菜廚子》。
廖亦武 得獎紀錄
1995年 美國赫爾曼-哈米特寫作獎
2002年 美國《傾向》文學獎
2003年 美國赫爾曼-哈米特寫作獎
2007年 獨立中文筆會之自由寫作獎
2009年 《地震瘋人院:四川大地震記事》獲澳洲之推動中國進步獎
2011年 美國《當代基督教》雜誌「最佳圖書奬」
2011年 德國圖書行業協會「紹爾兄妹獎」
2011年 德國廣播協會「最佳廣播劇奬」
2012年《吆屍人》卡普欽斯基國際報導文學獎
2012年 德國書業和平獎
2013年 德國公民勇氣奬
2013年 法國法蘭西文學藝術軍官獎章
章節試閱
吆屍目擊者羅天王
採訪緣起
無論在中國南方還是北方,吆屍的傳聞一直都有,但往往是以訛傳訛,神祕得不著邊際。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曾在〈吹鼓手兼嚎喪者李長庚〉的文字末尾,虛實參半地描述過「三位一體」的吆屍情景,引起不少讀者的特別關注。
但此篇對話卻是具體的,時間為 2003 年 10 月 7 日晌午,我父親李德奎逝世一週年的忌辰。記得其時天氣晴朗,我、媽媽、妹妹、王魯、兩個姪女……總之,一大堆人,開了兩輛車回老家鹽亭縣境李家坪鄉下拜祭。默哀、燒香、放鞭炮都是免不了的,但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拜訪住在鄉場上的風水先生羅天王─他曾是我爺爺早年的朋友,父親下葬的時辰由他演算之後確定。他還一筆一劃寫了黃貼,慎重地交付我和妹妹。因為腿腳不靈便,父親隆重的入土儀式即由他的長孫主持。
「羅天王」是在方圓百里傳揚的民間綽號,暗示某種通靈的能力。他已九十歲出頭了,卻眼不花,氣不是太喘,顯得非常祥和。我至今感謝他花了幾個小時的精力跟我擺龍門陣,把一樁吆屍引起的冤案活生生地凸現出來。要知道,那已是五十多年前的事兒,若是一般人,記憶早被磨損得千瘡百孔了。
「羅天王」的確名不虛傳。
正文
老 威:這吆(四川方言,意為吆喝,借聲勢驅趕。)死人的傳聞,我打小就聽說過。文化大革命爆發,爸爸成了牛鬼蛇神被關進學習班;媽媽自身難保,避禍回成都,有一段時期,我和妹妹就流落到這李家坪鄉下。我爺爺您曉得不,那個窮得蝨子成團的老地主?
羅天王:你爺爺李樹凡嘛,我們是老相識,在舊社會,他可是個勤勞致富的老好人,已做上保長了,還保持著泥腿子的本色,與長工一道耙冬水田。有一次牛太累了,在田裡強著不走,他也攔住不准長工鞭打,而是自己扒個光脊梁,去代牛拉犁。可一九四九年一解放,他就慘了,磚頭豎著放,讓他站上面挨鬥,不知摔了多少跟頭,老骨頭都散架了……
老 威:我曉得,一直到一九八○年代初淡化階級成分之前,我爺爺都沒好日子過。那破四合院,拆去兩面屋,剩下的兩面風雨飄搖……爺爺已去世多年,可我還夢見過他,腰間繫牛鼻草繩,上唇掛清鼻涕,被生產隊民兵押去開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鬥爭會。那年月,給我幼小的心靈莫大安慰的,卻是隔著堂屋與爺爺比鄰而居的貧農王三婆。她養了很多貓,一到冬天,貓就鑽進被子和她一起睡。月明之夜,王三婆就坐在我家的祖墳頭下,邊搖蒲扇邊講鬼故事;還叫我和妹妹把篩子扣頭上,讓我們透過針孔大的篩子眼見識六一、二年的成群餓鬼。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吆死人。
羅天王:你說的是李王氏,那個五保戶孤寡老太,她吹牛呢。
老 威:她講得活靈活現。多年以後,我還把這種記憶寫進叫《死城》的詩裡了,什麼「我透過篩子目送趕屍人遠去,我燒完紙錢鑽出山崖」;什麼「趕屍的吆喝不絕於耳,我的髮根溢蕩著屍臭」之類。
羅天王:你說啥子?「趕屍人的吆喝」?誰聽見了?
老 威:小子賣弄了,還是聽您老人家講。
羅天王:我可不背詩,我說的是真事。吆屍這一行雖然在正當的七十二行以外,但據說從古至今就存在。我已九十歲了,早年在兵荒馬亂之中,跑過陝西和河南,那時販鹽的腳商,由於交通不便,一般都是六、七個青壯年同鄉結伴步行,遇上運氣好,也花幾個銅板搭上一截便車。蜀道太難了,沒有整段的跨省公路,有時汽車還沒腳板快呢。
從鹽亭經梓潼、劍閣、廣元到陝西南鄭的漢中地界,翻的幾乎是山路。在荒嶺野店之間,我們偶爾也乜見地攤上鋪開幾個大字:「包吆死人過界。」陰風刮起幾張紙錢,我們急忙掩面而過,心悸之餘,卻覺得懷疑:人死了就硬邦邦的,怎樣過界?又不是豬狗雞鴨,你吆喝幾聲就能跑起來?
老 威:「過界」是指陰陽界嗎?
羅天王:也指省界或縣界。舊社會,沒高速公路,所謂國道跟現在的鄉下機耕道差不多,泥濘難行。如果遊子外出,不幸身患重病,不治而亡,總得有人收屍。當時不興火葬,如果死者的福薄,經濟條件一般,就只能由同伴湊幾個錢,買一副棺材,草草葬於異地。
老 威:對,我的五舅在一九四○年代領著戲班出川,後來在江西鄱陽湖邊遭遇大難,五舅橫死,就葬於當地。
羅天王:中國傳統講究葉落歸根,死不能歸里入土,就叫孤魂野鬼。所以,有經濟能力的死者,都無一例外地遺囑兒孫,要不惜一切代價把自己弄回去!可咋個弄?沒車運沒人抬,而且路上耽擱的時間太久。
老 威:您親眼見過吆死人哪?
羅天王:見過,可那是一樁奇冤哪。
老 威:老人家您慢慢道來。
羅天王:一九五○年初吧,四川全境都解放了,鹽亭縣裡的工作組也下來了,開始清匪反霸、減租退押、土改劃階級成分。運動一個接一個,轟轟烈烈的,可我現在回想,卻覺得迷迷糊糊的。
總之,鄉下不安寧,大戶人家跑了許多,山溝裡躲城裡藏,有袍哥背景的就合夥上山。我家三代都看風水,成分就劃為「迷信職業者」。有一天晌午,剛下過雨,天氣陰沉,我才從家門出來,忽然有體積很龐大的東西從眼皮下一晃就過去了。我不禁打個冷戰,就好奇地跟上。我終於看清楚濺滿泥漿的黑袍子蕩起,有一雙落地很重的皮幫鞋,咚咚咚,沉得像夯土的木樁。這時,恰好有個和我一樣好奇的本村人攆上來,對我耳語:「吆死人囉。」
我起了一身雞皮疙瘩,更仔細地看,原來在黑袍子的前頭,還有個引路的,對襟短襖,紮著褲腿,特別精悍。此人左手挽個裝紙錢的籃子,右手提個白燈籠,斜斜地倒退著走。他每退走幾米,就向冥空揚揚手,一枚紙錢撒出去,竄過人的腦袋,而後旋下來─這叫黃泉買路,鄉下死人出殯都有這道手續。
老 威:白天還打燈籠?這也是製造氣氛吧?
羅天王:不是。所謂「死人」的黑袍子從頭罩到腳,並且比常人高出一頭……
老 威:怎麼會呢?裡頭有啥機關?
羅天王:黑袍子內的「死人」兩眼一抹黑,頂上還扣一頂大草帽,草帽下還吊了一張紙殼糊的臉,慘白慘白的,像川劇舞臺上遭冤枉的小生。你想,他的上半身猶如被捆著,只有兩條腿在挪動,在咚咚咚地往前打樁,那麼,他憑啥辨別方向?
老 威:憑燈籠發出的白光。
羅天王:對,從黑袍裡看出去,就是一團暗淡的光暈,再加上引路人嘴裡不斷發出「荷荷荷」的聲音,「死人」只要配合就行了。
老 威:這「死人」沒手臂麼?
羅天王:沒見手臂在行走時擺動。
老 威:那上坡下坡咋辦?
羅天王:「死人」全憑引路人的招呼,比如上坡就叫:「坡,坡!」有石梯就叫:「梯坎,梯坎!」得提前叫。「死人」略略停頓,而後如笨熊,端著架子,亦步亦趨地仰面「打樁」;如遇下陡坡,就大吼「穩起」,「死人」就事先減速,再一顛一顛地穩步下去。另外,拐彎、急彎,都要令行禁止,比兵營操練還嚴格。
老 威:我還以為吆屍是一種世代相傳的巫術呢,像港臺電影裡演的,一揭鎮屍符,那東西就直挺挺地蹦達,雙手還平伸著。
羅天王:我是風水先生,見過的死人還少麼,你就不要取笑了。
老 威:抱歉。不過聽您的講解,吆屍就沒一點神祕感了。
羅天王:這只有一種不見光的職業。那一次,我一直跟蹤到七、八里以外的馮河鄉,見他們穿過兩三米寬的街,拐進靠河邊的那家僻靜的客店。「死人」在臺階下候著,引路人先閃進門,撲到櫃檯前拍兩下巴掌,輕輕叫:「喜神歇店來!」
老 威:啥意思?
羅天王:這一行的切口。一叫「喜神」,店家大約就明白了,心下又驚又喜。雖然那草帽下的紙臉殼怪嚇人的,但可以不客氣地收三倍的房費。況且,「喜神」一進門,就再不露面了,其他客人也不曉得。
老 威:旅店又不是停屍房,店家就不怕沾上晦氣?
羅天王:你剛好弄反了,夢死得生嘛。傳統風俗:「喜神」一衝關,財運擋不住。
老 威:哦。
羅天王:店家笑嘻嘻地將他們領入最裡面的客房,把臉盆、馬桶都遞進去。我們湊攏看,見「死人」就直直地靠在門後,而引路人擱下燈籠和紙錢籃子,橫在門口,瞪了我一眼,喝道:「爬開些!」店家也板著臉附和:「走嘛,嘴巴加鎖,莫亂開腔哦。」
我們兩個看客自討沒趣,就退回來。店家從引路人手裡接過一塊舊銀元,心花怒放。他趴在櫃前邊吹邊拿在耳邊聽響,好一陣,才鎖進去,換些零票出來,並招呼我們陪他一道去街上置辦伙食。先買幾斤滷豬耳朵、豬拱嘴和油炸花生米;又在館子裡炒了四個葷菜,其中還包括一條兩斤多重的豆瓣魚;最後才採購了白蠟燭和冥錢,供明日上路用。
我們跟著瞎忙,店家過意不去,就留飯。他把夥計打發開去,三個人就邊酌點小酒邊擺龍門陣。由於「死人」給的店錢可觀,他喝酒也豎起耳朵,只要那頭有些微響動,他也顛顛地竄過去,問「有啥吩咐」,連耗子打架也不放過。
趁著酒興,店家漸漸把持不住,吹自己在二十多年中,打理過十來起「喜神」。我們故意不相信,他就急了,說:「死人一進房,就籠著黑袍子立在門背後,草帽也不揭,恐怖得緊。」我問:「死人自己真走路嗎?」他說:「傳說是死人走,其實是活人走。祕密就在袍子裡頭。」我說:「吆死人嘛,當然是活人吆,死人走。據說人家還帶著一隻黑貓,反覆讓貓在屍體上下跑幾遍,叫『過電』,然後死人就木偶一般開動,然後就用棍子和燈籠吆。」店家斥道:「一片胡言!」另一人介面:「既然你覺得是胡言,我們就一起去看看。」店家說:「人家的門頂得死死的,看個逑。」我說:「聽一耳朵嘛。」店家說:「那人有武功,當心你的耳朵被他割了下酒。實話告之,這行當最忌見光,一般住進去就不露面了,吃飯屙屎都在裡頭。明早三更天,又得上路。」
正說得熱鬧,一陣陰風卻嗖地刮進堂屋裡,店家縮了縮腦袋,罵夥計咋不點店前的燈籠,此時壁上的掛鐘鐺地響了一下,8 點半,門外已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店家呷口酒,又說:「你剛才說的黑貓啦過電啦都是封建迷信。」另一人譏笑道:「封建迷信都進店了,你還有臉批我們?」店家說:「吆死人是真的,反正已經是新社會,這營生看著做不久,我就索性把這謎底揭了:吆死人的活人是兩個,一個明處,你們都看見了,打燈籠拋紙錢和動嘴的;一在暗處,把死人背掛在自己身上,再鋪天蓋地罩黑袍。這樣,像移動門板,必須硬扳著腰,垂直著臂,握拳用力去撐起死人的重量。因為死人有個向下沉的特點,剛魂飛魄散,骨肉又溫有軟,還比較好弄;可漸漸就變僵變硬,接著越僵越硬越沉,猶如石頭,沒絲毫彈性。如果他活著時 100 多斤,一個人輕易抱得動,可死時的重量要增加許多,兩個人抬還費勁……
我插話說:「也許是心理因素,一口棺材還要八人抬呢。」
店家點頭說:「這還像人話。總之,黑袍裡面生死兩人都苦啊,從北邊的漢中、天水、寶雞,經劍閣、梓潼入鹽亭縣界,在鄉關路上多少起伏,掐指一算,走捷路也得近一個月!所以春夏季幹不了,死人要臭;從九九重陽到來年春節,吆屍正好。」
我驚訝道:「你咋這麼清楚?」
店家說:「我這客店已歷三代,我爺爺在光緒初年開業才三月,就接了一樁『喜神』,所以這行當從何朝何代開始的,誰也追不清爽。史書裡記載,堯舜禹的上古時代就有,你信不信?」
吆屍目擊者羅天王
採訪緣起
無論在中國南方還是北方,吆屍的傳聞一直都有,但往往是以訛傳訛,神祕得不著邊際。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曾在〈吹鼓手兼嚎喪者李長庚〉的文字末尾,虛實參半地描述過「三位一體」的吆屍情景,引起不少讀者的特別關注。
但此篇對話卻是具體的,時間為 2003 年 10 月 7 日晌午,我父親李德奎逝世一週年的忌辰。記得其時天氣晴朗,我、媽媽、妹妹、王魯、兩個姪女……總之,一大堆人,開了兩輛車回老家鹽亭縣境李家坪鄉下拜祭。默哀、燒香、放鞭炮都是免不了的,但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拜訪住在鄉場上的風水先...
推薦序
英文版導讀:一群中國社會邊緣人的心聲 ⊙黃文
當中國政府的坦克車在 1989 年 6 月 3 日夜晚開進北京市,並殘忍地鎮壓支持民主運動的學生時,廖亦武正在中國西南的四川省家中。這些新聞令他內心深受震撼。他連夜創作了一首題為《屠殺》的長詩,就像畢卡索生動地描繪納粹轟炸屠殺格爾尼卡(Guernica)鎮一般,他以寫實的意象忠實描述了無辜學生與市民被殺害的情況。
他的詩沒有任何機會在中國出版,於是他錄製了一卷自己朗讀的錄音帶,以中國式的狂嘯形式朗誦,向死者招魂。這卷錄音帶透過中國的地下管道而廣泛流通。他在那時創作的另一首詩裡,描述了他無法起而反抗的挫折感:
你生就一個刺客的靈魂,你本該做荊軻聶政,
但是當你茫然四顧、
鬚髮賁張的時候,
竟無劍可拔。
肉體,
這生鏽的刀鞘,
這哆嗦的手腳,
這骨縫裡的黴班,
這瞄不了槍的近視眼!
那卷《屠殺》的錄音帶以及他與朋友錄製的續篇,題為《安魂》的影片,引起了中國祕密警察的注意。1990 年 2 月,當他正要搭乘一班前往北京的列車,幾個警察突然向他突襲。他的詩人與作家朋友,以及他懷孕的妻子,一共六人也因為牽涉他的拍片計畫而同時被捕。身為主謀者,廖亦武獲判四年徒刑。
從那時起,廖亦武就被永久列入政府的黑名單中。他的大部分作品在中國依然被禁,他住在雲南省的一個小鎮,在公安局的監視下,當起街頭音樂家賣藝維生。他在過去幾年曾因為從事「非法訪談」,以及在他的資料性書籍《中國底層訪談錄》中,揭露共黨社會的黑暗面,因而多次被扣押。出現在這本書裡的二十七篇故事,便是從該本合輯以及最近他發表在海外中文網站的貼文翻譯並改編而成的。
廖亦武出生於 1958 年,是十二生肖的狗年。那一年也是毛澤東發起「大躍進」的年份,這場運動的目的是要讓中國落後的小農經濟開始工業化。強迫性的集體農業生產,以及全國盲目的動員去採用最原始的方法生產鋼鐵,導致 1960 年的大饑荒,造成三千多萬人喪生。
在大饑荒期間,他罹患饑餓性水腫而瀕臨死亡。脫離險境之後,他的母親帶他到鄉下,那裏有一個中醫師,抓著他懸在一口燒著滾燙藥草熱水的炒鍋上,藥草蒸騰的熱氣竟神奇的將他治好了。
1966 年,廖亦武的家庭深受打擊,因為他擔任老師的父親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貼上反革命的標籤。他的父母申請離婚,以保護他們的孩子擺脫父親黑五類的身分。沒有父親,日子過得很苦。在他童年的記憶當中,有一件事他依然印象深刻:「有個親戚給我母親一張政府發行的配給劵,那很有用,可以換一匹兩尺長的布。但是,當母親將它拿去黑市販賣,以便為我們購買食物時,卻被警察抓了,並命令她與其他罪犯站在四川歌劇院的舞台上,在數千群眾面前列隊示眾。有幾個同學在現場看見我的母親,當他們告訴我這件事後,我崩潰了。」
廖亦武高中畢業後,在國內四處旅行,當過廚師,接著當卡車司機專跑川藏公路。閒暇之餘,他讀一些以前被禁的西洋詩,從濟慈到波特萊爾。他也開始創作自己的詩,並在文學雜誌上發表。
在整個一九八○年代,他成為中國最受歡迎的新詩人之一,並定期於具有影響力的文學雜誌,以及專門刊登當代西方風格詩作而被政府認為是一種「精神汙染」的地下刊物投稿。1989 年春,兩家著名的雜誌利用政治暫時較寬鬆之際,刊載他的兩首長詩,〈黃色城市〉和〈偶像〉。在詩中,他用諷喻性的暗示,批判他所謂的被集體血友病所麻痺和侵蝕的制度。他宣稱毛澤東的竄起,便是此一不治之症的徵狀。詩中大膽的反共訊息驚動了警察到他家搜索,並以徹底的審問、逼供及短期拘留令他屈服。這兩家雜誌社的發行人也遭到懲處,其中一家還被下令關閉。
他因為譴責政府鎮壓民運學生,而在次年 1990 年入獄。這件事在他的人生篇章中別具意義。在四年與世隔絕與滿懷絕望的監禁中,他反抗監獄的規定,只有濫用施虐的刑罰才能使他就範,包括:使用電擊棒戮刺、綑綁、手銬,以及強迫站在炎夏的艷陽下數小時。有一次,他單獨拘禁且雙手被綁在背後達二十三天,直到腋下長滿了膿瘡。他遭遇好幾次精神崩潰,並兩度企圖自殺。他在其他獄友眼中,是個出了名的「大瘋子」。
1994 年,伴隨著國際間的壓力,他在刑期屆滿前四十多天獲釋(中國政府宣稱,他是因行為表現良好而受獎勵)。他回到家後,發現妻子已帶著他們的孩子離他而去。他在城裡的居留登記已被註銷,使他無法找到工作,只好被迫離開而前往鄉村。他從前在文壇的朋友們,因害怕而對他刻意躲避。他僅有的財產只剩下一根簫,那是他在獄中學會吹奏的樂器。他走過他的出生地「成都」的吵雜街道,展開他當一個街頭音樂家的全新人生。
他沒有放棄對文學的追求。1998 年,他編了一本《沉淪的聖殿》詩集,全都是一九七○年代的地下詩,包括許多中國異議分子創作或參考的作品。一位中國副總理親自下令調查此書,聲稱該書「預謀顛覆政府,且受到強大反中集團的支持」。他再度被扣押,而出版商也被禁止發行新書一年。
當中國政府勒緊了他出版生涯的繩套,廖亦武也更進一步潛入底層,偶爾在餐廳、夜總會、茶館以及書店打打零工。他原本就計畫以他關切的社會邊緣人為題材寫書,而他的底層生活,更拓展了他這方面的視野。他與獄友及街頭上的人對
話,促使《中國底層訪談錄》這本書的誕生。這本書挑選的六十位受訪者中,有職業嚎喪者、人口販子、殺人犯、乞丐、算命師、小偷、異議人士、同性戀者、嫖客、昔日的地主、學校老師,以及法輪功學員。就像作者本身,他們所有人不是在毛時代的各種政治整肅期間被拋到社會底層,就是在今日中國快速演化的喧鬧改變中淪落至此。
這些訪談文章既是文學也是紀實報導—與其說他只是把訪問的錄音抄寫下來,不如說他是在做重新的整理建構。因為做這些訪談需要格外的敏銳度與耐心,他有時要避開通常使用的錄音工具和筆記本。無論他在獄中或街上,他總是花大量時間在受訪者身上,試圖在進行任何訪談之前,先獲得對方的信任。為了一個故事,他可能需要在不同的場合進行三到四次的對話。例如:他曾訪問一個殯葬業者七次,然後再把全部的對話內容合併成一篇。
2001 年,揚子出版社出版這本書的刪修及濃縮版,立刻成為暢銷書。住在北京的著名獨立文學評論家余杰,稱這本書是「一位社會學家的調查報告,可以做為當代中國的一份歷史紀錄」。另一位獨立評論家任不寐,在一次自由亞洲電台的訪談中觀察到: 「這本書裡所提到的每個人都有一個共通性—他們都被剝奪了發言權。這本書是針對他們被剝奪發言權的大聲譴責,以及對於這群獨特個人的精彩描述。」
廖亦武於這個國家所引用的「底層」或「社會底層」之字眼,還是首次出現在共產黨自 1949 年接管之後的中國。毛澤東共產主義運動的支持者對此概念嗤之以鼻,此運動自以為能創造出一個沒有娼妓、乞丐、幫派和吸毒者的平等社會。誠如預期的,宣傳部、中國新聞與出版主管機關下令所有廖亦武的書下架,並懲處出版社的編輯,而一家頗受歡迎、曾刊登其訪問與專題報導其書籍的中國周刊《南方周末》,所有關鍵的職員也被開除。
2002 年,作家兼耶魯大學講師康正果在中國與廖亦武見面,並將他完成的手稿夾帶出境。透過康正果的幫助,台灣的麥田出版公司出版了三冊完整版的《中國底層訪談錄》。同年,他獲得獨立中文筆會的文學獎;2003 年,又獲得美國赫爾曼–哈米特寫作獎(Hellman–Hemmett Grant),這是由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組織認可,一年一度頒發給勇於面對政治迫害的作家。
我第一次聽說過廖亦武,得回溯到 2001 年 6 月,當時我承接了翻譯自由亞洲電台對他的訪談錄音,就在他的書在中國被禁之後不久。這段訪談激起了我對作者的興趣。《中國底層訪談錄》使我想起史德茲‧特凱爾(Studs Terkel)的書《工作》(Working),特凱爾在書中收集許多來自美國各行各業的生涯訪談,從女服務生到電話接線生,到棒球選手和音樂家,他談及他們在美國的工作與生活。《工作》在一九八○年代被翻譯成中文,中譯本書名為《美國人談關於在美國的生活》。我當時是中國一所學院的學生,中文版與英文版兩者都讀過(我的老師選擇英文版當作美語日常會話的教材)。《Working》為我和其他許多中國人介紹了很多有關真實的美國和一般美國人的生活,那是以往我所不知道的。同樣地,我相信廖亦武書中提到的真實人生的故事,對西方讀者也會達到相同的目的,幫助他們從一般中國人的眼光了解中國。
從 2002 年開始,我做過許多嘗試,想透過廖亦武在中國的朋友與其接觸。這種搜尋變成一場艱鉅的任務,因為身為一個異議作家,他必須不斷地遷移以躲避警察的騷擾。有一次,他在成都訪問一個未經核准設立的宗教團體成員之後,為了逃避追捕,只好從三樓的窗戶跳下逃跑。
在 2004 年初的某一天,我收到一位朋友的 e-mail,她以前是哈佛大學的訪問學者。他偶然間知道廖亦武安然無恙,於是在自美國返回北京之後,開始打聽他的行蹤。我從她的 e-mail得知,廖亦武已同意我將他的作品譯成英文的提議,並且給了我他的手機號碼。我檢查區域號碼,那是來自中緬邊界附近的某個小鎮。
兩個小時的談話,標記著我們合作關係的開始。廖亦武和我透過 e-mail 與手機合作翻譯。有時,如果我們覺得我們的談話正在被錄音,我們就會以我們彼此瞭解的密語交談,或透過雙方都認識的朋友傳話。
2005 年夏天,廖亦武書中的三篇訪談—職業嚎喪者、人口販子和廁所門衛—首次以英文出現在《巴黎評論》上,這是該雜誌新主編 Philip Gourevitch 上任後的第一期雜誌。
隨著在《巴黎評論》成功的初試聲啼,我們又選了二十七篇我們覺得既具有代表性,而西方讀者也可能會感興趣的故事。我們也重新整理並縮短篇幅,添加背景資料,幫助那些對訪談內容裡提及的政治與歷史事件不熟悉的讀者閱讀。就如書名提出的,我們希望這本書將提供西方讀者,一瞥來自底層發聲的當代中國的樣貌。
同時,儘管反覆受到警察的騷擾,廖亦武還是持續透過在海外發表其作品,突破中國政府的檢查制度。2007 年 11 月,當他前往北京領取由獨立中文筆會頒發的自由寫作獎,他卻遭到扣押並審問超過四個小時。他不受要脅。藉由一位中國律師的協助,他目前正對政府提告,控訴其侵犯他的人權。「我正嘗試一點一滴的克服,那令我屈服的恐懼」,他說,「我嘗試保有我思想的健全與內在的自由」。
英文版導讀:一群中國社會邊緣人的心聲 ⊙黃文
當中國政府的坦克車在 1989 年 6 月 3 日夜晚開進北京市,並殘忍地鎮壓支持民主運動的學生時,廖亦武正在中國西南的四川省家中。這些新聞令他內心深受震撼。他連夜創作了一首題為《屠殺》的長詩,就像畢卡索生動地描繪納粹轟炸屠殺格爾尼卡(Guernica)鎮一般,他以寫實的意象忠實描述了無辜學生與市民被殺害的情況。
他的詩沒有任何機會在中國出版,於是他錄製了一卷自己朗讀的錄音帶,以中國式的狂嘯形式朗誦,向死者招魂。這卷錄音帶透過中國的地下管道而廣泛流通。他在那時創作的另一首...
作者序
英文版序 ⊙菲利浦‧高瑞維奇(Philip Gourevitch)
聽見新的聲音,是書本所能提供的最棒的刺激之一。尤其是透過廖亦武,我們不僅聽到了將近三十種新聲,而且是透過自己話語表達的重要心聲。廖亦武既是一個不畏強權的觀察家與記錄者,也是一個四處走訪的採訪者和說故事高手,更是一個口述歷史學家和擅長偽裝身分的人,以及民間學者和諷刺作家。此外,他也是所有在中國社會裏被噤聲、被共產黨視若無睹的群眾對外發聲的媒介,這群人有騙子與流民、偷渡犯與街頭藝人、脫黨黨員與身障人士、處理人類排泄物的廁所門衛與處理人類遺體的化妝師、藝術家與風水師、江洋大盜甚至盜墓者—然而他們每一個人所說的話,都比這個以「人民」為國名的國家所發行的官方出版品還要誠實。
廖亦武是被殘酷的人生經歷塑造的作家:他童年時差點餓死,父親被貼上人民公敵的標籤;他因為寫詩誠實地論及共產黨而被捕下獄,並因為拒絕禁聲而被責打。當他在獄中聽到許多和他相同遭遇的故事,他發現這些當局想永遠掩滅的真相具有極大的價值,於是他鼓起勇氣去寫。因為他瞭解甚麼是失去,所以無所畏懼。再也沒有甚麼東西可以令他依照官方的強制規定,對周遭的事物視而不見、裝聾作啞,並阻止他讓我們的視野不再被共產黨官僚所蒙蔽。這不僅是公然違抗,但還算不上是政治論戰,卻使收集在這本書裏的故事充滿了生命力。
無疑的,廖亦武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具原創性和最值得注意的中國作家。更確切地說,他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具原創性和最值得注意的作家,而他來自中國。是的,他使用的語言是中文,他創作的主題是他的國家及人民,而他的故事也一一來自他在各地的遭遇。然而,即使有些人從未到過中國,而且只能透過黃文的譯本認識他的作品,這些故事都能立即而直接地跨越一切的界線與階級。它們屬於偉大而共有的世界文學遺產。
廖亦武雖是一位原創性的作家,但作家們應該都會像馬克.吐溫之於傑克.倫敦、果戈里(Nikolai Gogol)之於喬治.歐威爾、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之於萊維(Primo Levi)一樣,即使文風殊異,仍然視他為精神上與文學上的同道中人。如果人類世界像個馬戲班子,他就是馬戲表演裏的指揮者,而他的作品則具有強而有力的提醒作用—在一個說出真相可能會犯罪的封閉社會裡,其重要性與必要性就如同在開放社會中,自由可以讓人心感到安穩一樣—它提醒我們在人類歷史中,不只是公開而喧鬧的權力支配需要被關注,同樣的在那些被邊緣化、被忽略、無法被聽見的角落裡,他們的心聲更需要牢牢地被銘記。
英文版序 ⊙菲利浦‧高瑞維奇(Philip Gourevitch)
聽見新的聲音,是書本所能提供的最棒的刺激之一。尤其是透過廖亦武,我們不僅聽到了將近三十種新聲,而且是透過自己話語表達的重要心聲。廖亦武既是一個不畏強權的觀察家與記錄者,也是一個四處走訪的採訪者和說故事高手,更是一個口述歷史學家和擅長偽裝身分的人,以及民間學者和諷刺作家。此外,他也是所有在中國社會裏被噤聲、被共產黨視若無睹的群眾對外發聲的媒介,這群人有騙子與流民、偷渡犯與街頭藝人、脫黨黨員與身障人士、處理人類排泄物的廁所門衛與處理人類遺體的化妝師、藝...
目錄
英文版序
英文版導讀:一群中國社會邊緣人的心聲
卡普欽斯基國際報導文學獎頒獎辭
德國阿沙芬堡公民勇氣獎頒獎辭
1. 吹鼓手兼嚎喪者李長庚
2. 人販子錢貴寶
3. 廁所門衛周明貴
4. 吆屍目擊者羅天王
5. 「麻瘋病人」張志恩
6. 農民皇帝曾應龍
7. 風水先生黃天元
8. 作曲家王西麟
9. 百歲和尚燈寬
10. 老右派馮中慈
11. 工作組組長鄭大軍
12 老地主周樹德
13. 土改受害者張美芝
14. 鄉村老教師黃志遠
15. 遺體整容師張道陵
16. 街道居委會主任米大喜 .
17. 老紅衛兵劉衛東
18. 六四反革命萬寶成
19. 法輪功修煉者陳氏
20. 偷渡犯黎憶豐
21. 盜墓賊田志光
22. 江洋大盜崔志雄
23. 街頭瞎子張無名
24. 街頭藝人雀躍
25. 夢遊者之妻黎英
26. 打工仔趙二
活著去說的故事—出版後記
英文版序
英文版導讀:一群中國社會邊緣人的心聲
卡普欽斯基國際報導文學獎頒獎辭
德國阿沙芬堡公民勇氣獎頒獎辭
1. 吹鼓手兼嚎喪者李長庚
2. 人販子錢貴寶
3. 廁所門衛周明貴
4. 吆屍目擊者羅天王
5. 「麻瘋病人」張志恩
6. 農民皇帝曾應龍
7. 風水先生黃天元
8. 作曲家王西麟
9. 百歲和尚燈寬
10. 老右派馮中慈
11. 工作組組長鄭大軍
12 老地主周樹德
13. 土改受害者張美芝
14. 鄉村老教師黃志遠
15. 遺體整容師張道陵
16. 街道居委會主任米大喜 .
17. 老紅衛兵劉衛東
18. 六四反革命萬寶成
19. 法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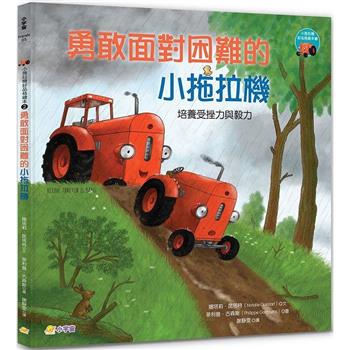
![念君歡卷四] 念君歡卷四]](https://cdn.kingstone.com.tw/book/images/product/20185/2018561884609/2018561884609m.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