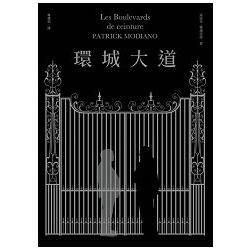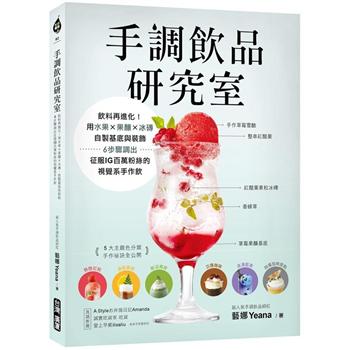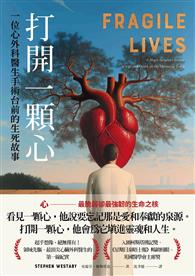導讀
「他是我父親……」—《環城大道》與迷宮中的尋父記
追尋失落的黑暗時光
歷史不斷往前邁進,但是不論如何開向未來,過去發生的事情並非就此煙消雲散,船過水無痕。現在與過去要如何協商?要架構在甚麼樣的比例之中?要如何擺脫集體失憶或曇花一現的懷舊風潮?要如何叩問過去而不將歷史關入僵化的範疇?官方歷史總是將過去框囿在似是而非的表相之中,可以重溫,可以緬懷。至於那些埋藏在過去地底深處竄動不安的靈魂則被拋除在界域之外,由於不可視,由於無以名狀,於是草率收編。二十世紀過去了,許多作家不禁要詢問這世紀發生了甚麼事。這塵封的過去留下甚麼?而我們又從過去記取了甚麼?透過虛構,我們得以重返過去,回溯歷史某些難以抹滅的記憶殘骸,調查那埋在深不見底的幽暗蔭谷。
二○一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蒙迪安諾(Patrick Modiano)出生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換言之他並未親身經歷過戰爭的恐慌,然而他大多數的作品都用來挖掘這段與他素昧平生的歷史—德軍佔領期。從1968年的《星形廣場》(La Place de l’Etoile)到二十世紀末的《三個陌生女子》(Des inconnues),他的小說或其他形式的作品都以二戰納粹時期為背景,人物游移在一個遭德軍佔領的巴黎,法奸與德軍合作、投機客、密告者橫行的這段黑暗歲月。
作家之所以對這段歲月念茲在茲,自然有其個人的心理悲劇纏捲其中,而非出於後世代對昔日歲月的懷舊或執迷。古老的社會回溯過去,藉此捕捉原初的時光,因為那段時光就是伊甸園時光,是一段關於失樂園的想像,是人類處境之前一段恬靜的歲月。然而,在蒙迪安諾的小說世界中,沿著時光之河,逆流而上,找尋到的並非純樸的樂園,而是人世間最難將息的地獄—德軍佔領期的法國。因為父親被遺留在那個黑暗時代,因為那段時光裡有太多的謎團,且關係著自己的身分,所以敘述者鍥而不捨地想回到那一段歲月,那一段作者並未親身經歷,卻令他既惶恐又著迷不已的鬼魅歲月。蒙迪安諾的父親是猶太移民,巴黎遭德軍佔領的那段歲月中,他從事黑市交易,也跟許多通敵分子有來往。這段隱誨不明的關係足以為蒙迪安諾的小說提供一個背景,同時也解釋何以小說家特別執迷於這段過往,他自己就像是從這段猙獰的歲月誕生出來的,用「後災難」、「後記憶」的想像力譜寫虛構創作。「佔領期的那個暗夜,」作家曾說,「那是我的源頭,我就是從那個源頭走出的。」
《環城大道》(Les Boulevards de ceinture)的背景正是二戰德軍納粹恐怖時期。發表於一九七二年,同年獲得法蘭西學院小說大獎,小說講述兒子尋找父親的故事:敘述者從小寄養在別人家裡,不識自己的父親,直到十七歲那一年,父親才真正現身找他,兩人開始一同居住在巴黎,父親似乎從事黑市交易,非法買賣,兩人也經常開車在巴黎的一些休憩站停留,咖啡館、酒吧、豪華飯店、應召站,有時兒子也陪父親去探勘一處廢棄的環城鐵路驛站。一日,他們在探勘中迷路,只得坐地鐵離開現場,到了「喬治五世」地鐵站時,敘述者遭到推擠跌落地鐵的軌道,有人從背後推他,敘述者覺得推他下去的人不是別人,就是他父親。兩人被帶往警局做完筆錄,父親便離他而去,此後音訊全無。數年下來,敘述者不斷打聽父親的下落,自己也是渾渾噩噩的過日子,後來終於查到父親的下落,父親跟一群戰爭期間走私藝術品、從事黑市交易、反猶的報社編輯等不法分子混在一起,這一群人經常聚在楓丹白露附近的一個小鎮,住在豪宅,飲酒作樂,形跡可疑。敘述者設法闖進這個詭異的團體,一心一意想要與父親再續前緣。小說一開始,敘述者從一張老照片出發,從中敘述父親與這群走私集團的聚會,敘述者接著以倒敘的手法講述自己如何與父親相認,共同一段巴黎居無定所的歲月,直到一場地鐵的意外之後,又與父親分開,再次遇見時已經過了十數年了,父親並沒有認出他來,敘述者為了能和父親再見一面,潛入了這個黑市集團,混入這個反猶的報社中,最後就在與父親一同逃離了這個蛇鼠集團之後,準備逃亡到比利時的路上,父親遭到警察逮捕,父子再也沒有見過面,小說末了只剩下敘述者多年過後舊地重遊,回到這個以前那一群走私通敵團體常來的酒吧,追憶當年……
「我們處於甚麼樣的年代?這又是甚麼時代?哪一段人生?我怎麼會認識你,在一個你還不是我父親的年代?我又為什麼費盡心力尋找源頭?」《環城大道》的敘述者曾不只一次語重心長地問道。德軍佔領期這段黑色時期是蒙迪安諾小說最常見的背景,然而作家也說,「德軍佔領期這段歷史本身並不特別吸引我,我感興趣的是其他的事物。我的目的是想要試著烘托出一個日暮西山、黯然退隱的世界。我之所以鎖定德軍佔領期,正是因為這段歷史提供了這樣的氛圍,有點混濁不明,隱約綻放著一縷撲朔迷離的光芒。」這段混沌不明的時光特別能夠突顯生命的迷惘失落,這段歷史本身就是撲朔迷離,格外能夠傳遞生命的虛空、不確定性,存在的兩難選擇:「我們做甚麼也沒用,我們注定永無寧日,無法享受事物的溫和與靜謐。我們一路走到底,四處都是流沙。」
蒙迪安諾雖未以歷史家或寫實主義的精確手法書寫德軍佔領期的市井生活,然而,書中獨特的暗示、朦朧的佈局、點到為止的影射都指向德軍佔領期。書中涉及的黑市交易猖獗,偽造身分,製造假鈔或是反猶刊物等線索都指向這個黑暗時代。作家欲言又止的講述這段歲月,帶出一種濃密黏稠的不適感,人活得空洞,意義抽空,陷入泥濘不可自拔,從中釋放出一種混濁不清、陌異疏離的氛圍,焦慮詭譎。這是一個投機份子橫行的黃金年代,時間好像開了一個大洞,讓這群非法份子一股腦地跳進去,懷抱著一種命運重新洗牌的投機心理,重新塑造一個身分,即便知道最後的下場會是槍決。報社總編輯穆哈就是這樣的人物,敘述者提到他時曾寫道:
「我們這個混濁的年代」給了他實現夢想的契機。他利用時局的動亂與黑暗時期來達到目的。在這個千瘡百孔的世界裡,他反而從容自在,如魚得水。
蒙迪安諾運用德軍佔領期這段意識形態遭遇危機,價值瓦解潰散的年代,除了傳達某種存在的困頓,也運用幻覺、夢遊和現實交錯的手法打造一種諜對諜的偵探小說氛圍,同時質疑了法國官方對於這段黑暗歷史避而不談、息事寧人的態度。雖然蒙迪安諾並未直接公開表態,但是在《環城大道》中,作家透過虛構的手法逐漸讓這段塵封、潛匿的法國近代史浮現,直接牴觸了當時戴高樂主義下的抵抗運動神話,瓦解了英雄主義金碧輝煌的表相。然而,讀者似乎也無法因此就下結論,認為蒙迪安諾捍衛政治立場或意識形態。作家的心思細膩幽微,他重現德軍佔領期這段歲月,揭露其中的矛盾與曖昧不明,讓現代人可以重探禍害的根源,也開啟了其他研究者重新研究這段歷史的興趣,提供閱讀德軍佔領期的另一個觀點。
林德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