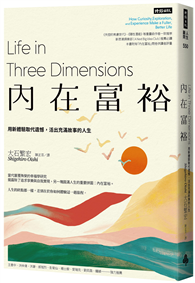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片腕:川端康成怪談傑作集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10 |
二手中文書 |
$ 298 |
小說/文學 |
$ 308 |
日本文學 |
$ 308 |
日本文學 |
$ 315 |
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步入晚年,我想創作的小說還有五、六篇,
〈片腕〉便是其中之一……
日本文豪川端康成 探究魔性的詩性獨白
「尚未讀畢,我便深深被那女孩的一隻手臂所掠住了。」──三島由紀夫
女孩別致的細長指甲,如同疼愛我似的搔著我的左手掌。
在這種隱隱約約的觸感中,我深深沉睡……
最後竟連形影都消失了。
一名女孩將右手臂拆下,借給獨自生活的男子。孤獨的氛圍襲擊故事中的角色,而讀者也將因種種由妄念而生的孤獨深淵,而感到恐懼不已。川端康成晚年名作〈片腕〉深深觸及最根本的人性和生命本身,此時正是川端康成密集服用安眠藥、精神恍惚的時期,受到藥物的影響,川端所追求的「病態美」、「頹廢美」、「老境美」幾乎達到顛峰之境。步入晚年的川端曾說「要敢於創作背德的作品,否則的話,小說家的生命便會凋萎而去。」
剝去一切倫理道德與禁忌,
真正的生命才能毫無掩飾地顯露出來……
夜幕低垂,川端康成的銳利眼神看穿世間生死的愛戀與孤獨,
寫出一篇篇幽暗妖美的短篇傑作──
《片腕》收入24篇川端康成經典短篇小說,窺探文豪內心世界的愛戀、孤獨與悖德之美。從少年時代處女作〈千代〉到晚年傑作〈片腕〉,讀者可以窺視川端文學中的特異感受,毫無疑問地,川端康成用小說體現日本最為詭譎幽玄的特殊美學。1968年,川端康成成為日本第一位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他的作品在國際間廣受高度評價,並讚譽他:「以優異的感受性,發揮日本人性格與感情的精隨,成為東西精神的橋樑。」
作者簡介:
川端康成
1899年6月生於大阪,幼年父母相繼過世,其後撫養他的祖父母又陸續病故,一生多旅行,心情苦悶憂鬱,逐漸形成了哀傷與孤獨的性格,這種內心的痛苦與悲哀後來成為川端康成的文學底色。作品富抒情性,追求人生昇華的美,並深受佛教思想和虛無主義影響。
早年多以下層女性作為小說的主角,寫她們的純潔和不幸,其成名作《伊豆的舞孃》即是此一時期的代表作。晚年的作品則描繪近親之間、甚至老人的變態情愛心理,手法純熟,渾然天成,代表作有《山之音》、《睡美人》、《湖》等,〈片腕〉,亦是此時期的傑作之一。1968年川端康成以《雪國》、《千羽鶴》、《古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為日本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第一人。
1972年4月,在工作室含煤氣管自殺身亡,沒有留下任何隻字片語。
譯者簡介:
邱振瑞
曾任前衛出版社總編輯。從小立志當小說家,著有小說集《菩薩有難》、《來信》。目前在文化大學講授日本現代小說筆譯課程。譯作有《太陽與鐵》、《我青春漫遊的時代》、《編輯這種病》、《鈴木商店的當家娘》等。
「嗯。」女孩點頭同意。「對了,如果手肘和手指不能彎曲,而是直挺挺的,您難得拿著也像拿著假手,那可沒什麼意思呢。我讓它更靈活些!」說罷,她從我手中取回自己的右手臂,往手肘輕輕地吻了吻,然後又輕吻過每根手指的關節。
「這樣它就能伸展了。」
「謝謝。」我接下女孩遞來的右手臂。「這隻手臂也會說話嗎?它會跟我聊天嗎?」
「手臂只能做它能做的事情。倘若手臂會說話,您把它還給我之後,我會很害怕的。不過,您不妨試試⋯⋯對它體貼些,或許它能聽懂您說的話吧。」
「我當然會對它體貼的。」
「去吧。」女孩像是要...
千代
處女作的魔咒
無言
弓浦市
地獄
故鄉
岩石上的菊花
離合
殉情
龍宮的公主
靈車
屋頂上的金魚
顯微鏡怪談
蛋
不死
白馬
女人
恐怖之愛
歷史
皎潔的圓月
花姿疊影的照片
抒情歌
安魂曲
- 作者: 川端康成 譯者: 邱振瑞
- 出版社: 大牌出版 出版日期:2015-09-23 ISBN/ISSN:978986579752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44頁 開數:14.8*21 cm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日本文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