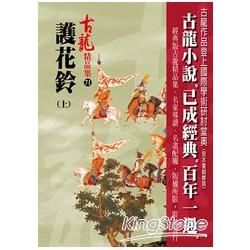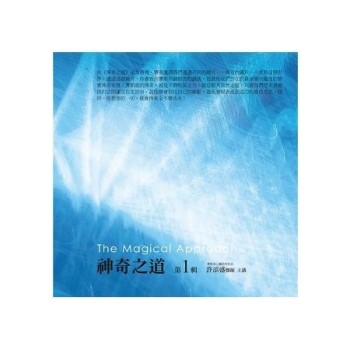導讀推薦
筆底驚濤腕底風--以《護花鈴》和《彩環曲》為亮點的古龍早期名作
古龍的崛起、茁壯、成熟與突破、掙扎、再突破、再掙扎……堪稱是台港武俠小說創作高潮時期的一大「奇蹟」。就作品的數量而言,他在二十餘年的創作期間總共留下了六十一部,約兩千五百餘萬字的心血成績,平均每年的創作量不下於一百萬字;就作品的質量而言,幾乎每一部都有可觀之處,成熟時期的作品尤其往往生機盎然,靈光四射,堪與金庸作品分庭抗禮,而毫不遜色。
才華橫溢的古龍
古龍的創作生涯與創作表現,有不少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中之一,是他的才華在相當年輕的時期即已光芒四射。他從十八歲寫作第一部武俠作品《蒼穹神劍》開始,即與武俠小說的創作結下了不解之緣;到三十一歲時,他已完成《武林外史》、《名劍風流》、《絕代雙驕》、《楚留香傳奇》等膾炙人口的名作。而金庸則在三十一歲時,才開始撰寫他的首部武俠作品《書劍恩仇錄》;相形之下,古龍的「早慧」是十分明顯的。金庸在四十七歲時完成了他總計十五部武俠作品的撰作,而開始進行逐步的修訂工作;而古龍卻在四十八歲那年猝然逝世,留下了一個甫在進行嘗試的寫作計劃,即:以一系列短篇武俠作品,串連成長篇巨帙的「大武俠時代」。
而在三十一歲至四十七歲之間,諸如《蕭十一郎》、《流星.蝴蝶.劍》、《天涯.明月.刀》、《多情劍客無情劍》、《邊城浪子》、《陸小鳳傳奇系列》、《七種武器》、《大地飛鷹》、《英雄無淚》等風格驚絕、生面別開的力作逐一問世,真令讀者有置身山陰道下,目不暇給的驚喜。時值金庸停筆之後,唯古龍以一支生花妙筆獨撐武俠文壇;於今想來,若是古龍也有機會修訂他的全部作品,則他的文學地位必較目前大可提升,殆可斷言。
苦悶時代的閃光
依照古龍自己的說法,沒有寫武俠小說之前,他本身就是個武俠迷,而且是從被稱為「小人書」的連環圖畫看起的。古龍曾回憶道:「那時候的小學生書包裡,如果沒有幾本這樣的小人書,簡直是件不可思議的事。可是,不知不覺小學生都已經長大了,小人書已經不能再滿足我們,我們崇拜的偶像就轉移到鄭證因、朱貞木、白羽、王度廬和還珠樓主,在當時的武俠小說作者中,最受一般人喜愛的大概就是這五位。然後就是金庸。於是我也開始寫了。引起我寫武俠小說最原始的動機並沒有什麼冠冕堂皇的理由,而是為了賺錢吃飯。」--見古龍:「不唱悲歌」
其實,古龍在此處的陳述顯得過於簡略。一九五○至一九六○年的台灣,在物質生活上確然相當匱乏,古龍隨其家人從香港到台灣時年方十三歲,對世間當充滿憧憬;但由於家庭變故,父母仳離,他在上大學時的第一年即已面臨生計的煎熬,亦是事實。然而,一個必須正視的因素是當時的大環境、大氣候十分苦悶,整個台灣在戒嚴令的威權統治下,有一種近乎窒息的感覺;知識分子不敢議論時政,庶民大眾當然更噤若寒蟬。但嚮往公平正義,尋求超現實的理想境界,是源自人性深處的強烈需求;唯在當時的苦悶氛圍下,這種人性需求也仍須覓致其表達或渲泄的形式。然則,武俠小說在當時的台灣應運而生,原有不可漠視的社會基礎。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是台灣武俠創作的極盛時期,作者多為移遷到台的流亡學生、國軍將士、基層公務員;既然時代與社會對幻想式的武俠作品有其需求,而一旦有出版社願予印行,寫作這類作品又確能賺錢吃飯貼補家用,於是,一時之間武俠作者多如過江之鯽,武俠小說儼然成為紓解時代苦悶的主要消閒讀物。但也正因如此,絕大多數作者都並不將寫作武俠小說視為一種長久的職志,或視為在文學上、藝術上有其獨特意義的事業;於是,正邪對立、善惡分明、陳陳相因、交互模仿的武俠刻板的窠臼逐漸形成,嗜血的、粗糙的、抄襲的、胡編的末俗濫惡之作,開始充斥於當時的市井書坊。恰在此時,古龍以其清新的筆觸、流利的文采、典雅的敘事,以及天風海雨般的想像力與創作力,崛起於武俠文壇,確予人以耳目一新的驚豔之感!
一出手令人驚豔
即使在二十多年後被他自評為「內容支離破碎、寫得殘缺不全」的少年期初作《蒼穹神劍》中,古龍也展現了他獨具韻味的文字功能。他起筆即寫道:「江南春早,草長鶯飛,斜陽三月,夜間仍有蕭索之意。秣陵城郊,由四橫街到太平門的大路上,行人早渺,樹梢搖曳,微風颼然,寂靜已極。」像這樣優美、浪漫而富於古典詩意的文字,豈像是出於一個未滿十八歲的少年之手?更何況,他在書中所抒寫的秦淮風月、少豪意氣、英雄志業、兒女情懷,以及情節中的悲劇性衝突、傳奇性事蹟,實已預示了日後一連串作品的基調與特色。即使只就這部十八歲的少作而言,古龍筆下所抒寫的悲劇俠情與悲劇美感,較之他所推崇的前輩武俠名家王度廬的作品,也已不遑多讓。
在古龍的心目中,王度廬的作品「不但風格清新,自成一派,而且寫情細膩,結構嚴密,每一部書都非常完整」。以王度廬著名的「鶴—鐵五部曲」為例,古龍即推崇其「雖然是同一系統的故事,但每一個故事都是獨立的,都結束得非常巧妙」(古龍:「關於武俠」)。所以,古龍對自己早年的作品結構不夠嚴密、系統不夠完整,一直耿耿於懷。然而,以當時台灣的出版環境而言,為了適應租書店的需要,武俠小說的寫作本是片段進行、分冊付梓的;加以古龍當時因創作力旺盛,往往同時展開數個故事,而非集中心力於單一的、長篇的武俠作品之構作;所以,古龍的〈早期名作系列〉以文筆、氣力與瑰麗的想像力擅長,而非以嚴密的結構見長,完全是可以理解的現象。
(關於古龍的所謂〈早期名作系列〉,一般是指他在一九六三年首次有意識地改變寫作風格,將日本戰前名家如吉古川英治、小山勝清等人有關宮本武藏及幕府時代一系列忍者、劍客、武士的作品,加以消化吸收,而寫出《浣花洗劍錄》之前的全部作品而言。)古龍本人在生前也認可這樣的分期方式,他認為一九六三年之前的作品中,《湘妃劍》、《孤星傳》頗有嘗試「文藝武俠」新寫作路線的用意,因此,〈早期名作系列〉主要涵括了《彩環曲》、《護花鈴》、《失魂引》、《遊俠錄》、《劍客行》、《蒼穹神劍》、《月異星邪》、《殘金缺玉》、《飄香劍雨》、《劍毒梅香》、《劍玄錄》等十一部作品。
超越了俗套模式
這十一部作品,都是古龍從十八歲至二十三歲的五年之間,在大時代苦悶與青春期苦悶交互導引,亟待有所清洗和昇華的情況下,所完成的嶄露頭角之作。然而,縱使在這些初試啼聲的青春期作品中,除了文字的清新流利、構思的浩瀚恣肆之外,古龍對於當時所流行於武俠文壇的末俗濫惡的風氣,已蓄意要有所扭轉;故而一再尋求理念上、表達上及題材上的突破。這個時候,古龍當然尚未體認到武俠小說可以根本不以武功、武打、武技來吸引讀者,而逕自以氣氛的營造、情節的鋪陳、人物性格的刻畫,以及人性深度的發掘與試煉,作為作品展開的主體;然而,為了向當時流行於武俠文壇的刻板窠臼之作明示區隔,以建立自己的風格和特色,古龍揚棄了正邪對立、善惡分明的武俠敘事模式,而著意於抒寫正邪、善惡、是非、黑白往往相互糾纏,而無法明晰劃分的情境與人物。換句話說,古龍的早期作品即已超越了陳陳相因的武俠寫作模式,而呈現他自己獨特的認知與理念。
自我突破的契機
在古龍的早期作品之中,《護花鈴》與《彩環曲》的份量較為特殊,是最具有創意,結構也最嚴密的精心傑構。事實上,古龍在成熟期所撰許多膾炙人口的代表作中,有若干迥異流俗的情節、匪夷所思的橋段、戛戛獨絕中的人物典型,以及絲絲入扣的心理刻畫,在這兩部早期名作的表述中,已可看出端倪。當然,由於這些吉光片羽式的靈感與巧思,尚未被整合到充分系統化、節奏化的敘事模式之中;所以,往往予人以「七寶樓台,炫人眼目,拆散下來,不成片段」之感。儘管如此,配上了古龍那彙集浪漫才情與古典素養於一體的文字魅力之後,這些吉光片羽式的靈感與巧思,仍使得《護花鈴》與《彩環曲》展現出晶瑩剔透的風貌,並為六十年代初期的台灣武俠文壇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氣息。
《護花鈴》的故事情節,若加以充分的鋪陳與推展,大可以成為一部高潮疊起、驚心動魄的長篇巨著。事實上,像「諸神殿」與「群魔島」的對峙、「不死神龍」龍布詩與「不老丹鳳」葉秋白的比鬥、「風塵三友」與南宮世家的秘辛等,上一輩絕對高手之間的恩怨情仇,既複雜萬端,又交互牽纏,只消稍予點染,無一不可以發展成大開大闔的傳奇故事。然而,古龍卻以舉重若輕的敘事筆法,將這些雖然深具戲劇張力的前代軼事一一推向背景,而突出了少年英傑南宮平的入世奮鬥事蹟,細述他的成長、磨煉、迷惘、自我克制、自我提升的歷程,並以他的江湖遇合來弭平或化解上一輩絕頂高手之間的恩怨情仇。很顯然的,古龍將西方現代小說的敘事模式中,頗具普遍意義的「啟蒙」情節引進了《護花鈴》之中;所以,「諸神島」、「群魔殿」的神話式對立,及其最終的結局,反而成為次要。
即引入了「啟蒙」的概念,則南宮平居然與上一輩武林美人梅吟雪相戀,歷經波折,九死未悔,便成為不難理解的情節。因為,唯有通過了感情或愛情領域的考驗,南宮平才能成長為一個真正堅強的男人;而梅吟雪最終為了成全南宮平維護武林正義的聲譽,悄然離他而去,委身下嫁「群魔島」的少島主,使得「群魔島」轉而力助南宮平,便成為南宮平的「啟蒙」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至於南宮世家所珍藏的「護花鈴」,照古龍的說法,本是三對可以產生「共振」的金鈴,由相戀的情侶們各執一對,一人遇險,只消搖動金鈴,另一人立可往援,這當然是一種浪漫的想像;最終,梅吟雪黯然遠行,「護花鈴」並不能助使南宮平找到她,安慰她,則隱隱反映了「啟蒙」與「浪漫」之間的永恆矛盾。
至於《彩環曲》,規模上雖只是中篇的格局,內容之豐富卻儼然超過了長篇武俠的承載。古龍曾一再表示《彩環曲》是他早期作品中最重要的「明珠」,因為日後許多情節發展於此,良有以也。
《彩環曲》的行文之優美、落筆之精確、佈局之奇詭、節奏之明快,以及劇情轉折之搖曳生姿,在在顯示古龍在創作生涯中已瀕臨突破自我、更上層樓的契機。在本書中,他首次將以罌粟花提煉的「花粉」作為控制他人意志的有效工具一事,引入到武俠小說的主要情節之中,使得「意志」這個因素成為武俠小說的關鍵要素。事實上,本書中所抒寫的「石觀音」以罌粟花粉控制烏衣神魔的情節,正是日後古龍在「楚留香傳奇系列」中進一步發展相關故事的張本,連「石觀音」這個名稱,在後來的故事中也予以援用;足見古龍對《彩環曲》中創構的若干情節設計與人物典型,是相當滿意的。
不但如此,在《彩環曲》中,古龍也首次將「真正的劍客,必是以生命忠於劍、也癡於劍」這個理念,以具體的人物形象與情節推演,作了栩栩如生的表述。《彩環曲》中衣白如雪、一塵不染的白衣人,既是古龍中期作品《浣花洗劍錄》所凸顯的東瀛白衣人的前身,也是「陸小鳳傳奇系列」所刻畫的一代劍神西門吹雪的雛型。而《彩環曲》中,柳鶴亭與白衣人的一戰,將天候、地形、氣氛、心情、膽色,全都融入到一瞬間生死對搏的「極限情境」,也為古龍日後揚棄具體武功招術,著意營造決鬥氣氛的敘事技巧,作了動人心弦的展示。就這個意義而言,《彩環曲》其實是古龍擺脫傳統武俠敘事模式,銳意走向自闢新境之途的轉折點。
為了突破傳統武俠小說的刻板敘事模式,古龍在《彩環曲》中,還藉由對武林秘笈「天武神經」爭奪與搏鬥過程描述,而提供了一個強烈反諷的觀點。古龍如此寫道:在傳說中,每隔若干年,江湖上便總有一本「真經」、「神經」之類的武學秘笈出現,而江湖之人一定將之說得活龍活現,以為誰要是得到了那本「真經」、「神經」,便可以練成天下無敵的武功。
而在《彩環曲》中,為了爭奪「天武神經」而殞命的武林高手不計其數,但在武當掌門將它刻印了三十六部隨緣贈送之後,武林人士終於發覺,原來「天武神經」有其致命的缺點,往往使得習練之人在緊要關頭走火入魔,失去對外來侵襲的抵抗能力,這種對武學秘笈的反諷式描述,甚至已超出了金庸在《笑傲江湖》中對「葵花寶典」的傳奇式揶揄;當然,更超脫了金庸對「九陰真經」、「九陽真經」之神奇功能的執著;而這時的古龍在武俠文壇雖已嶄露頭角,卻年甫二十三歲,正是旭日初升的時節。
清新的古龍式武俠
綜看古龍的〈早期名作系列〉,主要特色是結合了浪漫的文學想像與古典的文學素養,而藉由對傳統武俠敘事模式的消化、吸納、突破、轉型與揚棄,而逐漸建立令人耳目一新的優美風格。起初,由於受到王度廬作品中那種沁人心脾的悲劇俠情、悲劇美感的影響,古龍的作品也隱隱沾染著耽美的悲情色彩;又由於受到金庸作品中某些結構佈局經營、人物性格發展、情節遞嬗轉折的影響,古龍的早期作品力求在浪漫的抒情與嚴密的結構之間,尋求平衡。
但無論如何,即使在早期作品中,古龍對於傳統武俠敘事模式的所預設計的正邪、善惡、是非、黑白較易判然區分的那個武俠世界,即已在行文落筆之間,有意無意地予以揚棄;而展現出自創一個「古龍式武俠世界」的企圖心與創作力。
近來重新受到舉世矚目的現代德國文藝批評界英才班雅明(W.Benjamin)在其《天鵝之歌──歷史哲學論綱》中,曾引述「起源就是目標」的格言,論述許多文學作家的思想發展。對於古龍而言,這句格言實有歷久彌新的意義,因為,古龍畢生創作的起源與目標,均在於以清新脫俗的文學表述,寫出石破天驚的武俠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