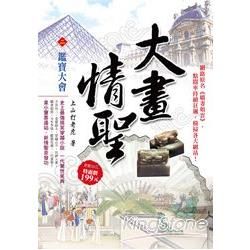史上最強搞笑穿越小說,一代驚世笑典!網路原名《嬌妻如雲》,點閱率持續狂飆,橫掃各大網站!
史上最具藝術天賦的大盜,竟然穿越到了北宋徽宗四年!看一代畫師如何在古今之間大展神威、嬌妻如雲!
當今世上最有前途的職業是什麼?不是醫師律師會計師,竟是畫師?!天才畫師穿越北宋,會發生什麼樣有趣的事?又會把北宋朝廷上下搞得如何天翻地覆?
他是仿造偽畫的高手,也是虜獲女人的情聖。
天下沒有他搞不定的女人,只有他看不上的妹子!
憑著一雙妙手,讓他傲視群鶯,
靠著舌燦蓮花,讓他縱橫花叢!
他是讓所有男人羨慕嫉妒的天才畫師,
也是讓所有女人又愛又恨的獵艷高手!
史上最具藝術天賦的大盜,竟然穿越到了北宋徽宗四年。搖身一變為祈國公府的當差僕役。雖然隱身為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小僕役,沈傲卻憑著他穿越前盜畫偽畫的一手功夫,再加上騙死人不償命的絕佳口才,不僅逐漸成為京城紅人,更欺騙了無數少女的心。看他如何在官場翻雲覆雨,又是如何嬌妻如雲!
雖然身為卑微的小小雜役,沈傲卻憑著他的「專業知識」,將周公子哄得五體投地,心服口服;更逐漸引起老爺夫人的注意與喜愛,除了將他升為書僮之外,更晉升為周夫人的遠房親戚,比周公子更受夫人疼愛。這都是靠著沈傲一張能言善道的口才,以及靈活狡詐的手段所致,誰說做下人沒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