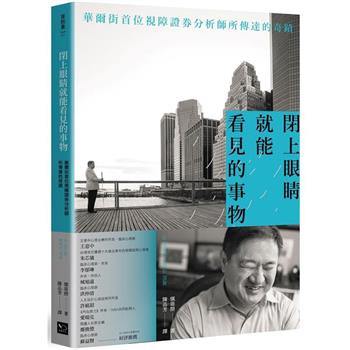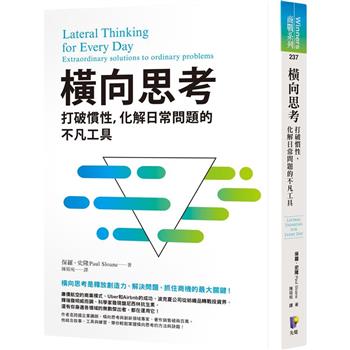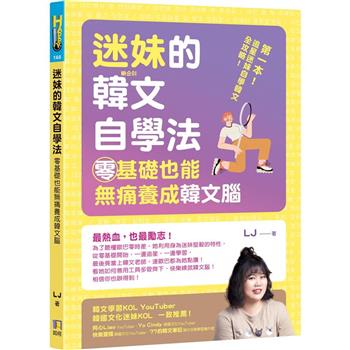天色已經入夜,街頭行人寥落,馬車在長街徐徐而行。任天翔看著外面熟悉的景色,心情十分平靜。見季如風和小薇均面帶憂色,他嘴邊又泛起了那標誌性的無賴式微笑:
「放心,咱們還沒有輸,而且就算是輸,也該學學司馬瑜,輸也要輸得瀟灑大度。」
從窗外收回目光,他對季如風正色道:「對了,蕭傲暗中指使顧心遠留標指路的事,大家暫時裝不知道,待咱們過了眼前難關,回頭再來細查。如果他真有勾結摩門暗算咱們,我想姜伯、顧心遠等兄弟的血,一定不能白流。」
季如風點點頭:「我心中有數,會叫兄弟們莫要打草驚蛇。」
馬車突然停了下來,任天翔從窗外望去,見離大理寺衙門還有好幾條街,他忙問:「怎麼回事?怎麼在這裏停車?」
趕車的任俠低聲答道:「有人攔路。」
任天翔從車中探出頭向前方望去,就見長街中央,一個頭戴方巾、身著長袍的儒生正袖手立在長街正中,剛好攔住了眾人去路。黑暗中看不清他的面目,只能看到他大袖飄飄的剪影,以及斜跨在腰後的那柄三尺長劍。
讀書人很少佩劍,就算佩劍也只是當成飾物,但是眼前這儒生的劍顯然不是飾物,這點就連任天翔這個沒練好武功的門外漢也感覺得出來,所以義安堂眾人不約而同地停了下來。
「喂,麻煩讓一讓!」熊奇走在最前面,見有人攔路,忍不住一聲輕喝,雖然刻意壓低了聲音,依舊渾厚如鐘鳴鼓震。
儒生不亢不卑地對眾人抱拳一禮:「敢問車上可是任天翔任大人?」
任天翔心中微凜,反問道:「先生怎麼稱呼?」
儒生淡淡道:「在下邱厚禮,奉楊相國之命,特請任大人過府一敘。」
任天翔有些茫然,記憶中好像從未聽過這個名字。不過對面的季如風卻是面色微變,任天翔見狀忙問:「季叔知道他?」
季如風微微頷首,低聲道:「儒門有天、地、君、親、師,仁、義、禮、智、信十大劍士,人稱儒門十大名劍,皆出自儒門研武院,江湖上幾乎無人不知。他便是儒門十大名劍中的『禮』,他原本是追隨出身翰林的儒門奸相李林甫,李林甫過世後,又被楊國忠收歸麾下。雖然楊國忠跟儒門沒多大關係,但對他卻頗為看重,已隱然將他視為相國府首席劍士。」
任天翔恍然醒悟,若有所思地點點頭,朗聲問:「任某乃待罪之人,不知相國何事相邀?」
邱厚禮淡淡道:「相爺有心為任大人脫罪,所以特令邱某前來相邀。」
任天翔奇道:「我與楊相國素無交情,相國為何這般好心?俗話說,禮下於人必有所求,不知相爺想要任某拿什麼做交換?」
邱厚禮愣了一愣,大約沒想到任天翔會這麼難纏,不由冷冷道:「相爺只令在下前來相邀,並未有任何說明。你有任何疑問,儘可當面問相爺。」
任天翔心知自己這次被聖上查抄緝拿,多半就是楊國忠使壞,既然如此,那麼看看他究竟打的是什麼主意倒也不壞。這樣一想,他便對一旁的小川和小薇低聲道:
「你們立刻去大理寺找柳少正,就說我正欲到大理寺投案,卻被楊相國請入了相國府,讓他速速帶人前來,免得讓人誤會我是被楊國忠所抓獲。」
二人心知事關重大,皆點頭答應,趁人不備,悄悄從別的路繞道去大理寺。
任天翔知道柳少正是太子殿下的人,不會賣楊家的帳,到時萬一在楊府出了意外,也好有個救兵和證人。安排完這一切,他才對邱厚禮道:「請邱先生前面帶路。」
眾人隨著邱厚禮來到相府,但見巍峨宏大的相國府,在黑暗中顯得尤其肅穆威嚴。義安堂眾人也算見多識廣,待進了相府大門,也不由自主放慢了腳步。就見邱厚禮在二門外停步,回頭對任天翔道:「相爺在內堂相侯,不相干的人請在此留步。」
任俠等人正想爭辯,任天翔忙對眾人笑道:「你們就在這等我吧,想堂堂相國,總不能對我使什麼下三濫的手段吧,這要傳了出去,他這相國的面子可就丟盡了。我這個四品御前侍衛副總管,現在在他眼裏,肯定還不如他的面子重要。」
眾人只得停步,季如風憂心忡忡地任天翔低聲道:「若形勢不對,你就高呼,咱們立刻衝進去救人。」
任天翔笑著點點頭,將身上背著的十多卷古卷交給季如風,這才隨邱厚禮進得二門。直到這時,他才有機會認真打量領路的儒門十大名劍之「禮」。
但見邱厚禮年紀在四旬出頭,面黑微鬚,兩腮無肉,晃眼一看就像個普通儒生,但那雙半開半合的眸子中,偶有精光迸出,尤其他貌似隨意的步伐,輕盈穩定毫不拖遝,無意間暴露出他那經歷過刻苦訓練的下盤功底。
轉過無數道迴廊門扉,邱厚禮終於在一間廳堂外停了下來,在門外輕聲稟報:「任天翔任大人到!」
「進來。」門裏傳出一個慵懶淡然的聲音,透著位高權重者特有的沙啞低沉。
邱厚禮輕輕為任天翔打開房門,然後向他抬手示意。任天翔帶著三分好奇、七分忐忑跨入大門,但見門裏是間寬敞奢華的書房,中堂懸掛著當今天子的御筆親書,兩旁則是顏真卿、吳道子等名家手筆,靠牆的梨花木書櫃,滿滿當當塞滿了厚厚的經典,紅木書案上的精緻玉鼎中,則燃著幽幽的龍涎香……相比這書房低調的奢華,書案後那個年過五旬、面白微鬚的華服男子,倒顯得有些平凡中庸。
任天翔認得他便是權傾天下的楊國忠,忙依官場禮數拜見。就見對方擺手道:「任大人不必多禮,來人,看茶!」
丫鬟奉茶退下後,任天翔不由笑問:「想當初卑職想求見相爺一面而不可得,不知今日相爺為何突然盛情相邀?」
楊國忠將任天翔上下打量了片刻,淡淡道:「任大人死到臨頭還笑得出來,真令人佩服。」
任天翔一聽這話便知是虛言恐嚇,心中反而輕鬆下來,笑問:「相爺何出此言?」
楊國忠微微冷笑道:「你不知聖上為何要緝拿你?」
任天翔不以為然地聳聳肩:「我不過是跟高仙芝將軍有點小誤會,我想聖上自會明察。」
「你倒是很自信啊!」楊國忠微微一笑,「若只是高仙芝要你死也還罷了,現在朔方節度右兵馬使郭子儀上奏朝廷,稱范陽節度使安祿山正秣兵厲馬,已有反意。你與那安祿山交情非淺,而且當初安祿山連夜離京,也正是由你親自送出長安,加上你屢借追查叛將突力的名義,大肆搜刮錢財,這任何一樁罪名,只怕都夠得上抄家殺頭了。」
任天翔心知別的罪名還好辦,唯有親自將安祿山送出長安卻是無法抵賴,要是安祿山真的謀反,自己可就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不過他知道,楊國忠既然這樣說,顯然還不想將自己置於死地,楊國忠這手欲擒故縱的把戲,在他眼裏簡直太小兒科。只是他不能表現得比楊國忠更聰明,便故作害怕地拱手拜道:「卑職還請相爺指點一條生路。」
楊國忠重重嘆了口氣,淡淡道:「本官本不想管這些閒事,是我妹妹韓國夫人求到我這裏,說你還欠著她鉅款,你的景德陶莊若是被查封,也會斷了她一條財路,所以要本官想法救你。只是你的罪名實在太過重大,要想救你實在是千難萬難。」
任天翔心知楊國忠是在趁機坐地起價,卻不知自己有什麼東西能讓這個權傾天下的權相看上,他忙問:「相爺有何差遣請儘管吩咐,若能幫下官渡過眼前難關,下官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也沒什麼大事。」楊國忠貌似隨意地道,「本官是聽說你找到了千年前墨家始祖墨子的陵墓,得到了墓中所藏的墨子遺作,本官一向對各種經典古籍心懷好奇和仰慕,不知能否借本官一閱?」
任天翔聽到這裏終於恍然大悟,原來楊國忠是看上了自己剛到手的墨家古卷,所謂借那是客氣,實則就是強索。他立刻想到,墨家古卷的事如此隱秘,楊國忠怎麼這麼快就知道?而且楊國忠是靠著妹妹的恩寵一步登天,並非真是由儒門出身,按說他對任何古書典籍的興趣,決不會超過金銀珠寶,怎麼會拐彎抹角向自己要這個?除非……
任天翔心中漸漸明瞭起來,楊國忠不是為自己,而是為別人在要,只是不知他身後的人是誰,又是從哪裡得知自己手中有墨家古卷。
只可惜墨家古卷已經讓任天翔掉了包,沒法用它來賄賂楊國忠,而且就算是有,任天翔也不願將義安堂眾人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墨家至寶,拱手獻給面前這奸相。他只得推諉道:
「這墨家古卷非我個人之物,卑職無權做主,相爺若要借閱,我得跟大家商量後再做決定。」
楊國忠權傾天下,還從來沒人敢當面拒絕他,聞言不禁臉色一沉,不冷不熱地道:「任大人要想清楚,你如今已是命懸一線、九死一生。若本相肯幫你,或可化險為夷;如本相要落井下石,只怕神仙也救不了你。」
面對楊國忠赤裸裸的威脅,任天翔心中反而湧出一種不服的倔傲之氣,對楊國忠拱手一拜:「多謝相爺好意,只是任某這條賤命,跟墨家古卷比起來實在微不足道,所以只好聽天由命了。」說完起身告退,再不停留。
在門外守衛的邱厚禮正要阻攔,卻聽楊國忠一聲輕喝:「讓他走!」邱厚禮只得收回手,示意內侍將任天翔送出去。
待任天翔離開後,楊國忠對邱厚禮低聲吩咐:「去將本相要的東西拿回來,不過不能在相府動手,更不能讓人知道是本相所為。」
邱厚禮心領神會地點點頭,拱手一拜:「相爺放心,小人知道該怎麼做。」
出得相府,任天翔依舊照原計劃趕往大理寺。
馬車走出三個街口,突聽兩旁的房檐上有夜行人輕盈的腳步,如狸貓般細微。眾人立刻暗自戒備,將馬車拱衛在中間,靜觀事態發展。
任天翔也聽到了外面的異動,不由一聲輕嘆:「沒想到楊國忠為了這古卷,竟然不惜冒險。我真不想再有人為這古卷送命,他若真要苦苦相逼,我只好將古卷全都燒掉,以免落到別有用心的人手中。」
季如風忙道:「公子不用擔心,這點蟊賊未必能攔住咱們。」說著,他探頭向車窗外略一示意,立刻有兩個墨士躍上兩旁的屋簷,片刻後,就聽屋簷上傳來一兩聲短促的驚呼,幾個黑衣蒙面人已從屋簷上摔了下來。跟著屋簷上傳來兩聲口哨,季如風立刻對任俠吩咐「走!」任俠抬手揚鞭,馬車立刻加速。
就聽黑暗中傳來稀疏的箭羽破空聲,卻都被守衛在馬車兩旁的杜剛等人撩開,眼看大理寺衙門遙遙在望,突見前方黑暗中奔出一道衣衫飄忽的灰影,速度快得驚人。
熊奇在馬車前方開路,見狀一聲大吼,戰斧猶如車輪橫掃而出,幾乎封住了半條街。就見那灰影隨著戰斧的來勢突然向後折倒,身形幾乎是貼著地面避過了戰斧迎面一擊,並借慣性滑過熊奇的堵截衝到了馬車面前。
任俠見狀,急忙拔劍在手,就見對方身形半跪,手中長劍斜刺而出,正中急速奔行的馬腿,且剛好是膝蓋位置。兩匹拉車的健馬突然前腿失力,一下子摔倒在地,令馬車也隨之傾側翻覆。而他則就勢仰倒,貼著地面從兩匹健馬中間穿入車底,趁馬車越過頭頂的瞬間突然揚劍上刺,長劍刺穿馬車下方的板壁,直達車廂後部,那裏正是任天翔所坐的位置。
就在長劍穿透馬車下方箱板的瞬間,季如風已拉著任天翔跳出馬車,剛好避過了致命一劍。二人回頭望去,就見馬車後半部轟然解體,一個灰衣人正從馬車碎片中傲然站起。灰衣人雖有白巾蒙面,但其眼神和服飾,已經暴露了他的身分。
「好!儒門十大名劍,果然名不虛傳。」季如風一聲讚嘆,跟著又搖頭嘆息,「只可惜儒門也算名門正派,為人做事一向自詡正大光明,不知何時出了你這種藏頭露尾的小人?趨炎附勢也就罷了,居然還幹出蒙面偷襲的下三濫勾當。」
灰衣人似乎對自己的失手有點意外,頷首道:「想不到義安堂還有些人才,居然能識破我這一劍,佩服。」他略微頓了頓,「我蒙面並非是要隱瞞身分,而是不想多造殺戮。你們若裝著沒有認出我是誰,我拿到想要的東西後還會放你們一馬,但你們偏要自以為聰明,我只好將你們全部滅口。」
季如風聞言,不禁嘿嘿笑道:「閣下好大的口氣,真不愧出身天下第一名門。只可惜就憑你這種蒙面偷襲的勾當,要想將咱們全部滅口,只怕是在癡人說夢。」
「閣下劍法超群,在下有心領教。」任俠持劍遙指灰衣人後心,眼中閃爍著隱約的渴望。方才他低估了灰衣人的膽色和武功,結果讓灰衣人貼地鑽入馬車下,差點釀成大錯,所以很想找回顏面。
灰衣人淡淡一笑:「憑我自己或許不成,不過我已令人封鎖了這條街,上百名武士早已嚴陣以待,就等我一聲令下,你們自信能從上百名精銳武士包圍下安然脫身?」
話音剛落,就見長街兩頭亮起了無數燈籠火把,無數黑衣蒙面人正手執兵刃嚴陣以待,就連兩旁屋簷之上,也有武士分頭把守,將義安堂眾人圍了個水泄不通。
他們人數雖眾卻鴉雀無聲,紋絲不動,顯然是經過嚴格訓練的精銳武士,非尋常江湖草莽可比。
義安堂眾人見狀不禁面面相符覷,雖然他們不懼惡戰,但他們怎麼也沒想到,在堂堂大唐帝都,有人竟敢出動上百武士公然搶劫,而且其中還包括邱厚禮這等儒門一流高手。
「上天有好生之德,本門也一向是以仁義為先。」邱厚禮故作憐憫地嘆了口氣,「所以我願意對你們網開一面,只要留下我要的東西,並裝著沒有認出在下,我可以讓你們平安離開。」
此言一出,幾個墨士修養再好也忍不住哈哈大笑。
任天翔越眾而出,示意大家安靜,然後將十多卷古卷擱到地上,對邱厚禮嘆道:「你們煞費苦心,無非就是為了我這十多卷墨家古卷。想墨子生前最崇尚和平,若知他留下的典籍竟成為世人爭奪的寶貝,已有無數人為它流血甚至喪命,墨子一定會非常後悔。既然如此,不如就由我來替墨子將它們全都燒毀,以絕世人貪念。」
任天翔說著拿出火絨點燃,作勢要往那些古卷上點去。邱厚禮神情頓時緊張起來,卻故作輕鬆地冷笑道:「你少用這一套來要脅,我不信你真會將它燒毀,你將它獻給相爺,好歹還能救你的性命,我不信你連命都不要。」
任天翔微微一笑:「我任天翔怕這怕哪,就是不怕別人威脅。既然你不信,我只好燒給你看看。」說著,他已將火絨湊到那些古卷之上,浸透了防水油脂的古卷遇火即燃,一下子便燒了起來。
「住手!」邱厚禮一聲大吼,沒想到任天翔真會點火,情急之下急忙仗劍衝來,想要撲滅火焰。誰知身形方動,一旁虎視眈眈的任俠已一聲輕喝,劍鋒直指邱厚禮必經之路。若他真要前衝,必躲不過任俠蓄勢而發的一劍。
「放肆!」邱厚禮擰身出劍,想要逼退任俠擺脫糾纏,誰知任俠像是看透了他的心思,搶先變招,劍勢延綿不絕將他纏了個結實。邱厚禮情急之下竟脫身不得,不禁一聲高喝,「快搶古卷!」
早已嚴陣以待上百武士,應聲撲向燃燒的古卷。任天翔見狀,急忙高呼:「嚴守!莫讓古卷落到他們手中!」
義安堂眾人立刻圍在任天翔周圍,阻止眾武士靠近。
他們武功比那些武士高出一大截,雖然以寡敵眾,難以從眾人包圍下突圍而出,但守衛任天翔和燃燒的古卷還是綽綽有餘。眾武士雖然奮勇爭先,奈何地方狹小擠在一起,難以發揮人多的優勢,只能眼睜睜看著那些古卷,漸漸變成了一堆熊熊的篝火。
邱厚禮幾次想要衝過去搶救古卷,卻怎麼也擺脫不了任俠的糾纏,他心中殺意頓起,不再理會那些古卷,回身專心對付任俠。
如此一來,儒門研武院十大名劍的實力便真正體現出來,但見他的劍速雖不及任俠快,卻能先一步預判任俠的劍路,先一步封住任俠出手的線路和角度,步步強佔先機,十餘招後任俠的劍勢就開始顯出一絲忙亂,不復先前的神勇迅疾。
「你死定了!」邱厚禮眼中寒意暴閃,嘴邊泛起了勝券在握的冷笑,手中長劍源源不斷地攻擊,逼得任俠連連後退。
二人實力其實相差極微,但臨敵經驗上卻是天差地遠。墨士因門派的原因,很少有機會與江湖上實力相當的對手正面過招;而儒門研武院卻是各派高手研武交流之所,比起墨門的閉門造車來,儒門劍士有更多實戰的機會。
眼看任俠就要落敗,突聽任天翔一聲高呼:「住手!」
雖然任天翔音量不高,中氣更不能與內氣充沛的高手相提並論,但他那種從容不迫的氣度,還是令眾人不約而同停了下來。
就見他指著那堆已經快燃成灰燼的羊皮古卷,對邱厚禮笑道:「別搶了,古卷我給你們。」說著向後退開,義安堂眾人也隨之後退,將那堆已經燒得不成形狀的古卷留給了對手。
邱厚禮兩步急衝上前,不顧烈焰的灼燒搶出一卷古卷,但見羊皮古卷早已燒焦,哪還看得清其上的字跡?他一掃先前的儒士風度,氣急敗壞地將燒焦的古卷一扔,從齒縫間迸出個殺氣凜冽的字——殺!
上百名武士緩緩向前逼近,將義安堂眾人圍了個水泄不通。義安堂眾人武功雖比這些武士氣高出一大截,但因為要保護不會武功的任天翔,不敢放手突圍,因此被眾武士逼到長街一角,形勢十分危急。還好眾武士在先前的搏殺中,已經領教了幾名墨士的殺傷力,沒人再敢搶先出手,雙方一時僵持不下。
邱厚禮見狀,不由踢開幾個畏縮不前的手下,正待率先出手,突聽後方傳來急促的馬蹄聲,跟著是有人急切的高呼:「住手!」
眾人回頭望去,就見一隊衙役正縱馬疾馳而來,領頭是個不到三旬的年輕官吏,看服飾應是大理寺少卿。
眾武士見是官兵,不約而同讓開一條路,就見數十名衙役直奔到戰場中央,將義安堂眾人與眾武士隔離開來。就聽領頭的大理寺少卿一聲斷喝:「哪裡來的盜賊,竟敢在京城聚眾鬥毆?還不快退下?」
眾武士雖然出身相府,但這次是蒙面行動,見不得光,如今見有大理寺的人插手,便都萌生退意。不過邱厚禮胸中憋著股怒氣,加上一向在相府當差,見慣了一二品大員,哪裡會將一個小小的大理寺少卿放在眼裏?
面對大理寺少卿的呵斥,他冷冷道:「別多管閒事,不然連你一起殺。」
敢對朝廷命官當面威脅,而且是在這京師重地,這令一向自大慣了的大理寺衙役都吃了一驚,眼看周圍黑壓壓全是黑衣蒙面人,面對官府也全然無懼,眾衙役哪見過這陣仗,心裏都是一陣發虛,不約而同向後退縮,顯然已在做逃命的打算。
邱厚禮看出了眾衙役的心虛,不由冷哼道:「我數三聲,誰再敢阻我,一律格殺勿論。」
就在這時,突聽後方傳來一個淡然冷定的聲音:「誰這麼大膽,竟然公然威脅朝廷命官?」
眾人循聲望去,就見長街那頭緩緩馳來一人一騎,騎手青衫飄忽,身形雋秀,面目清奇俊朗,看年紀不過三旬出頭,卻有著一種飄然出塵的淡泊寧靜,更有一種揮斥方遒的豪邁和自負。這兩種氣質竟和諧的出現在同一個人身上,實在是極其罕見。
眾武士雖然不識,卻也被其氣勢所懾,不約而同讓開了一條路。就見他緩緩控馬來到對峙雙方的中央,這才在眾目睽睽之下勒馬停步。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智梟(6):義璧重圓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智梟(6):義璧重圓
從大秦時代就散落四方的義璧,在有心人士及任天翔的努力追查下,終於一塊塊逐漸找了回來。 沒想到,這塊義璧不僅關係到義門一派的未來發展, 亦是開啟墨門經典的關鍵門鑰。 其中更涉及到了任天翔的身世之謎。 究竟任天翔能否贏得義門眾人的認同, 重新得到義門門主的地位?
而身分神秘的如意夫人又是誰? 他與任天翔又有什麼關係? 他又是否能找到墨子墓,並尋回墨子著作精義?
在義安堂智囊季如風指點下,任天翔終於知道父親當年的追求與夢想,原來義安堂正是義門最重要的一支,義門就是當年墨子傳下的墨門,因遭歷代官府鎮壓不得不隱藏真正的身份,成為以義為號的遊俠。 任天翔終於繼承父親的遺志,踏上了成為墨家钜子之路。義安堂中,他揭破魔門吞併義門之陰謀,在季如風等人幫助下,成為義門新一代钜子。 集齊七塊字璧,任天翔率墨門十三士,踏上了尋找墨家祖師墨子之墓的旅途。不想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司馬瑜、魔門紛紛尾隨而來,加入到墨家寶藏的爭奪中。
作者簡介:
方白羽,原為中規中矩的電子工程師,一時興起抱著玩票心態在網路寫作,意外引發廣大迴響,方白羽的名號頓時響徹雲霄,並開始為武俠和奇幻雜誌撰稿,成為一名專業寫手,至今已出版超過四百萬字的奇幻和武俠作品。
章節試閱
天色已經入夜,街頭行人寥落,馬車在長街徐徐而行。任天翔看著外面熟悉的景色,心情十分平靜。見季如風和小薇均面帶憂色,他嘴邊又泛起了那標誌性的無賴式微笑:
「放心,咱們還沒有輸,而且就算是輸,也該學學司馬瑜,輸也要輸得瀟灑大度。」
從窗外收回目光,他對季如風正色道:「對了,蕭傲暗中指使顧心遠留標指路的事,大家暫時裝不知道,待咱們過了眼前難關,回頭再來細查。如果他真有勾結摩門暗算咱們,我想姜伯、顧心遠等兄弟的血,一定不能白流。」
季如風點點頭:「我心中有數,會叫兄弟們莫要打草驚蛇。」
馬車突然停了下來...
「放心,咱們還沒有輸,而且就算是輸,也該學學司馬瑜,輸也要輸得瀟灑大度。」
從窗外收回目光,他對季如風正色道:「對了,蕭傲暗中指使顧心遠留標指路的事,大家暫時裝不知道,待咱們過了眼前難關,回頭再來細查。如果他真有勾結摩門暗算咱們,我想姜伯、顧心遠等兄弟的血,一定不能白流。」
季如風點點頭:「我心中有數,會叫兄弟們莫要打草驚蛇。」
馬車突然停了下來...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方白羽
- 出版社: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3-21 ISBN/ISSN:978986580367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開數:25開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武俠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