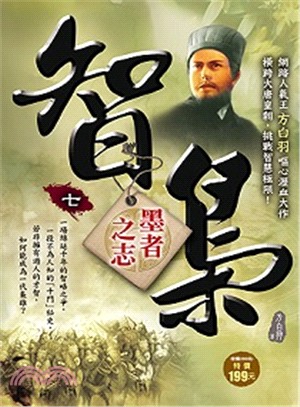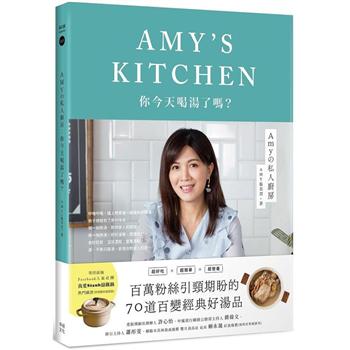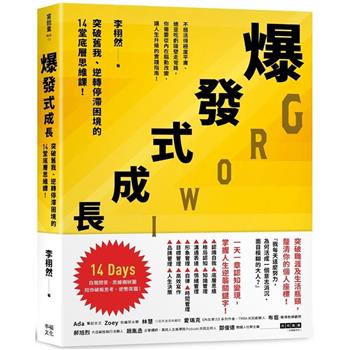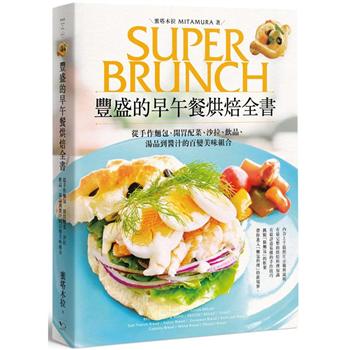朔風獵獵,捲起漫天風沙,模糊了遠方天地的界限,也讓天宇變得如大地一樣暗淡昏黃。這就是朔方,戈壁與黃沙交替出現的廣袤世界,偶爾的一片翠色綠洲,則如仙人遺落凡間的寶石一樣珍稀。
已經逃離蓬山三天半,憑著辛乙所給的那面通關腰牌,任天翔等人終於通過范陽最後一道關卡,進入漠北無人區。
這三天以來,一行人馬不停蹄夜不曾眠,總算搶在范陽的封鎖令到達之前逃離險地,眾人早已精疲力竭,人疲馬乏,就連一路都在懇求、威脅、央告的安祿山,現在也因饑渴困乏,無奈而疲憊地閉上了嘴。
就在這時,他們看到了立在沙丘之上那一根骷髏頭的細長藤杖,就像是從天而降的魔物,突兀地出現在漫漫黃塵之中,煥發著一種詭異而妖魅的氣息。
安祿山本已絕望的眼神,陡然間煥發出希望之光,掙扎著想要呼喊,誰知這幾天來不眠不休的奔波勞頓,加上前所未有的擔憂和驚嚇,已使他的嗓子徹底嘶啞,只能發出一種類似野獸般的嘶鳴。
任天翔扳過他的頭問:「你認識那根哭喪棒?什麼來歷?」
安祿山的嘴在張合,發出一種近乎耳語般的嘶啞聲。雖然聽不清他在說什麼,但從口型,任天翔讀懂了他的意思——你們死定了,一個也跑不了。
任天翔一聲冷哼:「我們就是死,也必定先殺了你,所以你最好別得意的太早。」
安祿山臉上一陣陰晴不定,跟著又努力張合著嘴唇,用「啞語」告訴任天翔——放了我,我讓他放你們走。咱們無冤無仇,何必為了李隆基那個昏君一道沒來由的口諭,拼個兩敗俱傷,魚死網破?
「少廢話,他究竟是誰?」任天翔說著拿出水袋,揚起脖子灌了一大口,見安祿山兩眼放光直舔嘴唇,他靈機一動,把水袋湊到他嘴邊,稍稍潤了潤安祿山乾裂的嘴唇,然後再問,「告訴我他是誰?說了給你水喝。」
渴極的人喝到一口水,反而感覺更渴。安祿山略一遲疑,努力發出了一點聲音:「那是薩滿教第一上師,月魔蒼魅的隨身法器,人稱白骨骷髏杖,它出現的地方意味著死亡,死亡,還是死亡。」
「月魔蒼魅?」任天翔皺起眉頭,「聽名號倒是挺唬人,白骨骷髏杖?骷髏我看到了,白骨又在哪裡?」
話音未落,任天翔就突然住口,因為他終於看到了白骨。藤杖頂端那個只有拳頭大小的白色骷髏,原本以為是由藤蔓雕刻而成,直到現在任天翔才看清,那是一個嬰兒的頭骨,不知經過怎樣的處理,已與藤杖結成了一體。
「放了我吧。」看到任天翔勃然變色,安祿山頓時多了幾分信心,綿裏藏針地威脅道,「月魔蒼魅是北方薩滿教第一嗜血殺神,就連家母對他也畏懼三分。趁他還未現身,你們放了我快走,我會求他放過你們。」
「閉嘴!」任天翔一面觀察著藤杖周圍的情形,一面向小薇示意,讓她看好安祿山。雖然他還沒有看到任何人影,但那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覺,卻已經清晰地出現在了周圍。
不用任天翔吩咐,杜剛、任俠、小川三人已握住兵刃緩緩逼近那根骷髏杖。杜剛率先喝道:「什麼人在故弄玄虛?有本事現身出來!」
四周中除了嗚嗚的風聲,就只有漫天飛舞的黃沙。眾人等了半晌不見動靜,心弦正待放鬆,突聽任天翔一聲輕呼:「留意腳下!」
話音剛落,就見杜剛腳下的黃沙突然揚起,一道黑影從浮沙中沖天而出。
幸虧杜剛先聽到任天翔的提醒,稍微提前了剎那跳開了半步,但終究未能避過突如其來的連環閃擊,勉強以唐手護住了下陰要害,小腿及腹部卻被由下而上的快拳連環擊中,頓時像個稻草人般跌出了數丈。
那黑影還想趁勝追擊,卻聽後方風聲微動,一柄快劍已經悄然刺到,速度驚人。
那黑影沒有回頭,鬼魅般倏然向前疾行三步,以他往日經驗,三步之內就能避開後方任何偷襲,但不曾想腦後那劍速度驚人,一劍落空緊接著又是一劍刺出,每一刺之間連綿不絕,幾無空隙,逼得他一連奔出十餘步,直到拔出黃沙中的骷髏杖反手回擊,才總算逼得對方回劍相格。
就聽「叮」一聲輕響,黑影已順勢回頭,脫口讚了聲:「好劍法!」
任俠收劍而立,心中暗自吃驚,他方才趁對方襲擊杜剛時悄然出手,以他出劍的速度加上又是由後方偷襲,這種情形下依然被對方躲開,那對方豈不是比自己更為迅速?任俠長這麼大,還從來沒遇到過比自己更快的人,心中震驚可想而知。
風勢漸弱,漫天的沙塵稍稍稀薄了一點,但見塵土飛揚的朔風之中,一個長髮披肩、黑衣如魅的老者手執藤杖蕭然而立,風沙拂動著他的衣袂,使他的身影看起來就像是一道不真實的幻影。
老者渾身瘦削無肉,臉上更是枯萎乾癟得就像一層黑皮包裹著的骷髏,加上手中所執那條白骨骷髏杖,讓他看起來就如同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妖魔。
「月魔蒼魅?」任天翔明知故問,同時以「心術」在不斷觀察判斷眼前這個可怕的對手。方才若非他先一步發現杜剛腳下沙土中那微不可察的異動,只怕杜剛已遭毒手。
老者微微頷首,沒有理會與之對峙的任俠,卻仔細打量了任天翔一眼,蕭然道:「既知是老夫,還不快逃命?」
老者帶有明顯的異族口音,聽著讓人忍不住發笑。但現在沒有一個人笑得出來,方才他雖是占了偷襲之利,但轉瞬間傷杜剛、擊退任俠,已證明他的武功明顯比二人高出一籌,這對極其自負的墨門墨士級高手來說,簡直是難以想像的遭遇。
「其實你並沒有把握殺了咱們,又何必故作自信?」
任天翔突然笑了起來,他已經看到了老者自己都未意識到的隱思,「你要真的有十足的把握,又何必藏在沙中,以那根哭喪棒吸引咱們目光,卻乘機從沙中偷襲。」任天翔長長嘆了口氣:「你的武功已經極高,只可惜膽子卻越來越小,你方才若是膽子稍微大一點點,出手更乾脆決絕一點,我就算再開口提醒,只怕也救不了同伴的性命。」
杜剛已被小川扶了起來,他的小腿雖然傷得不輕,卻還能穩穩站立。就見他對月魔怒目而視,心有不甘地挑戰道:「出手偷襲,算什麼本事?咱們再來!」
蒼魅眼中閃過一絲驚詫,跟著嘿嘿一笑:「既然說我膽小,那你們就一起上吧,看能不能嚇走老夫。」
雖然方才蒼魅出手很快,但任天翔依然看清了他的出手軌跡,並從中發現了他可能的弱點。聽他出言挑戰,任天翔忙對任俠低聲道:「這骷髏頭最怕受傷,出手總是留有餘力,也許這就是他最大的弱點。」
任俠心領神會地點點頭,突然一劍直擊蒼魅握杖的手。他不攻其要害卻只攻其手,那是因為對方速度太快,若不搶先限制其兵刃的發揮,只怕就沒有任何機會。
蒼魅果然收杖後退,身形越來越快,任俠經長途跋涉,早已精疲力竭,方才勉力出劍,已經耗盡了他大半力量,再追不上蒼魅迅若鬼魅的身形。
他腳步剛緩下來,蒼魅立刻返身殺回,骷髏杖直點任俠頭頂。那骷髏不知經過怎樣的處理,任俠連擋兩劍也沒損骷髏分毫,反而被骷髏震得手臂發麻,胸口血氣上湧,已然有體虛脫力的跡象。
任天翔看出任俠力竭,急忙出言指點:「退!兌位!」
兌位是八卦方位,練過武的中原人大多知道。任俠立刻往身後兌位退去,就見蒼魅杖勢大盛,鋪天蓋地追擊而來。二人一進一退十餘步,任俠左支右絀十分狼狽,而蒼魅杖勢卻越來越快,令任俠越來越難以招架。
就在這時,突聽任天翔陡然一聲厲喝:「斷喉刺!霹靂斬!」
斷喉刺是忍劍中的招數,而霹靂斬卻是唐手中的霸道殺著,這根本不可能同時使出來。不過任俠已對任天翔有了完全的信賴,毫不猶豫一劍刺出,目標直指蒼魅咽喉,正是忍劍中凌厲無匹的「斷喉刺」。
這一劍不留後路,完全是兩敗俱傷的打法,令蒼魅也不得不後退避讓,不過他在後退之時也不忘出招反擊,骷髏杖當頭下擊,任俠雖避開了頭頂要害,但肩上依舊吃了一記重擊,一個踉蹌差點跪倒。
幾乎同時,就聽杜剛一聲斷喝,一掌暴然擊出,正是唐手中的霹靂斬!
原來蒼魅被任俠的斷喉刺逼得後退之時,剛好退到杜剛的攻擊範圍內,杜剛雖然小腿已傷,行動不便,不過手上卻沒問題,這一掌蓄勢已久,隱然有開碑裂石之力。
蒼魅吃了一驚,急切間來不及避讓,只得沉肩硬受了杜剛一擊,一個踉蹌差點摔倒,黑漆漆的臉上泛起一陣紅潮。杜剛一招得手正要趁勝追擊,無奈腳下不給力,終究還是慢了一步,眼睜睜看著蒼魅從容退到三丈之外。
「好拳法!」蒼魅嘿嘿一笑,臉上紅潮漸漸褪去。
雖然那一記霹靂斬打得他氣血翻滾,差點嘔血當場,但憑他深厚的功力,稍一調息便無大礙。他將目光轉向了任天翔,他已然看出任天翔對他的威脅顯然不比杜剛和任俠小,這個貌似紈褲的傢伙,有一雙毒辣無比的眼睛,竟能從變幻莫測的戰場上,發現那轉瞬即失的機會,這小子究竟是人是鬼?
見蒼魅片刻間便若無其事,任天翔暗叫一聲可惜。遙見蒼魅深邃的眼窩中射出的寒光,他立刻猜到了對方下一步的企圖。但對方速度實在太快,不等他呼救,那柄骷髏杖已如閃電刺到,這一次是鋒銳如槍的杖柄,顯然是要一擊致命。
任天翔眼睜睜看著寒光閃閃的杖柄向自己心臟刺到,甚至能猜到它後續的可能變化,但身體卻來不及做出任何反應。他的目速、腦速雖然遠勝常人,奈何身體跟不上大腦的速度,只能眼睜睜看著杖柄刺來。
就在這時,突見一人挺身擋在了任天翔身前,剛好迎上了刺到的杖柄。就在杖柄刺中他肩胛的同時,他腰間的短劍也嗆然出鞘,順勢上撩,這一劍之迅捷突兀,已然超過任俠方才最快那一劍。饒是蒼魅留有後力也避之不及,只得拼盡全力暴然收腹,硬是將胸腹生生縮回一寸,就見這一劍由下而上,從蒼魅肚子到胸腹一劃而過,衣衫應聲而裂,乾瘦的胸腹上現出了一道細細的紅線。
蒼魅一聲痛叫,身形一晃暴然後退,再顧不得傷人,捂著胸口踉蹌而走。他已經有數十年未受過刀劍傷,對手的悍勇無畏令他再不敢戀戰,匆忙落荒而逃。
眾人驚訝地望向一劍重傷蒼魅的同伴,卻是一直守在任天翔身邊的小川流雲。
方才蒼魅與杜剛任俠惡戰之時,他不僅未曾出手相助,還藏起了自己胸中的殺氣,因此讓蒼魅錯誤地低估了他的實力。沒想到最後關頭他不僅替任天翔擋了一刺,而且還有餘力拔劍反擊,這隱然有墨家死劍之意,卻又沒有死劍之絕決。
「這是忍劍。」像是回答同伴疑問的目光,小川勉強笑了笑,話音未落,他身子就是一晃,差點軟倒在地。就見他肩胛上血流如注,頃刻間便濡濕了半幅衣衫,方才那一刺已將他肩胛洞穿,在他的肩頭留下一個血洞。
任俠連忙過去將他扶住,撕下衣衫為他包紮,然後將他緩緩放倒在地。
就在這時,突聽杜剛一聲驚呼,目瞪口呆地望著小川身後的任天翔,那神情將任天翔嚇了一跳。跟著他便感到胸口劇痛,低頭一看,就見胸前有血跡慢慢浸出,轉眼間便濡濕了一大片衣衫,任天翔不禁一聲驚叫,兩眼一黑軟倒在地——蒼魅那一刺,不光穿透了小川流雲肩胛,也刺中了他身後的任天翔。
幾個人一聲驚呼,急忙上前查看任天翔傷勢。
就在這混亂之時,被反綁雙手捆在馬鞍上的安祿山,突然低頭將身旁看守他的小薇撞下馬去,跟著猛踢馬腹,那馬吃痛不過,猛地將韁繩從小薇手中掙脫,一聲嘶叫放蹄飛奔。幾個人擔心任天翔傷勢,哪有心思追擊,片刻間,那匹馬便馱著安祿山消失在大漠深處。
「沒事沒事,公子沒事!」任俠手忙腳亂地解開任天翔衣衫,頓時舒了口長氣。就見那傷口雖然正在心臟要害,但入肉不到半寸,連肋骨都未刺穿。幾個人驚魂稍定,連忙為他止血療傷,然後將水噴到他臉上,總算令他醒了過來。
任天翔方才只是受了驚嚇,加上旅途勞頓極度虛弱,這才突然暈倒。見眾人都圍著自己,小薇在一旁更是淚水漣漣,一臉害怕,他茫然問:「我……我方才好像受傷了?」
「只是皮外傷,不算要緊。」杜剛忙寬慰道,「倒是小川傷得極重,得趕緊找大夫救治。」
任天翔想起方才那一幕,急忙查看小川傷勢,見他傷得不輕,任天翔不禁澀聲道:「你……又救了我一命!」
小川勉強一笑:「是你送我的墨家典籍救了咱們,不然咱們今日都逃不過月魔的魔掌。」
任天翔又驚又喜:「想不到那劍譜還真有奇效,你初學乍練,功力就如此迅速提高?你以前劍法顯然不及任俠他們,但現在只怕已與他們不相伯仲,甚至更勝一籌。」說著,他轉向任俠和杜剛,「我會將這些劍法都傳給你們,墨門得祖師遺作之助,必能更上一層。」
掙扎著站起身來,抬眼望向四周,突然發現安祿山已不見蹤影,任天翔心神大亂,失聲驚呼:「安祿山呢?」
眾人面面相覷,最後還是小薇期期艾艾地道:「方才大家見你受傷,都擔心你傷勢,沒顧上安祿山,結果讓他逃了。」
任天翔一愣,急忙問:「逃了多久?」
「逃了好一會兒,往那個方向。」小薇說著往前方一指,見任天翔呆若木雞,她不禁小聲建議道,「要不咱們再追,也許還能追上。」
「還追個屁啊!」任天翔仰天長嘆,「茫茫大漠,風沙漫天,百丈之外就看不見人影,咱們往哪裡去追?功虧一簣,功虧一簣啊!」
一騎健馬吃力地奔行在漫漫黃沙之中,這裏已經遠離風口,但見前方天地分明,地平線盡頭甚至能看到隱約的城郭。安祿山疲憊已極的眼眸中閃過一絲狂喜,不顧坐騎已口吐白沫,拼命踢其肚腹,驅使牠加快了速度。
雖然雙手被縛,但從小就在馬背上長大的他,用嘴叼著韁繩也能將馬操控自如。遙見前方漫漫黃沙之中,似有幾個黑點正排成一線,向自己這邊搜索過來,安祿山先是一驚,忙將自己隱到一座沙丘之後,足足等了小半個時辰,直到看清那些騎手的服飾,他才興奮地縱馬迎上前,拼盡全力高呼:「這裏!本將軍在這裏!」
幾名騎手立刻加快速度縱馬馳來,雖然隔得極遠,其中一人那脖子上的紅巾也已經十分顯眼。安祿山縱馬迎上前,放聲高呼:「阿乙救我!」
幾名騎手來到近前,最前方果然是辛丑辛乙兄弟。
終於見到自己人,安祿山不禁淚如泉湧,一顆懸著的心終於落地。他將手伸給辛乙,正待令他給自己鬆綁,誰知辛乙卻冷冷望著自己,突然莫名其妙地來了句:
「將軍,勃律爾部落所有冤魂,托我向將軍問好。」
安祿山一怔,眼中如見鬼魅,滿臉更有恐懼之色,這沒有逃過辛乙的眼睛。就見他縱馬上前,短刀凌空而出,猶如一道閃電從安祿山喉間一劃而過。鮮血頓如湧泉噴薄而出,跟著安祿山那肥碩的身體從馬鞍上栽了下來,「砰」地一聲激起一片黃塵,將沙土也砸出個大坑。
「你瘋了?」辛丑被兄弟的舉動驚得目瞪口呆。
就見辛乙若無其事地道:「我沒瘋,這根本就不是將軍,不信你們仔細看看。」
安祿山被任天翔等人剃去髯鬚化過妝,面目確實與原來迥異。幾名緊隨而來的武士將信將疑地來到安祿山近前,翻身下馬上前仔細查看,誰知辛乙這時突然向幾個人出手,幾名武士猝不及防,頃刻間全部栽倒,全是要害中刀。
「你……」辛丑瞠目結舌,本能地拔出長劍,卻又不知該不該向兄弟出手。
辛乙緩緩收起短刀,淡淡道:「大哥別害怕,我沒有瘋。因為我已知道安祿山並不是咱們的救命恩人,而是屠滅咱們整個部落的大仇人。二十多年前,他滅掉了契丹勃律爾部,只留下不懂事的孩子以補充自己部落人口。咱們兄弟僥倖活了下來,並憑著苦練而成的武功成為他的衛士,又因為比狗還要忠誠,得到了他最大的信任。他也許已經忘了咱們是契丹勃律爾部後裔,但是我卻決不會忘。」
「你怎麼知道自己是勃律爾部後裔?」辛丑質問。
辛乙解開衣衫,露出胸口那個隱約的狼頭刺青,緩緩道:「每一個勃律爾的男孩,一出生就會刺上部落的標誌,別跟我說你沒有。」
辛丑解開衣衫低頭望去,胸口果然有隱約的刺青,雖然已經極淡,但依然能看出那是一個狼頭。他疑惑地抬起頭,吃驚地問:「你怎麼知道這些?」
「因為我識字了。」辛乙臉上泛起一絲驕傲,「他只讓搶來的外族孩子學武,卻從不讓人教他們讀書識字,就是要他們永遠做一隻不知身世來歷的狗。幸虧我遇到了一位恩人和明師,才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來歷和血海深仇。今日大仇得報,咱們的族人九泉之下也可以安息了。」
辛丑聽兄弟說得有根有據,疑慮漸消。看看地上那些屍體,再看看自己兄弟,他不安地問:「將軍已死,咱們回去怎麼交代?」
「大哥不必擔心,你一切聽我的便是。」辛乙說著,將安祿山的屍體橫放到馬鞍上,然後跳上自己坐騎,縱馬往東而去。辛丑猶豫了一下,也打馬追了上去。
「爹——」
當看到安祿山的屍體時,安慶緒不禁嚎啕大哭,拜倒在地。
安秀貞更是渾身一軟差點摔倒。司馬瑜連忙將她扶住,低聲對安慶緒道:「少將軍節哀,現在不是哭的時候。」
安慶緒一躍而起,咬牙切齒喝問:「是誰?誰幹的?」
一名在蓬山被迷藥放倒的侍衛戰慄道:「一定是朝廷派出的密使任天翔,他以陰謀詭計迷倒咱們幾個兄弟,將大將軍秘密抓走。他知道帶著大將軍逃不掉,所以才下此毒手。」
「你們身為大將軍貼身護衛,竟然讓人在眼皮底下將大將軍抓走,還有何面目活在世上?」安慶緒說著一聲低喝,「來人!」
一名目光陰騺的將領應聲而入,安慶緒一揮手:「拉出去砍了!」
那將領一聲低喝,幾名親兵應聲而入,拉起跪在帳前的幾個侍衛就走。幾名安祿山的侍衛拼命掙扎哀求,卻不敢反抗,他們早已像狗一樣養成了對主子絕對服從的習慣,就是斧鉞加身也不知反抗。
直到幾名侍衛的哀求呼叫戛然而止,安慶緒才臉色鐵青地轉向辛乙。這契丹少年連忙拜倒,小聲稟報:「小人一路追蹤來到前方沙漠,發現了幾具屍體,除了幾個是先一步追來的同伴,其中竟有一具屍體身材相貌與大將軍依稀有些相似。小人不敢確定,便將它帶了回來。」
「混賬,你連大將軍的模樣也認不出來嗎?」安慶緒氣得渾身哆嗦,暴然一腳將辛乙踢開,拔劍還想砍人。卻被司馬瑜攔住道:「阿乙說得不錯,這人不是將軍,只是跟將軍長得有些相似而已。」
說著司馬瑜示意左右退下,並讓人將傷心欲絕的安秀貞送到後帳。這才回頭對安慶緒低聲道:「少將軍節哀,現在萬不能讓人得知大將軍已死。這消息若是傳了出去,軍心必定大亂,大將軍生前籌措多年的大事,只怕就要一夜崩潰。屆時范陽、平盧、河東三府將士,包括少將軍在內,皆如砧板上的魚肉,將任由朝廷宰割。別人或可得到朝廷赦免,少將軍合族上下卻是必死無疑。因為每一個想要活命的將領,都會樂於向朝廷供出大將軍生前意圖造反的真憑實據。」
安慶緒聞言面如土色,失聲問:「那先生的意思是?」
「密不發喪,立刻在軍中尋找與大將軍身材相貌相似的替身。」司馬瑜壓低聲音道。
「替身?」安慶緒一愣,「模樣再相似的替身,也只能瞞過普通將士,怎麼能騙過我爹爹身邊的親兵和愛將?尤其是我爹的結義兄弟史思明,若得知我讓人假扮我爹來騙他,那還不興兵問罪?」
「所以少將軍要立刻舉事,以大將軍的名義起兵討伐國賊楊國忠。將熟悉大將軍的將領全派出去,一旦戰事爆發,誰還顧得上理會大將軍的真偽?」司馬瑜說著,胸有成竹微微一笑,「至於將軍身邊的親兵,可以讓他們全部為大將軍殉葬。只留下知情的辛氏兄弟,並令他們嚴守這秘密,便可萬無一失。以後就算有人懷疑大將軍的身分,那時少將軍已經掌握實權,隨時可以殺掉替身取而代之。」
安慶緒似有所動,不過最終還是面有難色地自語:「倉促之間,哪裡去找體型外貌都與我爹相似的替身?」
司馬瑜微微一笑:「這個少將軍倒是不必擔心。大將軍生前就曾托我為他物色替身,以備舉事後代替他去冒險。我已找到一個神態外貌都有九分相似的備用人選,正養在府中秘密調教訓練,沒想到現在正好可以派上用場。」
安慶緒大喜過望,跟著卻又想起一事,不禁猶豫道:「我大哥還在長安做人質,萬一……」
「做大事者,萬不能瞻前顧後,形勢所迫時,親娘老子也可犧牲。」司馬瑜目光冷厲,沉聲道,「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大將軍就是顧忌大公子安危,遲遲不願舉兵,結果反受其害。」
見安慶緒還在猶豫,司馬瑜又追問了一句:「少將軍想清楚,大公子若是平安回來,這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的基業,是歸你還是歸他?」
安慶緒低頭沉吟良久,終於一咬牙一跺腳:「幹!就照先生意思去辦!」
司馬瑜眼中閃過一絲欣慰,頷首道:「我這就去安排,咱們連夜回幽州,以奉旨討伐國賊楊國忠為名,揮兵直驅長安!」
「等等!」安慶緒目中閃過一絲殺氣,「就算不能為我爹發喪,也不能放過殺害他的兇手。而且要想保住這秘密,也不能留下一個活口。」說著,他衝帳外一聲高喝,「來人!」
方才那名目光如狼的將領應聲而入,安慶緒解下佩刀遞過去,沉聲吩咐:「帶上我的獵犬和虎賁營精銳往西追擊,將任天翔一行和所有知情者通通殺掉,一個不留!」
「遵命!」那將領跪地接過佩刀,轉身大步而去。
片刻後,帳外傳來狗吠馬嘶,以及刀劍偶爾相碰的鏗鏘聲,緊接著,馬蹄聲如滾滾奔雷轟然遠去——追擊的虎賁營精銳出發了。
當天夜裏,安慶緒率大軍拔營東歸,除了派去追擊任天翔的百名虎賁營精銳,其餘人馬將連夜趕回幽州,以范陽、平盧、河東三府節度使、驃騎大將軍安祿山的名義,發動討伐國賊楊國忠的遠征。
在隨大軍趁夜東歸之時,司馬瑜不禁向西遙遙回望,在心中默默道:好兄弟,謝謝你祝我完成了這貌似不可能完成的偷天換日之舉,而且還替我背了個天大的黑鍋,但願你能逢凶化吉,逃過追殺。我還等著你與我連袂登上這歷史的大舞臺,一展胸中抱負!
轉頭遙望長安方向,司馬瑜心潮澎湃,胸中豪情萬丈,情不自禁地悄然低語:「天下,我司馬瑜終於來了!」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智梟(7)墨者之志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智梟(7)墨者之志
出版重點:
「智俠之父」方白羽嘔心瀝血大作 橫跨三大門派,挑戰智慧極限!
◎新一代武林盟主方白羽嘔心瀝血大作,以大唐盛世為背景,探討墨家與千門之術的奧妙!
◎若非擁有過人的才智,如何能成為一代梟雄?
◎一場綿延千年的智勇之爭,一段不為人知的千門秘史!
看似繁華興隆的大唐盛世,竟隱隱暗藏著波濤危機;一場安史之亂,如何竟替大唐埋下滅亡的伏筆?一塊墨玉殘片,藏著怎樣的歷史奧秘?
內文簡介:
安祿山離開長安後不服朝廷徵召,託病不再回長安,終於引起李隆基猜疑。任天翔臨危受命,要去范陽老巢將安祿山抓回,一旦失手,他留在長安的親人和朋友,將成為朝廷的人質,他不得不率義門眾高手,踏上了這條看似有去無回的征途。
范陽郊外,任天翔巧擒安祿山,帶他回長安複命。不想卻遭安慶緒虎賁營追擊,接著又遭到薩滿高手月魔伏擊,安祿山趁機逃脫,任務終至失敗。
安祿山剛逃脫敵手,卻死在了最信任的心腹劍下,原來這一切俱出自千門高手司馬瑜的謀劃,他要借安祿山的勢力實現自己奪取天下的夢想,安史之亂終於拉開了序幕。
在大唐皇帝李隆基有心的佈局之下,任天翔及義門一眾人等皆被關進了大牢,原來李隆基竟是為了安祿山的異心而故意所為,意使任天翔能一舉將安祿山擒獲。任天翔此行前去范陽,是否能順利完成任務?表面上是安祿山幕僚的司馬瑜,卻暗藏著不為人知的計畫,更將眾人玩弄於股掌之上,他的真實意圖又是什麼?而身為義門堂前堂主遺孀的蕭倩玉竟是摩門弟子!這又是怎麼回事?她又會對任天翔做出什麼報復的舉動?
章節試閱
朔風獵獵,捲起漫天風沙,模糊了遠方天地的界限,也讓天宇變得如大地一樣暗淡昏黃。這就是朔方,戈壁與黃沙交替出現的廣袤世界,偶爾的一片翠色綠洲,則如仙人遺落凡間的寶石一樣珍稀。
已經逃離蓬山三天半,憑著辛乙所給的那面通關腰牌,任天翔等人終於通過范陽最後一道關卡,進入漠北無人區。
這三天以來,一行人馬不停蹄夜不曾眠,總算搶在范陽的封鎖令到達之前逃離險地,眾人早已精疲力竭,人疲馬乏,就連一路都在懇求、威脅、央告的安祿山,現在也因饑渴困乏,無奈而疲憊地閉上了嘴。
就在這時,他們看到了立在沙丘之上那一根骷髏...
已經逃離蓬山三天半,憑著辛乙所給的那面通關腰牌,任天翔等人終於通過范陽最後一道關卡,進入漠北無人區。
這三天以來,一行人馬不停蹄夜不曾眠,總算搶在范陽的封鎖令到達之前逃離險地,眾人早已精疲力竭,人疲馬乏,就連一路都在懇求、威脅、央告的安祿山,現在也因饑渴困乏,無奈而疲憊地閉上了嘴。
就在這時,他們看到了立在沙丘之上那一根骷髏...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方白羽
- 出版社: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4-21 ISBN/ISSN:978986580368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88頁 開數:正25K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武俠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