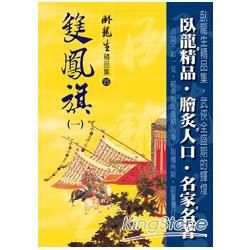導讀
臥龍生的武俠創作,其最大的特色,通常被認為是將故事情節敘述得栩栩如生,以吸引讀者一口氣閱讀下去而欲罷不能;然而,在他若干部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中,往往還含有某些值得深入玩味和省思的內涵或元素,〈雙鳳旗〉即是這類作品之一。
大體上,作為具吸引力的通俗文學作品,舉凡宏大的佈局、奇詭的情節、畸變的情慾、反覆的衝擊,乃至悲劇俠情的渲染、江湖爭霸的殘酷等臥龍生所擅長的技法,在這部書中可謂應有盡有;然而,在紛繁的頭緒與詭異的情節之外,本書確實還有某些足以觸動人性迴響的理念,引人沉思。
◎佈局的機巧與狡獪
長安「鎮遠鏢局」被劫走價值極鉅的珠寶,劫鏢者鴻飛冥冥,無跡可尋,總鏢頭王子方請來眾多成名的武林人物協助破案,仍是一籌莫展;在查案過程中,一干素負盛名的名家老手識見平庸,反而是年紀最輕且藉藉無名的少年「容哥兒」言必有中,在極短期間即於這個查案小組中脫穎而出。
當然,由於他既無門派靠山,又非世家子弟,馬上便被這些武林老手懷疑為敵方臥底者;但事實證明他的來意確是由其母派來向王子方「報恩」,而他的武功更遠在全部查案高手之上。因此,本書一開始即已設下懸念:誰是劫鏢者?目的何在?
但若讀者以為劫鏢與破案是本書的一條主線,故事將會循此展開,便不免小看了作者佈局敘事的機巧與狡獪。實際上,作者只是藉眾多名家高手追查失鏢下落的過程,一層層的抽絲剝繭,讓一個眾人從所未聞的神秘組織「萬上門」現出冰山一角,同時,也讓容哥兒的心性與才情得以相對凸顯。在雙方鬥智鬥力的交鋒中,少林、武當等名門正派的高手逐漸加入,王子方更請到丏幫幫主黃十峰出面協助,一時聲勢大振。但初時只由美女出面周旋的「萬上門」也陸續展示實力,雙方明爭暗鬥,此起彼落。這類情節,老於此道的作者處理起來自是舉重若輕。
◎真正的背景與主軸
但這類情節也只是鋪墊和過場,隨著雙方爭鬥的進行,另一個更詭譎叵測、規模也更龐大的神秘組織逐漸浮現,它不但以極嚴峻的手段逐級控制徒眾,而且徒眾中顯然不乏丏幫、少林、武當等名門正派的高手,而其主持人「一天君主」及轄下的「十大劍主」武功之高更是駭人聽聞。另一方面,作者也開始揭示故事真正的背景與主軸,原來,包括「萬上門」的崛起,及「一天君主」這個神秘組織的出現,似均與容哥兒之母「容夫人」有關。然則,容氏家族究竟是怎麼回事?
容哥兒從小由母親撫養長大,對父親並無印象。諸多旁敲側擊的情節顯示:「容夫人」雖然深居簡出,卻是一位既擅藥理、又精武學的絕頂高手。容哥兒在歷經江湖風暴的挑戰之餘,感到心勞力絀,衷心寄望於母親出山協助己方對抗邪惡勢力「萬上門」及「一天君主」。詎料,諸般波譎雲詭的情節轉折,竟讓他一步步憬悟到:所有他所目擊身歷的江湖風暴、武林殺劫,恐怕都和母親脫離不了關係!
◎權力的爭霸與操控
為了操控眾多出身於各大門派的高手,完成前所未有的武林霸業,「容夫人」及其恐怖組織於洞庭湖的君山島建立地下石府,利用各種伎倆威脅利誘,包括以名醫研製的奇毒暗害,連少林前輩高僧一瓢、一明、武當耆宿上清道長、崑崙赤松子、丐幫第一高手岳剛都不免被拘禁多年,故而現任幫主黃十峰等人或不慎入彀,或賣身投靠,誠然不足為奇。
容哥兒雖然生具俠氣,不畏強敵,一心以鋤強扶弱為己任,且在患難中贏得新交才女江氏姐妹的傾心與援助,但想要與龐大的黑暗勢力相抗衡,卻分明是以卵擊石,毫無僥倖的可能。
歷經諸般周折與考驗,最後進入隱秘重重的地下石府,容哥兒終於知悉了自己的身世。「容夫人」只是養母,是父親「閃電劍」容俊的繼室,而且來自敵國北遼,本就負有顛覆中土武林的使命。但容俊其實也不是他的親父,因為真正的父親「劍神」鄧玉龍當年是著名的風流浪子,勾引了容俊之妻──艷絕天下的蔡玉蓮,後者懷孕而生下容哥兒,被容俊發現,不得不出走,初生嬰兒則留在容家。因此,容哥兒真正的父母乃是鄧玉龍與蔡玉蓮。但在地下石府相逢時,人事已全非,蔡玉蓮衰病侵尋,容俊遭毒物控制,鄧玉龍亦失去了主導局面的能力。但不容諱言的是,容哥兒的上一代正是這場武林劫運的源頭。
◎暗合「後現代」理論
神秘組織為何可以控制如此眾多的一流高手?按「容夫人」的說法,任何人「只要心中有賊,不管是貪財好色,或是熱衷功名,都將為我所利用。我一個女流,能把你們中原武林同道攪得天翻地覆,只用了財、色、功、利四個字。」這即是臥龍生筆下邪派意圖稱霸江湖、乃至主宰天下的核心理念。其實,這倒是和當今流行的「後現代」社會思想家福柯(M.Fault)關於權力/知識/身體之激進理論暗相契合。在本書中,「一天君主」組織的幕後領導人要攫奪至高權力以主宰江湖,依恃的是以女色、毒藥等有形要素控制高手們的身體,並以虛榮、權位等抽象要素影響他們的心智,按照福柯理論,這就是人們不知不覺陷入極力之網的原因所在。
臥龍生當然不可能有意識地援引福柯理論,但他對傳統佛家的因果之說則非常熟悉;另一方面,他對於情節的迴轉與突變常用極大心力在經營;於是,隨著情節的推展,讀者看到:幕後指揮「容夫人」的藏鏡人竟是武當掌門三陽道長,而三陽道長又竟是最初以失鏢邀請眾人入局的王子方的身外化身,王子方背後更有偽裝潛伏多年的高手岳剛。而攤牌時分,在容俊和「容夫人」罹劫之後,有心贖罪的鄧玉龍亦與對方第一高手岳剛同歸於盡,蔡玉蓮隨即殉情自戕…故而,容哥兒在一夕間竟遭遇親父母及養父母全部喪生的慘事。這些慘烈的情節,顯然受過金庸《天龍八部》的影響。
◎冤孽、悲憫與俠義
容哥兒確實有理由大聲責問蒼天:「世人大約再也沒有我這樣可悲的身世了!我既不能奉養生母,卻又和養母為敵;生我之父,是大俠,也是淫盜,生我之母,是武林一代名花,也是個身犯七出之條的棄婦,她受盡了折磨,變成殘廢,仍不能安享天年,難道這都是上天給予的報應麼?」
追源溯始,鄧蔡二人的不倫之戀,是容俊走上邪路及「容夫人」得以禍亂江湖的根由;然而,愛情本來無罪,為何變成慘不堪言的冤孽?從本書的敘事邏輯來看,是因為其中有人的權力野心在作祟,而當權力慾、控制慾與男女情慾交織成難分難解的江湖恩怨之時,一切的道德規範、理性秩序全部發生了扭曲和畸變!
然而,畢竟還有仍堅持赤子之心和俠義之氣的容哥兒,以及對他鍾情至深的江烟霞。尤其,出於對江湖劫禍的悲憫,為了在絕境中拯救那些被毒藥控制的各門派人物,江氏姐妹不惜犧牲色相,出生入死,江玉鳳數度瀕危,江煙霞更為此割捨雙腿。有這樣生具至情至性的新生代,臥龍生筆下的江湖世界才能繼續牽繫武俠讀者的關注。
而浩劫餘生的武林群豪經過集議,共獻「雙鳳旗」給江氏姐妹以示感念,亦不啻暗示著:俠情與悲憫,畢竟不致全然被冤孽和野心所淹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