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明最新小說力作
★九○年代,臺北小酒吧真實故事改編。
★即使臺北已然改變,親身經歷過的人總還是記得的。
小時候,我有一本圖畫書,每一頁都有圖有鏤空,一頁圖畫單獨看是一種風景,一頁疊在另一頁之上,又有不同的想像。
這三篇小說也是這樣,發生在臺北的兩家小酒吧,蝴蝶養貓與龍舌蘭,時間橫跨二十年,故事還在延續,酒吧已經消失,在不同的人生截面我們看到了不同的圖像。
那些不存在的存在,使人滄桑,寂寞荒涼。
| 購物比價 | 找書網 | 找車網 |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從今往後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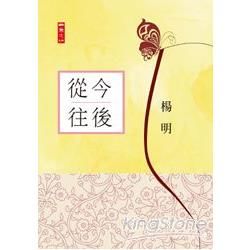 |
從今往後 作者:楊明 出版社: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12-25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90 |
二手中文書 |
$ 237 |
中文現代文學 |
$ 255 |
小說/文學 |
$ 264 |
中文書 |
$ 264 |
小說 |
$ 270 |
小說 |
$ 270 |
現代散文 |
$ 270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楊明最新小說力作
★九○年代,臺北小酒吧真實故事改編。
★即使臺北已然改變,親身經歷過的人總還是記得的。
小時候,我有一本圖畫書,每一頁都有圖有鏤空,一頁圖畫單獨看是一種風景,一頁疊在另一頁之上,又有不同的想像。
這三篇小說也是這樣,發生在臺北的兩家小酒吧,蝴蝶養貓與龍舌蘭,時間橫跨二十年,故事還在延續,酒吧已經消失,在不同的人生截面我們看到了不同的圖像。
那些不存在的存在,使人滄桑,寂寞荒涼。
作者簡介
楊明
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佛光大學文學碩士,四川大學文學博士。
曾任《中央日報》記者、《自由時報》副刊編輯,二○○三年赴成都重溫校園生活,二○○八年客居杭州講學。
曾獲《中央日報》文學獎小說類、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散文類,作品關注現代人的情感與心靈,擅長探討都會兩性關係,筆觸溫柔細膩,觀察深入獨到,字裡行間別有新意,既能滿足閱讀趣味,還能啟發對於人生的思考。
著有《城市邊上小生活》、《味蕾的愛戀記憶》、《夢著醒著》、《海邊的咖啡店》、《走出荒蕪》等三十餘種散文小說集。
自序
愛是沒有人能瞭解的東西
愛是永恆的旋律
愛是歡笑淚珠飄落的過程
愛曾經是我也是你
四年了,我多次夢到你。
一開始,夢裡的你跨越冥界,你清楚我也明白,我們一起守著秘密;後來夢裡你和我說,你有不得已的原由,編出這瞞天大謊,於是我們碰面如情報劇般大費周章;最近,你大方坦然,猶如度假回來,我也不覺有異。你新開的店在一家Shoping Mall的一樓,寬敞明亮,我們坐在鮮豔的L型沙發上用香擯杯喝氣泡白酒,陽光透過玻璃窗幾乎要碰觸到我的手指,有昔時龍舌蘭的熟客進來,悄悄問我:「她回來有事嗎?」我說:「沒事,就是回來不走了。」於是大家安下心來,在這座城市我們又有個地方可以去,可以安放情緒心事和什麼都不想做的時間。
你走後,我頻頻回顧,猶如一個老人,我們的人生是怎麼走到這一步?我於是驚覺,你走了,我也一下老了,我們一路相伴走過的年輕歲月原本那麼確實,如今卻沒了憑據。我開始寫這些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故事,起初我以為是為了兌現你曾經交代我為你寫傳的玩笑,當時你說書名就用《我的前半生》,說這話時自然沒想到你的一生遠比我們以為的倉促。在杭州對著電腦的我思緒回溯到臺北,在已然消失不可重現的二十個年頭裡穿行,清楚的意識到時間是不可逾越的鴻溝。我先寫了〈從今往後〉,這是這本書中寫的最順利的一篇,猶如小說開頭說的,你常說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我總得記下些什麼關於你的文字。寫完後,卻覺得還有更多的東西要說,至於那東西是什麼?其實我也說不清,有眷戀,也有怨尤,有不捨得,也有不甘心。我又寫了〈龍舌蘭〉,這次並不順利,我只能以我的視角去看這家曾經在臺北延吉街存在多年的Pub,天天在那裡出沒的你是一種怎樣的心情?我真的知道嗎?我隱約覺得你被深邃的黑洞攫住,我沒法分辨是我拉不出你來,還是你根本不想讓我拉出來,我們的關係開始出現矛盾與糾結,但是因為眷戀,所以隱忍著不戳破。
寫的過程裡,我不禁回憶許多日後的情由端倪是否發生在更早以前,我愈寫愈看見自己過去故意忽略的矛盾,不敢碰觸的纠結。這本書的寫作停了一段時間,走在臺北的我,意識到,不僅是龍舌蘭,還有更早我們在新生南路的經營的蝴蝶養貓,這二十年來,臺北許多曾經留有我們記憶的地方都消失不見了。
歲月將我遺棄在了這一頭,你也是。
龍舌蘭和蝴蝶養貓的朋友們,總以為我為你的驟然離世悲傷,其實,很長一段時間我是不可置信,你遺棄了我,將我留在長路的一端。當我開始寫〈不存在的存在,蝴蝶養貓〉,我終於意識到我怎麼都說不完整這個故事,我絮絮叨叨說的只是我的回憶,我的思念,我再也無人可說的話語。我沒法把你安放在我的文字裡,但是這些文字卻漸漸將我從一種我說不清的情緒裡釋放了出來。
如今,這三篇小說要結集了,他們各自獨立成篇,卻說的是同一個故事,小說裡的人儘管名字不同,但化身的原型重疊。小時侯,我有一本圖畫書,每一頁都有圖有鏤空,一頁圖畫單獨看是一種風景一種想像,一頁疊在另一頁之上,又有不同的風景與想像,這三篇小說也是這樣,故事是延續的,但在不同的人生截面我們看到了不同的圖像。
蝴蝶養貓還在的時候,我們一起去唱K,你總是會點〈不要問我過得好不好〉拉著我一起唱:「不要問我過得好不好,我的心事你應該知道,當寂寞越來越多,驕傲越來越少,只希望有你白頭到老。」是的,我一直以為不管誰離開了我,你都不會離開,結果你卻毫無預示的徹底離開了我停留的世界。那時曾以為領略到的蒼涼悲愴,如今想來都因為年輕,而有了光采,而這些都是你走後,我才明白的。
我依然會突然有打電話給你的衝動,回臺北時有到延吉街找你喝酒的念頭,但是,稍縱即逝。我不再提醒自己你不在了的事實,也不再告訴自己有些話有些事再也無人可說,你的離世是我的慢性病,我會找到新的活法,就像血糖高的人建立不同過往的飲食方式。
前幾天,走在超市,突然聽到這樣的歌:你會不會忽然的出現在街角的咖啡店,我會帶著笑臉回首寒喧和你坐著聊聊天。我多麼想和你見一面,看看你最近改變,不再需說從前。只是寒暄對你說一句,只是說一句:好久不見。這些年,我聽到許多情歌想到的都是你,於是,不論行走街頭還是斜倚咖啡店窗邊,總是猝不及防的惹起傷懷。但這一回,我沒有再偷哭,沒有再淚眼模糊,我明白這就是我現在對你的心情。而你,對於這本書,你會怎麼說?
別後
錢鐘書的《圍城》裡這樣寫道:「心像和心裡的痛在賽跑,要跑得快,不讓這痛趕上,胡扯些不相干的話,仿佛拋擲些障礙物,能暫時攔阻這痛的追趕。」你走了以後,很長一段時間,我就是這樣的感覺,我不能提到你,和你相關的事也不能,可我的腦子又無法控制的不斷想到你。我覺得自己接下來的人生像是一本裝訂錯了的書,還遺失了許多書頁,再也無法拼湊出原本的樣貌。
當你失去一樣珍貴的東西時,總是會忍不住回想起,初相遇的甜美,那甜美在初遇的那一刻,其實還不知情。
第一次見到你,是在台中綠川邊上的仁友公車站,你和JZ在一起,後來我才知道你們剛去千越百貨二樓吃牛排,而我剛從新大方書店的地下室走回地面,這樣的相遇,我總覺得你們略勝一籌。JZ為我們做了介紹,JZ是我幼稚園時代一起長大的朋友,而你是她中學最好的朋友,至少她是這麼告訴我的,你隨口和我開了個玩笑,雖然一身拘謹的白衣藍裙校服,頂著傻氣十足的短髮,但你看起來很開朗。那一年,你十六歲,我十五歲,從此我們開始了長長地相伴。現在回想起來,消失了的不僅是你,在更早的時候,千越百貨公司和新大方書店就已經從台中的地表消失了。
教室裡,學生的課堂報告,講的是王小波,太太到國外進修時,因為心肌梗塞過世,死時獨自在家,身邊再無他人,和你一樣,你離開時,也是獨自一人。那時的他比現在的你年輕,黃泉路上無老少,道理我懂,卻無法因此覺得比較能接受你的離開。年輕的學生望著我,輕聲說,老師,生命無常啊!
他們不知道,你走了,我失去的不僅是你,還有我們共同的記憶,再無憑證。二十三歲的時候,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說,高興的叫你去書店買,那時候新大方還在,我常故意走下樓梯看老闆將我的書放在哪,如果湊巧遇到有人正翻閱我的書,我就會在心裡高興上一陣子。我想你是為我驕傲的,每次你向別的朋友介紹我時,總說:「她是寫小說的哦,以後她會寫一本小說叫做我的前半生,主角就是我。」現在我卻發現,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相伴越久,我越不知道如何寫你,以及屬於你的故事。
你一直想披上白紗,至少一回,感情路上卻一直所遇非人,始終沒能完成心願,雖然你曾開玩笑說,我結婚,可使全天下的男人都得到解脫,只有一個男人倒楣;但如果你嫁人,就是全天下的男人損失,只有一個男人得到幸福,所以你才沒嫁。
下課鐘響,我收拾好東西從前門走出教室,一男一女兩個學生追著喊我,接著討論剛才課堂上提及的作品,男同學說,老師,這篇小說裡的主人翁似乎隨時可以拋下自己的人生,這是不現實的啊!我隨口反問,你認為現實人生是怎樣的?女同學搶著說,至少要結婚生子。
成為一名賢妻良母是你中學時代的心願,卻直到你離開人世都沒能實現。學校畢業工作數年的你勇敢和同事一起離職創業,卻也為日後多舛的命運埋下伏筆,昔時共同創業的夥伴卷款潛逃,你幾番掙扎,依然無法再起。愛情和事業的雙重打擊,我甚至不知何者傷你更重。
婚前,我曾經住在你樓下,後來又搬到你對面,去台中看你時,我留意到你對面的塔位仍是閒置的,我猶豫了一下,要先訂下,將來繼續和你當鄰居嗎?那段日子,不上班的時候,我們常常一起逛街吃飯,忠孝商圈的高雄木瓜牛奶、溫莎小鎮、聖瑪莉咖啡,往東的賽馬義大利餐廳、明洞韓國料理,往南的鑽石樓、躲貓貓,往北的京兆尹、中興百貨,我們曾經出入的這些地方,都已從臺北地圖徹底消失。消失的名單上,最讓我們念念不忘的,當然就是我們曾在新生南路經營的PUB蝴蝶養貓,和延吉街的三布五石。
一九九二年一月,我們不經思索的頂下了第一家店,那時你每天從貿易公司下了班就去開店,等到十點半,報社下班的我也就來了,一些不明究裡的酒商背後稱呼我們是苦情姐妹花,以為姐姐辛苦供妹妹讀書,妹妹夜校下了課就趕來幫姐姐。這些鐫刻著我們足跡話語的場所,通通在你離開前業已消失,記憶還留下些什麼給我,竟像是我平白哄了自己一場,歡笑悲傷全沒了憑據。
校舍走廊光線幽暗,盡頭的玻璃窗撒進的大片陽光,尚不足以漫淹至腳邊。我說,人生有很多種選擇,不是僅有單一選項,女同學仍在搶話,我媽說,中國人最重傳宗接代,孩子一定得生,那麼晚生不如早生。簡潔有力的人生哲學,你也曾這樣想嗎?怎麼沒人告訴你,如果你這樣做了,人生會有所不同嗎?我忍著沒跟學生說,人生除了死亡,其他所有選擇都不是唯一不可變的啊,生孩子不是,結婚更不是,只有死亡才是。
我以為無論人生怎樣往下走,至少我的身邊還有你,在我們老了以後,一起囉囉嗦嗦的數叨著,我們以前哪……我從沒想過你會比我們之中的誰先離開,一起變老成了不可能的願望時,原本對衰老的無奈與哀傷,此刻卻突然有了幾分溫馨,只是我永遠失去了這機會。你走的那天,我在杭州,回台後,朋友向我說起你走後的種種,我腦子裡浮現的卻是杭州窗外的雪景,接到你驟然離世的電話時,我正在廚房準備晚餐,掛了電話後,我回到廚房打開瓦斯爐,在鍋裡倒入油,依序放入蔥段、肉絲、木耳和金菇,我完全不相信你已經走了,我繼續工作、吃飯、睡覺,直到有一天早上醒來,發現窗外的街道、花圃、屋頂,全都覆蓋著白雪,在白茫茫的世界裡,是賈寶玉回身告別俗世的雪地,我突然明白,你走了的事實。
我想起了小說《City》中的一段對話,「我為什麼還活著?」「這是酒吧,你要教堂的話,在路的那邊。」龍舌蘭酒吧從臺北消失了,酒吧對面的天主教堂還在,我曾以為那座教堂會先搬走,寂寞的夜晚,微醺時我們也曾拿那座教堂開開玩笑、發發感慨,原來生死問題只適合教堂,不適合酒吧。
過了七七,我才夢見你,也是在你的酒吧,你見我來了,卻沒和我說話,反而打電話給二叔,要二叔催我快走。我聽見你說,楊明來了,二叔問,你沒告訴她嗎?你回答,我沒想到她會來這啊。朋友聽完我的夢,推測我誤入冥界,所以你急著要我走。
就是在我認清你走了是無法改變的事實的那一刻,我恍然明白,白雪是上天給人類的恩賜,這是生存在亞熱帶的我們沒能發現的。每年隆冬的白雪將一切覆蓋住,你熟悉的街道、樓宇,遊走潛藏其間的愛怨欲嗔,一併不見,你以為在你心裡,但眼前不見,遂失憑依,北國冬日,原是休憩之際,田裡農活已停,萬物具休,直到來春,人的心念也在白雪皚皚的覆蓋下冷寂了下去,不得不放下。我們卻不明白天地四時的道理,執著盎然愛欲,熾烈不息,只知夏耘,不知冬藏,於是你提前用盡額度,刷爆了時間給你唯一的一張卡,直到離去的一刻,才不得不學會了放手。
我也必須鬆開我的手,前去台中看你的那天,朋友囑我別哭,有人說生者的眼淚,會讓往生者不舍離去。於是,我對你說,既然走了,就放心地走,你曾說你沒法像我一樣,在感情尚未耗盡前瀟灑離開,這回你不就這樣做了嗎,搶在我前面,去了另一個國度。隨著年齡的增長,愈來愈多的朋友去了那一邊,我寧願當做你們移民了,總有一天我也會拿到那一個國度的簽證,只是這一回你竟然背著我偷偷先辦了。
徐志摩的詩,我們年輕時曾經唱過的:假如你願意,請記著我,要是你甘心忘了我。在悠久的墳墓中迷惘,陽光不升起也不消翳,我也許,也許我還記得你,我也許把你忘記。
那時不懂的哀傷,歲月已經都教給了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