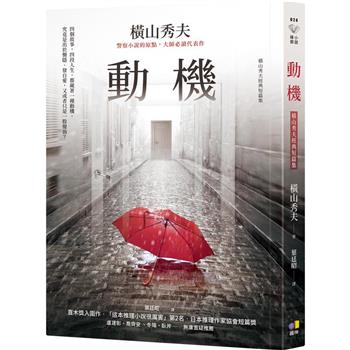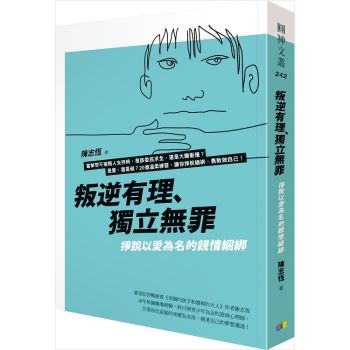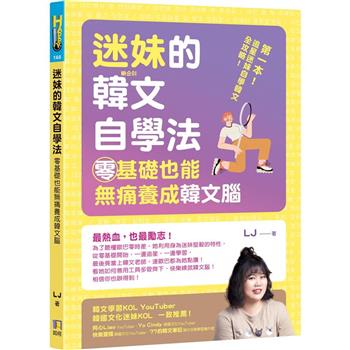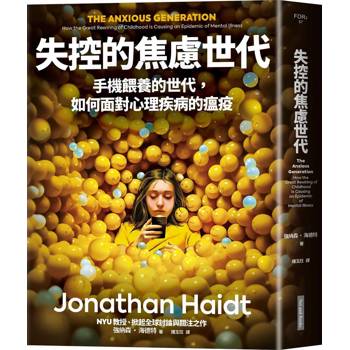蠔癡
沈愛雲,二十五歲的臺灣女子,在終於學會開生蠔之後,和名喚伯納.荷迪葉的法國男朋友正式宣告分手。
首先選好要撬開哪一邊。仔細看,不論形狀怎麼不規則的蠔殼,總是有脈絡可循:它必定一邊較平,一邊較凸。凸出的那邊就是蠔肉所在之處,所以你應該從平的那一邊下手,這樣不但困難度減低,它的汁液也不會流失。
和伯納分手後,她決定這是最後一次找語言交換的夥伴。語言交換,說得好聽,其實對某些人而言,不就等於找個性伴侶?學法文的方式不限於此。不過,嗜吃生蠔的她,從伯納身上學到開蠔技法,還是有相當的實用價值,從此她不再任餐廳予取予求,為那些處理好、整盤端上來、卻瘦扁得不像話的蠔,付出貴好幾倍的價錢。她不認為伯納是認真地想學中文,但至少他學會了怎麼說「小姐,一起去喝咖啡吧!」跟「我愛妳,去妳那兒還是我那兒?」等等對他來說也頗實用的句子,所以,往好處想,他們可不是各取所需,皆大歡喜?
今天巴黎的天空一反往常的陰沈,處處現出湛藍和金色的笑顏。心情不由得也開朗起來。即使地下鐵帶她進入一成不變的黑暗王國,即使電車慘白的燈光,掃落陽光在她髮稍留下的最後一絲溫暖回憶,她仍然固執地相信,今天,一定有什麼好事會發生在她身上。
她抓著車上的扶桿,思緒飄到不可知的遠方。再把它抓回來時,她注意到斜前方那人攤開的書裡,夾著莫迪里亞尼(Modigliani)的書籤。這位莫先生並不是她往常特別喜歡或關注的畫家,但是今天,不知怎地,突然覺得畫中女子的眼睛充滿一種無言的溫柔,溫柔得讓她心動,連女人那長得不像話的頸子,也傾訴著說不出的婉約,嘴角那一絲淡得快看不出的笑意,擴散在冷冷的空氣中,那一瞬間,慘白的燈光彷彿也暈上一抹紅橙色的甜蜜。
終於有座位了,她在那人對面坐下來。換個角度,莫迪里亞尼的女人彷彿換了另一種風情,對她微笑著。看書的女子驀地抬起頭來,臉上居然帶著莫氏畫筆下女人一樣的溫柔笑顏。
但她不是女人,他溫柔頸項上的喉結說明了一切。
文森有張漂亮得幾乎不像男人的臉龐,眼睛藍得像那天巴黎的天空,透明澄澈,藏不住一絲陰霾;薄薄的嘴唇捲出玫瑰花瓣精雕細琢的弧度,微笑時就像是蓓蕾緩緩打開,把春天帶到人間;連他說話也是那樣輕聲細語,將法文的陰柔發揮到了極致。那個「r」音真是無懈可擊,沒有某些法國人那種近乎西班牙或義大利式的吵雜氣聲,清淡的像英文的「h」,但你就是知道他確實是輕震喉門,發出那個優雅,若有似無的氣音。再怎麼專注仔細聆聽,就是聽不到那股「氣」,卻很清楚它是存在的。這是種只能用直覺解釋的神奇。
如果亞德尼斯(Adonis)真的存在,一定就像他這樣吧!
「愛|雲|。事實上妳的中文名字和法文的﹃愛蓮﹄(Helene)還比較接近呢!為什麼堅持要人用英文發音的﹃海倫﹄(Helen)叫妳呢?」
「就是因為接近我的原名,所以我不喜歡。如果我要一個外文名字,我希
望它給我一個全新的自我。」
「為什麼是海倫?妳特別喜歡這個名字嗎?」
「我要這個名字。如果我是傾國傾城的海倫,帕里斯王子(Paris)會拜倒在我的腳下。所以,熱戀著巴黎(Paris)的我,找不到比海倫更好的名字了。」
「說得好。都說海倫是禍水,但畢竟特洛伊戰爭真正的贏家還是她。帕里斯死了,特洛伊慘遭屠城,勝利的希臘人為十年圍城也付出不少代價,只有海倫還是舒舒服服地回去做她的斯巴達王后。」
文森正是她夢中的典型。她很納悶為什麼等到現在,才終於有這樣的男子出現在她生命中。她一向喜歡娃娃臉,看來有些稚氣的男生,但生命硬是跟她開了個大玩笑,她的前任個個都是「粗壯」型的,有些是個性幼稚,臉蛋兒可一點都不如此。
文森帶她到龐畢度,在美術館裡耐心的為她解說莫迪里亞尼、夏卡爾(Chagall)、馬諦斯(Matisse)的作品,當她買下那張為他們結緣的莫迪里亞尼海報時,那張可愛的臉上浮現出淘氣的笑容:「送給我吧!」
「好,我再去買一張。」
「不行,」他任性地撅起那張形狀美好的嘴,「不准妳再買,我就是要妳買的獨一無二的這一張。」
她覺得很納悶,但也沒說什麼。隔幾天他把那張畫裱好送來,她感動得幾乎落淚。他自告奮勇地幫她掛到牆上。
「喜歡嗎?」她點點頭,「你對我真好。」
「能為美麗的女士盡心,是身為法國男人的幸福。」
他帶她到一家名為「亞馬遜」的餐廳。一進門,侍者馬上親熱地在文森雙頰上啄了兩下:「近來好嗎?哇,」不可置信地,「今天帶女孩子來?」
她感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身為女人的光榮莫過於此。
「你和他們很熟?」她問。
「嗯,我和朋友常常來。這是家不錯的餐廳。」
「在亞馬遜,我們吃的是什麼?」
「抱歉也許要讓妳失望了,還是法國菜。」
燭火在他臉上投下抒情的光影,一杯酒下肚,他臉頰上竟泛起了紅暈,暈得她心裡也熱烘烘起來;儘管她仍面不改色,但是終究醉了。最是醉人的畢竟不是酒。
「你比我還能喝呢,海倫,妳真是比法國人更加法國。」他的笑顏在夜色中擴散開來,迴旋,盪漾,她不由自主地也被捲入這波漩裡,一顆心在暈眩中悸動著。他送到門口,「謝謝妳,親愛的海倫,謝謝妳陪我渡過一個美好的夜晚。」他在她雙頰印上兩個甜蜜的吻。她的心因期待而痛苦地抽慉著,還沒有呢,她在心裡吶喊著,這個夜晚還沒有結束,文森,還沒有結束啊
月光在他臉上變幻著魔法,那張清秀的臉竟也透出一分妖氣,氤氤氳氳把她整個人裹了起來,煙雲裡像是有千隻鉤子,劃穿了她的衣裳,鎖進她的皮肉,緊得她無法呼吸。
他走了。這是她回過神後發現的第一件事。
一千隻鉤子隻隻從她身上脫落,在這寂靜的夜裡,那清脆的墜聲顯得無比清晰,她覺得異常衰弱,像是身上最後一滴血,都隨著這些兇器離她而去,只留下一個空空的軀殼,暴露在慘白妖異的月光下。
純真之歌
想變成龍的蚊子
「...#@☆??」
龍感到背後有一點細微的動靜,尾巴輕輕一掃,闔起眼繼續睡。
「請問..」
似乎有點聲息,牠抬頭環顧四周,還是沒看到什麼。
「要怎麼做,才能變成像你這樣?」
這次聲音在耳邊,牠回頭一望,就是看不到誰在說話,「是我啦,前面,前面。」有個灰塵樣的小東西飛到牠鼻頭,拚命搖著小翅膀,到牠瞧見了才停下來,靦腆地,「我說,怎麼才能像你這樣強壯漂亮?」
這小龍打蛋殼裡出來不久就沒了媽媽,個兒又比人矮,難免畏畏縮縮;長出晶亮神氣的鱗片前,就一身五顏六色雜毛,活像個絨毛玩具,幼嫩的小翼還沒有力量,只能怯怯地這個樹頭飛到那個樹頭。第一次聽見有人說牠強壯漂亮,很是意外,「啊?」
「我好想當一隻龍,在高高的天上飛翔,翅膀一煽,是吹向大地的風,尾巴撥動層雲,降下滋潤萬物的雨。一噴火,燃燒的天空染得通紅,燒到盡頭,星星會從灰燼裡睜開眼,你得屏住氣,靜靜滑過它們身邊,星星很容易就被嚇著了,它們要是喜歡你,就會對你微笑。」小蚊子說得起勁,冠上的金色觸鬚興奮地抖動,「我好厭倦只能在人們身邊繞來繞去,找機會叮一口,像賊一樣,還得防他們動不動一巴掌過來|我姊就是這樣,啪一下,活生生斷成兩
截!」牠打了個哆嗦。
龍卻感到一股暖意,緩緩延燒到心底。牠聽見自己說,「或許有辦法。」小蚊子豎起耳朵,滿臉期待地,「我們族裡長老說,要成為偉大的龍,得從夢想裡得到力量成長。」
「那是什麼意思?」
「我也不是很清楚,」龍皺起眉頭想了一下,「但聽著,我有主意了。你從我這兒吸一滴血,那麼你身上流著龍的血,就是我們一族了。你要去採集各式各樣的夢,就能夠長成一隻偉大的龍,你說是不是?」
牠們決定這麼辦。但小蚊子試了又試,就是無法穿透那細密的絨毛,得到成為龍族需要的一滴血,最後龍伸出指爪,在腹部最柔軟處劃出一道血痕。小蚊子把針管湊了過去,顫抖著,吸進第一滴,「多喝一點,不要緊。」龍對牠喊著。
第二口,第三口,直到牠小小的身子脹得鼓鼓的,再也容不下。「這輩子我都不會再飢餓,也不需要再吸血。」小蚊子說,「現在我是龍了。」
牠飛走了,去世界採集夢想。牠答應會來告訴龍最新的進展。牠第一次回來,深不見底的夜剛浮起一彎纖細的新月,淡漠的夜色照上龍背脊微微突起的幾個小丘,「我的背鱗快長出來了,」龍告訴牠,「毛也開始脫落,這裡禿一塊那裡禿一塊,樣子很醜。」
蚊子說牠看不出來,只覺得龍似乎有些憂鬱。「我的心也沈著。我看到一個微小夢想的破滅,這能讓我更接近你嗎?」牠開始說第一個故事。
我停在一個小男孩病床上,用頭上的觸角輕輕碰他,牠說。像是接收器一樣,他心裡想望的,我都感覺得到|畫面、聲音、氣息、溫度都很完整地收進去。護士來了,我飛到天花板,看她為他擦身換衣服,扶上輪椅推到窗前。她走了,他把膝上的童話書丟開,瞪著窗外發呆。他想出去,像那一對彩蝶那般自在飛舞,他不要困在這張床、這台輪椅上。大人總是在說謊,他們老說他就快好了,到底他還要等多久?
我輕輕落在他肩上,他全心盯著那對天青鵝黃的蝴蝶,沒有發覺。我跟著他的心飛出窗外,隨著蝴蝶這朵花飛到那朵花,小池塘繞了一圈,荷花蕊心上蹬了蹬腳,輕輕巧巧翻出牆外。一大片山巒起伏的連綿紅瓦白牆之後,突地急轉直下,不住拍打斷崖的,是畢生所見最澄澈晶藍的海水,而我們早就不是彩蝶之身,已化為淺灰背羽腹部雪白的沙鷗。振翅翱翔,羽翼在豔陽下閃著銀光,貼近海面,向著碧藍海水的那一側絨羽,仿若早已浸入水裡,映上奇蹟似的藍光|一飛高,胸腹之間的藍色便淡去一點,於海上盤旋,下身光影連翩,儼然上演一齣碧海晴空的戲劇,從湛藍、天青到淡不可辨的微藍,然後白雲飄進來了,曾有的藍意成為記憶。遊船上有個孩子本以為遇見傳說中的青鳥,看到離水而去的我們轉瞬腹下雪白,失望地歎著氣。
再靠近,到海水泡沫能濺上身子,底下悠遊的魚群警醒地往深處竄去,提防有利爪尖喙突襲。我們順勢滑入海裡,羽翼收為兩鰭,搖尾成了藍綠底勾了赤金邊的熱帶魚,恣意在朱紅鹿角、妍黃瓣蕊、藏青腦紋的珊瑚間穿梭;閃著盈紫珠光的海葵魅惑著招手,但我們知道若非小丑魚,不該投入那看似溫柔的懷抱;從幽暗中昇起的水母,在淺海的陽光下通體透明,抽長的縐紗細帶,優雅地一搧一搧……。
停在窗前的藍蝶翅膀微微搧動,觸角挨著紗窗,小男孩伸出手指去逗,也沒有躲開。那一瞬間,我們明白牠懂得他的心思,也帶來一點陽光下曬得暖暖的飛翔之意。但在下一刻,那雙翅膀給行經窗外一個頑童捏住撕開,看牠還能不能飛,玩厭了就隨手丟下,拉著小胖腿跑開了。那黃蝶著急地在伴侶周遭盤旋,瞧牠一次次掙扎要起身,又一點一點地衰弱下去。小男孩的眼淚掉下來,濺在我翅膀上,沈重地讓我飛不起來。
流動的饗宴
薄酒萊與阿宗麵線
初到巴黎,如劉姥姥進大觀園,花都五光十色,絢麗精妙,看得人目不暇給,鄉巴佬之態畢露無遺。依著旅遊指南,覓進蒙帕納斯大道(Boulevard Montparnasse)上的圓頂﹝La Coupole
﹞餐廳,在保留裝飾藝術風格與美好年代(Belle Epoque)逸樂氣氛的餐室內,我仰望撐住這個廳堂所有金碧輝煌的廊柱,想像創建之時,藝術家們在此觥籌交錯,藉著酒興柱上大筆一揮,
成就一幅幅筆酣墨飽的嬉遊飲宴圖,迷濛之間,彷若身處蒙帕納斯山腳下,隱約可聞山頂謬思神殿裡,詩神畫仙笑語不斷。
侍者把電話簿般厚重的酒單丟到面前,敲醒我的白日夢。如同大多數法國侍者,他盡職地站在我身後,不是要提供任何貼心服務,而是在我犯下重大錯誤之時,厲聲予以糾正。我的額上開始冒出冷汗,縱然識得法文,這電話簿裡的產區酒莊品級仍不啻天書,看得懂的價格又恰如天文數字,難道我在巴黎初次高級餐廳的探險,就要以陣亡收場了嗎?
「您想要點什麼呢?」那語氣滿是等著看好戲的悠哉。
「呃..」我像失憶者,拚命找著任何跟酒有關的回憶,「我..也許想試薄酒萊(Beaujolais)
這個地方的,」那一瞬間,法國友人提過的某個單字浮上腦海,「您可以幫我介紹嗎?」
對方的眉毛揚了一揚,「您可以試試Brouilly。」
那時我懷疑著是否被耍了。想來對方或許心裡暗笑,卻很專業地推薦價廉的佳釀﹝從點的菜色來看,料到這些人決不會花太多錢在酒上面﹞,沒有拿一瓶去年沒賣完的薄酒來新酒(Beaujolais Nouveau)充數。
薄酒萊區的Brouilly成為第一課,我開始苦心誦習法國葡萄酒主要產區與特色,為的是不讓電話簿的悲劇重演。當我能夠平心靜氣看完酒單作好評估,在點酒時略略弓起眉心,優雅地吐出酒名、高傲地放下酒單之時,也發現La Coupole終究不是什麼高級餐廳,它略似大陸那些轉到國營體系下經營的老字號名店,過去的光環縱還閃亮,對觀光客的號召力仍是主要的賣點。本地人喜歡在向晚時分來啜一杯咖啡、喝點小酒,從靠窗那一排隔出來的雅座,饒有興味地瞧進大食堂內,堆得小山高的海鮮盤在侍者肩上閃著寒光,來往穿梭於沸騰洶湧的人聲與食慾之間。
我永遠都忘不了電話簿之劫救了我的薄酒萊,儘管酒的知識日漸累積,新寵繽紛絡繹,薄酒萊這產區對我還是特別的,它開朗、沒有心機、充滿年輕的活力,那樣理直氣壯地,把滿肚子濃郁的果香慷慨與人分享,教你想勸它世風日下人心難測,為人行事當世故內斂,都會覺得不忍。
去國多年,回來以後第一個薄酒萊酒節,就受到很大的文化衝擊。早在十一月第三個禮拜四之前,廣告就打得轟轟烈烈,經過仔細包裝的薄酒萊像個嬌貴的美人,一開口那帶著法國口音的英語﹝因為行銷手法與美式跨國企業如出一轍﹞,時髦又性感,惹得眾人又驚又愛。一個接著一個的暢飲派對接連而開,高檔精品、美食業者、名人影星加持,鎂光燈照耀之下,它的身價愈飆愈高,愈發不可一世。這酒儼然不是俗話裡不成敬意的那一杯「薄酒」,情願與否,你還是得乖乖付出「舶﹝來﹞酒」的價錢,買一點異國風情下的單薄滋味。
我已經不認得這個薄酒萊了。該產區向以清新爽口見長,不適久放,新酒尤為是。沒有人覺得薄酒萊新酒是上品,以當年收成的葡萄釀製,三個月內快速熟成上市,單價鮮有昂貴者;這個酒代表的是豐收的喜悅,在薄酒萊酒節這天,全國共飲慶祝風土富饒、美好一年,懂得的初試今年葡萄品質,不懂的照樣歡欣鼓舞,找到機會爛醉。富人與窮人都能共飲,因為它的價錢誰都出得起,這樣歡樂的氣氛也讓大家齊心舉杯,說起最民主的酒,莫非為是。
如今薄酒萊新酒走上全球化的道路,成功的品牌行銷,讓全世界在同一天舉杯高喊
“Vive la France!”﹝法國萬歲﹞,卻好像失落了什麼。
於是我懷著失落的心,鬼魂似地飄到西門町,在某個大排長龍的陋巷裡,瞅見阿宗麵線血紅的金字招牌。阿宗老兄顯見是發了,回饋在主顧身上的,是那打破你對傳統街頭小吃印象的晶亮華麗店面:如果你心裡想的是古樸的木擔頭攤子,一群人圍了汗衫腴肚的老板,看他肩披一條毛巾,不斷拭著額上擦也擦不盡的汗珠,從熱騰騰的鍋底,不斷撈出抖著鮮嫩嫩大腸頭的粉潤潤麵線糊,那麼你絕對會被以下的景觀震懾住|銀藍滷素燈照耀下,米黃石英磚的
牆面和黑色花崗岩的地板相映生輝,嵌入壁裡的寬螢幕液晶電視閃爍著霓光,辛苦的工作團隊隔在磨紗玻璃門後,為你盛碗的掌櫃們,整齊一致的紅白制服,在一塵不染的花崗.前微笑。
店面裝潢得閃亮,阿宗卻沒有忘記他發跡由來,以前的小麵攤沒有板凳,現在的豪華場子還是要捧著碗站了吃,他沒有因為賺錢就擺幾張椅子讓你坐。於是那慕名而來西裝筆挺的日本人,把公事包夾在腋下騰出手來,滿臉大汗地把麵條划入口中;隔壁的小情侶叫了一碗大的,你一調羹我一調羹地,那個笑靨說明有沒有位子坐並不重要;那對哥倆好,在人家公寓入口台階上坐了慢慢吃,恰把隔壁「吃麵線者請勿擋住本店招牌」的告示遮住;那一家子更大大方方拖鞋短褲佔了巷道,大人小孩蹲了捧著碗吃,一會兒燙了嘴哭起來,只見媽媽一邊罵一邊吹涼。街頭小吃難得一見的排場,配上廊前巷口那群遊民般聚散來去的食客,阿宗的麵攤當真是色香風景無限。
Vive Taiwan。漂洋過海來到臺灣的薄酒萊,在華貴的外衣下讓人看不清它的真實;鍍了一層金的阿宗金店面,在顯貴之後仍不失本土特色。你想不到法國人逐漸忘卻的自由平等博愛精神,在阿宗這裡得到徹底的實現─無論男女老少,不分貧富貴賤,人人一律站著吃,沒有例外,也和樂融融相安無事。說臺灣這個社會淺薄,還是有它可愛的地方。
聽說阿宗在別處還有分店,有桌有椅的餐廳化經營,但可想而知的,總還是沒有站著來得好吃。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食色巴黎Feast For Paris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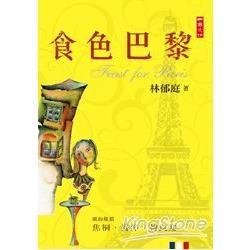 |
食色巴黎 作者:林郁庭 出版社: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1-27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13 |
飲食文學 |
$ 230 |
休閒生活 |
$ 237 |
中文書 |
$ 238 |
歐洲 |
$ 243 |
小說 |
$ 243 |
現代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食色巴黎Feast For Paris
作者以食色為題, 透過中篇小說〈蠔癡〉與十四篇飲食散記,
深刻書寫巴黎生活的感悟與體驗,刻劃異國游子的一抹鄉愁,與歲月的懷念。
文中收錄短篇童話〈純真之歌〉,引領成人讀者再一次乘著故事的翅膀,遇見心中隱匿許久的想望。
作者簡介:
林郁庭
美國柏克萊比較文學博士,曾獲中國時報人間新人獎。為小說《離魂香》浸淫調香,旅美法多年至回歸亞洲的如夢歷程,為散文集《夢.遊者》,多次進出上海不斷演繹的視野,琢磨出小說《上海烈男傳》,美食小說《愛無饜》、飲食雜文及巴黎回憶《食色巴黎》,反映了逛菜場作羹湯的原初好食慾。
繪者簡介:
歐笠嵬(Olivier Ferrieux)
我是歐子 ( 就是歐笠嵬) Olivier Ferrieux.
來自法國. 在台灣住了下來 還要繼續住下去.
快20年囉!
沒發現時間比我思想跑得快.
打從15歲我左手愛用畫畫呼吸
吸個不停. 它的天真, 直覺. 帶領
我的腦子讓我的眼光在時間之外漂流.
歐子
http://www.flickr.com/photos/olihuahua/
章節試閱
蠔癡
沈愛雲,二十五歲的臺灣女子,在終於學會開生蠔之後,和名喚伯納.荷迪葉的法國男朋友正式宣告分手。
首先選好要撬開哪一邊。仔細看,不論形狀怎麼不規則的蠔殼,總是有脈絡可循:它必定一邊較平,一邊較凸。凸出的那邊就是蠔肉所在之處,所以你應該從平的那一邊下手,這樣不但困難度減低,它的汁液也不會流失。
和伯納分手後,她決定這是最後一次找語言交換的夥伴。語言交換,說得好聽,其實對某些人而言,不就等於找個性伴侶?學法文的方式不限於此。不過,嗜吃生蠔的她,從伯納身上學到開蠔技法,還是有相當的實用價值,從此她...
沈愛雲,二十五歲的臺灣女子,在終於學會開生蠔之後,和名喚伯納.荷迪葉的法國男朋友正式宣告分手。
首先選好要撬開哪一邊。仔細看,不論形狀怎麼不規則的蠔殼,總是有脈絡可循:它必定一邊較平,一邊較凸。凸出的那邊就是蠔肉所在之處,所以你應該從平的那一邊下手,這樣不但困難度減低,它的汁液也不會流失。
和伯納分手後,她決定這是最後一次找語言交換的夥伴。語言交換,說得好聽,其實對某些人而言,不就等於找個性伴侶?學法文的方式不限於此。不過,嗜吃生蠔的她,從伯納身上學到開蠔技法,還是有相當的實用價值,從此她...
»看全部
目錄
I. 蠔癡
II. 純真之歌
想變成龍的蚊子
龍的古怪肚皮
雙面騎士
伴郎奇遇記
III. 流動的饗宴
鮮美
菜蟲之死
仙人掌之歌
溫泉親親魚
欲望之翼
櫻桃的滋味
醇情咖啡
蟹友
不吃苦
遙祭
面具之都
燻鮭
鹽之風華
薄酒萊與阿宗麵線
商品資料
- 作者: 林郁庭
- 出版社: 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1-27 ISBN/ISSN:978986581322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24頁 開數:25開
- 類別: 中文書> 旅遊> 歐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