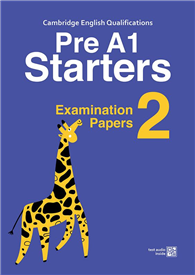★本叢書一套四本,為華文中篇小說之王──閻連科最經典的中篇小說選集
★集中認識最好、最精采的閻連科
閻連科以自己出生的村落(河南嵩縣)和生長的文化景況為基調,細細描寫著那些微小的存在與消逝。看那些介於大城與小村的人們,他們的過去、當下與未來,以及充滿艱苦、奮鬥、有時歡愉、有時哀慟,或許茫然也依然前進的生活。
本叢書(一套四本)共八篇小說,每篇小說都設定以河南嵩縣的耙耬山這個地點貫穿不同人物的生命故事,作者娓娓道來在他所構築的耙耬山世界中,農民對權力的崇拜,及生命的價值在權力面前遭到否定時,所體現的積極人生意義。
推薦群
王安憶 小說家
王德威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李歐梵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講座教授
張 錯 美國南加州大學東亞語文學系兼比較文學系教授
梅家玲 臺灣大學臺文所與中文系特聘教授
陳昌明 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
陳思和 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中文系教授
黃英哲 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兼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
楊 照 作家、評論家
廖炳惠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文學系「川流講座」教授
駱以軍 小說家
蘇偉貞 小說家、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黑白閻連科:中篇四書 卷四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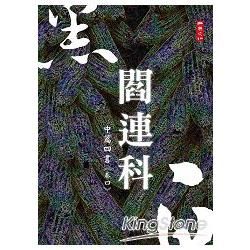 |
黑白閻連科:中篇四書《卷四》 作者:閻連科 出版社: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6-03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2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161 |
小說 |
$ 196 |
小說/文學 |
$ 202 |
中文書 |
$ 202 |
小說 |
$ 207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圖書名稱:黑白閻連科:中篇四書 卷四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閻連科
閻連科,著名作家,1958年出生於河南嵩縣,1978年應徵入伍,1985年畢業於河南大學政教系、1991年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1979年開始寫作,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情感欲》、《日光流年》、《堅硬如水》、《受活》、《為人民服務》、《丁莊夢》、《風雅頌》、《四書》、《炸裂志》等10餘部,中、短篇小說集《年月日》、《黃金洞》、《耙耬天歌》、《朝著東南走》等15部,言論集、散文《一個人的三條河》(二魚文化出版)等12部;另有《閻連科文集》17卷。曾先後獲第一、第二屆魯迅文學獎,第三屆老舍文學獎和馬來西亞「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入圍法國費米那文學獎和英國國際布克獎短名單。其作品被譯為日、韓、越、法、英、德、義大利、西班牙、以色列、荷蘭、挪威、瑞典、捷克、塞爾維亞等20幾種語言,在20多個國家和地區出版。2004年退出軍界,現供職於人民大學文學院,為教授、作家。
你不能不知道的閻連科
‧諾貝爾文學獎呼聲最高的華人作家
‧2005年老舍文學獎、2013年世界華文文學獎得主
‧獲《中國新聞周刊》評選為影響中國2013年度文化人物
‧中國當代最常被查禁的作家
‧中國最具反叛精神的作家
閻連科
閻連科,著名作家,1958年出生於河南嵩縣,1978年應徵入伍,1985年畢業於河南大學政教系、1991年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1979年開始寫作,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情感欲》、《日光流年》、《堅硬如水》、《受活》、《為人民服務》、《丁莊夢》、《風雅頌》、《四書》、《炸裂志》等10餘部,中、短篇小說集《年月日》、《黃金洞》、《耙耬天歌》、《朝著東南走》等15部,言論集、散文《一個人的三條河》(二魚文化出版)等12部;另有《閻連科文集》17卷。曾先後獲第一、第二屆魯迅文學獎,第三屆老舍文學獎和馬來西亞「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入圍法國費米那文學獎和英國國際布克獎短名單。其作品被譯為日、韓、越、法、英、德、義大利、西班牙、以色列、荷蘭、挪威、瑞典、捷克、塞爾維亞等20幾種語言,在20多個國家和地區出版。2004年退出軍界,現供職於人民大學文學院,為教授、作家。
你不能不知道的閻連科
‧諾貝爾文學獎呼聲最高的華人作家
‧2005年老舍文學獎、2013年世界華文文學獎得主
‧獲《中國新聞周刊》評選為影響中國2013年度文化人物
‧中國當代最常被查禁的作家
‧中國最具反叛精神的作家
序
作者序
被這一叢書書名所吸引——「黑白閻連科」。也就有了欣喜和欣然,感激著支持這書出版的臺灣同仁們。
我是一個相當矛盾、糾結的人,不相識的多說我好,而相識之後,便不再這樣說道。繼續近之,更想遠之。所以朋友偏少,也生怕別人認真瞭解,又常常渴望別人真正瞭解。可卻一旦成為朋友,會總是想著肝膽相照;然倘若有了生死牽累,自己也沒有把握自己會有怎樣的情舉義措,會背叛還是會執著情念,生死相依,同歸暗黑的末路。總之去說,人很黑白,相當混淆,矛盾到扯不清明,難說二一。就我自己,靜心去想自我時候,也不會把自我當做一個甚好或甚壞的東西看待。常想在這世上,其實你也是一個錯人罪人,不知有過多少錯事惡念。想有一天提筆去回望自己,如果膽略和勇氣可以讓我把自己的魂靈剝開來看,那人不知該是怎樣的虛妄和醜陋,只是偽裝,只是理想,只是一種執著和克制,才使大家看到了我今天的嘴臉,今天的這幅模樣。
盼望有一天可以養大育壯剝開自己靈魂的勇氣。可以寫出《懺悔錄》那樣的一部書來,讓真正的坦蕩,回到體內。讓混沌的黑白,成為清明的界線。現在,不僅我沒有這赤裸的勇氣,也還沒有挨到那個時候。
去說我的文學;去說我的寫作。本是沿著自己的感悟執著地走,可其結果,卻成了今天這幅異人模樣。讓人議論,讓人黑白,讓人矛盾和混淆。爭論是不消說的;批判是不消說的;有組織的罵和嘲弄,我也都聽到和看到。也知道,說好的不僅是對我文學的尊重,也還多少有著同道的那份情義與支持。說壞的,怕也還有著某種力量和利益。對支持說好者,報以情義;對罵和嘲弄者,細聽細辨,淡然處之。別人說你是中國最受爭議的作家,說你某某作品最好,或最為垃圾,我都聽著想著,修正著、固執著,黑白混淆著。這套「黑白閻連科」,其實是「黑白中篇四書」吧。雖是中篇,也足可以讓大家看到閻連科的文學黑白,明清出一條文學的楚河與漢界;或者,明清出一個混沌但卻來去鮮明的文學之壺口。總之去說,這一中篇的選叢,是為了閱讀的門扉和便捷,是認識閻連科的洞開和撕裂;是讓人知道,他(它)終歸是他(它),不是別的,不是別人;也還為了,因著閱讀而讓人對閻連科和他寫作的黑白淆混與糾結糾纏,有一條淺近的條理與辨析。
不希望你熱愛他(它),只希望你明白他(它)。
不希望你熱愛和喜歡他的文學和寫作,只希望你認識他的文學和寫作。
如此而已。
被這一叢書書名所吸引——「黑白閻連科」。也就有了欣喜和欣然,感激著支持這書出版的臺灣同仁們。
我是一個相當矛盾、糾結的人,不相識的多說我好,而相識之後,便不再這樣說道。繼續近之,更想遠之。所以朋友偏少,也生怕別人認真瞭解,又常常渴望別人真正瞭解。可卻一旦成為朋友,會總是想著肝膽相照;然倘若有了生死牽累,自己也沒有把握自己會有怎樣的情舉義措,會背叛還是會執著情念,生死相依,同歸暗黑的末路。總之去說,人很黑白,相當混淆,矛盾到扯不清明,難說二一。就我自己,靜心去想自我時候,也不會把自我當做一個甚好或甚壞的東西看待。常想在這世上,其實你也是一個錯人罪人,不知有過多少錯事惡念。想有一天提筆去回望自己,如果膽略和勇氣可以讓我把自己的魂靈剝開來看,那人不知該是怎樣的虛妄和醜陋,只是偽裝,只是理想,只是一種執著和克制,才使大家看到了我今天的嘴臉,今天的這幅模樣。
盼望有一天可以養大育壯剝開自己靈魂的勇氣。可以寫出《懺悔錄》那樣的一部書來,讓真正的坦蕩,回到體內。讓混沌的黑白,成為清明的界線。現在,不僅我沒有這赤裸的勇氣,也還沒有挨到那個時候。
去說我的文學;去說我的寫作。本是沿著自己的感悟執著地走,可其結果,卻成了今天這幅異人模樣。讓人議論,讓人黑白,讓人矛盾和混淆。爭論是不消說的;批判是不消說的;有組織的罵和嘲弄,我也都聽到和看到。也知道,說好的不僅是對我文學的尊重,也還多少有著同道的那份情義與支持。說壞的,怕也還有著某種力量和利益。對支持說好者,報以情義;對罵和嘲弄者,細聽細辨,淡然處之。別人說你是中國最受爭議的作家,說你某某作品最好,或最為垃圾,我都聽著想著,修正著、固執著,黑白混淆著。這套「黑白閻連科」,其實是「黑白中篇四書」吧。雖是中篇,也足可以讓大家看到閻連科的文學黑白,明清出一條文學的楚河與漢界;或者,明清出一個混沌但卻來去鮮明的文學之壺口。總之去說,這一中篇的選叢,是為了閱讀的門扉和便捷,是認識閻連科的洞開和撕裂;是讓人知道,他(它)終歸是他(它),不是別的,不是別人;也還為了,因著閱讀而讓人對閻連科和他寫作的黑白淆混與糾結糾纏,有一條淺近的條理與辨析。
不希望你熱愛他(它),只希望你明白他(它)。
不希望你熱愛和喜歡他的文學和寫作,只希望你認識他的文學和寫作。
如此而已。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2016/09/04
2016/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