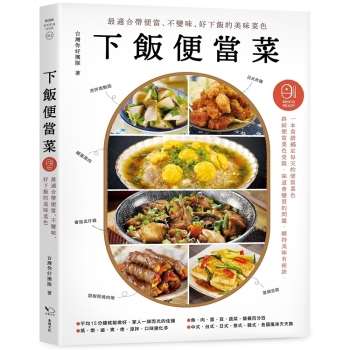安靜
「明天就開始限電。我看市役所網頁分成兩個區域,這邊是哪一個呢?」
「我們也不清楚……停電會使社會上出現很多問題。若可能,妳最好暫時離開東京。」
‧
地震後三天,我暫時離開東京,但並沒有「逃」離;超市貨架上的東西幾乎都空了,但是並沒有「搶」購一空。每個人都在排隊,安靜的排隊,在電車有半數以上停駛的月台上排隊,在已經沒什麼東西好買的超市結帳區排隊。很多人很多人……很有秩序的安靜的排隊。
三一一日本東北強震,震度五的東京嚴格說來不算災區,因為防震標準高,在密集的都市中,除了少數火警或屋頂掉落之外,建築的毀損幾乎是沒有的。但東京面臨的嚴峻在災後才正要開始,不僅做為「糧倉」的東北地區全毀,更糟的是核電危機。核電廠的狀況就好像人類養了一頭怪獸,忽然失控連飼主也不知牠變成什麼厲害的模樣,既無力控制、想「壯士斷腕」殺害卻又殺不死。
因為是一個人在東京,又遇到放假校園空無一人,不得不整天盯著電視看即時訊息。看久了讓人胸口窒悶,決定出去走走。災後的週末是晴天,社區人們在冬陽下呈現祥和安定的景象。東京人一面懷抱著不安、一面在過「正常生活」吧,我想。福島核電的憂慮持續著,東京人怕不怕呢?我沒有問東京朋友這個「無聊」的問題,因為無論如何這都是自己的國家,就算貨架已幾近全空,輻射危機一一逼近,氣氛彷彿像災難電影最愛使用的「風雨前的寧靜」。但電影畢竟是電影,這裡是他們的家園,人們除了用自己的步驟生活著還能如何。如果我對核電憂慮,要不趕快回台灣,要不就也是慢慢等待,不然對方能給我什麼答案?
到摩斯漢堡去喝咖啡,店內有三兩學生低聲討論功課,有溫暖笑臉的女店員說:「三月十二日是摩斯日。」所以遞給我一份折價券和幸運草的種籽,打開卡片內頁有各地蔬果以及農民的笑臉,一瞬間我的心好像被撫慰了。想著去年此日我也剛好光顧了台北的摩斯,拿到了紀念品,這是什麼訊號嗎?我要不要回台灣呢?
可是這個城市好安靜啊。也許哀傷、恐懼、不安,但是安靜。
為什麼這麼安靜呢?台灣與國際媒體已經對日本人在世紀災難下展現高度秩序與自制力,給予一致正面的評價,並深感敬佩。能安靜鎮定也許是來自防災的訓練有素,也或許是民族性、以及國民素養,我也有同感。但是幾天來我卻也忍不住想:為什麼這麼安靜啊?這不是問句,而是不忍。日本記者在災區訪問,災民說到失去的親人與家園,眼淚默默從臉上流下;眼見家人遺體,一面低聲而哀傷的啜泣還跟救難人員合十道謝;說到對未來的不安,眼前物資的短缺,憂懼深深藏在眼神裡。
不管是不是教育或法律的關係,如果像許多人說:「怕麻煩」和「避免麻煩別人」似乎已經內化成日本民族性的一部分了。那麼,我想,大聲哀嚎、呼天搶地、推擠搶先,就算是情緒的表達,大概都有違這個原則,特別是在共體國難的時刻。這種內斂與自制也反應在新聞播報上。屬於「台式風格」的高亢聲音是不可能出現的,更難以想像新聞畫面像綜藝節目一般任意打上大大的「慘」、「悼」、「哀」五花八門的印記,忽然「衝」進車站訪問乘客當然也讓人驚愕……媒體的衝鋒陷陣有好有壞,大家各有感受。只是這就是日本。
災後第二天,核電狀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危機加深,還在猶豫該不該離開的時候,東京電力開始宣布限電。第三天一早,日本朋友就建議我盡速離開東京,限電之後隨之而來的電車限駛、限水、限瓦斯,問題會愈來愈多,我立刻意識到東京已無法「正常生活」。東京人既已如此,恐自顧不暇,何況隻身的外國人?
東京電力、電車停電停駛的訊息連結,一早就自動發布在臉書、推特上,在日本的使用者不管有沒有「加入好友」一律都會收到。不知短時是否能再回到東京,我盡可能把能帶的行李帶著,在網路上確認電車訊息,進入因節電而電梯停擺的車站,奮力將行李拖上月台。愈往都心人愈多,電車減班,月台隨時大排長龍,但還是很安靜啊,沒人奔跑也沒人推擠,沉默安靜的排著隊。也許是因為這樣的秩序,所以我也可以不害怕吧,即使歸途仍充滿變數。
終於在羽田機場等待登機的時候,靜下來的我想起那些安靜的畫面:止不住的默默的眼淚、低聲而壓抑的啜泣、災區盼不到物資的無聲等待、沉默的排隊排隊排隊……忽然感到巨大的悲傷往胸口襲來。
曾經因為這個社會的安靜自制而喜歡,因為到哪裡都可以不受打擾、不被無禮的侵犯,咖啡店裡可以看書不會有哇啦哇啦大聲講話的吵雜,公車上不會被迫聽別人手機的大方對話……但這個時候我卻想說:可以不要這麼安靜吧。在台灣因為地震而跑出來的人不論識與不識都會互相嚷嚷嚇死了嚇死了,去超市搶貨一定亂糟糟可能還互罵,災民對著鏡頭大無畏的嚎哭,缺乏物資的憤怒立刻爬上嘴邊,也許整個「有勇無謀」像無頭蒼蠅,不知怎麼好像有種生命力。
「怕麻煩」和「避免麻煩別人」的有禮社會,另一面其實也是「我不麻煩你」、「請你也不要麻煩我」的同義,在關鍵時刻便顯出一種「有禮的冷漠」。譬如學生在八點的夜裡遇色狼襲擊,整條街狂奔喊叫沒有人探出頭聞問;譬如因為車站電梯停擺我拖著十七公斤的行李吃力上階梯,不會有人伸出援手;在這社會是正常的,因為「怕麻煩」,也怕「造成別人的麻煩(人家又沒說需要幫忙)」。彷彿看見別人的狼狽是無禮的,要趕快避開才是,若是如此,那麼暴露自己的狼狽便是難堪的,既是難堪的還呼天搶地無視於他人豈非更無尊嚴。
你們怕不怕呢?我不會問日本朋友這種「無聊」的問題,只會懷抱著祝福。
但是,其實不用這麼安靜的,真的。有時候就像在被埋在瓦礫堆的嬰兒,只管坦率而奮力的大哭就對了。
靠近
我上了四樓,如往常一般來得早一點,所以站在走廊的窗檯邊等著下一節課的開始。因為地震關係延後開學的大學,在我回到東京時剛好開始了第一周,我以觀摩者的身分了參與了這個課堂,偶而提供一些台灣文化、風俗等問題的解答。從剛開始的陌生,到後來學生們對於這位每周都會出現的台灣老師雖也說不上熟識,但也都習慣了。
「映像台灣(從影像看台灣)」是通識課,不知大家是懷抱什麼心情選擇這門課的,但其中有一位工科的男學生很明顯對課程、對台灣充滿了興趣。三一一大地震的時候是日本的春假,這位男學生在假期到了台灣一遊,正好遇見台灣人為日本三一一震災展現捐款與慰問的熱情,讓他感受甚深。所以課堂的參與感也比其他人強烈。
每次在看完影片的討論時刻他都會發問,課後的心得作業也寫了不少。雖然問題的本身顯示他對台灣其實是陌生的,但因為喜歡,所以每一個「陌生」都成為他想要去瞭解的開始。
漸漸的,他發問的時候不僅望著H教授,有時也會看看我,並似懂非懂的聽著我的解答。
有幾次下課後,他上前問問題,還與我和H教授並肩走下樓,所說的都是他短暫到台灣的經驗與認識,配合著這學期課堂才學習到的台日相關歷史,明顯懷有高度興趣。不過我和這名學生倒沒有單獨接觸過。
學期就要結束了,現在他站在我身邊大約一公尺左右,一樣等著進入下節課的課堂,他看看我,我對他微笑點頭。忽然想到,作為老師的我是不是應該主動過去招呼這個學生,對於他的高度學習精神表示讚許,並且鼓勵他學習中文,有機會可以到台灣讀書,或者,到我的課堂來?……
學生很靦腆,我也很猶豫,下節課教室開放了,這樣的心思也瞬間結束。
其實日本媒體在多年前就自立了公約(默契),對於台灣「身分」的報導始終是很模糊的,加上日本諱言戰敗的歷史,官方在正式場合對台灣冷處理,許多日本學生對於日台殖民史毫無所悉也十分「尋常」。兩年前我也曾到過這個課堂,當時便因學生幾乎對台灣「一無所知」而感到吃驚。
沒想到因為一場世紀災難的台灣熱情解囊,在日本民間引發意想不到的效應,也帶動了一些年輕人主動關注台灣,並在社群網站上熱烈討論。
所以,這位學生也可說是因為災難的「機緣」而來認識台灣的吧。
距離,因為災難而拉近了。
但災難,真的是會讓人因此而靠近嗎?還是,讓人看見疏離的真相?
‧
三一一大地震發生的下午,台灣很快就得到了消息,因為太過震撼,台灣媒體的報導又一向驚悚。電話雖然斷線但所幸網路是暢通的,知道我隻身在東京的各地朋友都紛紛捎來關心。有的非常迅速、有的則在一天兩天之後;有的持續關心著、有的如打卡應卯;有的不動聲色彷彿希望我先主動報平安……
我在電腦前看著這些朋友,感謝這些朋友的心意,但彼此也有種「重新調整」的認識。
天搖地動後第三天東京電力毫無緩衝期的宣布開始分區限電,社區很暗很安靜,我想像大家都在家中依偎取暖。我無法依偎,坐在床上開始盤算如何在停電的深夜度過仍會下雪的寒冬。電爐電毯電熱器之一切需要電的東西都無法使用,用瓦斯燒熱水還可以,不知會有熱水保溫袋嗎?清查電池後剩下兩顆,沒事就不開手電筒吧,並且記得先把電腦手機的電充滿。還有什麼呢?我需要地震笛嗎?
一個人在夜裡沉沉睡去。醒來後看電視都懷抱狀況變好的希望,但卻一次一次壞。三一一震災最棘手的不在地震本身,而是隨時充滿威脅的核電廠災變。福島二號機小幅氣爆後,要我回台北的呼喚湧進信箱,每一封都是擔心的語氣。
珍貴的情義,對照無論如何都改變不了的災難孤絕,愈發顯出人生在有常與無常之間難料的殘酷。
但真正的殘酷還在於,災難讓人知道人心如此靠近,也無可避免考驗了感情。
出發到東京之時,彷彿始終站在我身邊,說要到東京來看我的人,此時若說一聲「因為東京現在的狀況不太好所以取消了」,自然是合情合理的;如果說「倘若妳不回來,我還是到東京去看看妳吧」,便意外顯出情感的重量;然原本積極異常,至此卻彷彿擔心自己必須在「亂世」履約,就提也不提假裝從來沒有約定過的……內心除了啞然失笑,大約也能從中領悟「所謂感情」的真實模樣。
真正靠近的彼此,是願意為對方涉險,但對方絕不會願意你為他涉險。這是災變下最動人的互愛。人們總是喜歡看這樣的新聞,歌頌這樣動人的故事,成為太殘酷的災變下人性的救贖,用以撫慰倖存的人,以及因這一切心神震撼的旁觀者。
但如果這靠近的兩人,並不是人們認知中「應該」的那兩人呢?
‧
人們喜歡不離不棄的故事。也的確有許多不離不棄的故事在震災中上演。但同樣真實的是,災難發生時忽然發現另一半居然自顧自的逃生、或者只顧保護他最重要的東西,甚至那個本能反應想「不離不棄」、「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對象竟然不是自己。我們歌頌了這樣的在災難中仍努力靠近的心意,也許背後就是另一方領悟了自己「被放棄」的殘酷事實。
幾個月過去,倖存者的後遺症也逐漸出現。以家庭關係來說,新聞報導災後訴請離婚事件增多,至今在日本搜尋網站上打入「三一一離婚」關鍵詞,還是能看見一連串的討論資訊。被核災間接波及的東京,生活與人生信念的選擇都成為全新的課題。因為生活議題不是紙上議題,關於食物、關於居住,都是無法迴避的日日實踐。有些連人生觀也起了變化,才發現彼此所想走上的人生道路是多麼的不同。
災難讓人體悟人生苦短,有些人更加珍惜緊密靠近的時光,有些人則驚覺須積極追尋自由,自己毀棄了原本守住的家庭秩序,義無反顧的離開。
日本導演是枝裕和在二0一一年連載的專欄結集《宛如走路的速度》中說道:「三月十一日前後,展現在我眼前──也包括過去──的世界的意義,便起了很大的轉變。」
對我來說,這所謂的「世界」,還包括了人生與人情的體悟:災難中的確需要溫暖撫慰,但孤絕仍與之並列,是無法相互抵消的。對於沒有共處當下的人,我們有時只能把獨有的孤絕記憶藏起來。重新去定義「永恆」的價值。
短暫返台重新回到東京,在民生日常稍稍穩定、並摸索出新的規律後來到了夏天。災後仍不放棄約定的朋友說:「只要妳回去(東京)我(們)就會去」。作為盡責勸阻的朋友,我提供了許多在觀光宣傳辭令之外,該不該到東京旅行的資訊,以及必須注意的事項。作為情義的回報。
後來在東京見面,即使只是在摩斯漢堡內喝一杯冰紅茶,或者僅是在吉祥寺井之頭公園散步聊天,都覺得「是的,我們如此靠近」。不僅在東京見面的彼此,縱使見不了面,我也在心裡一一記下了那些災變以來始終不懈怠的關心;而那些過不了災變考驗的關係,就算見了面,心裡知道是再也無法「靠近」了。
‧
最後一節課結束,和H教授步出教室,那位工科學生一直伴隨著我們、聽著我們有關台灣與日本文化的討論。隔著H教授,我看見他求知的表情。這學期我們看了幾部台灣電影,包括侯孝賢王小棣李安魏德聖。「所以,你因此而更加認識台灣了嗎?」我想這樣問。「因為三一一捐款而讓你覺得『靠近』的台灣,是真正的靠近了嗎?」我也想知道。
但這對一個才修了一學期的通識課的大二工科男學生來說,應該是太為難了。
祭典媽媽
日本的夏季是充滿祭典的季節,因為如此,村上春樹說自己很喜歡夏天,覺得是個有活力並且開心的時光。但這年日本的夏天有悲傷的基調,因為震災與核災的關係,關東、東北的人們不僅沒有心情、也不敢去有輻射污染的海邊,夏季花火大幅取消,東北夏日祭典等不到觀光客,雖然仍勉強維持住一些夏日「儀式」,但大家心裡都明白這不是「真正的夏天」。
凝聚社區意識的「夏祭り」就是必須維持住的活動,一定要經過大大小小屬於「園遊會/遊藝會」式的「夏祭り」,宣告夏季的來臨才行。這些社區或大小學校的活動,都必須靠家庭的支持「協力」完成,像社區活動的擺攤、表演、佈置等等,無一不是自發性的支持,說是自發性,當然有種不容間斷的凝聚與互助意義,像商店街的組織通常就很堅固。
參與這種活動最累的其實就是主婦們,男人一旦有社區參與的熱忱(或興趣),準備餐食、張羅孩子表演的衣物、以及大大小小的瑣事就落在主婦身上。所謂主婦未必是沒有工作的婦女,但以日本社會對主婦的價值期待,「主婦的工作」永遠凌駕其他「不重要」的身分之上。
如果是樂在其中的婦女當然無所謂,但是不是樂在其中,「蠟燭兩頭燒」的婦女也不會跟其他人透露,這一方面違反日本社會價值,一方面也會被認為這是身為「女強人」自己必須去解決的問題,「失職主婦」不會獲得「同情」。
社區參與還說有選擇性,但學校的活動就完全無法「自由」,我的東京朋友身為大學教授,為期末事務忙得焦頭爛額,卻接到孩子保育園來的通知,說七月某週末要舉辦每年例行的「夏祭り」,孩子們要跳民俗舞,雖然知道媽媽們都很很忙,但也請協力幫孩子縫製舞衣。所謂舞衣就是小男孩跳日本民俗舞那種深藍色簡單浴衣,說是簡單,但剪裁、縫製,領口胸襟的對稱與襯裡,都需要費時費工。而且沒做過衣服的人,看那一張專業的「和裁」圖示根本就像天書!
「居然附了一張裁作圖示?」我有點驚訝。難道是建立在女性(媽媽)都必須會手作的前提上?
「這個要求的確是建立在這前提上的。」對方說。
意即這是身為主婦應該有的能力,無論如何都「請協力」完成。這個協力當然關係著自己以及孩子的顏面,不然上場那天沒衣服穿,或因為沒衣服穿而無法上場,讓孩子當場心靈受創,就是失職媽媽的最好註腳。
「妳看看,這不是找麻煩?明明知道職業婦女忙到翻,還是要媽媽們協力。」
「這種衣服不能用買的?」我很疑惑。
「當然可以,而且還便宜得要命!但保育園覺得媽媽有參與的責任,不能認為孩子送到保育園就算了。但媽媽就是因為沒辦法才會送孩子去保育園哪!」
「那怎麼辦?」
「有些媽媽就咬牙花一星期做到三更半夜。但像我這種忙到不行的怎麼可能,也不想做。這是整人嘛。」
「有代做的地方嗎?」
「有啊,可是非常的貴!好像要懲罰這些不會女工的媽媽一樣,代做費用大概可以買全新的衣服十件。而且時間還要提早預約。」
朋友最後把「那塊布以及製作圖」一起寄給了家鄉的日本婆婆請她幫忙,並且交代孩子就跟老師同學說是奶奶做的沒關係,她不想孩子過虛偽的人生。「反我就是這樣的媽媽,會不會做衣服跟失職根本無關。」她說。
因為某些元素,台灣有些女性也許對日本主婦生活充滿戲劇般的憧憬,但以多半具備自主意識的台灣女性來說,進入日本家庭,如果不是天生就對「主婦」一職充滿渴望,並且願意成為「依附性」的存在,那些快樂做愛妻便當、愛兒便當的生活背後,不可能毫無內在的衝突。日本社會對於「主婦制」的依賴,儘管因為經濟環境的改變,時至今日也有「雜音」,但是這長久以來的「分工」維繫了這個社會的穩定,似乎還是獲得了絕大多數男女的認同。
這使我想起夏天的颱風假。
氣象預測強颱即將橫掃東京的時候,我問東京朋友:「什麼時候會宣布要停課停班?」
「不一定。」
「那停班停課的標準是什麼?」
「就是看各單位的判斷吧。」
「咦,沒有類似台灣『人事行政局』之類的統一宣布嗎?」我問。
「沒有。」
原來日本沒有「颱風假」。沒有那種「統一宣布」的颱風假。
各個學校依照自己的情況,認為會危害學生安全了,就通知停課。各機關單位也一樣,所以有可能這家銀行放假了,那家還照常營業。
像這種「放假大亂」的情形,在台灣應該會被罵翻,或者立刻灌爆政治人物網站吧。關鍵民怨來自少子化社會、「生育為大」的父母心聲:孩子停課,我們卻要上班,那可怎麼辦?政府有體諒嗎?
同樣少子化的日本社會,並沒有因此想減輕父母「重擔」的意思。孩子停課大人要上班的狀況似乎常常有,所以父母雙方一定要有人請假帶小孩。不只如此,如果孩子在學校發燒了,絕對要請父母帶回家,不可能讓孩子留在學校傳染別人。學校有活動,也沒有什麼「統一訂外賣」這種事,午餐一定要家長幫孩子準備便當。因為這些本來就是「父母的責任」。
日本近年景氣不佳,上班族苦哈哈,雙薪家庭不少,養育孩子也很辛苦。但社會上對於「父母的責任」絲毫沒有鬆綁的意思。只是,可以理直氣壯大聲說「我要上班」、取得「社會正義」的一方還是男性(爸爸),女性(媽媽)不將工作放下來帶小孩就得不到同情。這也是女性在職場上的困境。
比起日本,台灣環境對於小孩還算是「友善」的,小孩在公共場合(甚或高級餐廳)大吵大鬧,幾乎都被能容忍;颱風假只停課不停班招惹民怨,大家也都覺得有理。
那天在日本的大學校園裡,有位推著娃娃車的媽媽被下課時學生飛馳的單車撞了,娃娃車也傾倒。媽媽扶起娃娃車後立刻跟學生說「對不起」,因為上課時間的校園本來就不屬於民眾,讓孩子陷入「險境」,又造成學生困擾,是媽媽自己的責任。
儘管如此,日本的生育率還是稍稍高於台灣。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東京暫停的圖書 |
 |
東京暫停 作者:黃雅歆 出版社: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11-20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10 |
二手中文書 |
二手書 |
$ 177 |
Others |
$ 213 |
小說/文學 |
$ 220 |
中文書 |
$ 220 |
文化研究 |
$ 220 |
Others |
$ 225 |
現代散文 |
$ 225 |
文學作品 |
$ 225 |
中文現代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東京暫停
暫停
離開原先日常的節奏,到另外一個國家去擔任客座研究員。不是旅客、不會久居,停留時間長到足以跟周圍的環境建立起一種關係、也短到會有離開的一天,回到原先的日常。
在東京的如常生活,311後也產生了變化,無法再一如往常。
作者黃雅歆,以一種既疏離又親密的角度,書寫自己的、旅居者的、在地人的東京的生活;身為外人所觀察到的文化差異、一般常民在經歷過災難後的反應。
一篇篇觀察手記,一個個暫停裡的生活。
書籍重點
作者於2008年與2011年以客座研究員身分至日本國立一橋大學研究,311東日本大地震之後於《聯合報》副刊「東京朝顏」專欄撰寫400字小品文專欄。本書為專欄的擴充與改寫。
‧2008年與2011年兩度到日本國立一橋大學,將近一年的東京生活觀察與紀錄。
‧日台文化的家常與人際往來的差異體驗。
作者簡介:
黃雅歆
臺灣大學中文系、中文研究所碩士,輔仁大學中文所博士。現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曾獲臺大文學獎、梁實秋散文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作品常見於《聯合報》副刊、《自由時報》副刊,入選各類散文選集與作文教學範本,並多次擔任國內文學獎散文類評審委員。
在2008年與2011年以客座研究員身分至日本國立一橋大學研究,311東日本大地震之後於《聯合報》副刊撰寫「東京朝顏」小品專欄。
著有散文集《旅行的顏色》、《無人的遊樂園》,以及唐詩導讀《不可不讀的五十首唐詩》、《值得大聲朗讀的五十首唐詩》等。
章節試閱
安靜
「明天就開始限電。我看市役所網頁分成兩個區域,這邊是哪一個呢?」
「我們也不清楚……停電會使社會上出現很多問題。若可能,妳最好暫時離開東京。」
‧
地震後三天,我暫時離開東京,但並沒有「逃」離;超市貨架上的東西幾乎都空了,但是並沒有「搶」購一空。每個人都在排隊,安靜的排隊,在電車有半數以上停駛的月台上排隊,在已經沒什麼東西好買的超市結帳區排隊。很多人很多人……很有秩序的安靜的排隊。
三一一日本東北強震,震度五的東京嚴格說來不算災區,因為防震標準高,在密集的都市中,除了少數火警或屋頂掉落之外,...
「明天就開始限電。我看市役所網頁分成兩個區域,這邊是哪一個呢?」
「我們也不清楚……停電會使社會上出現很多問題。若可能,妳最好暫時離開東京。」
‧
地震後三天,我暫時離開東京,但並沒有「逃」離;超市貨架上的東西幾乎都空了,但是並沒有「搶」購一空。每個人都在排隊,安靜的排隊,在電車有半數以上停駛的月台上排隊,在已經沒什麼東西好買的超市結帳區排隊。很多人很多人……很有秩序的安靜的排隊。
三一一日本東北強震,震度五的東京嚴格說來不算災區,因為防震標準高,在密集的都市中,除了少數火警或屋頂掉落之外,...
»看全部
作者序
【代序】我羨慕你
我羨慕妳。
暫離臺北到東京的時候,我的同行朋友(包括東京的同行朋友)這麼對我說。我明白這不是因為我個人的因素,也未必是因為這個城市,而是因為「暫停」。
我的職圈(也許其他的職業也一樣)日益以追逐各種量化評比為導向,逐漸遠離自己最初認識的樣貌。因為夾雜各種資源的劃分,打分數只有及格與不及格兩種,同行之間的關係有時也變得詭譎。像我這樣身在職圈卻盡量過著「繭居圈外」生活的人未必得到認同,當然也沒什麼可羨的。但我知道那些真心說羨慕的朋友,彼此都是懂得的,因為在感到疲累的既定軌道中,能擁...
我羨慕妳。
暫離臺北到東京的時候,我的同行朋友(包括東京的同行朋友)這麼對我說。我明白這不是因為我個人的因素,也未必是因為這個城市,而是因為「暫停」。
我的職圈(也許其他的職業也一樣)日益以追逐各種量化評比為導向,逐漸遠離自己最初認識的樣貌。因為夾雜各種資源的劃分,打分數只有及格與不及格兩種,同行之間的關係有時也變得詭譎。像我這樣身在職圈卻盡量過著「繭居圈外」生活的人未必得到認同,當然也沒什麼可羨的。但我知道那些真心說羨慕的朋友,彼此都是懂得的,因為在感到疲累的既定軌道中,能擁...
»看全部
目錄
‧代序──我羨慕你
卷一 裂縫
‧卒業之後
‧安靜
‧曬衣服
‧超市的表情
‧大學湯咖哩
‧食物的鄉愁
‧粽子
‧公民館與D女士
‧智子與久留米
‧靠近
‧正常生活
‧「應援」的熱血
‧請協力,與不要忍耐
‧不要麻煩
‧新生之光
‧靜止的空間
卷二 朝顏
‧閃亮與停滯的記憶
‧星巴克女生
‧狸,蛇、猴以及蜘蛛
‧單人用餐
‧「個室」的美味
‧家庭餐廳
‧祭典媽媽
‧和機器打交道
‧生活的紀念單
‧蔦屋與TSUTAYA
‧睫毛膏及其他
‧無時差按鍵時代
‧知惠袋的作弊
‧寶寶之路
‧暫停的時間
‧生活的依賴
卷一 裂縫
‧卒業之後
‧安靜
‧曬衣服
‧超市的表情
‧大學湯咖哩
‧食物的鄉愁
‧粽子
‧公民館與D女士
‧智子與久留米
‧靠近
‧正常生活
‧「應援」的熱血
‧請協力,與不要忍耐
‧不要麻煩
‧新生之光
‧靜止的空間
卷二 朝顏
‧閃亮與停滯的記憶
‧星巴克女生
‧狸,蛇、猴以及蜘蛛
‧單人用餐
‧「個室」的美味
‧家庭餐廳
‧祭典媽媽
‧和機器打交道
‧生活的紀念單
‧蔦屋與TSUTAYA
‧睫毛膏及其他
‧無時差按鍵時代
‧知惠袋的作弊
‧寶寶之路
‧暫停的時間
‧生活的依賴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黃雅歆
- 出版社: 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11-20 ISBN/ISSN:978986581344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08頁 開數:25開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