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蔗〉十一-五月
學齡前寄養在外婆家,當時高雄市三民區還很像鄉村。舅舅有一片果園,外公種田、養豬,外婆種菜、飼養雞鴨。農村廚房裡有一個大爐灶,煮過晚餐,外婆輒用灶內餘火烤甘蔗,未削皮的甘蔗受熱,糖水緩慢滲出表皮,有些凝結,有些猶豫滴落,宛如眼淚。我曾在〈外婆〉一詩中懷念:「暗夜的爐灶有回憶的餘燼/甘蔗偎在裡面流淚/輕語如體溫」。取出熱甘蔗,咬掉蔗皮,咀嚼間流動著甜蜜,溫暖,快樂,幸福感。這種幸福感竟永遠鮮明在記憶中。
似乎不會有人覺得甘蔗不好吃。中國最早出現甘蔗的文獻是《楚辭.招魂》:「胹鱉炮羔,有拓漿些」。柘,通蔗;柘漿,甘蔗汁。連橫《臺灣通史.農業志》將臺灣甘蔗分為三類:「竹蔗:皮白而厚,肉梗汁甘,用以熬糖。紅蔗:皮紅而薄,肉脆汁甘,生食較多,並以熬糖。蠟蔗:皮微黃,幹高丈餘,莖較竹蔗大二、三倍,肉脆汁甘,僅供生食」。竹蔗又稱高貴蔗,外皮綠色,質地粗硬,不適合生吃;紅蔗即中國竹蔗,皮墨紅色,莖肉富纖維質,多汁液,清甜嫩脆。
這種經濟作物產於熱帶、亞熱帶,栽培非常普遍,全球有一百多個國家出產,以亞洲為大宗,其次是中南美。甘蔗適合栽種於土壤肥沃、陽光充足、冬夏溫差大的地方,是製造蔗糖的原料。秋天的時候,甘蔗成熟,榨汁製糖。吳德功〈竹蔗〉:
蔗圃千畦植,村農利溥長。
節多如竹秀,葉密似葭蒼。
揭揭風吹響,湛湛露釀漿。
待當秋九月,處處獻新糖。
甘蔗種植連接著殖民,奴隸,剝削。荷治時期,臺灣長官定期向東印度公司例行報告,《巴達維亞城日記》一六二四年二月記載,蕭壠(Solang,即今之佳里)產甘蔗,及許多美味之鮮果;荷蘭東印度公司招募漢人來臺種甘蔗,生產蔗糖賣給日本。清道光年間詩人陳學聖〈蔗糖〉:「剝棗忙時研蔗漿,荒郊設廓遠聞香。白如玉液紅如醴,南北商通利澤長。」
日據時期,總督府政府更大規模種植甘蔗,臺灣俚語「第一憨,種甘蔗乎會社磅」, 反映了壓榨剝削的製糖株式會社。古巴詩人尼古拉斯.紀廉(1902~1989)長期流亡國外,以詩控訴帝國主義者剝削、壓迫黑人,直到古巴獨立才返回祖國。短詩〈甘蔗〉應是流亡時期之作:
黑人
在甘蔗園旁
美國佬
在甘蔗園上
土地
在甘蔗園下
鮮血
從我們身上流光 !
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描寫日據時代的製糖會社,「一片青青而高高的甘蔗園,動也不動;高聳著煙囟的工廠的巨體,閃閃映著白色」。這段描述連接了我的橋頭糖廠、甘蔗林印象。很多糖廠附近的人,童年時曾經追隨著五分車奔跑,從成綑疊堆的甘蔗板車上偷偷抽取來吃。那是一個多麼飢餓的年代呵,飢餓,卻不乏甜蜜。
郁永河有一首詩描寫蔗田:「蔗田萬頃碧萋萋,一望蘢蔥路欲迷。綑載都來糖蔀裡,只留蔗葉餉群犀」。甘蔗長得瘦高,蔗田茂密,走進去立刻隱沒,只聞蔗葉細碎的沙沙聲,蔗香幾乎就封鎖了個人的世界。彷彿宿命,甘蔗採收之前會先歷經整個颱風季,風災過後, 東倒西歪的甘蔗人為地重新站起來,不免就長得彎曲。芳香甜美前的磨練和摧折,彷彿隱喻。
每逢盛產的季節,飲料攤前常見甘蔗汁,或添薑汁,或加檸檬汁、桔汁調味。尤其貨車上疊滿長長的甘蔗,飄送著歡愉的甜香,堪稱臺灣街頭最甜蜜的風景。甘蔗生長過程中, 汲取的養料多貯藏在根部,故下半截較甜,東晉畫家顧愷之謂倒吃甘蔗為「漸入佳境」。
甘蔗汁好喝,可惜缺少咀嚼的快感。吃甘蔗是複雜的口腔運動,得邊啃邊吸邊嚼,只有吃過的人才能心領神會。焦妻生前嗜甘蔗,下班回家時看見攤車輒命我路邊停車,買一包帶回家。她總是坐在沙發上抱著甘蔗,悠閒嚼食;我牙齒動搖,只能望蔗流口水。從前常嘲笑她是好吃的懶妻;奇怪,如今竟覺得她嚼食甘蔗的慵懶模樣很優雅。
〈玉米〉全年,十月-隔年五月盛產
中午下課後趕赴海洋大學演講,我知道沒有時間坐在餐廳裡吃飯,只能買速食路上吃。外帶車道效率超高,五分鐘之內即完成了點餐、付款、打包:漢堡、薯條、可樂。我單手駕車,在高速公路上以時速一百一十公里單手吃著這些速食,心知肚明所吃的其實都是玉米:那塊漢堡有玉米甜味劑,肉餅和起司是吃玉米的乳牛所轉化,那杯可樂和番茄醬都含有高果糖玉米糖漿,炸薯條的油也來自玉米。連奔馳中這輛車也在吃玉米──燃油中摻入了乙醇。吃太快了,一坨美乃滋掉落襯衫上,美乃滋當然也有高比率的玉米。
絕大部分的美國玉米屬基因改造,玉米商為擴大產量,以基因改造方式培育出產量巨大的超級玉米,美國乃成為世界最大的出口國。約有40 % 玉米用來製造乙醇。剛成型的玉米芯,約一寸長,即作為蔬菜的玉米筍。玉米脫粒後通常磨成粉狀,間接製成食品、調味料;胚芽可以提煉玉米油。
玉米原產於中美洲,乃印地安人主要的糧食作物,十六世紀傳入中土。相對於歐洲的小麥文明、亞洲的稻米文明,拉丁美洲可謂玉米文明。一萬多年前,拉丁美洲就有野生玉米,印第安人種植玉米也已經三千五百年。
古印第安神譜中,有好幾位玉米神,祂們都象徵幸福和運氣。瑪雅神話敘述造物神用泥土、木頭造人都失敗了,最後用玉米才造出人,故世稱印第安土著為「玉米人」。瑪雅的圓形太陽曆,更以太陽的位置和玉米種植,劃分一年為九個節氣。
瓜地馬拉作家阿斯圖里亞斯(Miguel Angel Asturias, 1899 ~ 1974)長篇小說《玉米人》描述瑪雅人的現代遭遇,小說一開始寫土地大規模改種玉米:「玉米種植者砍倒原始森林中的古樹。甦醒的土地上種滿玉米。臭氣薰天的暗綠的河水在土地上四處流淌。玉米種植者燃起熊熊烈火,揮舞著鋒利的斧頭,闖進濃蔭蔽天的原始森林,一下子毀掉二十萬株生長了千年的茁壯的木棉樹。」玉米意象不斷出現在小說中,如描寫夤夜驟雨:「在黑黢黢的深夜裡,死去的印第安人從半空中傾倒下成噸的玉米粒。」又如敘述日常食物:「用黃澄澄的玉米麵烙辣玉米餅,用嬰兒指甲般鮮嫩的玉米粒煮雪白的玉米粥」。
中美洲印第安人以玉米為主食,玉米深入生活各層面,和社會的組織形式。玉米崇拜甚至成為墨西哥的文化現象。發展至今,玉米人已經有不同的意涵。這是全球總產量最高的糧食作物,品種甚多,顏色也多:白、黃、紅、深藍、墨綠……人們一般食用的是高甜度玉米,其它玉米則用作動物飼料,或食品工業、化學工業原料。如今天地間幾乎已無處不玉米,現在我們吃牛肉、豬肉、羊肉、雞肉時都像是在吃玉米。目前美國的原物料玉米大部分拿來餵養牲口,尤其是牛;從前的牛都在草原上低頭吃草。這當然違反了牛隻演化而來的消化系統,飼育場的牛或多或少都帶著病,必須靠抗生素維生。
麥可.波倫(Michael Pollan)指稱這是工業化玉米(industrial corn),說美國人是會走路的加工玉米(processed corn, walking ),玉米成功馴化了人類,它不但適應了新的工業化體制,消耗掉龐大的石化燃料能源,並轉變成更龐大的食物能源。
玉米的漢語別稱多到不勝枚舉,諸如:玉蜀黍、番麥、玉高粱、包穀、油甜苞、玉茭子、珍珠米、包粟、苞米……我喜歡吃玉米可能更甚於牛肉,這種食物鏈的基礎食物,或炒或蒸或烤都有滋有味。臺南保安路上「石頭鄉」燜烤珍珠玉米攤,口味多種:醬爆、蒜香、奶油、椰香、鹽爆、素食,最受歡迎的是刷沙茶醬燒烤。作法是先燜再烤,以熱石頭燜熟玉米,再上機器烤架,以挽留水份和甜份。靠近攤車即感受到熱氣,伴隨著洶湧的香氣;那熱騰騰的黑石頭中掩著臺灣產甜玉米,電風扇用力吹;上烤架之前才除掉葉衣和玉米鬚。燒番麥在木炭上烤,明火興旺,吃起來痛快,飽滿彈勁。
一年冬日我去雲貴高原探望助養的學生,在昆明,在昭通,在魯甸,在貴陽,在安順所有偏僻的窮鄉中,我看到許多小孩站在寒冷的天氣中,睜大好奇的雙眼望著走訪農戶的陌生人,鼻下掛著兩行髒污凍結的鼻涕;我看到飽受命運折磨的早衰女人,掙扎著為孩子的前程舉債;我看到勤奮的小女生,照顧癌末的父親……農舍旁總是成捆的乾玉米秸稈,屋簷下都掛著一串串成熟的玉米棒和辣椒,沉甸甸,豔紅與金黃交錯排列,美麗的玉米穗交錯著窮苦的生活,我想起瘂弦的名作〈紅玉米〉:
宣統那年的風吹著
吹著那串紅玉米
它就掛在屋簷下
掛著
好像整個北方
整個北方的憂鬱
都掛在那兒
這重要的莊稼作物,飽滿著泥土氣息,瘂弦通過它反映現代中國劇變的苦難境況,透露離散的滋味。玉米似乎是文學藝術永恆的題材,如墨西哥詩人帕斯(Octavio Paz)的詩〈石與花之間〉裡的玉米意象:「你有節制,溫馴順從,/像一隻鳥那樣生活,/靠著單耳罐裡的一點玉米炒麵糊」。又吟:「你的上帝由眾多神靈組成,就像玉米穗子。」長詩〈太陽石〉也激情歌詠:「你的玉米色的裙子飄舞,歌唱」。
吾家餐桌也常見玉米,兩個女兒從小吃焦妻煮的玉米濃湯:用超市買的湯包和玉米罐頭,加火腿屑加熱,輕鬆,方便,快速。我雖不喜這種罐頭速成品,卻明白是女兒吃了多年的「媽媽味道」,未便干涉。
現在換我煮玉米濃湯了,「爸爸的味道」肯定要捨棄罐頭玉米粒、速成濃湯包、火腿屑;我會先炒新鮮玉米,加入洋蔥、馬鈴薯拌炒後打成泥,以代替縴粉,再加雞蛋同煮, 避免使用火腿、熱狗。其實玉米濃湯的變化多端,可以加入玉米粒煮熟,還可依口味加入南瓜、雞肉丁、胡蘿蔔丁、青豆、蝦仁等等配料,變換口味。啊,希望調整心情也能那麼容易。
〈青梅〉三-五月
濱江市場規模相當大,各類蔬果肉品齊全,海產更多樣,我每次在家宴客總是來採購。有一天買齊了菜,本來還要買蓮霧,焦妻見青梅上市,遂買了一箱回家,她準備釀梅醋,說釀過的梅子也好吃。
翠綠的梅果誘舌生津,她忽然起心動念要買來加工。為了釀梅,她特別去買了廣口玻璃缸,以一種土法煉鋼的精神,先洗淨梅子,用電風扇吹乾;一層梅子一層糖,再加入大量的醋,密封,她宣布半年後就可以開缸飲用。
以糖、鹽、醋醃漬梅子都很好吃,諸如酸梅、話梅、紫蘇梅、奶梅、脆梅、茶梅、烏梅、咖啡梅、紹興梅等等。先秦已出現醃梅,《呂氏春秋》錄有鹽梅烹魚,《尚書》亦記載鹽梅合羹,《三國演義》曹操與劉備「青梅煮酒論英雄」。最早的文獻見於《詩經.摽有梅》,描述周代每年一次的舞會,男女在舞會中擇偶,自由訂婚或結婚:「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梅與媒同音,梅落乃有花開結實的隱喻,故興起男女宜及時嫁娶之義。
這種亞熱帶特產果樹,原產於中國南方,已栽培了三千多年。《齊民要術》記載的梅子加工:「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耳,實赤於杏而醋,亦可生噉也;煮而曝乾為蘇,置羹臛中;又可含以香口,類蜜葴而食」,可見當時已常製成零嘴。又如《東京夢華錄》中所述梅汁、梅子、香藥脆梅等,皆是梅子飲品和蜜餞。到了宋代,更以梅花入饌,《山家清供》所載包括:梅花湯餅、蜜漬梅花、湯綻梅、梅粥、不寒虀、素醒酒冰。
梅有兩百多品種,依果實色澤大別為青梅、紅梅、白梅,諸如歐陽修「葉間梅子青如豆」,劉秉忠「梅子黃時雨」,王安石「雨如梅子欲黃時」,王之道「梅子更紅肥」,吳文英「半紅梅子荐鹽新」……吾人吃的青梅並非一般觀賞梅花所結;果梅是薔薇科杏屬梅,又稱梅子、酸梅。
雖則《尚書》、《禮經》早就提到的梅,指的都是果實而不是花,唐人才題詠競作。對梅用情最深的人可能是宋代的范成大,《范村梅譜》贊嘆:「梅,天下尤物」,記載所居范村之梅,凡十二種,他所描述當然是梅樹,後序又說:「梅,以韻勝,以格高,故以橫斜疎瘦與老枝怪奇者為貴。」
梅子富含人體所需的多種氨基酸、維生素,和大量的檸檬酸,能促進血液循環、消除疲勞、抗老化;若與鈣質結合,還能強化骨骼,促進鐵的吸收,是優質的保健食品,被譽為「涼果之王」、「天然綠色保健食品」,日本人盛贊「鹼性食物之王」,可平衡人體酸鹼值。
華人一向愛梅,古來騷人墨客賞梅、詠梅、品梅的作品不少。李白〈長干行〉:「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用青梅那酸甜的滋味隱喻愛情,那是一種非常深刻的酸,令三國時曹軍「望梅止渴」,令楊萬里吟詠的「梅子留酸軟齒牙」。
實在太酸了,不適合鮮食,吾人多品嚐加工後的梅製產品,依照梅子成熟度不同,進行不同的加工處理。小妹盈君憂慮我長期暴食暴飲,常送我梅精,青梅產品已深入我的生活。我尤其歡喜「中華農桑文化工作室」煉製的梅精丸、梅醋,每次出國都帶著梅精丸,旅途中隨時含一粒,覺得很有安全感。
臺灣的農村酒莊善釀梅酒,車埕酒莊融入地方的鐵道文化,酒品命名都和鐵道有關,如「鐵道公主」、「車埕老站長」、「烈車長」、「鐵軌」,四款酒我都喝過。「鐵道公主」選用水里所產的梅子釀造,色澤金黃,酒莊的宣傳手冊上如此敘述:在七〇年代集集支線的通勤列車上,有位最明亮可愛的少女,她是所有少男們心儀的對象,也是當時所有火車族的共同回憶,更是許多人存封多年的暗戀。這個甜美的女孩,我們都叫她「鐵道公主」,品嚐之間彷彿時光回到往昔,又見到那健康美麗的身影緩緩走來。
好深情的青梅故事啊。《清稗類鈔》載錢枚之妻善作糖梅,味極甘脆,某年夏天,睹糖梅悼亡妻,作〈望梅〉一詞,後半段:
青錢細簸,白蜜生醃,紅瓷封貯。
追思十年前事,悵綠么絃斷,翠籨香炷。
又江南節物登盤,問舊時滋味,何嘗如許?
春夢銷沈,訪嫩綠池塘何處?
賸微酸一點,常在心頭留住。
焦妻生病時釀了一大缸梅醋,透過玻璃缸,那青梅和裡面的醋日漸轉成褐色。她離開後我想吃,可說來詭異,那缸梅醋竟無端消失。我問過母親、女兒,均搖頭不知,彷彿是一個謎,在迷茫的歲月中那麼真實存在過,我在記憶中努力想像那消失的青梅,酸得像寂寞中年。
|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蔬果歲時記(4款書衣隨機出貨)的圖書 |
 |
蔬果歲時記(4款書衣隨機出貨) 作者:焦桐 出版社: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08-03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蔬果歲時記(4款書衣隨機出貨)
蔬果生長寄歲月,寄土地,寄自然;人亦同。
以六十種蔬果道盡歲時轉換,天地人情
焦桐越過生命低谷、重新品嚐自然真滋味經典之作
「只有蔬果才能表現季節的節奏感。」
自古以來,農民跟隨節氣,春耕夏耘,栽種不同的作物,依循風土,創造各種美食,所謂「歲時」,便是人們如何配合四季運行而行事,是人與自然和諧互動的體現。農諺:「正月蔥,二月韭,三月莧,四月蕹,五月匏,六月瓜,七月筍,八月芋,九芥藍,十芹菜,十一蒜,十二白」。購買與食用當地當季的新鮮蔬果,美味,平價,保護環境,也保護人體,令飲食配合大自然的節奏。在春雨裡採收韭菜、盛夏醃蓬萊醬(情人果)、釀葡萄酒,秋日剝柚子,用乾柚皮薰香;而隆冬吃肉,客家人總要沾一碟桔醬.......在《蔬果歲時記》裡,找到土地上最新鮮也最悠久的收穫。
「像我這樣的糟老頭一餐比一餐肥,像快速膨脹的南瓜,
藏身寬闊的葉下,笨拙,覺得什麼遭遇都無所謂,什麼環境都可以……」
休耕、農藥、食安、氣候變遷、基因改造……食物本不該面目模糊、味道也不能虛應故事。重新探尋食物最初的樣貌與美好吧!經過歲月歷練、揉合生命苦痛酸甜,焦桐回歸土地及蔬果歲時書寫,脈脈情深。踏遍南北、寫遍山海,從詩詞、文學、史料,乃至於科學中,娓娓道來六十餘種蔬果身世。
「沒有人能真正忽略美麗的事物。我越來越歡喜蔬菜,在市場,蔬菜最能表現季節和鄉土風情;我發現,飲食文化越深刻的地方,越熱愛蔬菜。」
焦桐從年輕時一餐可暴食數十隻螃蟹,到中年後「漸漸愛上蔬果之美」。除了味道描寫與文化考察,這本書更滿是焦桐對食材的情感,每樣蔬果皆飽含記憶與愛,歷歷在目。是繼【臺灣味道三部曲】、《味道福爾摩莎》之後,焦桐為這塊土地獻上的溫柔記事。跟隨著這本書,再一次認識台灣的蔬菜水果,嚐遍季節的美味。
初春/青梅
翠綠的梅果誘舌生津,她忽然起心動念要買來加工。為了釀梅,她特別去買了廣口玻璃缸,以一種土法煉鋼的精神,先洗淨梅子,用電風扇吹乾;一層梅子一層糖,再加入大量的醋入,密封,她宣布半年後就可以開缸飲用。
她離開後我想吃,可說來詭異,那缸梅醋竟無端消失。我問過母親、女兒,均搖頭不知,彷彿是一個謎,在迷茫的歲月中那麼真實存在過,我在記憶中努力想像那消失的青梅,酸得像寂寞中年。
盛夏/韭菜
我覺得那重辛的味道似乎,可以喚醒昏眊的味覺記憶,和心神。在懵懂的童年,知道了父親離去的晚上,母親含淚作晚餐,那盤韭菜花炒蛋的滋味我永遠記得。韭菜發音久,不管普通話或閩南語,都帶著長長久久的願望,期待。
暮秋/西施柚
老欉柚樹,才會結出又大又沉又甜又優雅的西施柚。柚子出現,象徵暮秋般年華漸老;吾人飽嚐了生命的風霜雨露,心智逐漸成熟,往往才體會甘甜中的酸味,也才欣賞酸中有甜,甜蜜中透露著酸。
新冬/金柑
金柑大約在農曆年前盛產,過年時許多人家擺設金柑、四季桔盆景,澄黃飽滿。過年的食物最重視口彩,人們置金柑盆景於家中,象徵吉祥如意,祝福四季平安,吉星拱照。柑桔自古代表甘美,正如棗子象徵吉利,閩南語「拜好柑,好年冬;吃紅棗,年年好」。
金柑不似四季桔酸,果皮的風味可口,鮮食甚佳,宋.李清臣詩贊:「氣味豈同淮枳變,皮膚不作楚梅酸。參差翠葉藏珠琲,錯落黃金鑄彈丸」。鮮食金柑,都連皮帶肉一起吃;而且果皮的風味比果肉更迷人,清爽,微甜,柑橘香充滿口腔和呼吸道,如情人的呼吸。
作者簡介:
焦桐
1956年生於高雄市,曾習戲劇,編、導過舞臺劇於臺北公演。出版詩集《完全壯陽食譜》被誤認為美食家;就此「誤入歧途」,鑽研飲食文化成痴,創辦《飲食》雜誌、編選年度《飲食文選》;耕耘飲食文學二十載,人稱「飲食文學教父」。
已出版著作包括詩集《焦桐詩集:1980~1993》、《完全壯陽食譜》、《青春標本》,散文《在世界邊緣》、《暴食江湖》、【臺灣味道三部曲】;《滇味到龍岡》及臺灣小吃聖經《味道福爾摩莎》等等三十餘種。編有年度詩選、年度小說選、年度散文選及各種主題文選五十餘種。
TOP
章節試閱
〈甘蔗〉十一-五月
學齡前寄養在外婆家,當時高雄市三民區還很像鄉村。舅舅有一片果園,外公種田、養豬,外婆種菜、飼養雞鴨。農村廚房裡有一個大爐灶,煮過晚餐,外婆輒用灶內餘火烤甘蔗,未削皮的甘蔗受熱,糖水緩慢滲出表皮,有些凝結,有些猶豫滴落,宛如眼淚。我曾在〈外婆〉一詩中懷念:「暗夜的爐灶有回憶的餘燼/甘蔗偎在裡面流淚/輕語如體溫」。取出熱甘蔗,咬掉蔗皮,咀嚼間流動著甜蜜,溫暖,快樂,幸福感。這種幸福感竟永遠鮮明在記憶中。
似乎不會有人覺得甘蔗不好吃。中國最早出現甘蔗的文獻是《楚辭.招魂》:「胹鱉炮...
學齡前寄養在外婆家,當時高雄市三民區還很像鄉村。舅舅有一片果園,外公種田、養豬,外婆種菜、飼養雞鴨。農村廚房裡有一個大爐灶,煮過晚餐,外婆輒用灶內餘火烤甘蔗,未削皮的甘蔗受熱,糖水緩慢滲出表皮,有些凝結,有些猶豫滴落,宛如眼淚。我曾在〈外婆〉一詩中懷念:「暗夜的爐灶有回憶的餘燼/甘蔗偎在裡面流淚/輕語如體溫」。取出熱甘蔗,咬掉蔗皮,咀嚼間流動著甜蜜,溫暖,快樂,幸福感。這種幸福感竟永遠鮮明在記憶中。
似乎不會有人覺得甘蔗不好吃。中國最早出現甘蔗的文獻是《楚辭.招魂》:「胹鱉炮...
»看全部
TOP
目錄
序 / 菜園肚皮
蔬之屬
青蔥
紅蔥頭
馬鈴薯
韭菜
洋蔥
落花生
毛豆
大蒜
空心菜
綠豆
綠竹筍
香椿
野蓮
絲瓜
九層塔
過貓
瓠瓜
茄子
辣椒
山葵
番薯
苦瓜
花椰菜
高麗菜
山藥
玉米
胡蘿蔔
茼蒿
大白菜
芋頭
福菜
紅豆
香菇
南瓜
果之屬
香蕉
草莓
柑橘
蓮霧
青梅
芒果
玉荷包
荔枝
聖女番茄
檳榔
木瓜
西瓜
水蜜桃
檸檬
鳳梨
三灣梨
巨峰葡萄
蜜紅葡萄
釋迦
龍眼
文旦柚
西施柚
愛玉
番石榴
珍珠芭樂
楊桃
甘蔗
蜜蘋果
柳丁
金柑
蜜棗
蔬之屬
青蔥
紅蔥頭
馬鈴薯
韭菜
洋蔥
落花生
毛豆
大蒜
空心菜
綠豆
綠竹筍
香椿
野蓮
絲瓜
九層塔
過貓
瓠瓜
茄子
辣椒
山葵
番薯
苦瓜
花椰菜
高麗菜
山藥
玉米
胡蘿蔔
茼蒿
大白菜
芋頭
福菜
紅豆
香菇
南瓜
果之屬
香蕉
草莓
柑橘
蓮霧
青梅
芒果
玉荷包
荔枝
聖女番茄
檳榔
木瓜
西瓜
水蜜桃
檸檬
鳳梨
三灣梨
巨峰葡萄
蜜紅葡萄
釋迦
龍眼
文旦柚
西施柚
愛玉
番石榴
珍珠芭樂
楊桃
甘蔗
蜜蘋果
柳丁
金柑
蜜棗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焦桐 繪者: 李蕭錕
- 出版社: 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08-03 ISBN/ISSN:9789865813826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00頁 開數:25開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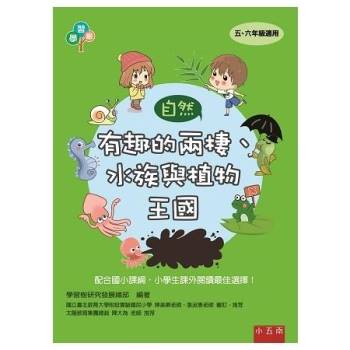








![114年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能力測驗(重點統整+歷年試題)[金融證照] 114年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能力測驗(重點統整+歷年試題)[金融證照]](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0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