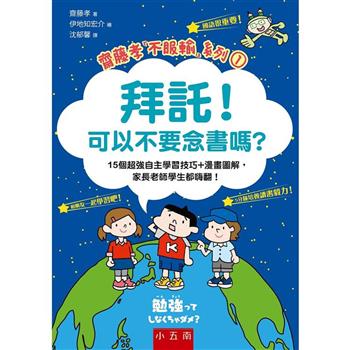阿魚回家了,文學回來了!
從顏凡《明星加工廠》到《阿魚的鄉思組曲》的兩種風景
「我們珍惜來自海島共有的情感。其間,無太多的驚奇點,卻是兩條可拉直的線,也是可以納入交響的音符。逃避、退卻、悲憐…它們都不應出沒的。」;「你周遭的朋友指你竟日在瞎忙。忙得徒留一道空虛的影子:事業無著。怎是個而立之年的骨幹?誰又能探,你尋求的是世俗外另一個清朗的空間;你以純淨之心對待自己、善待朋友。台北烽火紅塵十載,足夠使人的心靈扭曲、變形,你依然是不變的赤子心、文學情。都會中人迷戀於霓虹閃爍的繽紛色澤,你獨大隱於市,沈浸在圓通寺的菩提香;都會人在七彩絢爛的時尚街奔跑著,你卻揹著攝影機在林安泰古厝尋找老台北……。做生意,不懂投資報酬率。談感情,不計付出回收率。人說老古牌的你,仍是舊社會的零件,趕不上新世界的產品。」
——楊樹清《紅燭外一程》(一九八三)
二○一四年五月十一日,是母親節,也是竹君的文定之日。國民兄嫂在新店的豪鼎飯店,為女兒辦了場精采、溫馨的喜宴之後,我又受邀到台北市文山區的顏府喝茶。道別的時候,國民兄送我到萬隆捷運站,此時他忽地遞來置入一本書稿的牛皮紙袋,又掏出手機,說要拍張喜宴未及拍的兩人合影,好不容易才看到一位臉上綻放笑容、表露善意的過路女子,「小姐,可以幫我們拍張照嗎?」按下快門之後,合照與留言,PO 上臉書:「母親節嫁女。大俠(楊樹清)大駕光臨,蓬蓽生輝。宴罷來寒舍暢敍,並應允為拙作《阿魚的鄉思組曲》作序。特表感謝!」
母親節的喜宴、合照、留言,讓我的記憶之匣快速倒帶重播,回到三十年前,一九八二年歲暮,猶在征塵途中的我,歸營前趕赴板橋遠東百貨鑽石樓,我以一篇《紅燭外一程》,記載了那場風雨中的婚禮畫面,以及紅燭外與「顏公」相識、相知、相惜的點點滴滴:週末、元旦連續假期,風雨、車潮,堵住了新郎新娘的禮車,遲遲未能走上六點的觀禮台,而我是一個再過十九天就要退伍的戰士,從新竹、壽山、澎湖、桃園,再落定松山永春坡,不曾有過逾假、夜不歸營的紀錄,我必須在七點前趕回營區銷假;包出禮金,喝不到喜酒,早在算計之中,等不著新郎、新娘,握手道聲祝福,卻在意料之外;「不能再等了,匆匆的將禮金交付,我多情地在禮金袋封口寫了兩行字:「歲顏三十風雨行,一方女子捲簾來」;招來一部計程車,要求司機抽換兀自播放、洪榮宏的《一支小雨傘》,來首齊豫的《婚禮的祝福》。
《婚禮的祝福》歌聲中,車子越過華江橋,直駛向和平西路、和平東路,往松山永春坡前進。滴滴嗒嗒,落個不停的雨聲,模糊了車窗,迷濛了街景,夜台北在一把紊亂的視線裡,「五年前我十七。一個青衫少年,由島鄉初履台北。台北過濃的紅黃相間顏色,我心慌得不知走向哪裡。何處是兒家的悲抑感在心頭翻攪著。是你,是你伸出手領著我,在泰順街租到歇腳的斗室,在吉林路的金門文藝社安排了一張桌子,到金門街的愛書人雜誌拜訪社長陳銘磻盼能提供一份工作,進辛亥路的耕莘文教院寫作會協助我編印冬坡、旦兮快報,又跟你到所就讀的文化大學城區部大眾傳播系旁聽大眾傳播學,也帶我到野外學攝影,熬夜在編輯台貼版面,下工廠看師傅組版……。你熱絡得想要給我什麼,你卻從不說要給我什麼……。」
間隔了三十載的兩場婚禮,板橋、新店,主角從顏國民到他留美歸國的音樂博士顏竹君。兩場婚禮,形成了時空的對照,以及記憶的讀取、連結。
青色歲月,青澀文字的《紅燭外一程》裡,讓我再次讀到與顏國民始初交往的章節,接近黑白分明的畫面,也似一種緩慢、深沈的記憶節奏。跳接的描述,看得出文字裡藉由鄉情串連的兩個人,有了現實的交集,有了理想的追逐,也都在尋找生命的出口。而牽繫這份情感免於墜落的,是文化,更是文學。
在人生旅途上緊密纏結的兩個異鄉人,《紅燭外一程》之後,又歷經了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出版部、未來雜誌的工作夥伴,以及持續三載的唐山勤寫小組共同發起人,此後,一樣行走在台北大城的文化江湖,卻莫名地疏離,各自身陷在追趕忙碌的文化傳播職場,不再把酒桑麻,也失落了煮茶論藝的時光。儘管,我們都未放下筆,也常在書市場某個角落的書架上相遇,看到的卻是他的《預言家總動員》、《李登輝的身世之謎》,我的《生涯企劃書》、《上班族筆記》。我們都清楚,這不是文學,不是我們寫作的初衷,而是為了現實生活寫作。想起唐山勤寫小組分享文學閱讀、交換文學寫作心得的時光,他能交出《摩托和尚》、《那棟大樓很冷》、《瓦厝巷風波》、《遺忘的記憶》等小說佳構,我也能寫出《跋涉幾星霜》、《燕歌行》、《心之筆記》、《花崗岩層》等純淨散文。現此時的我們,離純粹性的文學創作越來越遠了。
那位曾經被我在《紅燭外一程》深情記載、深切期待的主角,鄉情┼友情的組合外,吸引我的,正是他的閱讀、文學狀態。在家鄉就讀高中時,為迷羅素,課業從第一念到倒數第一;來到台灣,釋放了文學能量,一九七七年起,有七、八年之久,大量發表小說作品,期間還接辦了《金門文藝》革新號。一九八九年,他以顏凡之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說集《明星加工廠》,接續,未再看到他的文學書目,反而是以《顏如蔚》、《顏兆鴻》之名,出版了不少星相、命理書籍。那位迷戀哲學、文學的男孩到那兒去了?文學的顏凡,《明星加工廠》,化作一段美好的回憶。
《明星加工廠》收錄了二十六個短篇,分出《生命篇》、《兩性篇》、《衝突篇》、《親情篇》、《社會篇》等五輯,寫作時間橫跨了六年,聚焦的是市井人物、都會男女,作家阿盛以《筆中市井情偏多》題序,直指:「顏凡的筆法並不奇特,遣詞用字平穩。也許顏凡無意『出奇』,他平平順順的將一些人事物道來,」又道出寫作者的筆法可以見出個性:「顏凡的筆法略偏『溫和』、『誠懇』,視其人個性亦如是。」並以書中《生命篇》輯中的《單行道》、《最後一件善事》、《談判》、《陸老師的天空》、《小丑》以及《摩托和尚》等六篇作品為例,評述:「敍述小故事,沒有大歡大悲,卻很有人味。」
「沒有大歡大悲」,阿盛直擊寫作者生命狀態或文字情境的一個描述,直讓我想起小說家黃克全的提醒:「沒有大痛苦,就沒有大文學」、「沒有大熱情,就沒有大文采」;那麼,「沒有大歡大悲」的作者?阿盛序中的顏凡「是有能力、有潛力寫出更多作品的」,惟無意「出奇」,除了少數幾篇使用推理懸疑的手法較「奇」外,其餘作品概皆「尋常人作尋常話」,阿盛也以「作者,多情何妨?」期許顏凡「若能擴大寫作題材、持之以恆的創作,相信佳作會更多」。
「多情」而不「奇情」,是顏國民筆下展現的文字、情節特性;我看到的他,並非沒有「大歡大悲」之人,他在《明星加工廠》自序《心動的頻率》文中記敍了創作心路:「緣於一介凡夫的動盪生涯,讓我有幸亦不幸地看盡了人世間的形形色色、大悲大樂、極尊極卑、最亮與最暗,其間不乏讓我心靈觸動而呑淚的旋律,亦有不少讓我悲憤莫名的情節,它們都鮮明地烙印在我心田」,從人生的自我觀照,「但不知是由於心性使然,還是資質魯鈍,雖然摰愛各種中外文學著作,卻總持著一份不驚不懼的怠慢態度,至今仍訝異於竟然疏懶至連理出個世界文學流派或桂冠大師世系表的成就都沒有,自己偏執地認為生活即是文學,創作只求適性達意,只求勤耕耐磨;也基於這種理念,曾經和楊樹清共同發起『唐山勤寫小組』,那一段白天忙於果腹營生,夜晚放情於寫作的歲月,如今思之仍覺彌足珍貴」。
重新檢索許多年以前,顏國民出版的書,阿盛的評述,作者的闡述,可以發覺看盡人間世的形形色色、大悲大樂的顏國民,早早認定了「生活即是文學」,創作只求「適性達意」。如此清楚的認知,「大痛苦,大文學」,顯然不適合套在顏國民身上了,「那些觸動也許描繪的技巧有待改進,但是它傳達的熱誠和頻率卻是一樣的,那是小人物如我,心中急於表白的喜怒哀懼愛惡欲!」
《明星加工廠》後,再一次漫長的等待。竹君的喜宴,舞動出的第二代青春旋律,台北萬隆捷運站,離去之前,自牛皮紙袋掏出的一疊書稿:《阿魚的鄉思組曲》。我急欲找回《紅燭外一程》裡文學路上踽踽獨行的主角,也熱切要讀到、填補《明星加工廠》後的文學空白。那位鍾愛、信仰文學的男孩,可溯及啟蒙時期,初「聞」國語課本印墨油香而產生的附體快感、喜悅,升上高中,仍不能自拔於浩瀚書海中,迷上新潮文庫,一度因而差點被拒於那升學窄門,滾滾紅塵,幾度沈寂的筆,當今的他,又交出了怎樣的一張文學成績單?
不再止於市井人物的生活悲歡、都會男女的情事糾結;這一回,顏國民化身阿魚,帶著有色彩、有亮度的一枝筆,帶領我們回到他遠離了二十多載未曾踏返的海島故鄉。
《紅土彩繪的故鄉》、《老故事》、《數羅漢與聽香》、《自來水革命史》、《鐵罐裡的鹹麵》、《九豬十六羊拜月娘》……從命題到單篇文章的連綴,我望見了,一隻緩緩洄游返鄉的鮭魚,在呢喃、在唱歌,也在回憶、說故事。
不同於《明星加工廠》純一的小說情節、文學語言;《阿魚的鄉思組曲》,比較接近文史┼文學、小說┼散文、遊記┼札記的混聲合唱。但就其架構而言,藉由一位返鄉的阿魚說書式的景點、故事串連,混聲中也拉出一個單一的「鄉思」節奏,時而隱身、時而投入、時而跳脫,是鄉思的組曲,也是鄉景、鄉情的返鄉進行曲。
《阿魚的鄉思組曲》,多重文字語言、文體交織下複合式的書,字裡行間,讀不到太重的鄉情負擔、鄉愁重量,隱藏了個人的離愁,筆下反倒是一種明亮的色調,說是一冊另類遊記也無妨,因為書中的阿魚,不似夾帶鄉情的返鄉客,而是隱身其間、搭「觀光公車」遊金門的觀光客,因而產生了另一種介入其中,又能游移在外的書寫風景。
讀罷《阿魚的鄉思組曲》,我又從書末收錄的一篇《酒店關門我不走,戀戀不忘雜誌情》,意外讀到忙碌於生活,汲汲營營於傳播職場,卻仍然難以忘情「創作」的顏國民,「三十多年來,我對『雜誌』和『創作』這兩大領域永不退熱情,它們是我生命裡兩顆重要的維他命;『雜誌』已經退冰了,但『創作』的熱情,隨著馬齒徒增,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再度被加溫!」
《酒店關門我不走》,從《明星加工廠》到《阿魚的鄉思組曲》,我再次讀到《紅燭外一程》的男主角,重新點亮一盞燈。阿魚回家了,文學回來了!
楊樹清
於二○一四年七月六日
還好有鄉愁
二○○八年四月四日早上,從台中港啟航的返鄉專船登陸料羅灣,我踏上睽違二十餘年的金門故鄉,記憶像抽絲剝繭,愈往裡鑽,愈見驚艷,自此如上了癮,成為一隻年年等待歸期的候鳥,清明時節,總不缺席。
第一次搭專船返鄉的見聞,寫成洋洋灑灑「紅土彩繪的故鄉」一文,想在家鄉金門日報的浯江副刊發表,正煩惱用什麼筆名,三妹湘芬建議:何不直接用「阿魚」?一語提醒夢中人。
阿魚是我的乳名,聽說嬰兒時期愛哭鬧,外祖父替人撿骨,身邊常有一些金銀銅鐵的陪葬品,順手拿了個金魚的飾品在我眼前幌動,我就破涕為笑了,後來家人把那金魚飾品當作吉祥物縫在帽沿戴在我頭上,順口也把「阿魚」叫成我的綽號,只有家人和最親暱的好友才會如此稱呼,阿魚也正是我和家鄉之間最好的連結,開始做為我創作懷鄉文章的筆名。
每次返鄉,好友總會餽贈最新著作,也才得知金門縣文化局有一個贊助地方文獻出版實施計畫,每年皆會撥出經費贊助描述家鄉相關的作品出版,去(二○一三)年清明返鄉拜訪國中同窗好友洪明燦時向他探詢此事,經常獲贊助出版的他表示,今年他也會送審,時間快到時會通知我,果然今年三月中旬,明燦說他已經送出去了,提醒我三月底以前要送件,我去年專程做了一趟金門觀光公車ABCD四條路線二日遊的二萬七千多字遊記,投稿浯江副刊卻只被刊出三、四百字的前言,十分沮喪,心想剛好可以和二○○八年的「紅土彩繪的故鄉」湊成單行本,再加上偶然間翻出來的三十年前描述家鄉作品剪報,以及近六年來陸續在浯副發表與家鄉有關的追憶性文章,做個結集紀念,趕在三月底以前,依規定裝訂六本送審,承蒙評審委員的不棄,僥倖過關,而明燦兄的大作也入選,兩人都歡喜不已,個人尤其對明燦兄的不藏私胸襟,大感敬佩。
身在異地台灣,偶有同鄉聚會;或登上返鄉專車和專船,以及接連二、三天的假期,濃濃的閩南鄉音瀰漫,談不完的兒時記憶,誰誰誰的共同話題,最能撫慰出外人的心靈。
什麼「近鄉情怯」、「無顏見父老」的理由,幸好有鄉愁,轉化掉一層層的鴻溝;多少恩怨情仇、功利對錯,幸好有鄉愁,沖刷一道道的傷口;我一生行事散漫,僅以養家糊口為念,幸好有鄉愁,得以在離鄉四十年後的花甲之年,還能重溫年少時期的美夢。
什麼是鄉愁?詩人余光中在一首「鄉愁」的詩裡詮釋得最好:
小時候
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
我在這頭
母親在那頭
長大後
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
我在這頭
新娘在那頭
後來啊
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
我在外頭
母親在裡頭
而現在
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
我在這頭
大陸在那頭
比較幸運的是,我八十餘歲的母親,目前還健在;隔著一灣淺淺海峽的家鄉並不是大陸,然而種種無奈的距離,仍常讓我喟然興嘆,也在字裡行間暗藏,不擅雕硺文采,也無追逐崇高理想的我,幸好有鄉愁,才得以發發牢騷,舞文弄筆,三十年才成就這一丁點小成果,希望這只是開端,未來能投注更多的能量,彩繪我這最心愛的家鄉。
鄉思就像一縷銜接風箏的細線,飛得再高再遠,風箏再花枝招展,那條線就是不能斷。
而經由相知相惜三十餘年大俠(洪建全時期大家對他的暱稱)樹清兄序中的剖析、點醒,我才豁然開悟,原來我的鄉思和文思是無法分割的,而兩人在文學領域上的無縫接軌,生命才能顯出意義,我用LINE告訴他:「年過六十,是我的文學元年,今後將專此為念,不作他想。」所以去年開始辦文創達人雜誌,剛好也是文創元年;也因為元年,所以還有許多可以慢慢改進的空間。
感謝「人文立縣」的家鄉,長期貫徹這項推動金門文風的德政,更承蒙贊助地方文獻出版審查委員會委員們的不棄,這本拙作才得以問世。
本書十九篇文字,有小說,有散文,有雜記,時間從民國七十一年到一○四年,萬幸留下那些古早的記憶,也保存了一些即將消失的民情風俗,或許在地方文獻上,略可野人獻曝些棉薄力量,返金遊記之深體驗,也希望能深化「觀光金門」的內涵,成為外來遊客的另一冊旅遊指南。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阿魚的鄉思組曲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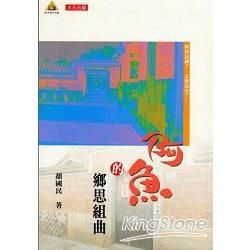 |
阿魚的鄉思組曲(不可退書) 作者:顏國民 出版社:大元書局 出版日期:2014-08-12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84頁 / 25k正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87 |
小說/文學 |
二手書 |
$ 220 |
二手中文書 |
$ 264 |
現代散文 |
$ 264 |
現代散文 |
$ 270 |
現代散文 |
$ 270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阿魚的鄉思組曲
鄉思就像一縷銜接風箏的細線,飛得再高再遠,風箏再花枝招展,那條線就是不能斷。
本書十九篇文字,有小說,有散文,有雜記,時間從民國七十一年到一○四年,萬幸留下那些古早的記憶,也保存了一些即將消失的民情風俗,或許在地方文獻上,略可野人獻曝些棉薄力量,返金遊記之深體驗,也希望能深化「觀光金門」的內涵,成為外來遊客的另一冊旅遊指南。
作者簡介:
筆名:阿魚、顏兆鴻、顏如蔚、顏凡,一九五三年生,世界新專編輯採訪科、文化大學大眾傳播系畢業。
著有:「明星加工廠」(短篇小說集)、「李登輝的身世之謎」、「預言家總動員」、「陳怡魁食物改運」、「陳怡魁卜療改運」、「陳怡魁風水改運」、「情慾告白X檔案」、「他們的公關藝術」、「命理傳燈錄」、「命理傳燈續錄」等書。
作者序
阿魚回家了,文學回來了!
從顏凡《明星加工廠》到《阿魚的鄉思組曲》的兩種風景
「我們珍惜來自海島共有的情感。其間,無太多的驚奇點,卻是兩條可拉直的線,也是可以納入交響的音符。逃避、退卻、悲憐…它們都不應出沒的。」;「你周遭的朋友指你竟日在瞎忙。忙得徒留一道空虛的影子:事業無著。怎是個而立之年的骨幹?誰又能探,你尋求的是世俗外另一個清朗的空間;你以純淨之心對待自己、善待朋友。台北烽火紅塵十載,足夠使人的心靈扭曲、變形,你依然是不變的赤子心、文學情。都會中人迷戀於霓虹閃爍的繽紛色澤,你獨大隱於市,沈...
從顏凡《明星加工廠》到《阿魚的鄉思組曲》的兩種風景
「我們珍惜來自海島共有的情感。其間,無太多的驚奇點,卻是兩條可拉直的線,也是可以納入交響的音符。逃避、退卻、悲憐…它們都不應出沒的。」;「你周遭的朋友指你竟日在瞎忙。忙得徒留一道空虛的影子:事業無著。怎是個而立之年的骨幹?誰又能探,你尋求的是世俗外另一個清朗的空間;你以純淨之心對待自己、善待朋友。台北烽火紅塵十載,足夠使人的心靈扭曲、變形,你依然是不變的赤子心、文學情。都會中人迷戀於霓虹閃爍的繽紛色澤,你獨大隱於市,沈...
»看全部
目錄
楊樹清序
自序
紅土彩繪的故鄉
搭「觀光公車」遊金門
瓦厝巷風波
遺忘的記憶
老故事
數羅漢與聽香
自來水革命史
鐵罐裡的鹹麵
九豬十六羊拜月娘
天上掉下來的五百元
彈珠王
救人的藥品
百年奇緣
節能減碳遠在天邊﹖
陪大小姐散步
你領終身俸沒﹖
返鄉﹐煩鄉﹖
遊「輪」驚夢
【「金門文藝」帶起的連漪】
酒店關門我不走,戀戀不忘雜誌情
■附溫馨回憶照片
自序
紅土彩繪的故鄉
搭「觀光公車」遊金門
瓦厝巷風波
遺忘的記憶
老故事
數羅漢與聽香
自來水革命史
鐵罐裡的鹹麵
九豬十六羊拜月娘
天上掉下來的五百元
彈珠王
救人的藥品
百年奇緣
節能減碳遠在天邊﹖
陪大小姐散步
你領終身俸沒﹖
返鄉﹐煩鄉﹖
遊「輪」驚夢
【「金門文藝」帶起的連漪】
酒店關門我不走,戀戀不忘雜誌情
■附溫馨回憶照片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顏國民
- 出版社: 大元 出版日期:2014-08-12 ISBN/ISSN:978986581716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84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