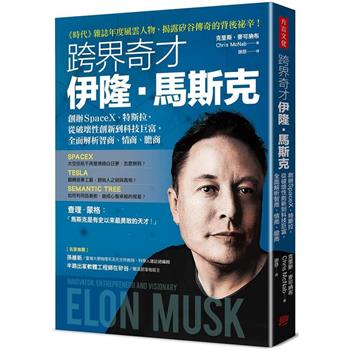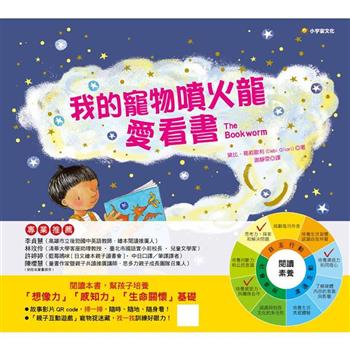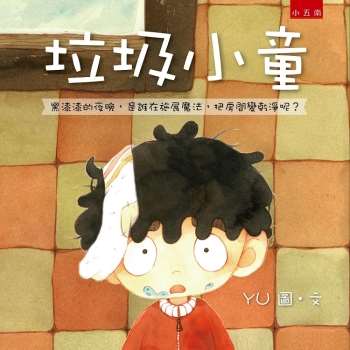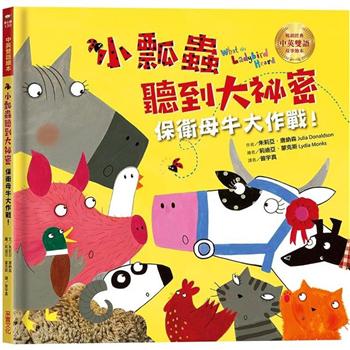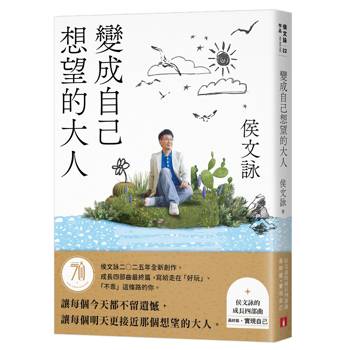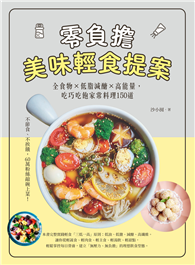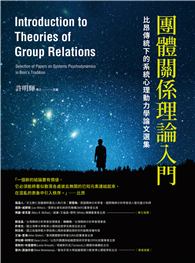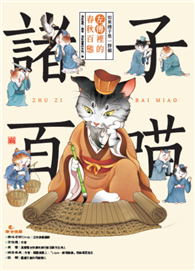《乙巳占》是一部綜合性的古星學著作,為[唐]李淳風(602-670)撰。一說:成書於唐太宗貞觀十九年(645)乙巳,故名。共分十卷。本書係將唐以前數十種星占書分類匯鈔而成。本書為九卷原鈔(非原本,亦後鈔本),年代無考,應為清初前後。
除星占外還有天文、氣象等內容。其中根據風力對樹林的影響和破壞程度,把它分為八級:一級葉動、二級條鳴、三級振枝、四級墮葉、五級折小枝、六級折大枝、七級折木、飛沙石、八級拔樹及根,是為世界最早的風力分級系統。
書中還保存有作者早年所撰《乙巳元曆》的若干資料,以及作者所發展的渾儀和所著天文儀器專著《法象志》等方面的資料。古代許多天文學名詞亦賴以傳世。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增補乙巳占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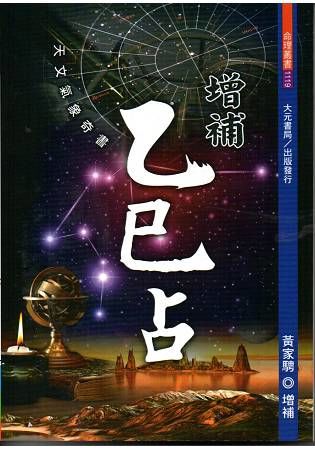 |
增補乙巳占 出版社:大元 出版日期:2017-02-14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560 |
二手中文書 |
$ 704 |
命理/占星 |
$ 704 |
命理/占星 |
$ 720 |
占星 |
$ 720 |
宗教命理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增補乙巳占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編者簡介
黃家騁
1948年1月,出生於台北,中華民國易經學會理事暨易經主講、華岡傳統醫學會副會長、港九中醫師公會永遠名譽會長。中華易學月刊專論數十篇,媒體專欄超過三千篇。著作易學提要、易學與醫學之綜合研究、洪範易知、易術概要、七政三王真躔萬年星曆、星海辭林六巨冊等。講授易經、天文、中西星象、三元地理、擇日等卅餘年。
黃家騁
1948年1月,出生於台北,中華民國易經學會理事暨易經主講、華岡傳統醫學會副會長、港九中醫師公會永遠名譽會長。中華易學月刊專論數十篇,媒體專欄超過三千篇。著作易學提要、易學與醫學之綜合研究、洪範易知、易術概要、七政三王真躔萬年星曆、星海辭林六巨冊等。講授易經、天文、中西星象、三元地理、擇日等卅餘年。
目錄
原鈔 李淳風撰 黃家騁增補
002 《乙巳占》黃序 黃家騁
016 唐代天文氣象學家李淳風
025 《乙巳占》目錄
033【首篇】古天文宇宙觀 黃家騁
034 一、蓋天說 036 二、渾天說
037 三、宣夜說 039 四、其他學說
043 天象奇書《乙巳占》李淳風簡介
047 《乙巳占》原鈔樣張
048 《乙巳占》李淳風序
053 《乙巳占》十卷陸心源序
055 《乙巳占》元鈔與今本對照
080 【古天文圖】
074 《敦煌卷鈔》全天星圖
079 世界現存最早宋代大型十顆科學星圖
089 全天星圖
117 【天文圖集】
149 古代知名天文星學家
153 新太陽系,全新面貌
174 全天星表
177 中國星官與曆法
204 黃道宮度表
205 廿八宿星圖
242 風級【風力分級】
247 李淳風風力分級
258 現代颱風分級表
260 【九宮分野】
272 [舊與新]氣象局介紹
294 【颱風】世界最大颱風南施
307 【正文】天文氣象奇書《乙巳占》
309 【乙巳占卷第一】
天象第一
天數第二
天占第三
日占第四 考異
日月旁氣占第五
日蝕占第六
358 【乙巳占卷第二】
月占第七
月與五星相干犯占第八
月干犯列宿占第九
月干犯中外官占第十
月暈占第十一
月暈五星及列宿中外官占第十二
月蝕占第十三
月蝕五星及列宿中外官占第十四
402 【乙巳占卷第三】
分野第十五
占例第十六
日辰占第十七
占期第十八
修德第十九
辨惑第二十(篇元闕)
史司第二十一
451 【乙巳占卷第四】
五星占第二十二
星官占第二十三
五星干犯中外官占第二十四
歲星占第二十五
歲星入列宿占第二十六
歲星干犯中外官占第二十七
475 【乙巳占卷第五】
熒惑占第二十八
熒惑入列宿占第二十九
熒惑干犯中外官占第三十
填星占第三十一
填星入列宿占第三十二
填星干犯中外官占第三十三
506 【乙巳占卷第六】
太白占第三十四
太白入列宿占第三十五
太白入中外官占第三十六
辰星占第三十七
辰星入列宿占第三十八
辰星入中外官占第三十九
534 【乙巳占卷第七】
流星占第四十
流星犯日月占第四十一
流星與五星相犯占第四十二
流星入列宿占第四十三
流星犯中外官占第四十四
客星干犯列宿占第四十五
客星犯中外官占第四十六
562 【乙巳占卷第八】
彗孛占第四十七
彗孛入列宿占第四十八
彗孛入中外官占第四十九
雜星祆星占第五十
氣候占第五十一
雲占第五十二
591 【乙巳占卷第九】
帝王氣象占第五十三
將軍氣象占第五十四
軍勝氣象占第五十五
軍敗氣象占第五十六
城勝氣象占第五十七
屠城氣象占第五十八
伏兵氣象占第五十九
暴兵氣象占第六十
戰陣氣象占第六十一
圖謀氣象占第六十二
【以下原鈔所無,疑原闕或後人增補】
吉凶氣象占第六十三
九土異氣象占第六十四
雲氣入列宿占第六十五
雲氣入中外官占第六十六
雲氣入外官占第六十七
625 【乙巳占卷第十】
候風法第六十八
占風遠近法第六十九
推風聲五音法第七十
五音所主占第七十一
五音風占第七十二
論五音六屬第七十三
五音受正朔日占第七十四
五音相動風占第七十五
五音鳴條已上卒起宮宅中占第七十六
推歲月日時幹德刑殺法第七十七
論六情法第七十八
陰陽六情五音立成第七十九
五音刑德日辰所屬立成第八十
六情風鳥所起加時占第八十一
八方暴風占第八十二
行道宮宅中占第八十三
十二辰風占第八十四
諸解兵風占第八十五
諸陷城風第八十六
占入兵營風第八十七
五音客主法第八十八
四方夷狄侵郡國風占第八十九
占官遷免罪法第九十
候詔書第九十一
候赦贖書第九十二
候大兵將起第九十三
候大兵且解散第九十四
候火災第九十五
候諸公貴客第九十六
候大兵攻城並勝負候賊占第九十七
候喪疾第九十八
候四夷入中國第九十九
雜占王侯公卿二千石出入第一百
713 【附錄】星象詩文
731 步天歌
743 西步天歌
756 天文大象賦 李淳風父李播
770 【推薦】
【星學寶典】《星海辭林-渾天大五星寶卷》
002 《乙巳占》黃序 黃家騁
016 唐代天文氣象學家李淳風
025 《乙巳占》目錄
033【首篇】古天文宇宙觀 黃家騁
034 一、蓋天說 036 二、渾天說
037 三、宣夜說 039 四、其他學說
043 天象奇書《乙巳占》李淳風簡介
047 《乙巳占》原鈔樣張
048 《乙巳占》李淳風序
053 《乙巳占》十卷陸心源序
055 《乙巳占》元鈔與今本對照
080 【古天文圖】
074 《敦煌卷鈔》全天星圖
079 世界現存最早宋代大型十顆科學星圖
089 全天星圖
117 【天文圖集】
149 古代知名天文星學家
153 新太陽系,全新面貌
174 全天星表
177 中國星官與曆法
204 黃道宮度表
205 廿八宿星圖
242 風級【風力分級】
247 李淳風風力分級
258 現代颱風分級表
260 【九宮分野】
272 [舊與新]氣象局介紹
294 【颱風】世界最大颱風南施
307 【正文】天文氣象奇書《乙巳占》
309 【乙巳占卷第一】
天象第一
天數第二
天占第三
日占第四 考異
日月旁氣占第五
日蝕占第六
358 【乙巳占卷第二】
月占第七
月與五星相干犯占第八
月干犯列宿占第九
月干犯中外官占第十
月暈占第十一
月暈五星及列宿中外官占第十二
月蝕占第十三
月蝕五星及列宿中外官占第十四
402 【乙巳占卷第三】
分野第十五
占例第十六
日辰占第十七
占期第十八
修德第十九
辨惑第二十(篇元闕)
史司第二十一
451 【乙巳占卷第四】
五星占第二十二
星官占第二十三
五星干犯中外官占第二十四
歲星占第二十五
歲星入列宿占第二十六
歲星干犯中外官占第二十七
475 【乙巳占卷第五】
熒惑占第二十八
熒惑入列宿占第二十九
熒惑干犯中外官占第三十
填星占第三十一
填星入列宿占第三十二
填星干犯中外官占第三十三
506 【乙巳占卷第六】
太白占第三十四
太白入列宿占第三十五
太白入中外官占第三十六
辰星占第三十七
辰星入列宿占第三十八
辰星入中外官占第三十九
534 【乙巳占卷第七】
流星占第四十
流星犯日月占第四十一
流星與五星相犯占第四十二
流星入列宿占第四十三
流星犯中外官占第四十四
客星干犯列宿占第四十五
客星犯中外官占第四十六
562 【乙巳占卷第八】
彗孛占第四十七
彗孛入列宿占第四十八
彗孛入中外官占第四十九
雜星祆星占第五十
氣候占第五十一
雲占第五十二
591 【乙巳占卷第九】
帝王氣象占第五十三
將軍氣象占第五十四
軍勝氣象占第五十五
軍敗氣象占第五十六
城勝氣象占第五十七
屠城氣象占第五十八
伏兵氣象占第五十九
暴兵氣象占第六十
戰陣氣象占第六十一
圖謀氣象占第六十二
【以下原鈔所無,疑原闕或後人增補】
吉凶氣象占第六十三
九土異氣象占第六十四
雲氣入列宿占第六十五
雲氣入中外官占第六十六
雲氣入外官占第六十七
625 【乙巳占卷第十】
候風法第六十八
占風遠近法第六十九
推風聲五音法第七十
五音所主占第七十一
五音風占第七十二
論五音六屬第七十三
五音受正朔日占第七十四
五音相動風占第七十五
五音鳴條已上卒起宮宅中占第七十六
推歲月日時幹德刑殺法第七十七
論六情法第七十八
陰陽六情五音立成第七十九
五音刑德日辰所屬立成第八十
六情風鳥所起加時占第八十一
八方暴風占第八十二
行道宮宅中占第八十三
十二辰風占第八十四
諸解兵風占第八十五
諸陷城風第八十六
占入兵營風第八十七
五音客主法第八十八
四方夷狄侵郡國風占第八十九
占官遷免罪法第九十
候詔書第九十一
候赦贖書第九十二
候大兵將起第九十三
候大兵且解散第九十四
候火災第九十五
候諸公貴客第九十六
候大兵攻城並勝負候賊占第九十七
候喪疾第九十八
候四夷入中國第九十九
雜占王侯公卿二千石出入第一百
713 【附錄】星象詩文
731 步天歌
743 西步天歌
756 天文大象賦 李淳風父李播
770 【推薦】
【星學寶典】《星海辭林-渾天大五星寶卷》
序
序
黃家騁
【成書年代,兩種說法】
《乙巳占》是一部綜合性的古星學著作,為[唐]李淳風(602-670)撰。一說:成書於唐太宗貞觀十九年(645)乙巳,故名。共分十卷。本書係將唐以前數十種星占書分類匯鈔而成。本書為九卷原鈔(非原本,亦後鈔本),年代無考,應為清初前後。
除星占外還有天文、氣象等內容。其中根據風力對樹林的影響和破壞程度,把它分為八級:一級葉動、二級條鳴、三級振枝、四級墮葉、五級折小枝、六級折大枝、七級折木、飛沙石、八級拔樹及根,是為世界最早的風力分級系統。
書中還保存有作者早年所撰《乙巳元曆》的若干資料,以及作者所發展的渾儀和所著天文儀器專著《法象志》等方面的資料。古代許多天文學名詞亦賴以傳世。
另一說法:撰成于唐高宗顯慶元年(656)丙辰或稍後。至於書名採六十甲子的「乙巳」名為《乙巳占》?
清代藏書家陸心源解釋說:「上元乙巳之歲、十一月甲子朔、冬至夜半、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故以為名」。此說,未必真確。
陸心源認為李淳風推算出準確的「曆元」為「乙巳之歲」,卻未詳加說明。「曆元」多採上元冬至值歲,或採冬至值月干支[月朔],亦有採冬至值日干支[日朔]。
余認為,古云「上古天正冬至甲子夜半朔旦、月建甲子、七政齊元、五星連珠、日月合璧」,乃訂曆元。「曆元」多採「四計甲子」,絕少採乙巳或其他值歲干支,因此陸心源之說保留。
【天正冬至曆元】
「太乙積年」是推算太乙數最為基本的因素,「積年」問題由多種太乙數古籍中的描述得知,起源皆與天象曆法有關,《太乙數統宗大全》卷一所言,最為詳明:
「此太乙積年之算,乃演紀上元甲子,七曜齊元之法也。其法自上古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時、天正冬至、日月合璧、五星連珠、皆合於子,是為上元,由此推來之數也。若以帝堯上元甲子造曆到今,上下止三千六百餘年,此七曜齊元之非術也」。
【四計甲子曆元】
制訂曆法需要一個起算點,稱為「曆元」。此「曆元」與天象有關,史書上常說:「上元混沌甲子之歲、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七曜齊元」。
《太乙金鏡式經》記載:「自上元混沌甲子之歲,至今大唐開元十二年(AD724)甲子歲,積得一百九十三萬七千二百八十一算」。
而《太乙統宗寶鑑》又取BC10153918年冬至為「曆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十一•子部二十一》已駁:
「其求積年術,置演上元甲子,距元大德七年(AD1303)癸卯歲,積一千零一十五萬五千二百一十九年,以為[七曜齊元]之法。然用此積算逆推至上元甲子,得氣應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七十五分,乃戊戌日酉正三刻,非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時也。其非七曜齊元明矣」。
邵子《皇極經世》又取BC67018年冬至為「曆元」(當年冬至為癸丑日)。直到目前為止,科學家發現地球上最古老岩石年齡是45到46億年,即地球形成於距今45-46億年前,而月球形成於距今45.27億年前(亦有50-52億年)。
假設地球形成之時為西安天文時間冬至甲子日之時,當時地月系還未形成,又怎麼有朔旦冬至之說呢?
【上古曆元值年月日不可信】
何況當時一個太陽日比現在一個太陽日的時間短,顯然當時一個太陽年的日數比現在一個太陽年日數多,即使地月系已形成,當時一個朔望月的時間比現在一個朔望月的時間短,即太陽年的時間與朔望月的時間都在變化,沒有一個固定的時間常數,用現在一個太陽年的日數和一個朔望月的日數來推算遠古「曆元」豈不可笑!
故《元史•志第四•曆一》云:「蓋天有不齊之運,而曆為一定之法,所以既久而不能不差,既差則不可不改也」。又云:「然古今曆法,合於今必不能通于古,密于古必不能驗於今」。
《春秋保乾圖》又云:「三百年斗曆改憲」。即便是當今科學家也要借助電腦程式計算天象變化的時間。
中華文明不過萬年,干支紀日源于夏朝,紀年于漢武帝太初元年(BC104年)始定為丁丑年,《晉書•志第八•律曆下》云:
「此元以天正建子黃鐘之月為曆初,元首之歲,夜半甲子朔旦冬至」。即夏曆癸亥年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可取,法國歐亞萬寶有限公司利用電腦程式根據《星曆表推算原理》計算結果表明,在已往的五萬年中,唯有格勒哥里曆BC21778年12月04日符合四甲子朔旦冬至的條件,應當是「曆元」。
【乙巳占係古星學代表作】
《乙巳占》卷首的自撰序,解釋撰述此書的目的及編撰構思。認為自然及人事變化多端,這些變化可以按不同種類相互感應,而人在其中最具典型性,即所謂:「門之所召,隨類畢臻。應之所授,待感斯發。無情尚爾,況在人乎」?
因此人可以通過觀察有關物象變化而瞭解人世事應。而在各種物象變化中,聖人最重視上天垂示的星象,這就導致古星學的誕生。因此按李淳風的理解,星學是有其天象依據的。
星學雖然有其天象依據,但在李淳風看來,歷代星學家卻良莠不齊,既有如軒轅、唐虞、重黎、羲和這樣的一流大家,也有如韓楊、錢樂之類「意唯財穀、志在米鹽」的庸人,還有如袁充之流「諂諛先意、讒害忠良」的奸佞。
有鑒於此,李淳風決定對古星學作一番整理,總結諸家學說,「集其所記,以類相聚,編而次之,采摭英華,刪除繁偽」,編寫一部純正的古星學著作。此即《乙巳占》之由來,並非純為所推算的曆元(乙巳)而寫。如同黃帝元年為甲子之誤。
史載黃帝命大撓氏作甲曆,因此史家或曆家咸認黃帝即位就是甲子年,以此作為黃帝紀元之始,實誤。一切皆須根據天象、依從天命,並非如此巧合。
黃帝元年有幾種說法:前2704丁巳、前2698癸亥、前2697甲子、前2694丁卯、前2674丁亥、《竹書記年》作前2491庚寅等多種,經余考據多時,確認前2704年丁巳為正確,其餘皆誤。
在內容上,《乙巳占》確如李淳風所言,係採擷唐以前諸家古星學學說,加上他自己的發明創造,分類彙編而成。因此《乙巳占》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科學著作,它是一部純粹的古星學典籍。
【乙巳占的重要價值】
《乙巳占》具有重要的文化史和科學史價值,它保存了許多現已失傳的古代文獻資料。隨著科學的發展,古星學逐漸被人們淡忘遺棄,相應地古星學著作也大量散佚,這就給後人的研究造成了巨大的不便。而《乙巳占》是雜採前代諸多占星著作編撰而成的,它為我們保留了許多可貴的古星學史料。
例如,「海上占星術」的史料,東漢已經非常罕見,天文學家張衡在撰述《靈憲》時,詳細敘述了中外星官數時提到:「海人之占未存焉」。而在《乙巳占》引用的古籍中就有《海中占》一書,這自然是極其可貴的。再如,漢代盛行的緯書,經過隋朝的嚴厲禁絕後,大都失傳,而《乙巳占》中卻保存了很多漢代五經緯書的內容。《乙巳占》提及石氏、甘氏、巫咸等的古星家及其著作,對於後人研究這些戰國時期的天文學亦頗有助益。
《乙巳占》在保存資料方面,雖不如其後的《開元占經》詳備,但它撰成於《開元占經》之前,有承前啟後之功。而且《開元占經》在對其前的古籍廣蓄並收之同時,對以往諸家並未加以別擇棄取,此對保存舊有資料極其珍貴,但亦不免失於瑣碎。相比之下,李淳風的《乙巳占》還是要略勝一籌。
《乙巳占》不足之處是未能明確注明占文的由來。李淳風對此解釋說:占文對前人學說「並不復具名氏,非敢隱之,並為是幼小所習誦,前後錯亂,恐失本真故耳」。
雖然他的做法情有可原,但對後人來講,畢竟不便。好在這一缺陷,在《開元占經》中得到了彌補。對於今人來說,只要把兩部書結合起來閱讀,對唐代以前中國古星學的發展狀況,就可以得到一個大致的輪廓。
另外,《乙巳占》有助於我們獲得對李淳風的全面瞭解。他是唐代一位傑出的天文學家與氣象學家,又是久享盛名的星學家、預言家,傳統上人們對他的古星學的瞭解,主要是通過新舊《唐書》本傳的記載及其他書籍的間接反映。如此所獲得的認識易有所偏失。
例如《舊唐書》本傳說他「每占候吉凶,合若符契,當時術者疑其別有役使,不因學習所致,然竟不能測也」。李淳風因其占候靈驗而聞名,但他本人在《乙巳占》中並不主張特別追求星象學的靈驗性,因為天命之學七成有其準驗之處,但仍有兩三成變數例外,不易掌握,難求絕對準驗。
他指出:「若乃天道幽遠,變化非一,至理難測,應感詎同?梓慎、裨灶,占或未周,況術斯已下,焉足可說。至若多言屢中,非余所尊」。這是說,自然界是複雜的,星測家在對應進行解說時,很難做到準確無誤。星家所要追求的,不應是「多言屢中」,而應是「權宜時政,斟酌治綱,驗人事之是非,托神道以設教」。可見他是將星學作為一種輔政措施來推行。
【今傳版本,訛誤甚多】
《乙巳占》有著巨大的文化史、科技史價值,這是不言而喻的,但它同時又是一部以星象學為主的著作,夾雜著大量的雜說異術。在閱讀此書時,對此應有清楚的認識。
對於《乙巳占》這樣一部文化史與星學著作,學界迄今的研究還遠遠不足。要真正揭示其全面的文化與學術價值,還有待進一步探索,而本書的刊行就是一個重要的開端。
《乙巳占》今本十卷。《新唐書•藝文志》在著錄該書時稱為十二卷,宋代以降都只著錄為十卷。陸心源鑒於最後一卷的字數約為其他各卷每卷字數的三倍,懷疑是後人把最後三卷合為一卷,因此與《新唐書》的記載不符。
但《舊唐書‧經籍志》在著錄此書時已標明其為十卷,這表明在《新唐書》成書之前《乙巳占》即為十卷本。故亦有可能北宋時人們鑒於最後一卷字數龐大而將其一分為三,但此種做法未得到後人認可,於是不久又被恢復為十卷本原貌。
宋代以後,《乙巳占》流布甚稀。清乾隆年間編修《四庫全書》竟未收錄,故《四庫全書》中無此書。
阮元的《疇人傳》對《乙巳占》亦未提及。朱彝尊見到的,也只是殘本七卷,只有錢曾《讀書敏求記》提到此書。
陸心源的門人從金匱蔡氏鈔得一本,被收入陸心源的《十萬卷樓叢書》,商務印書館在編輯出版《叢書集成》時,據《十萬卷樓叢書》本,將《乙巳占》重新標點排印,收入其哲學類。
近年大象出版社在彙編出版《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典籍通匯》時,亦據陸氏《十萬卷樓叢書》光緒三年丁丑本,將《乙巳占》收入其天文類中。至此一般讀者要閱讀此書較為方便。
而本書之九卷原鈔,看不出末卷有殘缺而遭刪裁之象,並有[後序淳風撰]一段(詳見下段),作為終結,已似完整終結,當無疑義。
【後序內容】
欲知吉凶之得失者,當觀所犯之宮座,在人之善察焉耳,預曉妖變,括量詮度,推氣出沒,精之益精,玄之又玄,其諸隱辭﹑占決,並在略例中苦志言求,得此圖指(旨要也)者也。予(即余,指淳風)且為之白首,粗得其門,後之學者深鑑此意,慎毋忽諸。
【研究天文氣象數十載】
余對易經、天文、中西星學、曆法、氣象等從小涉獵。舅家本係旅日華僑二代,三舅鄭國駒畢業於知名的關西學院,隨父親(中央特派「行政長官公署」專員、各處視察)來臺後,即任職於接收後的「臺北測候所」(後升格為臺灣省氣象局、國立中央氣象局)。
余自幼即接觸天文、氣象、颱風、地震、水文、地質等科學,加上家學《易經》、洪範、天文、星學、曆算等傳承,就讀圖書資料科系,蒐集研讀諸多線裝古籍,對星學、氣象特感興趣,埋首於此數十載,頗有收獲。又攻讀環境科學與生命生化醫學等專業學科。
因為深研天地人三才之學,因此融匯成一套新法天文星學體系,因為《易經》就是一部天文、星象、曆算與數學,以此為基礎,洞徹天文氣象之學。
一九八七年夏,中央氣象局天文站站長與某高層造訪敝宅,探討一九八八年農曆七月一日,當陽曆八月一日或二日。稱中央政府需要一份一九八八年正確的行事曆,訪遍各研究單位及教授學者,沒有答案,皆認係「八月一日」。但是大陸港版皆為「八月二日」。
當訪客提到此問題,余立即答覆說是「八月二日」,並將已演算好數十年的星曆表與陰陽曆對照表應證確係「八月二日」無誤,顯現國內萬年曆,皆採自清朝時期推算之時憲曆書,沿用至今,因以致誤。
余對置閏問題早已注意,並推算校正了西元前五千年至西元後三千年間,前後數千年的「閏月」與交年「正朔」與「節氣」換月問題,發現多七八成「閏月」有誤,一兩成「月朔」錯誤,導致月份錯亂,情況嚴重,必須更正,但中央氣象局沒有編曆單位與專才,以至官方曆法與民間通書,錯誤百出,貽害甚深。在座官員有意邀請余擔任中央氣象局局長職,遭余婉謝。又邀擔任該局最高顧問,亦無意願。余並提供一份編就完成的萬年曆以供參考,亦可對外發布。
一九九五年十月三日,義美公司舉辦「廿一世紀有幾次閏八月」之專題座談會,特邀中央氣象局天文站站長鄭秀能參與,因局內對該主題未及深入探討,又邀約余出席,並代表中央氣象局發言,提出專題報告,應邀六位貴賓僅余一人對主題提出研究數據與報告,餘等皆是作陪而已。
座談會主席為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天文學博士黃一農,亦肯定余之推算結果,並稱還需要用超級電腦複驗。事實上,古人無計算器或電腦,一樣能推算複雜的天象、日月食、曆算、置閏等諸事,不是電腦問題,而是通曉曆算與否的問題。
【重刊本書,光大星學】
元氣齋出版社特選本書新校重刊,認係千百年來沒有個人或出版單位,敢對本書作詮釋或校勘出版,林老闆有心弘揚星學,值得感佩、讚許與支持。
兩年前,余接到撰寫詮釋本書之邀約,深感榮幸,更感惶恐。以李淳風之天文、氣象專才與知識,余深感不如,但以現代科學的知識與電子電腦機具的輔助計算,適以補救知識與觀測上的不足,遂專心於此書的詮釋與考據,初感費力,已漸順手。
余深深認為,不是通曉天文、氣象即可詮釋本書。細察本書即知,其中諸多引用《易經》章句,因知李淳風和諸多學者專家,都有易學與經學根基與深入研究。因為《易經》就是一部天文學、星象學、曆算學與數學等,包涵一切現代科學在內的宇宙法則。
近年因身體不適,在醫療調適之餘,仍努力詮註本書,已初步完成序文與前兩卷,期間難免有滯礙難明之處,亦設法查證,務求精確無誤。對手中珍藏之九卷原鈔,認係清初或之前稿鈔,至為珍罕,現以此稿本作為詮釋依據,重新校勘,其中有誤鈔、闕文、衍文之處,亦一併更正。
至於被陸心源收錄於《十萬卷樓叢書》光緒三年丁丑版的《乙巳占》,係後刊本。今日坊間流傳之十卷百節之《乙巳占》,因流傳久遠,與九卷原鈔對比,訛誤、竄亂甚多,必須多所查證校刊,頗費時日,未敢採用,仍以九卷原鈔為主。
今將原鈔與原序作詮釋引據,編成一冊,先行出版。至於原鈔九卷內容,將於後續出版。對星學先賢古籍作出詮釋,責任重大,力求不失本意,並加現代科學詮釋,應能保留並增強古星學典籍的真實性與參考性,對研究學者而言,應是一項新的認識與方向,此序。
唐代天文氣象學家李淳風
【家世】
父親李播是隋時的高唐尉,後放棄官職為道士,道號黃冠子,著有《天文大象賦》。(《新唐書‧列傳第一百二十九方技》:「李淳風,岐州雍人。父播,仕隋高唐尉,棄官為道士,號黃冠子,以論撰自見」)。
602年(隋文帝仁壽二年)生於岐州,雍人(今陝西省鳳翔縣)。逝於670年(唐高宗總章三年、咸亨元年,68歲)長安城(今陝西西安)。曾於南坨山修練,師承至元道長。唐初,任職朝議大夫行太史令上輕車都尉。為唐初政治人物、天文學家、曆算家、預言家和數學家。
臺灣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三重環」結構古渾天儀即李淳風發明
【著作】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641年)任太史丞,撰《法象志》。《新唐書.天文志》載:「貞觀中,淳風撰《法象志》,因《漢書》十二次度數,始以唐之州縣配焉。而一行以為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注釋《算經十書》、《孫子算經》、《周髀算經》等。另有《秘閣錄》、《典章文物志》、《推背圖》、《乙巳占》等。
他的不朽成就頗多。唐高宗時,李淳風以劉焯的《皇極曆》為據,編成《麟德曆》。曾製作渾天黃道儀。《舊唐書》、《新唐書》皆記載李淳風曾研製「三重環」渾天儀。指出《戊寅元曆》的錯誤,唐高宗麟德二年(665),改用李淳風的《麟德曆》。
【李氏以星學推測聞名】
李淳風早年學道於天台山,通曉天文星象,最早是隋煬帝時的司監官。
[一]劉餗的《隋唐嘉話》記載:淳風能預測日蝕。唐太宗頗不信其言。李淳風說:「有如不蝕,則臣請死之」。一日,唐太宗等不到日蝕,於是對李淳風說:「我放你回家,和老婆孩子告別」。李淳風在牆上劃了一條標記說:「尚早一刻。等到日光照到這裡時,日食就出現了」。後來果「如言而食,不差毫髮」。
[二]一日李淳風與張文收同皇帝出遊,有狂風從南面迎來,李淳風認為在南面五里處一定有人在哭,張文收則認為那裡有音樂聲。後來果然有一送葬儀隊經過。
余認為,日食之準確時分,係由星算、曆數的精算得知,非由觀星、占候而來。後者則應由易卜或星學推知,若曉奇門,亦能得知。
[原文]《太平廣記》卷第七十六方士一:「李以為南五里當有哭者,張以為有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送葬者」。劉餗《隋唐嘉話》卷中:「李太史與張文收率更坐,有暴風自南而至,李以南五里當有哭者,張以為有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送葬者,有鼓吹焉」。
【觀星與星算有異】
[一]相傳與袁天罡跟唐太宗出遊,看見河邊有赤馬和黑馬。太宗要袁、李推算那隻馬先入河。袁占得離卦,離為火,稱是赤馬先入水。李淳風則認為,鑽木取火,應先見黑煙才見火,便稱是黑馬先入河。結果李淳風對了,但卻謙稱因袁天罡之卜,方能推知煙和火的奧妙關係。因此知道,觀其表象是觀星觀氣,不夠深入,因求其底蘊,方是真相。
李淳風與袁天罡(生卒年不詳,唐初任火山令,著名相士)二人,並不是杜撰出來的人物《新唐書‧列傳》第129,曾記載他們兩人的故事。《新唐書‧天文志》載:「貞觀中,淳風撰《法象志》,因《漢書》十二次度數,始以唐之州縣配焉。而一行以為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
[二]唐太宗貞觀十五年(641)任太史丞,撰《法象志》。貞觀廿二年(648)任太史令,奉詔註釋《算經十書》。一日,唐太宗得到一本秘讖,上面說:「唐中弱,有女武代王」。李淳風預知武后將稱帝,且改變會造成不能預計的後果(《新唐書‧列傳第一百九十五‧方技》)。
相傳唐太宗寵幸武則天,封她為才人。李淳風提醒太宗,武氏將會亂政,太宗只是半信半疑。李淳風於是預言今科狀元為「火犬二人之傑」,果然是狄仁傑(630-700)高中,太宗只好把武則天放逐為尼。
[原文]《薛剛反唐‧第二回》:「其時司天監李淳風,知唐室有殺戮親王之驚,女主專權帝位,因此密奏太宗……,李淳風知屈殺多人,連忙奏道:陛下勿殺害眾人。臣前日所奏,上達天意,不敢有誤。武氏乃宮中武氏也,望陛下去之。此時太宗正當錦帳歡娛,鴛枕取樂,怎肯將武氏貶殺,便道:卿既能知未來天意,可曉得今科狀元是誰?……臣見天榜名姓,乃火犬二人之傑……至放榜日期,首名狀元姓狄,名仁傑」。
如果此兩事當真,應該不是「察天星、觀雲氣、占候驗」而得知,此應是經由《易經》與星學之推算得來,世傳《推背圖》預知天下事,亦復如是,當然亦有可能由人相、體相上察知,或推算星命得驗,故能前知過去、逆算未來。
《易‧說卦》:「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因為後人不知其推算方法,視為千古神秘,指為迷信、巧合,不足為信。事實上,《易經》與星學是最佳的推測工具,絕對超越察星、觀氣或占候之學。
【天命之學宜修德禳之】
再如他在勸阻唐太宗不要濫殺無辜時說:「天之所命,必無禳避之理」,但《乙巳占》卷三的《修德》篇卻強調對天變要「修德以禳之」。這兩種見解,本質上是相互矛盾的。
不讀《乙巳占》,對李淳風的思想就很難把握。而且《乙巳占》所言,是符合中國星學的基本原理,古星學強調的就是要通過觀測星象,瞭解所謂的「天心」、「天意」,然後「修德以禳之」,讓上天收回對自己不利的成命。
如果沒有這一條,古星學的價值就不存在了。通過《乙巳占》的論述,我們對新舊《唐書》本傳的說法,也有了新的理解。
李淳風是位精通天文學的古星家,因而他對各類天象的描述,與其他人編撰的古星學著作相比,就比較準確。
《乙巳占》中有大量星學術語,對於這些術語,李淳風一般是先給出一個明確的定義,再闡述其對人事的象徵意義。這種做法有利於擺脫傳統星學的模糊和不確定。而古星學一旦不再模糊,就會很容易暴露出其不科學之處。古星學發展得愈具體明確,就愈容易暴露其缺點。
所以李淳風的這種做法有利於科學發展,儘管他並非有意識地要用這種做法暴露古星學的缺點。
對當代人來說,則可透過這些術語的定義,瞭解當時人們的天文學知識。由此《乙巳占》使古星學變得精確化,對於科學發展而言,是有價值的。
【包涵諸多天文知識】
《乙巳占》除了古星學內容之外,還記敘了許多實實在在的天文學知識。例如卷一《天數》篇記述其改進後渾儀的具體結構,就很有價值。儘管新舊《唐書》對李淳風所制渾儀,均有記述,但《乙巳占》的說明係李淳風親手所撰,內容比新舊《唐書》的記載更為詳細,時間上也早得多,這就補充正史之不足。
《乙巳占》有助於我們瞭解古代有關天文學理論的演變。例如關於五星運動與太陽的關係,《舊五代史•曆志》記載了後周王樸的一篇奏議,上面提到:「星之行也,近日而疾,遠日而遲,去日極遠,勢盡而留」。
而《開元占經》卷六十四則引韓公賓注《靈憲》曰:「五星之行,近日則遲,……遠日則速」。這與王樸的奏議正好相反。稍晚于李淳風的僧一行作《大衍曆議》,提到印度天文學關於行星運動速率變化原因的解釋,說「《天竺曆》以《九執》之情,皆有所好惡。遇其所好之星,則趣之行疾,舍之行遲」。
而李淳風在《乙巳占》卷三則給出了另一種說法:「歲星近日則遲,遠日則疾。熒惑近日則疾,遠日則遲。填星之行,自見至留、逆、復順,恒各平行,無有益遲益疾。太白、辰星,晨見,初則遲而後疾,疾則伏;夕見,初則疾而漸遲,遲則伏。此則五星當分遲疾大量也」。
顯然,如果沒有《乙巳占》的這一記載,我們對於古代行星運動速率變化學說多樣性的認識,就要打很大的折扣。
【世界最早將風力分級】
《乙巳占》另一頗值得一提之處是其對風力大小所做的分級。李淳風依據風力對樹木的影響和損壞程度將其分為八級,據《乙巳占》卷十《占風遠近法》的描述,這八級分別為:一級動葉、二級鳴條、三級搖枝、四級墮葉、五級折小枝、六級折大枝、七級折木飛沙石、八級拔樹及根。
李淳風認為不同大小的風其所由來的遠近也不同,風力越大,其所由來的距離越遠。他將風分為八級,就是為了標誌相應的風所由來的遠近,並據此進行占測。他將風的大小與其由來遠近相掛鉤的做法得不到現代科學的支持。
雖然如此,他對風力大小進行定量分級的做法卻是科學的。而且儘管他的著眼點在於占測,但這一分級本身在中國歷史上卻是最早的。
此外,卷十的《候風法》記述了兩種風向儀的製作方法及相應的使用場合,也有很高的科學價值。
黃家騁
【成書年代,兩種說法】
《乙巳占》是一部綜合性的古星學著作,為[唐]李淳風(602-670)撰。一說:成書於唐太宗貞觀十九年(645)乙巳,故名。共分十卷。本書係將唐以前數十種星占書分類匯鈔而成。本書為九卷原鈔(非原本,亦後鈔本),年代無考,應為清初前後。
除星占外還有天文、氣象等內容。其中根據風力對樹林的影響和破壞程度,把它分為八級:一級葉動、二級條鳴、三級振枝、四級墮葉、五級折小枝、六級折大枝、七級折木、飛沙石、八級拔樹及根,是為世界最早的風力分級系統。
書中還保存有作者早年所撰《乙巳元曆》的若干資料,以及作者所發展的渾儀和所著天文儀器專著《法象志》等方面的資料。古代許多天文學名詞亦賴以傳世。
另一說法:撰成于唐高宗顯慶元年(656)丙辰或稍後。至於書名採六十甲子的「乙巳」名為《乙巳占》?
清代藏書家陸心源解釋說:「上元乙巳之歲、十一月甲子朔、冬至夜半、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故以為名」。此說,未必真確。
陸心源認為李淳風推算出準確的「曆元」為「乙巳之歲」,卻未詳加說明。「曆元」多採上元冬至值歲,或採冬至值月干支[月朔],亦有採冬至值日干支[日朔]。
余認為,古云「上古天正冬至甲子夜半朔旦、月建甲子、七政齊元、五星連珠、日月合璧」,乃訂曆元。「曆元」多採「四計甲子」,絕少採乙巳或其他值歲干支,因此陸心源之說保留。
【天正冬至曆元】
「太乙積年」是推算太乙數最為基本的因素,「積年」問題由多種太乙數古籍中的描述得知,起源皆與天象曆法有關,《太乙數統宗大全》卷一所言,最為詳明:
「此太乙積年之算,乃演紀上元甲子,七曜齊元之法也。其法自上古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時、天正冬至、日月合璧、五星連珠、皆合於子,是為上元,由此推來之數也。若以帝堯上元甲子造曆到今,上下止三千六百餘年,此七曜齊元之非術也」。
【四計甲子曆元】
制訂曆法需要一個起算點,稱為「曆元」。此「曆元」與天象有關,史書上常說:「上元混沌甲子之歲、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七曜齊元」。
《太乙金鏡式經》記載:「自上元混沌甲子之歲,至今大唐開元十二年(AD724)甲子歲,積得一百九十三萬七千二百八十一算」。
而《太乙統宗寶鑑》又取BC10153918年冬至為「曆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十一•子部二十一》已駁:
「其求積年術,置演上元甲子,距元大德七年(AD1303)癸卯歲,積一千零一十五萬五千二百一十九年,以為[七曜齊元]之法。然用此積算逆推至上元甲子,得氣應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七十五分,乃戊戌日酉正三刻,非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時也。其非七曜齊元明矣」。
邵子《皇極經世》又取BC67018年冬至為「曆元」(當年冬至為癸丑日)。直到目前為止,科學家發現地球上最古老岩石年齡是45到46億年,即地球形成於距今45-46億年前,而月球形成於距今45.27億年前(亦有50-52億年)。
假設地球形成之時為西安天文時間冬至甲子日之時,當時地月系還未形成,又怎麼有朔旦冬至之說呢?
【上古曆元值年月日不可信】
何況當時一個太陽日比現在一個太陽日的時間短,顯然當時一個太陽年的日數比現在一個太陽年日數多,即使地月系已形成,當時一個朔望月的時間比現在一個朔望月的時間短,即太陽年的時間與朔望月的時間都在變化,沒有一個固定的時間常數,用現在一個太陽年的日數和一個朔望月的日數來推算遠古「曆元」豈不可笑!
故《元史•志第四•曆一》云:「蓋天有不齊之運,而曆為一定之法,所以既久而不能不差,既差則不可不改也」。又云:「然古今曆法,合於今必不能通于古,密于古必不能驗於今」。
《春秋保乾圖》又云:「三百年斗曆改憲」。即便是當今科學家也要借助電腦程式計算天象變化的時間。
中華文明不過萬年,干支紀日源于夏朝,紀年于漢武帝太初元年(BC104年)始定為丁丑年,《晉書•志第八•律曆下》云:
「此元以天正建子黃鐘之月為曆初,元首之歲,夜半甲子朔旦冬至」。即夏曆癸亥年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可取,法國歐亞萬寶有限公司利用電腦程式根據《星曆表推算原理》計算結果表明,在已往的五萬年中,唯有格勒哥里曆BC21778年12月04日符合四甲子朔旦冬至的條件,應當是「曆元」。
【乙巳占係古星學代表作】
《乙巳占》卷首的自撰序,解釋撰述此書的目的及編撰構思。認為自然及人事變化多端,這些變化可以按不同種類相互感應,而人在其中最具典型性,即所謂:「門之所召,隨類畢臻。應之所授,待感斯發。無情尚爾,況在人乎」?
因此人可以通過觀察有關物象變化而瞭解人世事應。而在各種物象變化中,聖人最重視上天垂示的星象,這就導致古星學的誕生。因此按李淳風的理解,星學是有其天象依據的。
星學雖然有其天象依據,但在李淳風看來,歷代星學家卻良莠不齊,既有如軒轅、唐虞、重黎、羲和這樣的一流大家,也有如韓楊、錢樂之類「意唯財穀、志在米鹽」的庸人,還有如袁充之流「諂諛先意、讒害忠良」的奸佞。
有鑒於此,李淳風決定對古星學作一番整理,總結諸家學說,「集其所記,以類相聚,編而次之,采摭英華,刪除繁偽」,編寫一部純正的古星學著作。此即《乙巳占》之由來,並非純為所推算的曆元(乙巳)而寫。如同黃帝元年為甲子之誤。
史載黃帝命大撓氏作甲曆,因此史家或曆家咸認黃帝即位就是甲子年,以此作為黃帝紀元之始,實誤。一切皆須根據天象、依從天命,並非如此巧合。
黃帝元年有幾種說法:前2704丁巳、前2698癸亥、前2697甲子、前2694丁卯、前2674丁亥、《竹書記年》作前2491庚寅等多種,經余考據多時,確認前2704年丁巳為正確,其餘皆誤。
在內容上,《乙巳占》確如李淳風所言,係採擷唐以前諸家古星學學說,加上他自己的發明創造,分類彙編而成。因此《乙巳占》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科學著作,它是一部純粹的古星學典籍。
【乙巳占的重要價值】
《乙巳占》具有重要的文化史和科學史價值,它保存了許多現已失傳的古代文獻資料。隨著科學的發展,古星學逐漸被人們淡忘遺棄,相應地古星學著作也大量散佚,這就給後人的研究造成了巨大的不便。而《乙巳占》是雜採前代諸多占星著作編撰而成的,它為我們保留了許多可貴的古星學史料。
例如,「海上占星術」的史料,東漢已經非常罕見,天文學家張衡在撰述《靈憲》時,詳細敘述了中外星官數時提到:「海人之占未存焉」。而在《乙巳占》引用的古籍中就有《海中占》一書,這自然是極其可貴的。再如,漢代盛行的緯書,經過隋朝的嚴厲禁絕後,大都失傳,而《乙巳占》中卻保存了很多漢代五經緯書的內容。《乙巳占》提及石氏、甘氏、巫咸等的古星家及其著作,對於後人研究這些戰國時期的天文學亦頗有助益。
《乙巳占》在保存資料方面,雖不如其後的《開元占經》詳備,但它撰成於《開元占經》之前,有承前啟後之功。而且《開元占經》在對其前的古籍廣蓄並收之同時,對以往諸家並未加以別擇棄取,此對保存舊有資料極其珍貴,但亦不免失於瑣碎。相比之下,李淳風的《乙巳占》還是要略勝一籌。
《乙巳占》不足之處是未能明確注明占文的由來。李淳風對此解釋說:占文對前人學說「並不復具名氏,非敢隱之,並為是幼小所習誦,前後錯亂,恐失本真故耳」。
雖然他的做法情有可原,但對後人來講,畢竟不便。好在這一缺陷,在《開元占經》中得到了彌補。對於今人來說,只要把兩部書結合起來閱讀,對唐代以前中國古星學的發展狀況,就可以得到一個大致的輪廓。
另外,《乙巳占》有助於我們獲得對李淳風的全面瞭解。他是唐代一位傑出的天文學家與氣象學家,又是久享盛名的星學家、預言家,傳統上人們對他的古星學的瞭解,主要是通過新舊《唐書》本傳的記載及其他書籍的間接反映。如此所獲得的認識易有所偏失。
例如《舊唐書》本傳說他「每占候吉凶,合若符契,當時術者疑其別有役使,不因學習所致,然竟不能測也」。李淳風因其占候靈驗而聞名,但他本人在《乙巳占》中並不主張特別追求星象學的靈驗性,因為天命之學七成有其準驗之處,但仍有兩三成變數例外,不易掌握,難求絕對準驗。
他指出:「若乃天道幽遠,變化非一,至理難測,應感詎同?梓慎、裨灶,占或未周,況術斯已下,焉足可說。至若多言屢中,非余所尊」。這是說,自然界是複雜的,星測家在對應進行解說時,很難做到準確無誤。星家所要追求的,不應是「多言屢中」,而應是「權宜時政,斟酌治綱,驗人事之是非,托神道以設教」。可見他是將星學作為一種輔政措施來推行。
【今傳版本,訛誤甚多】
《乙巳占》有著巨大的文化史、科技史價值,這是不言而喻的,但它同時又是一部以星象學為主的著作,夾雜著大量的雜說異術。在閱讀此書時,對此應有清楚的認識。
對於《乙巳占》這樣一部文化史與星學著作,學界迄今的研究還遠遠不足。要真正揭示其全面的文化與學術價值,還有待進一步探索,而本書的刊行就是一個重要的開端。
《乙巳占》今本十卷。《新唐書•藝文志》在著錄該書時稱為十二卷,宋代以降都只著錄為十卷。陸心源鑒於最後一卷的字數約為其他各卷每卷字數的三倍,懷疑是後人把最後三卷合為一卷,因此與《新唐書》的記載不符。
但《舊唐書‧經籍志》在著錄此書時已標明其為十卷,這表明在《新唐書》成書之前《乙巳占》即為十卷本。故亦有可能北宋時人們鑒於最後一卷字數龐大而將其一分為三,但此種做法未得到後人認可,於是不久又被恢復為十卷本原貌。
宋代以後,《乙巳占》流布甚稀。清乾隆年間編修《四庫全書》竟未收錄,故《四庫全書》中無此書。
阮元的《疇人傳》對《乙巳占》亦未提及。朱彝尊見到的,也只是殘本七卷,只有錢曾《讀書敏求記》提到此書。
陸心源的門人從金匱蔡氏鈔得一本,被收入陸心源的《十萬卷樓叢書》,商務印書館在編輯出版《叢書集成》時,據《十萬卷樓叢書》本,將《乙巳占》重新標點排印,收入其哲學類。
近年大象出版社在彙編出版《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典籍通匯》時,亦據陸氏《十萬卷樓叢書》光緒三年丁丑本,將《乙巳占》收入其天文類中。至此一般讀者要閱讀此書較為方便。
而本書之九卷原鈔,看不出末卷有殘缺而遭刪裁之象,並有[後序淳風撰]一段(詳見下段),作為終結,已似完整終結,當無疑義。
【後序內容】
欲知吉凶之得失者,當觀所犯之宮座,在人之善察焉耳,預曉妖變,括量詮度,推氣出沒,精之益精,玄之又玄,其諸隱辭﹑占決,並在略例中苦志言求,得此圖指(旨要也)者也。予(即余,指淳風)且為之白首,粗得其門,後之學者深鑑此意,慎毋忽諸。
【研究天文氣象數十載】
余對易經、天文、中西星學、曆法、氣象等從小涉獵。舅家本係旅日華僑二代,三舅鄭國駒畢業於知名的關西學院,隨父親(中央特派「行政長官公署」專員、各處視察)來臺後,即任職於接收後的「臺北測候所」(後升格為臺灣省氣象局、國立中央氣象局)。
余自幼即接觸天文、氣象、颱風、地震、水文、地質等科學,加上家學《易經》、洪範、天文、星學、曆算等傳承,就讀圖書資料科系,蒐集研讀諸多線裝古籍,對星學、氣象特感興趣,埋首於此數十載,頗有收獲。又攻讀環境科學與生命生化醫學等專業學科。
因為深研天地人三才之學,因此融匯成一套新法天文星學體系,因為《易經》就是一部天文、星象、曆算與數學,以此為基礎,洞徹天文氣象之學。
一九八七年夏,中央氣象局天文站站長與某高層造訪敝宅,探討一九八八年農曆七月一日,當陽曆八月一日或二日。稱中央政府需要一份一九八八年正確的行事曆,訪遍各研究單位及教授學者,沒有答案,皆認係「八月一日」。但是大陸港版皆為「八月二日」。
當訪客提到此問題,余立即答覆說是「八月二日」,並將已演算好數十年的星曆表與陰陽曆對照表應證確係「八月二日」無誤,顯現國內萬年曆,皆採自清朝時期推算之時憲曆書,沿用至今,因以致誤。
余對置閏問題早已注意,並推算校正了西元前五千年至西元後三千年間,前後數千年的「閏月」與交年「正朔」與「節氣」換月問題,發現多七八成「閏月」有誤,一兩成「月朔」錯誤,導致月份錯亂,情況嚴重,必須更正,但中央氣象局沒有編曆單位與專才,以至官方曆法與民間通書,錯誤百出,貽害甚深。在座官員有意邀請余擔任中央氣象局局長職,遭余婉謝。又邀擔任該局最高顧問,亦無意願。余並提供一份編就完成的萬年曆以供參考,亦可對外發布。
一九九五年十月三日,義美公司舉辦「廿一世紀有幾次閏八月」之專題座談會,特邀中央氣象局天文站站長鄭秀能參與,因局內對該主題未及深入探討,又邀約余出席,並代表中央氣象局發言,提出專題報告,應邀六位貴賓僅余一人對主題提出研究數據與報告,餘等皆是作陪而已。
座談會主席為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天文學博士黃一農,亦肯定余之推算結果,並稱還需要用超級電腦複驗。事實上,古人無計算器或電腦,一樣能推算複雜的天象、日月食、曆算、置閏等諸事,不是電腦問題,而是通曉曆算與否的問題。
【重刊本書,光大星學】
元氣齋出版社特選本書新校重刊,認係千百年來沒有個人或出版單位,敢對本書作詮釋或校勘出版,林老闆有心弘揚星學,值得感佩、讚許與支持。
兩年前,余接到撰寫詮釋本書之邀約,深感榮幸,更感惶恐。以李淳風之天文、氣象專才與知識,余深感不如,但以現代科學的知識與電子電腦機具的輔助計算,適以補救知識與觀測上的不足,遂專心於此書的詮釋與考據,初感費力,已漸順手。
余深深認為,不是通曉天文、氣象即可詮釋本書。細察本書即知,其中諸多引用《易經》章句,因知李淳風和諸多學者專家,都有易學與經學根基與深入研究。因為《易經》就是一部天文學、星象學、曆算學與數學等,包涵一切現代科學在內的宇宙法則。
近年因身體不適,在醫療調適之餘,仍努力詮註本書,已初步完成序文與前兩卷,期間難免有滯礙難明之處,亦設法查證,務求精確無誤。對手中珍藏之九卷原鈔,認係清初或之前稿鈔,至為珍罕,現以此稿本作為詮釋依據,重新校勘,其中有誤鈔、闕文、衍文之處,亦一併更正。
至於被陸心源收錄於《十萬卷樓叢書》光緒三年丁丑版的《乙巳占》,係後刊本。今日坊間流傳之十卷百節之《乙巳占》,因流傳久遠,與九卷原鈔對比,訛誤、竄亂甚多,必須多所查證校刊,頗費時日,未敢採用,仍以九卷原鈔為主。
今將原鈔與原序作詮釋引據,編成一冊,先行出版。至於原鈔九卷內容,將於後續出版。對星學先賢古籍作出詮釋,責任重大,力求不失本意,並加現代科學詮釋,應能保留並增強古星學典籍的真實性與參考性,對研究學者而言,應是一項新的認識與方向,此序。
唐代天文氣象學家李淳風
【家世】
父親李播是隋時的高唐尉,後放棄官職為道士,道號黃冠子,著有《天文大象賦》。(《新唐書‧列傳第一百二十九方技》:「李淳風,岐州雍人。父播,仕隋高唐尉,棄官為道士,號黃冠子,以論撰自見」)。
602年(隋文帝仁壽二年)生於岐州,雍人(今陝西省鳳翔縣)。逝於670年(唐高宗總章三年、咸亨元年,68歲)長安城(今陝西西安)。曾於南坨山修練,師承至元道長。唐初,任職朝議大夫行太史令上輕車都尉。為唐初政治人物、天文學家、曆算家、預言家和數學家。
臺灣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三重環」結構古渾天儀即李淳風發明
【著作】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641年)任太史丞,撰《法象志》。《新唐書.天文志》載:「貞觀中,淳風撰《法象志》,因《漢書》十二次度數,始以唐之州縣配焉。而一行以為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注釋《算經十書》、《孫子算經》、《周髀算經》等。另有《秘閣錄》、《典章文物志》、《推背圖》、《乙巳占》等。
他的不朽成就頗多。唐高宗時,李淳風以劉焯的《皇極曆》為據,編成《麟德曆》。曾製作渾天黃道儀。《舊唐書》、《新唐書》皆記載李淳風曾研製「三重環」渾天儀。指出《戊寅元曆》的錯誤,唐高宗麟德二年(665),改用李淳風的《麟德曆》。
【李氏以星學推測聞名】
李淳風早年學道於天台山,通曉天文星象,最早是隋煬帝時的司監官。
[一]劉餗的《隋唐嘉話》記載:淳風能預測日蝕。唐太宗頗不信其言。李淳風說:「有如不蝕,則臣請死之」。一日,唐太宗等不到日蝕,於是對李淳風說:「我放你回家,和老婆孩子告別」。李淳風在牆上劃了一條標記說:「尚早一刻。等到日光照到這裡時,日食就出現了」。後來果「如言而食,不差毫髮」。
[二]一日李淳風與張文收同皇帝出遊,有狂風從南面迎來,李淳風認為在南面五里處一定有人在哭,張文收則認為那裡有音樂聲。後來果然有一送葬儀隊經過。
余認為,日食之準確時分,係由星算、曆數的精算得知,非由觀星、占候而來。後者則應由易卜或星學推知,若曉奇門,亦能得知。
[原文]《太平廣記》卷第七十六方士一:「李以為南五里當有哭者,張以為有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送葬者」。劉餗《隋唐嘉話》卷中:「李太史與張文收率更坐,有暴風自南而至,李以南五里當有哭者,張以為有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送葬者,有鼓吹焉」。
【觀星與星算有異】
[一]相傳與袁天罡跟唐太宗出遊,看見河邊有赤馬和黑馬。太宗要袁、李推算那隻馬先入河。袁占得離卦,離為火,稱是赤馬先入水。李淳風則認為,鑽木取火,應先見黑煙才見火,便稱是黑馬先入河。結果李淳風對了,但卻謙稱因袁天罡之卜,方能推知煙和火的奧妙關係。因此知道,觀其表象是觀星觀氣,不夠深入,因求其底蘊,方是真相。
李淳風與袁天罡(生卒年不詳,唐初任火山令,著名相士)二人,並不是杜撰出來的人物《新唐書‧列傳》第129,曾記載他們兩人的故事。《新唐書‧天文志》載:「貞觀中,淳風撰《法象志》,因《漢書》十二次度數,始以唐之州縣配焉。而一行以為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
[二]唐太宗貞觀十五年(641)任太史丞,撰《法象志》。貞觀廿二年(648)任太史令,奉詔註釋《算經十書》。一日,唐太宗得到一本秘讖,上面說:「唐中弱,有女武代王」。李淳風預知武后將稱帝,且改變會造成不能預計的後果(《新唐書‧列傳第一百九十五‧方技》)。
相傳唐太宗寵幸武則天,封她為才人。李淳風提醒太宗,武氏將會亂政,太宗只是半信半疑。李淳風於是預言今科狀元為「火犬二人之傑」,果然是狄仁傑(630-700)高中,太宗只好把武則天放逐為尼。
[原文]《薛剛反唐‧第二回》:「其時司天監李淳風,知唐室有殺戮親王之驚,女主專權帝位,因此密奏太宗……,李淳風知屈殺多人,連忙奏道:陛下勿殺害眾人。臣前日所奏,上達天意,不敢有誤。武氏乃宮中武氏也,望陛下去之。此時太宗正當錦帳歡娛,鴛枕取樂,怎肯將武氏貶殺,便道:卿既能知未來天意,可曉得今科狀元是誰?……臣見天榜名姓,乃火犬二人之傑……至放榜日期,首名狀元姓狄,名仁傑」。
如果此兩事當真,應該不是「察天星、觀雲氣、占候驗」而得知,此應是經由《易經》與星學之推算得來,世傳《推背圖》預知天下事,亦復如是,當然亦有可能由人相、體相上察知,或推算星命得驗,故能前知過去、逆算未來。
《易‧說卦》:「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因為後人不知其推算方法,視為千古神秘,指為迷信、巧合,不足為信。事實上,《易經》與星學是最佳的推測工具,絕對超越察星、觀氣或占候之學。
【天命之學宜修德禳之】
再如他在勸阻唐太宗不要濫殺無辜時說:「天之所命,必無禳避之理」,但《乙巳占》卷三的《修德》篇卻強調對天變要「修德以禳之」。這兩種見解,本質上是相互矛盾的。
不讀《乙巳占》,對李淳風的思想就很難把握。而且《乙巳占》所言,是符合中國星學的基本原理,古星學強調的就是要通過觀測星象,瞭解所謂的「天心」、「天意」,然後「修德以禳之」,讓上天收回對自己不利的成命。
如果沒有這一條,古星學的價值就不存在了。通過《乙巳占》的論述,我們對新舊《唐書》本傳的說法,也有了新的理解。
李淳風是位精通天文學的古星家,因而他對各類天象的描述,與其他人編撰的古星學著作相比,就比較準確。
《乙巳占》中有大量星學術語,對於這些術語,李淳風一般是先給出一個明確的定義,再闡述其對人事的象徵意義。這種做法有利於擺脫傳統星學的模糊和不確定。而古星學一旦不再模糊,就會很容易暴露出其不科學之處。古星學發展得愈具體明確,就愈容易暴露其缺點。
所以李淳風的這種做法有利於科學發展,儘管他並非有意識地要用這種做法暴露古星學的缺點。
對當代人來說,則可透過這些術語的定義,瞭解當時人們的天文學知識。由此《乙巳占》使古星學變得精確化,對於科學發展而言,是有價值的。
【包涵諸多天文知識】
《乙巳占》除了古星學內容之外,還記敘了許多實實在在的天文學知識。例如卷一《天數》篇記述其改進後渾儀的具體結構,就很有價值。儘管新舊《唐書》對李淳風所制渾儀,均有記述,但《乙巳占》的說明係李淳風親手所撰,內容比新舊《唐書》的記載更為詳細,時間上也早得多,這就補充正史之不足。
《乙巳占》有助於我們瞭解古代有關天文學理論的演變。例如關於五星運動與太陽的關係,《舊五代史•曆志》記載了後周王樸的一篇奏議,上面提到:「星之行也,近日而疾,遠日而遲,去日極遠,勢盡而留」。
而《開元占經》卷六十四則引韓公賓注《靈憲》曰:「五星之行,近日則遲,……遠日則速」。這與王樸的奏議正好相反。稍晚于李淳風的僧一行作《大衍曆議》,提到印度天文學關於行星運動速率變化原因的解釋,說「《天竺曆》以《九執》之情,皆有所好惡。遇其所好之星,則趣之行疾,舍之行遲」。
而李淳風在《乙巳占》卷三則給出了另一種說法:「歲星近日則遲,遠日則疾。熒惑近日則疾,遠日則遲。填星之行,自見至留、逆、復順,恒各平行,無有益遲益疾。太白、辰星,晨見,初則遲而後疾,疾則伏;夕見,初則疾而漸遲,遲則伏。此則五星當分遲疾大量也」。
顯然,如果沒有《乙巳占》的這一記載,我們對於古代行星運動速率變化學說多樣性的認識,就要打很大的折扣。
【世界最早將風力分級】
《乙巳占》另一頗值得一提之處是其對風力大小所做的分級。李淳風依據風力對樹木的影響和損壞程度將其分為八級,據《乙巳占》卷十《占風遠近法》的描述,這八級分別為:一級動葉、二級鳴條、三級搖枝、四級墮葉、五級折小枝、六級折大枝、七級折木飛沙石、八級拔樹及根。
李淳風認為不同大小的風其所由來的遠近也不同,風力越大,其所由來的距離越遠。他將風分為八級,就是為了標誌相應的風所由來的遠近,並據此進行占測。他將風的大小與其由來遠近相掛鉤的做法得不到現代科學的支持。
雖然如此,他對風力大小進行定量分級的做法卻是科學的。而且儘管他的著眼點在於占測,但這一分級本身在中國歷史上卻是最早的。
此外,卷十的《候風法》記述了兩種風向儀的製作方法及相應的使用場合,也有很高的科學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