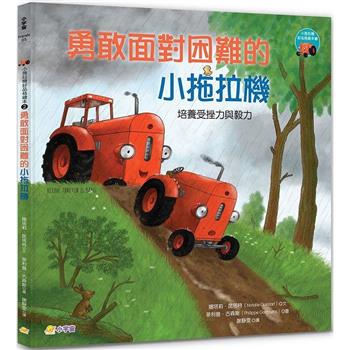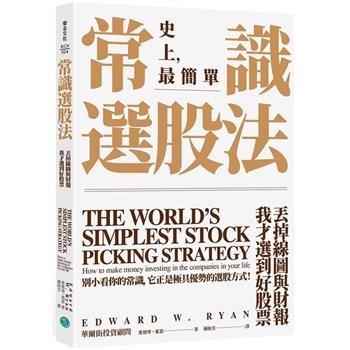文學, 局外人的回憶
梁文道
一
以前母親、祖母、外婆、保姆、傭人講故事給小孩聽,是世界性好傳統。
有的母親講得特別好,把自己放進去。
這段話出自《文學回憶錄》,是陳丹青當年在紐約聽木心講世界文學史的筆記。講世界文學,忽然來這麼一句,未免突兀,不夠學院。木心講課的框架底本,借自上世紀二十年代鄭振鐸編著的《文學大綱》。坦白講,鄭本在縱向時間軸上的分期、橫向以國別涵蓋作家的方法,今天看來已經太落伍了。而在木心的講述裡頭,史實又大幅簡略,反倒是他個人議論既多且廣。興之所至地談下來,重點選擇的作家和作品,多是木心自己的偏愛,全書很難找出一貫而清晰的方法。因此,我們不能把它當成今日學院式的文學史來看。好在,讀者不傻。
木心不是學者,他是個作家,是一個藝術家。以作家身分談文學史,遂有作家的「Artistic Excuse」。同樣的例子,在所多矣。艾略特、米沃什、昆德拉、卡爾維諾、納博科夫⋯⋯有誰真會用專業文學史家的眼光去苛求他們?我們讀這些作家述作的文學史,目的不在認識文學史,而在認識「他的文學史」。就像木心所講的母親說故事,說得好,會把自己說進去一樣,這類文學史述作好看的地方正在於他們自己也在裡頭。
所謂「在裡頭」,別有兩個意思。一個比較顯淺,是他們自己不循慣例、乾綱獨斷的見解。好比昆德拉的小說史觀,不只史學家不一定同意,說不定他頻頻致意的現象學家都不買帳。但那又怎麼樣呢?看他談小說的歷史,我們究竟還是看到了一種饒富深意又極有韻味的觀點。沒錯,這種文學史也是(並且就是)他們的作品。一個稍微講理的讀者絕對不會無理取鬧,從中強求史實的真理;果有真理,那也是 Artistic Truth,一個藝術家自己的真理。
「在裡頭」的第二個意思由此衍生:它是一位作家以自己的雙眼瞻前顧後,左右環視,既見故人,亦知來者,為自己創作生涯與志趣尋求立足於世的基本定向。如此讀解文學史,讀出來的是這位作者之所以如此寫作的由來,是他主動報上家門,是他寫作取向的脈絡,是他暴露「影響之焦慮」的底蘊。更好的時候,他還會藉著他的文學史道出他之所以寫作的終極理由。也就是說,大部分一流作者的文學史,其實都是他們的自我定位。《文學回憶錄》裡的木心便是一個在世界文學史中思索自身位置,進而肯定自身的木心。這就是木心的「文學回憶」,也是《文學回憶錄》中的木心。
二
屈原寫詩,一定知道他已永垂不朽。每個大藝術家生前都公正地衡量過自己。有人熬不住,說出來,如但丁、普希金。有種人不說的,如陶淵明,熬住不說。
具有這等企圖、這等雄心的中國作家,是罕見的,這是木心之所以是木心的原因。耐心的讀者或許就會慢慢明白:木心為什麼和「文壇主流」截然不同。他不但在談文學史的時候是個專業門牆的局外人;就算身為作家,他還是一個局外人。他「局外」到了一個什麼程度呢?剛剛在大陸出版作品的時候,大家以為他是臺灣作家,或是不知從哪兒來的海外作家;更早在臺灣發表作品的時候,那邊的圈子也在探聽是不是一個民國老作家重新出土;他竟然「局外」到了一個沒有人能從他的作品中讀出來處的地步,「局外」到了讓人時空錯亂的地步。
有些讀者感到木心的作品「很中國」,甚至要說它是「老中國」;不過你從今日大陸(所謂的中州正統),一直往回看到「五四」,恐怕也找不到類似的寫作。既然如此,為什麼大家仍然以為木心「很中國」?這裡的「中國」究竟是指哪個「中國」?另一方面,木心的文學實踐又非常西化、非常前衛。早在五十年代,他便在大陸寫過帶有荒謬劇況味的劇本;青年時期,更自習意象主義和超現實主義。於是我只好猜想,三、四十年代,以江浙一帶文脈之豐厚蘊藉,傳統經典既在,復又開放趨新,如無中斷,數十年下來,也許就會自然衍生出木心這樣的作家;但它畢竟是斷了。所以,一個不曾中斷、未經洗劫的木心才會這般令人摸不著頭腦。如今看來,一個本當順理成章走成這般的作家,居然是個局外人。雖說是局外人,但又讓人奇詭地熟悉,仿佛暌違多年的故人。如若強認他是漢語寫作的自己人,繼承了傳統正朔,那便只好勉強說他是「不得禰先君」,遠適異鄉,自成一宗的「別子」了。儘管,我不肯定眼下的主流到底算不算是漢語書寫的嫡傳。
三
《紅樓夢》中的詩,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
《紅樓夢》裡的詩,是多少人解析過的題目,有人據此說曹雪芹詩藝平平,也有人說他詩才八斗。而木心這句斷語,也並非沒人講過,只是說不到這麼漂亮,這麼叫人服氣;「水草」,何等的譬喻,就這一句,便顯見識,便能穿透,正是所謂的「斷言」,無須論證,不求贊同,然而背後的識見,全出於其高超的「aesthetic quality」,令人欣賞,乃至嘆服。
這就是木心,也只有木心,才會大膽說出這樣透闢的句子。他的作品,好讀難懂,難懂易記,因為風格印記太過強烈了,每一句說,自有一股木心的標識,引人一字一字地讀下去,銘入腦海,有時立即記住了某一句,回頭細想,其實還沒懂得確切的意思:於是可堪咀嚼,可堪回味。
與《紅樓夢》中的詩不同,木心的斷語,取出水面,便即「兀自燃燒」起來。這一評價,本是劉紹銘教授形容張愛玲的名言。在我看來,現代中國文學史,木心是一位「金句」紛披的大家。但他的「火焰」,清涼溫潤,卻又凌厲峻拔,特別值得留意的是,他的一句句識見,有如冰山,陽光下的一角已經閃亮刺眼,未經道出的深意,深不可測。
四
本書的題目,叫做《文學回憶錄》,書裡的講述全部出自木心,然而這是陳丹青五年聽課的筆錄。很自然的,讀者會猜測,甚至追究:筆錄中的木心到底有多真實?又有多少帶著筆錄者的痕跡?不尋常的是,木心當初備有完整的講義,但他不以為用來講課的底本可以作為他的創作,因此,他在生前不贊成出版講義。自重自愛如木心,後人應當尊重他的意願。饒是如此,陳丹青出版筆記的用心,便如他所說,乃出於木心葬禮上眾多年輕讀者的懇求了。
但我們仍然面對著微妙的困境:木心不把講義視為他的文學作品,那麼,眼前這本《回憶錄》,還是他的書嗎?
熟悉歷史和文學史的讀者,應該明白,這個問題,是個「述」與「作」的問題,這個問題又古老,又經典。佛陀、孔子、蘇格拉底、耶穌,全都述而不作。他們的言論與教化全部出自後人門生的記錄。今人可以合理地追問:佛經裡的「如是我聞」,到底有多「如是」?「子曰」之後的句子,又是否真是孔子的原話?其中最著名的公案,當屬柏拉圖與蘇格拉底的關係。當年至少有十個跟隨蘇格拉底的學生記有「聽課筆錄」,唯獨柏拉圖《對話錄》影響最大,是今人瞭解蘇格拉底的權威來源。
好在木心既述又作,既作且述,生前便已出版全部創作。其風調思路,無須轉借陳丹青筆錄才能一窺全貌。這本《文學回憶錄》,無論敘述的語氣,還是遍佈全書的斷語、警句、妙談,坦白說,不可能出自木心之外的任何人。
在這部大書的前面,說了這些話,難免有看低讀者之嫌──木心從不看低讀者。倒是我所遇見的不少木心讀者,將自己看得太低。我至今遺憾沒有親見木心的機會,而他們崇敬木心,專門前去烏鎮探他,到了,竟又不敢趨前問候。想來他們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了。要不,便是自我太大。遇到高人,遂開始在乎起自己如何表現,如何水平,生怕人家瞧不上自己。
你看木心《文學回憶錄》,斬釘截鐵,不解釋、不道歉、不猶疑。他平視世界文學史上的巨擘大師,平視一切現在的與未來的讀者,於是自在自由,娓娓道出他的文學的回憶。
後記
陳丹青
二十三年前,一九八九年元月,木心先生在紐約為我們開講世界文學史。初起的設想,一年講完,結果整整講了五年。後期某課,木心笑說:這是一場「 文學的遠征」。
十八年前,一九九四年元月九日,木心講畢最後一課。那天是在我的寓所,散課後,他穿上黑大衣,戴上黑禮帽,我們送他下樓。步出客廳的一瞬,他回過頭來,定睛看了看十幾分鐘前據案講課的橡木桌。此後,直到木心逝世,他再沒出席過一次演講。
那桌子跟我回了北京,此刻我就在桌面上寫這篇後記。
另有一塊小黑板,專供木心課間書寫各國作家的名姓、生卒年、生僻字,還有各國的詩文,隨寫隨擦,五年間輾轉不同的聽課人家中。今年夏初,我照例回紐約侍奉母親,七月,母親逝世。喪事過後的一天,清理母親床邊的衣櫃──但凡至親亡故而面對滿目遺物的人,明白那是怎樣的心情──在昏暗壁角,我意外看見了那塊小小的黑板。
聽課五年,我所累積的筆記共有五本,多年來隨我幾度遷居,藏在不同寓所的書櫃裡,偶或看見,心想總要靜下心再讀一遍,倏忽近二十年過去了,竟從未複讀。唯一讀見的老友,是阿城,一九九一年,我曾借他當時寫就的三本筆錄。
木心開講後,則每次攤一冊大號筆記本,密密麻麻寫滿字,是他備課的講義。但我不記得他低頭頻頻看講義,只目灼灼看著眾人,徐緩地講,忽而笑了,說出滑稽的話來。當初宣布開課,他興匆匆地說,講義、筆記,將來都要出版。但我深知他哈姆雷特式的性格:日後幾次懇求他出版這份講義,他總輕蔑地說,那不是他的作品,不高興出。前幾年領了出版社主編去到烏鎮,重提此事,木心仍是不允。
先生的意思,我不違逆。但我確信我這份筆記自有價值:除了講課內容,木心率爾離題的大量妙語、趣談,我都忠實記錄:百分之百的精確,不敢保證,但只要木心在講話,我就記,有一回甚至記下了散課後眾人跟他在公園散步的談話。
去年歲闌,逾百位年輕讀者從各地趕來,永別木心。在烏鎮昭明書院的追思會上,大家懇請我公開這份筆錄,我當即應承了──當年講課時,木心常說將來怎樣,回國後又怎樣,那天瞧著滿屋子陌生青年的臉,戚戚然而眼巴巴,我忽然想:此刻不就是先生時時矚望的將來嗎?
今年春,諸事忙過,我從櫃子裡取出五本筆記,摞在床頭邊,深宵臨睡,一頁一頁讀下去,發呆、出神、失聲大笑,自己哭起來:我看見死去的木心躺在靈床上,又分明看見二十多年前大家圍著木心,聽他講課⋯⋯我們真有過漫漫五年的紐約聚會麼?瞧著滿紙木心講的話,是我的筆記,也像是他的遺物。
電子版錄入的工作,細緻而龐大。速記潦草,年輕編輯無法辨讀,我就自己做。或在紐約寓所的廚房,或在北京東城的畫室,朝夕錄入,為期逾半年。當年手記無法測知字數,待錄畢八十五講,點擊核查,逾四十萬字。為紀念木心逝世一周年,近日忙於編校、排版、配圖、弄封面,十二月必須進廠付印了:眼前的電子版不再是那疊經年封存的筆記,而是木心讀者期待的書稿──「九泉之下」這類話,我從不相信的,而人的自欺,不過如此。喂,木心,恕我不能經你過目而首肯了,記得你當年的長篇大論嗎?年底將要變成厚厚的書。
*
現在可以交代這場「文學遠征」的緣起和過程了。
一九八二年秋,我在紐約認識了木心,第二年即與他密集過往,劇談痛聊:文學課裡的許多意思,他那時就頻頻說起。我原本無學,直聽得不知如何是好。我不願獨享著這份奇緣,未久,便陸續帶著我所認識的藝術家,走去見木心──八十年代,紐約地面的大陸同行極有限,各人的茫然寂寞,自不待說──當然,很快,眾皆驚異,不知如何是好了。
自一九八三到一九八九年,也是木心恢復寫作、持續出書的時期。大家與他相熟後,手裡都有木心的書。逢年過節,或借個什麼由頭,我們通宵達旦聽他聊,或三五人,或七八人,窗外晨光熹微,座中有昏沉睡去的,有勉力強撐的,唯年事最高的木心,精神矍鑠。
木心在大陸時,與體制內晚生幾無來往,稍事交接後,他曾驚訝地說:「原來你們什麼都不知道啊!」這樣子,過了幾年,終於有章學林、李全武二位,糾纏木心,請他正式開課講文藝,勿使珍貴的識見虛擲了。此外,眾人另有心意:那些年木心尚未售畫,生活全賴稿費,大家是想借了聽課而交付若干費用,或使老人約略多點收益。「這樣子算什麼呢?」木心在電話裡對我說,但他終於同意,並認真準備起來。
勸請最力而全程操辦的熱心人,是李全武。他和木心長期協調講課事項,轉達師生間的種種信息,改期、復課、每課轉往誰家,悉數由他逐一通知,持續聽課或臨時聽課者的交費,也是他負責收取,轉至木心,五年間,我們都稱他「校長」。
事情的詳細,不很記得了。總之,一九八九年元月十五日,眾人假四川畫家高小華家聚會,算是課程的啟動。那天滿室譁然,很久才靜下來。木心,淺色西裝,笑盈盈坐在靠牆的沙發,那年他六十二歲,鬢髮尚未斑白,顯得很年輕──講課的方式商定如下:地點,每位聽課人輪流提供自家客廳;時間,寒暑期各人忙,春秋上課;課時,每次講四小時,每課間隔兩週,若因事告假者達三五人,即延後、改期,一二人缺席,照常上課。
開課後,漸漸發現或一專題,一下午講不完。單是《聖經》就去兩個月,共講四課。上古中古文學史講畢,已逾一年,愈近現代,則內容愈多。原計畫講到十九世紀收束,應我們叫喚,木心遂添講二十世紀流派紛繁的文學,其中,僅存在主義便講了五課。
那些年,眾生多少是在異國謀飯的生熟尷尬中,不免分身於雜事,課程改期,不在少數,既經延宕,則跨寒暑而就春秋,忽忽經年,此即「文學遠征」至於跋涉五年之久的緣故吧。到了最後一兩年,這奇怪的小團體已然彼此混得太熟,每次相聚有如小小的派對,不免多了課外的閒聊,我的所記,則仍是木心的講課。
*
以下追蹤記憶,由年齡順序排列,大致是全程到課、長期聽課的學員名單:
金高(油畫家)、王濟達(雕塑家),五十年代中央美院畢業,一九八三年來美。
章學林(版畫家),六十年代浙江美院畢業,一九八○年來美。
薄茵萍、丁雅容,來自臺灣的女畫家,一九七七年來美。
陳丹青、黃素寧(國畫家),一九八○年中央美院畢業,一九八二年來美。
曹立偉(油畫家)、李菁,一九八二年中央美院畢業,一九八六年來美。
李全武(油畫家),一九八四年中央美院畢業,一九八五年來美。
殷梅(舞者、編舞家),來美年份不詳。
黃秋虹,廣東女畫家,一九八○年來美。
陳捷明,廣東畫家,一九八○年來美。
李和,不詳。
其中,殷梅由全武介紹而來,黃秋虹、陳捷明,由別人介紹木心認識。五年間,因呼朋喚友而聽過幾課、不復再來,或中後期聽說而加入的人,也頗不少。我所熟悉的是上海畫家李斌,南京畫家劉丹、錢大經、薛建新,北京人薛蠻子、胡小平夫婦。兩位木心的舊識:上海畫家夏葆元(「文革」前與木心同一單位)、上海留學生胡澄華(其父是木心的老友),也來聽過課,久暫不一。人數最多的一次是講唐詩,也在我的寓所,來三十多人,椅子不夠,不記得終於是怎樣安排落座的。
這是一份奇怪的組合:聽課人幾乎全是畫家,沒有跡象表明有誰聽過文學史,或職志於文學,課中說及的各國作家與作品,十之六七,我們都不知道──木心完全不在乎這些。他與人初識接談,從不問起學歷和身分。奇怪,對著這些不相干的臉,他只顧興味油然地講,其狀貌,活像談論什麼好吃透頂的菜肴。我猜他不會天真到以為眾生的程度與之相當,但他似乎相信每個人果然像他一樣,摯愛文學。
木心講課沒有腔調──不像是講課,渾如聊天,而他的聊天,清晰平正,有如講課──他語速平緩,從不高聲說話,說及要緊的意思,字字用了略微加重的語氣,如宣讀早經寫就的文句。錄入筆記的這半年,本能地,我在紙頁間聽到他低啞蒼老的嗓音。不止十次,我記得,他在某句話戛然停頓,凝著老人的表情,好幾秒鐘,呆呆看著我們。
這時,我知道,他動了感情,竭力克制著,等自己平息。
講課與聊天究竟不同。自上世紀五十年代木心在上海高橋做過幾年中學老師,此後數十年再沒教過書──起初幾堂課,談希臘羅馬、談《詩經》,他可能有點生疏而過於鄭重了,時或在讀解故事或長句中結巴、絆住,後來他說,頭幾課講完,透不過氣來──兩三課後,他恢復了平素聊天的閒適而鬆動,愈講到後來,愈是收放自如。
我的筆記,初起也頗倉促,總要三四課後這才找回畫速寫的快捷,同其時,與木心的講述,兩皆順暢了──好在木心說話向來要言不煩,再大的公案、史說、是非、糾葛,由他說來,三言兩語,驚人地簡單。
而筆錄之際最令我感到興味的瞬間,是他臨場的戲談。
木心的異能,即在隨時離題:他說卡夫卡苦命、肺癆、愛焚稿,該把林黛玉介紹給卡夫卡;他說西蒙種葡萄養寫作,昔年陶潛要是不就菊花而改種葡萄,那該多好!在木心那裡,切題、切題、再切題,便是這些如敘家常的離題話。待我們聞聲哄笑,他得意了,假裝無所謂的樣子──且慢,他在哄笑中又起念頭,果然,再來一句,又來一句──隨即收回目光,接著往下說。
如今座談流行的錄音、攝像,那時既沒有器具,木心也不讓做。他以為講課便是講課。五年期間,我們沒有一張課堂的照片,也無法留存一份錄音。
「結業」派對,是「李校長」安排在女鋼琴家孫韻寓所。應木心所囑,我們穿了正裝,分別與他合影。孫韻母女聯袂彈奏了莫札特第二十三號鋼琴協奏曲。阿城特意從洛杉磯自費趕來,扛了專業的機器,全程錄像。席間,眾人先後感言,說些什麼,此刻全忘了,只記得黃秋虹才剛開口,淚流滿面。
木心,如五年前宣布開課時那樣,矜矜淺笑,像個遠房老親戚,安靜地坐著,那年他六十七歲了。就我所知,那也是他與全體聽課生最後一次聚會。他的發言的開頭,引梵樂希的詩。每當他借述西人的文句,我總覺得是他自己所寫,脫口而出:
你終於閃耀著了麼?我旅途的終點。
*
八、九十年代之交,國中大學的文學史課程,早經恢復。文學專業的碩博士,不知用的什麼講義,怎樣地講,由誰講──我們當年這樣地胡鬧一場,回想起來,近於荒謬的境界:沒有註冊,沒有教室,沒有課本,沒有考試與證書,更沒有贊助與課題費,不過是在紐約市皇后區、曼哈頓區、布魯克林區的不同寓所中,團團坐攏來,聽木心神聊。
木心也從未修過文學課。講畢唐詩一節,他送當時在座每位學員一首七絕,將各人的名字嵌入末句,這次錄入,我注意到他也給自己寫了一首:
東來紫氣已遲遲,群公有師我無師。
一夕絳帳風飄去,木鐸含心終不知。
木心所參考的鄭振鐸《文學大綱》,最早出版於上世紀二十年代,想必是少年木心的啟蒙讀物之一。前年得到這兩冊大書的新版,全書體例與部分資料,大致為木心所借取,我翻了幾頁,讀不下去。「可憐啊,你們讀書太少。」暮年木心又一次喃喃對我說。那時他已耳背,我大叫:「都聽你講過了呀!」 他一愣,怔怔地看我。
聽課五年,固然免除了我的蒙昧,但我從此愚妄而惰怠。說來造孽:木心所標舉的偉大作品:古希臘,《聖經》,先秦諸子,莎士比亞,尼采,拜倫,紀德⋯⋯二十多年過去,我一行也不曾拜讀。年來字字錄入這份筆記,我不再將之看做「世界文學史」,誠如木心所說,這是他自己的「文學回憶錄」,是一部「荒誕小說」。眼下全書付印在即,想了很久,以我難以挽回的荒率,無能給予評價。實在說,這是我能評價的書嗎?
如今我也接近木心開課時的歲數,當年愚昧,尚於講課中的若干信息,惘然不察,現在或可寫出來,就教於方家,也提醒年輕的讀者──
上世紀三十年代末,抗戰初期,十三、四歲的木心躲在烏鎮,幾乎讀遍當時所能到手的書,其中,不但有希臘羅馬的史詩、神話,近代以來的歐陸經典,還包括印度、波斯、阿拉伯、日本的文學。鄭本《文學大綱》所列舉的龐大作者群,當年不可能全有漢譯本,木心也不可能全都讀過,他誠實地說,哪位只是聽說,哪本沒有讀過,但他多次感慨:「那時的翻譯家做了好多事情哩。」最近承深圳的南兆旭、高小龍二位提供數百冊私藏民國舊書,供我選擇配圖,雖難測知其中哪些曾是木心昔年的讀本,但他的閱讀記憶,正是一部民國出版史的私人旁證。
講述《聖經》時,木心念及早歲與他頻繁通信的十五歲湖州女孩,使我們知道早在四十年代的浙江小城,竟有如此真摯而程度甚深的少年信徒,小小年紀,彼此辯說新舊約的文學性。提到《易經》,他說夏夜乘涼時教他背誦《易經》口訣的人,是她母親,抗戰逃難中,這位母親還曾給兒子講述杜甫的詩,這在今日的鄉鎮,豈可思議。他憶及家中僕傭對《七俠五義》之類的熱中,尤令我神旺,他的叔兄長輩居然日日去聽說書,此也勾連了我的幼年記憶:五、六十年代,滬上弄堂間尚且隱著簡陋的說書場所⋯⋯這一切,今已蕩然無存,而木心的記憶,正是一份民國青年的閱讀史。
這份閱讀史,在世界範圍也翻了過去。木心的生與長,適在同期步入印刷時代與新文化運動的民國,他這代人對文學的熱忱與虔敬,相當十五至十九世紀的歐洲人,電子傳媒時代的芸芸晚生,恐怕不易理解這樣一種文學閱讀的赤子之情了。
以上,是木心生涯的上半時,下半時呢?
自一九四九年到「文革」結束,近三十年,歐美文學的譯介幾乎中止,其間,值木心盛年,惟以早歲的閱讀與文學相濡以沫(他因此對五十年代專事俄羅斯文學的推介,甚表好意)。講課中一再提及的音樂家李夢熊先生,也是此等活寶:他倆聽說喬伊斯與卡夫卡,但「文革」前夕的大陸,哪裡讀得到。而早在三、四十年代,他們就知悉歐洲出現意識流、意象主義、存在主義等等新潮,之後,對鐵幕外的文學景觀該是怎樣的渴念。浩劫後期,戰後文學如「黑色幽默」與「垮掉的一代」,曾有內部譯本(如《第二十二條軍規》),他們當然不會放過,總之,就我所知,五、六十年代,各都市,尤其京滬,尚有完全在學院與作協系統之外,嗜書如命、精賞文學的書生。而木心出國前大量私下寫作的自我想像、自我期許,竟是遙不可及的西方現代主義。
「文革」初,木心早期作品被抄沒。「文革」後,大陸的地下文學與先鋒詩,陸續見光,漸漸組入共和國文學史話。現在,這本書揭示了更為隱蔽的角落:整整六十多年目所能及的文學檔案中──不論官方還是在野──仍有逍遙漏網的人。
漫長,徹底,與世隔絕,大陸時期的木心沒有任何舉動試圖見光。到紐約後,帶著不知饜足的文學的貪婪,他在恢復寫作的同時,靠臺灣版譯本找回被阻隔的現代文學圖景,與他早年的閱讀相銜接。久居紐約的港臺文人對他與世界文學的不隔,咸表驚異,他們無法想像木心與李夢熊在封鎖年代的文學苦談──「出來了,我才真正成熟」,木心如是說──私下,我完全不是可以和他對話的人,他幾次歎息,說,你們的學問談吐哪裡及得上當年李夢熊。但木心要說話,要以他所能把握的文學世界,印證自己的成熟,不得已,乃將我們這群人權且當做可以聆聽的學生。
多少民國書籍與讀者,湮滅了。木心的一生,密集伴隨愈演愈烈的文化斷層。他不肯斷,而居然不曾斷,這就是本書潛藏的背景:在累累斷層之間、之外、之後,木心始終將自己盡可能置於世界性的文學景觀,倘若不是出走,這頑強而持久的掙扎,幾幾乎瀕於徒勞。
*
一個在八十年代出道的文學家,能否設想木心的歷程?一個研修文史專科的學者,又會如何看待這份文本?木心不肯放過文學,劫難也不曾放過他,但我不知道他怎樣實踐了尼采的那句話:
在自己的身上,克服這個時代。
固然,尼采另有所指,尼采也不可能知道這句話在二十世紀的中國語境──在這大語境中,木心怎樣營造並守護他個人的語境?去年秋,木心昏迷的前兩個月,貝聿銘的弟子去到烏鎮,與他商議如何設計他的美術館。木心笑說:
貝先生一生的各個階段,都是對的;我一生的各個階段,全是錯的。
這不是反諷,而是實話,因為實話,有甚於反諷──講課中,他說及這樣的細節:五十年代末,國慶十周年夜,他躲在家偷學意識流寫作(時年三十二歲);六十年代「文革」前夕,他與李夢熊徹夜談論葉慈、艾略特、史賓格勒、普魯斯特、阿赫瑪托娃;七十年代他被單獨囚禁時,偷偷書寫文學手稿,我親眼看過,驚怵不已:正反面全都寫滿,字跡小如米粒;八十年代末,木心年逾花甲,生存焦慮遠甚於流落異國的壯年人,可他講了五年文學課──我們交付的那點可憐的學費啊──九十年代,他承諾了自己青年時代的妄想,滿心狂喜,寫成《詩經演》(編按:即《會吾中》,一九九八年五月版。後改稱《詩經演》。)三百多首;新世紀,每回走去看他,他總引我到小陽臺桌邊,給我看那些毫無用處的新寫的詩。
在與筆記再度相處的半年,我時時湧起當初即曾抱有的羞慚和驚異,不,不只於此,是一種令我畏懼到至於輕微厭煩的心情:這個死不悔改的人。他摯愛文學到了罪孽的地步,一如他罪孽般與世隔絕。這本書,佈滿他始終不渝的名姓,而他如數家珍的文學聖家族,完全不知道怎樣持久地影響了這個人。
中國文學史、西洋文學史,魏晉或唐宋文學、伊麗莎白或路易王朝文學,各有專家。其他國家所修的世界文學史又是怎樣講法呢?當年鄭振鐸編撰《文學大綱》,想必也多所參照了外國的寫本。迄今,我沒有讀過一本文學史,除了聽木心閒聊。若非年輕讀者的懇求,這五冊筆記不知幾時才會翻出來;其實,每次瞧見這疊本子,我都會想:總有一天,我要讓許多人讀到。
或曰:這份筆記是否準確記錄了木心的講說?悉聽尊便。或曰:木心的史說是否有錯?我願高聲說:我不知道,我不在乎!或曰:木心的觀點是否獨斷而狂妄?嗚呼!這就是我保有這份筆錄的無上驕傲──我分明看著他說,他愛先秦典籍,只為諸子的文學才華;他以為今日所有偽君子身上,仍然活著孔丘;他想對他愛敬的尼采說:從哲學跑出來吧;他激賞拜倫、雪萊、海涅,卻說他們其實不太會作詩;他說托爾斯泰可惜「頭腦不行」,但講到托翁墳頭不設十字架,不設墓碑,忽而語音低弱了,顫聲說:「偉大!」而談及沙特的葬禮,木心臉色一正,引尼采的話:唯有戲子才能喚起群眾巨大的興奮。
我真想知道,有誰,這樣地,評說文學家。我因此很想知道,其他國家,誰曾如此這般,講過文學史──我多麼盼望各國文學家都來聽聽木心如何說起他們。他們不知道,這個人,不斷不斷與他們對話、商量、發出詰問、處處辯難,又一再一再,讚美他們,以一個中國老人的狡黠而體恤,洞悉他們的隱衷,或者,說他們的壞話。真的,這本書,不是世界文學史,而是,那麼多那麼多文學家,漸次圍攏,照亮了那個照亮他們的人。
*
講課完結後,一九九四年早春,木心回到遠別十二年的大陸,前後四十天,期間,獨自潛回烏鎮,那年他離開故鄉將近五十年了。回紐約後,又兩年,他搬離距我家較近的寓所,由黃秋虹安排遷往皇后區一處寬敞的公寓,在那裡住了十年。到了七十九歲那年,二○○六年九月,我陪他回國,扶他坐上機場的輪椅,走向海關。黃秋虹,泣不成聲,和年逾花甲的章學林跟在後面:自我二○○○年回國後,就剩他倆就近照看木心。
同年春,聽課生中年齡最大的金高女士,逝世了。其他學員早經星散,很少聯絡了。之後,每年春秋我回紐約侍母,走在街上,念及木心經已歸國。去年木心死,我瞧著當年眾人出沒的街區,心情有異──今夏侍奉母親,黃昏散步,我曾幾次走到木心舊寓前,站一站。門前的那棵樹,今已亭亭如蓋,通往門首的小階梯磚垛,放滿陌生租客的盆栽。這寓所的完整地址是:
25-24A, 82 Street Jackson Heights, NY 11372.
(中譯:紐約市,傑克遜高地,八十二街,郵編一一三七二)
木心講課時,還給眾生留下這裡的電話:七一八─五二六─一三五七。
如今不能上前叩門了。木心在時,書桌周圍滿是花草,臥室的小小書櫃旁豎一枚樂譜架,架上攤著舊版的蘇東坡字帖──在我見過的文人中,木心存書最少最少──自一九九○到一九九六年,文學課講義、蓄謀已久的《詩經演》,都在這裡寫成。凡添寫幾首詩經體新作,他會約我去北方大道南側一張長椅上見面,攤開我根本看不懂的詩稿,風寒街闊,喜孜孜問我:味道如何?
講課中,他兩次提到與他相熟的街頭松鼠,還有寓所北牆密匝匝的爬牆虎:「它們沒有眼睛哎!爬過去,爬過去!」每與我說起,木心嘖嘖稱奇。忽一日,房主未經告知,全部拔去了,他如臨大事,走來找我,狠狠瞪大眼睛:
「那是強暴啊!丹青,我當天就想搬走!」
木心絕少訴說自己的生活。五年講課間,難得地,他說出早歲直到晚年的零星經歷,包括押送與囚禁的片刻。他說,和朋友講課,可以說說「私房話」。本書編排時,我特意在每講之前排幾行摘錄,並非意在所謂「關鍵詞」,而多取木心談及自己的略略數語,俾使讀者走近他(編按:繁體版的摘錄另擇引述):經已出版的木心著作,刻意隱退作者,我相信,這本書呈現了另一個木心。
有次上課,大家等著木心,太陽好極了。他進門就說,一路走來,覺得什麼都可原諒,但不知原諒什麼。那天回家後,他寫成下面這首「原諒」詩,題曰〈杰克遜高地〉:
五月將盡
連日強光普照
一路一路樹蔭
呆滯到傍晚
紅胸鳥在電線上囀鳴
天色舒齊地暗下來
那是慢慢地,很慢
綠葉藂間的白屋
夕陽射亮玻璃
草坪濕透,還在灑
藍紫鳶尾花一味夢幻
都相約暗下,暗下
清晰 和藹 委婉
不知原諒什麼
誠覺世事盡可原諒
選這首詩,因為木心、金高、全武、立偉、我,均曾是杰克遜高地的居民,當年輾轉各家的上課地點,多半散在那片區域:二十年前,木心這樣地走著,看著,「一路一路樹蔭」,其時正在前來講課的途中;下課了,他走回家,「天色舒齊地暗下來」。木心的所有詩文,隻字不提這件事,紐約市、杰克遜高地,也從不知道一小群中國人曾在這裡聽講世界文學課。如今木心死了,母親死了,金高死了,此後我不會每年去到那裡──「不知原諒什麼,誠覺世事盡可原諒」。現在,惟願先生原諒我擅自公開了聽課筆記,做成這本大書。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日寫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