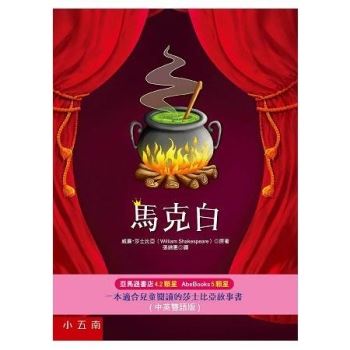溯流而上,直抵生命之源、黑暗之心,一探人間邊界。
沿著河走,走向堤外。長期關注城市日常、庶民百態的房慧真,緩步探抵澤岸水畔的邊界,繁華與喧囂未達的角落:橋下、沙洲、浮島、河邊聚落、邊城舊區、化外無主之地,她冷靜而澄澈的筆,引領觀者直視,那些似被遺忘,卻從未停止運行的街厝店攤,大河盡頭廢汙擱淺的浮島,挨著電梯大廈的簡陋木板小屋,傍水而居的部落,高架橋下臨時拼湊的計程車營地,傳統委託行透著塵光的玻璃櫥窗,老舊國宅的鏽蝕水管與蔓延壁癌,無人光顧的冷攤……。
漂流,至路的盡頭,看見城市的流浪者之歌。
作者簡介:
房慧真
另一個名字是「運詩人」,生於台北,長於城南,養貓之輩,恬淡之人。碩士論文寫陰陽五行,台大中文系博士班肄業,目前任職於平面媒體,撰寫人物專訪。著有散文集《單向街》、《小塵埃》。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一種溫柔的凝視,在近乎絕望的世界裡辨析出底層的人相濡以沫的情感、活著的理由。——黃錦樹
河流與人間
黃錦樹
房慧真的散文,從她的第一本集子《單向街》(遠流,二○○七)就幾已確定了方向:關於身世,自童年以來的種種經歷,父親母親—這是抒情散文的﹁傳統領域﹂;對寫作者而言必須藉文字來清理,自我省視。文字的簡勁讓她的文章沒有多餘的水分。但在房慧真的世界裡,總是挺立著一個巨大陰影般的父親,及苦刑般的熱帶之旅。再則是成年以後她對處身的世界的微物觀察。與及,旅行所見。
《小塵埃》(木馬,二○一三)亦復如此。當細心的讀者發現〈小塵埃〉一文其實出於《單向街》時,可能會發現這兩本書其實是一本展開中的大書的兩個局部—它們相互補充著開展,隨著作者的生命旅程與寫作活動,自己的河流。
散文預設的自我同一性(敘事者我沒有權力更換身世、更換父母)讓她的寫作一定程度的必然被規範在特定的方向,這不止凸顯了散文寫作本身的困難度,也凸顯了需要寫作的生活本身的困難。
假如恪守散文的界限,不藉由虛構想像來做敘事的飛躍,寫作者勢必要克服經驗的侷限。或許我們可以觀察一下這本《河流》相較於前者,到底有怎樣的開展。
那個在前兩本書裡還是敘述者恐懼的核心的,來自印尼加里曼丹的父親,終於消散至只剩下他的故鄉婆羅洲本身(〈黑暗之心〉);童年經驗裡的傷害,也滌盡剩下童年的世界本身((汀州)、〈劍潭幻影〉),文章轉而藉由知識性開展那世界本身的歷史厚度或精神意義。但也許僅僅是把那些傷害暫時隱藏起來,來日再慢慢重新處理。
於是《河流》裡清晰的凸顯了兩個世界,一是廢墟一般的底層台北,一是台灣之外的世界—旅行所見:印尼、印度、中國,但作者的觀照點還是相似的,若不是底層的人,就是人間卑瑣的微物,世間的幽黯角落,某個瞬間。後者有賴於旅行,也是散文寫作者最常用以克服題材侷限的方式。以她受過攝影機訓練的眼睛,映現細節,兩個世界之間終歸會是互喻的關聯著。
底層的觀察,在近年的台灣文壇就比較少見了,那需要有顆柔軟的心,也需要一雙勤快的腳。有的文章近乎人類學式的鉅細靡遺的描繪—且在﹁賦比興﹂這三種手法中偏向於賦,敘述沿著對象空間的不同方位展開。如極具代表性的〈大河盡頭〉寫基隆河、新店溪沖積扇上﹁多中南部移民﹂的社子島,都會底層世界的縮影,那與垃圾、汙染、被大水沖走的無根的、卑渺的存在。〈大橋下〉、〈水上人家〉、〈河岸生活〉、〈大河之歌〉都是〈大河盡頭〉人類學視野的延伸。那是人類最古老的生活場域之一,幾乎可以說是極其接近生物本能的選擇。是「逐水而居、傍水而生,最低限度的生活﹂,不論是在台灣,還是其他任何有河的地方,底層的人的掙扎總是相似的。
賦體又如〈夜市,人生〉,這是全書最長的一篇,細寫夜市這一獨特的世界,各色的攤販及遊客,衣食住行與奇淫巧技。在她筆下,那是一處溫暖明亮的所在,帶著若干奇幻的色彩。如其言:﹁夜市是夜不拔營的馬戲團,夜夜上演著都市傳奇。﹂〈流浪藝人〉、〈江湖在哪裡〉可說是這〈夜市,人生〉的延伸,猶如〈彼岸〉是它的變奏。
但有的篇章則如廢墟考古一般的,如〈邊城〉中敘述者進入歸綏街一帶性產業遺址,那周邊衰疲的市井民生;彷彿看到一種啟示:「再找不出任何一個地方若此,彷彿人生的縮影公園,不出幾條街廓,便可將生、老、病、死一網打盡」,也﹁一網打盡﹂各種原料、各種行業、各種沒落,無言的喘息著。那是個廢墟般的世界,昔日繁華遠去,惟餘憑弔而已。
又或重心也許並不盡然在於那些景象,而是一種溫柔的凝視,在近乎絕望的世界裡辨析出底層的人相濡以沫的情感、活著的理由。如〈浮島森林〉裡萬華﹁蝴蝶蘭大旅舍﹂墜落人間底層的眾妓的﹁守望相助﹂的情感,敘事者溫柔的理解她們的處境。或如〈彼岸〉,在熱鬧的夜市攤販的巷弄裡,尋找不尋常的一隅,﹁一家隱蔽於深巷的精神病院」。這種獨特的觀察角度,讓她會特別去關心各種生意冷清的攤子,為箇中生態寫出觀察報告(〈冷攤〉),也找到一種不尋常的認同感(﹁寒夜裡的冷攤,實是心底一道炙燙妥貼的熱風景。﹂)這也標出了敘述者的位置—她身在其中,並不是局外人。
這樣的寫作取徑,彷彿要一探人間的邊界似的。
作為散文寫作者,房慧真的優勢除了對底層角隅異於同代人的熱情關切、文字的精準刻繪之外,就是她的博覽雜書,與及對電影的熱愛熟稔。這讓她的寫作,常常可以縱向橫向的調動不同文學作品、影像裡的關聯場景或細節、情節,以對所見所歷做比較印證。這一特色在之前的兩本書也有充分展現。
《河流》裡諸如〈流浪藝人〉、〈江湖在哪裡〉、〈水上人家〉、〈劍潭幻影〉、〈黑暗之心〉、〈看不見的城市〉等都有盡致的展現。大抵可以分為兩種型態,一是從個人經驗出發,互文似的延伸開去(〈水上人家〉、〈劍潭幻影〉、〈黑暗之心〉);一是純粹知識性的引文牽連(如〈流浪藝人〉、〈江湖在哪裡〉)。
它的長處是可以增加個人體驗的文本的厚度,縱橫印證,而帶有學術筆記的趣味。但如果個人經驗占的篇幅很小,彷彿就是純粹的筆記叢談了。
在這樣的寫作中,父親不在場的婆羅洲之旅應該有其獨特的位置。〈黑暗之心〉的婆羅洲溯河之旅,已是父逝後女兒的尋根。敘事者調動非洲、南美洲那兩塊飽受殖民蹂躪的大陸來對應婆羅洲;調動剛果河、亞馬遜河來對比卡布雅斯河。在這樣的對照裡,婆羅洲其實是世界史裡相對被忽略的小老弟。在這父亡後的熱帶原鄉,除了眾所周知的奇花異果、怪獸詭禽之外,借來做對比的洲與河讓她可以較自由的調動系列鏡映交錯的文本,以幫助她理解那陌生地,就像邀請熟人伸以援手。《黑暗之心》。《陸上行舟》。《天譴》。《奧邁耶的癡夢》。《一掬泥土》。而結以《大河盡頭》。家族史裡的錯亂倫常,狂悖的生殖意志,被代以尋根女兒的﹁經血反哺﹂,那象徵生殖已然失敗的血,「溯流而上,直抵生命之源、黑暗之心。﹂
這裡最直接的關聯文本當然是李永平兩大卷的近著《大河盡頭》。
身為婆羅洲人的女兒,在寫作的精神淵源上,李永平理應是那父親(如果女兒寫作……)。她那一心想返鄉且費盡心力為女兒辦了印尼護照,絲毫不認同中華民國,對中文甚至頗為憎惡的,絕對認同那不斷排華的印尼的土生華人(peranakan)父親,晚年因執意返鄉而徹底失去自己。對比於那因為對大馬政府打從心底的畏懼而三十年不敢返鄉,對中文和中國有著狂熱的愛的新客的兒子李永平,認同上的對照像斑馬的黑白線條那麼分明。他們同樣來自婆羅洲,但那土地因殖民分割及後續的效應而分屬兩個國家。出生於民國台灣的房慧真,以中文寫作,她的婆羅洲之旅將是李永平人生旅程的顛倒,以未來式的時態。
《大河盡頭》中的敘事也是鬼月,但那敘事其實是過去完成式的,敘事還未開始故事就已經結束了。是死者尋找自己死因的敘事。但婆羅洲女兒的故事才正要開始,還在試音的階段。
整體的看房慧真這三本書,為逃離恐怖的父親,少女時期主人公曾在台北都市的迷宮巷弄裡遊蕩,幾幾乎就是個稚齡的漫遊者(流浪漢、人)了。無怪乎她對都市底層的人有著一種異乎尋常的親切與愛,對城市的隅角熟稔如家。而那雙健壯的腳也常不知不覺走到都市盡頭的河岸、河沿、沙洲,那畸零人與廢棄物匯聚之地。作為都市的孩子,她其實老早就走進她喜愛調動的文學作品裡了。不止常與小鎮自私自利有時還會性騷擾小女孩的亞茲別們(〈小鎮畸人〉)擦身而過(俐落的閃開那突然伸過來的髒兮兮的鹹豬手);在她遊蕩的八、九○年代,在那個以海棠地圖命名的台北大街小巷,她應該會多次與《海東青》裡那傻乎乎愛掉書袋、喃喃唸著國父的名字的靳五相遇。有時,她幾乎就是那個蹺家的小女孩朱鴒了。還好她並沒有迷失在《海東青》那詰屈聱牙灰暗的變態成人慾海裡。對書及電影的愛好或許讓她早早的找到一條逃離荒涼的此在之路,也避免成為戒嚴國民教育裡的又一隻乖順的填鴨。她常光顧楊索筆下悲愴的夜市,對她而言那有著超乎家庭的溫暖;駱以軍《月球姓氏》裡的外省畸零人幾乎就是她街巷裡的親朋了。《第三個舞者》裡的暗巷她一定經常穿越,遇見的不是空娩的母親,而是流浪的貓與狗與翻找垃圾的人。那時婆羅洲對她來說還只是謎樣空洞而燥熱的灰色符號,一如生身父親漂泊生命裡難以言說的傷害。
那時她或許就已經知曉,有一天她會找到自己的路徑,用語言文字更為飽滿的重建自己的世界。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日中秋次日,埔里牛尾
(本文作者為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
名人推薦:一種溫柔的凝視,在近乎絕望的世界裡辨析出底層的人相濡以沫的情感、活著的理由。——黃錦樹
河流與人間
黃錦樹
房慧真的散文,從她的第一本集子《單向街》(遠流,二○○七)就幾已確定了方向:關於身世,自童年以來的種種經歷,父親母親—這是抒情散文的﹁傳統領域﹂;對寫作者而言必須藉文字來清理,自我省視。文字的簡勁讓她的文章沒有多餘的水分。但在房慧真的世界裡,總是挺立著一個巨大陰影般的父親,及苦刑般的熱帶之旅。再則是成年以後她對處身的世界的微物觀察。與及,旅行所見。
《小塵埃》(木馬,二○一三)...
章節試閱
邊城
曾經有一段不長不短的時期,每個週末,我繞過圓環,穿過瀰漫著快炒煙火氣味的寧夏夜市,穿過蚵仔煎、肉羹湯、知高腿庫飯的路邊小攤,最後,會接上隱身於靜修女中後面,羊腸般窄窄一條的歸綏街。
從寧夏到歸綏,從光明隱入黑暗,彷彿有種更往邊緣去的荒涼。煙火退散,人聲已寂,位於歸綏街上的﹁日日春關懷協會﹂,裡頭的唯一義工,正等著我來交班。交接完成,鐵門拉下,已是午夜時分,我在辦公室看電視,裡頭的小房間裡,有一具沉睡的女體,一整夜她極少醒來,像川端康成《睡美人》中被餵以安眠藥的裸身少女,而我是一個清醒的陪睡者。
清晨微明之際,蓄積了一整夜終於要一次洩洪的膀胱,驚醒了她。輕度中風的前公娼白蘭,掙扎起身,顫巍巍地向我走來,有時候她還沒到目的地便撕開紙褲,撇了稀屎散落一地,成了她行走的線索,我亦步亦趨地收拾善後。上完廁所,幫她擦拭私處,抹上痱子粉,重新包好尿布。忙亂一陣,從蟹殼青到魚肚白,天通體地亮了,輪值時段結束,走出歸綏街,仍無一絲睡意,卻又不能說是完全的清醒,我往往在這樣徹夜未眠過後的早晨,宛如夢遊一般,梭巡於迪化、歸綏、寧夏、酒泉、伊犁、蘭州、甘州、涼州、敦煌,最遠不過玉門街。
這樣帶著邊荒想像的街名,春風不過玉門關,再過去,還有些什麼呢?還有圓山、劍潭、士林、石牌、天母、北投⋯⋯台北還沒完成一半,然而,這個以大稻埕碼頭為軸心輻散出去,想像中的地理,確實就如當初命名就已埋下的讖言,真正成為邊城而沒落了。
歸綏街的前身也曾熱鬧一時,隨著大稻埕的繁華而起的藝妲間,天字第一號的﹁江山樓﹂即棲身此處,樓塌灰飛煙滅,如今也只能在侯孝賢《最好的時光》中的﹁自由夢﹂一窺昔日榮景。相較於達官貴人進出的江山樓、春鳳樓,轉入暗巷,在日日春對面的公娼館﹁文萌樓﹂,對象是在大橋頭苦力市場集散的零工、粗工。
狹長型的公娼館,一進去首先是前廳,牆上掛著標示有小姐藝名的相片,方便警察臨檢。靠牆擺放一整排的高腳凳,沒有生意的小姐,就坐著蹺腳看電視。少了神明桌,低處角落盤踞著一隻虎爺,神祕、隱蔽如這小屋的營生。揭開紅色門簾,從前廳進去,後頭還別有洞天,計有四間以木板隔間的執業房,裡頭除了比雙人床略窄的木板床外,別無他物。更往深處走,盡頭處有臉盆架、毛巾,以及恆常燒著熱水的瓦斯爐。沒有盥洗處,而是由小姐打了熱水,端進房幫客人清洗。
目睹這一切,是在台北市廢娼之後,這裡已成了可供參觀的性產業遺跡。走到底,從後邊的小門出去,娼館後巷,明明是再平凡不過的尋常民居,清白人家晾曬的被褥衣物,毫不避諱地跨界到這邊來。文靜少言的白蘭,沒生意的時候,少到前廳和其他姊妹往來,而是開了後門,在僻靜的巷間想著心事,她餵養的幾隻野貓有時來探,於腳邊磨蹭,喵喵討魚喫。早上八點開門,中午十二點阿桑做飯,姊妹共進午餐,凌晨兩點收工。只除了每星期三的性病防治所檢查,以及週二、四的午後,大伙不會忘了去簽支六合彩。有時白蘭接了一個客人,還不到中午,賺夠買魚的錢,她就收工不做,曾經那樣的任性,與自由。
附近一帶的生計,往往與娼館息息相關,位於陋巷或者二樓的便宜小旅館多,西藥房多︵賣出最多的是淋病藥︶,婦產科、割包皮的泌尿科多,按摩店、內設卡拉OK的清茶店多,深夜燈火通明的小吃店也多。過了重慶北路,民生西路上的﹁杏花閣﹂,或是延平北路的﹁黑美人﹂、﹁五月花﹂,算是昔日河港紅燈區的丁點遺留。
除了食、色兩項,婚喪嫁娶等生死大事,皆可在此交辦。出生所需,有油飯行︵兼賣肉粽、粿製品︶、命名館。嫁娶大事,相親可至﹁波麗路﹂,嫁妝可至百貨店採辦,婚服至永樂布市量身訂做,喜餅則有百年糕餅老鋪,婚期選定可至擇日館。生病調養,有南北貨中藥行,西藥則有迪化街34號空留廢墟的屈臣氏大藥房,日治時代是進口西藥的大批發商。來到生命之終,三角臉和小瘦ㄚ頭的西樂隊,或者國樂的嗩吶鼓吹,多集中在大橋頭一帶,橋下人力勞動市場沒被挑選走的,露宿於亭仔腳的羅漢腳,也許就拼拼湊湊出一個鑼鼓隊陣頭來。
再找不出任何一個地方若此,彷彿人生的縮影公園,不出幾條街廓,便可將生、老、病、死一網打盡。
一網打盡的還不止於此,各式原料:化工行、儀器行、木材、塑膠、染料、布帛⋯⋯天工開物,與一般五金行,或者B&Q特力屋不同,一家小店就專賣一物,賣塑膠的他就專攻塑膠,不雜賣木材金屬。短短一條天水街,有七、八家化工材料行,也不覺其怪。靠近承德路的興城街,還常見一些隱身於民宅間的家庭工廠:軸承工廠,不遠處還有魚丸加工廠,邊城舊區,還容得下此種早期常見的小型製造業,還沒過橋被放逐到新北市的新莊、五股工業區一帶,也還被驅逐渡海至珠江三角洲,或者更往南邊去的東南亞一帶。
此區老行業多,原料行多,小型製造業猶存。
除此之外,老人也多,時常街衢交會處,稍有一處畸零空地,便見三五老人搬了板凳來聊天,有些閒聊之外,還不忘經營小生計,鐵桶裝了紅茶,十元一袋。甫放學,還穿著制服不及脫下的小女孩,提著兩包紅茶回家去。老人煮紅茶賺些零花,小兒呷涼,自然而然的供需,不需透過大盤中盤,便利店層層的物流系統。又例如保安街﹁慈聖宮﹂前的一排食攤,不做晚市,下午四、五點即收,光顧的多是老人。攤車前擺放的清一色是長條板凳,頗有古意。一家賣家常菜的小店,綠格子窗櫺上掛著活動菜牌,白底紅字寫上菜名:蝦仁淮山、紅糟鰻魚、蒜苗魚片等等,可因應季節時蔬不同而隨時替換。
廢墟也多。有些民居一樓還做小生意,二樓已全然荒廢,甚或傾頹了,格窗以木板封起,寂寞的女兒牆,再無人憑欄倚望。蕨類野蔓攀爬牆間,長得特別青綠,特別好,甚至比老老實實栽出來的盆栽還好。有時候一棟棄屋的內部,被一棵樹侵入,生根、茁壯,自然的意志穿刺天花板,從二樓的窗口擊碎玻璃伸出枝葉,凶猛的綠意,最是生機勃發。
有些廢墟,還留有這一帶常見,不見底的長樓梯。樓層之間,沒有絲毫迴旋轉圜之處,階階相連到天邊,像座天梯。從梯口望去,對於未知盡頭的著迷,心底有個聲音不斷慫恿著前去。才踏上幾步,便有樓傾之勢,只得作罷。
邊城的邊緣,例如往昔有﹁洋樓街﹂之稱的貴德街,越臨近河邊碼頭,往日越繁盛不可方物的,時代的浪潮,越是退卻得厲害。
從台北橋上回望,迪化街臨河一排,年貨大街的背面,往常貨物於岸邊卸下,直接後門進,前門出。如今,翠翠和爺爺不在,河岸不再擺渡貨物,越近河,水氣濕度越增,整排老屋已經壞毀得差不多了,恣意伸展的枝葉,綠巨人掀翻整片屋頂,往晴空猙獰抓去。
夜市,人生
對夜市最早的印象來自小時候,不假外求,家附近就有,或許是改道後,河水不再流經的廢棄舊河道;或許是荒置已久,芒草已抽長至半人高,堆置貨櫃,遲遲未起高樓的大片空地。通常不是在禮拜六、日這樣的週末假期,週末一到,人們整好衣裝,便往西門町鬧區,或者較具規模的士林夜市去。半路插花的流動夜市,通常選在小週末,星期三晚上前來紮營,次數亦不頻繁,有時隔週才來一次,不太讓人想起,但也不容易忘記。還未走近,遠遠就聽到三、四十台發電機的馬達一齊嗡嗡作響,那震幅會使人心跳增速,腳步加快,原來形同鬼域的畸零地,忽地架燈打光,成了一處泊滿長舟的碼頭,引擎正熱著,芭蕉剛摘下,群聚成一隨機集散的水上市場。
逛夜市,或許正服膺著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道理,從不是為了買東西去。沒人像對待百貨公司周年慶一樣地,將折扣情報蒐集好,折價券準備好,信用卡的紅利點數算清楚,如臨大敵似地,甚至是百貨公司的動線圖,哪一個電梯口衝到哪一個櫃位可以截彎取直節省最多的時間。滿額送、滿千送百,一方面是講求快、狠、準的精明俐落,是法家的寧可錯殺,不可輕放;一方面卻是拖泥帶水的癡心,是墨家的兼愛。
逛夜市是道家的無為,是興之所至,是臨時起意的隨波逐流。
一家大小的穿著有點隨意,晚餐之後的散步,短褲拖鞋就出來了,也許還提包垃圾順道去丟,邋遢一點也無所謂,發電機所能供應的,就是昏黃暗淡的燈光,那燈光並不勢利,而是包容得多,再猥瑣的人身在其中,都有些朦朧美。逛夜市帶的閒錢也不多,我成長的年代,主婦還需做點家庭手工來貼補家用,錢總是用在刀口上,也許就準備個一百、兩百,回程順便買半條明早抹果醬吃的吐司。
儘管節制如此,總有一攤令我們流連忘返。那是賣五金的攤子,文件夾大小的紅色塑膠籃內,裝著各種五金百貨,統統一樣十元,全部大概也有四、五十籃的物事,很難說清楚到底是什麼,隨人各取所需,老闆會發給一個塑膠籃,人人從那眼花撩亂接枝雜生的果樹裡,採擷自己要的,丟入自己的籃內。媽媽丟進菜瓜布,廚房收納小幫手;爸爸丟進計算機老虎鉗;哥哥丟進無敵鐵金剛;妹妹丟進紙娃娃。一樣十元,不用為了成全A而割捨B,不必男尊女卑,孔融讓梨,人人有獎,皆大歡喜。
我相中的總是那些紅紅綠綠的色筆、拍紙簿,因為便宜,所以用不著月考前三名母親才會犒賞你,隨手就可以指個一、兩樣,母親總有些零頭可以允許你帶回一樣。日後很難找到同樣的實體店面,結合了五金行、文具店、雜貨店⋯⋯,而神奇地大概是那載體,一籃一籃地像盛滿碎五金的廉價珠寶盒,拼貼鋪排在地,每個人下腰屈膝去挑選自己要的。在夜市,時常看見這種蹲踞的身體姿勢,小販蹲踞著等生意上門,人客蹲踞著挑物品。在百貨公司則彷彿美姿美儀,人是直挺挺地,唯有電梯小姐會極不自然地,對人鞠躬九十度。
長大以後,自己一個人還逛夜市。我甚少在夜市吃喝,採買,卻總有逛不厭的物事。於我而言,夜市是最好的人間秀場,不看歹戲拖棚的八點檔連續劇,何妨關掉電視,往夜市去。
夜市裡新舊雜陳,總能看到最具巧思的新發明。近來注意到雨後春筍般冒出的鹽水雞攤子,我所見過最輕簡陽春的設備,用不著傳統笨重的攤車,一個菜籃車,上頭架了一個鋁製臉盆,就可在夜市裡占得一席之地。菜籃車裡的空間,可供擺放各式待用的材料;鹽水雞無需汆燙過火,就直接在上頭的臉盆裡攪拌,呼應現今的樂活風,無火無碳無油煙氣,只要香油、辣椒、蒜頭、香菜等,就可以不升火進行涼拌。臉盆裡的料,除了傳統的雞翅鴨胗,也加入茭白筍、蘆筍、小黃瓜等時蔬野菜,看來清新可喜。
也愛看老攤,滷味總標榜是從前西門町老戲院外的那一家,乾脆取名為﹁萬國﹂滷味︵雖則戲院早已不再︶,滾輪推車,上置木頭矮櫃,覆以草綠紗窗,裡頭腸胗腳爪一一分門別類擺好,滷味講究浸滷的老湯汁,彷彿也浸透到那木櫥的紋路裡,油亮油亮的。看電影時,有人吃雞腳搓得塑膠袋嗶剝響,一度是我最痛恨的擾人噪音,但滷味與老戲院,似乎就是特別合拍,如西門町電影街與老天祿。還有紅泥炭爐烤魷魚,老婆婆拿蒲扇搧呀搧,再加上煮玉米、花生、菱角蒸騰的水煙繚繞,豈是熱狗、可樂、爆米花可比擬。
夜市,或許還可見早期生活型態的遺留。儘管逛的人,早已不分本省外省、閩南客家。但閩南人聚集的艋舺,賣粥的多,不是其他夜市常見的廣東粥,而是需再配上漬菜、炸物的白粥、鹹粥。一個在騎樓下賣地瓜稀飯的,等著銀行三點半關門後才開張營業,一路賣進深夜,越清晨,稀飯易消化,是消夜也是早點。儘管只是路邊攤販,卻一點也不馬虎,光是蛋類就有好幾種選擇:水煮蛋、剖半的紅心鹹蛋、松花皮蛋、菜脯炒蛋,還有煎好堆成小丘的荷包蛋⋯⋯,座位不多,來光顧的通常不是觀光客,常見浪人捧著盛滿熱粥的保麗龍碗,加瓢肉鬆,便蹲踞在路邊稀哩呼嚕喝了起來,如此便能飽肚。後來,騎樓越加壅塞,也許樹大招風,整攤被趕入昏暗後巷,不到黃昏,小燈泡就要事先點上。那後巷本來聚集著一些帶著流浪狗的浪人,平日便住在那裡。地瓜稀飯加入後,浪人和流浪狗都還在,少了尿騷味,熟門熟路的依然找去,從巷口溢滿出來的人流,有跡可循,盛況依舊。
在龍山寺前的艋舺廣場上,有那種無啥明顯招牌,就一個大推車出來,上頭是米粉湯、芋頭粥、鮮魚湯,只賣這三樣,但不知如何能湊在一塊,且看起來都灰灰糊糊地一片,無啥賣相,大匙撈送進保麗龍碗裡,有時還會在碗沿留下幾條漏網之魚,糊溜溜的麵條,就像冷天裡有些遊民臉上還未以衣袖拭去的兩管糊溜溜鼻涕。
也有賣佐以紅燒肉、天婦羅、炸蚵仔各類炸物,加了絞肉熬煮,米粒猶粒粒分明的台式鹹粥。台式鹹粥不做正餐吃,也不常見人結伴來吃,通常就是當地人,在兩餐之間需墊墊肚子,一個人來,點一小碗薄粥,卻頗豪氣地配上三、四樣炸物,擺成一桌看上去就頗澎湃,在畫布裡紅燒肉的豔紅尤有點睛之妙,像是吃巧而不吃飽,再點上一瓶蔘茸藥酒,便有那麼一點江湖味了。
又如油條,在早餐店裡與燒餅、豆漿配套,被視為外省食物。在艋舺則時可見油條花生湯,單飛後佐以花生湯吃,手抓整根油條,一口炸油條,一口濃郁的花生湯,則變身為台味吃法。也可將油條置換成椪餅,店家先用調羹將蓬鬆的椪餅壓碎,以十字切成四等分,繼而淋上花生湯。愛吃鹹的點油條,愛吃甜的點椪餅,不變的主角是花生湯。
在艋舺,也賣那種大骨直接劈裂下來的原汁排骨湯。不是一小缽一小缽,加了鐵蓋在蒸籠裡分煮的金針苦瓜排骨湯,端上來一個湯匙就可舀起一塊排骨。艋舺的原汁排骨湯,則是那種極粗豪的吃法,一整塊大排骨最大的湯碗猶然無法全部盛得住,筷子夾不住,湯匙舀不住,就只能用手對待,人人面前都是一座排骨山,無啥調味,加了蘿蔔下去熬煮,大嘴吃肉,大口喝湯,愛鹹味的就把排骨沾醬油辣椒吃。
艋舺清茶館附近的鵝肉攤,還可見到那種外送至酒家的,有著提把的白鐵大餐盒,用不著塑膠袋餐盒層層裹裹,只是手提著,或者綁在腳踏車後頭,就近送下酒菜去,順道收回前一次的杯盤狼藉。切鵝肉,鵝血米糕,鵝腸鵝胗鵝下水,都是很好配酒的下酒菜。
在艋舺,在常見的蚵仔煎、蚵仔麵線外,還有一種﹁乾蚵﹂的吃法,名為﹁乾蚵﹂,其實吃起來頗為濕潤,是蚵仔用太白粉勾芡裹粉之後,下鍋稍燙,起鍋瀝乾後,加點蒜頭與薑絲。除了乾蚵,也有蚵仔麵,蚵仔米粉,但當地人通常不這麼吃,點了乾蚵,就不再加點蚵仔麵,而是點一盤豆皮壽司。不知怎麼約定成俗形成的慣例,賣乾蚵的店一定有豆皮壽司,這樣的混搭不知來由,是台式加日式,吃巧加吃飽。
屬於台式的豪氣、隨意與灑脫,也顯現在做生意的性格上,有日經過,每年年終固定自費擺上流水席宴請街友的﹁刈包吉﹂,攤車用木板封起,貼出告示:﹁海邊釣魚,暫時休息兩個月﹂,離年終尚遠,刈包吉暫時不做生意,度小月去了。
離艋舺不遠的南機場夜市則多外省麵食,許多人為吃餃子而來,這裡的餃子館都會附上大量蒜頭,每張桌子上都有滿筐滿籮的蒜頭,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人人點好餃子之後,便會隨手抓了一把蒜頭,擱在桌面上彷若一座白色小丘,等餃子起鍋的期間,還有一段時間,這時或許去切一盤滷菜,或者開始將那面前的蒜頭一一剝皮除膜,弄得光滑白淨地,等會,便好一口餃子,一粒蒜頭,吃得滿口腥嗆,這豪氣是北方大漢式的,和艋舺的本省江湖味不同。
南機場夜市上樓就是住宅,住商混合,底下的店家通常就住在樓上,樓梯間常堆滿了濕淋淋地,剛洗切好的青菜,擱在後場,正等著前頭的自助餐下鍋。窄仄的樓梯間還有公休未推出的攤車,甚至還有幾桶瓦斯桶囤積備用,公共安全的憂慮暫時擺在後頭,前頭有兵荒馬亂、急如星火的夜市營生得先維持。(未完)
邊城
曾經有一段不長不短的時期,每個週末,我繞過圓環,穿過瀰漫著快炒煙火氣味的寧夏夜市,穿過蚵仔煎、肉羹湯、知高腿庫飯的路邊小攤,最後,會接上隱身於靜修女中後面,羊腸般窄窄一條的歸綏街。
從寧夏到歸綏,從光明隱入黑暗,彷彿有種更往邊緣去的荒涼。煙火退散,人聲已寂,位於歸綏街上的﹁日日春關懷協會﹂,裡頭的唯一義工,正等著我來交班。交接完成,鐵門拉下,已是午夜時分,我在辦公室看電視,裡頭的小房間裡,有一具沉睡的女體,一整夜她極少醒來,像川端康成《睡美人》中被餵以安眠藥的裸身少女,而我是一個清醒的陪睡...
目錄
序:河流與人間 黃錦樹
下游
邊城
浮島森林
大河盡頭
水上人家
大河之歌
河岸生活
大橋下
天鵝
中游
流浪藝人
江湖在哪裡
彼岸
冷攤
小鎮畸人
麵攤
夜市,人生
上游
小城故事
奔流入海
汀州
劍潭幻影
流水人家
下水底
黑暗之心
看不見的城市
序:河流與人間 黃錦樹
下游
邊城
浮島森林
大河盡頭
水上人家
大河之歌
河岸生活
大橋下
天鵝
中游
流浪藝人
江湖在哪裡
彼岸
冷攤
小鎮畸人
麵攤
夜市,人生
上游
小城故事
奔流入海
汀州
劍潭幻影
流水人家
下水底
黑暗之心
看不見的城市


 2017/02/04
2017/02/04 2015/09/08
2015/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