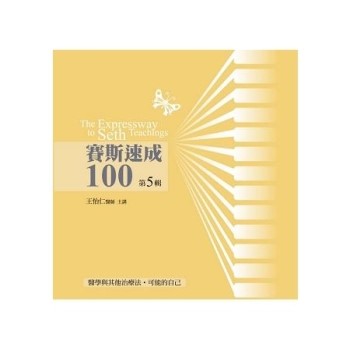十四道通往文學幻境的任意門,魔魅瑰奇的時光歸返術。
所有移動中的事物,一切存有,可能,真的不過是漫長時光的一種織網形式。——童偉格
真正的閱讀是重讀,真正的書寫亦是重寫。
閱讀之於人生,是經驗的一再解離與碰撞,是內心旅程如夢似幻且近乎永恆的探索歷程,童偉格彷彿穿透時光來去,試圖引領讀者走進小說家龐闊繁複的書寫迷宮,抵達記憶與遺忘的庫存之所,去「看」去「回應」那些失而復得的存在。
虛實交錯的筆法,謊稱在場的預視,跟隨史溫侯的腳步,重返一八五八年的福爾摩沙與二〇〇八年的河港;走進李維史陀的旅行裡,彷彿聽見這位無處安居的旅行者說,每一次回返,都在內心,讓自己向更深處退隱。他進入卡夫卡、杜斯妥也夫斯基、聖艾修伯里、吳爾芙、但丁、卡謬等文學家的意識中,與班雅明、波特萊爾、傅柯、契訶夫等人對話,彷彿與他們同在。
碰觸死亡、現代性與故事深處,一次又一次地借閱,開啟謎題與禁忌之門,最私密的書寫,最深層的隱喻,讓文字成為一種歸返,一種溫暖的救贖。
名人推薦
以人生片段召喚起借閱,借閱以喚回過往經驗,歸返運動循環發動,我相信,《童話故事》一直是這樣在練習的。歸返的欲望,重新變回原初的欲望,追尋遺忘與諒解,傾向愛與死的欲望。——朱嘉漢(巴黎高等社會科學院博士生)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童話故事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圖書名稱:童話故事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童偉格
一名潛行於時光中的小說家。
1977年生,新北市人。台大外文系畢業。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碩士,現就讀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博士班。拉美魔幻風格融會「鄉土」的題材,在他的文字中自由出入,使他成為備受注目的文壇新銳。作品〈王考〉獲2002年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大獎,〈暗影〉獲2000年全國大專學生文學獎短篇小說參獎,〈躲〉獲2000年台灣省文學獎短篇小說優選,〈我〉獲1999年台北文學獎短篇小說評審獎,《西北雨》獲2010年台灣文學獎圖書類長篇小說金典獎。著有短篇小說集《王考》,長篇小說《無傷時代》、《西北雨》,舞台劇本《小事》。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