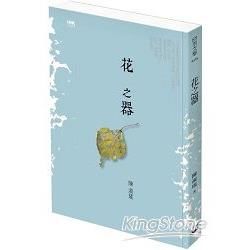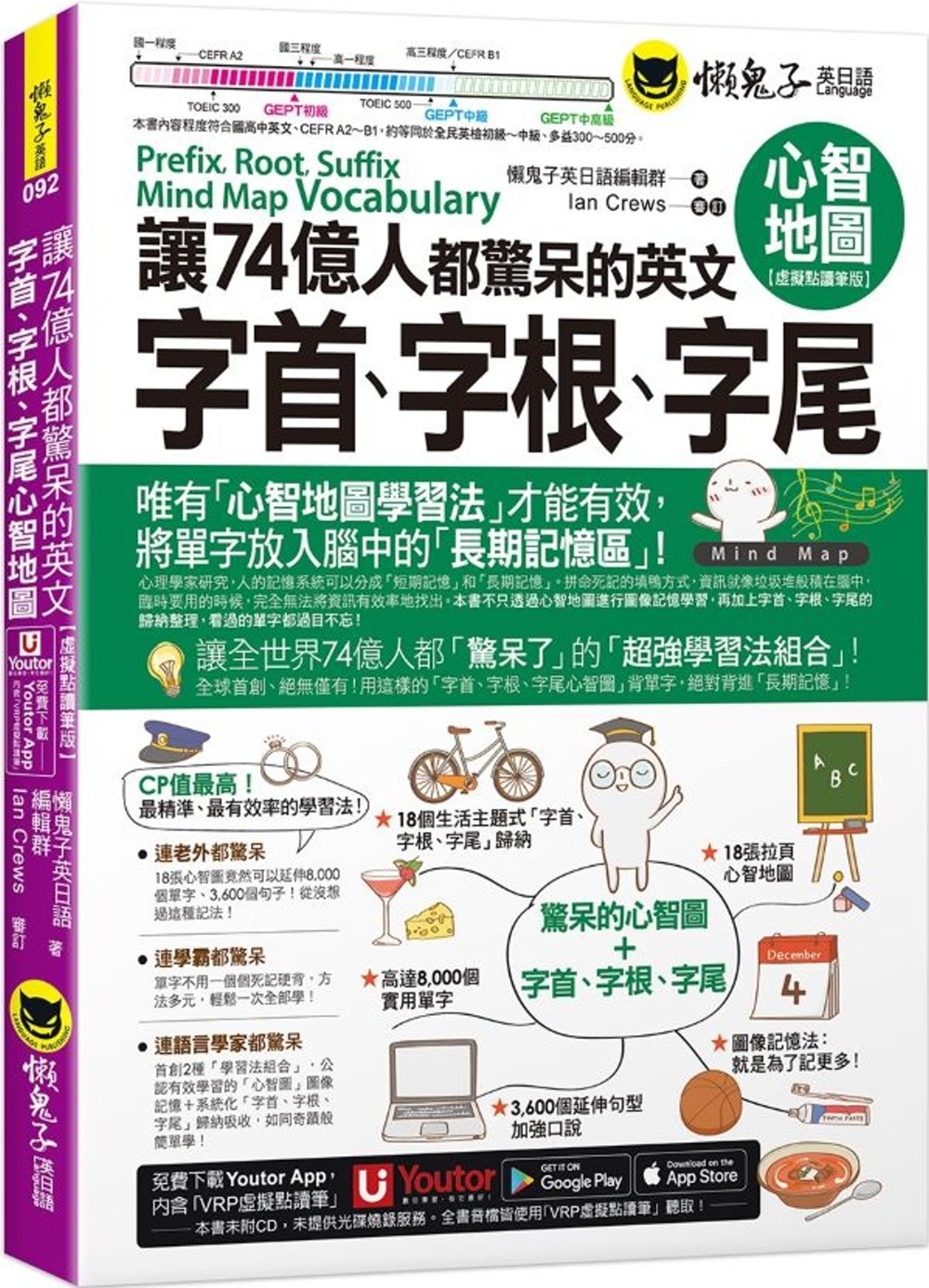捕風
從山腳下的窩居搬至高樓,最覺不慣的是風,有時甚至到了心驚膽顫的地步。自己都不大相信,被偏激的風掐大的人?!大學的一個年初一風和日麗,我提議去走跨海大橋,真這麼做了,和朋友各帶一個來澎湖過年的親戚,一個大男孩和一個小男孩,那時的跨海大橋尚未拓寬,護欄沒這麼高,走上橋才知道,風導演的天滔駭浪簡直要將人颳下橋去,雖然兩名台灣客很信任我們,勇敢是裝不來的,回頭是岸。今日家常的風帶給中年人的恐慌居然更甚當時。
各個窗子吹進來的風各有不同的風味。旁無高樓,書房裡的風一來便是大江大海,瞬間滿樓,招架不住的瓶罐乒乓墜地,一掃而空的感覺差勁透了。搶步過來,落單的卡片紙張全湧至房口,風有多大,關窗的力道就有多大,像回揮那個瘋人一巴掌,將它飄逸的長髮夾在窗框裡。
和室的風徐徐,透過參差的葉隙塵漫的紗窗,如靜詠的山泉,帶來幾許涼意,偶爾被踉蹌入侵者關閉,鐵定是它挾雨偷渡,濕了一角床墊,變天了。
晾衣間的風不算礙事,預防瓦斯外洩,一縫窗息永遠必要,掛在窗上的月曆用以遮蔽正對面住戶的窗子,三四月已整本僵硬,下擺翹起,風撥弄它們不再俐落。這窗位於大樓的凹處,風較溫吞,但個把月窗臺上也會走出一道塵泥,偶爾來一陣刁鑽的風長驅直入,將恐龍領軍的一排甲蟲蚱蜢颳得人仰馬翻,好像在搬演玩具總動員。
而看似單純的浴室小窗卻多次惹惱我自床上跳起,窗上那張備而不用的百葉遮簾成了捕風的籠子,窗開得越小賊風哨子吹得越響,並且幾分鐘就夾雜一次持續數秒的簧片抖音,像隻哀痛的蜻蜓正設法救出牠那亮麗的翅膀。間或控制遮簾的拉桿敲打牆壁,摳摳摳。一向好睡的人不能成眠,它便成了代罪羔羊。而當你一個動作將它排除在外,立即陷入幽蔽的迴音中。
通風,臥床旁的邊窗盡可能不關,這窗風擾亂我也是感覺聽覺上的,無常的。處於陽台左側的迎風面,窗戶外推,像隻招風的耳,感覺風加倍猛烈,嘩嘩嘩,簾幔鼓脹起來,像蝙蝠俠的披風漫天飛舞,一揚一吸的衝撞紗窗,即使簾幔束緊,鬆弛的紗網也會像頻死的鰓一樣喘動,即使再三告誡自己不必管它,最後還是起身拉上了玻璃窗。風突如其來也就罷了,多少回是未先關窗就上床,或者放縱忍受它好久還是投降。
讓我把這麼緊張兮兮歸因於牽掛陽台高踞的植物,而不是垂垂老矣。為了吸收陽光冒險將開花植物擺上高樓的圍牆,當然稍有風吹草動得趕緊一盆盆乖乖收起來,像流動攤販躲避員警查緝。有一兩回忘記已經撤退,聽到風聲才慌張跑出客廳,一望圍牆上空無一物,瞠目結舌,心跳差點停止,以前看演員這樣演戲總覺得誇張,這就懂了,一點也不。風與植物的衝突,常使我處於心則狂亂狐疑不信的狀態,在圍牆曬植物是自討苦吃第一重,錯上加錯是在陽台掛風鈴。
陽臺上的冷氣台做擺放盆栽的平臺使用,邊緣釘了三根釘子來垂吊植物,卻常不小心將植物駝到背上而打翻,懸空澆水也不方便,取下綠葉,改懸掛適於懸掛的東西。在同一家藝品店,我先後買了兩串破碎的風鈴,第一串是杏白色的長條形石片垂綴於木環下,石片上面刻有祝福的字眼,「May you be happy」、「May you be healty」,巧手的老闆娘用黏膠和透明貼布將斷裂的兩條祝語接了回去。第二串則是一根橫槓掛了三條共六片淺磚色的楓葉,加上一串果核小簾,織成一道流蘇,高度與圍牆相仿,風平行而來,吹個正著,時而搖搖晃晃,時而敲敲打打,舊傷招架不住,很快又添新傷。斷落的祝福殘片和楓葉隨處平放在盆栽的土面上,隻字片語無限溫柔。
風持續磨著風鈴銳利的傷口和我的耳朵,以及薄薄的耐性。祝福風鈴碰撞的碎石,楓葉風鈴飄浮如割瓦,尤其是祝福,鈴舌長而又圍成圈,像聒噪不散的宴席,風起個話頭便喋喋不休。雖說這麼一來好似繫鈴於貓頸,它們絕對盡責於通風報信,但藉此衡量風的級數,輕重緩急,著實勞神。等危機解除,尚得忍受它們有一句沒一句的叮嚀。就算你無所謂了,也得顧慮其他人的聽覺。每回不堪其擾去解鈴,還怕聽見的人笑話,動作極其輕緩。見它摺疊手腳癱軟在花盆裡,像瓦解成一堆碎片的傀儡,切掉聲帶的狗兒,心裡並不好受。幾次夜半被鈴聲鬧醒,不及披衣,反射動作直奔陽台,精神恍惚,卻莫名一種飄飄何所似的孤寂脹滿心口。
聽說硌磯山脈冬天的氣溫有時會降到攝氏零下五十度,我大嚷怎麼可能有人回答那是因為風,我便無言吹過那樣的風的人再不覺得世上有風了,現在無須那樣衝風破浪了,呆在房底聽著橫掃陽台的強風與風鈴交響,腦子裡自動遞出一個阻斷恐懼的畫面,空蕩蕩的圍牆。再無法轉移心思,甚至有個聲音提醒,放心啦,危險的遊戲不是已經結束了。理智上如此,但還是靜定不下來,疑似颱風,它在拍打搖撼落地門,不知又在摧毀什麼。
隔著密閉的玻璃,我站在臥房窗邊從側面觀看陽台。陽臺上的植物違背趨光的天性一波波向內傾斜,唯有那株彩虹木與風正面衝突,這是臣服者微小的反抗。高出圍牆的彩虹木自動彎下腰桿,成一支折曲的茅,風壓著它敲扣圍牆,它啄傷了自己,一個三角形的傷口坎進枝幹中心。風至狂暴時,我忍不住去轉動它的盆子,將它探頭汲取光和雨露的部分旋入圍牆內。雖然我懷疑這種示弱的舉動不會讓它比較好受,只是換一個不耐痛的部位繼續接受鞭打。
看得入神回頭踢到風扇,窗下這個位置,床的左前方,專門放風扇,沒風的日子或拒風於千里之外,全仰賴它,一就桌畔床邊就先將開關切至「微風」,夏日它常徹夜未眠,大約五月初吹到十月底,十一月,棉被出籠時,搖頭擺腦規律的風聲如輕柔的潮水有助睡夢。書桌邊的風扇靠得更近,是專為我搧風的書僮。
再讓我說一點。一個適於春遊的好天氣,近傍晚斷然消失,新竹的山風強勢兇悍,一夥人用完餐急急躲上車,坐到暖和的車內,我自顧自陶醉地說起少年時冰風的澎湖冬夜,看電視也把手窩在口袋裡,忽然有一雙手正費勁地推動你家笨重的門,屋裡的人全都注視著,都盼望隨風出現在門口的是自己的朋友,想到為了來找你她冒著刺骨的寒風一個人走在黑漆漆的路上,心底有多感動,那是一個最想念朋友的年紀。
吃水果
讀愛亞的〈吃芒果之後〉,她說吃完芒果應直接洗手,而不是抹了紙巾再去清洗,這我贊同,有更徹底的是一位非常節儉的男性友人,他說他專挑雨天站在屋簷下啃芒果,啃完就地洗手洗臉,紙也省了水也省了,方便暢快。這種經驗小時候或許有過,現在已非常難得,這種人畢竟不多,問題是雨果淋漓可能順著兩肘流下來而濺到衣服,這對只愛自己和衣服乾淨不知道地球也愛乾淨的人們怎麼行,也許得等到限水非環保不可時才會有這樣的情景,在雨天屋簷下排排站練習啃芒果。
吃水果吧,有什麼東西像水果那麼全然的令人甜蜜清心。在泰國工作多年的舅舅別的都沒說,只說每逢假日必至市場採買水果,直到提不了得乘計程車回家,很多時候他都是以水果果腹的,他喜歡那樣的日子,打算長久住在那兒。水果讓人樂不思蜀!聽得我好羨慕。水果確有如此吸引力,前年夏天妹妹一家打著採水蜜桃的口號從離島來,舟車勞頓幾個水蜜桃下肚,妹妹在路邊就吐了起來,怎麼今年又祭出採荔枝來了。
縱使再厭煩的工作,再鬱悶的心情,吃水果吧。家中不是時時有好花插在瓶供養,卻每日有鮮果擺在盤中,書桌上、水壺邊、窗口下,雖然沒有供佛,卻有佛在那兒。特別偏愛一隻藍色復古花瓷碟,搭配任何水果都相得益彰,彷彿為寫生作畫而擺設,光線視線皆停留,時間為之靜止。另有兩個會變戲法的木雕容器,果子一擺進去,就好像睡到搖籃吊床裡,極富度假風情。
光就水果而言,我的童年生活是再飽足美好不過了。夏日屋內疊堆著自家收成的瓜果,孩子學著用刀,個個都是一刀兩斷的切瓜法,再以湯匙盛挖果肉,托著一個綠缽︵嘉寶瓜︶或黃缽︵香瓜︶邊玩邊吃。而現在屋裡只要一顆完好的西瓜哈密瓜在就會令我牽腸掛肚,時時自問:「差不多了嗎?會不會太熟了?」不止是瓜,還有返鄉的親友帶來作伴手的水果,早年還是用個竹簍子裝著果葉紮著,看到這行李便問:「誰回來了?」帶當季水果,即時沉重好有心意。但這可能只是小孩子的想法、嗜好水果的人的想法,遇到世故的老祖母,卻要鄙視的看它一眼說:「拿這!」特別是對那些荷包滿滿的來客,即使是昂貴的整箱蘋果水蜜桃,冰箱冰不完,還不是四、五天賞味期早早送進嘴巴了事。最好別不捨得,當天即分送一些給別人家做人情,其餘攤散在大圓篩,搬到床上去。這幾日不需覓零食,早晚進房間去瞧瞧聞聞,奢華極了。
瓜不熟客人不來,大多數的平常日子就只有等父親進城買水果,半日功夫便搶食一空,剩下綑著紅繩像掃把頭的荔枝枯枝、一個像被折掉琴鍵的香蕉頭,嘈嘈切切,吃的人沒吃的人都有話說。也有又吃又拿的,他什麼都不說。同學雅青就說她兒時很賊,暗地裡黑眼珠往奶奶衣櫃上飄,竊笑著用蹩腳的閩南話跟奶奶說「扣︵釋︶迦仔!」原來藏水果的人還真不少,有時藏忘了,就慘了。
離家外出,開始學著買水果,學校對面一處「田邊」,據說往昔是農地,後來變作夜市,另名「田邊俱樂部」,女學生結伴來此挑選水果養顏美容,夜空下低頭專注之際,背地裡一聲「學姐!」大家紛紛回過頭去,有人笑了,叫學姐不應,叫學妹才答。現在清晨上市場,攤位還未擺齊,邊散步邊張望,越看越多,買這買那,明知將有遠行,還是克制不了,有時還得拜託朋友幫忙消化。
初到馬來西亞婆家過年,最不習慣的是在那樣的豔陽天重口味,他們竟然沒有吃水果的習慣;他們說「生果」,彷彿野人的飲食。最常見的是他們拜年必備的伴手和回禮,柑,熱天吃柑很不錯,可惜那些中國大陸來的暗沉小柑又醜又乾,根本不能和台灣豐滿的柑橘相比,聊勝於無,我也吃著吃著。偶爾廚房門口那張擱舊報紙的木桌上出現了生果,肯定是別人家送的,剛從枝頭飛下來,且數量龐大。例如一掛好幾串上百條青澀的香蕉,聽說筋骨不好的人不宜吃香蕉,我才不管,還特別偏愛六七分熟。沒人捧場,青色香蕉一日日斑黃甜膩起來,更加努力的吃,吃成一種饑饉荒涼的心情,難怪他們看我很鄉下人。
有時是年初二大嫂回娘家自產地載回來七、八隻黃梨︵鳳梨︶,因為大哥愛吃黃梨。有時是獨居的大姑丈剝好的一大袋波羅蜜,說是很熱︵火氣大︶,也沒人賞臉。年初一表兄弟妹們去給大姑丈拜年,偏僻的屋子,左鄰右舍空無人住,兒子遣一外勞陪他在此過年,門口一條小梯斜下去,赤地裡幾樹木瓜波羅蜜,安逸寂寞的家園。可惜今年他老病無法獨居,入住安養院,不再拎著蔬果來看我們。
現在家婆封我為「水果王」,我們回來前她已買好芭樂蘋果放在雪櫃裡,光想到這個就覺得幸福,好像戶頭裡有了存款。有時他們看我要了幾張馬幣汲著拖鞋出門,就知道是上街買生果去了。幾步的馬路常常車水馬龍,不容易過,烈日當空瞇眼望,木屋下高高低低金黃的果攤被車一刷一刷忽隱忽現,我滿心澎湃像會老情人般。
最常買的是台灣沒有的香梨和「嚕咕」。香梨是中國大陸來的,我猜一定是新疆來的,才會這麼甘美,外表似台灣俗稱的西洋梨,更青脆多汁,吃一百顆就有一百顆好吃,有時我還會偷偷挾帶幾顆上飛機,回臺北擺在盤子上,看它們疲累的臥姿似乎也有鄉愁,我也意盡了。只是當地好吃的水果太多,漸漸就把它給拋棄了。嚕咕是當地水果,看似龍眼,體積較大果皮較厚,不用剝的用扒的,裡頭一瓣瓣小果肉,甜中微帶酸。水果無分貴賤,對味就是了,但是我覺得第一等水果就是這種及時行樂赤手空拳就能吃,吃完也不需洗手,像橘子香蕉荔枝龍眼釋迦,嚕咕也屬這類。他們看我一個接一個,一面囑咐別吃多上火,一面也剝一個吃吃,真有那麼好吃嗎。
我邊吃還要邊問,怎麼每次回來都沒遇見榴槤山竹?他們說不多久前才有人送一布袋榴槤也沒人要吃。榴槤我倒真的不能多吃,怕喉嚨痛,且每次買就一定會這裡不對那裡不好而不能吃,只是想起我媽,一個奶味椰子味什麼不合常理的味都排斥的歐巴桑竟然很愛吃。山竹,他們也說不清,好像是五月吧!沒有季節的地方還真麻煩,不像我們四季四隻碟子擺著四色水果。山竹則讓我想起峇裡島之旅,早年國家地理譽為眾神的傑作的地方,如今顯然走了樣,只有大吃山竹的滋味令我想念。同飯店一名貴婦指稱打掃房間的婦人偷了她兩個山竹,我明明數過,她說。珍愛那些果子如同珠寶的數著,我懂;只是,當地的婦人怎會稀罕那兩個山竹呢;若她真的吃了,也不過是種惡作劇的不屑的心態吧。
常聽他們說要看花看山看春天就要上金馬崙去,今年過年終於成行,沿途土產都買來嘗嘗,我又貪吃提起想吃山竹,他們不可思議齊聲驚問:「山豬?」聽見是山竹便低八度說現在沒有。我們先在麻六甲逗留,這裡我已來過兩回,並無新意,卻還是在一個像吉普賽人的灰撲撲的遊樂場流連入夜,驅車離開時忽然眼尖瞥見路邊簷燈下掛著串串山竹,緊急煞向路旁,全車人爆出感動的歡呼:「山豬!」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花之器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9 |
二手中文書 |
$ 190 |
中文現代文學 |
$ 204 |
小說/文學 |
$ 211 |
中文書 |
$ 211 |
現代散文 |
$ 216 |
現代散文 |
$ 216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花之器
一個淒清的冬日在冰涼的街頭,回神看見一群落葉自地上飄回樹梢,瞬間一陣狂喜,整個精神都來了。當然是眼花撩亂,那是一群麻雀,而非落葉。我所寫的無非就是捕捉、呈現落葉飄回樹梢的情景。我以為我有這樣的能力。——陳淑瑤
輕培慢拈,手植七年終於養成的青脆散文集
一冊塵與光與霧的迷濛顧盼,收藏心頭的美好物事與記憶
作者從山腳窩居搬至高樓,植栽與人需重新適應大樓節候,家常的風、滲入的雨、挪移的陽光等,左右著盆栽的遷徙,花草掩映的日子,自然有了新解,然而撲面的風塵,仍是古老季節的氣味,於是她小心翼翼地拾起細節,記錄日常小事與衣食樣貌,是陽台乍見杯觥交錯的綠光、老獵人採來的新鮮山蘇、隱於破瓦盆的錦黃小菊、父親贈送的貝頁、遺失歌詞的兒歌、大嫂的年夜飯、阿嬤的土豆糖仔……, 她將無用的小物與故鄉的人情採擷成生活中雀躍的色彩,長短之間收放自如,淺淺淡淡,如一陣風,拂過春光。
作者簡介:
陳淑瑤
一九六七年生於秋天的澎湖農村,就讀馬公高中、輔仁大學。一九九七年參加文學獎比賽展開文學之旅,曾獲時報小說獎、聯合報小說獎、吳濁流文學獎、國際書展大獎、金鼎獎等。
現居台北,栽培小樹,眷養青苔。
著有短篇小說《海事》、《地老》、《塗雲記》,長篇小說《流水帳》,以及散文集《瑤草》。
章節試閱
捕風
從山腳下的窩居搬至高樓,最覺不慣的是風,有時甚至到了心驚膽顫的地步。自己都不大相信,被偏激的風掐大的人?!大學的一個年初一風和日麗,我提議去走跨海大橋,真這麼做了,和朋友各帶一個來澎湖過年的親戚,一個大男孩和一個小男孩,那時的跨海大橋尚未拓寬,護欄沒這麼高,走上橋才知道,風導演的天滔駭浪簡直要將人颳下橋去,雖然兩名台灣客很信任我們,勇敢是裝不來的,回頭是岸。今日家常的風帶給中年人的恐慌居然更甚當時。
各個窗子吹進來的風各有不同的風味。旁無高樓,書房裡的風一來便是大江大海,瞬間滿樓,招架不住的...
從山腳下的窩居搬至高樓,最覺不慣的是風,有時甚至到了心驚膽顫的地步。自己都不大相信,被偏激的風掐大的人?!大學的一個年初一風和日麗,我提議去走跨海大橋,真這麼做了,和朋友各帶一個來澎湖過年的親戚,一個大男孩和一個小男孩,那時的跨海大橋尚未拓寬,護欄沒這麼高,走上橋才知道,風導演的天滔駭浪簡直要將人颳下橋去,雖然兩名台灣客很信任我們,勇敢是裝不來的,回頭是岸。今日家常的風帶給中年人的恐慌居然更甚當時。
各個窗子吹進來的風各有不同的風味。旁無高樓,書房裡的風一來便是大江大海,瞬間滿樓,招架不住的...
»看全部
作者序
等候新書排版進入編輯程序的一小段時間,我提筆在空白紙上列出幾個待寫的題材:「花之器」、「風」、「跳舞的雨滴與彩券」、「草」、「卡片」、「綠光」、「衣魚」、「鉛筆」,似乎都是名詞,一些物。
如此躍躍欲試,乃因這些東西背後的故事曾帶給我美好的記憶,比如再訪徘徊過的林中小路,沿途有斷斷續續留下的記號,且非麵包屑之類的食物,不怕蟲鳥蟻獸叼取,不怕迷路,相信很快即能到達目的地。更令人鼓舞的是,加上先前零零星星完成的散文作品,好像離下一本書也不遠了。忽然到了的心情勝過期待已久。
第一本散文集出版於二〇〇六年,在...
如此躍躍欲試,乃因這些東西背後的故事曾帶給我美好的記憶,比如再訪徘徊過的林中小路,沿途有斷斷續續留下的記號,且非麵包屑之類的食物,不怕蟲鳥蟻獸叼取,不怕迷路,相信很快即能到達目的地。更令人鼓舞的是,加上先前零零星星完成的散文作品,好像離下一本書也不遠了。忽然到了的心情勝過期待已久。
第一本散文集出版於二〇〇六年,在...
»看全部
目錄
自序
輯一
捕風
盆栽
鐵窗
如山蘇
花之器
羽衣
冬陽
包法利夫人掉下來
愛哭的小孩
吃水果
跳舞的雨滴與彩券
祖母臂
茉莉
鞦韆與吊床
小物欲
鉛筆秀
綠光札記
本事
輯二
竺肥菊瘦
石蓮
賣花的男人
書籤
幾盆有紀念性的植物
抹布
取暖
貓居
春天在母親樓上
阿清嫂與年夜飯
花生糖
畫牆與燈
十八個月亮
兒歌
找牙醫
好花
聖誕樹
識字
輯三
春天的三個名字
五月
小草盆
衣魚
年
憶苦餐
蝴蝶與彩券
畫像
颱風
微塵與白來
玫瑰
買名兼盜名
夾腳拖鞋
花床
桔梗
輯一
捕風
盆栽
鐵窗
如山蘇
花之器
羽衣
冬陽
包法利夫人掉下來
愛哭的小孩
吃水果
跳舞的雨滴與彩券
祖母臂
茉莉
鞦韆與吊床
小物欲
鉛筆秀
綠光札記
本事
輯二
竺肥菊瘦
石蓮
賣花的男人
書籤
幾盆有紀念性的植物
抹布
取暖
貓居
春天在母親樓上
阿清嫂與年夜飯
花生糖
畫牆與燈
十八個月亮
兒歌
找牙醫
好花
聖誕樹
識字
輯三
春天的三個名字
五月
小草盆
衣魚
年
憶苦餐
蝴蝶與彩券
畫像
颱風
微塵與白來
玫瑰
買名兼盜名
夾腳拖鞋
花床
桔梗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陳淑瑤
- 出版社: INK印刻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4-06-09 ISBN/ISSN:978986582376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08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