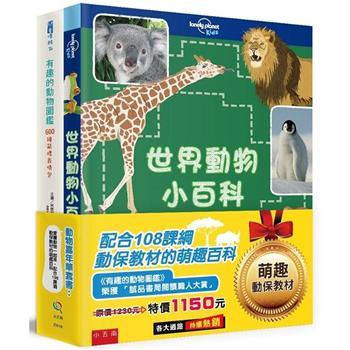推薦序一
從板車拉出的青春樂章/劉克襄
七〇年代初,就讀高中時,我經常回到瑞昌書中僅淡淡提過二三回的地方,九張犁。
那兒是我出生的家園,卻或許是他最不想回憶之處。至少,在我跟他聊及過往台中諸事時,從未聽他提及。但我必須從這個讓他父親傷心之地破題。
年過半百時,我畫了一張九張犁的簡圖,同時把周遭鄰居家族的居住位置繪出。我們家是長長的竹筒厝,在我五歲舉家前往台中時,有些屋頂搭蓋茅草,後來才鋪為黑瓦白牆之厝。有回,姑姑來台中探望母親,我取出手繪地圖展示,忍不住問道,阿嬤娘家的位置在哪?
阿嬤姓張,也是村裡的人,年輕時嫁到劉家。姑姑按圖指著我們家北邊不遠的地方,還提醒我那是間三合院。阿嬤是瑞昌父親的姑姑。
一如瑞昌在〈板車上的家族記憶〉所述,因為昔時家境貧窮,在大家庭的環境裡,其他房的人對他們並不友善。瑞昌的祖母那時不得不越過一塊水田,走到我們家,跟阿嬤賒一口米,借一把菜。或許是這一物質援助的情誼吧,後來瑞昌父親跟家父在台中各自成家立業後,便常像兄弟般的敘舊,偶有生活事業的討論。
至於,瑞昌在書裡提到,當祖父病逝台中醫院,其父親借板車拉回九張犁,竟被阻擋於大廳之外,不得安厝於內。受此屈辱後,他毅然帶領家人遠離傷心地的往事。我年輕時即耳聞,此等家族親情之澆薄。因而常和父親感嘆,這一昔時九張犁的憾事。
我經常回九張犁,因青光眼而失明的祖父仍獨居在那兒。我跟瑞昌一樣是長孫,總會受到家族最多疼愛,但責任亦背負最重。再怎麼樣繁瑣辛苦的照顧,好像理當都要做最後的承擔。那些年回鄉,我一定拎著蔬果,固定月初去探望,順便幫他清理家屋。又或者,帶他走動一下,因而對村子屋宅的分布也有幾分熟稔。
那回當姑姑指出瑞昌或許不曾去過的,我阿嬤的老家位置時,我彷彿也有了更具體的九張犁圖像,同時揣想著瑞昌父親帶著家人遠離村子的情境。
九張犁在我的印象裡,好像沒出過什麼人才,倒是有兩位兄弟綁架殺人,被判死刑,因而轟動一時。母親曾說我四歲時,這對惡童兄弟將我藏在某一處草寮裡,但那只是遊戲。我對他們印象挺好的,因為他們教我如何利用蜘蛛網捕捉蜻蜓。
瑞昌父親帶著家人搬遷到台中下橋仔後,瑞昌在那兒出生。我小時好像去過一回,因而有些模糊印象。之後,其家族再搬到南屯,那兒我便熟稔了。青春歲月裡的釣魚、讀書或打籃球,幾乎都在這一帶渡過。只是對照瑞昌少年回憶錄,我明顯少了一層狂野。
「一九八一年夏天的記憶,早熟的青春如哭過的月色……」
「就像電影裡渴望自由的暹邏鬥魚,在黑白鏡頭的運轉下,伴隨著重機車輪的奔馳,一路駛向大海。」
瑞昌從飆風少年描述自己的狂野,一路晃蕩到青年的熱血,文本鋪設了三條回溯自己成長的路線。許是持續溫暖的遠親關係,以及青少年的成長地圖如此大量重疊,我在讀瑞昌的文章時,感懷特別多面。也試著,想從這一微妙血緣的角度,凝視這一系列平易近人的回憶之文,進而摻入這等必須勾勒的隱私。
他的家族回憶,與我最為貼近。瑞昌父親的奮鬥,以及最後出走九張犁,在台中從黑手起家,年輕時我斷續從父親那兒聽聞。今日從此一文本,終有清楚的回顧。同一時期,父親也離開九張犁,因為擔任教職,舉家搬遷到台中。
瑞昌跟我一樣就讀同一國中,但我虛長他六七,過度乖巧守禮,讓我的少年時代如白紙般空白。從國中到高中,他的乖違不羈,卻在日後形成璀璨的奇幻成長。但那不是對一個年代知識的回憶或爬梳,而是用自己和夥伴青春肉體換取的生澀經驗,在書裡引領大家去發現和迷路。透過不同的事端,我們看到一個青少年的叛逆,在台中的探險地圖,卻也看到台中老城區的變遷風貌。
瑞昌北上讀書後,我才和他認識。那時我在自立報系任職,他則就讀大學。我退伍回台中,進入職場的第一份工作是瑞昌父親的幫忙引薦。瑞昌來找我時,我亦幫他介紹,跟著楊渡、李疾等人在各地從事報導工作。
好學的他從這兒開啟另一視角,延續著少年時代的好奇,觸鬚伸向各階層。八〇年代解嚴前夕社會運動到處迸發,重大政治環境議題亦浮出檯面。瑞昌不僅走進現場,見證這一階段諸多台灣的重要變革,也是振筆疾書者。後來他會成為一位優秀的政治記者,大抵是這時期的慢慢磨鍊養成。這一完整豐沛的記者生涯,或許可供有志社會報導的後進參考。
輯雖分三,實有一個圓心。再怎麼遠離,台中都是主要磁場。整本的書寫繞著它運轉,也繞著它自我修正。從這城市角度觀察,這一系列文章不只是瑞昌的青少年圖像,也是台灣快速蛻變下,回顧老台中變遷的小縮影。
推薦序二
我的人生行路夥伴/夏珍
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是互為左右的人生行路夥伴,轉眼竟是廿年前的事了。
那一年,我從台北南調中興新村,迎接修憲後的「第一次省長民選」,瑞昌很快後腳跟到,成為我極倚重的同事。台中衛爾康大火,死傷無數,我懷著女兒要到殯儀館現場跑新聞,瑞昌臉一沉說,「大姐,你別鬧了,肚子裡有小孩,就好好坐在辦公室。」於是乎,他一肩頂上成了「現場指揮官」。
我們的家都在台中,開開心心地回鄉要把地方新聞搞他一個天翻地覆。彰化福興鄉非法垃圾場被黑道把持,瑞昌帶著同仁深入險境,持續追蹤,硬是讓兩年沒人管的非法佔用公地的垃圾場關門,也為報社拚到一座吳舜文新聞報導獎,讓地方記者揚眉吐口氣。
新聞戰的確激昂人心,但我們都沒想到紮根於地方的時間這麼短。隔年,第一次總統大選,我又被調回台北,肚子裡的娃兒落地才剛滿月,卻無法扭轉北調的任務,因為修憲凍省大勢已明,中興新村這個「基地」遲早要收攤的,果不其然,不多久,瑞昌隨著我的腳步北調。
從此之後,我們倆成了「北獨派」,只有周末才相偕南下,基於尊重「男性尊嚴」,也為了偷懶,大多數的時候是由他掌握方向盤,開著我的小破車,一路聊回家。
每周兩個小時南下車程裡,我們無話不談,從政局到報館人事,從新聞檢討到觀點補遺。而我始終沒忘記那一年南下,瑞昌老爸慎而重之的特別請我吃一頓飯,把他的兒子交代給我的情景,老派人物的端肅誠敬,讓我對自己的工作都多一了份鄭重。
在新聞路線上,我們剛好兩端,他的主線在綠,我的主線在藍,對時局的看法時有歧異,卻恰恰可互為補強。二〇〇四年秋,他赴日本朝日新聞擔任客座研究員半年,電郵往返無數,多少也挑起我對日本這個彷彿熟悉實則陌生的國度的些許興趣。
在成長背景上,我雖長他幾歲,勉強還算得上是「同一代人」,但顯然也是兩端。他的家裡沒姊妹,我的家裡沒兄弟,這十幾廿年相伴跑新聞,人生各自多了一姊一弟,可這弟弟管起人來比姊姊還念叼,我念他要疼惜老婆,他就念我要疼惜自己。
有一回,夜裡下了班與同業酒聚,小飲兩杯,當年抓酒駕沒這麼嚴,我開車返住處,但瑞昌不放心,騎著機車跟在我車後,好確認我安全無虞,巧不巧碰上警察臨檢酒測,我搖下車窗,員警看都不看我,揮揮手讓我離開,我眼睜睜的從後照鏡看他被攔下來,呵呵,我安全回返住處,小老弟卻未躱過這一劫,災情慘重,他大氣都沒吭一聲,其人之重「江湖情義」可見一斑。
他念二中,在台中這是皮小孩念的學校;我讀曉明,在台中是出了名管得緊的女校。我老懷疑他慘綠少年時代是不是「混過」?他總笑兮兮的說誰高中沒打過架?他說,他是扁人而非被扁的,但看他一副「白面書生」相,實在懷疑他有多大本事扁人,這回好好看了《結拜——我的青春追想曲》,恍然大悟,各種路數的人物都可結拜,難怪他打起架來氣勢十足。
同樣的青春,他的風風火火;我的青春一頁一頁翻過去,蒼白得幾乎難以在記憶中停佇。連家裡姊姊都狐疑的問:「奇怪,我最慘最慘在拚聯考的時候,你在哪裡?為什麼記憶裡沒你?」我可不是石頭縫裡老了才迸出來的毛猴子,那幾年,我可憐巴幾地住在學校裡,「享受」獨立自主的人格與人生,這大概算是我最大最大的叛逆了,老媽為了我堅持住到離家門騎自行車不到十五分鐘的學校去,足足哭了一個月,倒楣的是,沒了爸媽的管教,卻多了修女的框架,簡直逃都沒處逃,完全失策。
他的偶像是高凌風,我是看到高凌風就頭痛,〈冬天裡的一把火〉尤其讓我抓狂,鳳飛飛都是到老了才感覺她的好。他的日本是流動的,我的日本卻是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源氏物語》……,十六歲女孩聚在一起討論的是「介錯之美學與力量」,神經病到無以復加,還好「自殺小組」討論將近一學期之後,考量到各種方案之殘忍與疼痛,非有超人般的勇氣與毅力難以達成,結論是:一頭栽進垃圾桶悶死會不會好過點?
我的搞笑青春就是這種雞毛蒜皮的「耍嘴創意」,當年劉墉大紅,短語片句的「人生是……」,隨便仿著寫就是一大本,讀書心得忽而林語堂全集「套評」、張愛玲小說「集評」、高陽歷史小說分冊「點評」,唬得國文老師一愣一愣;這學不夠,還要比擬《紅樓夢》,把女孩們全套個花神,百花榜讓全班競搶;女孩們不知是樂了還是怒了,校慶表演,她們迷上了林懷民還迷上了余光中,仿雲門編舞,丟了一本《蓮的聯想》,要我改寫詩成舞的序曲引言,余光中的詩還改得了嗎?抓破頭三天,就徹底斷了我的文學夢,十六歲的女孩兒們,說有多殘忍就有多殘忍。
他的青春在街頭,我的青春很早就趕上了此刻流行的「宅」,連人生的第一根菸都是因為同學在校外抽菸被記過,躲在家裡廚房偷拿老爸一根長壽,半嗆半吞抽完後,隔天到校完好如常,到現在我還是搞不懂,為什麼我沒被記過而她被記過?只有一句話能形容:笨到掉下巴。
完全不搭的兩路姊弟,卻在新聞路上相遇,政治,是我們永遠不膩的話題,生活則是消遣,在政治與友誼的權衡中,我們有著完全的共識:什麼叫朋友,錯了也相挺到底!還好,錯的都是政客。人生行路多艱難,有友相伴不寂寞,祝福我的結拜:瑞昌的青春追想。
(本文作者為「風傳媒」總主筆)
後記
當青春已不再
關於青春的追憶,最早是從〈我那住在豬屠口的同學〉開始,因為每次一群人閒來無事練肖話時,總是把這段江湖奇談當話題,眾人聽得津津有味、放聲大笑,彷彿那「日夜雙修、工讀兩棲」的阿丁重現眼前。有一回,酒過三巡、話題再起,衝著副刊同事的建議,就這麼動筆寫下來,誰知一發不可收拾,竟然滔滔不絕地連寫了兩年多的「青春追想曲」專欄。
少年荒唐事的話匣子一打開,最感驚訝的是我阿母,最初她看完會笑說:「喔,天公伯保庇,好加在你沒有去做流氓!」後來她越看越覺得離譜,原來一直被蒙在鼓裡,打來電話消遣我:「你哪有這麼多『有空無榫』的代誌好寫?」其實我那聰明伶俐的母親老早知道她兒子沒那個能耐去闖江湖,終究曉得這個好勝叛逆的長子不過是花果山下的野猴子罷了。
然而,如果沒有阿母一輩子的佛心,我放蕩不羈的青春不可能還找得到回家的路。就像十八歲那一年,我即將離家前往梨山時她紅著眼眶說的一句話:「你們父子倆長年衝突,我是做石磨心,你敢知影?」在母子交心的對話當下,我淚崩了,「為母如石磨心」,從此鑲在生命軌跡中,叫我牢記這份慈恩。
因著母親的愛、諒解與包容,我才得以擁有一段敢於冒險的青春旅行,並且在人生過了中場之後開始追憶,進而動筆寫下家族的集體記憶、結拜兄弟的情義和初涉江湖的洗禮。
每一篇的「青春追想曲」宛如我生命成長的單格漫畫,這個月是高中死黨阿榮,下個月是國中同窗老夏,經常跑出來串場的是番仔火。每幅畫像歲月的定格,暗藏著時代的密碼,那些橫跨一九七○至九○年代的社會現象與群體記憶,譬如「客廳即工廠」、「餐廳秀」、「電玩小蜜蜂」、「搖滾樂與校園民歌」、「地下盜版錄影帶」、「A片性感女神」、「三冠王棒球熱」、「美麗島事件」,以及剛萌芽的反核和環保運動等。
我的青春記事當然也有屬於我們那個世代所擁有的生活體驗,包括升學主義下的苦悶壓力、軍旅生涯中的糗事趣聞,乃至愛在心裡口難開的青澀戀情等。這些看似再尋常不過的成長經歷,雖然是一般四、五年級生都曾有過的生命史,但對我而言,卻是一趟漫長又苦澀的青春之旅。不論是大學聯考、入伍當兵或是戀愛,我總是一路跌跌撞撞,未曾間歇,奮力在貧瘠的土地裡開出花朵來。
為了追想昔日的青春故事,我因而經常返鄉去尋找逐漸失落或模糊的記憶,聯繫最多的無疑是我那一群從少年時期就結拜至今的死黨,有時幾個歐吉桑重新聚在一起,聊起三十年的往事還不忘插科打諢,互相漏氣求進步。然而,當年在關老爺前義結金蘭的少年家,如今若不是兩鬢添霜、身材中廣,就是齒搖髮禿、擔心三高指數破表。我望著這群死黨,個個臉上兩道法令紋刻得出滄桑,既為家裡生計忙碌終日,也為子女前途憂心忡忡。只有重聚換來時光倒流的剎那,才讓我們深深地體會,當青春已不再時,唯有情義永流長。
也正是「情義」這兩個字,引領我從少年走到今日,屢屢在生命旅程的轉折處隱隱地觸動著心底那根弦。畢業典禮前,那次面對教務主任凶狠的拳頭,寧可挨揍也不能出賣同伴;及至北上求學,遇見素昧平生的阿伯載我去國術館療傷,讓我想起父執輩出身黑手的辛酸。我常覺得,情義之於我,已是植入自己生命底層的DNA,因為有情義相伴,始能在職場叢林中仿若孤懸一身卻不寂寞,也才可以真正領悟出門在外靠朋友的拚鬥意義。
儘管我的死忠兼換帖,有些人已不知去向,猶如辭根散作九秋蓬,但留在家鄉而且還經常連絡的死黨們,卻像同一國的棋子般散落在人生棋盤上,默默地圍成一個隱形的兄弟圓,然後支撐著我這樣長年在異鄉走闖的遊子,有個去處可以慰藉鄉愁。那是一種沉靜相挺的義氣情誼,多年後的職場相逢,在某個皎月當空的中秋夜,當我與三位兄長舉杯邀月、歃酒為盟,又重溫那結拜的感動時,即使沒有年少舉香齊眉的豪氣干雲,卻多了幾許久經歲月風霜後的人間情義。
有時想想,談結拜、論情義,自己有一半的基因源自父親,而我若真有絲毫江湖味,那大抵也是循著父親廣交好義的生命模板依樣畫葫蘆。近些年,父親的健康狀況大不如前,他那壯碩的身影顯得有些老邁,記憶力也開始退化,我寫家族故事讓他有了回憶,找到生命最初最艱難的那一段。有些與家族相關的故事見報那天,阿爸一讀再讀,據阿母事後形容:「你爸讀到目眶紅,文章都快要背起來了。」
我的孩子也是如此,小兒子讀過我夏日去梨山打工的記事後佩服地說:「你們那個年代是奔放的!勇於上山當苦力,朋友感情又如此好。」我不知道他是否曾想起自己跟著紙風車劇團下鄉表演的辛苦經驗;他的死黨自組了一個太陽花樂團,早在太陽花學運還沒出現之前就到處走唱,但看了他老爸的狐群狗黨當年也曾搞過一個北半球樂團去百貨公司擺攤賣藝,他欣羨不已地說:「嘿,你們還真不賴,有人幫你們畫海報、做模型,搞行銷宣傳耶!」
不同的世代卻有相同的生命軌跡,父親與我、我與孩子,一家三代之間以看似迥異但又相互交錯的閱讀心得,連結了跨越世代且緊緊依偎的生命臍帶。在這一路書寫的旅途裡,我既為父親艱苦奮鬥的青年人生留下雪泥鴻爪,也從自己和孩子的心靈對話回溯了早已遠離的青春。
我喜歡文字工作,也愛閱讀生活,退伍後進入媒體這行業一做就是二十五年。直到每個月在副刊的書寫,才發現那已成了忙碌工作和繁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逃生門,彷彿只要打開這扇門,就能看見藍天、聞到花香,並且在蟲鳴鳥叫與蝶飛蜂舞的環繞下,優游地享受一種赤腳踩在柔軟泥土裡的幸福感。因著這持續不斷的書寫動能帶來的幸福感,撫平了我慘綠年少的生命傷痕,也咀嚼了人生成長的苦澀滋味。
總結地說,這是一部「五年級生」的生命回顧史,也是一個羈旅天龍國的台中人穿越時空、重返家鄉的青春記事。在苦短的人生裡,我何其幸運,有上蒼的疼惜與眷顧,那個十七歲的大男孩因此能克服心中的恐懼與迷惘,勇敢地走到今日,並且書寫來時路,再次告別苦澀青春,告別蒼茫年代。
既然來到謝幕的這一刻,最該感謝的是我的頭號讀者兼校對苦工,我那結縭二十年的妻子,如果沒有她無悔的支持,這伏案書寫的日子仍是孤寂困阨,不知何時能破繭而出。當然,還有許許多多一路曾陪我走到這裡的人,無論相交深淺,無論天涯海角,都讓我敬你一杯,感謝你的情義相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