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空繁星閃耀
收在這本書中的,是一些談音樂的文章。
我常聽音樂,以前寫的散文,也有談音樂的部分,不過多是隨興所寫,事先沒有計畫,事後沒有整理,浮光掠影,往往不夠深入。友朋之中常勸我稍稍「努力」一點,不要像以往那樣輕描淡寫為滿足,我就試著寫了幾篇篇幅比較長也比較用心的聆樂心得,但畢竟不是學音樂出身,裡面免不了總有些外行話。我身處學術團體幾十年,知道知識雖可救人迷茫,但所形成的壁壘既高且深,是不容外行囂張的。
寫了幾篇談巴哈的,也寫了幾篇談貝多芬的,看看還好,但發展下去,就有了問題,因為可寫要寫的東西太多了,光以巴哈來說,討論他的幾個受難曲,便可以寫幾本厚厚的書,短短一篇文章談他,不浮光掠影的,成嗎?還有,有關研究古典音樂的書實在太多了,快二十年前,我到美國馬里蘭大學探視正在那兒求學的大女兒,乘機參觀她學校的音樂圖書館。這圖書館所藏書籍很多,我發現光是研究貝多芬的英文專書就占滿了一整面牆壁,要仔細看完,至少要花幾年的時間,但還不夠,德文、法文還有包括義大利文的專書,也是汗牛充棟的,弄通那些,要比古人皓首窮經還難。
假如最後真得到了孔子所說的「朝聞道,夕死可矣」的那個「道」,皓首還不算白費,問題是往往「空白了少年頭」,門道也不見得摸得著,那就悲慘了。學術強調專精,有時自鑽牛角尖而找不到出路。我曾看過一篇討論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米開朗基羅的論文,論文主旨在強調工具的重要,說如果沒有一種特殊的鑿子與鎚子,米開朗基羅絕不可能雕出那樣偉大的作品。所說不見得錯,但他忘了,這兩把同樣的工具握在別人手裡,並不保證能完成跟米開朗基羅一樣的作品。這又跟我看到另一篇討論貝多芬鋼琴曲的論文有點相同,論文說貝多芬在第二十九號鋼琴奏鳴曲上特別標明了題目:《為有槌子敲擊器的鋼琴所寫的大奏鳴曲》(Grosse Sonate für das Hammerklavier),是因為他從友人處獲贈一台能發特殊強音的鋼琴,因而寫了這首大型的奏鳴曲,結論是貝多芬如果沒有這台鋼琴,就不可能寫出這首繁複多變的曲子。這也沒有錯,其實改以木槌敲擊鋼弦的鋼琴在海頓與莫札特的時代就有了,貝多芬得到的是特別改良的一種罷了,鋼琴到這時候,已接近現代的鋼琴了,能發出十分巨大的聲響,當然影響了貝多芬的創作。但我認為對貝多芬而言,這事並不重要,個性與才情,才決定了作品,要知道就是讓莫札特同時用同樣的一台鋼琴來創作,他與貝多芬的作品也絕不相同的。
專家所談,大約如此,有所發明,也有所蔽障。其實有關藝術的事,直覺很重要,有時候外緣知識越多,越不能得到藝術的真髓。所以我聽音樂,盡量少查資料,少去管人家怎麼說,只圖音樂與我心靈相對。但討論一人的創作,有些客觀的材料,也不能完全迴避,好在音樂聽多了,知識聞見也跟著進來,會在心中形成一種線條,變成一種秩序,因此書中所寫,也不致全是無憑無據的。我手上還有一本1996年出版第四版的《牛津簡明音樂辭典》(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Music),一本Gerald Abraham 1979年編的《簡明牛津音樂史》(The Concise Oxford History of Music),查查作者生平、作品編號已夠了。
寫作其間,一友人建議我在文末附談一下唱片,說這一方面可以讓讀者按圖索驥,以明所指,一方面可使這本書有些「工具」作用,以利銷售。我先是不願意,後來想想也有道理,我平日與音樂接觸,以聽唱片為最多,所以對我而言並不困難。關於唱片的資料與評鑑,坊間很容易看到有美國企鵝版的《古典唱片指引》(The Penguin Guide to Recorded Classical Music)與英國Arkiv Music所出的《古典老唱片》(The Gramophone Classical Music Guide),後者標明「老唱片」,通常指的黑膠唱片,但我書中所舉還是以現今市面所見的CD為多,就以我手中的這本2012年的Arkiv Music版本,大約談的都是CD,當然CD之中有部分是由黑膠所翻印的。我平日不太信任指引這類書,這種書都是由許多不同人所寫,各人的好惡不同,有的只注意錄音,有的只欣賞技巧,拼湊一起,其實是本大雜燴,過於聽信他們的說法,反而模糊了該聽的音樂,所以這類書當成參考固可,信之太過,反而削足適履,得不償失。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處理藝術時,這句話顯得更為真切。
音樂是寫出來讓人演奏來聽的,聽音樂是欣賞聲音的美,但有時不僅如此。好的音樂有時會提升我們的視覺,讓我們看到以前看不到的東西,有時會提升我們的嗅覺,讓我們聞到此生從未聞過的味道,有時又擴充我們的感情,讓我們體會世界有很多溫暖,也有許多不幸,最重要的是,音樂也擴大我們的想像,讓我們知道小我之外還有大我,大我之外還有個浩瀚的宇宙,無盡的空間與時間,值得我們去探索翱翔。人在發現有更多值得探索的地方之後,就不會拘束在一個小小的角落,獨自得意或神傷了。
克羅齊說過,藝術是在欣賞者前面才告完成。這話有點唯心的成分,但不能說是錯的。如果視創作為一種傳達,而欣賞就是一種接受,光傳達了卻沒人接受,像寫了很長的情書得不到回音一樣,對藝術家而言,石沉大海是他最大的懲罰。因此欣賞者無須自卑,他雖然沒有創作,卻往往決定了藝術創作的價值。
這本書很小,所談當然有限,第一輯談的都是貝多芬,卻也只談到他的交響樂與弦樂四重奏而已,第二輯因談巴哈,也談了幾個有關西方宗教與音樂關係的事,第三輯是十二篇記與音樂有關的短文,這些文章湊在一起,看了再看,覺得除了欠缺深度之外,又欠缺系統。我覺得書中談巴哈、談貝多芬與馬勒的稍多了,談其他音樂家的就顯得不足。譬如布拉姆斯,只有第三輯中有一篇談他,他是貝多芬之後最重要的作曲家,我沒有好好來談他是不對的,我其實寫過一些有關他的文章,但權衡輕重,發現放在這本書中有些不搭,就捨棄了。在德奧音樂之外的俄國作曲家如普羅高菲夫及蕭斯塔高維奇,還有西貝流士與德伏乍克,以及法國的佛瑞或德步西,英國的艾爾加與布列頓等等的作品,我都常聽,而且還曾用過心。我一度對現當代作曲家如荀伯格、史特拉汶斯基,或現在還在人世的布列茲(Pierre Boulez, 1925-)感到興趣,他們對十八、十九世紀以來的音樂,往往採取了另一方向的思考,喜歡在原來的音樂元素中又增添了許多新的材料,作風大膽而前衛。近代音樂還有不少「怪胎」式的人物,譬如凱吉(John Cage, 1912-1992),他在鋼琴琴弦上插上各種物品,彈琴時不正襟危坐,又把琴蓋掀起,用手去亂撥琴弦,這些人為了樹立新觀念而不惜與傳統決裂,他們的舉動看起來離經叛道,但也很好玩,在思想史、藝術史與文學史中,有同樣行為的人很多,議論其實也很近似。上面這些問題原都想一談,但遺憾沒有談到,原來一本書是無法道盡人世的滄桑的。
對我而言,音樂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東西,本來不在我生命之中,但由於我常接近,不知覺中已滲入我肌膚骨髓,變成我整體生命的一部分,影響到我所有的行動坐臥。幸好音樂包括所有的藝術給我的影響,好像都是正面的。藝術帶來快樂,帶來鼓舞,大家視作當然,萬一藝術表現的不是那麼「正面」,我們該怎麼看呢?成熟的藝術不是童話,都可能有陰暗與痛苦的一面,我覺得那些陰暗與痛苦是必要的,有了這些,世界才是立體與真實的。藝術一方面領我們欣賞世上的優美,一方面帶領我們體會人間的悲苦,當一天苦難臨到我們頭上時,我們便有更大的勇氣去面對、去超越。
人類最大的困窘在於溝通,愛因斯坦曾說過,我們要為一位天生盲者解釋一片雪花的美麗,幾乎徒然。因為盲人是靠觸覺來填補視覺的,當讓他用手指去碰觸雪花時,那片脆弱的雪花便立刻融解了。用文字解釋音樂也有點類似,解釋得再詳盡,卻也只是文字,不是音樂,最怕的是音樂像脆弱的雪花,禁不起文字的折騰,已全然消失了。了解音樂最好的辦法是聆聽,是以直覺與它相對,以其他方式來描述、來形容,都是多餘。
路遙夜深,寒風正緊,見到頭上群星閃耀,便覺得走再長的路也不會困乏。音樂給我的支撐立力量,往往類似,這也是我為這本小書取名《冬夜繁星》的原因。
2014年4月 序於南港暫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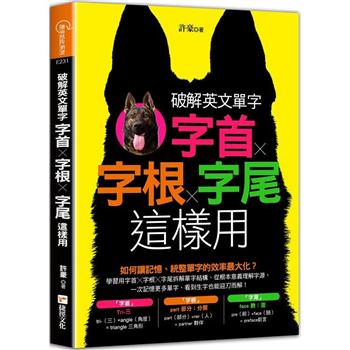





![114年國語文歷年試題解題聖經(十四)113年度[教師甄試] 114年國語文歷年試題解題聖經(十四)113年度[教師甄試]](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08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