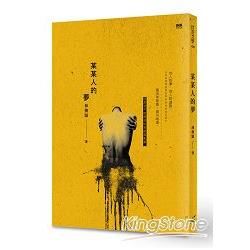《人的夢》之一 補夢人
整個下午,他與他等待雷響。
等雷響將兩人貫穿,胸腔打開如同大海。
間歇的只有珊瑚枝狀的閃電,鞭亮了潛伏著暗礁的海岸,一瞬間的銀色大海。
大雨下在遠方的海域,因為嗅到了海風送來的雨點混著淡水的清新氣息。
銀白電光照亮了同梯好友曝曬、海浴了長長一整個夏天之後如同海豚的身軀,緊繃,光滑,跳進滾來的海浪裡時,那弓背繃出的脊骨好像一條鑄鐵,隨即又被吐在沙灘上。同梯如此與大海搏鬥甚久而吁氣,下腹部的性器冷縮一如果核。
他希望握住自己劇烈跳動的心臟,像一隻驚慌而輕狂拍翅的巢鳥。
以為意志控制了它,感覺它遂像是遭焚風收乾的堅硬花苞。
海浪的白沫裏,同梯不動了,多純潔的葬禮啊,他在心裡嘆息。
海上的烏雲就像那些夜晚,同梯睡在他身旁,隨著呼吸而發熱的身軀是白天奔馳過了一個沙漠的一具引擎。
伸手過去,紗窗外墨黑的芒果樹群的葉叢裡有花緩緩開著,累累沈重開著,若有似無的花香穿過腦殼。
海邊其實非常腐臭,堆積著多年無人撿拾的漂流木爛穿了成為洞窟,勾纏著多種塑膠物,死去的招潮蟹仍在等著返回大海。
前一年的秋颱之後曾經沖上大片遭海浪洗淨的豬屍,豬身發酵膨脹,海灘遂成了妓院的午後通舖,張開的豬嘴似乎集體做著美夢笑開了。
他們的單位銜命坐卡車、戴防毒面具來清理。強風掃淨了的海天一如太古時,紫外線沸騰,大家彎腰嘔吐光了肚裡的早餐,淚眼中看著矮儸老排附上刺刀挺進,俐落戳刺著死豬群,一挑,收刀,再挺刺,老屁股跟著律動。同梯跟進,汗水披掛下兩顆大眼,踢翻一頭豬屍讓牠腹部朝天,膠鞋底蹂躪牠一排乳頭,「做兵三年,母豬賽貂蟬,貂蟬你娘咧。」
海上的天空指甲刮傷般有一弧月影。
他往蔓延著馬鞍藤且紫花盛開的海灘上方跑去。
防毒面罩裡熱氣瀰漫令人窒息,失去知覺之前,他看見同梯一腳踢破豬腹,踩進去,嚇得朝後一顛,不遠處海平線上晃盪著一艘膠筏漁船。眾兵散開,各自擇定一隻豬屍,那臂肌不成比例墳起的瘦小伙夫大叫,割下了一顆豬頭,高高舉起頂在頭上如起乩。
整片泛著清藍光的灘岸,眾兵頭罩黑膠面具如同外星人,濾嘴就像豬鼻,比賽割那些憨笑的豬頭,試圖當球拋,他們沒料到豬頭的重量,甸甸地一滾,靜止了如同佛頭側臥沉睡。那個愛炫耀他偉大男性的老兵掏出來轉圈灑了一大泡尿。另一老兵刺刀指著那個性器根部有刺青的譙,好膽你幹一隻予我看。刺青的應,欲幹就做夥來,一雙對對啦。
海風止息,軟弱地撲上岸的浪沫雪白,無頭豬的下肢交疊,彷彿有著少女矜持的嫵媚。他又看見同梯與一兵抬起豬身,一撕,豬身裂開,一團臟器掉下。他以為最後看見了一個豬頭人身在沙灘上搖晃走著,伙夫兵摘下面罩,三角眼兇光怒放,猱身一躍,一刺刀戳進豬頭的兩眼之間。
他始終不知道是誰在他背部等同心臟處重重一椎,他悶哼一聲,倒栽蔥滾下灘岸,滾進一個噩夢,那剖開的滿滿是美麗白蛆的豬肚等著他滾進去。
終於,雷響了,悶悶的,像極了一個未成形的噴嚏。
同梯閉目仰躺波浪上彷彿一條銀色魚屍。
在青壯生命最初最好的時光,據說這世界的戰事已經凍結,但他們遇見,因為一道命令徵召他們一起去遠方。
連下了幾天雨,陰潤的大清早,古老慘澹的車站,夜蚊孳生,鐵道後水泥柵欄下遍開著骯髒的變葉木,犁過的水田結了一層厚韌的膜,吸收著所有的光成為一塊幻鏡,讓天地顛倒,最早醒的一批鳥游移其上。弟弟騎機車載他來,霜風撲了兩人罩了一層冰殼,卸下他時,弟弟皴乾的手從口袋摸出一個紅膠袋平安符塞到他手心,講,媽叫你得掛著。
漸漸車站內集結了報到的人,嘴唇為粥氣與漿液糊住,只發得出似乎昆蟲翅膀摩擦與搓手搓腳的聲音。冷空氣裡都是少年男體剛烈的味道。他看見日後是同梯那黑得釉亮的方臉,兩頰的肌肉倔強。之後緩慢且搖晃的列車上,同梯沉睡得頭倚放他肩上,平穩的呼吸,車窗外向後移動著狹窄的平原、單薄的綠樹,醜怪的廟寺,鐵皮屋頂上陰翳的日光,他心裡啄殼而出一隻新生的獸,在胸腔囓咬,翻滾,頂撞,讓他痙攣,嘴巴發苦,因而扭曲了窗外流逝的景物。
列車經過小站不停,他聽見尖銳的哨音,長椅上坐著失神的候車者,一瞬間,在另一列靜止的列車濺著銀光的窗玻璃上看見驚惶、瑟縮的自己如同鬼影。肩上同梯的頭好沉重,雖則心裡有著沉甸甸的喜悅。但此後他惑於那樣的故事畫面,遭囚置古井底的鬼物在第一道日光射入時灰飛煙滅。
然而所有的想望與慾念確實唯有在暗夜才能夠如鬼魅叢生,他並不以為恥辱,甚至有所期待,如同草間螢火蟲的冷光。
營區寬闊的草地吸收了一整個暑天的炎陽之氣,他們受令仰躺其上,圍牆外紅色脊土種著低矮作物有某種窸窣,一軍官,深刻如刀疤的法令紋教他們重複直腿挺腰,突發一句驚人之語,有本領給我將天空肏出洞來;巡到同梯旁,突然一手抓住他的胯下一提,同梯悶哼一聲。軍官暴喝,起,挺住。某個週末,突然宣佈放假,匆促的午餐之後,同梯張大嘴要他幫忙夾出喉嚨的一根魚刺,含淚譙,臭腟屄。
寒涼了,晝短夜長,燈光初萌的時刻,整片營區只有黑影,人聲嗡嗡如蠅群,單槓掛著兩條人身,雙腿剪刀鉸著對方的腰,鉸成功的劇烈搖動全身,猿猴腿剪揚起鉗住對方脖子,眾喊,幹下來。敗者下頦跌擊沙堆,一口血沫。
只一盞黃燈泡的粗糙浴室,池底池壁長著青苔的蓄水池,每兩週洗衣兵穿著高筒膠鞋猴蹲水泥池邊,持一支竹竿攪著浸泡的衣褲好像福馬林泡屍池。背後看到老排附兩腿岔開下垂的一累性器晃盪,都驚駭詫笑,他看得清晰的是同梯鼓實臀部有一塊烏青胎記。畫虎卵臭蓋,當年觸犯天條,被太上老君踹下南天門。
那彷彿永遠不會天亮的行軍,因為沒有具體的敵人,因為每人都知那是無謂的兒戲而漸行漸渙散,如同民間故事鴨母王以竹篙驅使的鴨群。遠方矮矮的山脈稜線,山背後的曉雲如螺髻,田地飄著濃重的雞屎味,他相信唯有他一人是喜歡走路的,在這片已無空白、祕境的土地上,只是為了可以親近與緩慢。走在他後面的同梯則敵不過凌晨的睡意屢屢踩上他鞋跟,一踉蹌,額頭撞擊槍管上的準星,一點血跡在稍後初升有著溫暖香氣的太陽照耀下,讓同梯的頭臉像個神偶。
營區大門前的灰白公路,日正當中,毫無遮蔽的路邊杵立著一個光礫頭顱如苦瓜的出家人,不知從何而來的風吹得他一襲海青蓬飄,好像一朵烈焰,也不知他究竟全心全意在等待一個什麼。
但同理心告訴他,老和尚內心持有某種不可說的信念,枯木待春。
午夜,電話響,弟弟飼養的白鳥並不驚醒來啼叫而是感應般的拍翅,鮮紅的鳥喙神經質的空中點啄著。
屋後露台看下去,一長街夜市夜夜有如一長條燒透的紅炭,蔓延到窗下是一座香火燻得焦黑的福德宮廟,傍廟牆一家牛肉湯攤子,湯頭鮮美,有一日來訪推銷的年輕業務員說,當然好食,就是摻了我公司的化學香料。母親捶著大腿,罪咎看著父親,紅著臉喃言:「夭壽喔。」常常母親拿著一隻白瓷碗去買回來,滿滿一碗端給父親喝得額頭津津生汗。父親只是笑一笑。大姊夫縮著肩剔牙,「謀殺親夫喔。」
同梯在電話裡的呼吸如同風管破了洞,猛然打個酒嗝,射擊子彈的力道幹譙,臭膣屄。他將才抽了兩口的菸擰熄在窗台上,牛肉湯攤頭坐滿了一板凳咻咻喝湯的人。臭膣屄。
同梯的妻側躺在沙發的衣服堆上,蜘蛛似的細長手腳;顴骨緋紅,擦了鮮紅指甲油的赤腳踢同梯,喊一聲喂,意思是倒酒;同梯故意斟滿,她一滴不灑潑,一口乾了,舌尖舔了上下唇。妻的酒量非常好,未曾輸過他,婚前兩人喝酒,他舌頭開始漲大時,她扶著他的頭,吸一大嘴再一口一口餵他,她的舌好像蚌足,他心思遁走剩一個寄居蟹空殼。同梯抓一樣小物件丟她,她手一抖,酒液濺了一臉,咯笑著拉出一幅布拭了拭,一伸腳踢得更用力。垃圾諸嫫,臉色豬肝紅的同梯瞪著她譙。
電視螢幕一對男女賣藥兼歌唱,她調大音量,大腿夾緊了一個抱枕,眼光迷濛看著男主持人。
十歲卻已經胸部開始鼓凸、屁股翹圓的女兒睡醒了,臭臉從房間走出來,海狗趴在茶几上,信手抓起花生殼、蜜餞果核丟擲,朗聲,兩個酒鬼,兩個醜鬼,最好一起酒精中毒一起下地獄。你做夢啦,唱歌難聽死了,狗聲乞丐喉,那種爛節目找你去錄影還不是騙你買藥,笨死了,不會播出來的,你等下輩子吧。妻笑吟吟,閃電揚手給了女兒一巴掌,啐,幹你娘。女兒翻落地板,隨即起身,仰著頭,臉頰清楚的紅斑手印;兩腿夾緊慢慢痙攣了,夫妻才聞到一股屎味,女兒一手掏內褲底,接了一掌新鮮的糞一把甩給妻。
妻尖叫,螳螂跳起。女兒用全身力氣也尖叫,高頻率剃刀般割了他耳朵,才咯咯咯一直笑。同梯抿一口酒,笑了。
枯井底仰望那發黴的月亮。他打開後車廂,蜘蛛妻的頭塞在女兒剖開的肚子裡,細長四肢與女兒豐腴手腳捆一捆老榦新枝,平板的胸,乳頭像一粒疣,母女血液凝結成一層膠凍。同梯切下一塊,刀尖挑起給他食。兩人咀嚼著,面如芙蓉。
妻的母親總是纏著花布頭巾,讓顴骨更高聳,一雙大雨後山林泛綠光的眼睛,警犬般嗅遍了房子,立在客廳,與嚼著檳榔的隨侍男弟子交換眼神,然後喃喃著雙手比劃符咒,敵視著同梯說,你真孽。數日後男弟子單獨搬運來一座大石鑿成的盆子,靠牆安裝了小型馬達,務使活水不斷,投注了水萍與大肚金魚。金魚每日一死,浮屍無人收,腐臭一池,孑孓的培養皿。男弟子再來,平頭卻髮根密如稻秧,濃眉汗濕,撈起魚屍,投入新魚;等到魚全數暴斃,男弟子再來。妻笑如春花,讚他狗公腰喔,仰頭張大嘴,男弟子將一尾金魚投入。兩人出門,水泥地一前一後、一大一小的泥沙腳印,跨騎上機車,妻抱著狗公腰,呼嘯遠去。
一長街夜市的火光熊熊,現在,等待是一頭熊大而且溫暖的獸環抱著他,不似從前快速將心磨成針。直到在窗台捻死一排整齊的菸蒂,他下樓,昏暗街角找到同梯熄火的車子,知道他必然左腳提高踏在儀表板上,椅背放倒躺下但沒睡著。
他指關節敲敲窗玻璃,同梯期待他的眼睛凜然一亮,身軀卻像寒冷海水下的一塊暗礁。
上次同梯來,全家正在轟轟車流聲中晚餐,折射進牆壁上的夕陽一抹胭脂。肩扛一箱進口牛肉,碰的放桌上,解釋是給一個做貿易的朋友捧場,認購了幾箱,開車繞一圈分送親朋好友。打開紙箱,要全家人看那分佈均勻的脂肪像霜淇淋,真嫷。說起那一台不鏽鋼肉片切割機,推送刀刃的聲音爽脆,好像金牌體操少女的俐落動作。
等綠燈時,店招的霓虹燈光瀑將同梯擱在方向盤的雙手染得血紅。
同梯說尾隨到妻娘家,柚木地板一層霧光,倒映屋旁大樹,妻的母親帶他入內室,臉上封了一層蠟,不再招呼他,加入妻與男弟子狗公腰靜坐,各自盤腿一個蒲團上。樹上有鳥生命力強旺的叫著,太強烈的冷氣與薰香令他想要嘔吐,妻換了一身潔白棉衣,兩頰罕見有著經過劇烈運動後的血色,回望他時卻視他有如穢物的無情眼光。數日後,妻回家,又癱躺在沙發的衣服堆上,他聞著一屋腐臭,女兒拿著電話肉顫顫像果凍跑來,歡叫著師兄來電,童音音質如同新紙,邊緣銳利割人。同梯抓起一瓶酒,捶擊妻的頭顱之前,先槓打桌沿。那姿勢有如在強大氣流中俯衝山谷的鷹,不顧一切,以為之後將是無限寬廣。
同梯婚後,兩人斷絕聯絡逾十年。有一年半,他外派去飛航需一日夜、大島城轉機的熱帶海岸城市,管理三四百人的工廠,配有傭人司機,每三個月有一次休假。氣候、植物、地貌與貧窮和三十年前的家鄉相似,同樣的椰子樹與鳳凰木,懶洋洋、昏昏欲睡的漫長下午,但從沒見過如此耽溺今日及時逸樂的人民,對明天絲毫無所謂。一個愛說話的員工告訴他,工人週日的娛樂是集資租個旅館房間擠得滿滿看錄影帶。休假時他常飛去大島城找一位老朋友,公寓大樓如同墳塚,終日自己一人在街上無目的走路,走遍上中下城,走得衣褲汗溼又乾了,樓叢空隙間吹起混著酒味的風,吹起降落的野鴿子。傍晚的蒼黃光照,亮燈前照亮所有牆與窗,一家工藝店舖的門窗全是收納一顆心的小方格;走琴弦大橋,黃昏時在河海邊的高地坐定,眺望對岸狹長的島城末端,心有著一個填補不了的空洞。一次飛機落地,一邊機翼突然冒煙,大家拿著鞋子從機腹逃生門滑梯下去,狂奔一段,喘氣回頭,他看見黑煙裡同梯跑來,他熟悉他頭略微左傾、隱隱一股怒氣的樣子。他覺得自己那心的大洞大風呼呼颳著。
奔跑的時候,時間與風景緩緩逆流,襪子與褲管是野草的倒鉤刺,刺裡藏著種子,他去到那裡就繁衍到那裡。
之後認識了一位來經營農場的同鄉,數次見面源源本本告訴他移民的故事。一個黃昏,與同鄉全家晚餐,地平線開闊,夜晚遲遲不來,歸巢的飛鳥叫得清脆,圍桌的一家人身上有著太陽光的熱力與重量,下一代每個人好健康好無憂無慮,食量好大。他既有了個位子,一桌人也當他是親人。暖暖地聯想到古時以糯米、糖、蚌殼粉調和糊石塊而成的牆,正如這樣的家。他動心了,就留下吧,這是南方家鄉的複製,而因為距離遙遠更臻完美,他可以在這裡創造一個家,同鄉必定奧援他,生養兒女,繁殖眾多。
椰子樹上的鳥噪叫醒他,看著自己胯下奮起如金字塔,單純是生理反應,一下子就消失。他努力地想,想不出有驅力使他再奮起。完全沒有。
他返家,家兩旁的大路進行漫長的施工,季風颳起沙塵遮蔽了日頭。弟弟在某一天下午,幫白鳥連同鳥籠清洗乾淨,沖淨了蘭花葉子,浴後好心情因而甜蜜啁啾的鳥鳴聲中,弟弟穿著白色內衣、拖鞋走進如同蚊帳的沙塵裡給吞噬不見。
大路施工結束,季風轉向,陰溝邊的小紫花盛開;陰曆十六,福德宮廟飛簷上有月亮,收音機播放尺八吹奏的音樂;晚飯時兩張白鐵皮桌面合併,留給弟弟的位子空著。疾駛過的車輛掀起氣流震動了鋁門,母親抬頭一望,期望是弟弟進門。父親要他上樓去看看弟婦。房間冷氣很強,她彷彿從灰燼裡艱難起身,乾澀喊一聲大伯。感覺她又臃腫了一圈。他帶她下樓,母親將筍湯又熱了,她咕嚕喝下。姊夫說,有聲表示好食,毋知有摻化學香料無?大姐斥,烏白講。弟婦單獨告訴他,幾天前弟弟來託夢,「死了才叫託夢。」他反駁,拒絕問她夢的內容。
他們新婚時,弟弟羞赧抱怨,新娘打鼾,害他睡不著,翻身時一條大腿壓他腹肚,重得他未得喘氣。他惆悵想到同梯一樣的習慣,身體與跨過來的腿成為一個h,他規矩睡直,兩人便成為H,那均勻鼻息讓他從騷亂滑向安穩的睡眠。
父親笑笑接口說起婚前少年時去東部的一個漁港工作,六個人睡一個通舖,齁齁叫像彈雷公,感覺像睏在天頂。
他帶弟婦到那漁港已是接近黃昏,她下身燈籠褲涼鞋,離開了家就顯露了精神,逗著港口海產店門前一隻白鸚鵡玩,鸚鵡也應她,聒聒喊出你好你好,她開心笑了。陌生人一定視兩人為夫妻。漁港沒落很久了,港灣瞌睡著幾艘漁船,一條塑膠繩晾著發著餿味的衫褲,山丘上有座油漆鮮亮的寺廟。父親說過那廟,依父親寡言的習慣,他忖度是要他去看看,他要弟婦等著,自己走上去表示心意到了,供桌前的拜墊塑膠皮裂了,香火味令他頭暈,廟前呆坐一個老人牙齒掉光了。哪來的神?他仍然代父親投了兩張紙鈔進功德箱。往回走,弟婦在帆布篷下吃一碗澆著豔紅糖漿的銼冰。他想到了兄終弟及。
很快找到父親說的魚工廠,成了廢棄鬼屋,牆壁爛穿,鐵管鏽洞,唯獨製冰廠還在,只一工人穿著高筒膠鞋持長鐵鉤鉤著長方冰塊寂寞地拖滑著。他確定弟弟不在這裡。確定的是父親提過旁邊的雜貨店,當年頭家女兒與母親有淡薄像,果然有一個頭臉輪廓與母親彷彿的老婦。夜暗前離去,唯一聯外道路也是隘口,乾旱土丘上直立著幾莖單薄的紫紅小花,父親說過當年每天行這條路往返,一人在太大的天空下行走,颱風天看見海湧潑上半空。他回望蒼茫中的漁港,寥落的人影,有一個瘦高的似乎接收到他的頻率與他對望,有一剎那他想鎖住那鹹腥味的人影奔回去看清楚。但他知道那是自己的幻覺作祟。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某某人的夢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10 |
二手中文書 |
$ 174 |
中文現代文學 |
$ 187 |
小說/文學 |
$ 193 |
中文書 |
$ 194 |
小說 |
$ 198 |
小說 |
$ 198 |
現代小說 |
$ 198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某某人的夢
他人的夢,他人的道路,當流年替換,銀河暗渡,便是我不能推卻的長路與亂夢。
自命擁有虛構特權的小說作者——真的嗎?誰賦予的?誰認證的?
我是否再次肆意入侵了他人生活或生命的神聖領域,遂行竊盜之實?
古傳說更有所謂食夢貘的神獸,潛入人的夢境,食盡惡夢,人就清吉了。
〈補夢人〉
許多年前,他們在機堡的草坡相擁睡著,在破曉前猝醒,體熱上蓋了一層冰涼的露水。月亮完全沉沒的最後一刻,夜氣嘶嘶地席捲退去,在太陽追獵他們之前,兩人一前一後奔跑著,手中的老步槍響亮著,跑向新生的第一道日光,他叫喚他的名字,那麼大聲,充滿力氣,那麼喜悅,一如上古之人發出第一個字音。
〈原子人〉
那個暑假,童伴與他共同搭蓋了一間好像狗窩只能塞進一人的小木屋,一次他在樹葉沙沙聲中醒來,發覺自己孤獨睡在那隨時會倒塌的小木屋中,整個院子黑沃沃的,散發著蘊藏著強烈繁殖力的微腐氣味;他看見一片麵包樹葉掉下來,看見一長列螞蟻慌急地傳遞消息,聽見角落老鼠的吱吱叫聲。
〈異鄉人〉
通訊器材如此發達的年代,對方的聲波就像候鳥飛翔的路線,經過的緯度對應著地上的某個河海口、某處被列為文化遺產的廢墟、某個他毫無興趣的大城市、某個大沙漠,多麼奇怪的感覺,他像是戒酒聚會中那只聽不發一言的人。只是聽,一道光伸進昏暗中,遂得以看清一切;相遇之後,離開之後,最好的所得。
作者簡介:
林俊頴
一九六○年生,彰化人。政治大學中文系畢業,紐約市立大學Queens College大眾傳播碩士。曾任職報社、電視台、廣告公司。著有小說《我不可告人的鄉愁》、《鏡花園》、《善女人》、《玫瑰阿修羅》、《大暑》、《是誰在唱歌》、《焚燒創世紀》、《夏夜微笑》等,散文集《日出在遠方》、《盛夏的事》。
章節試閱
《人的夢》之一 補夢人
整個下午,他與他等待雷響。
等雷響將兩人貫穿,胸腔打開如同大海。
間歇的只有珊瑚枝狀的閃電,鞭亮了潛伏著暗礁的海岸,一瞬間的銀色大海。
大雨下在遠方的海域,因為嗅到了海風送來的雨點混著淡水的清新氣息。
銀白電光照亮了同梯好友曝曬、海浴了長長一整個夏天之後如同海豚的身軀,緊繃,光滑,跳進滾來的海浪裡時,那弓背繃出的脊骨好像一條鑄鐵,隨即又被吐在沙灘上。同梯如此與大海搏鬥甚久而吁氣,下腹部的性器冷縮一如果核。
他希望握住自己劇烈跳動的心臟,像一隻驚慌而輕狂拍翅的巢鳥。
以為意...
整個下午,他與他等待雷響。
等雷響將兩人貫穿,胸腔打開如同大海。
間歇的只有珊瑚枝狀的閃電,鞭亮了潛伏著暗礁的海岸,一瞬間的銀色大海。
大雨下在遠方的海域,因為嗅到了海風送來的雨點混著淡水的清新氣息。
銀白電光照亮了同梯好友曝曬、海浴了長長一整個夏天之後如同海豚的身軀,緊繃,光滑,跳進滾來的海浪裡時,那弓背繃出的脊骨好像一條鑄鐵,隨即又被吐在沙灘上。同梯如此與大海搏鬥甚久而吁氣,下腹部的性器冷縮一如果核。
他希望握住自己劇烈跳動的心臟,像一隻驚慌而輕狂拍翅的巢鳥。
以為意...
»看全部
作者序
淺薄是最大的罪惡
這本小說據以為藍本的真人真事,放在我心上有若干年。
而今寫成,唯一令我懸念,幾分不安的還是那一個老問題,自命擁有虛構特權的小說作者——真的嗎?誰賦予的?誰認證的?——我是否再次肆意入侵了他人生活或生命的神聖領域,遂行竊盜之實?
但我始終記得,在那些時間大河浩蕩無聲匆匆前行卻無與倫比的時刻,我做為傾聽者、旁觀者也是見證者,我滿心願意作為那回頭一望而成為鹽柱之人。記憶的鹽柱,爰以寫出。
據說古希伯來人行獻祭,所獻的動物切成兩半放在地上,立約的兩方得以從中間走過去。所以正確說法是,...
這本小說據以為藍本的真人真事,放在我心上有若干年。
而今寫成,唯一令我懸念,幾分不安的還是那一個老問題,自命擁有虛構特權的小說作者——真的嗎?誰賦予的?誰認證的?——我是否再次肆意入侵了他人生活或生命的神聖領域,遂行竊盜之實?
但我始終記得,在那些時間大河浩蕩無聲匆匆前行卻無與倫比的時刻,我做為傾聽者、旁觀者也是見證者,我滿心願意作為那回頭一望而成為鹽柱之人。記憶的鹽柱,爰以寫出。
據說古希伯來人行獻祭,所獻的動物切成兩半放在地上,立約的兩方得以從中間走過去。所以正確說法是,...
»看全部
目錄
《人的夢》之一 補夢人
《人的夢》之二 原子人
《人的夢》之三 異鄉人
淺薄是最大的罪惡(後記)
《人的夢》之二 原子人
《人的夢》之三 異鄉人
淺薄是最大的罪惡(後記)
商品資料
- 作者: 林俊頴
- 出版社: INK印刻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4-11-13 ISBN/ISSN:978986582397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184頁 開數:14.8*21 1.2CM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