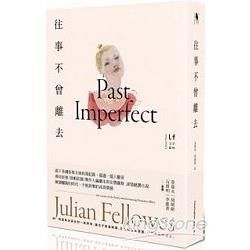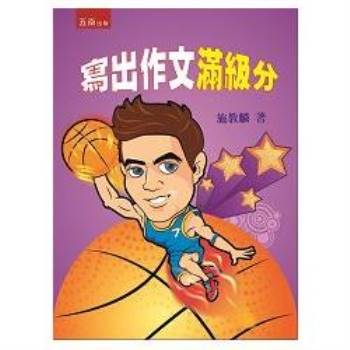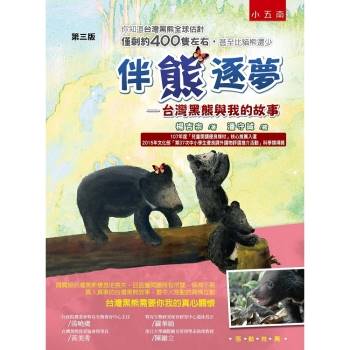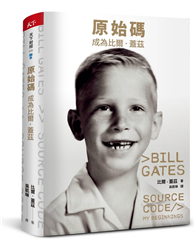英國「理察與茱蒂」讀書俱樂部夏季選書
金球獎、艾美獎最佳影集、創下1.2億人觀看的風潮英劇《唐頓莊園》才子製作人、《迷霧莊園》奧斯卡金獎編劇朱利安.費羅斯自傳式的深情絕讚小說。
這是英倫版的《大亨小傳》,
平民出身的劍橋大學生愛上高不可攀的貴族,
這是一九六O年代的《唐頓莊園》,
階級與時代都無法抹去的一段不可能的愛。
「四十年前,他背叛了我,闖入我們規矩有序的世界,破壞了一切。四十年後,我卻再度為他重返青春當年,揭開塵封的舊世界。因為,過去的一切並未結束。」
擅長觀察英國舊階級與新世界的變化,並以這類題材作品屢屢拿下大獎的朱利安.費羅斯,在這本小說中展現他對時間更替、文化衝擊和人心深度的描寫功力。四十年前,敘事者與德米安是同學,將他帶進外人難以闖入的上流生活圈,結伴青春年少友,後來卻恩斷義絕,因為他恨透了他,因為他正是在半世紀前迷倒倫敦上流社會女士們、辜負了所有愛情與友情的負心漢。但是錯真的在德米安嗎?
小說英文書名Past Imperfect暗示了:過去的一切並未結束。兩位故友在六十歲後,重拾不曾真正離去的過往、直視在他們的階級鴻溝中那難以言喻的浪漫與哀愁。全書充滿了《唐頓莊園》的寫實浪漫色彩。
名人推薦
蔡康永、胡晴舫、石偉明、李維菁 老派深情 推薦
「諷詞犀利﹑俱細靡遺﹑機智幽默﹑時而感人肺腑﹑自始至終饒富趣味的一齣上流社會百態。」--《波士頓地球報》
「作者展現過人的文采﹐精密刻劃人情世故與階級涇渭…。堪與伍爾夫(Tom Wolfe)相提並論。」-- 《出版人週刊》
「從臥房到舞宴大廳﹐作者帶讀者回溯記憶之巷﹐故事中不斷提及一場轟轟烈烈的晚宴——那是一場事關破碎的碗盤與破滅的幻夢之宴——直到故事尾聲才現出全貌。在全書的鋪陳與伏筆之後,夜宴過程總算揭曉﹐是完美的懸疑期待,令人拍案叫絕。」-- 《華爾街日報》
「四十年前﹐倫敦的元媛舞會季期間﹐絢爛的舞會與茶會一場接一場﹐心胸狹窄、內在面目猙獰的貴婦潛伏其中﹐急著為初長成的女兒尋覓金龜婿。這樣的場景現代人已經陌生﹐但作者朱利安﹒費羅斯不擔心現代讀者缺乏了解,大膽此書《願與怨》吸引讀者注意…」-- 《Daily Beast》
「一趟穿越四十年的時空旅程﹐詼諧逗趣﹐情節起伏跌宕,絕無冷場。」--《Standard Evening標準晚報》
「洞察人性之作﹐經歷過當年情景者肯定會驚嘆,必讀的一冊。」--《每日郵報》
「作者對筆下人物投注深切情感﹐讀來深刻有感,小說價值感超越一般描寫社交情境的作品。」 -- 《觀局者雜誌》(The Spectator)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往事不曾離去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55 |
二手中文書 |
$ 323 |
小說/文學 |
$ 334 |
中文書 |
$ 334 |
英美文學 |
$ 342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往事不曾離去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朱利安•費羅斯(Julian Fellowes)
著名作家、演員、電影導演製作人。在從事電影編劇之前,費羅斯有過30年不太成功的演員生涯。2002年,53歲的朱利安•費洛斯憑藉第一個被拍成電影的劇本《迷霧莊園》Gosford Park獲得第74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原創劇本獎,其後擔任編劇的作品《浮華世家》、《年輕的維多利亞》和音樂劇《保母包萍》等都廣獲好評。2011年,費羅斯憑藉《唐頓莊園》榮獲第63屆美國電視艾美獎最佳編劇。該劇集不但創下高收視並打破1981年《拾夢記》的收視紀錄,成為當代最成功的英國時代劇,並榮獲今氏世界紀錄「2010年全球最受好評的電視影集」,是首獲此殊榮的英國電視影集。
朱利安•費羅斯目前的劇作還有鐵達尼號電視劇集。
譯者簡介
宋瑛堂
台大外文學士,台大新聞碩士,波特蘭州立大學專業文件碩士﹐曾任China Post記者、副採訪主任、Student Post主編等職。譯作包括《修正》、《禪與摩托車維修的藝術》、《單身》﹑《斷背山》、《冷月》、《永遠的園丁》、《幸福的抉擇》、《蘭花賊》等書。
朱利安•費羅斯(Julian Fellowes)
著名作家、演員、電影導演製作人。在從事電影編劇之前,費羅斯有過30年不太成功的演員生涯。2002年,53歲的朱利安•費洛斯憑藉第一個被拍成電影的劇本《迷霧莊園》Gosford Park獲得第74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原創劇本獎,其後擔任編劇的作品《浮華世家》、《年輕的維多利亞》和音樂劇《保母包萍》等都廣獲好評。2011年,費羅斯憑藉《唐頓莊園》榮獲第63屆美國電視艾美獎最佳編劇。該劇集不但創下高收視並打破1981年《拾夢記》的收視紀錄,成為當代最成功的英國時代劇,並榮獲今氏世界紀錄「2010年全球最受好評的電視影集」,是首獲此殊榮的英國電視影集。
朱利安•費羅斯目前的劇作還有鐵達尼號電視劇集。
譯者簡介
宋瑛堂
台大外文學士,台大新聞碩士,波特蘭州立大學專業文件碩士﹐曾任China Post記者、副採訪主任、Student Post主編等職。譯作包括《修正》、《禪與摩托車維修的藝術》、《單身》﹑《斷背山》、《冷月》、《永遠的園丁》、《幸福的抉擇》、《蘭花賊》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