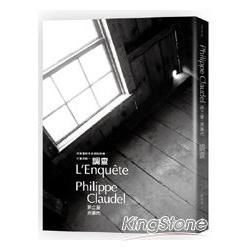只有當你不去找的時候,才會找到。
「在這裡,要矇上眼睛才看得見。」
--要是K踏進了城堡,會發生什麼事?
*** EDISTAT不分類Top 200
*** L’Express文學暢銷排行
***荷蘭、德國、英國、義大利、西班牙、加泰隆尼亞、希臘、挪威、丹麥、冰島、波蘭矚目出版
為了調查在一家看似平常的企業裡所發生的自殺潮原因,「調查員」一如往常地前往企業的所在地,以完成蒐證與分析任務。
街道上空無一人的夜晚、冰冷的雨和雪、默默消失的時間與有著女巨人擔任夜間櫃檯的「希望旅館」,「調查員」交出了身分證件、誦讀旅館規定,並爬上位在六樓的「一樓」,終於一身疲憊地睡在大得不可思議的旅館房間。
早晨,他先是接到莫名其妙的求救電話,接著發現與房間不成比例的浴室;他走進餐廳,發現講著陌生語言的觀光客、服務態度過差的服務生,以及坐在儲藏室裡的警察;來到大街上,擁擠而規律的人潮帶著他進入巨大的「企業」--空白的企業說明手冊、身兼夜間警衛的「導遊」與在辦公室做體操的「領導人」,只讓「調查員」的內心愈發不安起來。
不連號的旅館房間、每天早晨的求救電話、喜怒無常的警察、擠滿餐廳的陌生人、失蹤的證件與衣服……「調查員」相信,有某個人正不惜一切在阻止他調查這些自殺案件,「他」不僅想奪走調查員的神智,也包括他的身分。
作者簡介
菲立普.克婁代(Philippe Claudel)
1962年生於法國洛林區Dombasle-sur-Meurthe,身兼大學講師、作家和劇作家,為法國備受矚目的中生代作家,已出版過14本小說。曾以《莫斯忘記了》獲法國廣播金獎(Prix Radio-France-la Feuille d’or)、《千百悔恨中的一些》獲馬塞巴紐爾獎(Prix Marcel Pagnol)、《我放棄》獲法國電視獎。2003年以短篇小說集《小機械》獲龔固爾短篇小說獎,同年另以《灰色的靈魂》一書獲荷諾多文學獎,並登上法國暢銷排行榜。
克婁代擅長以平實卻富詩意與韻律感的文字,描畫生命複雜的情境。繼《灰色的靈魂》之後,2005年再以《林先生的小孫女》登上排行榜長達半年。2007年底推出全新力作《波戴克報告》,獲得高中生龔固爾文學獎,並入圍龔固爾文學獎決選。
2008年克婁代首度跨足電影領域,自編自導電影《我一直深愛著你》,榮獲英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法國凱薩獎最佳影片、入圍金球獎最佳外語片,於2008年台北金馬影展受邀來台放映,深受觀眾好評。
譯者簡介
嚴慧瑩
輔大法文系畢業、法國博士,譯作《口信》、《六個非道德故事》、《永遠的山谷》、《沼澤邊的旅店》、《羅絲 .梅莉.羅絲》、《終極美味》、《灰色的靈魂》,並著有多部旅遊美食書,文章散見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