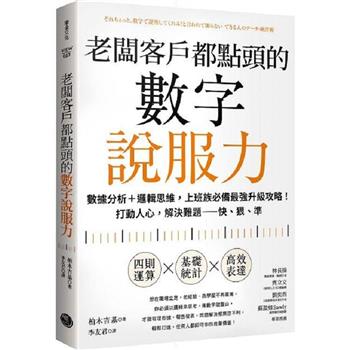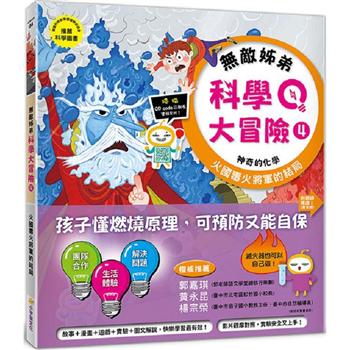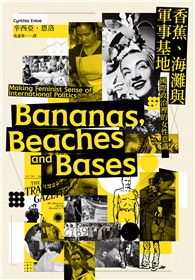在這連呼吸都被規定的世界,我們只偷得了你和我。
現在,這些人連我們愛的自由都想收走——
「就算全世界與我為敵,我還是要愛你。」——陳綺貞
我端詳著手機上的臉孔。疲憊的眼,腫脹的唇,太陽穴上新出現的暗沉膚色。我閉眼不願再看。那就是威爾看到的我。當我的臉上毫無遮掩,沒有彩妝,他就會看到這樣的我。這無所謂。當他望著我,他眼中的我就是那個模樣。
「我看起來好慘。」
車子猛然轉彎,我整個人往右邊滑,安全帶頓時繃緊。輪胎輾過碎石子,他粗暴地踩下煞車。我擔心自己是不是惹他生氣了,只見他下了車,轟然摔上車門,繞過來,打開我這一側的車門。他解開我的安全帶,拖我下車。
「妳、很、美。」他強壯的手臂緊緊箍著我。甚至,有一股豁出一切的氣勢。「妳只可以說自己很美,懂嗎?這個──」他碰觸我的嘴唇、我的眼睛。「這些會消退,妳的心會癒合,妳永遠不必再煩惱怎麼掩蓋傷痕。妳明白了嗎?」
在他熾烈的目光下,淚水湧上我的眼眶。我不想讓他看到,便將頭靠在他的心口,依偎著他柔軟的上衣。
「妳這麼美好。以後不會再有人傷害妳。」
這一年,她十五歲,他十八歲。
轉學那天,威爾對柔依一見鍾情。在他眼裡,她聰明、美好,脆弱得需要一個人保護。
而他不過是輾轉無數個寄養家庭的棄兒,像「變身怪醫」一樣身體裡有個易怒的威爾。他自己就是個麻煩。
當威爾發現,柔依只有一個爸爸,酗酒之後就只會狠狠地揍她,他只想帶心愛的女孩遠走高飛,飛去一個沒有人能傷害他們兩個人的地方。
可是。
如果再晚幾個月相愛,也許他們就不會被全世界通緝了。
如果威爾能控制他身體裡的憤怒,就不會惹來警察的注意了。
當全世界都在追你,有時候似乎怎麼跑都不夠快。
而柔依無法回頭。她不能回到那個家,也沒辦法離開會像他父親一樣失控的威爾。他們只能一直往前走,直到公路的盡頭,直到世界決定安排给他們的終點。
名人推薦
陳夏民(出版人) 羅毓嘉(詩人) 青春無敵推薦
「美麗、心碎、爽快──《沒有別人,只要我們》會讓你屏住呼吸到最後一頁。」——可荻•凱普琳潔(Kody Keplinger),《甜蜜逃避法則》作者
「筆觸優雅,發人深省,引人入勝的處女作。以前不曾看過這樣的愛情故事,我說真的。」——珂特妮•薩莫斯(Courtney Summers),Cracked up to be作者
《書單》雜誌(Booklist):
威爾,十八歲,因為年齡而剛剛脫離寄養制度的照顧。柔依,十五歲,飽受父親拳打腳踢。兩人駕駛威爾破舊的Camaro逃離北達科塔州。柔依覺得自己被救出了父親的魔掌,威爾也自認為在救她,但隨著故事推展,這項核心議題卻曖昧難明了起來。兩人一心只想被愛、擁有安全感,讀者也看到他們對未來懷抱希望的對話(「幸福不可能只是一則神話」)。可是當暴力悄悄滲進小兩口之間,隨後發生了一場「意外」,他們還有路可逃嗎?作者在這部處女作中塑造了複雜的人物,透過他們苦苦思索的過程,打造發人深省的閱讀體驗。(適讀年齡:九至十二年級)──安.凱麗(Ann Kelley)
一段黑暗、浪漫、狂亂的公路之旅,令人想起電影末路狂花(Thelma and Louise)。——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
我們怎樣愛人?愛一個人會有什麼後果?作者犀利、鮮明地描繪出兩個逃亡的邊緣青少年。筆觸優雅,發人深省,引人入勝的處女作。以前不曾看過這樣的愛情故事,我說真的。
——珂特妮.薩莫斯(Courtney Summers),著有《名不副實》(暫譯,Cracked up to be)、《有些女生就是那樣》(暫譯,Some Girls Are)、《信以為真》(暫譯,Fall for Anything)
在這個極具說服力的愛情故事中,兩個邊緣青少年亡命天涯,逃離辜負他們的社會,盼著公路盡頭的燈光不會只是海市蜃樓。緊張、抒情、令人心疼,餘韻久久不散的那種書。——克麗絲坦.胡巴德(Kirsten Hubbard),著有《美好戀情》(暫譯,Wanderlove)、《像曼德琳一樣》(暫譯,Like Mandar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