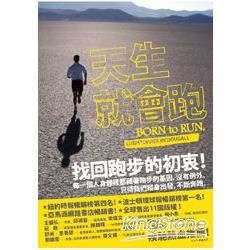*2013年新版
人的身體,天生就是為了跑步而設計的。
演化上……
* 人類的氧氣使用效率極佳。大部分動物都有「一步一呼吸」的限制,只有一種動物例外,就是你。你非常適合跑步。
* 人可以徒步追獸。哈佛大學研究發現,任何人只要有能力在夏天一口氣跑上六英里,就能成為動物界的致命殺手。
* 非洲的布希曼獵人,通常每次跑上三到五小時,就能追到羚羊。所需時間恰好與馬拉松差不多。可見,人類愛跑步並非出於偶然。
* 長途跑步讓我們取得食物,找到伴侶,得以存活、繁榮、向外繁衍。
身心靈……
* 跑步之後,飲食習慣自然會改變。吃得清淡,吃得較少。
* 跑步之後,睡得更好,平常更放鬆,心跳率也下降了。
* 運動可以從內心深層穩定情緒,不論任何問題,如果四小時的跑步沒辦法帶給你答案,那別的方式也辦不到。
本書作者麥杜格是一位喜愛跑步的業餘跑者,但他始終對一件事情很困擾:為什麼跑步的時候腳會痛?
為了治療腳痛,他遍訪名醫,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樣:人體天生不適合跑步,最好換另一種運動試試看。
在尋找解決腳痛問題的同時,他看到有關原住民「塔拉烏馬拉」族人的報導,發現他們是世界上最厲害的長距離跑者,於是前去請教跑步的秘訣。作者從這個族人身上學到關於跑步的所有事情,也發現原本自己對於跑步的觀念是錯誤的。
「塔拉烏馬拉」族人一直過著遺世獨立的日子,好幾個世紀以來,他們就在崎嶇的山中奔跑,可以不用休息就跑個上百公里且面不改色,輕鬆就可以跑贏山裡的野生動物,更不用說奧運的馬拉松選手。也因為擅長跑步,這群族人身體非常好,性格平靜,從不生病,現代各種的流行傳染病都不曾出現在他們身上。
而他們的跑步哲學,就是回歸基本,不為財富、勝利或名聲而跑,單純是為了追求「使用身體的暢快感覺」。
作者從這群健康、快樂又長壽的原住民族人身上,學會了跑步真正的要領,腳痛的問題不藥而癒,原本被所有醫生判定他塊頭太大不適合長距離跑步,也因為學會跑步的秘訣,居然發掘出自己可以參加極限跑步的潛能。
《天生就會跑》不單是他追尋跑步秘訣的故事,其中更穿插許多當代最擅長跑步者的傳奇故事,以及過去人類在跑步運動上的種種突破,向讀者證明了一點:我們天生就是適合跑步的生物,我們是地球上最有耐力的跑者!
沒有愛,我們不會出生;沒有速度,我們就無法存活!
本書特色
凡是想要活得更充實,跑得更快的人,都會受到這本書的啟發。
閱讀時只覺得腦內啡受刺激大量生成,產生高度的愉悅。
作者簡介:
克里斯多福‧麥杜格(Christopher McDougall),美國賓州人,哈佛大學畢業後加入美聯社擔任記者,派赴里斯本,並在非洲的安哥拉、剛果與盧安達等三地報導戰事。返回美國後他先後為《戶外雜誌》、《紐約時報雜誌》、《跑者世界》、《男性健康雜誌》等刊物工作,報導曾三次獲全美雜誌報導獎決選。目前他居住在賓州的鄉間,除了練跑之外正在撰寫下一本書。
譯者簡介:
王亦穹,目前居住南台灣,專職譯者,譯有《感染》等書。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疾馳熱血推薦!
王盛弘(作家)
李偉文(荒野保護協會榮譽理事長)
邱淑容(超馬媽媽)
飛小魚(馬拉松作家)
紀政(希望基金會董事長)
陳幸蕙(作家)
陳錦輝(64日穿越歐洲超馬賽選手)
郭豐州(國際超級馬拉松總會技術委員)
舒米恩‧魯碧(金馬獎新人、圖騰樂團創作歌手)
游象錄(台北縣馬拉松協會會長)
彭蕙仙(作家)
楊基旺(台灣大腳ㄚ協會會長)
蔡文甫(九歌出版社社長)
劉震雲(作家、北京奧運聖火隊跑者)
【按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媒體推薦:
* 就算你不在乎跑步應採取什麼步態,不想知道補充熱量的能量包果膠,這本書還是非常好看。書中的「創意非文學」筆法尤為獨特,以小說故事般的言語來講述真正的事實,華盛頓郵報
* 令人愛不釋手,高度可讀。作者以當今世上最罕為人知的「塔拉虎馬」族人的跑步文化為基準,仔細檢視當代慢跑的風潮。舊金山記事報
* 這本書綜合了探奇、生理學文獻、跑步史三大特點,內容有如一個精采的短跑衝刺。這本書,只會讓你興起奔向戶外的念頭。戶外雜誌
* 《天生就會跑》具有高度的可讀性,是多年來有關「跑步」這個主題的最佳寫作。愛爾蘭時報
* 這是一個讓人愛不釋手的故事,文筆流暢,內容充滿了可用的知識,包含了當代運動鞋的演化到人體天生就善於跑步等多個主題。高度推薦給所有想運動的人。Kirkus評論
* 《天生就會跑》是非常吸引人的故事,一定會成為經典作品。作家Daniel Coyle
* 《天生就會跑》內容非常有趣好玩,詭異古怪,一讀起來就不能停。愛跑的人更會喜愛。波士頓馬拉松四度冠軍Bill Rodgers
* 作者洞悉了長途路跑的科學和精神,帶領讀者進入墨西哥崎嶇的山區,完成一件不可能的任務:一窺赤腳跑者「塔拉烏馬拉」族人的神秘世界,以及他們瑰麗壯闊的文化特質。作者Hampton Sides
* 作者的行文有如超級馬拉松,下筆看似輕鬆,充滿豐富的內容,讓我一讀就不能停止。讀完這本書,我只想做一件事:跑!作者Benjamin Wallace
* 這本書好有趣,充滿有用的知識,又深深吸引著我,還揭開了一個美麗的神秘部族之謎。書中的訊息,不但可以適用在跑步這件事情上,還有更廣泛的運用。凡是想要活得更充實,跑得更快的人,都會被這本書啟發。作者Lynne Cox
* 隨著書中的記載,讀者奔馳在變化多端的山區地形,有時緊張刺激,有時妙趣橫生,內容令人目不暇給,閱讀時只感覺腦內啡受到刺激而大量生成,高度的愉悅。作者John Gimlette
* 關於跑步,沒有其他作品寫得比這本書還好。這本書會讓你的人生更堅強。作者Lloyd Bradley
* 每個人都可以跑,都可以跑得更好。這本書,是經典之作。作者Sir Ranulph Fiennes
名人推薦:疾馳熱血推薦!
王盛弘(作家)
李偉文(荒野保護協會榮譽理事長)
邱淑容(超馬媽媽)
飛小魚(馬拉松作家)
紀政(希望基金會董事長)
陳幸蕙(作家)
陳錦輝(64日穿越歐洲超馬賽選手)
郭豐州(國際超級馬拉松總會技術委員)
舒米恩‧魯碧(金馬獎新人、圖騰樂團創作歌手)
游象錄(台北縣馬拉松協會會長)
彭蕙仙(作家)
楊基旺(台灣大腳ㄚ協會會長)
蔡文甫(九歌出版社社長)
劉震雲(作家、北京奧運聖火隊跑者)
【按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媒體推薦:* 就算你不在乎跑步應採取什麼步態,不想知道補充...
章節試閱
前情提要
二〇〇六年間,墨西哥的銅峽谷內舉辦了一場史上罕見的五十英里超級馬拉松賽,由擅於長跑的塔拉烏馬拉族人派出「昆馬利家族」,出戰有「超馬之神」的美國選手史考特‧傑瑞克(綽號「大鹿」)以及美國東岸超馬新銳珍‧雪頓(綽號「女巫」)。其他與賽者還有專打赤腳跑步的超馬菁英「赤腳泰德」、曾經贏得夏威夷百英里賽的攝影師路易‧艾斯克博等人。這場超級菁英賽堪稱空前絕後,已是美洲超馬界不朽的史詩傳奇,也成為《天生就會跑》這本書內最精華的篇章。
時序接近比賽當天清晨,忙碌的準備工作正要開始……
---------------------------------------------------------
清晨五點時,蒂塔媽媽的鬆餅、木瓜和熱皮諾爾已經上桌。阿納佛和西爾瓦諾則特別點了「波索爾」當賽前早餐,這是一種加了蕃茄與飽滿玉米粒的牛肉燉湯。蒂塔媽媽只睡了三小時,說話卻仍像小鳥般興高采烈,要她弄出「波索爾」這道菜餚簡直是易如反掌。西爾瓦諾換上了特殊的賽跑服,那是一件亮眼的天藍長襯衫,還有白色的傳統裙子,邊緣繡上了花朵。
「真漂亮。」卡巴羅讚賞道。西爾瓦諾害羞地低下了頭。卡巴羅在院子裡繞著圈,啜著咖啡,心中卻煩惱不已。他聽說有牧人會趕牛經過路線上的一條小徑,所以整晚難以入眠,盤算最後一刻如何改變路線。不過等到起床吃早餐時,他發現路易的父親和老鮑伯已經及時趕到,成了他的救星。鮑伯跟卡巴羅一樣是美國人,也常在巴托畢拉斯一帶漫游。他倆前天在野外拍照時,剛好遇見那些牧人,而且提醒他們避開比賽路線。現在卡巴羅不必再擔心選手被牛群踩扁了。但他還有一件事情需要煩惱,而且這個煩惱就在眼前。
「那兩個小鬼呢?」他問道。
大家聳聳肩。
「我最好去找他們,」他說道:「我可不希望他們再次空著肚子來自殺。」
我和卡巴羅一起走到街上,驚訝地發現全鎮的人都在路邊歡迎我們。我們在屋裡吃早餐時,他們沿街綁上了鮮花與綵帶;街頭樂團頭戴墨西帽,身穿牛仔服,正在試吹暖身的曲子。婦女與孩子已經在街上跳起了舞,鎮長則將槍口指向天上,練習鳴槍起跑的動作。
我看看手錶,突然覺得無法呼吸:再過三十分鐘就要開始了。之前到烏里克的三十五英里路正如卡巴羅所說:「將我生吞活剝,嚼爛了再吐出來。」再過半小時,我就得從頭再來一遍,而且這次還多了十五英里。卡巴羅設計的比賽路線有如地獄:五十英里的賽道上,我們得登上六千五百呎的高峰再下山,這跟里德維爾百英里賽前半段的山路一樣高。卡巴羅雖然不欣賞里德維爾的主辦單位,但談到路線規畫,他跟他們一樣冷酷無情。
卡巴羅和我爬到山丘上的小旅館。珍和比利還在房間裡,正在跟比利吵是不是該多帶個水壺。不過後來發現,反正那個水壺也不見了。我剛好有個裝咖啡的多餘水壺,所以我連忙趕到房裡,倒掉咖啡,把水壺拋給比利。
「現在吃點東西!動作快。」卡巴羅責備道:「鎮長七點整準時鳴槍!」
卡巴羅和我抓起裝備——我的是裝滿能量凝膠與能量棒的攜水背包,卡巴羅的則是一瓶水,一小袋皮諾爾。然後我們下山回街上。只剩十五分鐘了。我們繞過街角往蒂塔媽媽的店那裡過去,發現街頭派對已經擴大成小型狂歡節。路易和泰德正抓著兩名老太太繞圈圈,一邊擋開想插進來的對手——路易的爸爸。史考特和鮑伯正盡力跟著樂隊的節奏打拍子唱歌,烏里克鎮的塔拉烏馬拉人已經組成了自己的打擊樂隊,在人行道上用隨身的棍子打著節拍。
卡巴羅非常開心。他擠進人群中,擺出拳王阿里的姿勢,邊跳邊搖擺上身,一面往空中不斷揮拳。群眾吶喊起來,蒂塔媽媽送了他幾個飛吻。
「我們要跳舞跳上一整天!」卡巴羅將手圈在嘴邊大喊道:「不過前提是沒有人掛點!比賽時自己當心點!」他轉向樂隊的方向,然後作勢用手指劃過喉嚨。停下音樂,好戲開鑼了。
卡巴羅和鎮長開始將群眾趕離街道,然後招手要跑者到起跑線上來。我們全都聚集起來,像大雜燴的人群滿是不同的臉孔、身材、裝扮。烏里克鎮的塔拉烏馬拉人穿著短褲和跑鞋,外加隨身的棍子。史考特脫下T恤,阿納佛和西爾瓦諾穿著特地為這次比賽買下的鮮豔上衣,擠到史考特身邊;這兩個獵鹿人不打算讓大鹿離開視線範圍一秒。出於某種無言的默契,我們全都站到龜裂柏油路上一條無形的線後。
我再次覺得呼吸困難,這時艾瑞克擠到我身邊。「聽著,我有壞消息要告訴你。」他說道:「反正你不可能贏的。不管你再怎麼拼命,都得花上一整天才能跑完。所以你還不如放輕鬆,慢慢來,盡情享受。記住了,只要覺得有一絲勉強,那就意味著你跑得太快。」
「所以我會慢慢來,等到別人打盹的空檔。」我啞聲說道:「然後抓住機會行動。」
「別妄想要暴衝!」艾瑞克警告我。哪怕我只是在說笑,他也不希望我有一絲一毫這樣的念頭。「比賽中氣溫可能會高到一百度。你的任務就是靠自己的雙腿回到這裡來。」
蒂塔媽媽從我們面前一一走過,眼眶含淚,握住我們的手。「小心點,親愛的。」她叮嚀道。
「十……九…….」
鎮長開始領著大家倒數。
「八……七……」
「那兩個小鬼呢?」卡巴羅吼道。
我四處張望,珍和比利不見人影。
「叫他先別數!」我也回吼道。
卡巴羅搖搖頭。他轉過身,擺出準備比賽的姿勢。他已經等了許多年,甚至為這次比賽賭上性命,才不會為任何人喊暫停。
「那裡!」士兵們指向我們身後喊道。
群眾已經數到「四」了,珍和比利才從山丘上衝下來。比利穿著衝浪垮褲,沒穿上衣,珍則穿著黑色緊身短褲與黑色運動胸罩,頭髮中分緊緊紥著兩條辮子。士兵粉絲的歡呼讓珍一時分心,不小心將裝著食物與備用襪子的袋子一甩而出,往街道另一端飛出去。嚇一大跳的旁觀者全都往袋子撲過去,但它直飛向地面,消失在人群中。我衝過去,抓起袋子,交給旁邊急救桌旁的人。就在這時鎮長扣下扳機。
砰!
史考特一躍而起放聲大叫,珍發出長嚎,卡巴羅尖聲高嘯。塔拉烏馬拉人逕自衝出,烏里克鎮的塔拉烏馬拉人成群跑在泥土路上,消失在天亮前的陰影中。卡巴羅警告過我們,塔拉烏馬拉人會全力以赴,但不得了,他們可真是猛啊!史考特落在他們身後,阿納佛和西爾瓦諾則緊跟在史考特後面。我慢慢跑著,讓眾人越過我身旁,直到我落在最後。有人在身邊當然不錯,但現在我覺得還是獨自一人比較安全。比賽中我可能犯下最嚴重的錯誤就是一時心動,跟著別人的速度跑步。
一開頭的兩英里是出鎮後通往河邊的泥土路,還算平坦。烏里克鎮的塔拉烏馬拉人最先抵達河邊,但他們沒有直接衝進五十碼寬的淺水處過河,反而突然停下,在河邊的岩石間四處翻找東西。
怎麼回事……?鮑伯心裡疑惑著。他先和路易的父親趕過來,正在河的另一端拍照。他看到塔拉烏馬拉人從石頭底下掏出塑膠購物袋,這是他們前晚先過來藏好的。然後這些人將棍子夾在腋下,將塑膠袋套到腳上,拉住束繩往上提緊,然後才涉水過河。行之萬年的古老傳統被新科技取代後就是有這種結果:烏里克塔拉烏馬拉人怕弄濕他們寶貴的跑鞋,只好穿著他們自製的防水套過河。
「天哪。」鮑伯喃喃自語道:「我從來沒見過這種事情。」
烏里克鎮的塔拉烏馬拉人還在滑溜溜的石頭上拼命前進,這時史考特到岸邊了。他直接嘩啦啦衝進水中,阿納佛和西爾瓦諾這個昆馬利家族雙人組緊跟在後。烏里克鎮的塔拉烏馬拉人抵達對岸後踢掉腳上的塑膠袋,再將它們塞進短褲備用。他們開始登上陡峭的沙丘,史考特則迅速逼近,飛快移動的雙腳下只見沙土飛揚。等到烏里克塔拉烏馬拉人踏上通往山上的泥土小徑時,史考特和昆馬利雙人組已經趕上了他們。
珍則在一開始就遇上難題。她和比利、路易已經與一群塔拉烏馬拉人併肩過河,但珍衝上沙丘時,她的右手開始製造麻煩。超馬跑者隨身只帶輕便的小水壺,上面有帶子可以將水壺固定在手臂上,便於攜帶。珍本來有兩個水壺,但她給了比利一個,自己則用運動貼布和礦泉水瓶另外做了個水壺。當她努力奔上沙丘時,固定在手臂上的自製水壺讓她覺得又黏又礙手礙腳,這不是什麼大問題,但如果不解決的話,接下來八小時內每分每秒都會讓她感到困擾。她該留下這個水壺嗎?還是再冒一次險,只帶幾口水就往峽谷裡闖?
珍開始咬掉膠帶。她知道碰上塔拉烏馬拉人,自己唯一的勝算就是全力一搏。她寧可賭上一把,就算失敗也甘心。要是因為畏手畏腳輸掉這場世紀大賽,她知道自己會後悔一輩子。珍丟掉瓶子,立時覺得舒服得多,甚至更有勇氣。她馬上做了另一個危險的決定。眼前是路線上第一個困難的關卡——三英里長的陡峭上坡山路,途中幾乎沒有遮蔭。太陽一旦昇起,要與習慣高溫的塔拉烏馬拉人賽跑的她根本不會有勝算。
「啊!去他媽的。」珍心想:「我還是趁涼快時快衝吧。」跨出五大步後她已經超出人群一段距離。「待會見!」她對身後叫道。
塔拉烏馬拉人馬上展開追逐。兩名年紀較長的老練跑者,塞巴提諾與赫布里托,堵住了珍前方的去路,另外三名塔拉烏馬拉人則從旁邊圍住她。珍抓住一處空檔衝出重圍,拉開距離,但塔拉烏馬拉人馬上包抄上來,讓她再次陷入重圍。塔拉烏馬拉人平常也許愛好和平,但一到跑步場上,他們對敵人可是毫不留情。
「我很不想這麼說,但看來珍會被累死。」看到珍第三次搶上前去想脫出重圍,路易對比利說道。現在不過是五十英里賽跑的第三英里,但她已經和塔拉烏馬拉族的五人追逐小組展開肉搏戰。「像那樣跑是撐不到終點的。」
「不過她總是可以找到辦法撐下來。」比利說道。
「在這種路線上行不通。」路易說道。「對上這些傢伙更是不會贏。」
多虧卡巴羅巧妙的規畫,大夥兒可以看見比賽的即時進展。卡巴羅的路線呈Y字形,起點則在正中央,這樣選手在路線上來回折返時村民可以看見比賽進度,跑者也看得到前方的對手領先多少。Y形路線還有一個意料之外的好處——現在卡巴羅非常懷疑烏里克鎮的塔拉烏馬拉人會作弊。
卡巴羅落後領先群約四分之一英里,所以史考特和獵鹿雙人組過河後逼近烏里克鎮的塔拉烏馬拉人時,他看得一清二楚。烏里克組第一次折返朝他逼近時,他大吃一驚:就在短短四英里內,這些人已經領先長達四分鐘,甩開的不光是當代最優秀的兩名塔拉烏馬拉跑者,還有西部百英里賽史上最快的爬坡選手。
「他媽的!怎.麼.可.能!」卡巴羅怒吼道。他和其他人,包括赤腳泰德、艾瑞克、馬努爾.魯納跑在一起。跑到五英里處的折返點,也就是塔拉烏馬拉小村落瓜達佩.科羅納時,卡巴羅和馬努爾開始問村裡的旁觀者問題,很快他們就弄清到底是怎麼回事:烏里克塔拉烏馬拉人抄了小徑,少跑了一段距離。卡巴羅沒有大發脾氣,反而感到一陣憐憫。烏里克鎮的塔拉烏馬拉人已經遺忘古老的跑步藝術,連自尊心也一併失落。他們再也不是奔跑一族,而是不擇手段想保住一絲昔日榮光的可憐蟲。
卡巴羅身為他們的朋友,能夠體會他們的悲哀,但身為比賽主辦人他不能姑息他們。他要眾人把話傳出去:烏里克鎮的塔拉烏馬拉人失去資格了。
趕到河邊時輪到我大吃一驚。我一直專心注意自己在黑暗中的腳步,一邊在心中重複注意事項(膝蓋放彎……腳步放輕……不要留下痕跡)。開始過河時我才突然想到:我已經跑了兩英里,卻一點感覺也沒有——不,比沒有感覺更棒,我覺得身體輕快自如,甚至比剛開跑時更輕盈、精神更好。
「大熊,幹得好!」鮑伯從對岸對我喊道:「前面有一點他媽的小山丘,沒啥大不了的。」
我涉水上岸,開始登上沙丘,隨著每步跨出,我的期望便越來越高。的確,我還有四十八英里要跑,但照這樣下去,也許在開始覺得累之前,我可以跑上十幾英里。跑到上山的泥土路時,太陽剛從峽谷邊緣露臉,一瞬間週遭景物全都明亮了起來,河面波光粼粼,綠色森林微光閃閃,還有腳下卷曲的帶紋赤蛇……
我大聲尖叫,一躍從小徑跳開,但結果卻滑下險峻的斜坡,還得抓住矮樹叢止住跌勢。我看得見蛇就在我頭頂,沉默、蜷曲,準備發動攻擊。我要是重新爬回小徑,可能會遭到致命的蛇吻;要是往下朝河邊的方向爬,可能會從懸崖邊墜下,唯一的出路就是設法從旁邊過去,雙手交替抓住坡邊樹叢,慢慢移動身子繞過去。
第一次抓住的樹叢撐住了我的重量,然後是下一個。當我這樣移動了十呎遠後,我小心翼翼回到小徑上。那條蛇仍然盤踞在小徑上,原因一點也不令人驚訝——牠已經死了。有人已經用棍子打斷了牠的脊骨。我抹掉眼睛上的塵土,開始檢查自己的狀況:兩邊腳脛都被岩石磨得紅腫,植物的尖刺插進手上,心臟在胸腔裡不斷狂跳。我用牙齒將尖刺咬出,然後從水壺裡倒點水,草草沖洗一下傷口。該重新動身了,我可不希望有人撞見我因為一條死蛇嚇得驚慌失措,甚至受傷流血。
一路往山上爬,太陽越來越高,陽光也越來越烈,但經過清晨的刺骨寒意後,陽光不但不影響鬥志,反而令人精神抖擻。我牢牢記著艾瑞克的忠告:「只要覺得有一絲勉強,那就意味著你跑得太快。」所以我決定不再緊張兮兮、一直注意著自己的步伐。我把注意力轉移到週遭的峽谷風景,看著陽光下金色的山谷頂端。沒多久我就發現,自己已經跟金色的谷頂幾乎一樣高了。
一會兒之後,史考特從前方轉角處冒出來。他對我燦然一笑,豎起大姆指,然後便消失在小徑上。阿納佛和西爾瓦諾緊跟在他身後,他們飛奔通過我身旁時襯衫就像船帆般劈啪作響。我這才想到我一定就在五英里折返處附近了。再往前爬上一個山坡,折返處赫然出現在我眼前:瓜達佩.科羅納村。這裡只有一間漆成白色的學校教室,幾間屋舍,還有一間小店,裡面賣的是沒有冷藏的汽水與沾滿灰塵的袋裝餅乾,但即使遠在一英里外,我仍然可以聽見那裡傳來的歡呼與鼓聲。
一群跑者正衝出瓜達佩,往史考特與昆馬利二人組的方向追。獨自一人跑在最前頭的正是小女巫。
珍一逮到機會,馬上撒腿猛衝。在橫越巴托畢拉斯山的路上,她注意到塔拉烏馬拉人下坡的跑法和上坡一樣,步調維持一貫的自制與穩定。但珍卻最喜歡在下坡時放馬狂奔。「這是我唯一的長處。」她後來說:「所以我決定死抓住這個機會不放。」於是上坡時她沒有浪費精力與赫布里托單挑,反而決定讓他主導上坡的步調。等到抵達折返點,開始長長的下坡路時,她甩開追著她不放的對手群,開始加速下坡。
這次塔拉烏馬拉人放過了她。這段路讓她拉開老長一段距離,等她開始第二個上坡——一條單線岩石小徑,這是 Y字形的第二個分叉,一路往上至十五英里——赫布里托和其他人還在後面,已經沒辦法像先前那樣包抄她。珍開始充滿自信,抵達第二個折返點時,她甚至還停下來休息了一下,重新裝滿水壺的水。到目前為止她補水的運氣好極了。卡巴羅已經拜託過烏里克鎮民,請他們帶著瓶裝的過濾水分散在峽谷各處,每次珍只要一喝完水,似乎就會遇見下一個有水的志工。
她還在往瓶裡注水時,赫布里托、塞巴提諾,還有其他追逐者終於趕上了她。他們沒有停留,隨即轉身往反方向跑,但珍沒有馬上追上前去,直到裝完水她才開始下坡的猛衝。兩英里後她已經重新趕上他們,而且將他們拋在身後。她開始在心裡模擬前方的路線,盤算著她還有多長的路可以拉開距離。讓我瞧瞧……前面還有兩英里下坡路,然後是通往村裡的四英里平地,然後——
砰一聲大響,珍臉部著地重重摔在石地上,胸部成了支點,讓她滑出一段距離,最後才驚魂未定地停住。她躺在原地,痛得看不清眼前的情況。膝蓋骨感覺像已經裂開,一隻手臂則滿是鮮血。她還沒來得及起身時,赫布里托和其他人已經從小徑另一端狂奔而至。他們一個接一個跳過珍的身子繼續前進,連看都沒有回頭看一眼。
「他們一定在想,這就是妳不知道如何跑石子路的下場,」珍心裡想道。「好吧,算他們有理。」她小心翼翼地重新站起身來,檢查自己的傷勢。她的小腿像五彩繽紛的披薩,但膝蓋骨似乎只是瘀青,而原本以為流得滿手的鮮血不過是綁在瓶上、後來被壓爆的巧克力口味能量凝膠。珍先小心試走幾下,然後輕輕跑了兩步,傷勢似乎比預期中好多了。事實上,她的狀況好到衝到山腳時,所有從她身上跳過的塔拉烏馬拉人都已經被她甩在身後。
「小女巫!」沾著血,卻仍面帶微笑的珍跑回村中,抵達二十英里處時,烏里克的群眾幾乎全為她瘋狂。她在急救站停了一會,從自己的袋子裡又摸出一條能量凝膠,開心得又叫又跳的蒂塔媽媽則用圍裙擦著她血淋淋的腳脛,一邊高興的大嚷出一句西班牙文。
「我什麼東西?我是個房間?」她對西班牙文只略通皮毛,直到她開始衝向鎮外,才想通蒂塔媽媽的話:她是第四名,只有史考特、阿納佛、西爾瓦諾在她前面,而且她正持續拉近與他們三人間的距離。卡巴羅給她取的暱名真是再適合不過:里德維爾賽後十二年,重現江湖的女巫果真來勢洶洶。
但她還得先克服當天的高溫。珍抵達路線中最嚴厲的試驗時,氣溫已經幾乎高達一百度。前方是忽上忽下的崎嶇山路,通往小村羅斯.艾利索。小徑先繞著垂直的山壁行進一段,然後陡然下降、急速昇起、再次陡降,高度差距達三千多呎。通往羅斯.艾利索小村的道路上,山峰之險峻堪稱珍這輩子之僅見,而且數目高達六座,巍然聳立在小徑上。從岩壁蒸散的熱氣彷彿快要將她燙出水泡,但她必須緊挨著岩壁前進,否則就可能滑落崖邊,墜入下方的萬丈深谷。
珍登上其中一座山峰頂端時,突然得緊急貼到岩壁上:阿納佛和西爾瓦諾肩併肩,正朝她急衝過來。這兩名塔拉烏馬拉族獵鹿人讓所有人大吃一驚;大家都以為他們會全程跟在史考特身後,直到最後才加速超越他,但他們卻加快節奏,在中途便搶佔領先位置。
珍貼住岩壁,讓他們兩人先通過。她還沒來得及細想史考特究竟在哪裡時,馬上又被迫退到岩壁旁。「史考特拼了命在跑這場該死的比賽,我從來沒見過有人這麼專注在跑步上。」珍後來說道。「他埋頭猛衝,呼呼呼地飛快前進,根本已經渾然忘我。我正在想不知道他還認不認得我時,他抬起頭來開始狂吼,『呀呀呀啊!小女巫!喔喔喔喔!』」
史考特停下來,簡單告訴珍前面的路況,還有哪裡有山上滴下的泉水。然後他便盤問起阿納佛與西爾瓦諾的情況。他們在前面多遠的地方?神態看起來怎麼樣?珍告訴史考特,他和雙人組之間大概有三分鐘的距離,而且他們正全速奔跑。
「好極了。」史考特點頭道。他在珍背後用力拍了一下,然後再次飛奔而出。珍看著他離開,注意到他跑在小徑的最邊緣,而且緊貼著彎道前進,這是馬歇爾.烏利奇的老招數:這樣領先的人比較難回頭,注意到你從後方慢慢逼近。阿納佛突來的奇襲並未使史考特吃驚,現在大鹿反過來追起獵鹿人了。
「打敗賽程就行了。」我告訴自己:「不要管別人,只要跑完賽程就行了。」
踏上通往羅斯.艾利索的山路前,我稍作停留,重新調整自己的狀態。我將頭埋進河裡,在裡面停了一會,希望河水能降下我的體溫,而缺氧的感覺能將我重新拉回現實。我才剛通過路線中點,而且我已經跑了四小時——溫度高如沙漠,路線狀況非常嚴苛,而我只花了四小時!這比我的預期成績好太多了,我開始有了挑戰別人的野心:「要贏過赤腳泰德會不會很難?他的腳在這段石子路應該不會太好過。還有波菲利歐,他看起來似乎快累垮了……」
幸運的是,在河裡泡了一下後,我的腦袋清醒過來,然後我才領悟到,今天我之所以這麼有精神,全是因為我用喀拉哈里布希曼人的方式跑步。我的目標不是追過羚羊,而是保持牠在視線範圍內。上次在巴托畢拉斯山之旅讓我慘不堪言,全是因為我一直想趕上卡巴羅與其他人的速度,但今天到目前為止,我一直只以賽程為目標,從來沒想過與其他選手較量。
在我被眼前的成就沖昏頭前,該是試試另一樣布希曼技巧的時候了。我開始逐一檢查全身各處的狀況。我發現自己的狀況比原先以為的還糟。我又渴、又餓,而且只剩下半瓶水。我已經超過一小時沒有小解,這個徵兆似乎不太妙,因為我喝下的水著實不少。如果不趕快補足水分,吞些卡洛里,待會兒在雲霄飛車般上下的山路可能會遇上大麻煩。開始涉水五十碼到對岸時,我用河水裝滿攜水背包,然後再丟進幾顆碘片,淨化河水大概要花上半小時,所以我趁此時吃了一根能量棒,是用燕麥片、葡萄乾、棗子、糙米糖漿製成的軟質雜糧棒,配上我最後一點清水一起下肚。
好在我先做了上述準備,因為我過河後遇見艾瑞克跑回來時,他對我喊道:「作好心理準備。那裡的路況比你記得的還要難纏得多。」那段山路實在難跑,艾瑞克承認自己也差點退出比賽。聽到這樣的壞消息就像被人在腹部狠狠揍了一拳,不過艾瑞克的信念是,對跑到中途的跑者打擊最大的就是錯誤的期待。未知的事物會使你全身緊繃,不過只要明白自己即將面對的事物,你反而能放鬆心情,一點一滴完成任務。
艾瑞克沒有誇張。接下來一個多小時,我一一上下各座山峰,有時相信自己已經迷失方向,即將葬身曠野,一去不返。這裡只有一條小徑,而我就在小徑上,但羅斯.艾利索村那座該死的葡萄園在哪裡?照理說那裡離河邊只有四英里,但感覺上我似乎已經跑了十英里,卻仍然看不到它。最後我跑到大腿像火燒,而且抖得很厲害,我還以為自己要倒下了,這時我終於看到前方山坡上有一叢葡萄樹。我努力爬到山坡頂部,然後倒在一群烏里克鎮的塔拉烏馬拉人身邊。他們聽說自己已經失去資格,決定在樹蔭底下休息一會,然後再慢慢走回村子。
「沒關係,」其中一人說道:「反正我也累得不想再跑了。」他遞給我一個舊錫杯,我從大家共享的皮諾爾鍋裡大大舀了一杯,管他有沒有梨形鞭毛蟲症。食物是冰冷的,有著甘美的穀類滋味,彷彿是爆米花冰砂。我先大口喝下一杯,然後又舀了一杯,一邊看著我剛剛跑過的路程。遙遠的遠方裡,河流淡得像是人行道上模糊的粉筆字。我無法相信自己居然從那麼遠的地方跑到這裡,而且等等馬上就要再來一遍。
「太驚人了!」卡巴羅驚嘆道。
他現在全身是汗,雙眼因興奮而神采奕奕。大口喘著氣的他抹了汗水淋漓的胸膛一把,我眼前飛過一大堆汗珠,在墨西哥的烈日下閃閃發光。「我們眼前的是世界級比賽!」卡巴羅喘著氣道:「就在這鳥不生蛋的荒郊野外裡!」
比賽進行到四十二英里處,西爾瓦諾和阿納佛仍然領先史考特,珍則在後面逐漸逼近三人。第二次通過烏里克鎮時,珍倒在一把椅子上喝可樂,但蒂塔媽媽抓住她的手臂,將她拉起身來。
「妳辦得到的,甜心!」蒂塔叫道。
「我沒有放棄。」珍反駁,「我只是想喝東西。」
但蒂塔的手就在珍背上,把她推回街上。她回來的正是時候;赫布里托和塞巴提諾趁著回鎮上這段平地的機會拉近距離,現在就在四分之一英里外;「蠢蛋」比利則甩開了路易,離他們兩人也只有四分之一英里。
「大家今天都過癮極了!」卡巴羅說道。他落後領先群大約有半小時,這點讓他焦躁不已,不是因為自己落敗,而是因為他怕錯過結果揭曉的時刻。提心吊膽的感覺實在難過,卡巴羅最後終於決定放棄比賽,趕回烏里克鎮,以便親眼見證最後的大決戰。
我望著他跑開,恨不得自己也能跟上。我已經疲倦不堪,甚至找不到過河的小吊橋,不知怎的竟然跑到了下游,最後不得不第四次涉水渡河。過河後我在沙堆間勉強前進,浸濕的腳重到幾乎提不起來。我已經在野外跑了一整天,現在又再次到達山腳下,也是我早上被死蛇嚇壞時差點跌下的地方。我不可能在天黑前登頂又下山,換句話說,我得摸黑走山路了。
我垂下頭,開始步履維艱地慢慢前進。再次抬起頭時,我發現身邊圍繞著一群塔拉烏馬拉小孩。我閉上眼睛,然後再次睜眼,他們沒有消失。確定他們不是幻覺後,我高興得幾乎要哭出來。我完全不曉得他們從哪裡來,又為什麼選擇跟著我,但我們就這樣結伴慢慢前進,一步步往上坡爬。
這樣前進半英里後,他們閃進路旁一條幾乎看不見的小路,招手要我跟上。
「不行。」我滿懷遺憾地拒絕他們。
他們聳聳肩,奔進樹叢間。我啞著聲驚嘆出聲,因為他們一下子就跑得不見蹤影了。我繼續在上坡路上勉力前進,小跑的速度幾乎不比走路快。好不容易抵達一處小平台時,那些孩子就在那裡等著我。原來這就是烏里克鎮的塔拉烏馬拉人可以領先一大段路的秘密。孩子們蹦蹦跳跳地在我身邊一起跑,然後再一次消失在樹叢中。半英里路後,他們又冒了出來。慢慢地整件事變得像場惡夢:我跑了又跑,卻什麼也沒改變。山峰依然綿延不斷,不管我朝哪裡看,這些玉米的子孫總是會突然冒出來。
卡巴羅會怎麼辦?我忍不住想道。他在峽谷裡不斷遇上各種近乎絕望的難關,但他總是能跑出一條生路。他一開始會放輕鬆跑,我告訴我自己,因為如果你還有力氣這麼做,那代表事情還不算太糟。然後他會輕快地跨出腳步,不花力氣,彷彿他一點也不在乎山有多高,路有多遠——
「大熊!」朝我迎面跑來的是赤腳泰德,他看起來神色倉皇。
「有幾個小孩給我一些水,水很冷,所以我就用它們來沖涼。」赤腳泰德說道。「所以我把水灑到身上,噴濕全身……」
我幾乎聽不懂泰德在說些什麼,因為他的聲音聽起來忽遠忽近,就像收訊不良的收音機。我這才意識到我的血糖已經太低,幾乎快不支倒地了。
「……然後我才發現,糟糕呀糟糕,我沒水了——」
我從赤腳泰德的嘮叨中拼拼湊湊,得知這裡離折返點大概還有一英里。我急著趕到休息站去,在那裡吃根能量棒,休息一下,挑戰最後五英里,根本無心聽他說些什麼。
「……所以我告訴自己如果要撒尿的話,最好撒在這些瓶子裡,這是最後,你也知道,最後迫不得已的手段。所以我把尿撒進瓶子裡,顏色呢,居然是橘色的。這看起來可不太妙,而且氣味臭得很。我覺得看見我撒尿進瓶子裡的人都在想,『哇,這美國佬可真不是蓋的。』」
「等等。」我打斷道,終於開始聽懂他在說什麼。「你該不會是喝了尿吧?」
「味道糟透了!這是我這輩子喝過最難喝的尿。把這玩意裝瓶拿去賣,連死人喝了都會跳起來。我知道人可以喝尿,不過前提是這些尿不能在腎臟裡保溫搖晃上四十英里。這次實驗完全失敗,下次就算全地球就只剩這些尿,我也不會喝半滴。」
「拿去。」我說道,把自己最後一點水給他。我想不通如果他這麼緊張,為什麼不回急救站去裝點水,但我已經累到問不出其他問題了。赤腳泰德倒空他的瓶子,裝進我的水,然後就跑開了。這傢伙怪歸怪,他的應變能力與決心還是不容否認:穿著橡皮五趾套的他,再差五英里就能結束這場五十英里賽跑,而他為了抵達終點,甚至不惜喝下自己的尿。
直到抵達瓜達佩村後,我渾沌不清的腦袋才終於弄懂赤腳泰德一開始為什麼會沒有水:水全都沒了,當地人也全部消失。村民已經下山到烏里克鎮參加比賽後的派對。小商店已經關門,沒有人可以指點泉水的方向。我癱倒在一塊大石上,腦袋天旋地轉,嘴裡乾到嚼不下食物。就算我拼命吃下一點東西,身體也已經缺水到無法再花一個小時跑回村裡。要回烏里克唯一的方法就是靠雙腳,但我已經累到走不動了。
「所謂的慈悲心也不過如此。」我喃喃自語道。「我把水給了別人,自己得到了什麼?不過落得個完蛋大吉。」
就在我垂頭喪氣地坐在那裡時,爬山後急促的呼吸慢了下來,我也開始注意到附近的聲響——一種像是鳥囀般的特殊口哨聲慢慢接近。我抬起身子來看個究竟。就在前方,老鮑伯正爬上這絕望的山峰。
「嘿,好朋友。」鮑伯一邊叫道,一邊從肩袋上找出兩罐芒果汁,舉到頭頂上搖晃。「我想你大概用得著這個吧。」
我吃驚得說不出話來。老鮑伯在九十五度的高溫下爬了五英里艱難的山路,就為了給我帶果汁?然後我想起另一件事:幾天前,鮑伯對我借給赤腳泰德造涼鞋的刀子稱賞不已。那是我之前到非洲探險的紀念品,但鮑伯對大家親切有加,所以我就把刀子送給他。也許鮑伯奇蹟般的現身純屬偶然,但當我大口吞下果汁,準備踏上最後一段路時,我忍不住覺得這正是拼湊塔拉烏馬拉之謎的最後一塊拼圖。
卡巴羅和蒂塔媽媽擠在終點線前的人群中,伸長了脖子,期待領先者的第一道身影出現。卡巴羅從口袋中掏出一只破舊的天美時錶確認時間。六小時。現在還早,但也許——
「他們來了!」有人大喊道。
卡巴羅猛然抬起頭,在興奮的群眾腦袋間眯著眼,望向筆直道路的盡頭。看走眼了吧,只是一陣煙塵而已——不,真的有人來了。來人黑髮飛揚,身穿深紅色長襯衫——阿納佛仍然領先。
西爾瓦諾位居第二,但史考特正快速逼近。就在最後一英里處,史考特追上了西爾瓦諾,但他沒有快速奔過西爾瓦諾身邊,反而用力拍了他的背一把。「快來!」史考特大叫道,揮手要西爾瓦諾跟他一起前進。大吃一驚的西爾瓦諾彎低了身子,趕上史考特的步伐,兩人一起朝阿納佛追過去。
三名選手朝終點線做最後的衝刺,尖叫與歡呼的聲浪蓋過了街頭樂隊。西爾瓦諾慢了下來,然後又重新加快腳步,卻跟不上史考特的速度。史考特繼續狂奔。過去他也曾有同樣的經驗,也就是在逼近終點時發現自己還有餘力猛衝。阿納佛往後一瞥,發現擊敗過世界上最強高手的男人豁出一切朝他追來。阿納佛直衝進烏里克鎮中央,隨著他越來越接近終點線,群眾的尖叫也越來越高昂,當他終於衝破終點線時,蒂塔媽媽已然淚流滿面了。
第二名的史考特抵達終點時,群眾正團團圍住阿納佛。卡巴羅連忙趕過去恭喜他的表現,但史考特一言不發地走開。他不習慣失敗的滋味,尤其不習慣在荒郊野外臨時湊合的比賽中,輸給從沒聽過名號的無名小卒。這樣的事從未發生過,但他知道該怎麼辦。
史考特走到阿納佛身前深深鞠躬。
群眾完全為比賽瘋狂了。蒂塔衝向前擁抱卡巴羅,卻發現卡巴羅正擦著眼淚。在一片混亂當中,西爾瓦諾奮力奔至終點線,在他之後則是赫布里托和塞巴提諾。
珍到哪去了?她不顧生死放手一搏的決定,終於讓她吃到苦頭了。
抵達瓜達佩村時,珍已經快要昏倒了。她跌坐在樹旁,將昏頭轉向的腦袋擱在膝蓋中間。一群塔拉烏馬拉人圍上前來,鼓勵珍重新站起來。她抬起頭來,做出喝水的動作。
「水?」她問道。「乾淨的水?」
有人塞了一罐溫可樂到她手中。
「有這更好。」她虛弱地微笑說道。
她還啜著可樂時,眾人突然一陣呼叫,塞巴提諾和赫布里托正跑進村裡。村民湧上前將他們團團圍住,稱讚他們的表現,問他們要不要來點皮諾爾,珍連他們的身影都見不著。然後赫布里托突然站在她身前,一邊伸出他的手,一邊指向跑道。她要一起跑嗎?珍搖搖頭。「再等等。」她答道。赫布里托原本已經開始跑開,卻突然又停下走回來,他再次對珍伸出手。珍面露微笑,擺手示意要他先走:「快出發!」赫布里托只好揮手道別。
他消失在小徑上不久,眾人又叫了起來。有人告訴珍最新消息:小狼來了。
蠢蛋!珍將自己的可樂留了一大口給他,當比利灌下可樂時,珍勉力站起身來。儘管兩人在許多比賽中互相陪伴過對方,又在維吉尼亞海灘上的落日下併肩奔跑過許多回,他們從來還沒有併肩完成過一場比賽。
「準備好了嗎?」比利問道。
「你說走就走。」
兩人一起跑下長長的下坡路,奔過搖搖晃晃的吊橋,一邊高聲吶喊,一邊進入烏里克鎮。兩人的表現大大提昇眾人對他們的評價:儘管珍的腿受傷流血,比利在比賽前還幾乎睡過頭,但他們打敗了除了領先四人外所有塔拉烏馬拉人,也勝過了路易和艾瑞克這兩名經驗豐富的超馬跑者。
馬努爾中途就退出了比賽。儘管他已經為了卡巴羅盡量努力,但他兒子的不幸讓他無法將心神投注在比賽上。不過雖然無心比賽,他卻盡心盡力幫忙另一位跑者。馬努爾在比賽路線上來回奔跑,尋找赤腳泰德的蹤影。不久之後,先抵終點的跑者也都出來一起尋找其他人,阿納佛、史考特,然後是珍和比利都出動了。接著不尋常的事發生了:儘管後來抵達的跑者速度越來越慢,迎接他們的歡呼卻越來越響亮。每次一名跑者勉力衝過終點線——包括路易和波菲利歐、艾瑞克和赤腳泰德——他們馬上轉身回到賽道中,開始尋找還在比賽的跑者,陪著他們跑回來。
我正在山峰高處,看得見通往烏里克鎮的道路上閃爍成串紅紅綠綠的微光。太陽已經下山,留下我在峽谷深處銀灰色的薄暮中獨自前進。一絲月光般的微光靜靜灑落,週遭事物彷彿凝結在時間裡,除了我之外沒有任何東西改變。然後就從薄暮矇矓的陰影裡,高原上的獨行俠突然出現在我面前。
「要人陪伴嗎?」卡巴羅道。
「歡迎之至。」
我們一起跑過吱嘎作響的吊橋,河面上的清涼空氣讓我有種異樣的飄飄然感。我們轉過通往烏里克鎮上最後一處轉角時,小喇叭開始響起,我和卡巴羅就這麼肩併肩,一步步地跑進鎮上。
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真的越過終點線。我只見到一個甩著馬尾的模糊影子,那是珍從人群裡朝我飛奔過來,撞得我差點站不住腳。艾瑞克在我跌倒前拉住我,將一瓶冷水貼在我後頸。阿納佛和史考特兩人已經紅了眼眶,各自塞了一瓶啤酒到我手上。
「你真是太驚人了!」史考特道。
「是啊,慢得驚人。」我答道。我花了超過十二小時才結束,換句話說,史考特和阿納佛可以來回跑上兩趟,仍然比我早抵達終點。
「沒錯,我就是這個意思。」史考特堅持:「老兄,我以前也有過同樣的經驗。我常常有同樣的經驗。跑得慢時更需要勇氣的支持。」
我一跛一跛走向卡巴羅,他在一片歡聲振耳中懶洋洋地坐在樹下。再過不久,他就會站起身來,用他的蹩腳西班牙話發表一篇動人的演說。他會將恰好即時趕回的鮑伯介紹給眾人,並送給史考特一條塔拉烏馬拉的典禮腰帶,再將鮑伯的一把小刀送給阿納佛。然後卡巴羅會頒發獎金,儘管珍和比利這兩名新新人類連回美國的車票錢都快付不出來,他們仍然當場將自己的獎金轉贈給在他們之後跑抵終點的塔拉烏馬拉族跑者,這個高貴的行為也讓卡巴羅感動到不禁哽咽。然後赫布里托和路易會跳起機器人舞,逗得卡巴羅哈哈大笑。
但這些都是待會的事了。現在卡巴羅正滿足地坐在樹下,一邊微笑一邊啜著啤酒,看著他的夢想在眼前成真。
【未完待續】
故事還沒結束……
二〇〇六年這場驚心動魄的傳奇超馬賽事結束後,白馬卡巴羅依舊住在墨西哥的銅峽谷內,卻也碰上了個天大的好機會。著名的戶外運動品牌The North Face主動希望成為他的比賽贊助商,看起來卡巴羅的下半生與未來在銅峽谷內舉辦比賽所需的經費,似乎都可以高枕無憂了。
卡巴羅仔細思考了一番。大約歷時一分鐘。
「不,多謝了。」他決定:「我什麼都不要,只希望大家都能來跑一跑、吃吃喝喝、跳跳舞、熱鬧一下。跑步不是為了向別人推銷東西。老兄,跑步應該是自由的。」
前情提要
二〇〇六年間,墨西哥的銅峽谷內舉辦了一場史上罕見的五十英里超級馬拉松賽,由擅於長跑的塔拉烏馬拉族人派出「昆馬利家族」,出戰有「超馬之神」的美國選手史考特‧傑瑞克(綽號「大鹿」)以及美國東岸超馬新銳珍‧雪頓(綽號「女巫」)。其他與賽者還有專打赤腳跑步的超馬菁英「赤腳泰德」、曾經贏得夏威夷百英里賽的攝影師路易‧艾斯克博等人。這場超級菁英賽堪稱空前絕後,已是美洲超馬界不朽的史詩傳奇,也成為《天生就會跑》這本書內最精華的篇章。
時序接近比賽當天清晨,忙碌的準備工作正要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