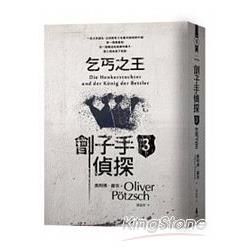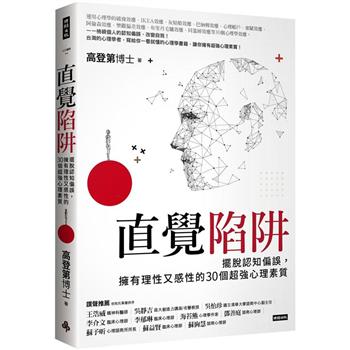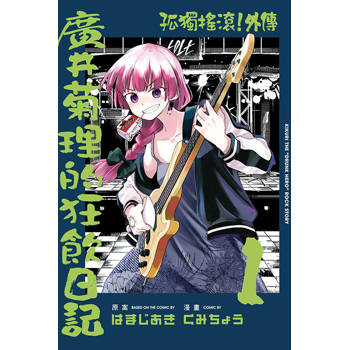確實發生於歷史上的細節,形成他幻想中、
卻又嚴格精心設計的偵探故事中之佐料。
——南德日報
一六六二年八月的雷根斯堡。
最新一次的帝國會議即將在幾個月內召開,有使節已經開始在大城市裡準備會議。這時,匈皋的劊子手雅克布.庫伊斯爾為了探望他生病的妹妹而來到雷根斯堡。而在他妹妹家裡等著他的卻是慘不忍睹的景象:妹妹與妹婿皆被割開喉嚨、躺在血泊中。城市衛兵在屍體旁發現雅克布‧庫伊斯,未加思索即將他以凶嫌的身分逮捕。在刑訊中,雷根斯堡議會想要迫使他召供。如今,劊子手從他雷根斯堡的同行手中體驗到他自己經常使用的刑具:肢刑架、拇指夾……雅克布‧庫伊斯爾拚命苦思對策。他猜想,有人私下想以殘暴的手段報復他。
與此同時,他在匈皋的女兒瑪德蓮娜與醫生西蒙‧佛隆維澤爾被迫放棄他們不合乎禮儀的愛情。在一次的民間私刑中,劊子手的房子幾乎被燒毀,這兩個人因而逃往雷根斯堡。當他們得知雅克布‧庫伊斯爾無辜地被逮捕,而且還面臨處刑的危機時,兩人開始尋找真兇。劊子手可以忍受拷問多久呢?瑪德蓮娜和西蒙只有幾天的時間。他們馬上領悟到,在錯誤指控的背後,隱藏的不只有個人私自報復的願望:有人正在執行一個能夠顛覆整個帝國的計畫。
作者簡介:
奧利佛.普茨(Oliver Pötzsch)
出生於1970年,常年作為電影編劇,服務於巴伐利亞廣播公司,特別是非主流節目「橫貫」。他本身是庫伊斯爾的後裔,庫伊斯爾家族在16至19世紀是巴伐利亞最有名的劊子手王朝。奧利佛.普茨與他的家人生活在慕尼黑。
譯者簡介:
張詠欣
東吳大學德國文化學系碩士,主修德國教育。目前從事德文教學工作。由於熱愛德國足球開始學習德文;嗜好為外語,德英日文佳。喜好遊戲與動漫,奇幻、偵探類型小說亦有涉獵。對人文歷史興趣濃厚,由此愛上旅行,是通過國家考試的外語領隊及導遊。
賜教信箱:yunghsin0112@gmail.com
各界推薦
媒體推薦:
※非常吸引人的偵探小說。我們期待續篇。——紐倫堡新聞。
※是大家所期盼的歷史長篇小說,經過仔細的研究調查,並且投注許多熱情撰寫而成。——濾鏡雜誌。
※不可思議、令人緊張的一本著作。——巴伐利亞廣播公司對劊子手的女兒一書之評論。
※非常精采的故事,同時也就歷史中那段獵捕女巫,以及審判者們寧可相信自己的手段而非影響力,以安撫迷信鎮民的時期,有極為出色的研究……普茨本人即出身劊子手世家,成功創造了一部緊湊易讀、無論是城鎮權力與社會結構的細節或是大學醫科及傳統療法對立都栩栩如生的小說,並高明地透過角色的互動——特別是瑪德蓮娜與西蒙——向讀者溝通。來自最不可能角色最驚人的動機,也讓讀者難以相信竟有如此才華洋溢的作家,第一次便能創作出這樣複雜的故事。——《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
※(普茨)小說讀起來栩栩如生……本著作者的家族歷史,這部刺激的小說令十七世紀的巴伐利亞躍然紙上——它的恐懼、迷信與政治——雅克布‧庫伊斯不是你以為的那種劊子手,而讀著將為這個人物及他對真相的追索感到無法自拔。——《學校圖書館期刊》(School Library Journal)
媒體推薦:※非常吸引人的偵探小說。我們期待續篇。——紐倫堡新聞。
※是大家所期盼的歷史長篇小說,經過仔細的研究調查,並且投注許多熱情撰寫而成。——濾鏡雜誌。
※不可思議、令人緊張的一本著作。——巴伐利亞廣播公司對劊子手的女兒一書之評論。
※非常精采的故事,同時也就歷史中那段獵捕女巫,以及審判者們寧可相信自己的手段而非影響力,以安撫迷信鎮民的時期,有極為出色的研究……普茨本人即出身劊子手世家,成功創造了一部緊湊易讀、無論是城鎮權力與社會結構的細節或是大學醫科及傳統療法對立都栩栩如生的小說,並高明地...
章節試閱
1
巨浪從前面打中雅克布.庫伊斯,將他如一塊浮木那樣沖離板凳。
劊子手在滑溜的甲板上失去平衡,他拚命地到處抓,試圖尋找任何支撐點,直到他突然感覺,他的雙足正沉入河流汩汩旋轉的漩渦裡。他自己將近二公擔的體重緩慢地、卻毫不留情地把他拖進冰冷的水中。他的指甲刮過厚木板,耳邊隱約聽見激動的尖叫聲,彷彿是透過牆壁傳來。最後他的右手抓住一根被打進木頭裡的木匠釘。庫伊斯爾靠著它將自己往上推,這時有另外一個身體也從他旁邊滑進河中。他用空的那隻手往那個方向一抓,剛好抓住一個大約十歲少年的衣領,少年正死命地揮動手腳,急促地喘息。劊子手把他推回船筏的正中央,而鬆了一口氣的父親在那裡用手臂環抱住小男孩。
雅克布•庫伊斯氣喘吁吁地跟在後面爬上來,再度於船首前端的板凳上坐下。他的亞麻襯衫與皮革獵裝緊黏著他的上半身,水流到他的臉、鬍鬚與眉毛上。當他將視線對準前方,他明白了,最嚴重的還在前面等著他們。在他們左邊突出一道巨大的、肯定有四十步高的牆,旅人們如今只能無助地慢慢朝著它駛去。這裡是維騰堡的窄道,幾乎沒有任何一處可與多瑙河這段相比;特別是在漲潮時,這翻騰的地獄已奪走不少撐筏船夫的性命。
「上帝保佑,抓緊!你們要抓緊,看在老天的份上!」
當船筏陷入另一個漩渦中,最前面的舵手急速扭動船槳。肌肉纖維像粗糙的樹根般從他手臂浮出,然而他手中的長棍依舊不為所動。連日來的豪雨使得河水暴漲,淹沒了河岸上向來寧靜的礫灘;樹枝與被連根拔起的樹木在白色浪花中漂流。愈來愈快,扁平的船筏不斷加速地朝懸崖峭壁衝去。當雲杉製的圓木船身刮過石灰玉時,雅克布•庫伊斯聽進身旁傳來難聽的噪音。現在這面牆就在他們正上方,像個石巨人將他的影子投在這一小群人身上。尖銳的稜角挖進船筏左側,並像切麵包一樣把雲杉木製的圓木船身給縱向切開。
「聖聶波穆克,請與我們同在!善良的聖母瑪麗亞,請在急難時幫助我們!聖尼古拉,請饒恕我們……」
庫伊斯不悅地看向一旁,一位修道院修女正抓住象牙十字架念珠,不停地對著無雲的天空哭喊她的祈禱文。木板凳上其他的旅人也臉色蒼白地喃喃訴說著各自的祈求,並在胸前比畫十字。肥胖的富農閉起眼睛、額頭浮現汗珠,等待著他毫無疑問的結局;方濟會的修士以響亮刺耳的假音呼喚起十四位救難聖人。剛才在溺死前一刻被雅克布•庫伊斯救起來的小男孩,現在則緊抱著他的父親哭泣。此時,距離岩石將被壓迫的圓木船身磨碎,只剩下時間的問題。船筏上只有極少數人會游泳,不過這能否幫助他們脫離湍急的漩渦,始終都是個疑問。
「可惡的水,該死!」
庫伊斯吐了一口口水,然後往前撲向舵手的位置。舵手仍在前方試圖用力將以繩索固定在船頭的船槳轉過來。匈皋的劊子手雙腳岔開、站在撐筏船夫旁邊,然後用他粗壯的上半身往長棍施力。他感覺到,在冰冷的河水底下深處,有某個東西纏住了船槳。撐筏船夫的恐怖故事閃過庫伊斯的腦袋:是河底一隻黏滑、惡毒的巨大怪物。昨天漁夫才跟他提過,多瑙河決口的一個洞穴中,可能住著一隻長達五步的鯰魚。在那下面,到底是什麼該死的東西抵住了長棍?
同一時間,他又感覺到船槳稍微被移動了一下。他呻吟著繼續頂住,有一種骨頭隨時會斷裂的感覺。最後一次響起嘎吱聲,船槳突然鬆開,船筏逆著漩渦旋轉,並隨著最後的震動從懸崖峭壁僵硬地彈開。
一轉眼,他們像箭一般迅速飛向河岸右側的三座岩石小島,一些旅人再度尖叫起來,然而撐筏船夫此時又控制住他們的船隻。船筏急速衝過被浪花沖刷的岩峰,接著船首再度潛入水中;然後他們度過了危險的河流窄道。
「非常感謝你!」舵手擦去眼睛上的汗水與河水,並對庫伊斯伸出他長繭的手。「長牆差一點就讓我們所有人都斃命了。你想不想當個撐筏船夫?」他對庫伊斯咧嘴一笑,同時摸著庫伊斯的二頭肌。「你有兩頭牛的力氣,而且可以像我們這樣罵人。所以,如何?」
雅克布•庫伊斯搖搖頭。「願上帝保佑你。但是你們不會願意我加入的。再來一次那樣的漩渦,我就會把你們丟進水裡。我需要腳底下的土地。」
撐筏船夫大笑,而庫伊斯甩了甩蓬亂、潮濕的頭髮,水珠四下飛濺。
「還有多久才會到達雷根斯堡?」他問舵手。「這條河仍讓我覺得頭暈。我肯定這是第十次,我認為我們會死在這裡了。」
雅克布•庫伊斯回頭望向仍聳立在河岸兩側的懸崖峭壁。有些形狀讓他想起石化的猛獸,或是巨人的頭顱,他們往底下盯著些熙來攘往的凡人。他們不久前經過維騰堡的修道院,那裡因為戰爭與高水位的侵蝕,已經成為廢墟。儘管它現在悲慘的狀況,還是有些旅人會造訪該地,以尋求寧靜的祈禱。緊鄰其上的河流窄道,在凶猛的降雨之後,被每位撐筏船夫視為真正的挑戰——在這之前唸段主導文也無妨。
「我向上帝發誓,長牆是最險峻的位置,」舵手說道,並比畫了一個十字。「特別是在水位高漲之際。但是,接下來就平靜了,我跟你保證。我們再過幾個小時應該就能抵達。」
「希望你說得沒錯,」劊子手嘀咕。「否則我就用你那根該死的船槳打你的背。」
雅克布•庫伊斯轉身離開,並踩著小心翼翼的步伐,沿著板凳座位間狹窄又溼滑的走道步向後方,那裡存放著裝成桶子與箱子的貨物。他相當厭惡搭船旅行,即使要前往其他城市這肯定是最快、而且最安全的方法。劊子手比較愛感受腳底下森林的堅固地面。圓木是用來蓋房子、製造桌子的,或對他來說是製造絞刑架的,而不是用來搖搖晃晃經過湍急的水流時、讓人在上面跌跌撞撞行走的。庫伊斯爾很高興這陣搖擺即將結束。
旅人臉上此時又重現了一些顏色,並鬆了一口氣地禱告或歡笑,他們懷著感謝的心打量庫伊斯。獲救少年的父親想要擁抱他,但劊子手推開這個男人,然後喃喃自語地消失在被包裹起來的箱子之間。
這裡,在多瑙河上,他離家鄉已經有四天的旅程了,無論是旅客或全體船員都不知道他是匈皋的死刑執行官。這對前端的舵手來說也是一件幸運的事。如果劊子手幫助撐筏船夫掌舵的事傳開,那個男人可能會被驅逐出同業公會。庫伊斯聽說過,在某些地區光是和死刑執行官眼神接觸,就能夠毀壞一個人的名聲。
在存放貨物區域的後半部,雅克布•庫伊斯爬上一個裝有醃漬鯡魚的桶子,並點燃他的菸斗。現在,在穿過維騰堡惡名昭彰的狹窄河道後,多瑙河再度變得寬敞起來。小城市克爾海姆在左手邊出現,裝載滿沉重貨物的駁船從船筏旁邊如此接近地滑行而過,庫伊斯幾乎可以觸碰上面的貨物。從另一艘距離更遠的船隻上,可以聽見小提琴演奏的樂曲,伴隨著鈴鼓叮鈴噹啷的聲音。一艘像房子一樣寬的船正好從那後面犁過,從容地滑過水流。那艘船載了石灰、紫檀木與磚瓦,它吃水很深,因此不斷有小浪花沖刷過圓木船身。當有一些較小的漁船危險地接近它時,船筏大師就會站在交通工具正中央臨時搭建起來的船樓上,敲響警鐘。
劊子手吐出幾朵菸草雲,讓它們攀升到蔚藍、而且幾乎沒有雲的夏季天空,試圖忘卻他這趟旅行的悲傷理由幾分鐘。距離現在已經六天了,一封來自遠方雷根斯堡的信送到他在匈皋的家。信上的內容對他造成莫大的打擊,庫伊斯根本不願向他的家人說明。他的妹妹伊麗莎白幾年前成為澡堂老闆的妻子,生活在遙遠的帝國城市,如今她生了重病。據說是腹部有腫瘤,以及可怕的疼痛和黑色的分泌物。在用潦草字跡寫於羊皮紙上的字裡行間,他的妹婿請求他盡可能馬上趕往雷根斯堡,因為不確定伊麗莎白還能活多久。因此,匈皋的劊子手清理了家中的醫藥櫃,將罌粟、山金車菊與聖約翰草打包進他的亞麻袋裡,並登上下一班駛往多瑙河的船筏。身為死刑執行官,事實上他並能在沒有議會的批准下離開城市,但是庫伊斯完全不理會這項禁令。就讓法院書記官約翰•雷希納爾在他回來以後,用四匹馬將他支解吧!他妹妹的命運對他來講更重要。庫伊斯不信任受過大學教育的庸醫,他們大概只會給伊麗莎白放血,直到她像個浮水屍體一樣慘白。如果有人能幫助他妹妹,那就只有他自己,別無他人。
匈皋的死刑官殺人,也治療人。兩方面他都是高手。
「嘿,大塊頭!要不要也來喝一杯啊?」
驟然從他的思緒中被拉回來,雅克布•庫伊斯抬起頭,看見撐筏船夫向他舉起玻璃杯祝酒。劊子手搖搖頭,接著把他的寬邊軟呢帽拉到額頭上,以保護自己不受強烈的日光照射。他的大鷹勾鼻從帽沿底下凸出來,而鼻子下方則插著冒水蒸氣的菸斗柄。在帽子的隱蔽下,他打量著旅人及撐筏船夫們。那些船夫就站在箱子之間的正中央,飲下一口燒酒,為他們戰勝可怕的航段而舉杯慶賀。有一個念頭困擾著庫伊斯,它就像惱人的蚊子般來來去去,而只有在經過長牆邊的漩渦時,這個想法才短暫地被屏除。
從啟程以來,他就有種被監視的感覺。
這並非精明,只不過是直覺,與他長期在大戰中擔任傭兵所掌握到的經驗,兩者相互作用的結果。他的肩胛骨之間輕微地發癢。他不知道是誰、以及為什麼要監視他,不過搔癢的感覺持續存在。
庫伊斯環顧四周。在乘客間有兩名方濟會的僧侶,以及一位修女,除此之外還有四處遊歷的工匠、旅人及一些單純的商賈。連同劊子手在內,總共有大約兩打人參加五艘船筏組成的船隊。在多瑙河這上面,有可能只花一星期不到就旅行至維也納,三個星期甚至能抵達黑海。夜晚,當船筏都停泊在河岸時,大家會在火堆旁碰面,彼此交換一、兩句話,並敘述他們之前的旅行和遇見的危險。只有庫伊斯不認識任何人,因此大多都是獨自一個人坐著。他這麼做是對的,反正他也只把大部分的人當作是愛聊天的傻瓜。每天晚上,劊子手都從他坐的邊緣位置觀察那些男男女女,看他們圍繞著火光而坐,歡笑、喝廉價的葡萄酒並啃著他們的羊腿。而他始終相信,自己感覺到一個視線正不停地瞄準他。而現在是正午時分,他的肩胛骨之間依然發癢,就像有小蟲子在上面爬。
雅克布•庫伊斯讓雙腿從木桶上垂盪下來,做出無聊的樣子。他重新填塞他的菸斗,並往遠方的河堤望去,就像在觀察站在那裡的一群小孩,他們從斜坡處朝他揮手。簡直就像是他正在觀察從斜坡那邊朝他揮手的一群孩子。
然而,他相當突然地將頭轉向船尾。
不到短短一秒間,他注意到有一個人朝著他這邊緊盯不放。是負責操作船筏後半部船槳的第二位舵手。根據庫伊斯的記憶,他是在匈皋上船的。這個男人相當肥胖,而且幾乎要和劊子手一樣高大,在他藍色短上衣的側邊掛著一把與前臂同長的獵刀。他的肩膀寬大,大腹便便的肚子在銅腰帶與及膝短褲上隆起,他將及膝短褲塞進粗糙的長筒皮靴中。他頭上戴著船員間常見的提洛爾帽。但是最引人矚目的是男人的臉。整個右半邊布滿了凹痕與傷疤形成的皺紋,大概是出於嚴重的燒傷。男人的一隻眼窩上戴著黑色眼罩;一道發著微光、略呈紅色的傷疤從他的額頭延伸到下巴,就像一條肥蟲在來回抽動。
庫伊斯爾瞬間覺得他看到的並不是一個臉,而是一團形狀詭異的東西。
一張充滿怨恨、醜陋的臉。
這個片刻轉瞬即逝,舵手再度彎腰到他的船槳上。他迴避劊子手,就好像他們的眼神從未接觸過。
一片過去的景象從庫伊斯的腦中掠過,但他來不及捉住它。多瑙河緩慢地從他旁邊流過,並帶走了記憶。只留下模糊的揣測。
究竟是在哪裡……?
雅克布•庫伊斯認識這個男人。他不記得是在哪裡,不過他的直覺正在警告他。匈皋的死刑執行官在大戰中擔任傭兵,認識了各式各樣的人:懦弱的與勇敢的、正直的與狡猾的、犧牲者與殺人者,其中有許多人因為戰爭而變得瘋狂。只有一件事庫伊斯可以肯定:距離他只有幾步、從容地將船槳划過水中的這個男人,十分危險。既奸詐又危險。
劊子手不慌不忙地挪正他腰帶上用松木製成的棍棒。一切的一切都不構成擔心的理由。有足夠的人會站在他這邊。
雅克布•庫伊斯在小村莊普呂芬寧離開船筏,距離雷根斯堡已經只剩幾哩路程。
劊子手露齒一笑,同時把裝有藥物的袋子背上肩,再一次向撐筏船夫、商人與工匠們揮手道別。如果那個臉上有燒傷的陌生人真的跟在他後面的話,那他現在就有麻煩了。身為舵手,在船筏抵達雷根斯堡前,他很難從甲板下來。這名船夫確實用他健康的那隻眼睛朝庫伊斯瞪來,幾乎就像他也要跳到小防坡堤上一樣——不過後來他改變心意——最後他投來充滿怨恨的一眼,只有一瞬間,所以沒有人發現,接著他再度轉回去做他的工作,將又濕又滑、胳臂般粗的繩索綁在防波堤的柱子上。
船筏停泊在原處,直到要前往雷根斯堡的少數旅客登船,才啟程緩慢地划往帝國的主要城市;城市中最高的幾座塔已經可以從地平線上望見。
雅克布•庫伊斯短暫地目送船筏離開,然後用口哨吹著士兵的行軍進行曲,沿著通往北邊的狹小街道邁進。很快地,他就離開了這個小村莊,左右兩側有在風中波瀾起伏的麥田一路展開。一塊界石標示出分界線,庫伊斯從這裡離開巴伐利亞的領地,踏入帝國自由城市雷根斯堡的區域。到目前為止,他只從故事中得知這個著名的地點。他知道,雷根斯堡算得上是帝國中最大的城市之一,並直接隸屬於皇帝。而且他還聽說,所謂的德意志帝國會議將在此處舉行,選帝侯、主教與公爵們聚集一堂,協商帝國的命運。
當庫伊斯正從遠處眺望高聳的城牆及高塔時,思鄉之情突然襲向他。匈皋的劊子手不是為了這個廣大的世界而誕生的,在教堂後面的「太陽釀造」客棧、綠色的萊希河與深邃的巴伐利亞森林,這些對他來說就已足夠。
時間是八月的一個炎熱正午,太陽位於他正上方的天空,令穀物閃耀著金色的光芒。在更後方,開始有黑色的雷雨雲於地平線上聚攏。右側有一座絞刑丘聳立在田野間,上面有一些軀體在輕輕地前後搖擺。荒廢的小碉堡證實了大戰距今也並不遠。劊子手早就不是獨自一人在街上了。馬車與獨身的騎馬者從他身旁疾馳而過,牛隻緩慢地拉著載有來自周邊地區農夫的運貨車。廣大的人流喧鬧嘈雜地往雷根斯堡湧進,最後堵在西側城牆的高聳大門前。在穿著毛料衣物與粗劣料子的貧窮農夫、朝聖者、乞丐與貨物搬運車夫之間,雅克布•庫伊斯還可不斷瞥見裝扮華麗的城市新貴,他們騎乘高大的駿馬,在人群中闢出一條路來。
匈皋的劊子手皺著眉觀察這罕見的人群行進。顯然,很快又要舉行一場這所謂的帝國會議。他排進這條站在大門前、等待入城許可的人龍。依照責備與咒罵聲判斷,似乎會花上比平常還久的時間。
「嘿,大個子!那上面的空氣怎麼樣?」
雅克布•庫伊斯朝著這個顯然在向他搭話的農夫彎下腰。當這名矮小的男人發現,劊子手咧嘴而笑的臉就在他眼前時,他不禁吞嚥了一下口水,接著才繼續開口。
「你可以看見前面發生了什麼事嗎?」他帶著些微的微笑問道。「我一個星期會帶我的紅蘿蔔上市場去兩次;通常都是星期二和星期六;但我還沒有碰過這種混亂。」
劊子手踮起腳尖。用這個方法,他高出所有站在附近的人幾乎兩顆頭。庫伊斯可以看到大門前正站著半打守衛。這些武裝男子拿著錫製的大門金錢箱,向每位過路人收取通行費。守衛在農夫們憤怒的抗議聲中,不斷拿刀子往裝載穀物、稻草和甘藍菜的貨車刺進去,完全就像是在尋找某人。
「他們正在檢查每輛貨車,」劊子手喃喃地說,並挖苦似的向下看著農夫。「是皇帝進城了,還是你們總是搞得這麼麻煩?」
男人嘆了口氣。「或許是又有哪位重要公使要駕臨吧。話說,帝國會議確實是明年才要召開啊!再是繼續這樣下去,在我抵達海德廣場之前,所有的市場攤位就都收攤了;可惡!」他咒罵道,並憤怒地咬了一口他放在前面籃子裡的紅蘿蔔。「該死的公使!真是像穆斯林一樣的災害!他們帶給城市的就只有麻煩。不用動一根手指就能阻礙交通。」
「他們為什麼會在那裡?」雅克布•庫伊斯問道。
農夫笑了。「為什麼?為了將我們剝個精光,就是這樣!沒有賦稅還帶來他們自己的工匠,那群人搶走了我們的工作!他們宣稱要共同想出對策,好阻止該死的土耳其人入侵德意志帝國;但要是你問我的話,我會告訴你那只是空談!」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為什麼皇帝不也去其他城市召開一次他的帝國會議?但是不,他沒這麼做,而是每隔幾年就要重新找我們麻煩。民眾幾乎都要相信,那些公使一直住在這邊了!」
雅克布•庫伊斯點點頭,儘管他並不是真正很用心在聽。這個帝國會議關他什麼事?他只想見到他的小伊麗莎白。即使這些高層官員們,這段時間正冷靜地決議發動下次戰爭。他們將會找到夠多的人,可以為了金錢與名聲而犧牲生命。而他,無論如何都不會再去做大規模的砍殺與刺殺這類事。
「那你呢?你為什麼會來這裡?」農夫繼續問道。「你已經有可以過夜的地方了嗎?」
雅克布•庫伊斯閉上眼睛。顯然,他是被整個雷根斯堡地區最愛說話的農夫給纏上了。
「我會住在我妹妹家。」他嘀咕,希望這個矮個子的男人能夠讓自己安靜一會兒。
這段時間,劊子手和他的鄰人不斷在人龍中往前移動。只剩兩輛裝載乾草的貨車,將他們和所謂的雅克布斯大門分開。守衛往貨運車底下張望,並拿刀刺進乾草中,揮手示意車輛通過,再轉身處理下一個通行者。可以聽到遠方傳來第一聲雷鳴;不久後,雷雨將會來臨。
最後,隊伍終於輪到他們。農夫不用進一步檢查就可以通過,然而雅克布•庫伊斯卻被揮手叫過去。
「嘿,你!沒錯,就是你!」一名頭戴鋼盔、身穿胸甲的哨兵指著劊子手,並示意要他上前來。「你從哪裡來的?」
「從奧古斯堡下面的匈皋。」劊子手低沉地說,同時看著面前的人,就像在觀察一顆石頭。
「是嗎,來自奧古斯堡……」守衛開口,捻著他那充滿藝術性的鬍鬚。
「不是奧古斯堡,是匈皋。」劊子手嘀咕。「我不是骯髒的施瓦本人,我是巴伐利亞人。」
「無所謂。」守衛回答,並對他身後的同事眨眼示意。然後他打量著庫伊斯,就好像在拿他與一張內心的圖像核對。「你來這裡做什麼,巴伐利亞人?」
「我妹妹住在你們這兒,」劊子手簡潔扼要地回答,沒有對那嘲諷的影射口吻做出回應。「她生了重病,而我要來探望她;如果你們允許的話。」
衛兵沾沾自喜地咧嘴笑了。「你妹妹,這樣啊。喏,如果她看起來就像你這樣,你很快就會找到她。」他大笑,並再度笑嘻嘻地轉向他的同事。「有鷹勾鼻的活生生岩石在我們這裡很少見,不是嗎?」
大笑聲從他們四面八方響起。雅克布•庫伊斯保持沉默,同時衛兵繼續揶揄道:「我聽說過,他們用起司麵條餵你們這些施瓦本人,直到麵條從你們的耳朵跑出來。這個東西會讓人變得又肥又笨,你就是最好的證明。」
臉部表情絲毫不變,劊子手向這個男人跨近一步,然後抓起他的領子。當雅克布•庫伊斯將他朝自己往上拉時,守衛的眼睛像玻璃彈珠一樣凸出來。
「聽著,年輕人,」他嘀咕道:「如果你想從我口中知道什麼,那就直接告訴我。否則就閉上你的嘴,讓我過去。」
突然間,劊子手感覺到他背上抵著刀尖。
「放他下來,」聲音在他背後響起。「慢一點,大塊頭。否則我就把刀插進你的腸子裡,然後讓它從前面出來。你聽懂我說的話了嗎?」
劊子手慢慢地點頭,然後將這個嚇壞了的男人放回地上。當雅克布•庫伊斯轉過身時,他看見一位身材高大、身穿閃亮鎧甲的守衛長站在他前方。和他的同僚一樣,他有著捲曲的大鬍子、從在陽光底下閃閃發亮的頭盔中露出金色的毛髮。他的刀子現在直接舉在雅克布•庫伊斯的喉嚨前面。此時已經有一小群愛看熱鬧的民眾圍觀,急切地等待接下來將發生的事。
「這樣很好,」首領將嘴唇拉成一條細線,微笑說:「現在你轉過身去,然後我們一起走樓梯到塔樓上面去。那裡有給巴伐利亞人反省的臨時處所。」
領頭的大門守衛將他的刀尖移到距離劊子手喉嚨只有幾公分的地方,以強調他的要求。瞬間,庫伊斯想要抓住刀子、把這個男人朝自己拉過來,然後用松木棍攻擊他的兩腿之間。但是後來他注意到其他守衛,他們高舉長槍與斧槍包圍他,並在一旁竊竊私語。他怎麼能夠讓自己被激怒呢!這簡直就像是該名守衛故意設計要挑釁他。難道雷根斯堡人都是這樣對待外地人的嗎?
雅克布•庫伊斯轉過身,然後朝著塔樓走去。他只能祈禱在他妹妹蒙主寵召之前,他們能夠釋放他。
當門在劊子手的身後關上時,第一陣雨滴在外面劈啪作響,落到鋪石路面上。大雨緊接著淅瀝嘩啦地下,在大門前面等待的人於是將大衣拉到頭上,或是到附近堆放乾草的穀倉裡尋求庇護。冰雹跟鴿子蛋一樣大,從天而降,因此有些農夫開始咒罵自己沒有早一點收成作物。這已經是本星期第三次的暴雨,大家祈禱著,並在起居室裡掛有耶穌像的牆角緊緊窩在一起。有不少鄰近村莊的居民都將暴雨視為上帝正義的怒吼。祂以此來懲罰那些可惡城市的放縱過度!五顏六色的衣服、投機買賣、嫖妓、傲慢自大,以及愈蓋愈高的房子。索多瑪與蛾摩拉不正是以類似的方式走向滅亡的嗎?明年一月帝國會議舉行時,所有傲慢的高層大人們又會來到此處,他們將酗酒、嫖妓,而且用他們自己的權力取代彌撒來舉行儀式——儘管如此,確實只有上帝能決定德意志帝國的幸福與痛苦!
在一個巨大的爆裂聲響中,一道閃電擊中防禦通道上方;接著是一陣雷鳴,連遠至艾莫蘭廣場的小孩都在哭泣。在緊接而來的這陣閃電閃光中,可以看見一個人影從雅克布斯大門努力往城市的方向前進。這個男人彎腰行走,冰雹與雨水打在他臉上。沒有其他人敢在這樣的天氣裡走在街上。但是這個男人必須傳達訊息。
他臉上的傷疤在痛。一如往常,每當天氣變化時總是如此。劊子手差點從他手中溜走,但是這個男人知道,他的敵人必須通過雅克布斯大門。沒有其他可以從西邊進入城市的道路。因此,他從船筏渡口以最快的路線奔往大門,去那邊通告守衛。用一點錢爭取到不可或缺的時間,也就是他們需要將行動付諸執行的時間。
復仇……他們兩個已經等待多久了!
男人咧嘴而笑,他臉上的傷疤開始激動地顫動。
1
巨浪從前面打中雅克布.庫伊斯,將他如一塊浮木那樣沖離板凳。
劊子手在滑溜的甲板上失去平衡,他拚命地到處抓,試圖尋找任何支撐點,直到他突然感覺,他的雙足正沉入河流汩汩旋轉的漩渦裡。他自己將近二公擔的體重緩慢地、卻毫不留情地把他拖進冰冷的水中。他的指甲刮過厚木板,耳邊隱約聽見激動的尖叫聲,彷彿是透過牆壁傳來。最後他的右手抓住一根被打進木頭裡的木匠釘。庫伊斯爾靠著它將自己往上推,這時有另外一個身體也從他旁邊滑進河中。他用空的那隻手往那個方向一抓,剛好抓住一個大約十歲少年的衣領,少年正死命地揮動手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