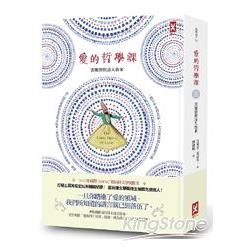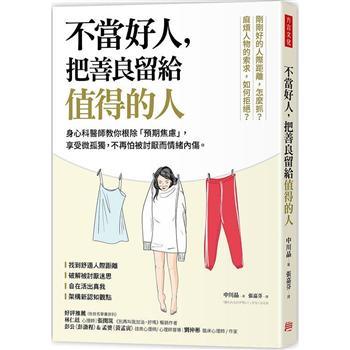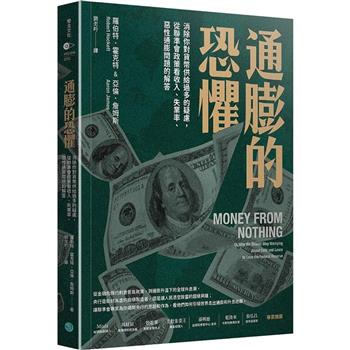★2012年國際IMPAC都柏林文學獎提名★
!打破土耳其有史以來暢銷紀錄!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接班人!
一旦你踏進了愛的領域,
我們所知道的語言就已經落伍了。
伊斯蘭世界的莎士比亞,
魯米受雲遊僧「愛的四十法則」啟發,
成為偉大詩人的傳奇經歷!
年輕時主修文學、如今已過了二十年平凡主婦生活的艾拉,為了躲開變調的婚姻,在一家文學經紀公司覓得工作,第一個任務就是試讀一部投稿小說《甜蜜褻瀆》。
這部從遠方投遞的作品,帶她走進了13世紀更遙遠陌生、神祕又迷人的世界,也使她了解到「一般人無法理解的愛,其實正是通往更深沉智慧與洞見的管道」。
七百多年前,兩個渴求找到靈魂知己的人相遇了。
受人景仰的伊斯蘭神學家魯米,與異教雲遊僧夏慕士,兩人一認識就在書房閉關四十天,夏慕士向魯米分享「愛的四十條法則」:
追尋愛的人,沒有一個不會在路途中成熟。
尋找愛,就是尋找靈魂伴侶的過程——這個人是自己的鏡子,映照出自己生命的匱乏。
你可以靠齋戒禁食淨化身體,但只有愛才能淨化你的心。
正如陶土必須經過高溫淬鍊才會變硬一樣,唯有歷經痛苦的愛才能臻至完美。
一旦你踏進了愛的領域,我們所知道的語言就已經落伍了。……
魯米受此啟發,成為吟詠愛的偉大詩人,更發明了蘇菲派苦行僧的迴旋舞。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接受魯米與夏慕士的想法,他們在精神上的緊密聯結,也成為謠言與誹謗攻訐的目標,甚至還遭到最親近的人背叛……
從13世紀以來,魯米以歌頌愛的詩句聞名於世,有「伊斯蘭世界的莎士比亞」美稱;而他與蘇菲派雲遊僧夏慕士堅定而特殊的友誼,更為人所津津樂道。本書作者擷取魯米的詩與夏慕士的言談,將他們之間的動人事蹟,一一重現在《愛的哲學課》中,並將13世紀與21世紀的時空巧妙交錯,在其中點綴含意深遠的寓言,帶出關於愛的各種哲思。出版後普受好評,銷售量逾75萬冊,成為土耳其有史以來最暢銷的書。獲得2011年法國心靈圖書獨立書店協會外國文學特別獎,以及2012年國際IMPAC都柏林文學獎的提名。
作者簡介:
艾莉芙.夏法克(Elif Shafak)
土耳其小說家、專欄作家、學者。1971年出生於法國史特拉斯堡,畢業於土耳其中東理工大學國際關係學系,擁有性別及女性研究碩士學位,與政治學博士學位。
夏法克目前共出版12本書,其中8本為小說。寫作成績斐然,不但獲獎無數,更是讀者最多的土耳其女性作家,被讚譽為「當代土耳其與世界文學中最出色的聲音之一」。
從1998年開始,夏法克以土耳其文寫了四部小說,在土耳其創下高銷售量,並獲得獎項肯定。從2004年開始,她開始以英文寫作,拓展其作品在全球各地的能見度。其中,《伊斯坦堡的私生女》內容引起爭議,令她曾經遭到起訴,被土耳其當局列入黑名單。她在第三本英文小說繼續挑戰宗教與思想的禁忌,以魯米和雲遊僧夏慕士之間的故事為藍本的小說《愛的哲學課》,銷售量已逾75萬冊,成為土耳其有史以來最暢銷的一本書。
夏法克的作品目前已被翻譯成三十餘種文字,並在2010年獲頒法國文藝騎士勳章的殊榮。除了小說,夏法克還書寫大量關於女性、少數族裔、移民、年輕人與訴諸全球心靈的故事;同時也對歷史、哲學、蘇菲派神祕主義、文化、政治有極深的興趣。她現在仍然持續替土耳其一家主要報紙《Haberturk》,以及好幾家國際性的日報與周刊撰稿,其中包括英國《衛報》的網站。
查詢更多關於的夏法克訊息,請連結官網:http://elifshafak.com/
作品獲獎/入圍紀錄
土耳其文作品
★《神祕主義者》(Pinhan),1998年土耳其魯米獎.最佳神祕主義文學作品
★《凝望》(Mahrem),2000年土耳其作家協會最佳小說獎
★《跳蚤宮殿》(Bit Palas),入圍英國《獨立報》最佳小說獎決選名單
英文作品
★《伊斯坦堡的私生女》,入圍2006年柑橘獎初選名單
★《愛的哲學課》,2012年國際IMPAC都柏林文學獎提名
★《名譽》(Iskender),2012 年曼氏亞洲文學獎(Man Asian Literary Prize)提名
譯者簡介:
劉泗翰,資深翻譯,悠遊於兩種文字與文化之間,賣譯為生近二十年,譯作有《四的法則》、《卡瓦利與克雷的神奇冒險》、《裴少校的最後一戰》、《陌生人的孩子》、《非普通家庭》等二十餘本。
章節試閱
艾拉
二○○八年五月十七日,北安普頓
艾拉一個人在露台,坐在她最喜歡的搖椅上,看著橘紅鮮艷的北安普頓落日;感覺上,天空是如此的廣袤又如此的逼近,好像一伸手就可以摸得到似的。她腦子裡一片寧靜,彷彿厭倦了裡面的種種噪音:這個月的信用卡帳單、歐莉的不良飲食習慣、艾維慘不忍睹的成績、愛思德阿姨跟她可悲的蛋糕、她的狗狗小精靈的健康每況愈下、珍妮特的結婚計畫、她丈夫的祕密外遇、她那沒有愛的生活……她將這些聲音,一個個鎖進小小的心靈保險箱裡。
在這樣的心理狀態下,艾拉從紙袋裡抽出書稿,放在手上拍一拍,彷彿在掂掂它的重量。書名以藍色墨水寫在封面上:甜蜜褻瀆。
艾拉只知道有人真的認識這位作者──某位住在荷蘭的阿濟茲.薩哈拉先生。他的書稿從阿姆斯特丹寄到這家文學經紀公司,信封裡還附了一張明信片;明信片的正面是一大片炫麗奪目的鬱金香,遍地的粉紅、金黃與姹紫,背面則用秀麗的筆跡寫著:
親愛的女生/先生,
這是來自阿姆斯特丹的問候。隨信附寄給您的故事發生在十三世紀小亞細亞的孔亞,但是我衷心希望這個故事能夠跨越國界、文化與時代。
我希望您有時間閱讀《甜蜜褻瀆》,一本神祕的歷史小說,講述魯米與塔布里斯的夏慕士之間的故事,他們一個是伊斯蘭史上最偉大的詩人和最受尊崇的精神領袖,一個卻是不為人所知,不遵循傳統,醜聞纏身又充滿驚奇的蘇菲教派僧侶。
願您始終與愛同行,也始終受愛包圍。
薩哈拉 謹上
艾拉意識到這張明信片勾起了文學經紀人的好奇心,可是史蒂夫是個大忙人,沒有時間看業餘作者的書稿,於是就交給了他的助理蜜雪兒,然後她又轉交給她的新助理,所以這本《甜蜜褻瀆》最後才會落在艾拉的手上。
她完全沒意識到這不僅僅是隨隨便便的一本書,而是那一本改變她生命的書。在她閱讀這本書的同時,她的生命也改寫了。
艾拉翻開第一頁,上面有作者的小傳。
薩哈拉在沒有雲遊四方的時候,就跟他的書、貓和烏龜一起住在阿姆斯特丹。《甜蜜褻瀆》是他的第一本小說,也很可能是最後一本。他並不想成為小說家,寫這本書純粹因為他發自內心的景仰與愛,獻給偉大哲學家、神祕派詩人魯米,以及他最愛的太陽──塔布里斯的夏慕士。
她的目光往下看了幾行,然後看到一些熟悉的有點怪異的字眼。
因為儘管有人這樣說,但是愛絕對不只是來得快、去得也快的甜蜜感覺而已。
她發現這句話跟她今天下午在廚房裡跟她女兒所說的話正好針鋒相對,連用字都一模一樣時,訝異地張大嘴巴,彷彿下巴都快掉下來。她靜靜地站了一會兒,想到這冥冥宇宙中有一股神祕的力量,不由得渾身顫抖;又或者是這位作者──姑且不論他是何方神聖──正在監視她。或許他在寫這本書的時候,就已經預先知道什麼樣的人會第一個看到這份書稿,所以這位作者就以她為讀者來創作。不知道什麼原因,這個想法讓艾拉既困擾又興奮。
在很多方面,二十一世紀跟十三世紀沒有那麼大的差別:在歷史上,二者都目睹了前所未有的宗教衝突、文化誤解和普遍的不安全感以及對他者的恐懼;在如此的時代之中,對愛的需求就以前更強烈。
突然有一陣風往她這裡襲來,強勁清涼,吹得落葉飄滿了露台;夕陽美景往西方的地平線飄散,氣氛突然變得單調無趣。
因為愛是生命的原始根本與最終目的。誠如魯米所說,愛會發生在每一個人的身上,包括那些逃避愛的人──即使有人會把「浪漫」視為禁忌的象徵。
艾拉接下來看到的文字,更是讓她震驚到無可復加:
愛會發生在每一個人的身上,就連住在北安普頓一位叫做艾拉.魯賓斯坦的中年家庭主婦也不例外。
她的本能告訴她:立刻放下書稿,回到屋子裡,打電話跟蜜雪兒說她絕對不可能寫這本小說的審閱報告。可是她沒有這麼做,反而深呼吸一口氣,翻開書頁,繼續讀下去。
________
夏慕士
一二四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巴格達
在垂懸冰柱與雪封道路之外,有名信差從遠處走來;他說,他來自開塞利。此事在僧侶之間引起了一陣騷動,因為大夥兒都知道:在這個時節有客人來訪比吃到甜美的夏日葡萄還要難得。信差身懷緊急訊息穿越暴風雪而來,只有兩種可能:要不是發生了什麼可怕的事,就是有什麼重要的事情即將發生。
信差的到來在僧侶修院裡引起議論紛紛,大家都很好奇,不知道交給師父的那封信內容為何;可是他彷彿披上了神祕的斗篷,絲毫沒有透露。好幾天來,他不動聲色,不時地陷入長考沉思,充滿了戒心,臉上偶爾露出那種天人交戰的表情,好像很難下定決心的樣子。
在這段期間,我用心觀察巴巴•札曼,倒不全然只是出於好奇,而是因為在我內心深處隱隱然覺得那封信與我個人有關,只不過我一時也說不上來有什麼樣的關係。有好幾個晚上,我在禱告室裡祈禱,覆誦真主的九十九個尊名,祈求真主指引;結果每一次都有同樣的名字跳出來:「大能的主」──在祂的統治之下,除了祂願意發生的事情之外,其他事情都不會發生。
在接下來的那幾天,修院裡的每個人都在猜測那封信裡到底寫了些什麼,但是我卻獨自在花園裡,觀察在密雪覆蓋下的大自然。終於有一天,我們聽到廚房裡的銅鈴不斷地響,召集我們所有的人緊急聚會。等我走進僧侶中心(khaneqah)的主屋,看到每一個人都在場,從見習修士到資深的苦行僧全都來了,大夥兒圍坐成一個大圓圈;修院師父坐在圓圈的正中央,緊抿著嘴唇,雙眼朦朧。
他清清嗓子,然後說:「奉真主之名。你們一定在想:今天我為什麼召集大家開會。那是因為我最近收到的那封信。姑且不管信是誰寄來的,只要知道這封信讓我知道一件後果極為嚴重的事情就行了。」
巴巴•札曼暫停一下,目光瞟到窗外。他看起來好虛弱、瘦小、蒼白,好像在這短短幾天之內老了許多歲似的。可是當他再次開口說話時,聲音裡意外地充滿了堅定的決心。
「在離此地不遠的一座城市,有一位博學的學者。他擅長文字表述,卻不善於解釋隱喻,因為他本身不是詩人。他受到數以千計的民眾愛戴、尊崇與景仰,但是本身並不擅長愛人。因為某種遠非你我所能理解的原因,我們這個修院裡可能有一個人必須去見他一面,做他的夥伴。」
我的胸口一緊,緩慢地、非常緩慢地吐了一口氣;不期然想起一條法則:寂寞與孤獨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你感到寂寞時,很容易欺騙自己,誤信自己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孤獨對我們則比較好,因為這代表你一個人獨處卻不感到寂寞。不過最好還是終究找到一個人可以做你的鏡子。要記住:唯有在另外一個人的心裡,你才能真的看見自己以及真主與你同在。
師父接著說:「因此我想問你們是否有人自願去走一趟心靈之旅?我當然可以指派一個人去,但此行任務不能靠責任心來完成,只能憑藉愛的力量,以愛為名來完成。」
一名年輕僧侶徵得同意發言。「師父,請問這位學者是誰?」
「我只能對自願去的人透露他的姓名。」
聽到此話,好幾名僧侶都舉起手來,不耐煩地蠢蠢欲動。總共有九個人舉手,我也加入其中,成為第十位候選人。巴巴•札曼揮揮手,叫我們等他說完。「在你們決定之前,還有一些事情應該要先知道。」
然後,師父跟我們說了這趟旅程會有極大的危險與前所未見的艱難,而且不保證一定能回來;所有的手立刻放下,只剩我一個人仍然高舉著手。
巴巴•札曼看著我,這是他好久以來第一次直視我的眼睛;當我們四目交會,我立刻知道他打一開始就已經知道我會是唯一的自願者。
「塔布里斯的夏慕士,」師父慢慢地、嚴厲地說,彷彿我的名字在他嘴裡留下濃厚的味道。「我尊重你的決心,但是你不完全屬於這個教團;你是我們的客人。」
「我不覺得這有什麼問題,」我說。
師父沉默思索了好久,然後出人意料地站了起來,說:「我們先談到這裡吧。等春天來了之後再說。」
我心裡不服氣。巴巴•札曼明明知道這個使命是我到巴格達來的唯一理由,但是他卻剝奪我完成天命的機會。
「為什麼,師父?我此刻就已經準備好可以啟程,為什麼還要再等呢?只要告訴我那個城市和學者的名字,我立刻就出發!」我大喊道。
可是師父的回應冷漠而嚴厲,我從未聽過他用那樣的聲音說話:「沒什麼好討論的。會議結束!」
***
那個冬天漫長而酷寒。花園凍僵了,我的嘴唇也是一樣。接下的整整三個月,我沒有跟任何人說話;每天都花很長的時間在鄉間散步,希望看到枝椏冒出花朵。可是風雪過後,仍然是更多的風雪,地平線上看不到春天的蹤影。儘管我外表看來心情低落,但是內在仍然心存感激、抱持希望,謹記著另外一條此刻最能符合我心境的法則:不管生命中發生了什麼事,也不管這些事情看起來有多麼麻煩,千萬不要走近絕望的疆界;即使所有的門窗緊閉,真主也會只替你一個人另闢蹊徑。要心存感謝!一切順遂時,心存感謝很容易;但是蘇菲僧侶不只要為他獲得的事物心存感激,也要為他得不到的事物心存感激。
終於,到了某日清晨,我看到了一抹耀眼的色彩,從層層積雪中冒出頭來,就像一首甜美的歌聲一樣的賞心悅目;那是一叢胡枝子,上面蓋滿了薰衣草花。我心中漲滿了喜悅,回到修院時,碰到那名紅髮的見習生,於是歡天喜地的跟他打招呼;他向來習慣看到我繃著一張臉,此刻詫異地下巴都快要掉下來。
「微笑吧,孩子!」我喊道。「你沒看到春天已經來了嗎?」
從那天開始,大地的風貌以驚人的速度改變;最後的積雪融解,樹枝冒出新芽,麻雀與鷦鷯也回來了,不久,空氣中就充滿了淡淡的辛香味。
有天早上,我們又聽到銅鈴聲響起;這一次,我是第一個趕到主屋的人。我們也再一次圍坐成一個大圓圈,把師父圍在圓圈的正中央,聽他講到這位了解世間萬物唯獨不懂愛的知名伊斯蘭學者。還是一樣沒有人自願要去。
「看來夏慕士還是唯一一位自願者,」巴巴•札曼宣布;他的音量提高,然後像風聲一樣慢慢地減弱。「但是我要等到秋天再做決定。」
我大吃一驚,不敢相信會有這種事情發生。經過了三個月漫長的延宕之後,我已經準備好可以出發了,但是師父又跟我說我的旅程還要再拖延六個月。我的心一沉,大聲抗議埋怨,乞求師父告訴我那個城市與學者的名字,但是他還是再一次地拒絕了。
不過這一次,我知道等待會變得容易的多,因為不可能再拖延下去了。我既已從冬盡等到春來,當然可以再從春日等到秋月。巴巴•札曼的拒絕非但沒有讓我灰心,反倒更砥勵我的精神,加深我的決心。另外一條法則說:耐性不只是被動的忍耐,而是要有足夠的遠見相信這個過程的最終結果。耐性代表什麼呢?代表看到花刺就想到玫瑰,看到黑夜就想到曙光;而沒有耐性就代表著太短視而無法看到最後的結果。愛真主的人絕對不能沒有耐性,因為他們知道:從弦月變成滿月也需要時間。
等到了秋天,銅鈴又再度響起。我不急不徐、充滿自信地走進主屋,相信事情終究會塵埃落定。師父看起來比以前更蒼白、更虛弱,彷彿他身上的能量已經蕩然無存。然而,當他看到我又再次舉起手來,他既沒有轉移目光,也沒有轉移話題,反而堅定地對著我點點頭。
「好吧,夏慕士,毫無疑問的,你就是那個應該啟程展開這趟旅途的人。明天一早,你就出發吧。但憑真主之意!」
我親吻了師父的手。終於,我要去見我的伴侶了。
巴巴•札曼親切而若有所思地對著我微微一笑,就像父親將唯一的兒子送上戰場前的微笑一樣,然後從淺褐色的長袍裡掏出一封密封的信,送給我之後,就默默地離開了;其他人也尾隨離開,只留下我一個人在房裡。我拆開封蠟,信內有兩張以優雅筆跡寫成的字條,分別是那座城市和那位學者的名字。顯然我要去孔亞找一位叫做魯米的人。
我的心突地一跳。我從未聽說過他的名字;他很可能是很知名的學者,但是對我來說,卻完全是個謎。我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拼出他的名字:清晰而有力的R,如絲絨般柔順光滑的U,自信勇敢的M,還有神祕有待解答的I。
我把四個字母湊起來,一再地覆誦著他的名字,直到這個字像甜甜的糖果一樣在我的舌尖融解,變得跟「水」、「麵包」、「牛奶」一樣的熟悉。
___________
魯米
一二四四年十月十五日,孔亞
明亮而豐潤,美好的滿月懸在半空中,像是一顆巨大的珍珠。我從床上起身,凝望著窗外沐浴在月色中的庭院。然而,即使是如此的美景當前,仍然止不住我心頭的震盪與雙手的顫抖。
「阿凡提,你的臉色好蒼白。是不是又做了同樣的夢?」我妻子低聲說道。「要我為你倒一杯水嗎?」
我叫她不要擔心,回去繼續睡。反正她也無能為力。人的夢境就是我們命運的一部分,只能憑真主的本意,讓它自然發生。再說,我想事出必有因,否則我不會連續四十天,每天晚上都做同樣的夢。
每一次夢境的開頭都有一些不同,又或許這始終都是同一個夢境,只是我每天晚上都從不同的門進去。這一次,我看到自己坐在鋪滿地毯的房間裡研讀古蘭經,那個房間感覺上很熟悉,卻又不是任何我曾經去過的地方;在我對面,坐著一名僧侶,瘦高挺拔,臉上蒙著面紗,手裡拿著一個燭台,上面插了五根蠟燭,讓我有足夠的光線可以閱讀。
過了一會兒,我才抬起頭來,把我正在讀的章節拿給那名僧侶看,直到這個時候,我才驚覺:原來我以為是燭台的東西,竟然是他的右手。他一直向我伸出右手,每根手指頭都在起火燃燒。
我驚慌失措地找水,但是眼前卻看不到,於是我脫掉罩袍,朝著僧侶丟過去滅火,但是等我掀起罩袍一看,他又消失不見了,只留下一根燃燒中的蠟燭。
從這裡開始,後面的夢境總是一模一樣。我開始在屋子到處找他,找遍了每一個角落和縫隙;然後,我跑進庭院裡,院子裡的玫瑰盛開,像是一片亮黃色的花海。我左右呼喊,但是到處都看不到那人的蹤影。
「回來吧,心愛的,你在哪裡?」
最後,彷彿在不祥預感的引導之下,我走近水井,往下看著漆黑翻攪的井水。起初,我什麼都看不見,但是過了一會兒,閃亮的月光照到我身上,院子裡漾著一片罕見的光明。這時候,我才看到一對漆黑的眼睛從井底向上望著我,眼底有前所未見的悲哀。
「他們殺了他!」有人喊道。或許是我吧。或許我自己的聲音在盛怒中聽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我一直尖叫、一直尖叫,直到妻子緊緊地抱著我,把我拉到她的胸前,輕輕地問:「阿凡提,你是不是又做了同樣的夢?」
***
妻子綺拉又回去睡了之後,我一個人溜進院子。在那一瞬間,我彷彿感覺到自己仍在夢中,一切都如此的栩栩如生,又駭人心神。在靜止的夜色裡,看到那口水井,讓我感到一股寒流從脊柱往上竄,可是卻又忍不住坐到井邊,聆聽晚風輕輕拂過樹林的聲音。
在這樣的時刻,我總是覺得一股悲哀的浪潮將我淹沒,但是卻始終不明白為什麼。我的生活完善而美滿,有幸獲得我認為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件事:知識、美德和幫助他人找到真主的能力。
現年三十八歲的我,從真主那裡獲得的東西已經遠超我所能要求的;最初,我接受的訓練是成為一名教士和法官,後來開始涉獵神知方面的學問,也就是給先知、聖人、學者的各種不同程度的知識。我在先父的啟蒙引導下,受教於我們這個時代最好的老師,努力奮發深化我的認知,一心相信這是真主賦予我的責任。
我以前的老師席伊德.布拉內丁常跟我說,我是一個最受真主寵愛的人,因為我被賦予這個榮耀,將祂的訊息傳遞給祂的子民,協助他們辨別是非。
多年來,我一直在伊斯蘭學校授課,跟其他伊斯蘭律法學者議論神學,指導門徒,研習法律與穆罕默德《聖訓》,每個星期五還要在城裡最大的清真寺講道。我早已數不清到底教過多少學生,而且每次聽到有人讚揚我的布道技巧,說我的言詞如何在他們最需要指導的時候徹底改變他們的生活等等,總是有一種受寵若驚的感覺。
我有幸擁有美滿的家庭、良師益友,還有忠誠的門徒。我這一生中,從未經歷過貧困與匱乏,不過失去我第一任妻子卻讓我悲痛欲絕;我以為這輩子不會再婚,但是我還是又娶了綺拉,也感謝她讓我體驗到愛與喜樂。我有兩個兒子,他們都已長大成人,但是看到他們變成兩個迥然不同的人,始終都讓我感到驚異不已;他們就像是兩顆種子,雖然並排種在相同的土壤之中,又受到同樣的陽光、水分滋潤,但是卻長成完全不一樣的植物。我深以他們為榮,就如同我以我們的養女為榮一樣,因為她有與眾不同的天分。無論於私於公,我都是一個幸福滿足的人。
可是,為什麼我會覺得內心如此的空虛呢?而且隨著日子一天天地過去,這樣的空虛還越來越深、越來越廣?它像是疾病一樣啃噬我的靈魂,無論我走到哪裡,它都像一隻安靜的老鼠一樣如影隨形,而且也跟老鼠一樣的貪婪。
艾拉
二○○八年五月十七日,北安普頓
艾拉一個人在露台,坐在她最喜歡的搖椅上,看著橘紅鮮艷的北安普頓落日;感覺上,天空是如此的廣袤又如此的逼近,好像一伸手就可以摸得到似的。她腦子裡一片寧靜,彷彿厭倦了裡面的種種噪音:這個月的信用卡帳單、歐莉的不良飲食習慣、艾維慘不忍睹的成績、愛思德阿姨跟她可悲的蛋糕、她的狗狗小精靈的健康每況愈下、珍妮特的結婚計畫、她丈夫的祕密外遇、她那沒有愛的生活……她將這些聲音,一個個鎖進小小的心靈保險箱裡。
在這樣的心理狀態下,艾拉從紙袋裡抽出書稿,放在手上拍一拍,彷彿在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