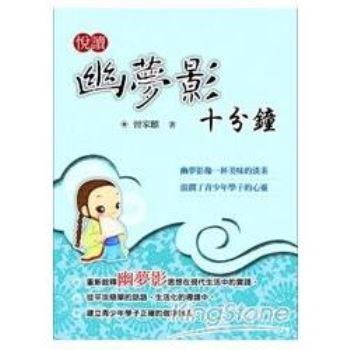第五卷 第一章
流水便隨春遠,行雲終與誰同
載著棺木的牛車慢慢停下來,張鵬以女真語笑道:「大人,方才不是檢查過了嗎?」
金兵粗聲道:「打開棺木看看。」
張鵬賠笑道:「這是小人母親的屍首,沒什麼好看的。」
「叫你打開就打開,囉嗦什麼?」金兵喝道。
「是是是,不過這天怪熱的,小人擔心棺中的腐臭味熏著大人,壞了大人的胃口。」
「打開!」
「是是是!」
不得已,他們打開半釘住的棺木板,我立即閉目,保持「死」的平和安詳。
棺木板剛剛打開,金兵便叫起來,「什麼味道?這麼臭?」
張鵬趕緊笑道:「大人,小人剛才說過了,這天熱,母親的屍首擱了幾日,自然會有屍臭味。」
「好了好了,快點走。」金兵催促道。
「是是,小人這就馬上走。」
他們火速釘上木板,留了一點縫隙,推著牛車快步前行。
順利通過第一關,我鬆了一口氣,思及父皇還在韓州受苦受難,不由得難過起來。
我不能自己南下而丟下父皇不管不顧,我不能那麼自私。
這通關牌子是端木先生弄來的,仍然是那個受過他恩惠的克群找來的。
沒有追兵追來,這夜,我們在荒郊野外歇一晚,次日一早繼續趕路。
已是初夏,金國的夜晚仍然深涼,我靠坐在樹頭上,攏緊粗布衣袍。
葉梓翔坐在我旁側,將乾糧和水袋遞給我,「帝姬餓了吧,吃點兒東西。」
我問:「韓州那邊可有消息傳來?」
「暫時沒有。」他避開我追問的目光,眉宇略低,「帝姬無須擔心,派過去的人是末將的屬下,他們做事很有分寸。」
「葉將軍,為什麼每次提到父皇,你總是避開我?」
我仔細審視著他的表情,他看我一眼,又立即垂眼,那表情分明是尷尬與羞愧。
刹那間,我明白了,怒問:「你根本沒有派人去韓州營救父皇,是不是?」
他終於迎上我憤怒的目光,仍然不夠坦蕩,「有,末將派人前往韓州,但是金兵監管很嚴,他們……還未見到太上,還未聯繫上。帝姬,營救太上須從長計議,不可操之過急,否則營救計畫一旦敗露,金帝風聞我意欲營救二帝,一怒之下會殺了太上。」
他說得沒錯,若要營救,就要萬無一失,需有十足的把握,否則便是置父皇於死地。
「我不能就此離開金國,棄父皇於不顧,葉將軍,我想……我們秘密前往韓州,救出父皇之後再一道南下。」
「不行!」葉梓翔立即反對,「此行兇險,末將好不容易救出帝姬,豈能再入狼窩犯險?我等數人前往韓州,勢必引起金人注目,還未救出太上,便被金人抓住,那時還談什麼營救?」
「可是,我不能丟下父皇……」
「帝姬思父之心,末將明白,然而,陛下叮囑末將,量力而行,能救一個是一個。」
他口中所說的「陛下」,自然是六哥。
六哥竟是這麼想的,難道六哥……
我不敢想,不敢深入地想……更不願把六哥想得那麼不堪。
我質問道:「那你為什麼不先去韓州營救父皇?父皇乃一國之君,比我重要千百倍……」
葉梓翔被我問得一愣,須臾才耐心解釋道:「帝姬,並非末將不想營救太上,而是……不可操之過急,否則太上便有殺身之禍。」
「你不是將我救出來了嗎?有這麼難嗎?」
「救出帝姬,是因為……有端木先生這樣的高人作內應。」他握住我的雙肩,語重心長道,「帝姬,陛下有句話要末將轉告帝姬:切不可任意妄為,一切聽從葉將軍指令。」
「六哥真的這麼說?」我不信六哥會料到我想去救父皇。
「末將縱有千萬個膽子,也不敢假傳聖旨。」
我怔怔不語,內心掙扎。
六哥與葉梓翔沒有錯,能夠救出我已是萬幸,要救父皇,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必須謀劃得毫無破漏,方能行事。
既是六哥的旨意,我也就不再多說什麼了。
次日,來到一個小鎮上,我們吃了較為豐盛的一餐,買了五匹馬,直奔第二個關卡。
我們仍然是中年、老嫗的打扮,奉上通關牌子,第二個關卡輕而易舉地過了。
過了中京大定府,我們略微安定,卻也不敢疏忽大意。
奔馳數日,未曾好好歇息,這一夜,葉梓翔決定好好休整一晚再趕路。
露宿野外,夜裡的風很涼,我蜷縮著身子,凍得瑟瑟發抖。
月上中天,淡青的月華流瀉整個寰宇,使得整個荒郊愈發的清冷死寂。
我打了一個噴嚏,倏然清醒,便抬眼望著那輪孤月。
孤月泊於浩瀚的銀河,潔白無依,一身孤清。
想起遠在韓州的父皇,想起遠在揚州的六哥,想起會寧府中的完顏磐,想起姐妹們,想起很多人……這樣的深宵,他們已經熟睡,我望月懷人,也是一身孤清。
一心悵然。
有輕微的腳步聲靠近,該是葉梓翔,我立即閉眼。
一襲袍子輕輕地覆在我身上,頓時,我覺得暖和一些,有點感動。
他卻沒有立即離去,而是坐在邊上,不知想做什麼。
他輕輕一歎,片刻後,我覺得臉上有些癢,是他的指腹輕輕撫著我的臉,娥眉,左腮,動作輕得不能再輕。
白日裡,他恪守禮數,對我畢恭畢敬,可我知道,他的意中人應該還是我。現在,深更半夜,他這般「輕薄」我,足以表明他的心,也說明他克制著對我的情意,在我熟睡後才敢「色膽包天」地碰觸我。
我不敢動,擔心他發現我是清醒的,那樣一來,他會尷尬,我也會尷尬。
所幸,片刻後他便離去。
我放鬆下來,過了好久才有睡意。
猛然間,死寂的荒郊深夜出現不尋常的驚亂,我驚醒,立即起身。
他們倉促地收拾包袱上馬,葉梓翔箭步衝過來,將我抱上馬,接著他也上馬,「有追兵。」
一語驚散所有睡意,我緊張得發抖,冷冽的夜風刮面而過,生生的疼。
驅馬飛馳,我思忖著後面的追兵會是誰?完顏宗旺?還是完顏磐?
不久,後面傳來震天動地的聲響,在這深夜,馬蹄踏擊大地的巨響異常清晰,就像踏在心坎上,令人心驚膽顫。
所買的馬和我們一樣疲累不堪,再過不久,追兵就會追上我們,那可怎麼辦?
若是完顏磐,也許還有商量的餘地。
若是完顏宗旺,只怕我苦苦哀求也不會心軟。
苦思對策,仍是想不到良策。
葉梓翔籌謀那麼久才救出我,而且逃出會寧這麼遠,想不到會在這裡被追兵追上,難道我這輩子都不能南歸嗎?註定一生淪落金國?
想到此處,我咬牙切齒,又悲又怒。
「帝姬莫怕,就算是死,末將也會護帝姬周全。」葉梓翔絕烈道。
「嗯。」此時,我還能說什麼?
金兵終於超越我們,匆促勒馬,那些趾高氣昂的駿馬前蹄仰天,長嘶破天。
青黑的月光下,金兵約有二十來騎,個個彪悍,不約而同地引弓搭箭,箭鏃對著我們。
那人昂然立於駿馬上,穩如山嶽,月光灑了他一身,使得他的身影看起來孤硬寒涼,又別有一番睥睨眾生的傲然氣勢。
完顏磐。
他如何知道我還活著,如何知道我已南逃?
「小貓,過來。」他倨傲而溫柔地喚我,朝我伸出手。
「你是何人?為何追我們?」我拿捏著嗓子,變得像老嫗的蒼老聲音,我是老嫗的打扮,他為何這麼肯定我就是趙飛湮?
「趙飛湮,過來!」完顏磐固執道,聲音不再溫情,略有怒氣。
葉梓翔攬在我腰間的手突然加力,「他是誰?」
我低聲道:「金帝嫡長子,宋王。」
完顏磐驅馬近前,死死地盯著我的腰間,目光如炬,「放開她!」
嗓音冷寒。
「宋王,在我們大宋,以多欺寡非好漢,若想抱得美人歸,你我單獨打一場,決勝負,如何?」葉梓翔溫言帶笑,彰顯大宋男兒的磊落自信。
「我叫你放開她!」完顏磐氣急敗壞地怒吼,寶刀尖鋒直指我們。
「我不會隨你回去,寧死不回。」我決然道。
完顏磐緩緩收回寶刀,寒聲下令:「放箭!」
箭雨疾射,張鵬和兩名護衛舉劍擋箭,擋得了一支兩支,卻擋不住源源不斷的箭雨,不久,三人中箭身亡。
眨眼之間,他們死於非命,葉梓翔悲痛不已,我亦悲傷。
我眨去眸中的濕意,「阿磐,可否談談?」
「好,你想怎麼談,都可以。」完顏磐冷沉一笑。
「不可,帝姬三思。」葉梓翔更緊地抱著我,不鬆手,「末將死不足惜,帝姬……」
「無妨,他不會傷害我。」我掰開他的手,俐落地下馬。
他立即跟著下馬,扣住我的手腕,不讓我去。
「把他的手砍下來。」完顏磐冷酷的聲音再次傳來。
「你敢傷他,我與你勢不兩立!」我怒吼。
我決然拂開葉梓翔的手,「無須擔心,我不會有事。」
葉將軍,你孤身一人,如何保護我?我不願你死,你還要為六哥安邦定國,為大宋子民保家衛國,還要率軍北伐、驅除金賊,我怎能讓你死?如果我不與完顏磐談談,他一定不會放過你。
我朝完顏磐走去,金兵策馬逼近葉梓翔,所有的箭鏃都對著葉梓翔。
完顏磐瀟灑地下馬,拉起我的手,我巧妙地避開,「假若你傷他一根毫毛,我會自毀一根。」
他怒目圓睜,沒想到我會說出這樣的話。
半晌,他下令:「兄弟們,好好招呼這位朋友,把人看緊了。」
話落,他強硬地握著我的手,走向遠處。
此處是土地平整的野外,有遼闊的視野,也有高聳的樹木,夜月下的風光,秀麗幽靜。
走出不遠,完顏磐便伸臂攬在我腰間,我心神一蕩,刻意保持的冷靜與疏離瞬間瓦解。
遠離了葉梓翔和金兵,他解下披風鋪在草地上,扶著我坐下來。
他問:「他是誰?」
我笑,「很早以前我就說過,父皇為我尋了一個駙馬,他就是我的駙馬,葉梓翔。」
「葉梓翔是你的駙馬?」完顏磐微驚,「葉家軍頗有名望,此人頗有膽略。」
「是宋王來追我的,還是得你皇叔的命令?」我與他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你放心,對於你的死,皇叔沒有起疑心。」
「宋王如何知道我已逃出會寧府?」
「叫我阿磐。」他低低道,曲起雙腿,抱膝而坐,「我始終不相信你就這麼死了,以端木先生的醫術,不可能束手無策。」
「端木先生不是神,中毒已深,人已死,怎麼可能救活?」
「還有一件事,讓我確定你的死只是一個障眼法。」他苦笑,「我命人暗中跟著父皇的侍衛前往城郊,後來,我的屬下回來說,火葬時發生了一件怪異的事,在火葬處附近竟然有薩滿教做法,而且所有的侍衛都去看薩滿教做法,忽略了火葬。」
我莞爾道:「因此,你猜到有人會偷龍轉鳳,猜到我只是假死?」
完顏磐頷首,「我派人前往韓州,自己帶了二十多騎南追。」他握住我的手,「南追之前,我猶豫了一日,徘徊於追與不追之前。」
我譏誚地問:「那為什麼還是追來了?」
他澀笑,「追你回來,讓你繼續留在皇叔身邊,你會很痛苦;不追你回來,我會因為失去你而心痛。」
「現在你追到我了。」
「我在城郊有一座別苑,你暫時住在別苑,誰也不會知道你還活著。然後,我向父皇請旨外調,去雲中樞密院也好,去燕京樞密院也罷,只要離開了會寧,你我便能在一起,誰也不會阻止我們。」
「宋王的打算可真周到。」我冷冷譏笑,「你以為你的皇叔蠢得永遠也不會發現嗎?」
「發現又如何?那時你已是我的妻,我不會再拱手相讓。」完顏磐目光冷厲。
「這麼說,你承認你曾經將我讓給你的好皇叔?」我又是一聲冷笑。
他突然扣住我的手腕,「小貓,為什麼你總是對我冷嘲熱諷?」他又氣又急,「我不是把你讓給皇叔,而是……皇叔一年半載不會放手,我只能讓你暫時留在皇叔身邊,暗中佈局籌謀,再把你搶回來。」
我甩開他的手,「別再叫我小貓,噁心。」
我再次嘲諷,「在你們金國,可以無視綱常人倫,皇叔的侍妾,作為侄子的可以堂而皇之地納為妾嗎?」
他騰地跪起身子,拽我起身,「你們宋人講究那麼多,我們金國,只要喜歡,就算是父親的姬妾、伯伯叔叔的妻妾,或者是兄長的妻妾,都可以娶之、納之。」
我搖頭失笑,「果真是蠻夷。」
完顏磐怒目而視,我不懼地抬起下巴,四目相對,他怒,我冷。
突然,他伸臂攬過我,以袍角擦拭著我的臉,力道適中,舉止溫柔。
我掙了一下,卻聽他道:「別動,我不想對著一張陌生的臉。」
這雙俊眸專注而深沉,令我心瀾微漾。
我靜靜地望著他,此時此刻,我不知道應該如何面對他,面對金帝的嫡長子,宋王完顏磐。
如果他不是金人,或者不是金國宗室中人,或許我與他就不會這般艱難。
可是,「如果」往往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假設,是一種美麗而脆弱的幻想,瞬間即滅。
他的吻不知何時落在我的唇上,待我發覺,他已緊抱著我,右掌扣著我的後腦不讓我閃避。
這樣的親密,這樣的熾情,我期待了多久?
可是真正面臨的時候,我又退卻了,大宋與金國之家的國仇家恨,提醒我不能與他為伍,不能陷入他的情意與懷抱。
我瞬間的迷失,已讓他有足夠的時間得到他想要的。
擁吻越來越激烈,他糾纏著我的唇舌,沉醉於這一場想念已久的情愛裡。
我看見他微睜的眼中皆是纏綿之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纏綿,眼中的火花漸漸燎原……
我用力推開他,他怔忪地凝視我,臉上的激情慢慢消退,卻仍然摟著我,「為什麼?」
「你是我的敵人。」我再次推離他,想起適才他冷酷下令射殺保護我南逃的護衛,不寒而慄。
「只要你還愛我,所有的仇恨都可以淡化。」
「你可以淡化,那是因為你是強者,是入侵他國的一方。」
片刻後,完顏磐無奈地放手,頹喪地坐下,「我想不到你會變成這樣,更想不到你對我會有敵對、仇視的一日。」
他所說的,正是他作為強者所想的:我是亡國奴,理應被他囚禁,在他的憐憫中屈辱地度過下半生,老死金國。
我亦無奈一笑,「我也想不到你是金人,甚至還是皇子皇孫。」
夜寂,月冷,露清。
長長的靜默。
「我不會再回去。」我的聲音竟然可以變得這般冰冷,不含一絲一毫昔日的情意,「若你執意帶我回去,帶走的會是一具屍首。」
「我會安排得很好,沒有人會發現你還活著。」完顏磐音量微高。
「尊貴的宋王,你想將我藏在一個無人知曉的金屋,讓我在你的寵愛下屈辱度日嗎?」我輕笑,問得尖銳。
「湮兒,你完全可以將我當做石頭哥哥,我們會像以前那樣,開心地打鬧,快樂地在一起。」他的眼中滿是期待,「你愛我的,是不是?愛我,就跟我回去。」
「我們再也回不去了,除非你們金國從未入侵過大宋,除非大宋和金國仍然是井水不犯河水。」
我悄然解開衣帶,「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還愛你,但我知道,我恨你,恨你這個滅我家國的金人。」衣袍滑落,我僅著抹胸,刹那間,冷意襲身,「若你執意帶我回去,那麼,就像你皇叔那樣,現在就強行要了我,然後我會恨你一輩子,你帶走的只會是一具屍首。」
完顏磐驚震地望我,眸色立時轉濃,火花四濺。
我悽楚地望著他,決然道:「你有第二個選擇,放手,就當沒追過我。」
他黯然低眸,「你不要逼我。」
我失笑,「是你逼我,不是我逼你。」
「放你走,對我有什麼好處?」
「我會覺得,你和你的皇叔不一樣,你真的愛我,在乎我的感受,而不是像你皇叔那樣,強取豪奪。」
「湮兒。」他低聲喚我,取了落在草地上的衣袍裹在我身上,然後擁我入懷,「你可知,要我放手,是多麼殘忍的一件事,而且需要多大的勇氣?」
淚濕雙眸,我啞聲道:「那你又可知,再留在金國,我真的會死?你真的願意看我死嗎?」
他一震,深深地凝視我。
半晌,他俯唇,吻著我的眼眸,吻去淚水,雙唇微顫。
我看見他微閉的俊眸滴落一顆淚珠,頓時心痛如割。
「阿磐,放我走……求求你……如果你真的愛我,就放我走……」
完顏磐尋到我的唇,輕輕觸著我的唇角,「萬一我找不到你了,怎麼辦?萬一你嫁給你的駙馬,我怎麼辦?我說過,我會娶你……我要娶你……」
淚珠簌簌而落,「我答應你,不嫁人……一輩子都不嫁人。」
「真的嗎?」
「嗯。」
「好,你等著我攜聘禮娶你。」
話音甫落,他吻住我,唇舌交纏,深切,繾綣。
我知道,他已心軟,不會再帶我北歸。
而此刻,我只能滿足他的需索,或許我也是情不自禁。
他抱我愈緊,鼻息愈發急促,滿目慾念,好像不滿足於單純的擁吻,大掌不安地摩挲著我的背,慢慢傾身欲倒。
在他的激情裡,我迷亂了。
離開了會寧,沒有完顏宗旺這座大山橫亙在我們中間,他沒有顧忌,我心中的壓力好像也少了,只想著他是我此生唯一愛的男子,我怎能拒絕他?
我的心,彷彿也需要他的慰藉與愛撫,才能填滿畢生愛戀的空缺。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鳳囚金宮(3)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鳳囚金宮(3)
高不可攀的宋朝帝姬在一夕之間淪為戰俘
薄歡誘敵、迎合奉承於敵將之下
為報國仇,也為心裡從未忘懷的愛情…
沁福帝姬──趙飛湮藉著假死逃離金國,
不料卻在途中遇見帶兵追趕而來的完顏磐。
一心想回宋,洗刷亡國屈辱的她,
面對一生摯愛的懇求又該怎麼抉擇?
金帥完顏宗旺因趙飛湮之死而痛苦憤怒,甚至荒廢軍事,
更與金朝皇帝之間產生嫌隙,權力逐漸動搖……
當他發現真相時,又會採取何種行動?
為國恥、為情仇,
他們各自的願望又會如何推動命運,
又會引起什麼樣的波瀾?
作者簡介:
端木搖
處女座,現居蘇州。熱衷文字、歷史和影像。
深情在睫、孤意在眉、滿懷蕭瑟。
出版長篇小說多部。
章節試閱
第五卷 第一章
流水便隨春遠,行雲終與誰同
載著棺木的牛車慢慢停下來,張鵬以女真語笑道:「大人,方才不是檢查過了嗎?」
金兵粗聲道:「打開棺木看看。」
張鵬賠笑道:「這是小人母親的屍首,沒什麼好看的。」
「叫你打開就打開,囉嗦什麼?」金兵喝道。
「是是是,不過這天怪熱的,小人擔心棺中的腐臭味熏著大人,壞了大人的胃口。」
「打開!」
「是是是!」
不得已,他們打開半釘住的棺木板,我立即閉目,保持「死」的平和安詳。
棺木板剛剛打開,金兵便叫起來,「什麼味道?這麼臭?」
張鵬趕緊笑道:「大人,小人剛...
流水便隨春遠,行雲終與誰同
載著棺木的牛車慢慢停下來,張鵬以女真語笑道:「大人,方才不是檢查過了嗎?」
金兵粗聲道:「打開棺木看看。」
張鵬賠笑道:「這是小人母親的屍首,沒什麼好看的。」
「叫你打開就打開,囉嗦什麼?」金兵喝道。
「是是是,不過這天怪熱的,小人擔心棺中的腐臭味熏著大人,壞了大人的胃口。」
「打開!」
「是是是!」
不得已,他們打開半釘住的棺木板,我立即閉目,保持「死」的平和安詳。
棺木板剛剛打開,金兵便叫起來,「什麼味道?這麼臭?」
張鵬趕緊笑道:「大人,小人剛...
»看全部
目錄
第三冊
第五卷 南朝事‧人清絕
第一章 流水便隨春遠,行雲終與誰同
第二章 何人月下臨風處,起一聲梨塤
第三章 天遙雲黯,杳杳神京路
第四章 兵戈淩凌滅,豪華銷盡,幾見銀蟾自圓缺
第五章 想得玉樓瑤殿影,空照秦淮
第六章 望京國,空目斷、遠峰凝碧
第七章 千里江山寒色遠,蘆花深處泊孤舟
第八章 長江千里,煙淡水雲闊
第九章 旌旗麾動,坐卻北軍風靡
第十章 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
第六卷 興亡替‧孤心悲
第一章 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
第五卷 南朝事‧人清絕
第一章 流水便隨春遠,行雲終與誰同
第二章 何人月下臨風處,起一聲梨塤
第三章 天遙雲黯,杳杳神京路
第四章 兵戈淩凌滅,豪華銷盡,幾見銀蟾自圓缺
第五章 想得玉樓瑤殿影,空照秦淮
第六章 望京國,空目斷、遠峰凝碧
第七章 千里江山寒色遠,蘆花深處泊孤舟
第八章 長江千里,煙淡水雲闊
第九章 旌旗麾動,坐卻北軍風靡
第十章 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
第六卷 興亡替‧孤心悲
第一章 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端木搖
- 出版社: 月之海 出版日期:2014-10-01 ISBN/ISSN:978986583462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20頁 開數:25K(14.8*21cm)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