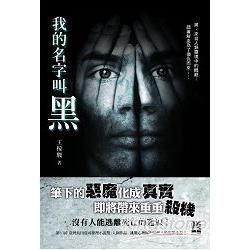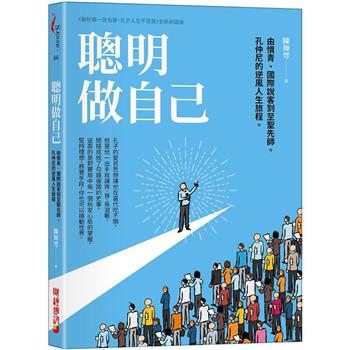引子
日出時的第一縷陽光,就像個遠方的親人,穿過厚厚的雲層,不遠萬里來到地平線另一頭的這座城市。似乎沒人會刻意去在乎它的到來,理所當然地享用著屬於大地的這份暖意。
一個男人站在窗邊,迎著陽光瞇眼眺望。一頭金燦燦的鬈髮下,整張臉像被鍍了層銅,加之其沒有任何表情的生硬面容,彷彿一尊栩栩如生的雕像。
身後仍在熟睡中的妻子,鼻腔裡發出難聽的鼾聲,沒頭沒尾地說了幾句夢話,具體內容並未聽清。
男人佝僂著身軀走到床邊,他默默地注視著妻子,生怕將她吵醒。
男人輕輕拿起床頭櫃上的鬧鐘,把原先設置在七點三十分的鬧鐘,往後撥了一小時。他扶起一個正面扣下的相框,仔細端詳了一番,臉上浮現出慈父般的笑容。
忽然,他劇烈地咳嗽起來,男人邊捂住嘴巴,邊朝窗邊挪了幾步,將動靜控制在了最小範圍內。
他將相框放在窗臺上,自己像個調皮的小孩兒,兩隻手撐起身子,不過男人似乎身體有點兒問題,一個簡單的動作,卻耗費了不少體力才坐上窗臺。
他背著光,痛苦地大口呼吸著,他機械地轉動著腦袋,掃視著房間裡的每一個角落,那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東西散落了一地,兒童的衣服、玩具車、奶嘴、小帽子,似乎有個孩子正在屋子裡歡快地嬉戲著。
他閉起眼睛,嘴唇微微顫動著,像是在對自己被拉長的影子說著什麼:「思思,妳不會孤獨的,我不會讓妳一個人待著,是爸爸對不起妳,爸爸這就來陪妳。」
他雙手騰空,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了弓起的背上,任由身體向後倒去。
他的房子、他的妻子,如晃眼的陽光般在眼前一閃而過,下墜的身影如匆匆過客,房間瞬間變得明亮起來。
窗臺上,被他腳趾劃到的相框,滑出窗臺一大半,勉強支撐了幾下後,「哐啷」一聲跌碎在地板上,三口之家幸福的表情上布滿了裂縫,在陽光折射之下形成扭曲的表情,甚是詭異。
被吵到的妻子只是不耐煩地「哼」了一聲,連眼睛都沒睜開,捲著被子翻了個身,繼續睡去。
當然,她更不可能注意到,幾秒前,那記沉悶的墜地聲。
血色風箏
昏昏晨霧中,鱗次櫛比的路燈如骨牌般,沿著街角一路熄滅。
早班的清潔工沈阿姨推著垃圾車,哼唱著昨晚從電臺聽到的歌曲,踩著一圈一圈逐漸消失的光暈打掃著,橙色工作服如一盞燭火,主宰著整條街道的明暗。
今天的工作看起來會輕鬆不少,地面幾乎沒有可掃的雜物。
突然不遠處,一片汙穢讓沈阿姨覺得不快,她提著掃把快步走向它,結果走近一看,才發現並不是什麼髒東西,而是一個黑色的影子。
沈阿姨退後一步,意識到了什麼,她抬頭望向身邊那盞高高的路燈,漸漸地,她按住帽子的那隻手止不住地顫抖起來。
一如尋常的靜謐中,一抹火紅懸於半空,在昏黃的光線下發出奇異的光芒。定睛看去,那竟是個弱小的女孩兒,手臂從紅衣寬大的袖管中穿出,裙子下面是極其纖細的小腿。她的腦袋乖巧地耷拉在胸前,似乎在想著什麼心事;脖子則像是被巨大的手硬生生扯成了不可思議的角度;一條毒蛇般的黑繩將她柔弱的身軀定格在細長的燈桿上。
早晨的微風不時掠過,她的身形輕輕搖擺。如同這座尚未甦醒的城市,在陰影中固化著安然入睡的表情。沒有鮮血,沒有痛苦,長髮遮蓋了半邊臉頰,那是略帶滿足的安逸笑顏。隨著風越來越大,小女孩似乎從睡眠中醒過來了,如一只追求自由的風箏,擺動幅度越來越大,想要掙脫束縛,隨風而去。
「她死了嗎?」
等到沈阿姨終於想到這個問題時,她喉嚨裡不由得發出低低的哀號。她睜大眼睛,滿是淚水地癱軟在地,接著用力捂住了自己的嘴。
這是寧夜最新創作的小說的開場,算起來這已經是他《暗黑》系列推理小說的第十本了。作為一名專職的作家,寧夜算不上高產,城市裡高額的生活成本,讓他的稿酬看起來更顯微薄。
在拮据的時候,家裡就靠妻子蔣曉清的薪水了。女兒很聽話乖巧,但寧夜對她的照顧卻少之又少,可能是職業的關係,結婚以後的寧夜,仍像一個人生活一樣。
每天寫到清晨三、四點才會上床睡覺,然後睡到第二天下午起床,這時妻子已經將女兒送去幼稚園裡,自己上班去了。微波爐裡總會有妻子留給他的飯菜,足不出戶的寧夜又開始了一天的生活。
一家三口只有在晚飯的時候才有機會聚在一起吃飯聊天,可寧夜每次總掃興地沉思著自己小說的情節,一語不發地投入自己的創作中。
他的工作也讓他的情緒長期處於不穩定的兩個極端,有時他想起書中的某一個死者,創作的愉悅感就會在內心裡轉化為極度的痛苦,這種痛苦像癌細胞一樣揮之不去。
寧夜還會時常自夢中驚醒,口中大喊著自己小說裡某個人物的名字。對他如此癡迷於小說,妻子默默含著淚說:
「你別真的哪天分不清自己的生活和小說了。」
愛情不能只是單方面的付出,再深的愛也會有累的那一天。
結婚紀念日臨近,妻子先後暗示了好幾次都不見成效,便當面和寧夜撒起嬌來,寧夜雖不情願,但也答應了她。
沒想到,那一天的晚餐,成了他和妻子一起吃的最後一頓晚餐。
在妻子預訂的餐廳裡,寧夜吃得心不在焉,他滿腦子都是自己的小說,連對面妻子漸漸陰沉的臉色也絲毫沒有察覺。
突然,他失聲痛哭起來,鄰桌的顧客和服務生都被嚇得不輕,妻子以為是飯菜出了問題,忙不迭問道:「怎麼了?」
誰知號啕大哭的寧夜來了句:「凶手殺錯人了,他不該死呀!不該死啊!」
耳邊傳來其他人輕聲的咒罵──
「神經病!」
「這人肯定腦子有問題!」
「這麼高級的餐廳怎麼會放這樣的人進來?」
妻子忍住眼淚,起身結帳後,獨自回家了。
妻子發現寧夜已不是新婚時的那個男人了,寧夜為了他的小說,將癡狂陶醉的情緒帶入現實,像是換了個人似的,成天浸淫在他小說的世界裡,與外界的溝通越來越少,包括自己的家人。
妻子能夠接受丈夫的任何改變,但無法忍受被丈夫忽視的待遇。
寧夜回家後,看見妻子早早睡下,也就沒把自己晚上的失態放在心上,又一頭埋進了書房裡。
翌日,妻子消失了。
她並沒有一如往常地準備早餐,送女兒去幼稚園,洗衣機裡的衣服也沒有洗,她只是收拾了自己的隨身衣物,決絕地離開了寧夜,離開了原本屬於他們的家。
我寫小說也是為了讓這個家更富裕,究竟哪裡做錯了呢?寧夜對著空蕩蕩的床,茫然無措。
打電話去妻子的公司,總機人員說她今天請假沒有去上班,寧夜轉而詢問妻子的幾個好朋友,但一無所獲,不僅如此,幾個好友反問他發生了什麼事,寧夜含含糊糊地混了過去。
最後,寧夜硬著頭皮打電話給妻子的父母,他想不出妻子還有別的去處。得到的回答依然是沒有看見她,過了一個晚上,熟悉無比的妻子彷彿從人間蒸發了一般,就像從來沒有這個人一樣。
寧夜想起妻子曾對他說過:「我不需要一個天才作家,我只要一個和正常人無異的老公,過平平凡凡的日子,難道不行嗎?現在的你,就算能寫出扣人心弦的小說,也沒有辦法打動我的心。」
寧夜以為這只是妻子在耍性子,並未太在意,仍執著地創作每一部小說,在現實和幻想的世界中交錯穿行。想起妻子的時候,寧夜有時候會覺得妻子也是自己小說裡杜撰出來的人物,只是在女兒拉住自己的手,問媽媽去了哪裡的時候,才回過神來,知道自己又在神遊了。
直到某一天,他發現已經整整一年沒有見過妻子了。
更奇怪的是,這些日子裡除了女兒寧小櫻,再無別人在寧夜面前提起過妻子。
客廳書架上已經擺了十幾本《暗黑》系列推理作品,寧夜取下一本,隨手翻了幾頁,獨自品味著文字中蘊含的心境。只是那本新寫的書,卻遲遲沒有落筆寫下去。
記得這個系列的原始構思,還是妻子提出的,而今妻子出走,自己的小說也被擱置了。
「我該結束這個系列了,或許,我該結束寫作生涯了。」寧夜重重合上了書頁。
寧夜重新回到書桌前,翻出開場的文字,凝視良久。
他安靜地思考著這個重大決定。
一旦做出改變,他不在乎失去任何擁有的東西。專一和固執,是寧夜性格上最大的缺陷,但也是成功者必不可少的強大精神來源。
憶起與妻子共同生活的零星片段,妻子那清澈明眸半彎時的笑容,每晚為正在創作的他送上暖暖的煲湯,他忽然發覺離開妻子的自己,就好像被這個世界拋棄的孤兒,禁錮在虛幻無邊的幻想中,孤獨終老,無人問津。
他在稿子標題旁,快速寫下了三個字:完結篇。
生活不只有小說,寧夜想要尋回妻子的念頭變得迫不及待起來。
他不再猶豫。
「您好,這裡是一一○報案中心,請講。」
「有個男人明天就要被人殺了,他會被淹死的,你們快去救救他。」
「先生,您說的這個男人現在哪裡?」
「他……他應該在上班吧。」
「地址呢?」
「中泰大廈,哦!不,是上泰大廈。」
「您是說他明天會淹死在辦公室裡?」
「是的。」
戴著耳機的凌薇在電腦裡輸入顯示的來電號碼進行搜索,她對報案內容的真實性產生了懷疑:
「您認識那個男人嗎?」
「不認識。」
「那您是怎麼知道他要被殺的事情的?」
電話那頭沉默不語。
「先生,您如果沒有證據,光靠推測來報告一起未來將要發生的事件,我們將無法受理您的報案。為了備份您的報案記錄,請問您的姓名是?」
「沒這個必要。」對方毫不猶豫地掛了電話。
「喂……喂……先生!先生!」
凌薇用筆記下了電腦螢幕上的搜索結果,電話是從市東一家快遞公司打出來的。但報案者所說的案發地點上泰大廈與這家快遞公司相隔甚遠,並沒有密切的聯繫。何況一個人又怎麼可能淹死在自己的辦公室裡呢?
「又是一個報假案的。」凌薇嘆了一口氣,近來社會風氣越來越差,報假案的事情頻發,幾乎占到了所有報案電話的五成左右,面對這樣的局面,總部要求將報假案或疑似報假案的電話錄入備案,以便今後整治該類不正之風。
凌薇快速地整理著這次通話的錄音和資料,不知不覺已過了下班時間,她摘下耳機,按了按發脹的太陽穴,發現窗外一片煙雨濛濛。
後腰眼的老傷又開始隱隱作痛,類似條件反射的痛感令她難以忍受,凌薇蜷起身子,用手按在了傷處。隔著衣服也能感覺到掌心厚厚的老繭,視線中的一切變得灰暗起來。
她厭惡下雨的日子,雨水總能沖刷掉往日美好的一面,顯露出這個世界骯髒墮落的醜陋嘴臉。排水不暢的街道、避雨狂奔而不顧左右的行人,像末日來臨一樣,對周遭視若無睹。
她垂下雙手,熟練地轉起輪椅的輪子,回想起正是一個雨夜,自己失去了對所有人的信任。
「薇薇,我來晚了,真不好意思!」換班的同事姍姍來遲,一坐下就埋頭甩著被雨淋濕的長髮。
「看起來外面的雨還不小呀!」凌薇遞了包面紙給她。
「謝了。來,我送妳到電梯那兒。」山姍用面紙擦乾了額頭上的水滴,把頭髮束了起來,俐落地站起身子,推著凌薇朝這層樓的電梯走去。
「這天氣妳怎麼回家?」山姍擔心地問道。
「拜託,我只是腿不方便,又不是全身癱瘓!回家這點兒小事還能應付得了。」
「可是……」
「放心,我已經叫了計程車,車現在應該已經到樓下了。」
凌薇把輪椅往前推了一點兒,伸長手臂艱難地按下了電梯按鈕。
「那我替妳去借把傘吧!妳等等。」山姍往員工休息室裡跑去。
「不用了,電梯馬上就來了。對了,桌子上有份疑似報假案的資料,妳記得拿去備案,這次可千萬別再忘了啊!」凌薇叮囑道。
「這事包在我身上。」山姍一口答應,「電梯來了,妳路上小心。」
凌薇小心翼翼地推著輪椅,生怕金屬踏腳板鉤壞電梯裡其他乘客的褲管。電梯裡的人們,自覺讓出一個輪椅的空間。
「到家記得給我電話。」山姍做了個話筒的手勢,就像在叮囑自己的孩子一樣。
「妳快回去上班吧!」凌薇急忙關上了電梯門,嘴裡依然嘟囔著那句話,「真是的,只是腿出了問題,又不是全身癱瘓,把我看得和小孩兒一樣。」
劈劈啪啪的雨滴打在石磚地上,放眼望去,天地間蒙上了陰鬱的灰調子。
凌薇扯了個小謊,她沒有預訂計程車。如此惡劣的天氣,卻是計程車司機的春天,每輛呼嘯而過的計程車全都滿客。
凌薇伸出手臂測了測雨勢,發現雨已經轉小。從這裡走路回家大約十分鐘的路程,咬咬牙,凌薇的輪椅衝了出去。
然而衝了一半路不到,凌薇渾身就沒一處是乾的了,她索性慢起來,邊推邊回想著剛才的那通報案電話。
一個人要如何被淹死在自己的辦公室裡?如果不是天方夜譚,那會不會是黑道的報復呢?應該不會,電話裡提到的上泰大廈,是鬧市區的著名辦公大樓,治安不至於差到這種地步。
在滿是監視器的高級辦公大樓裡要殺死一個人,只有精心策劃安排一起謀殺案了。況且,辦公室裡真的有足夠淹死人的水嗎?
越往深處想,心中越有疑慮和擔心,灌進衣服裡的雨水,也沒那麼冰涼了。
報案的男人在這起謀殺案中,究竟是一個怎樣的角色?
通常的報案內容都是已經發生的事件,這個報案人卻預告了殺人事件,他既然知道了案發的時間地點以及死法,除了報案,難道就沒有其他辦法阻止了嗎?為什麼不讓被害人躲去一個安全的地方呢?
更讓凌薇不解的是,一詢問報案人的名字,他就匆匆結束了通話,難道他的名字比一條人命還重要嗎?
將這通電話歸為報假案,草率了一些,凌薇打算明天核對一遍資料再做決定。
經過一片泥濘的小水窪,一排土黃色的六層公寓就在跟前了。
凌薇的手上已滿是汙泥,她停在了一棵大槐樹下,用手背抹了抹額頭上的水珠,發現今天的公寓周遭和以往不太一樣,原本空闊的公寓前,停著好幾輛汽車,凌薇看車牌覺得有點兒眼熟。她雙臂再次使勁兒推動自己的輪椅,朝著其中一輛汽車前進。
貼著咖啡色隔熱紙的車窗內,一個大腹便便的男人懶散地斜躺著。
凌薇用指關節敲了兩下車窗,男人如被驚醒般轉過了頭。
「果然是你啊!我老遠看著像你的車。」凌薇笑道,「孟警官,你怎麼會在我家樓下?」
「這裡是妳家?」
「這間就是。」凌薇指了指一層的某扇窗戶。
孟警官略微有點兒意外,嘴上機械地說了句:「那真是巧了。」
當發現凌薇竟渾身濕透在雨中時,他立刻冒雨從車裡鑽了出來:「這麼大的雨,怎麼也不知道找個人接送妳?看妳都淋成落湯雞了!快到車上來!」
「不用勞煩你了,我到家洗個熱水澡就行了。」凌薇婉言謝絕了。
可孟警官就像沒聽見一樣,把凌薇推到了副駕駛座旁,將她強行塞進了車裡,凌薇再三推託也奈何不了五大三粗的孟警官,只得乖乖上了車。
替她關上車門後,孟警官蹲身耐心地折起輪椅來。這時,一個留著平頭的年輕人,一溜煙小跑到了他的身邊。
凌薇看見孟警官朝年輕人擺了擺手,就將輪椅丟給了那個年輕人,年輕人哭喪著臉還在說著什麼,孟警官頭也不回,自顧自地縮著脖子鑽回了車裡。
「孟警官,我的濕衣服把你車裡弄得到處是水,真是給你添麻煩了。」凌薇深表歉意。
「沒事,沒事。這車早就被那小子搞得烏煙瘴氣的了,車裡弄點兒水反倒乾淨了。」孟警官拍著被淋濕的頭髮安慰道。
「你和張警官今天到我家這邊來,是發生什麼事了嗎?」凌薇關切地問道。
「嗯。」孟警官嚴肅地點了點頭,「有人在自己家裡跳樓自殺了。」
「真可惜呀!」凌薇前傾身子,想透過擋風玻璃找找是哪戶人家。
「妳剛才說妳家是這間對嗎?」孟警官問。
「是的。」凌薇從孟警官臉上捕捉到了一種怪異的神情,但她不知道這種神情意味著什麼。
「跳樓的人,是妳的隔壁鄰居。」說完,孟警官長嘆一口氣。
凌薇並沒有立刻領悟這句話中的意思,幾秒後,當她恍然大悟的時候,才明白孟警官的表情,那是在看魔術表演的觀眾臉上,才能見到的。
她的鄰居,在一樓家中,墜樓死亡。
他的名字叫作黑
寧夜在昏黃的檯燈下奮筆疾書,手邊的稿紙比前幾天厚了不少,情節開始進入正軌,他筆下的系列偵探登場亮相了:
黃色的警戒線在龍東大樓下,圍成了一個圓形,白布覆蓋下的屍體,凸顯出短小的輪廓,被孤零零地置於人行道上。
警方的取證工作已告一段落,大部分現場鑑識人員已經撤離,而留在現場的警察卻遲遲沒有動作,他們守在屍體周圍,似乎在等待著什麼。
警戒線外,兩名年紀相仿的好事者,神采飛揚地議論著:
「這裡肯定是出了殺人案了!聽說那個死了的小女孩兒,被製作成了紅色的人形風箏吊在電線桿上,真是作孽!」
「可憐呀!救護車怎麼還不把屍體載走?」
「你不知道吧!我跟你說,這案子不簡單。」
「怎麼說,難道警察已經找到凶手了?」
「不是。」年齡稍大的那位搖搖頭,神秘地說,「警察在等一個厲害的人物。」
他這邊話音剛落,那邊一個黑衣短髮的男人匆匆鑽進警戒線,某位負責現場的警官立刻領他來到屍體邊,簡短交談幾句後,警戒線中的所有人員都退了出去,只留下那個黑衣男人和女孩兒的屍體。
男人長得眉清目秀,看起來二十出頭的年紀,再加上高䠷瘦削的身材,稱作大男孩兒可能還更貼切些。只見他面無表情地拉了拉褲管,在屍體旁蹲了下來,將白布拉開一角,露出了死者的面部。
「很漂亮的小女孩兒嘛。」
他嘟囔了一句,漫不經心拂過女孩兒的面頰,修長的手指在死者額前頓了一頓,接著將死者雙眼撐開,自己面頰朝她直直俯下──
整個世界開始如同幻燈片般旋轉,無數個閃爍的亮點出現在男人的瞳孔裡,他感覺到一陣刺痛,但又強忍著朝光亮看去:一朵枯黃色的花在混濁的水中微微搖曳,揹著包的漂亮少婦正彎腰從玄關拿出高跟鞋換上,大風中袖襬啪啪作響,龍東大樓全玻璃的外牆映出一個小小的影像……
男人猛然抬頭睜開眼睛,將死者雙眼又合上。依舊是那副淡然的表情,不過此時已多了幾分倦意,他輕輕地嘆了口氣。
這一刻,在場所有人都屏息靜氣,唯獨那兩位維持秩序的員警交換了個輕鬆的眼神,彷彿案件已經水落石出。
但男人依舊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彷彿外界一切都與自己沒有關係。他突然想起了什麼,皺了皺眉,緊接著就做了件令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事。
他將遮蓋屍體的白布掀到了死者的腰際,右手從小女孩兒的領口伸了進去。
「你在幹嘛?」離他最近的那位警官終於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尷尬地詢問道。
男人依舊我行我素,手掌向女孩更隱秘的部位探去。
在場的人們幾乎看傻了眼,在大庭廣眾之下,褻瀆死者屍體是違法行為,男人不可能不明白這點,但他卻絲毫沒有住手的意思。
「喂喂喂……還不快住手啊你!」負責現場的警官向前幾步,忍不住對著男人低吼道。
兩個正聊著天的手下,眼見情勢不對,趕緊拋開圍觀群眾去拉蹲在屍體旁的男人。男人不為所動,頑固地不願離開,手依舊在死者衣服裡摸索。
人群爆發出低沉的騷動,場面眼看就要陷入混亂。
「找到了。」男人第一次開口說話,語調透著滿足,彷彿一個孩童終於找到了他丟失已久的玩具。
兩位員警一時愣在了原地。
男人抽回右手,緩緩攤開掌心,一枚圓潤剔透、帶著死者餘熱的玉觀音吊墜出現在大家面前。
男人將翠意盎然的玉墜高高舉起,對著陽光長久地看了一眼,接著溫柔地放入女孩兒的手掌中,將她手指握拳。
當白布重新蓋好死者全身,負責現場的警官關切地問男人:「你剛才是在找這枚玉墜啊?」
「嗯。」
「找它幹什麼?」警官更加一頭霧水了。
「這是死者的心願。」男人笑了笑。
警官似懂非懂地點了點頭,又問道:「那這個案子你有什麼眉目了嗎?」
男人指了指身後高聳入雲的龍東大樓,開口道:「小女孩兒是這棟樓的住戶,墜樓時纏到了高壓電線被勒住了脖頸。至於死者墜樓的動機,我目前還沒完全弄清。」
男人說到「動機」這兩個字時,雙頰的肌肉微微鼓動了一下,似乎有些不甘心,但很快就恢復了淡漠。
「我先告辭了。」
男人的語氣分明帶著些厭惡,但那些警官卻還是用著習以為常的神情目送他揚長而去。
在旁人眼裡普通的自殺,經他這麼一說卻演變成詭異的死法,這個案件頓時披上了一件神秘的面紗。
年輕的那位圍觀群眾,捅捅身邊人,問道:「這個年輕人是誰啊,這麼跩?」
年長的驚訝不已:「你真不知道他?」
「是啊。」年輕的那位說,「他叫什麼名字?」
「他的名字叫作『黑』。」
筆尖的墨水如黑色大麗花般綻開,寧夜甩了甩流水不暢的鋼筆,不經意透過窗簾縫隙發現外面天色漸亮。
寧夜擰暗檯燈光線,熬夜寫完主角第一次登場,疲憊不堪的他蜷攏著身子縮在椅子上。儘管眼睛已經支撐不住,可寧夜並無絲毫睡意,一種淡淡的難捨之情瀰漫在面前的稿子上。
這起案件,是寧夜為筆下主角精心策劃的一場陰謀,為了完結這個系列,書中的主人公「黑」──將會「死」在這疊稿子中。
無論對作者寧夜,還是主人公「黑」來說,這樣的小說結尾同謀殺無異,最終都是要終結一條生命。
敏感的創作情緒稍有抬頭之勢,寧夜立刻拍了拍腦袋,將自己驅趕回真實的生活中。
微亮的天際稍露晨光,不知不覺中,房間變得明亮起來,已經是早上六點。
寧夜用冷水沖洗著臉,刺激刺激倦怠的神經。他泡了一杯熱氣騰騰的咖啡,在六點十五分,準時推開了女兒的房門。
「小櫻,起床要去幼稚園囉。」寧夜對被子下隆起一塊兒的方向,溫柔地喚道。
但沒有回答,孩子在賴床。
寧夜走過去,掀開被子,被窩裡是一隻絨毛玩具,沒有女兒寧小櫻的蹤影。寧夜失魂地坐在床沿,從混沌的思緒中猛然驚醒過來。
原來,這個家只剩下他一個人了。
三個月前,寧夜愛撫著女兒嫩嫩的小臉蛋,看著神似妻子的可愛女兒寧小櫻,寧夜想尋回妻子的渴望就越發無法遏制。
妳到底在哪裡呀?我和小櫻都需要妳!
寧夜溫柔地縱容女兒在床上撒了會兒嬌,最終他用麥當勞早餐把她騙了起床。
在妻子離家後的這段時間裡,每天送女兒去幼稚園成了寧夜的任務,這短短的十幾分鐘裡,可以心無旁鶩地和女兒待在一起,體會一個做父親的責任,寧夜十分珍惜。
他喜歡抱著女兒走這段路,哪怕女兒日漸增長的體重已經讓他感到有壓力,他仍然堅持。
那一天,氣溫降了幾攝氏度,下著不大不小的雨,陰冷的空氣刺激著上呼吸道。
街道上排氣管如爆竹聲的摩托車呼嘯而過,一陣寒風尾隨而至,寧小櫻緊了緊鉤住父親脖子的手臂,生怕被吹走似的。
「爸爸,以後我不想吃麥當勞了。」
「為什麼呀?小櫻不是最喜歡吃這個嗎?」寧夜往後仰了仰腦袋,和女兒鼻尖抵著鼻尖。
「我想吃媽媽做的早飯。」小櫻噘了噘嘴,聲音越來越輕。
「爸爸也想啊。」寧夜緊緊摟住女兒。
「媽媽什麼時候回來呀?」小櫻明亮的眼睛裡露出了興奮的光芒。
「媽媽一定會回來的,爸爸向妳保證!」
「真的嗎?」
「爸爸什麼時候騙過小櫻了?」
「嘻嘻,爸爸最好了!」
小櫻用剛吃完早飯油膩膩的嘴唇,重重壓在寧夜的左臉上。
前方像是有人在吵架,未散去的迷霧中傳來幾聲驚呼,金屬摩擦聲和刺耳的喇叭聲由遠及近,寧夜撥開女兒阻擋視線的頭髮,側頭看去,僅僅幾公尺外,一部失控的藍色轎車如發瘋的野牛,徑直向寧夜的方向馳來,已經完全沒有剎車的可能性了,車裡的司機一個勁兒地揮舞著伸出窗外的手。
寧夜閉上眼睛,喉嚨裡爆發出駭人的吼聲,用盡全力將懷中的女兒推了出去……
濛濛細雨逐漸轉為滂沱大雨,除了嘩啦啦的雨聲,這天早晨,整條街道的人都聽見了一聲巨響。
寧夜睜開眼睛的時候,縷縷青煙從折起的引擎蓋裡冒出來,汽車頭部一側的燈撞得粉碎,滿地碎片中一個小小的身影,在歪向一側的前輪下。
「小櫻!」寧夜瘋了一般撲過去。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我的名字叫黑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48 |
二手中文書 |
$ 236 |
推理/犯罪小說 |
$ 263 |
推理小說 |
$ 263 |
推理小說 |
$ 269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我的名字叫黑
懾人心魄的冷血殺手,漠視生命的可怕氣場。
漸露端倪的案情,剝開後竟是亂麻一團。
兩通神秘的報案電話,預告了兩起死亡案件:
一名計程車司機從一樓的窗口墜落,竟內臟破裂死亡;
一名出版社主編溺死在辦公室的魚缸裡。
然而嫌疑人卻如同火柴般,在密閉的偵查室中自燃,活活被燒死!
三件令人不思議的命案,卻意外地與一篇未完成的小說內容雷同,
隨著進一步調查,更讓人無法置信的是,
所有證據都指向了同一人──「黑」,推理小說中的虛幻人物!
「他」為了試圖改變自己在書中被殺害的命運,
正策劃著一起瘋狂的殺人計畫,
「他」要將僅有幾位看過原稿的人逐一殺害……
窺視者如同蟄伏的獵人,到底誰將會成為最後一名死者?
又究竟是誰讓書中的命案成了現實?
作者簡介:
王稼駿
以《謀殺攻略》一文獲第四屆華文盃偵探小說大獎最佳構思獎。二○○九年至二○一三年以《魔術殺人事件簿》、《篡改》(即《我的名字叫黑》)、《熱望的人》連續三屆入圍「島田莊司推理小說大賞」,成為華文推理小說代表作家。
章節試閱
引子
日出時的第一縷陽光,就像個遠方的親人,穿過厚厚的雲層,不遠萬里來到地平線另一頭的這座城市。似乎沒人會刻意去在乎它的到來,理所當然地享用著屬於大地的這份暖意。
一個男人站在窗邊,迎著陽光瞇眼眺望。一頭金燦燦的鬈髮下,整張臉像被鍍了層銅,加之其沒有任何表情的生硬面容,彷彿一尊栩栩如生的雕像。
身後仍在熟睡中的妻子,鼻腔裡發出難聽的鼾聲,沒頭沒尾地說了幾句夢話,具體內容並未聽清。
男人佝僂著身軀走到床邊,他默默地注視著妻子,生怕將她吵醒。
男人輕輕拿起床頭櫃上的鬧鐘,把原先設...
日出時的第一縷陽光,就像個遠方的親人,穿過厚厚的雲層,不遠萬里來到地平線另一頭的這座城市。似乎沒人會刻意去在乎它的到來,理所當然地享用著屬於大地的這份暖意。
一個男人站在窗邊,迎著陽光瞇眼眺望。一頭金燦燦的鬈髮下,整張臉像被鍍了層銅,加之其沒有任何表情的生硬面容,彷彿一尊栩栩如生的雕像。
身後仍在熟睡中的妻子,鼻腔裡發出難聽的鼾聲,沒頭沒尾地說了幾句夢話,具體內容並未聽清。
男人佝僂著身軀走到床邊,他默默地注視著妻子,生怕將她吵醒。
男人輕輕拿起床頭櫃上的鬧鐘,把原先設...
»看全部
目錄
《我的名字叫黑》
引子
血色風箏
他的名字叫作黑
金魚墳墓
白色記憶
交織的世界
藍色火舌中的救贖
回憶之殤
灰色離別
重回起點
弱點
尾聲
《人系列》
惶恐的人
孤獨的人
徘徊的人
微笑的人
平靜的人
如果的人
獨白的人
遺忘的人
重疊的人
自白的人
引子
血色風箏
他的名字叫作黑
金魚墳墓
白色記憶
交織的世界
藍色火舌中的救贖
回憶之殤
灰色離別
重回起點
弱點
尾聲
《人系列》
惶恐的人
孤獨的人
徘徊的人
微笑的人
平靜的人
如果的人
獨白的人
遺忘的人
重疊的人
自白的人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王稼駿
- 出版社: 月之海 出版日期:2015-02-11 ISBN/ISSN:978986583478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84頁 開數:25K(14.8*21cm)
- 類別: 中文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