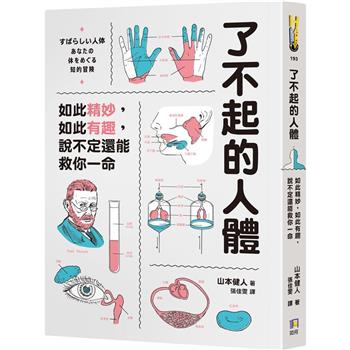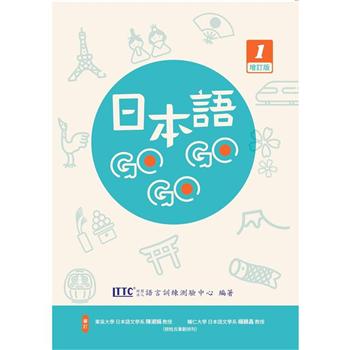一個獵鬼人的真實詭異經歷
喚醒每個鬼魂背後隱藏的故事
不僅驚悚恐怖、更引發內心最深處的感動
喚醒每個鬼魂背後隱藏的故事
不僅驚悚恐怖、更引發內心最深處的感動
每一個故事背後 都有一個值得喚醒的理由
獵鬼人的真實經歷,再次顛覆你的認知。
湘西趕屍、河北冥婚、殺人續命、招靈鏡仙…
集結了更離奇詭異的神祕事件,更恐怖震撼的靈異體驗。
鬼與人之間的交集,陰與陽的交會,
喚醒深藏於人性的真實面貌。
十四年的獵鬼人生、十四年的難解情緣,
你怎麼確定,一生所見到的,全都是人?
本書特色
完全為作者真實經歷,收錄眾多令人不敢置信的詭異事件,顛覆你的世界觀。
於網路上一發表即在3個月內達到2億次點擊,橫掃各大文學網站。
讀者皆感動落淚!不同於其他靈異小說,本書雖然主題為獵鬼,但也藉由鬼神之事宣揚人性,喚醒人心深處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