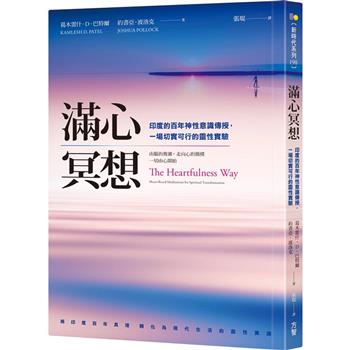「崛起的中國會往何處去?」
乾隆之後中國和世界互動的這250年,已給出答案。
顛覆國、共兩黨的中國近現代史,隆重問世。
英國《衛報》2012年度最佳歷史書,
作者文安立為美國歷史協會最高榮譽得主,漢學界深具洞見的傑出學者,
史景遷、朱嘉明、張戎、楊照等人,一致推薦。
乾隆年間,中國曾處於全球外交的中心,國力鼎盛,海內外承平。20世紀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又站上一個新的頂峰。未來的中國它會何去何從?它重返盛世之路是暢行無阻亦或是窒礙難行?有國際關係和中國近現代史背景的文安立,他認為:中國在這從帝國轉變到現代國家的250年,其中多次的內部動亂與躁動的對外關係,已給出答案……
這段歷史要從乾隆談起。大清帝國的國力在18世紀達到鼎盛,乾隆14年(1750年),大清帝國已經鞏固了全中國的統治,並把帝國的統治範圍擴張到中亞、西藏、以及東亞沿海從朝鮮到緬甸諸小國。滿洲皇帝和前人不一樣,對於帝國的對外關係訂出規範,在外交體系中,北京處於中心地位,本區域全都明確承認大清的霸主地位。
然而巔峰無以為繼。自乾隆後期,滿清的聲望便逐漸大受傷害。文安立指出:清朝的統治者已經失去交易、妥協的天分,變得愈來愈脫離清廷之外的世界。而此後的世界,就是這個以自己為中心的帝國艱難地尋求現代國家轉型的偉大歷程,直至今日仍然躁動不安。中國的近代史並非像國、共兩黨所簡化的那樣,是被動挨打的屈辱歷史,而是帝國更早地與資本主義現代性接觸的故事,也是帝國藉著和外部世界的互動而發生自身蛻變的歷史。作者指出,在尋求現代性的歷程中,如果暴力和破壞曾扮演重要角色,那麼來自內部的暴力和災難也遠比外部所施加的更為嚴重。
從乾隆到鄧小平,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就不斷地波動變化:日清戰爭、義和團起義、八國聯軍、中日戰爭、國共內戰、韓戰、冷戰等等,這些都使得帝國陷於各種外在和內在的不安之中,這不僅僅是處於羞辱和憎恨的情緒,也在於它被迫調整之前在世界外交事務中所確立的三個原則:正義、講究規則,以及中國中心論。
這250年的歷史是彼此有內在邏輯聯接的歷史:越南1978年攻打柬埔寨,鄧小平發動懲越作戰。鄧小平在北京,一定想到兩百年前乾隆朝的清越戰爭,以及乾隆皇帝未能贏取此役如何傷害到自己的歷史地位。1870年起的李鴻章,引領朝廷輸入西方技術,希望直到中國強大到足以自衛之前,能夠不陷入戰爭,而20世紀30年代的蔣介石也曾面臨此種抉擇。乃至於北京保護今日北朝鮮政權三代移交的心理,正可以和清朝作為朝鮮保護國之立場對抗日本互為對照。
有些熟諳歷史的評論家認為,亞洲、或至少是東亞,正在回到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其他國家都順服接受中國的權力象徵。這是中國追尋的目標,然而這可能達到嗎?即使250年前的情勢與今天的情勢有相似之處,文安立也不認為會是如此。他深刻地指出:「今天中國若試圖主宰及控制其鄰國,將面臨難以克服的障礙。因為今天的中國,是民族主義掛帥,而非普世主義當家。」作者強調:縱使中國試圖重新參與外部的世界,它因為發展而產生的諸多內部衝突,也使得它被拖回到與外界隔絕的泥淖中。作者還指出,當下的中國試圖重複著古代的朝貢體系或國與國單一外交關係,這在當今世界格局中顯得非常不合時宜。
250年來,中國已經變成蛻變成夾雜著帝國和現代性的混成社會。它的一部分向外看,尋找機會,一部分向內看,注意危險。本書預測了中國和外部世界的關系可能會如何發展。它會變得像融合了不同族群並控制了鄰國的美國嗎?還是會像英國或俄羅斯一樣放棄帝國的虛名?在當代國際關係與東亞歷史中,中國對我們來說最是最重要的國家,而《躁動的帝國》這本書將有助於你深入理解這個國家的近代與未來,以及它複雜的內在動力,如何與它的周邊(如北韓、日本、越南,還有台灣)發生關連。
如何讓歷史在重演時,不是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鬧劇?中國躁動不安的狀態,從哪裡來?又去向何方?本書將帶給我們無數的例證與啟發。
作者簡介:
文安立 Odd Arne Westad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國際歷史學教授,他曾以訪問學人的身分在北京大學、香港大學、劍橋大學與紐約大學等校講學。著有十餘本書,包括《決定性交會:中國內戰1946-1950》、《緩和的衰落:卡特時代下的美國-蘇維埃關係》,並以《全球冷戰》一書獲得美國歷史協會(AHA)最高榮譽班克洛夫特獎(Bancroft Prize),作者現居英國劍橋。
譯者簡介:
林添貴
國立台灣大學畢業,歷任企業高階主管及新聞媒體資深編輯人。現任逢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譯作極豐,將近七十本,包括《惡兆:中國經濟降溫之後》、《蔣經國傳》、《裕仁天皇》、《季辛吉大外交》(合譯)、《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密》、《買通白宮》、《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雅爾達:改變世界命運的八日秘會》等。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史景遷 (國際知名中國近現代史家)
朱嘉明 (學者,維也納大學教授)
楊照 (作家,知名文化評論人)
一致推薦
「2012年度最佳歷史書。」------英國《衛報》(2012.11.30)
「文安立的《躁動的帝國》敘事周詳縝密、視野宏闊明快。對於250年來中國變幻莫測的外交關係,它提供了極好的介紹。」
------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作者
「《躁動的帝國》是一本關於從18世紀帝國鼎盛期到現今的中國的外交關係的權威性著作。任何一個想要知道中國在未來世界中將扮演什麼角色的人都可以從本書得到答案。」
------斯蒂芬˙普拉特(Stephen R. Platt),《太平天國之秋》作者
「本書乃一位漢學杰出學者所著,帶來了透視複雜歷史議題的明晰與洞見。」
------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作者
「這是一本中國為何總是與其他國家暴力相向的基本導覽之書。」
------馮客(Frank Dikotter),《毛澤東的大饑荒》作者
「從1799年乾隆之死到1997年鄧小平之死,相隔198年,中國經歷了後半期的清朝,中華民國的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毛澤東、鄧小平代表的共產黨政權,卻始終沒有建立一個現代與理性的國際關係,經常貶抑別的國家,甚至對別國的犯錯幸災樂禍,缺少真正的大國風範。《躁動的帝國》解釋了原因所在:滿清後期、南京政府後期主宰中國的是一群高官和資本家,如今的中國則是和政權及與西方有特殊關係的既得利益集團,是他們阻礙中國實現政治制度的現代化。所以,『唯有擴大政治討論及參與政府,才能克服當前中國外交政策的不足。』
」-----朱嘉明,《中國改革的歧路》作者
名人推薦:史景遷 (國際知名中國近現代史家)
朱嘉明 (學者,維也納大學教授)
楊照 (作家,知名文化評論人)
一致推薦
「2012年度最佳歷史書。」------英國《衛報》(2012.11.30)
「文安立的《躁動的帝國》敘事周詳縝密、視野宏闊明快。對於250年來中國變幻莫測的外交關係,它提供了極好的介紹。」
------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作者
「《躁動的帝國》是一本關於從18世紀帝國鼎盛期到現今的中國的外交關係的權威性著作。任何一個想要知道中國在未來世界中將扮演什麼角色的人都可以從本書得到答案。」
------斯蒂芬˙普拉特(Steph...
章節試閱
一九三九年夏末,中國抗戰的外部環境產生了劇烈變化,而且不是變得更好。八月底,蘇聯和德國簽訂所謂莫洛托夫-李賓特洛甫條約(Molotov- Ribbentrop Pact),承諾雙方就歐洲事務進行合作。幾天之後,希特勒揮師攻打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於焉開始。日本起先感到相當震撼,這兩個意識型態上的敵人竟然簽約締盟、而且他們的德國盟友事先也未和日本諮商;不過德蘇條約倒是除去他們的北翼壓力,使他們可以集中力量和中國作戰。國民黨政府也失去蘇聯的軍事援助。往後二十八個月,中國必須咬緊牙關,獨力應戰日本強敵。對於中國的民族主義和國民黨政府,這是極為艱鉅的考驗。
日本在中國既能放手作戰,遂於一九三九年底從幾個戰場發動攻勢。華中方面,日軍兵分數路,打進湖南,雖然未能達成目標,攻克省會長沙,但已經大大改善其戰略地位。當年年底,日軍又進攻廣西省,於一九四○年一月攻陷省會南寧。對蔣介石而言,更糟的是,華北與國民黨淵源極深的一些地方強人,如山西的閻錫山,竟與日軍洽商停火。國際方面,戰事亦對國民黨不利。英國研判德蘇條約會使柏林和東京關係變壞,希望能和日本有某種有限度的合作,於一九四○年七月暫時關閉滇緬公路——這是重慶政府從外界取得重要物資的管道。同時,越南的法國當局已效忠當時聽命於德國的法國維琪政府,也切斷從南方進入中國的補給線。一九四○年九月底傳來另一個惡耗:日本和德國簽訂軍事同盟,組成軸心國家。根據盟約條文,其宗旨是「在大東亞圈和歐洲範圍彼此並肩合作,其主要目的是建立及維持新秩序、並促進相關民族之共同繁榮及福祉」。(註8)
日本針對中國進行類似德國對付英國的大規模轟炸,來慶祝它在國際上的新突破。中國空軍被摧毀後,日本完全掌握空中優勢,中國城市及老百姓都嘗到苦頭。日本在南京扶立傀儡政府後,它認為蔣介石終究會被迫同意停火。不料,蔣介石選擇纏鬥到底,不去管華中方面已有大規模部隊叛逃,以及有愈來愈多戰場指揮官抗命不從的現象(抗命的有些來自中共部隊的指揮官),搞得政府軍在和日軍苦戰之際,還得和他們打了幾場戰。可是,救了蔣介石的仍是日軍作戰線拉得太長。日本的全面大進攻讓自己的部隊曝於險境,而且由於後勤有問題,搶下的領地有時候又必須放棄。一九四一年春天發生在華南的上高會戰是個好例子。皇軍達成所有的戰略目標,卻因為無法透過長距離增援其前線,而在傷亡慘重下被迫後撤。
在蘇聯實質上已退出亞洲戰事之下,蔣介石必須積極尋覓新盟友。他從德國在歐洲如秋風掃落葉、頻頻告捷時就曉得,唯一務實的希望是美國,因而他竭盡全力遊說華府提供援助給中國。到了一九四○年秋天,美國人終於開始聽他說話;到了十一月,蔣介石得到第一筆美國的借款。一九四一年春天,國民黨在華南、華中陷入最激烈作戰時,羅斯福政府把決定「租借法案」(Lend-Lease)亦適用於中國——英國在最黯淡的時候,透過「租借法案」得到重大的援助。美國志願人員開始駕駛美方交運給中國的新軍機。雖然蔣介石曉得美國還不預備派出部隊參加在中國的戰爭,可是美國對東京愈來愈嚴格的禁運措施,使他相信羅斯福已經認為日本日益威脅到美國在太平洋的地位。當日本領導人和蘇聯於一九四一年四月簽訂中立條約時,蔣介石判斷日軍將會南進,企圖攻佔東南亞。他預測日本將會和英、美發生戰爭,而且日本是「自取滅亡」。中國只需要再忍一段時候,「太平洋局勢將會變化」。(註9)
一九三七年之後,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以救亡圖存、民族主義的理念動員全民抗戰。以國民黨當時超高難度的勝算機會來說,它表現得可圈可點。最重要的是,它避免軍事崩潰——以戰爭爆發後頭幾個月的情勢看,它的確危如疊卵。這一次和中國自一八四○年以來所打過的國際戰爭都不同,政府軍沒有在一開戰就士氣崩潰。反而在許多地方,面對技術、訓練高明多倍的敵軍,中國部隊不畏犧牲、堅挺奮戰。
德國在一九四一年六月進攻蘇聯,害中國領導人擔心了好幾個星期。他們試圖研判:歐洲戰事擴大,是否也代表亞洲戰事會擴大?日本人很快就認定德國不會照其盤算的時間之內攻克他的新敵人,所以並不想和蘇聯交戰。中國方面,希特勒攻打蘇聯最主要的結果是,中國政府與共產黨重新結盟,現在中共奉莫斯科指示要加入反抗侵略者及其盟國的全面戰爭。即使蔣介石從來沒有能夠讓中共照他的指示作戰,現在至少中共在非淪陷區已不是頭號搗亂者。但是他也必須醒悟,蘇聯已為自己的生存陷入苦戰,不可能在軍事上援助中國。
東京方面,日本領導人對中國抗戰的能力愈來愈有挫折感。到了初秋時,力主進攻美國和英國的軍人在罕見的政策辯論中佔了上風,日本領導人亦認為西方企圖扼殺日本。有一派人士主張,征服東南亞,既可迫使中國投降,又可取得需要的資源打更大規模的戰爭。陸軍一九四一年底未能在中國獲得重大戰果,使得主張擴大戰爭才能勝利並進一步維護榮譽的論述更加強烈。私底下,許多日本軍官開始議論「中國泥淖」。動用海軍在亞洲擊敗西方列強,才能消除掉陸軍在中國戰場迄乏戰果的罵名,讓大家看到日本是帶給亞洲其他民族現代化的大國。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清晨蔣介石被副官叫醒時,他一點兒也不驚訝耳中所聽到的新聞。中國領導圈裡,蔣委員長比任何人都更相信日本人遲早會南進。聽到珍珠港遭日軍全面攻擊的報告後,蔣介石發信給羅斯福說:「針對我們共同的戰爭,我們將全力以赴與貴國並肩作戰,直到太平洋及全世界不再受暴力及背信忘義之苦。」(註10)即使日軍快速席捲東南亞,也沒讓委員長動搖,只不過新加坡在十二月十五日就迅速投降,令他相當震驚。蔣介石本來以為英國人會更堅決作戰。三分之二的日本陸軍仍被牽制在中國戰場,蔣介石有理由自豪他能堅守戰場,不讓日本在東亞建立新秩序。
蔣介石最大的憂慮是,日本南進攻勢會切斷中國透過緬甸取得補給供應的生命線。他無法信任英國人的作戰能力。一九四二年初蔣介石表示願意調遣國軍幾個師的兵力到緬北,英國駐印軍總司令魏維爾元帥(Archibald Wavell)遲疑不決時,委員長對他發火:「你們英國人根本不曉得怎麼跟日本人作戰。打日本人,不是像撲滅殖民地叛變、不是像殖民戰爭。日本是嚴重的大敵……我們中國人跟日本人打了這麼多年,我們曉得怎麼打。這種事,你們英國人不行、幹不來。你們應該向中國人學習如何抗日。」(註11)蔣委員長和這位獨眼龍英軍元帥會面時,他一定感想到從他青年起迄今的國勢變化:中國已不再是被鄙視、被摒棄在國際體系之外的國家,英國也不再是高高在上、居於世界頂端的大國。即使英軍在一九四二年五月退入印度,使剛到緬北的國軍陷入進退維谷困境、棄守滇緬公路,蔣介石並沒有頹喪。他曉得國軍入緬作戰,就足以表徵中國已是大國,讓他在唯一一個能夠支持中國的軍事大國(美國)的面前說話有份量。
日軍進襲珍珠港之後,中、美同盟快速發展。即使滇緬路封閉,盟軍飛機還是載著美國物資補給、軍事裝備及顧問人員「飛越駝峰」,跨越危險的喜瑪拉雅山,從印度北部進入中國。沒有美國支持,國民黨政府能否撐過最後三年的抗日戰爭是有極大的疑問。可是,蔣介石仍有理由哀嘆盟國的對華戰略。美國提供給盟國的援助當中,國民黨得到的部分直到一九四五年,平均只佔百分之一左右。原因不只在於運輸困難。盟國也決定了歐洲第一的戰略。他們的主要資源將先用於對付德國的戰爭,唯有在歐洲戰場戰勝後才會用來對付日本。[…]
中國從和美國結盟得到的最大好處就是國際地位大幅升高。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同盟國在開羅舉行高峰會議,蔣雖無從參加有關歐洲和蘇聯問題的討論,卻已和美國總統、英國首相平起平坐。他也得到美國保證在戰後將繼續援助中國,中國可與世界最大國永久結盟。根據美國國務院的官方紀錄:「羅斯福總統提議,戰後,中國和美國應制訂某種協議,一旦遭遇外國侵略,彼此應相互援助;美國應在太平洋各地基地維持適度兵力,以便可以有效承擔防止侵略的責任。」(註13)因為需要中國協助贏得太平洋戰爭,羅斯福給予蔣介石中國躍居四強的地位,對於佔領日本,以及朝鮮和東南亞的未來,有著特別的影響力。遠在開羅會議召開之前的一九四三年一月,美國和英國已經放棄他們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國民黨驕傲地宣稱他們已恢復中國的地位:「我們中華民族經歷五十年的浴血革命和五年半的抗戰犧牲,終於化百年的不平等條約屈辱史,成為終結不平等條約的光榮紀錄。」(註14)
***
任何社會承受大規模戰爭的壓力,一定會付出沈痛代價,而且不僅當時吃苦,往後多年也會隱隱作痛,中國也不例外。日軍所到之處,中國老百姓無不遭殃——被戰爭暴行傷害、陷於飢饉或因外敵控制而受到欺凌。但是,防守的這一方(國民黨部隊)所到之處,百姓也遭殃。國民黨士兵在戰時死於疫疾和飢饉的人數,似乎還多過在戰場陣亡的人數。國民黨部隊一旦補給斷缺,他們就沒收農民已經很稀少的物品和蔬果。戰爭愈是拖下去,中國愈來愈多農村才沒心去管是誰當家控制,只關心他們如何才能避開殺戮和飢餓。在許多地方,日本人只被當做是許多外來勢力之一,人民對中國士兵的行為怨恨之心有時候比怨恨日本人更加深重。
從經濟面講,抗戰給中國帶來災厄。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建設有相當大多數遭到毀滅:通訊、工業、水利等等。一般人常說,仰賴基本農業生產的地區在戰時的損失,還小於有複雜先進經濟的地區,但是二十世紀中葉的中國則不然。抗日戰爭發生在一個世紀來農村凋敝的最高點時刻,農民生存的空間已經十分狹窄。在中國農業經濟中一向扮演關鍵角色的貿易受到阻滯,在某些地區甚至停止。肥料和水,很難取得。河南省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經歷一場大飢荒,乾旱肆虐和軍方徵購合起來造成兩、三百萬人餓死,另有三百萬人流離失所。農民已經忍飢挨餓,中國軍隊還徵收穀糧、徵集役力。美國記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形容它:
路有餓死殍。一個年紀不到十七歲的女孩,瘦小、漂亮,躺在潮濕的地上,嘴唇死白;她雙眼睜得大大的,雨水落在她身上。人們嚼樹根果腹;小販兜售樹葉、一束一塊錢。一隻狗在泥堆裡挖出一具人屍。像行屍走肉的男子從死寂的水塘撈水上的綠色漂浮物當食物。(註15)
戰爭使得六千萬至九千萬中國人成為難民。在淪陷區及國民黨區,都有人奔向城市求生存,製造出新的城市環境。犯罪和壓榨盛行,難民和城市居民的生活都陷入混亂。(註16)即使想和當局合作的人也被他們所見到的國家之不合理要求、未來之不確定性,澆熄了熱情。今天所做的抉擇,明天可能變得十分荒謬,上午在社會還被稱讚的行為,下午可能招致死罪。在腫脹、嚇壞了的城市裡,戰時面對的是在存亡之間掙扎、或至少是在擁有資本財產或鬧窮挨餓之間依違,不是要和日本合作或對抗。痛恨日本人、又覺得遭國民黨政府遺棄,大部分城市裡的中國人,不分貧富,對戰爭不再有所寄望、憂鬱沮喪。[…]
中國可謂「成也抗戰、敗也抗戰」。(註17)一方面,它促進了集權中央、講求效率和在二十世紀末期(抗戰早已結束、而且換上中共當權主政)實現現代國家的理想。另一方面,它給中國許多地方造成幾近無限的破壞,以遺棄和殘暴的方式影響到人民的生活。對於經歷過抗戰的人士而言,戰爭毫無疑問指的是物質破壞和人命犧牲,而非民族復興和國家現代化。它把中國的苦難帶到新的境界,在中國人眼裡,也使它成為世界各國責難、遺棄的國家。
***
中國方面,中國共產黨成為抗戰最大的受惠者之一。日本的威脅幫助共產黨躲過國民黨的追剿。抗戰使得中共得以在其西北新根據地和敵後地區持續發展。抗戰開始時,中共規模很小,可是到了一九四五年,它的勢力已經不容小覷,具有一百二十萬黨員、九十萬男女士兵。比起數字擴大更重要的是,中共透過一套集中決策制度而有能力與社會各界互動。抗戰使得毛澤東和擁立他領導的一派人同時達成兩個非常不同的目標:讓所有的黨員遵從秘密的、以毛澤東為首的內圈組織,但對外又呈現出溫和、合作的形象。這個大轉變有助於中共從抗戰得利,並於戰後取得政治上的勝利。
中共已經一再主張抗日統一戰線,但是抗戰真的爆發了,它究竟要怎麼做卻又不清楚。共產國際希望中共能在軍事上對日本人施加壓力,但是不論史達林或蔣介石怎麼說,毛澤東就是來個相應不理,不肯對敵人發動大規模作戰。他反過來強調游擊戰術——也就是在敵後秘密行動,藉機坐大、發展黨組織的力量。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中共的作戰主要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地盤,或是在中共有政治運作的敵後地區,針對日軍對百姓的暴行進行報復。中共殺死的中國人(不論是國民黨、通敵漢奸或只是擋路的地方勢力)遠比日本人殺的還多。但是毛澤東需要和莫斯科維持良好關係,因此在一九四○年底發動一場「百團大戰」。這不僅是回應史達林一再要求要有行動,也是回應中共黨內頻頻求戰的聲音。百團大戰是針對華北日軍的一系列攻勢,但是就中共而言可謂慘敗。中共傷亡的士兵是日軍的四倍。戰役之後,日軍又對當地人民展開瘋狂報復。
到了一九四一年,毛澤東的部隊和國民黨已經等於在打內戰。最激烈的衝突發生在安徽省。蔣介石決心在此要制止中共的擴張,迫使中共接受他的領導(譯按:即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事變」或「新四軍事件」)。但是,政府軍的勝利不夠堅固到足以嚇阻中共,於是又把部隊調離對日作戰的戰場。抗戰期間從頭到尾,毛澤東口頭堅守共產國際政策,呼籲堅持抗日統一戰線、組織聯合政府,可是私底下卻集中力量擴大中共勢力。共產國際頭子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iov)(譯按:保加利亞共產黨人,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三年擔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告訴毛澤東說:他認為中共「降低對中國的外來佔領者之鬥爭的政策,以及明顯悖離了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犯了「政治錯誤」;但是毛澤東堅持他的內部重於外部的政策,給他帶來極大收穫。(註18)
毛澤東一方面不理會對國民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一方面卻在中共控制的區域內祭出統一戰線。中共沒有像以前那樣槍斃地主和商人、分田和沒收財產,現在宣布他們所謂的溫和政策,實行減低田租、集體耕作、物價凍漲和貸款等辦法。中共亮出全民抗戰的旗幟,提出面面俱到的政策:農民(保證不讓他們餓肚子)、地主(可以收到地租、又有穩定物價)、店東(得到可預料的稅負和財產保障)、工(得到最低工資)。中共現在擱下馬克思和列寧,開始談「合理稅負」。山東西部邊區產鹽的地方人士利用戰時國家機關的力量衰退,避繳討厭的稅,因此相當賺錢。中共在當地保證保衛地方福祉和降低稅負,大獲人心。在中國其他地區,中共吸收黨員和士兵,保證維持中共已在當地建立的穩定、也要嚴懲通敵的漢奸。(註19)換句話說,抗戰給了中共近乎完美的機會擴大勢力。
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對外擴張黨的勢力之同時,對內亦發動黨內鬥爭,鬥倒舊敵,爭取到一九三七年以後入黨者全心全力的效忠。所謂的「整風」運動批判、逮捕,甚至槍斃那些不肯接受黨的新戰術、不依毛澤東所了解的中共歷史任務觀念進行文藝工作的人。毛澤東這一派人馬不再高舉黨所據以誕生之國際主義者的馬克思主義,引進此一曾被強調為黨在中國歷經百年羞辱之後,做為中國人民救贖者之論述。中共擱下共產主義的唯物論,開始宣傳靠意志力可以達成解放。毛澤東告訴他的黨內聽眾,中國既不弱、也不窮。中國是強大的,因為中共帶來革命精神,使得中國脫離桎梏。
一九三九年夏末,中國抗戰的外部環境產生了劇烈變化,而且不是變得更好。八月底,蘇聯和德國簽訂所謂莫洛托夫-李賓特洛甫條約(Molotov- Ribbentrop Pact),承諾雙方就歐洲事務進行合作。幾天之後,希特勒揮師攻打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於焉開始。日本起先感到相當震撼,這兩個意識型態上的敵人竟然簽約締盟、而且他們的德國盟友事先也未和日本諮商;不過德蘇條約倒是除去他們的北翼壓力,使他們可以集中力量和中國作戰。國民黨政府也失去蘇聯的軍事援助。往後二十八個月,中國必須咬緊牙關,獨力應戰日本強敵。對於中國的民族主義和...
作者序
二十一世紀開始之際,中國正愈加朝全球事務的中心移動。身為全球人口最多、面積也名列前茅的國家,即使它在歷史上也曾有罕見地衰弱、分裂或貧窮的時期,但中國仍一向受到各方矚目。今天,許多中國人和外國人相信中國已走出相當無力的時期,集聚了不尋常的國際力量。經常有人預測,二十年之內它將超越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國社會科學院預估,屆時中國將是世界科技重鎮,它將消除其十五億多人口的貧窮,並提升他們的壽命期至八十歲。(註1)同時,但也有人,尤其是鄰近國家,深怕中國將加強軍事力量以逼迫他人服從它的意志。
然而,即使中國經濟在過去三十年飛升,從歷史上可顯示出,中國要通向未來可能不會像若干專家認為的那麼平順。共產黨統治時期,以及中國更深層的歷史(在帝國與專制統治者之下數百年的傑出發展)都留下了極深的歷史裂隙,未來的領導人必須小心謹慎才能達成他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目標。在今天狂熱追求進步的表面底下,有些暗流和斷層可能把中國帶離非常不同於我們目前追求的方向。這些其他道路對中國及世界而言或許是正面,或許是負面,誰也不敢斷言。但是鑒於中國在國際事務上已經取得的重要地位,我們姑且不談不利的那一面。
這些因素有些要歸結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些則與它無關。中國和許多鄰國的關係、它和美國的關係,乃至於中國人民的信念和世界觀、中國組織其國家和社會事務的方式,以及它的經濟和資源需求,在在都攸關我們了解它的軌跡。但是,中國和世界的邊界線本身並非一直都清晰可見。在內與外之間的交會處,存在著一些中國心理地圖上最為重要的部分:即國界、僑居外國人口、種族、貿易和思想交流等。談到大國時,當你湊近一瞧,其邊界線往往模糊不清。當內與外的分界線淡化,剩下的中國就是跨國的、甚至全球性質的中國。
如果說邊境的分界線是模糊的,那么時間的劃分恐怕更加模糊。往日鮮明地鐫刻在中國的精神地圖上,決定了它今天絕大多數的作法。因此歷史對中國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其影響遠比我所知的其他文明來得更直接。今天,這些東西很少是機械式的——中國人未必會拿過去的事件和目前的事件做鮮明的對比。例如,在當今世代,很少有中國人在省思目前國際局勢時,會去想到戰國時期(西元前四七五年至二二一年)的事件。但是他們有關正義、行為準則、看待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這一類觀念,卻是在好幾百年前就已形成。雖然我們不可能依據這個過去預測中國的未來,但我們卻必須了解它們,以在看待將來時才至少有些指引。[…]在思考中國外交政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時,千萬記住正義、規則和中心意識這三個重要概念。
***
中國現代外交關係史始於清朝(一六四四年至一九一二年)。清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朝代。到了一七五○年,它已粉碎在其北方邊境所有小國家的政治與軍事獨立,把它們併入日益擴大的中國版圖。它根據中國的條件以及中國的優越感,規範它和其他鄰國(北起俄羅斯帝國、南迄東南亞以及喜馬拉雅山區各王國)的關係。到了十八世紀中葉,大清帝國已在東亞建立一個唯我獨尊的世界。
大清帝國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要上溯到十七世紀初。當時關外一批豪強開始佔領屬於明朝(自西元一三六八年起開始統治中國)的部分領土。侵略者宣示的目標是征服全國,恢復在失德的明朝皇帝統治下已然淪喪的儒家禮教。征服者大軍的領導人來自一個通古斯族部落,過去名稱女真,現在自稱滿洲。他們勢力往南擴張,許多蒙古人、朝鮮人和漢人,以及東北的小部落紛紛前來歸順。一六三六年,滿洲人建國,國號清。一六四四年,清軍攻克中國首都北京,開始綏靖全國。明朝最後一個王族一六六二年兵敗,在緬甸被擒、處決。
清朝公布的目標是要依據儒家經書所訂的古代智慧治理。他們宣稱明朝失敗是因為統治者鬆懈、軟弱,一連好幾代失去方向感。現在,滿洲人,雖是外族入主中原,卻是要重振中國的偉大。但是和高唱傳統與價值的許多政治領導人一樣,清朝皇帝的話隱瞞了一個事實:他們想依自身形象重新打造中國,使它成為偉大的多文化國家。他們的組織相當現代,不同於原先存在的東西,強調協調運用經濟、技術和意識型態資源。他們依靠軍隊打天下,其軍隊與鄂圖曼帝國、俄羅斯帝國或甚至奧匈帝國的部隊的相似之處,還大過與明朝部隊的相似之處。他們依賴快速移動的騎兵、火器和大砲,以及綿密的後勤作業。他們的意圖是建立一個超級大國,讓所有不同族裔和信仰背景的人都找到順服聽命的位置。(註6)
儘管意識型態和軍事力量強大,若非康熙和乾隆兩位聖明天子長期在位,清朝或許也不會那麼成功。康熙一六六一年登基,一七二二年才駕崩。他的孫子乾隆則由一七三六年至一七九六年,足足在位六十年。(註7)祖孫兩人統治中國超過一百二十年,把大清的統治鞏固到活在一六五○年代的人所無法想像的地步。他們也把個人特質貫注進他們創造的帝國中。康熙機智、活潑,對外在世界充滿好奇心,但強力保護他的權力以及滿人的權力。乾隆則有教養、勤奮,但是沒有他祖父聰明,因此在民政及政治事務的理論上相較有些空疏。但是兩人都了解他們統治的人民以及周遭世界,熟諳駕馭一個複雜的區域所需要的外交和軍事工具。
到了乾隆十四年(一七五○年),大清帝國已經鞏固了全中國的統治,並把帝國政府擴張到中亞、西藏和蒙古。滿洲皇帝和前人不一樣,對於帝國的對外關係訂出規範,使本區域從朝鮮到緬甸諸小國全都明確承認中國和大清的霸主地位。國內方面,帝國承平,經濟相當擴張,農業尤其發達(同時中國也有相當大的製造業,其中又以瓷器和絲織品出口最有名)。水利和交通都有良好的開發,市場開始興起,所交易的商品涵蓋了從土地到工具都有。它是一個愈來愈專業化的社會,個人和家族之間的書面契約和協議扮演重要的角色。(註8)
國家的影響在各行各業都可感受到,有點像大革命之前的法國絕對王權君主,大清希望控制臣民每一方面的生活、以及規範那些他們未能直接控制的人。和歐洲君王一樣,大清在許多方面也有敗績,但是他們建立的意識型態模式倒是由國家堅守直到二十世紀清室傾覆為止。國家的無所不在和帝國擴張大夢有密切關係。乾隆相信清朝的統治應該澤被四方,文化先進到足以理解中國原則的人都應該運用它們。這種普世主義超越其他一切,在十八世紀末期驅動帝國在其邊疆進行耗費不貲的軍事遠征。因為用兵邊疆的舉措,於是最終在十九世紀初造成國庫空虛。
歷史學家直到今天仍說大清中國褊狹、內觀。但是當時在區域內和康熙、乾隆對抗的人,絕對不會說他們是內觀。清朝持續對外擴張,除了康熙在一六八三年征服台灣之外,他們重心擺在陸上邊境。到了一七五○年,乾隆的外交事務大體上以三個區域為主:中亞方面,重點是擴張;亞洲海岸,重點是貿易和朝貢;俄羅斯,重點是外交。所有這些陣線的政策都經協調到讓大清皇帝有時間全力統治中國,同時消滅邊界上那些北京認為有能力威脅其統治的敵人。清朝本身以武力奪取中國,它要防止任何新的競爭者依樣畫葫蘆。[…]
一七五○年的清朝在亞洲的地位已經登峰造極。乾隆皇帝喜歡誇耀帝國不畏外敵入侵,農業供應亦已自給自足。它和亞洲大陸國家互動的形式由北京決定,雖然皇廷不能越俎代庖,替其他國家決定政策,但透過外交、教育或文化,它經常對他們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大清首都被公認是東亞區域的中心,吸引各方人士前來,而關於思想、品味和流行的重要判斷則由北京散發出去。甚且,它的菁英堅信大清政治制度是治理帝國唯一的合理方式,可做為亞洲、乃至全世國各國的楷模。
***
北京西北郊的圓明園完成於一七五○年,是清廷國力鼎盛、威震寰宇的偉大象徵。乾隆御批興建這座林園,以展示他的美學知識和帝國威力。圓明園面積是北京市區皇室居住的紫禁城的五倍大,有意攬天下之勝於一園,有如十八世紀的世界博覽會。圓明園內亭台樓閣林立,有來自不同朝代的中式建物,以及來自中國內地、朝鮮和東南亞的建築和園景。但是最讓中國遊客驚艷的是在園後方的建築物,它由來自米蘭的畫家、建築師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設計成義大利巴洛克風格。主建物取名「晏海堂」,俯瞰中央噴泉,皇帝蒐藏的歐洲藝術品,包括他最喜愛的法國鐘,都放置在這裡。
直到一八六○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軍侵入北京,大肆掠奪與破壞之前,圓明園象徵大清的驕矜自負和其首都的中心地位。一百二十年之後,我以學生身份首次來到這個中國首都時,圓明園舊址除了入口處散布一些反帝國主義招牌(「打倒帝國主義及其走狗!」) ,以及幾塊窮農民的菜園之外,空空盪盪。對我而言,這是下午散步的好地方,也是避開眾多閒人會女朋友的幽靜地點。但是有些本地人不肯進去,因為裡頭有太多寧可忘掉的歷史幽魂。
寫作本書的念頭起於二○○六年有一天我在圓明園舊址散步之時。我在圓明園舊址對面的北京大學開課,講授中國與世界關係。一動筆之後,這本書花了相當長時間才完成(該讀的材料浩瀚如海,而且更慘的是,由於二○○○年代各方對中國的興趣大增,似乎每六個月材料就倍增。推動我堅持不懈的原因是:我需要提供給我的學生及其他讀者關於中國對外關係方面的修正主義的知識)不僅要談到衝突與民族主義,也要強調文化轉變及中西合璧的認同;要同等對待傳教士和外交官、生意人和革命家、工人和老闆。傳統有關中國國際事務的歷史,直到近幾年,大多集中在各種形式的國與國之關係。雖然討論政府如何發展外交政策並沒有不好,但是這樣的敘事不能讓我們了解國際與國內之間關係如何演進、或是不同群組的人如何互動的全貌。它們太狹隘地集中在國家的中心功能(行政管理、交通、戰爭)因此建立的建構與解構的印象,並不契合大多數人如何看待他們本身和國際或外國互動的情況。[…]
***
本書的中心是中國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蛻變的故事。現在已是中國人把生活和實踐轉化為全球現代化參與者的時候了。擁抱新事物的中國人(若有機會擁抱的話)人數一向遠超過不擁抱新事物的人。中國人出國旅行、唸書和定居,以便了解向他們敞開大門的新世界,從中汲取益處。從時間和重要性來講,他們和國際接觸的經驗非常像歐洲農民(例如我的祖父母們)進入資本主義市場的新世界。市場很嚴酷,同時又很興奮。它含有機會與危險、吸引力與驚恐,愈來愈讓地理上、心理上都遠離它的人也逃脫不了和它的關係。中國過去兩百五十年的國際史,就是它與資本主義現代化接觸的故事,也是中國人如何打造現代化、同時如何受現代化影響的故事。
破壞和暴力也在這個故事扮演重要角色。圓明園的歷史顯示,西方軍隊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侵入中國,所到之處造成極大破壞。(註12)但是就破壞和暴力而言,真正的災難起自二十世紀中葉,日本人進攻中國掀起大戰,特別就中國農民來講,恐怖一直持續到一九七○年代中期。
就許多中國人而言,戰爭和毛澤東主義結合成為完美風暴(perfect storm)。戰爭證實外在世界仇恨中國,毛澤東的共產主義證實除了資本主義和外國影響,還有別的方法可以追求現代化。沒有前者,後者不會如此旺盛。但實際狀況是,中國在血腥的一九四○年代把路線定向現代史上最大的悲劇:毛澤東時代的大屠殺、恐怖和自招羞辱,在這段期間兩千萬人喪生,還有不計其數的更多人一生也毀了。這些大多是中國人對其他中國人犯下的罪行,其傷天害理的地步使得中國絕多數人依然寧可避而不談。這些犯罪的中國人受到共產黨想抄捷徑搞現代化的想法所牽引,而這種想法也在二十世紀的其他地方造成重大破壞。
當毛澤東主義在一九七○年代隨著毛澤東一起死亡之後,中國開始蜿蜒曲折走回國際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道路,而這是過去一個世代其領導人繞道不走的路。中國有些歷史學家說,因為有毛派分子在過去數十年的大破壞,今天建設新中國的工作變得容易多了:毛澤東殺死了舊中國,卻在無意間留下一塊空白,得以寫下市場發展的律令。我可不敢如此肯定。一九七○年代的中國有許多不同的方向可以走——從柬埔寨式的種族屠殺,到類似台灣的民主發展。市場發展的可能性已經在那裡,不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大破壞所造就,而是早在共產黨企圖摧毀它們之前,中國早已有很長一段時候實驗市場整合。這些根源是本書故事的主幹,不只因為它們對現狀十分重要,也因為它們影響中國在十九、二十世紀的進程。
***
過去影響現在。今天的中國被其現代蛻變、及內外壓力造成的轉變所影響。因此歷史是了解今天中國的外交關係的最根本的基礎。在我們這個世代,有些人用中國多苦多難的過去當做它專制威權或偶爾在國際上販賣力量的藉口。其實不應該如此。中國血腥的二十世紀,其實中國人對自身造成的傷害遠大過列強造成的傷害、而且傷害還會持續長久一段時候。中國可以接下這段不光彩的過去,往兩個不同的方向擇一前進。一個選項是,它可以在國力大盛下,行徑愈來愈有侵略性,就像中國國勢衰弱時遭到列強侵凌,現在終於可以一報還一報。但是如此外顯的敵意很有可能是內部持續衰弱的跡象,一個和過去掙扎、卻走不出歷史困境的中國,因此隱含著不穩定。另一個選項是,中國依據它本身的價值和過去的教訓,與別的國家尋求合作。這樣的中國很可能是國內穩定,因為它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和平的政治改革,因此得到更大的正當性,有個更活潑的政府。唯有時間可以告訴我們中國將朝哪個方向走,但不論它往哪裡走,走過之處,歷史將留下痕跡。
有些中國人喜歡說中國的歷史治亂相乘:幾千年來,中國從光輝燦爛走到衰頹,然後又復興。他們相信今天我們正處於復興階段的開端:中國將在未來愈來愈成為中心、愈來愈強大。他們非常引以為傲,現在中國在許多領域都蒸蒸日上,走向世界強權大國。不論我們要從哪個角度看歷史,從十八世紀以來,即本書故事開始以來,已有一個根本改變:今天沒有人預期過去會回來,至少不會以從前同樣形式回來。現代的環境是望向未來大過回首過去;中國人也一樣如此,即使那些相信歷史發展循環論的人也不例外。中國與世界的未來關係或許形式上似乎恢復過去的樣貌,其實它的內容將不容置疑是全新的。
二十一世紀開始之際,中國正愈加朝全球事務的中心移動。身為全球人口最多、面積也名列前茅的國家,即使它在歷史上也曾有罕見地衰弱、分裂或貧窮的時期,但中國仍一向受到各方矚目。今天,許多中國人和外國人相信中國已走出相當無力的時期,集聚了不尋常的國際力量。經常有人預測,二十年之內它將超越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國社會科學院預估,屆時中國將是世界科技重鎮,它將消除其十五億多人口的貧窮,並提升他們的壽命期至八十歲。(註1)同時,但也有人,尤其是鄰近國家,深怕中國將加強軍事力量以逼迫他人服從它的意志。...
目錄
緒論 帝國
第一章 蛻變
第二章 帝國主義的崛起
第三章 中國與日本
第四章 走向共和
第五章 異邦人
第六章 出走海外
第七章 對外與對內的戰爭
第八章 共產主義
第九章 中國孑然獨立
第十章 中國與美國
第十一章 中國與亞洲
結論 現代性
緒論 帝國
第一章 蛻變
第二章 帝國主義的崛起
第三章 中國與日本
第四章 走向共和
第五章 異邦人
第六章 出走海外
第七章 對外與對內的戰爭
第八章 共產主義
第九章 中國孑然獨立
第十章 中國與美國
第十一章 中國與亞洲
結論 現代性